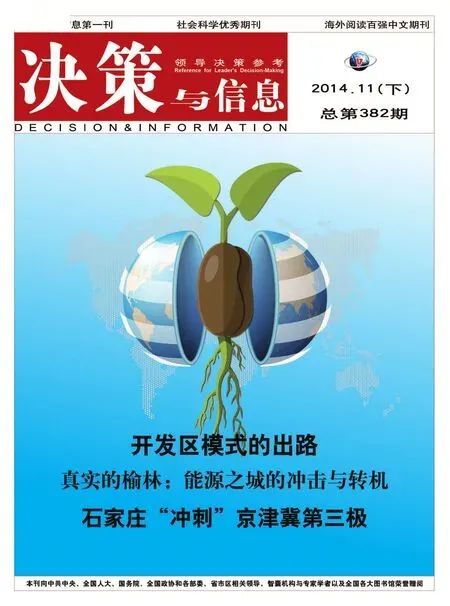論我國環境犯罪之立法完善
羅殿甲
廣東工業大學 廣東廣州 510006
論我國環境犯罪之立法完善
羅殿甲
廣東工業大學 廣東廣州 510006
當前我國環境刑法體系無法適應打擊日益嚴重的環境犯罪以保護環境的迫切需要,立法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打擊環境犯罪的理念之后,罪名體系設計也不合理。對此有必要采取相應的完善措施。應首先從根本上入手,使得環境犯罪的刑法規制具有整體性。其次,完善刑法中具體的與環境犯罪的相關刑法條文內容。
環境犯罪;立法不足;完善措施
一、我國當前環境刑法現狀的不足
(一)人類中心主義使環境法益本身缺乏保護
在人類中心主義下,刑法保護環境是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不受到損害為條件的。如果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沒有受到直接的侵害,或者該種侵害是在人類社會可以忍受的程度之內,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行為是不會受到刑法處罰的。因此,在以“人類中心主義”作為指導的環境刑法中,污染必須達到給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財產造成損害的地步,才能作為犯罪處理。生態環境本身的權利和價值則沒有得到體現。這樣的立法理念使得使環境法益得不到足夠的重視與保護。
(二)刑法罪名體系存在問題
其一,罪名規制范圍較窄。作為保障法,環境刑法的罪名設置應當與環境管理法所包含的環境要素對應一致。中國《環境保護法》第2條從廣義上規定了環境的概念,即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過的自然因素的總體,不僅包括大氣、水、海洋、草原、野生生物等自然環境,也包括人文遺跡、風景名勝區等人文環境,甚至還包括了城市、鄉村等社會環境在內。然而,環境刑法卻采用了最狹義的環境概念,不包括人文環境和社會環境。即使是自然環境,也未能涵蓋諸如草原、濕地、自然保護區等自然環境要素包括在內。這種過窄的罪名設置,也導致環境刑事治理與行政治理之間相互脫節。
其二,環境犯罪罪名設置分散化。刑法總則沒有對環境保護做出任何指導性規定。此外,除了刑法分則第六章第六節設置的環境犯罪罪名以外,還有一些相關罪名分散規定于刑法分則其他章節中,使得環境犯罪罪名之間的關系松散化,從而違背了刑法設專節規定環境犯罪的初衷。如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非法制造、買賣、運輸、儲存危險物質罪”,第三章第二節走私罪中的“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走私廢物罪”,第九章瀆職罪中的“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環境監管失職罪”、“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罪”、“動植物檢疫徇私舞弊罪”、“動植物檢疫失職罪”等等。這種分散的立法體例不僅影響了整部刑法體例的周延,而且嚴重淡化了環境犯罪的客體特征,對環境犯罪的集中治理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1
二、我國環境刑法的整體完善措施
(一)完善刑法總則
以《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為例,完善總則第二條對刑法任務的規定,將保護環境作為刑法的任務之一。筆者建議將刑法第二條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護環境,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通過此舉,可將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理念逐步轉為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理念使得“環境”明確成為刑法保護的法益,提高環境刑法在刑法中的地位,并有效指導刑法分則完善各個具體的環境犯罪條文規定。
(二)將環境犯罪獨立成章并增加新罪名
鑒于中國環境犯罪罪名分散化的弊端,筆者認為,應將刑法分則第六章第六節規定的環境犯罪罪名從該章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立一章,并將分散在刑法各章節中有關環境犯罪的規定納入其中,章名可稱為“侵害環境罪”,位序排在現行刑法分則第五章“侵犯財產罪”之后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之前。這樣就能夠體現環境犯罪客體的獨立性以及環境犯罪特定的社會危害性。
在新增的“侵害環境罪”一章中還應增加新的罪名。目前急需增設以下五個罪名:破壞草原罪,破壞濕地罪,大量虐殺動物罪,破壞自然保護區罪,抗拒環保行政監督管理罪。2
通過以上措施,可提高環境刑法在刑法中的地位的同時,擴大刑法對環境保護的范圍和打擊面,加強環境的刑法保護力度。
三、完善刑法對各具體環境犯罪的規定
(一)完善刑法第338條污染環境罪
刑法第338條的罪過形態一直被學術界爭議,有學者人認為該條規定的主觀為故意,有學者認為是過失,還有的學者認為既有故意也有過失且對故意過失進行了比例考量。筆者看來,解決此學術爭議的最佳辦法,就是對該條條文再次進行修改,明確規定故意和過失,使得司法實踐中對本條的適用更加精確化。修改方法為,增加第二款“環境污染事故罪”,內容如下:
“過失犯前款罪,造成環境污染事故的,處……,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處……”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增加的“環境污染事故罪”不同于刑法修正案(八)對刑法進行修訂之前的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而筆者建議增加的“環境污染事故罪”是一個新的過失犯罪名,強調的是“污染環境罪”的過失形態。
(二)完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由于破換環境的犯罪的犯罪性質、行為方式、危害結果以及波及范圍等方面,都與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有著極大的相似性。筆者認為,如若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危險行為沒有產生危險也沒造成嚴重的實際危害結果,卻破壞了環境保護,可適用刑法第六章第六節第338條污染環境罪的規定。因此,筆者建議,在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4條條文下,增加第二款,內容為:“實施前款所規定的的行為,尚未危害公共安全,但污染環境的,依照本法第338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三)完善走私犯罪
首先,應將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二節中的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貨物、物品罪中的有關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的犯罪行為,以及走私廢物罪納入上文所述的新增的“侵害環境罪”這一章中。其次,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規定“在走私過程中污染環境的,按相應的走私犯罪與相應的破壞環境犯罪數罪并罰。”如在走私核材料的過程中,使核材料泄露并擴散導致核污染的,判決成立走私核材料罪與污染環境罪,數罪并罰。
(四)完善對單位犯罪的規定
刑法346條只是籠統的規定了“單位”犯本節之罪的處罰方法,大量的個體工商戶合作者及家庭聯產承包戶合作組織,沒有什么組織機構,這些組織犯本節之罪目前只是依照個人犯罪處罰。筆者認為,應對上述組織的處罰也應比照單位犯罪處理。筆者建議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對環境犯罪中的“單位”進行擴大解釋。
注釋
1張秉志,陳璐.當代中國環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J].2011(6):90~98.
2趙秉志,陳璐.當代中國環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J].現代法學.2011(11):90~98.
[1]趙秉志,王秀梅,杜澎.環境犯罪比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趙秉志,陳璐.當代中國環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J].現代法學,2011(6)
[3]趙秉志,陳璐.當代中國環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J].現代法學,2011(11).
[4]侯艷芳.環境刑法的倫理基礎及其對環境刑法新發展的影響[J].現代法學,2011(7).
[5]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