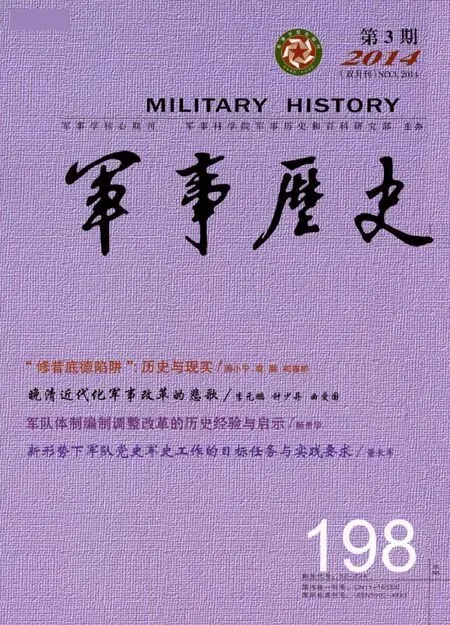“修昔底德陷阱”:歷史與現實
□ 周小寧 袁 鵬 柯春橋
一、“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由來
【周小寧】“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從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引申出來的。修昔底德是古希臘奴隸制城邦雅典的公民,大約生于公元前460年,卒于公元前400~公元前396年之間。他親身經歷和參與了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雅典同盟與斯巴達同盟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24年,他成為雅典 “十位將軍”之一。同年冬天,愛琴海北岸的阿姆菲波利斯城遭到斯巴達人攻擊,他率領一支艦隊由附近的薩索斯島前往支援。不過,在他趕到之前,阿姆菲波利斯城已經向斯巴達投降。但因為誣告,他被放逐20年。被放逐期間,他有機會來往于色雷斯和伯羅奔尼撒半島之間,搜集第一手資料,完成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大部分書稿。公元前404年雅典戰敗投降,第二年修昔底德獲得特赦,回到雅典。他本打算將長達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全部記述下來,但實際上只記述了20年,止于公元前411年。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述客觀翔實,分析全面深刻,文筆簡潔優美,是西方古典歷史著作中的經典,在史學、政治學、文學等領域都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據說,雅典著名的雄辯家德謨斯提尼(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為了學習該著作文筆,將它抄寫了8遍。近代客觀主義史學之父、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蘭克(1795~1886年)將其奉為案頭書,常年反復研讀。馬克思、恩格斯也在著作中多次引用本書。
兩千多年來,本書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發行。中國根據英譯本翻譯出版兩種中譯本。一種為謝德風先生翻譯、商務印書館1960年出版;另一種由徐松巖教授等翻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約50多萬字。
美國著名小說家、普利策小說獎獲得者赫爾曼·沃克(二戰期間曾在美國海軍服役)曾使用過 “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1980年4月16日,他在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所作的題為《悲傷與希望:對現代戰爭的一些思考》的演講中說:“雅典、斯巴達是兩大對手,是希臘世界的 ‘兩個超級大國’。它們結成聯盟擊退和戰勝了共同的敵人波斯。勝利之后,聯盟分裂,陷入冷戰。由于雙方的小盟國發生戰爭,雅典、斯巴達之間的和約被廢止,它們被拖入一場大戰。這場大戰也就是修昔底德所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主題。……在希臘這個小 ‘世界’里,類似當今世界發生的事情都發生了:如聯盟破裂,政治家與軍事將領之間災難性的競爭,背叛與反背叛,內部不和損害戰爭努力。……二千多年后,我們似乎仍然陷于修昔底德所處的世界中……我們怎么才能擺脫這個即使沒有破壞但也令這個世界窒息的修昔底德陷阱呢?”
不過,當前流行的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人們普遍認為其提出者是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貝爾弗(Belfer)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學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阿利森生于1940年,曾在里根政府時期擔任國防部長的特別顧問,在克林頓第一屆政府中擔任助理國防部長,現在是美國國防部長、國務卿和中央情報局局長三個顧問委員會的成員。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他現在主持的貝爾弗中心,今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思想庫與社會團體研究項目”排名中,名列全球大學附屬思想庫第一名。
阿利森思想十分活躍,幾乎每個月都要發表幾篇份量很重的文章。2012年8月22日發表于英國《金融時報》的《修昔底德陷阱已凸顯于太平洋》,副標題是 “格雷厄姆·阿利森說,中國與美國就是今天的雅典與斯巴達”。文章載:“未來數十年全球秩序的關鍵問題是:中國與美國能夠避開 ‘修昔底德陷阱’嗎?修昔底德的隱喻提醒我們,一個崛起中的國家挑戰一個居主導地位的國家時(如公元前5世紀雅典、19世紀末德國所做的那樣),雙方面臨著怎樣的危險。這種挑戰多數的結果是戰爭;那些和平解決的事例要求雙方政府和社會大力調整各自的態度和行為。……雅典的急劇崛起震驚了伯羅奔尼撒半島既有陸上強國斯巴達,恐懼迫使斯巴達領導人作出反應。雙方之間的威脅與反威脅引起競爭,接著是對抗,最終是戰爭。……對此,修昔底德寫道:‘正是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達引起的恐懼導致戰爭不可避免’。”文章接著說:“任何新強國的快速出現都打破現狀。”根據阿利森的文章, “修昔底德陷阱”的基本含義是:一個新崛起的強國(如中國)必然挑戰既有強國(如美國),而既有強國也必然作出反應,這樣戰爭就很難避免。
阿利森提出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后,在西方學界、政界、軍界影響很廣,被不少人接受和宣揚。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羅斯克蘭斯就說:“中國的崛起,即使沒有引起恐懼,也引起了誤解。”
我認為,阿利森有關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引伸和對比值得商榷:
第一,阿利森的引文與修昔底德的原意有出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從修昔底德有關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那句名言—— “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中引申出來的。
阿利森在2012年發表的《修昔底德陷阱已凸顯于太平洋》、2014年1月1日發表的《2014年:是大戰的高危年嗎?》兩篇文章中的直接引文是:“正是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達引起的恐懼導致戰爭不可避免。”
區別在于,修昔底德名言的原意是 “雅典勢力的增長……”,阿利森所用引文為 “雅典的崛起……”,二者含義大不相同。
阿利森引文對修昔底德名言的改動給人一種感覺,即用 “中國的崛起”這種當代具有特定含義的概念,生搬硬套于古希臘,借用修昔底德的名望,為他提出特別適用于當代中美關系的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供歷史的、理論的支撐。
第二,把雅典、斯巴達分別看作崛起強國和既有強國,與史實不符。如前所述,赫爾曼·沃克將雅典、斯巴達稱為古希臘世界的 “兩個超級大國”。這種表述,比較符合史實。雅典、斯巴達幾乎同時建立于公元前8世紀,是希臘人在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小亞細亞沿岸建立的二三百個被稱為 “城邦”的奴隸制國家中最發達的兩個。雅典位于希臘中部的阿提卡半島,是提洛同盟的盟主,在海上稱雄;斯巴達位于希臘西南部的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南部,是伯羅奔尼撒同盟的盟主,在陸上稱霸。在公元前492~公元前449年的希波戰爭中,雅典的戰功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斯巴達。希波戰爭前期,斯巴達人是希臘聯軍統帥;戰爭后期,雅典人是希臘聯軍統帥。
古希臘文明的中心是雅典,而不是斯巴達。雅典被稱為希臘文化的搖籃。公元前443~公元前429年,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連續15年擔任雅典首席將軍,雅典達于極盛,史稱 “伯里克利時代”。馬克思也說 “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是伯里克利時代。”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雅典的勢力比伯羅奔尼撒同盟的任何一個成員國的勢力都要強大,當時希臘的大部分已經在雅典控制之下。
因此,雅典、斯巴達實際上都是既有強國,都是霸權國家,而非一個崛起強國,一個既有強國。
第三,中國不是雅典,美國也不是斯巴達,不能拿歷史與現實進行簡單類比。中美兩國都擁有核武器,很難想象兩國會爆發大規模戰爭。中國對外奉行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和平外交政策,與雅典當時奉行的結盟與擴張政策完全不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美國是發達的超級大國,兩者實力差距懸殊,中國既沒有向美國挑戰的實力,更沒有向美國挑戰的意圖。這與當時雅典與斯巴達基本勢均力敵的情況也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學者將中國比作雅典,將美國比作斯巴達,借用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片面強調和渲染崛起強國可能挑起戰爭的危險性,應引起注意。
第四,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阿利森是美國政府的前任高官和現任高級顧問,其研究目的一向非常明確,就是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2012年因日本 “購買”釣魚島造成中日關系緊張時,他研究美國如何在釣魚島問題上給中國畫出一條紅線。
“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有探討如何避免中美沖突的一面,其用意更在提醒世人:從古至今崛起強國必定挑戰既有強國,破壞既有國際秩序,但最終都可能遭到失敗,歷史上的雅典、德國即是例證。其影射意義是:崛起的中國也不會例外。他由此提醒美國政府警惕和遏制中國,同時也不乏對中國的警告和威嚇。
照搬西方處理大國關系的邏輯思維方法,必然會掉進 “修昔底德陷阱”。2013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接受21世紀理事會專訪時,向世界傳遞著這樣的聲音: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強國一定會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于中國,這不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基因。中國正在用中華歷史文化的思維,與美國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避免這個陷阱。
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發展前景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袁鵬
【袁鵬】周研究員對“修昔底德陷阱”清晰簡明的介紹,同時有意識地引出 “修昔底德陷阱”與中美關系這個話題。實際上我們今天談論 “修昔底德陷阱”及 “一戰”教訓等,意在為今天的中美關系破局。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把中美關系比作一戰前的英德關系,二戰前的德日崛起,西方學者借用 “修昔底德陷阱”把我們的視線往歷史上引。現在在中國國內思考中美關系,常作兩個比較:一個比較是把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中美關系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中美關系作比。1978年12月16日,中美簽署 “建交公報”,兩天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后1個星期,亦即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宣布建交。4個星期后,鄧小平訪美。可以說,中國的第一次改革開放,和中美關系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是正相關的關系。過去35年,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中美關系也同時取得超出想象的大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被國際、國內許多媒體稱為 “中國的第二次改革開放”,那么,這次改革開放與中美關系到底將呈現怎樣的關聯呢?第二個比較,就是現在國際社會普遍思考的,把今天的中美關系跟古代的雅典、斯巴達,跟一戰前的德國、英國,跟二戰前的美國、日本相提并論。
今天的話題,關涉第二個比較,涉及中美構建 “新型大國關系”。因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提出,就是要打破 “修昔底德陷阱”,開創歷史新篇。這里不妨回顧一下奧巴馬上臺以來中美關系的歷史。奧巴馬上臺(2009年)后,中美關系一度開局良好。新任國務卿克林頓上任1個月就訪問中國,奧巴馬總統上任不到1年就正式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以前都沒有過的,開創了歷史先例。究其原因,奧巴馬當時在三大問題上有求于中國:一是需要中美同舟共濟助美度過金融危機;二是需要中國提供實質性幫助助美在阿富汗反恐;三是希望拉住中國共同應對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來自歐日的壓力。其結果,中美互動并不順暢,既有主觀戰略誤判的原因,也受客觀因素的影響。總之從2010年伊始,奧巴馬對華政策出現了重大轉變:2010年1月美對臺軍售,2月奧巴馬接見達賴,3月 “天安艦事件”突發引發中美互疑加重,5月美韓大規模黃海軍演,7月南海紛爭又起,中美關系突然間從2009年的 “高開高走”變得 “急轉直下”。2011年初,為中美關系破局,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在兩國簽署的聯合聲明里,雙方決定 “共同構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當時中國國內普遍認為這是對未來十年中美關系的新定位。這個定位的邏輯是:中美既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那么就應該是伙伴;伙伴又分兩類,一類競爭伙伴,一類合作伙伴,雙方決意做合作伙伴;既然是合作伙伴,前提就應該是相互尊重,結果就應該是互利共贏,所以才有了 “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的提法。但中美新的戰略共識很快被2011年美國開啟的 “亞太再平衡戰略”沖擊,因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被中國普遍理解為針對中國的戰略圍堵,更重要的是,周邊一些國家利用美國的戰略調整對華挑事,最終誘發中美之間的對抗,使得中美關系再度降溫。2012年初,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再度訪美。正是在此訪中,習近平副主席提出構建 “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遺憾的是,當時除國務卿克林頓等少數有戰略遠見的人士對此有回應外,美國朝野對此關注度不高。隨后,因2012年日本 “購島”事件引發中日釣魚島爭端升級,接著中菲黃巖島爭端加劇,使中美關系再陷低迷。2013年,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上臺,恰逢釣魚島爭端愈演愈烈,中國在年底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美國強力反制,隨后又無端連續在東海、南海問題上大放厥詞,于是,中美關系在一波三折中步入了2014年。
從奧巴馬上臺后中美關系的簡單回顧可以看出,中美雙方領導人都在為改善兩國關系做努力。奧巴馬上臺之后和中國領導人會面16次,這種高頻次的接觸本應拉近兩國關系,但實際上的中美關系卻差強人意。原因無他,在于過去這幾年,中美關系已經或正在發生四個重大的根本性變化:
一是力量之變。小布什上臺時,中國GDP僅只是美國的1/8,到奧巴馬上臺時,已接近1/2,2013年則達到60%。中國GDP的增長速度在歷史上是空前的,在短短的幾年中連續超英、超德、超日,近逼美國,這是一切問題的根本。而美國在看中國實力時不僅關注GDP,而且看重中國軍事實力的增長。中國每年都有新式武器登臺亮相,軍費連續兩位數增長,其速度和變化之快讓美國有點跟不上中國的節奏。相反,過去幾年,美國深陷兩場戰爭、一場危機,實力地位呈現下滑之勢。一進一退之間,使得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被放大。也可以說,中美力量對比正在從量變發生部分質變。這個量變向質變過渡的過程是最危險的。
二是戰略之變。美國的戰略變化,在中國看來就是全球收縮、亞太發力;美國看中國,正好相反,是全球擴展、亞太為甚。所以雙方不約而同地聚焦在亞太地區。中美在亞太地區全方位正面博弈,這在以前是沒有的。美國 “亞太再平衡戰略”給中國帶來了經濟、軍事、外交的多重挑戰。但是最重要的挑戰,還是心理層面的。過去10年我們習慣于美國深陷中東泥潭,著力反恐,但是沒想到美國戰略重心東移說移就移,“亞太再平衡戰略”瞬間付諸實施。這種心理上的不適應很容易使中國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每一個動作理解成針對中國的圍堵,而中國的反制則同樣使美國得出結論,認為中國要排擠美國的亞太利益。
三是基礎之變。中美關系之所以在過去35年發展順暢,因為冷戰時期有共同的蘇聯威脅,冷戰后有共同的經貿利益,“9·11”后有共同的反恐合作。而現在兩國找不出一個類似的、厚重的、能夠拉動和推進中美關系的合作基礎。這個共同基礎的松動和弱化,使中美兩國求同存異產生困難。過去中美能夠求同存異,就是因為有一個“壓艙石”,現在這個 “壓艙石”變輕了,中美關系這艘 “航船”自然出現漂浮不定狀態。那么新的基礎在哪兒呢?雙方正在苦苦地摸索,但是還沒有完全摸索到。基辛格說,冷戰前靠共同的威脅,冷戰后靠共同的利益,今后則靠共同的問題,以共同應對全球化時代帶來的全球性問題作為中美共同的基礎。但是雙方還沒有從理論層面、戰略層面把哪些是中美共同關心的問題梳理清楚。
四是環境之變。從內部看,美對華決策日趨多元化,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專家學者、不同的網絡媒體都爭先恐后發聲,試圖影響兩國的對外決策,使得發展中美關系的國內共識不足。從外部看,中美關系越來越深受第三方因素的干擾。過去幾年的實踐證明,中美之間的矛盾通常不是兩國雙邊意義上的,往往都是因為釣魚島、黃巖島、仁愛礁、朝核、伊核、敘利亞、烏克蘭,這些關涉中美之外、涉及中國同第三方或美國同第三方引發的矛盾,最后這些矛盾統統演變成中美之間的矛盾。
上述四個變量疊加在一起,就可以感受到中美關系確實正在發生重大的根本性的變化。換言之,那些曾經成功塑造過去35年中美關系發展的基本經驗或規律,未必能夠指引未來35年中美關系的發展走向。這其中最大、最根本的變化,在我看來就是中美從過去 “老大”和 “老五”、“老六”的關系,變為現在 “老大”和 “老二”的關系,這才有了我們今天來討論 “修昔底德陷阱”、一戰戰前格局等問題。如果沒有這個 “老大”、“老二”對應關系變化的話,我們就沒有必要討論今天這個話題。盡管我們不承認中國是 “老二”,但全世界包括美國都在不約而同說中國是 “老二”,所以就由不得中國不面對,因為中國已經被人塑造成了 “老二”。冷戰后中國對美外交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努力避免過早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的首要戰略對手,現在看來,這個目標很難實現了。烏克蘭事件美國對俄羅斯的政策顯示,美國不想因克里米亞危機改變戰略重心東移的步伐,其潛臺詞就是,中國而非俄羅斯更是美國必須全力應對的主要戰略對手。
(3)采用氯化銨直接沉淀法,萃鈀余液不需要再進行中和除雜工序就可直接進行鉑提取,避免了中和工序鉑進入中和渣中造成鉑的損失。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怎么看待中國這樣一個對手?歷史地看,美國擁有對付 “老二”的足夠經驗:對德國通過熱戰,對蘇聯通過冷戰,對日本通過經濟戰,后來對歐盟通過貨幣戰,把位居第二位的國家要么搞垮,要么制服。針對中國這個 “老二”,美國會采取什么辦法?美國也在思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像剛才講的阿利森這些人,像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這些人,主張對華遏制,認為如果現在不下手的話,等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就晚了;也有不少美國人認為應對中國崛起,美國應該有新思維,比如提出 “利益攸關方”的佐利克,提出 “兩國集團”(G2)的伯格斯騰等。不管美國人怎么想,怎么看,美國人思考中國崛起時有三點回避不掉,或者說,未來美國對華戰略的依據有三個基本點:
第一,中國作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擁有13億到15億人口大國的崛起,給美國和西方帶來的資源、能源和經濟上的挑戰,如何應對?
第二,中國作為世界上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的崛起,其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對美國和西方帶來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及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政治上的挑戰,如何應對?
第三,中國作為現存大國中唯一一個還沒有完全解決主權和領土爭端的大國崛起,伴隨民族主義情緒的增強和軍事現代化的加速,以非和平手段解決領土主權爭端的可能性在增大,而不是在減小,這種軍事安全上的挑戰,如何應對?
這三大挑戰擺在美國人面前,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在共同思考。遺憾的是,美國在既有對付 “老二”的 “工具箱”里,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辦法應對中國。全面遏制似乎行不通,因為中國不是蘇聯,中美之間5200億美元的經貿規模(2013年)、90多種對話機制,彼此利益已然深度捆綁,所以遏制中國可能傷及自身。全面接觸行不行呢?美國認為沒能奏效。因為接觸政策有兩個前提:一個是中國可能崩潰,第二個是中國可能被改造。但過去35年的歷史證明,中國不僅沒有崩潰,反而崛起;中國不僅沒有被改造,反而更加自信。那么,通過金融戰、貨幣戰行不行呢?也難。因為中國在10年前就對金融黑手、貨幣戰爭保持高度警惕,陰謀變成陽謀,還如何下得了手?所以,美國看中國,既可愛也可恨,可恨的是中國正在逐步趕超自己,可愛的是中國是個廣闊的市場,中美民族性還很相近。一句話,美國已不是當年的美國,中國也不是當年的中國。中國既有蘇聯的國土規模和軍事規模,也有日本的經濟實力,還有歐盟這樣獨特的價值體系和文明體系,這是一個 “三合一”的 “新型老二”。
對付中國這樣 “三合一”的 “新型老二”,必須有新思維。但美國囿于歷史慣性和霸權思維,新思維落地生根很難。近期對華政策的種種做法,使人覺得美國人有些亂了章法,是在采取 “競爭+打壓”的好勇斗狠式的方法在臨時性應對中國挑戰。真正長遠的對華戰略是什么?恐怕要等到中期選舉甚至2016年大選之后。這期間,則奉行預防沖突、管理競爭、擴展合作的基本準則。
那么,針對奧巴馬這種思辨,針對中美關系的新變化,我們怎么辦?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中美 “新型大國關系”,正是中國新領導集體在繼承和發展既有對美戰略思想基礎上,為今后中美關系破局提供了創新性思維。2012年初習近平作為國家副主席訪問美國,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提出我們應該有勇氣打破歷史上大國興衰必然發生沖突的歷史宿命,以 “摸著石頭過河”的智慧和 “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勇氣,開創一個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新型大國關系。2012年底黨的十八大召開,構建 “新型大國關系”寫進了十八大報告。自此,中美兩國學者開始掀起研究、探討新型大國關系的熱潮。2013年6月兩國領導人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期間,關于如何理解新型大國關系,習主席提出了十四個字的解讀:“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其中,不沖突、不對抗,體現了中國的底線思維,即千方百計避免中美軍事沖突,謀求和平共處,應該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內容;而相互尊重對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則是新型大國關系的基本前提;合作共贏則意味著,中美不僅要雙贏,更要通過自身蹚出來的新路,給大國興衰史劃上句號,給國際關系史譜上新篇。
美方對新型大國關系的態度,總體是既不排斥,也不跟進,多少顯得有些勉強。但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和學者逐步重視這個概念,開始深入研究其中內涵,這是值得關注的新氣象。中美關系發展至今,已經到了我們必須擺脫被動牽引、而應主動塑造的新階段。
我覺得,“新型大國關系”理念提出的最大意義在于使雙方在思考未來10年、20年中美關系時,有了基本的框架。所有的競爭、沖突都將被框在其中,防止中美關系突然崩局。它也給理論界、戰略界、學術界思考大國關系提供了新的啟迪。反過來,它也會影響中國具體決策的推進。在具體落實過程中雙方發現,喊口號容易,落實起來很困難。美國人以其特有的 “務實”精神,提到一系列檢驗中國是否真心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清單,包括朝核問題、網絡問題、兩軍關系問題、國企改革問題等等。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從中國方面講,既是兩難,也是繞不過去的坎兒。
新型大國關系的提出,為中美關系的破局開了一個好頭,在具體操作層面還有好多東西沒有展開。我認為根本原因是:第一,中美相互間對彼此的戰略判斷還需要更精細化、科學化。簡單地認定美國現在對中國施行全方位戰略圍堵、遏制,或者簡單地講中國就要挑戰美國,都失之簡單。如果以此作為思考前提去塑造新型大國關系,那肯定沒法實現。中國要精細化思考美國的動作,要看到美國有遏制中國的一面,有同中國競爭的一面,同時也要看到與中國合作的一面。第二,還需進一步解放思想。既然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那么有些方面就要創新思維。比方說,阿富汗方面中美有共同的利益,沒有直接的對抗,今后能不能合作,怎么合作,能不能有些新的思維?如果雙方都觀望而不出手作為,那么新型大國關系就建立不起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要千方百計規避中美之間的正面沖突、正面對抗,因為一旦出現沖突對抗,“新型大國關系”這個概念本身就會被束之高閣。
三、一戰前德國戰略調整的教訓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外國軍事歷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柯春橋
【柯春橋】關于能否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大國能否順利崛起,我個人認為,這既取決于國際大環境,更取決于大國自己的戰略選擇和戰略運籌。現從大戰略角度,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威廉二世的戰略調整進行分析,希望對我們今天有所啟迪。
第一,定下 “世界帝國”的大戰略目標,遠遠超出了德國國力。大戰略目標,即國家戰略目標,集中體現了國家的根本利益和奮斗方向。它在大戰略諸要素中處于核心地位。目標正確,全局皆活;目標錯誤,滿盤皆輸。正如喬治·馬歇爾所說:“只要目標正確,連一個尉官也能制定戰略。”在確定大戰略目標時,要考慮多種因素的平衡,最關鍵的是達成目標與力量之間的平衡。
1871年,俾斯麥經過三場王朝戰爭實現德國統一后,精心制定了所謂 “大陸政策”,確立了達成 “有利于德國的歐陸大國平衡”的大戰略目標。這個目標是在全面分析了歐洲各國力量對比和各國戰略趨向的基礎上制定的,有相當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但是,1890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迫使俾斯麥辭職后,開始對德國的內外政策進行一系列調整,特別是1897年改組內閣后,將俾斯麥的“大陸政策”調整為 “世界政策”,提出建立 “世界帝國”的戰略目標。
威廉二世進行的戰略調整,主要是基于對德國綜合國力的過高估計。實際上,當時德國的殖民地不到英國的1/10。海軍力量與視海軍為生命線的英國相比,更是差距較大。況且,確立這一目標,等于是向 “有利于舊的、老資格的大國的國際秩序”發起挑戰。可以說,威廉二世戰略目標過大,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禍根。
第二,大國戰略思路不清晰,致使在爭取盟國斗爭中一敗涂地。大國歷來是國際政治舞臺的主要玩家。能否運籌好大國關系,構建有利于己的戰略平衡,防止陷入孤立,是德國大國戰略的首要任務。俾斯麥深諳此道。他深知德國地處中歐,戰略環境復雜,只有巧妙地處理好大國關系,力避兩線作戰,集中打擊主要敵人,才能確保立于不敗。為此,他始終將復仇情緒強烈的法國作為主要敵人,采取 “聯奧、拉俄、親英、打法”的大國戰略。但其繼任者不理解俾斯麥的深刻用意,不明白大國戰略的復雜性,采取了 “要么全部,要么沒有”(“不全寧無”)的簡單化、情緒化的處理辦法,致使德國在與法國爭取盟友的斗爭中一敗再敗。
首先是拒絕與俄國續訂《再保險條約》,客觀上促成了法俄同盟的建立。該條約是俾斯麥大國外交體系中的重要一環,雖然不能保證俄國在德法戰爭中支持德國,但卻能束縛俄國的手腳防止法俄接近。拒絕續訂,等于給俄國行動的自由,促成了法俄接近直至結盟。1891年,法俄結盟后,德國的安全面臨著東西兩線腹背受敵的險境。其次,爭取英國再遭失敗。法俄結盟后,歐洲大陸形成了德奧意同法俄互為對手的兩大軍事集團。英國老大處于 “四兩撥千斤”的地位,誰能爭取到英國的支持,誰必將力量倍增。當時,英國與法俄集團的矛盾遠遠大于與德奧意集團的矛盾。應該說,德國爭取英國有較好的條件。兩國內閣中都有人強烈主張建立英德聯盟。但德國 “不全寧無”的態度最終使談判不歡而散。對此,基辛格曾評論道:“德國應該要求英國的不是聯盟,而是在歐洲大陸一旦發生戰事時保持友好中立,要達到這個目的,協約式的安排已足夠了。但德國卻為了沒有必要爭取的保證,提出英國不想要的交換條件,以致使對方懷疑德國其實是想追求全球霸權。”當然,英德談判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德國企圖建立 “世界帝國”的野心,大力發展海軍,挑起同英國的海軍軍備競賽,觸動了英國的戰略紅線。
第三,對深層國家利益認識不統一,造成對外政策自相矛盾。國家利益是指確保國家生存、發展和安全需求諸要素的集合,是決定軍事力量發展的根本因素。從歷史經驗看,可將國家利益分為深層國家利益和表層國家利益。深層國家利益是指攸關國家長期生存和發展的利益,必須全力以赴去爭取。表層國家利益主要是指不影響國家長期生存和發展的短期利益。有時為了維護深層國家利益,可以擱置甚至犧牲表層國家利益。有時,受大環境所限,即使是深層國家利益,也要講究方法節奏,以間接穩妥的方式,逐步實現之。
事實表明,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如何認清深層國家利益和表層國家利益,是一個復雜的戰略問題。19世紀中葉,俾斯麥認為統一是德國的深層國家利益。為此,當普魯士大軍在薩多瓦戰役大勝,千年古都維也納已敞開大門的情況下,他不惜以辭職相威脅,堅決反對進軍維也納,力主與奧地利簽訂停戰協定,此舉為確保奧地利在即將到來的普法戰爭中保持中立創造了條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各界對其國家利益的認識極不統一。對德國來說,在面臨著法俄兩強東西夾攻的險惡形勢下,本土安全應該是第一位的。但是,德國各利益集團卻不顧國家的整體利益,從各自狹隘的利益需要出發,影響和干擾了國家的重大決策。以海軍大臣蒂爾皮茨為代表的海軍派認為海上利益是 “德國的生死問題”,力主發展海軍,并全力準備對英作戰。陸軍派則主張全力發展陸軍,重點打擊法國。金融家和商人們希望進入巴爾干、土耳其和近東,要求優先打擊俄國。東普魯士的容克貴族們則要求優先保護他們的財產安全。時任德國宰相的貝特曼·霍爾韋格悲嘆道:“向每一方挑戰,又妨礙了另一方,而且在所有這些進程中實際上削弱不了任何一方”。更為可悲的是,作為最高決策人的威廉二世缺乏戰略眼光和堅定意志,對深層國家利益和戰略重點缺乏深刻認知,常常受狹隘的利益集團所左右,忽左忽右,忽東忽西,到處擴張,四處樹敵,政策和策略相互抵觸,最終將俄、英等強國都推入主要敵人法國的懷抱,將自己逼上絕路。
第四,對本國的地緣戰略環境缺乏深刻認知,造成資源投入嚴重分散。地緣環境始終是影響國家戰略的重要制約因素。一個國家的地緣環境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其戰略資源的投向和戰略方向的選擇。歷史表明,陸海大國與海洋大國爭奪海權,皆以失敗告終。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海權關系到海洋大國的生死存亡,它們必然傾全力發展海權,而陸海大國既要發展海權,又要發展陸權,造成資源分散,最終陷入被動。第二,陸海大國地緣環境相對復雜,海洋大國易搞 “離岸平衡”。英國曾多次利用奧地利、普魯士、西班牙牽制法國;后來,又利用法國、俄國制衡德國。冷戰期間,美國則是利用西歐和中國制衡蘇聯。現在,繼續玩古老的 “離岸平衡”游戲,利用印度、日本,甚至越南、菲律賓來牽制中國。第三,遠洋海軍消耗龐大,后勤補給困難,需要遍布全球的基地網,陸海大國難以承擔。
德國的地緣環境決定了它主要是一個陸地大國,其主要敵人是法國,主要資源應投向陸戰力量。但是,威廉二世是馬漢的狂熱信徒,早在1897年就宣稱:“德國的未來在海上。”此后德國瘋狂的造艦計劃,不僅將自己置于與海洋霸主英國對立的地位,而且耗費了大量的資源,從而嚴重地影響到對陸軍的投入。事實上,德國每向海軍多投入一馬克,就等于幫助法國一份力。歷史證明,德法之間的西線戰場才是決定一戰勝敗的主戰場。
第五,缺乏戰略魄力,未能抓住稍縱即逝的戰機。抓住時機推進國家利益是戰略謀劃的本質要義。戰略指導者要善于發現并全力抓住歷史轉變的契機去開創新局面。一旦抓住了時機,堅決出手,就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否則就可能喪失機遇而受到歷史的懲罰。俾斯麥之所以能夠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盤根錯節的環境下實現德國統一,關鍵是抓住了幾個重大機遇,特別是利用拿破侖三世在歐洲處于孤立的機會,一舉打敗法國,掃除了統一的外部障礙。統一完成后,俾斯麥看到法國力量恢復很快,憂心如焚,至少有兩次企圖對法國發動預防性打擊(1875年和1887年),但都因俄國的堅決反對而未敢行動。但是,1905年夏天卻是天賜良機。因為當時法國的主要盟國俄國正在被日俄戰爭所困擾,根本無力支援法國。遺憾的是,德國已再無俾斯麥那樣的大戰略家。錯過這次難得的 “一線作戰”良機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再無避開兩線作戰困境的機會。
德國一戰前戰略調整的教訓表明,大國崛起需要有正確的戰略選擇和高明的戰略運籌。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中美兩國完全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吸取歷史的教訓,走出歷史的宿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開創 “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果真如此,則中美幸甚!亞太幸甚!世界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