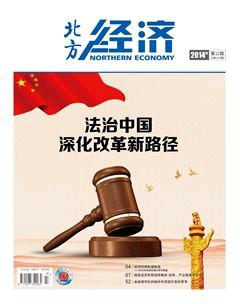從世界各國碳排放看中國減排
胡蓉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開始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世界經濟有了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大量能源被消耗,增加了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給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針對目前碳排放現狀,許多學者進行了研究。樊剛等提出了以最終消費來衡量各國的碳減排責任,通過對二者關系的研究指出中國的碳排放實際是由他國消費所致,而大部分的發達國家恰恰相反,所以應該平衡國際碳排放責任;朱江玲、岳超等研究了從1850年到2008年世界主要國家的碳排放量,提出我國今后要進一步促進減排,推動產業轉型;張志強、曲建升等以19世紀20年代以來7個工業化國家和5個新興經濟體國家的CO2排放數據為基礎,計算了相應的碳排放強度以及與人均GDP的關系,分析了各國的減排歷程。
從目前的世界經濟形勢來看,可以分為兩大經濟集團:七國集團(美國、加拿大、意大利、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簡稱“G7”國家)和金磚四國(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七國集團于1976年正式成立,是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的聯合體,當時他們的GDP占世界總量的2/3,對推動世界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金磚四國”反映了21世紀世界經濟格局的巨大變化,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進一步促進了世界經濟的迅猛發展。目前,七國集團與金磚四國的經濟產值占世界經濟份額的2/3,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本文以這11個國家為研究對象,在總結前人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對其2002年到2012年的碳排放量進行研究,通過比較分析各個國家的能源和產業結構對世界碳排放現狀進行說明,最終為中國的進一步減排提供有效的對策建議。
二、數據分析
本文通過世界銀行數據庫得到了11個國家2002—2010年的碳排放量,再根據國際上通用的IPCC法計算2011—2012年的碳排量,能源消耗量取自《世界能源統計》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網站。
根據得出的數據來看,碳排放量排在前四位的國家分別為美國、中國、俄羅斯以及印度。美國作為經濟第一大國,其碳排放量在全球碳排放中占到了很大的份額,在2008年之前是逐年上升,由于2008—2009年爆發了金融危機,其經濟發展受到影響,所以2009年的碳排放驟降,之后略有回升,但是增速緩慢;日俄與美國情況相同;中國和印度都屬于發展中國家,兩國的經濟正處在蓬勃發展時期,所以碳排放量每年在增加,尤其是中國的碳排放數額占到了世界的20%以上,近幾年更是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的碳排放國家;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碳排放量總體上呈逐年遞減的趨勢,正在向減排逐步靠近;加拿大、意大利以及巴西的碳排放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前是逐年增加的,之后由于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而出現低峰值,隨后經濟發展緩慢恢復,碳排放逐漸增加。
總的來說,中國、印度、美國、日本以及俄羅斯是全球碳排放量的主要成員,他們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其中,作為世界兩大經濟強國的美國與中國,其碳排放的變化對全球碳減排起著重要作用。在2006年之前,美國的碳排放量一直最多,從2006年開始,中國的碳排放總量超過美國,之后兩國碳排放量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主要是因為2003年以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商品不斷增加,導致國內資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中國碳排放的急劇增加;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貿易量較少,再加上美國“頁巖油氣革命”的進行,使煤炭的消費大大減少,極大地降低了碳排放量;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于俄羅斯的經濟水平,但是其碳排放卻比俄羅斯少,這主要是源于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尤其是油氣儲量豐富,而日本國土狹小,能源儲量少。剩下6個國家的碳排放總量較少,其中德國的碳排放量最多,平均為8億噸左右;法國的年均碳排量最少,為4.06億噸。
三、討論
通過上述對兩大經濟集團2002年到2012年碳排量進行分析、比較之后我們看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量有很大差異,同時不論是在發達國家內部或是發展中國家內部,也存在碳排放的差異性。由此體現出了各個國家不同的能源結構以及產業結構:
(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碳排量差異較大
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在技術使用方面更是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開始調整能源結構,制定相關的“綠色能源”發展戰略,同時調整產業結構。美國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開始發展半導體、電子計算機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同時把傳統產業向日本、聯邦德國等國轉移;20世紀60~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沉重打擊了西方發達國家高能耗的重化工業,迫使這些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開始發展能源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將鋼鐵、造船等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重點發展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產業,尤其是金融、保險及其他的企業服務業等信息密集型產業,深化了產業結構。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起步晚,現在正是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工業還是整個產業的重心,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暫時不會減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2012年,我國工業對GDP的貢獻率為40.6%;同時,我國能源新技術的使用率較發達國家不高,新能源在總能源中不到10%,能源使用以煤為主。2012年我國一次能源總消耗折36.2億噸標準煤,約占全球的21.3%,單位GDP能耗是國際的2倍,是發達國家的4倍。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階段,第二產業比重較大,產業結構不合理,同時新能源發展技術落后,能源結構亟待調整。
(二)發達國家之間也存在差異
美國、俄羅斯和日本的碳排放量分別排在前三位,一直以來他們主要靠發展重工業提高經濟產值,在新技術的趨勢下開始走向新的能源發展道路;意大利的工業化起步晚,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在新的經濟形勢下開始探索新能源發展道路。英法德加等國的碳排放量相對較低,這主要得益于第三產業在整個產業中占主導地位。例如,英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逐步實現了以金融服務和創意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結構調整;加拿大與法國擁有較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它們的產業結構相近,服務業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德國的自然資源比較貧乏,而依賴進口會存在能源安全問題,所以本國主要走發展綠色能源的道路。
(三)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異
在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中,中國、印度和巴西屬于發展中國家,且他們是“金磚四國”中的三個國家,但是中印與巴西的經濟結構卻不盡相同。目前,中印兩國仍然是以第二產業為主,雖然第三產業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但是比重不高;巴西的產業結構順序與發達國家一致,第三產業的比重最高。所以巴西的碳排放量少,而中印的碳排放較多。
四、戰略與政策建議
為了實現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制定的到2020年的減排目標,同時發展低碳經濟、應對全球氣候變暖,中國可以從以下方面努力:
(一)加快煤炭清潔技術的利用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2年,我國煤炭的消費量占能源總消費的66.6%,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煤炭的地位不會有太大變化。所以要加快發展煤炭的清潔技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吸取國外先進技術,進一步提高已研究出來的煤炭清潔技術效率,如發展空氣霧化水煤漿技術,利用煤粉、大量減少煤粉燃燒帶來的粉塵污染,經物理加工達到以煤節油、代油的目的;同時可以嘗試壓縮空氣來代替蒸汽作為霧化介質。
(二)加快新能源的開發使用
目前,我國在新能源利用方面有了很大進步,水能、風能、太陽能等均有使用,且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新能源技術也在不斷進步。但是總體上與發達國家相差較遠,平均技術水平比較低,也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弱。為了實現我國2020年的減排目標,應加快新能源技術的進一步開發,開發太陽能、生物質能等的利用,從根本上改變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
(三)建立與國際緊密合作的長效機制
單靠一個國家的力量是不能改變世界的,所以在碳減排的行動中,中國應該進一步加強與世界各國的緊密合作,把《京都議定書》真正貫徹到每個成員國的經濟發展任務中。同時,要加強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相關技術的支持,在國際中形成一個互動的良好氛圍,做到技術共享、資源共享;我國也要加快新能源技術的研發,既有創新又有吸收,推進碳減排工作的發展。
(作者單位:內蒙古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康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