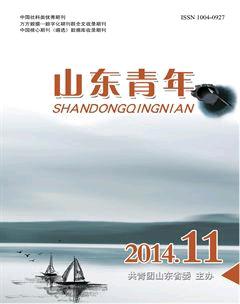被毀壞與壓抑的男性世界
柳曉曼
摘要:隨著女性主義的發展,近年來,女性的生存狀態已經受到了很大重視,但隨著女性主義的發展,在女性去追尋自我的情況下,男性的生存狀況,情感狀態也不得不引起重視。《嘉莉妹妹》和《再見,維羅妮卡》兩部作品中都塑造了這樣被所謂追尋自我的女性所拋棄的男性形象——赫斯渥和吉爾。這兩個男性形象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但無一例外他們都是女性主義發展狀況下的犧牲品。
關鍵詞:女性主義;“嘉莉妹妹”;“再見,維羅妮卡”
引言:
一八九九年的秋天,西奧多·德萊賽在半頁黃色抄寫紙上寫下“嘉莉妹妹”這幾個字,從而開始了他的第一部小說的創造,這部發生在美國的小說迄今已經有一百余年,盡管這部作品一直以來飽受非議,但始終是讀者愛不釋手的一部名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的獲得者讓—路易·居爾蒂斯在將近半個世紀以后也創作出一部名為《再見,維羅尼卡》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雖然沒有像德萊賽的作品《嘉莉妹妹》或者是居爾蒂斯后來的作品《夜深沉》那樣獲得廣大的社會影響,但它仍舊可以被評價為“現代西方婚姻生活的一面鏡子”①。
1. 女性主義視角下的作品分析
兩部作品都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即《嘉莉妹妹》中的嘉莉和《再見,維羅妮卡》中的維羅妮卡,而作品的成功也和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主人公形象息息相關,嘉莉妹妹百年來都是人們爭論不休的關注點,她的性格特征,她的美國夢的實現,她的種種抉擇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為不同國度,不同時間里的兩個女性,維羅妮卡的身上也有著和嘉莉相似的地方,“維羅妮卡既非浪女,也不是淑女,她身上的一些特點不一定就是缺點或者過錯,但也絕非優點和美德。她年輕,冒昧,活波,風姿綽約,憑著這些條件,她愛慕虛榮愛表現,不自覺地把生活當做自己進行表演的舞臺,近乎賣弄風騷。她明顯地不滿足于自己小家庭溫飽有余的小康生活,而懷著一種熱切的世俗的欲望,因此,面對著消費社會中不斷襲來的物質享受的熱潮,她自然地熱衷于精美的物質生活與時髦的生活方式,特別重視能保證所有這一切的金錢……這樣,她就不免陷于對奢華生活的渴望和期待……”①用這些對維羅妮卡的評論來分析嘉莉,似乎也沒有任何不妥之處,這兩部作品都塑造了為了夢想抑或是好的生活而“奮不顧身”的女性形象,但在數以萬計的分析評論這兩部作品的論文中,卻鮮少有目光投在作品中由于被這種女性的拋棄而導致的被毀壞與壓抑的男性世界,即《嘉莉妹妹》中的酒店經理赫斯渥和《再見,維羅妮卡》中維羅妮卡的丈夫吉爾,將這兩個在女性主義下“失語”的男性形象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社會發展過程中一些普遍存在卻未引起足夠關注的問題。
從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女性主義開始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初露端倪,無論是簡·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還是后來伍爾夫的《一件自己的屋子》,千百年來女性的生存,思想和情感狀況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大量的揭露和反應女性生存狀況,描寫女性追尋自我和獨立的作品出現并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平時生活在客廳和廚房里的“房間里的天使”們亦開始在這些作品的啟蒙下反思自己的生活狀況。一兩百年來,女性主義如火如荼地發展著,以至于到后來有一部分走向極端發展成了女權主義,面對女性研究的深入發展,在帶給女性諸多變化的同時,也使得男性的生存狀況變得岌岌可危起來。在女性對“奢華生活的渴望和期待”中,很大一部分男性由于無法滿足女性的追求,而遭到了決絕的拋棄。在一個畸形的女性依靠姣好的容顏和優美的體態就可以獲得生存和生活的社會里,在一個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環境下,一部分男性如赫斯渥一流成了“失語者”,他們在奉獻一切所能給與的之后依舊遭到了心愛女人的拋棄,最后只得郁郁寡歡,消散和溶解在這個依舊在迅速發展著的社會里,也有一部分如吉爾之流,頑強地用精神與這個物質社會進行著搏擊,發出自己反抗的聲音,然而這聲音同勢如破竹的女性主義者的聲音相比,太微不足道,最后也只得固守自己“被毀壞與壓抑的男性世界”。
2. 赫斯渥和吉爾的形象對比
德萊賽的作品《嘉莉妹妹》中赫斯渥真心深愛著嘉莉妹妹,自身的家庭出現情感危機之后,年輕美麗充滿活力的嘉莉妹妹猶如他黑暗生命中忽然出現的光明,他幾乎是用一種“誘拐”的手段騙走了嘉莉妹妹,并從自己先前任職的酒店偷走了一筆錢財帶嘉莉妹妹私奔到了紐約。然而在當時那個城市叢林法則至上的社會,性格柔弱的赫斯渥無法適應殘酷的優勝劣汰的社會現實,他從一個穩健而自信的酒店經理,急劇而驚人地變成了一個可憐而全然可鄙的畸零人,身無分文的赫斯渥當然無法滿足嘉莉妹妹虛榮浮夸的美國夢,最后也遭到了嘉莉妹妹的背叛,從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美國中產階級人士淪落為一個沿街乞討的乞丐,最終在絕望中用煤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再往前來說,赫斯渥在遇到嘉莉之前,自己的婚姻生活已經出現了問題,他的妻子自私貪婪,和那個時期的任何一個中產階級的女人一樣,過分注重物質享受而忽略家庭溫情,導致赫斯渥無法從家庭中獲得片刻的慰藉與溫情,便把目光轉向了年輕美麗的嘉莉。
吉爾不是赫斯渥一樣柔弱的性格,他的個性主要表現在對西方現代模式化的時髦生活潮流的鄙視,他依然故我,厭嫌周圍那些追逐銅臭與物質享受的人,他對維羅妮卡所熱衷的一切淺薄的時髦都很瞧不起:時髦的賺錢方式,時髦的交往方式,時髦的趣味,時髦的話題都使他反感。相比這些,他更喜歡關心精神層面的追求,喜歡關心人類的命運,對古典的文學藝術很感興趣。在人際關系中,他更傾心于淳樸自然地感情——家庭的感情,父女的感情,兄妹的感情,他認為一個人得到了這些感情便應該得到滿足,而不需要到世俗的熱鬧虛榮的社交生活中去尋找樂趣,更主要的是,他不愿意為了獲取金錢而犧牲人格獨立和個性獨立。這是一種與維羅妮卡一整套的愿望,理想,追求格格不入的人生態度。吉爾認為維羅妮卡“虛榮心重,庸俗,淺薄,空虛,貧乏”①,而吉爾在維羅妮卡的眼里則“保守,落伍,寒酸,沒有出息”①,這兩種人生觀的不同在作品開頭就從細節之處初露端倪,新婚的兩人在威尼斯度蜜月,他們沉浸在新婚的歡樂之中,然而他們的歡樂看起來只是以對方的容貌和肉體所給予的愉悅為內容,在兩人的談話中,便有隱隱的暗點出現在了新婚的一片玫瑰色之中,“告訴你,我想去!我要在一個晚上當當闊人,風光風光。”“要是不去餐館巴爾巴羅別墅的話,我想還是可以的……”“巴爾巴羅別墅有什么看的?”“那是帕拉第奧式的建筑,里面有壁畫,還是……”“算了,別去了!”②壁畫,建筑對維羅妮卡的誘惑比不上在高檔酒店住上一個晚上,“我寧愿在達尼埃利飯店住上一宿。咱們回去就說,旅行期間全是住在那兒的。”②這些暗點在開始時時隱時現,并未顯示出強大的力量,然而最終匯聚成為一大陰影,把這一對結合了的夫婦隔離開來:維羅妮卡遇到了能給與她好的生活的人,她離開了吉爾,義無反顧地向她所認為的富裕高貴的新生活奔去,“吉爾深愛她,了解她,雖然憂慮她的將來,卻無法不放手。”①
赫斯渥的人生以悲劇告終,在經歷著身無分文的落魄與失敗,被原先的好友孤立與拋棄之后,嘉莉的背叛仿佛是壓在駱駝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終摧毀了赫斯渥全部的精神,導致他在某一個夜晚開了煤氣自殺;而吉爾在尋求精神生活和物質追求的平衡的過程中并未找出什么有效的解決方法,他失去了自己摯愛的維羅妮卡,最后自己也落得吸毒,和頹廢的流浪青年為武的下場,雖然這些青年人的精神世界比維羅妮卡和阿麗亞娜之流要寬闊一些,雖然他們對社會問題的態度相當激進,但他們也并未找出合適的出口,也只是“頹廢而已。”從這個方面來看,這兩部作品在取了一個以女性主人公為名字的外表之下,講述的卻都是是男性在壓力重重的現代社會的悲劇,以及通過容易被我們在理解作品時所忽視的男性形象,來反抗這個早就男性“失語”“異化”和“畸零”的現代社會。
威廉·海涅曼在英國出版《嘉莉妹妹》的時候,把赫斯渥出場前的開頭的兩百頁刪掉成了八十四頁,因為他認為這部作品主要是講述赫斯渥的故事。然而,但弗蘭克·道布爾戴無可奈何地于一九零零年出版這部小說,要將書名改成《肉與靈》的時候,德萊賽卻堅持要保留原來的書名,這是正確的。德萊賽認為嘉莉不僅是赫斯渥驚人的毀滅的催化劑,而且也是人們生活中的最深刻的力量,他很自然地認為女人是具有這一作用的。赫斯渥和吉爾的命運沉浮是分別掌握在兩個女性,嘉莉和維羅妮卡的手里的,她們的每一個選擇都影響了這兩位男性主人公,甚至于在最后導致了兩個男人的悲慘命運。
3. 男性“失語者”的擴展研究
當然,將過錯歸結于兩個女性身上并不正確,無論是在十八世紀的美國還是在十九世紀的法國,資本主義社會所展露出來的都是一種“消費社會中物質享受的熱潮”,女性在走出家庭去追尋成功和夢想的同時,難免會受到這股熱潮的沖擊,嘉莉渴望走進上流社會,維羅妮卡熱衷于提高物質生活和消費水平,她們都年輕美麗而充滿活力,有著吸引男人的特質,在城市叢林法則的殘酷現實下,獲得好的生活對于她們來說相對容易,而受到物質享受與虛榮生活沖擊的她們便會在讓人眼花繚亂的社會中做出最現實的選擇,一批新的男人成為新的選擇對象,便會有一批男人成為淘汰的對象,這種模式在并非是過去的《包法利夫人》《嘉莉妹妹》《還鄉》中存在,也在現在社會的《再見,維羅妮卡》《跳來跳去的女人》中存在,不僅存在于當今的西方社會,也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的發展過程中也以一種迅猛的姿態發展開來,并形成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近兩年熱播的電視劇《北京愛情故事》《我們生活的年代》中都塑造出了諸如此類的人物形象。
德萊賽和居爾蒂斯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的存在,他們用兩個不同性格特征,不同身份地位,不同人生觀的男人的相似經歷,來讓我們注意到了在女性研究蓬勃發展的同時,在人們過多地關注女性生存境遇和命運的同時,女性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主動權,這種主動權的掌握和整個社會的畸形發展造就了男性的生存壓力,讓他們成為了家庭和社會生活中的“失語者”。
和幾百年前的美國社會,幾十年前的法國社會相比,現代社會更加險象叢生,女性的選擇更加多遠和便捷,婚姻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固性更加凸顯。如何在一個險象叢生的社會保留住關于愛情和婚姻的棲息地,如何在關注女性生存狀況和精神困境的同時注意到男性在現代社會的窘境,這不僅是西方社會,也是我們現在要面臨的共同課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嘉莉妹妹》和《再見,維羅妮卡》留給我們的還有更加深刻的啟迪作用。
[參考文獻]
[1]柳鳴九(2010)《當代西方婚姻問題的一面鏡子》[J]。
[2]路易-居爾蒂斯(Jean-Louis Corties)、李玉民 《再見,維羅妮卡》 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 (2010) 。
[3]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裘柱常(2011) 《譯文名著精選:嘉莉妹妹》 上海譯文出版社。
[4]王鋼華 (2010)《嘉莉妹妹的欲望和驅動力》《外國文學研究》。
[5]王艷峰.(2009).《從依附到自覺: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