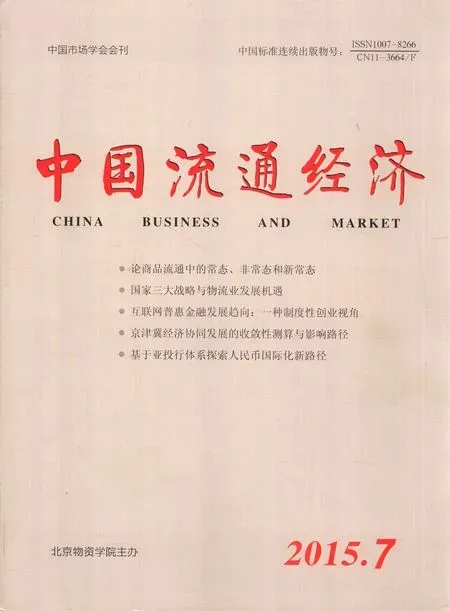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的收斂性測算與影響路徑
吳蒙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天津市300071)
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的收斂性測算與影響路徑
吳蒙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天津市300071)
本文從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性測算這一角度,對三地協同發展的演進特征及影響因素進行了闡述。研究表明,從1995—2013年的較長時期看,京津冀總體上呈現經濟發散趨勢,但其間經歷了收斂—發散—再收斂三個階段;從影響因素看,京津冀地區存在生產要素配置失衡、國有企業比重過高以及產業同構與結構梯度差異并存等問題。三地經濟協同發展的突破路徑主要在于推動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加快市場化進程以及合理的產業轉移和錯位發展。
京津冀;協同發展;收斂性
一、引言
當前,我國經濟已步入中高速增長期,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已上升為國家戰略,主要目的是尋求動力轉換期的新經濟增長點。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思路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但時至今日仍然進展不大,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尚未形成特色鮮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特征,首都北京“燈下黑”的區域極差現象一直受到詬病。那么長期以來,京津冀經濟發展是否具有收斂性,是哪些因素影響著京津冀三地的協同發展,這將是本文探索的問題。
我國區域經濟收斂性的研究由來已久,從全國省級地區收斂性研究看,宋學明[1]在研究中發現,利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變異系數測度的1978—1992年我國各省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斷縮小,但基尼系數在1983年后由于人口因素的影響而出現增長趨勢。魏后凱[2]使用巴羅和薩拉-伊-馬丁(Barro&Sala-i-Martin)的分析方法,檢驗了1978—1995年我國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各地區人均GDP以每年2%的速度收斂,同時發現在1978—1985年各地區經濟收斂速度相對較快,而1985—1995年期間則不存在顯著的收斂性。林毅夫等人[3]認為在1990年以前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呈現收斂趨勢,但在1990年后開始迅速發散。從三大經濟區域的收斂性看,馬國霞等[4]將空間項加入到傳統收斂模型中,對京津冀地區的區域經濟收斂機制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在1992—2003年間京津冀地區的經濟增長存在收斂趨勢,但區域內部仍存在較大差異,收斂率較低。孫洋[5]綜合考察了1990—2006年的三大經濟區域經濟增長的收斂性,發現長三角和環渤海區域在1990—1998年期間存在顯著的條件β收斂,而珠三角收斂趨勢不明顯,在1998—2006年三大區域都沒有條件收斂的情況,同時他得出產業結構調整是實現經濟收斂重要原因的結論。張學良[6]在對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作用機制的研究中發現,物質資本積累是促使該地區經濟增長差距縮小的最主要因素。董冠鵬等[7]認為京津冀地區已經形成了以北京、天津和唐山為核心的中心區域和以張家口、保定為核心的外圍區域,在京津冀中心區域存在著速度較快的經濟收斂,而外圍區域則不存在經濟收斂。鄧慧慧[8]利用協整分析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進行研究,認為長三角區域和珠三角區域具有內部收斂趨勢,而環渤海區域內不存在收斂趨勢。無論是對全國范圍的研究,還是具體針對三大經濟區域的研究,收斂性的影響因素大致包括生產要素、發展環境、效率等方面,生產要素主要包括人力資本、就業率和投資率等,發展環境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市場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城市化程度等,效率類因素主要涉及投資效率、全要素生產率、資本積累速度等內容。[9-10]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首先采用絕對收斂分析方法對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性的階段性特征進行判斷,然后按照階段劃分,從生產要素、所有制和產業結構等三個視角,采用β條件收斂模型分析這些因素對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的作用程度和方向。通過上述分析,一方面深入探索京津冀經濟收斂性的演進特征和規律,彌補這方面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結合京津冀地區國企多、產業結構趨同等現實問題,分析各種因素對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的影響路徑。
二、檢驗方程與數據說明
最早將經濟收斂性納入研究范疇的是新古典增長理論。該理論認為各個經濟體人均收入的差異會導致不同的經濟增長率,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增長率的差異有可能會消失。巴羅和薩拉-伊-馬丁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框架下,對經濟收斂性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他們將收斂假說區分為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收斂(σ收斂)和經濟增長率上的收斂(β收斂),并且把β收斂區分為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11-12]
1.檢驗方程
(1)σ收斂。根據薩拉-伊-馬丁[13]的定義,σ收斂是指隨著時間的變化,經濟體的人均GDP的標準差逐漸縮小,人均GDP表現出趨同。σ收斂可以直觀地度量不同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差距,最接近現實中對于收斂的直觀理解。在實際計算時,一般以人均GDP對數的標準差計算σ值:

式(1)中n為經濟體個數,Xi為第i個經濟體人均GDP的對數值,為其均值,σ為收斂系數,σ越小說明收斂性越強。
(2)絕對β收斂。絕對β收斂假設在封閉的經濟體內經濟系統各項參數均相同的條件下,經濟體具有相同的增長路徑和穩定水平,經濟增長率和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絕對的負相關關系,即落后經濟體擁有比發達經濟體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的經濟增長都將收斂于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該方法只是檢驗人均GDP與經濟增長率間的線性關系,與σ收斂分析方法一樣沒有考慮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設yit表示第i個經濟體在第t年的人均GDP向量,它在第t年到第t+T年間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向量為git,t+T= ln(yit+T/yit),則絕對β收斂檢驗方程為:

式(2)中α為常數項,β為收斂系數,εit為隨機擾動項,一般假定εit在不同經濟體之間是獨立分布的,均值為零。如果參數β小于0,就稱這n個經濟體間呈現絕對β收斂,β值越小,收斂越強,其收斂速度為-ln(1-β);若β大于0,則表示這n個經濟體的經濟趨于發散。
(3)條件β收斂。條件β收斂是在絕對β收斂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放松假設條件,加入了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外生因素。條件β收斂認為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不同的初始條件,各項經濟參數也不盡相同,各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僅取決于人均產出,還要受到要素稟賦、產業結構等其他因素的影響。落后經濟體只有在滿足一定的必要條件下才能實現比發達經濟體更快的增長,從而使各經濟體的人均GDP增長率與其初始水平呈現負相關關系,達到經濟收斂的目標。這種方法考慮了經濟增長的復雜性,更符合經濟增長的現實。檢驗條件β收斂的方法是在絕對β收斂模型中加入相應的控制變量,條件β收斂檢驗方程為:

式(3)中git,t+T、yit和β與絕對β收斂的設定相同,Xit為影響經濟增長的控制變量組成的向量,Γi為控制變量的待估系數向量。控制變量的加入表明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不同的特征,這些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增長差距將長期存在。
薩拉-伊-馬丁[14]還在研究中證明了σ收斂與β收斂存在一定的一致性。σ收斂檢驗的是地區收入差異隨時間的變化,而β收斂研究的是在相同條件下收入的流動問題,β收斂是σ收斂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即落后經濟體的高速增長能夠降低經濟體之間人均收入的差異,但其他因素的影響會抵消這一過程的作用。
2.數據說明
本文涉及的基本變量為人均GDP及其增長率,其中人均GDP是利用1995年不變價格計算得到的實際人均GDP。影響經濟收斂性的因素很多,最常使用的是資本要素指標,包括投資和人力資本兩種形態。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由資本拉動,但在經濟轉型期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日益顯現,人力資本作為研發中的關鍵投入會促使新產品和新思想的產生,并最終導致技術進步。[15]另外,經濟的開放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高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技術擴散,從而決定收斂速度的快慢。[16]本文分別使用投資率、人力資源水平和外商投資比重來測度投資、人力資本和開放程度。其中投資率(Inv)即各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人力資源水平(Hum)由各地區科研活動人員數占總人口比重表示;外商投資比重(FVG)以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重來衡量。從所有制角度來看,國有化程度與市場化水平關系密切,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仍然是我國目前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這不僅關系到市場競爭水平的高低,而且對我國地區經濟增長、縮小經濟發展差距的作用也至關重要,本文使用的國有化程度(Mar)由各地區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占全部工業總產值比重表示。產業結構因素是本文重點考察的一個影響因素,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能力,從而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收斂性,本文的產業結構控制變量分為工業和服務業兩個方面,其中工業劃分為資源加工業、輕工業、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四個行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分為I1、I2、I3、I4;①服務業結構變量(S)由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
本文所指京津冀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其基礎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6—2014)、三省市統計年鑒(1996—2014)、《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1996—2014)、《中國高技術統計年鑒》(1996—2014),樣本期間為1995—2013共19年。
三、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性檢驗
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性的檢驗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利用σ收斂方法進行一般化考察,確定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的階段性特征,并使用絕對β收斂模型驗證σ收斂劃分方法的準確性,為之后的分段分析提供依據;然后,利用條件β收斂模型考察各影響變量對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的作用。
1.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的階段性特征
根據公式(1)考察京津冀地區人均GDP是否存在σ收斂的問題,1995—2013年的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

圖1 1995—2013年京津冀地區實際人均GDP對數值標準差
觀察圖1可以發現,京津冀地區實際人均GDP對數值的標準差在0.46~0.54之間變動,存在著一定的波動性。從基本的變動趨勢來看,在整個研究期間京津冀地區具有一定程度的收斂趨勢,而2000年和2004年前后三地的經濟增長差距的基本特征出現了轉變,在2000年由收斂轉變為發散趨勢,而在2004年則由發散趨勢向明顯的收斂方向變化。由此,可將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性的變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1995—2000年、2001—2004年以及2005—2013年。為保證以上階段劃分的合理性,根據公式(2)提供的絕對β收斂檢驗方程,使用Eviews7.2的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對σ收斂方法得到的階段劃分結果進行驗證,經檢驗得到的計算結果見表1。
如表1所示,1995—2013年期間β系數符號為負,說明京津冀地區存在絕對β收斂,收斂速度為0.46%,這與前面對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性的σ收斂檢驗結果相同。同時,不同的發展階段又具有不同特點。分階段看,1995—2000年京津冀地區的經濟差距存在縮小趨勢,收斂速度為0.63%;2001—2004年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出現了明顯的發散趨勢,發散速度為6.53%;從2005年開始,京津冀地區重現經濟收斂趨勢,這個階段的收斂速度為4.99%。京津冀地區的經濟收斂性之所以出現這種階段性的變化,主要是由于在2000年之前我國正處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各地區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為京津冀三地之間的經濟差距縮小創造了條件;進入2001年,京津冀三地的經濟增長差距逐漸顯現,雖然三地實際人均GDP都處于上升趨勢,但河北省的人均實際GDP一直處于下游水平,遠遠低于北京和天津兩市,這就造成三地經濟發散狀況的出現;2004年天津的實際人均GDP水平超過北京,改變了三地一直以來的經濟格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三地從2005年開始出現的經濟收斂趨勢。
三個時間段的絕對β收斂檢驗的變動趨勢均驗證了前文對京津冀地區σ收斂的考察結果。因此,本文將按照這三個階段對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的階段性特征進行研究。
2.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的影響因素分析
(1)要素和所有制因素的影響。在絕對β收斂模型中加入投資率(Inv)、人力資源水平(Hum)、外商投資比重(FVG)和國有化程度(Mar)等控制變量,利用公式(3)考察要素和所有制影響變量對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性的作用,條件β收斂檢驗結果見表2。

表1 1995—2013年京津冀地區經濟增長絕對β收斂檢驗
與絕對β收斂的檢驗結果類似,1995—2013年京津冀地區經濟增長在加入要素和所有制影響變量后呈現一定程度的發散態勢,而影響因素變量的加入,對京津冀地區的收斂方向和速度產生了一定影響。
從資本要素來看,投資率因素對推動京津冀地區的經濟增長起到積極作用。根據投資率的實際數據,1995—2000年期間京津冀各地投資率沒有太大的改變,其中北京的投資率最高,一直保持在50%以上但有下行趨勢,天津保持在40%左右,河北保持在30%~40%之間。2005年三省市的投資率基本持平,從2006年開始天津與河北的投資率超過北京,在2013年河北的投資率達到了接近82%的峰值。這說明近年來京津冀一體化進程為天津與河北兩地提供了眾多新的投資機會,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

表2 1995—2013年京津冀地區經濟增長要素和所有制的條件β收斂檢驗
從人力資本要素來看,人力資源是制約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一方面,京津冀地區人力資源分布極為不平衡,其中北京地區的人力資源極為豐富,1995—2013年北京科技活動人員占地區總人口的平均比重為2.07%,分別是天津的2.34倍、河北的11.48倍,各地人力資源比重與北京的巨大差異顯然對整個地區經濟增長的收斂產生潛在的瓶頸作用;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區人力資源缺乏流動性影響到京津冀地區一體化進程。但同時,2005年這種局面開始扭轉,2005—2013年人力資源水平的系數顯著為正,對經濟增長開始發揮正向作用,這主要得益于京津冀三省市對人才流動與共享的重視和為加快推進京津冀人才開發一體化進程所作的努力。
從外商投資比重來看,外商投資水平對京津冀地區經濟協同發展的促進作用正在逐漸弱化。1995—2000年期間各地區外商投資占GDP的年均比重為7.27%,2000年以后開始降低。雖然這一指標在2005年后有所改觀(4.21%),但仍未恢復到1995—2000年期間的高位。近年來我國土地和人口紅利日益趨弱,外國企業的投資逐漸向東南亞國家轉移,加之2008年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的實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京津冀地區外商投資的減少。同時,在京津冀三省市內部,外商投資的差距依然很大,在整個考察時期,北京和天津的外商投資年平均比重分別為4.71%和8.94%,而河北省只有1.48%。雖然京津冀地區是全國開放程度和外商投資較高的地區,但由于河北省與京津兩地投資環境一體化程度較低,不能共享京津的開放市場資源,影響了京津冀地區的經濟增長和一體化進程。
從所有制因素來看,國有化程度對京津冀地區經濟增長保持正向作用。實際上,京津冀地區的國有經濟比重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95—2000年該指標平均值達到50.53%,2001—2004年降低至45.45%,2005—2013年期間進一步下降到39.42%。伴隨京津冀地區國有企業比重的下降,落后產能得以淘汰,優質資源逐漸向國有企業集聚,提高了京津冀地區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和管理水平,京津冀地區國有企業的競爭力不斷提高,國企戰略性結構調整已經產生了積極效果;同時國有化程度的降低說明民營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2)結構因素的影響。為了進一步考察結構因素對地區經濟增長收斂性的影響,將I1~I4和S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公式(3),主要分析資源加工業、輕工業、裝備制造業、高技術產業以及服務業的結構性變動對京津冀地區經濟增長收斂性的影響,條件β收斂檢驗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在整個研究期內β系數為正,說明在結構性因素影響下1995—2013年京津冀地區的經濟增長呈現發散趨勢,發散速度1.85%。分階段的變動情況與要素和所有制的條件β收斂情況類似。造成京津冀地區結構性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區服務業發展失衡,而工業在全時期推動了京津冀地區的經濟增長,其中以輕工業、高技術產業工業的貢獻為主,資源加工業與裝備制造業的作用次之,這也反映了我國處于工業化階段、工業仍然是支撐經濟增長主要力量的現實;從分段考察結果來看,某些工業行業在有些階段對經濟增長未能發揮正向作用,這體現了京津冀地區工業內部長期存在的一些問題。

表3 1995—2013年京津冀地區經濟增長結構因素的條件β收斂檢驗
首先是資源加工業比重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河北省,其資源加工業占比一直在40%左右。而資源加工業受到資源稟賦的限制以及高污染、高能耗的環境壓力,需通過資源深加工和延伸產業鏈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其次是裝備制造業在三省市的分布不均。近年來北京的裝備制造業發展迅速,而天津與河北省比較穩定,且河北省一直在較低水平徘徊。三是與京津相比,河北省的高技術產業比重嚴重偏低。1995—2013年北京和天津的高技術產業平均比重分別為26.75%和20.30%,而河北省只有3.48%。高技術產業對京津冀地區經濟的作用主要依靠京津兩地,對河北省的帶動作用不明顯。
與工業各分行業對經濟增長收斂影響完全相反,服務業的阻礙作用在整個時期十分明顯,但2005年這種阻礙作用開始改變。服務業阻礙作用產生的原因,主要是京津冀區域的第三產業發展極不平衡,1995—2013年北京服務業比重平均為71.13%,天津以43.63%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0.12%),而河北省只有33.78%。而且在整個研究期間,只有北京的服務業比重呈現逐年遞增趨勢,天津和河北省的服務業比重沒有明顯的上升。京津冀地區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導致高水平的分工協作難以有效實現,同時北京作為京津冀地區現代服務業中心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對周邊地區服務業水平提升的帶動作用不足,這都導致京津冀地區服務業難以實現對本地區經濟增長的推動。
四、結論與建議
第一,京津冀地區在資本、人力、技術等生產要素的配置上極不均衡,推動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協同發展的基本前提。在投資方面,把握京津冀區域交通一體化、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科技協同創新等有利契機,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投資來源,實現資金的統一調配與合理使用,并適度向河北省傾斜;在人力資源培養與共享方面,要依托京津教育優勢,完善區域教育合作機制,發揮京津優質教育資源的輻射帶動作用,幫助河北省提高教育水平,同時建立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搭建區域人力資源信息共享與服務平臺,完善人力資源流動政策;在科技創新方面,要明確京津冀三地科技創新優先領域,重點發揮北京原始創新和技術服務能力、天津應用研究與工程化技術研發轉化能力以及河北省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和示范推廣能力,推進三地技術市場一體化建設,完善科技成果轉化和交易信息服務平臺,將北京的科技資源和成果向津冀輻射,加快科技成果在京津冀地區的轉化速度。
第二,京津冀地區國有企業比重過高,加快市場化進程是協同發展的重要突破口。國有企業比重過大意味著市場不完全特征或壟斷因素存在,會導致企業交易成本增加,難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可以通過建立內部市場體系,用企業管理機制替代市場機制進行資源配置和區際產業轉移過程,從而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獲得跨區域經營的內部化優勢。同時通過多途徑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境外投資者參股國有企業,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引導國有資本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重要資源開發、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
第三,京津冀地區產業同構與結構梯度差異并存,合理的產業轉移和錯位發展是縮小地區差異的核心內容。根據京津冀三地的城市功能定位,北京將去經濟中心化與建設津冀產業承接平臺,推動京津冀三地產業的有序轉移承接,北京的產業發展主要定位于服務經濟、知識經濟、總部經濟和綠色經濟;天津則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河北省在承接北京產業功能轉移、改造提升傳統優勢產業的基礎上,推動產業優化升級,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此分工基礎上逐漸形成京津冀三地明確有序的分工格局,同時加強三地在制造業、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方面的產業協作,提升京津冀三地的區域產業競爭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非均質后發大國中經濟極化、區域互動與協調發展的路徑選擇研究”(項目編號:11YJC790307)、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京津同城化發展的對策研究”(項目編號:TJYYWT1401)的部分成果。
注釋:
①資源加工業包括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石油加工業、煉焦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輕工業包括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煙草制品業、紡織業、造紙及紙制品業,裝備制造業包括金屬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高技術產業按照《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的統計分類包括醫藥制造業、航空航天器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等。
[1]宋學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及其收斂性[J].經濟研究,1996(9):38-44.
[2]魏后凱.中國地區經濟增長及其收斂性[J].中國工業經濟,1997(3):31-37.
[3]林毅夫,劉明興.中國的經濟增長收斂與收入分配[J].世界經濟,2003(8):3-14,80.
[4]馬國霞,徐勇,田玉軍.京津冀都市圈經濟增長收斂機制的空間分析[J].地理研究,2007(5):590-598.
[5]孫洋.產業發展戰略與空間收斂: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區域增長的比較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09(1):46-59.
[6]張學良.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及其作用機制:1993—2006[J].世界經濟,2010(3):126-140.
[7]董冠鵬,郭騰云,馬靜.空間依賴、空間異質與京津冀都市地區經濟收斂[J].地理科學,2010(5):679-685.
[8]鄧慧慧.中國三大都市圈經濟增長趨于收斂還是發散?——基于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J].城市發展研究,2011(11):70-73.
[9]蔡昉,都陽.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趨同與差異[J].經濟研究,2000(10):30-37.
[10]沈坤榮,馬俊.中國經濟增長的“俱樂部收斂”特征及其成因研究[J].經濟研究,2002(1):33-39、94-95.
[11]Barro R.J.,Sala-i-Martin X..Convergence across States and Regions[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1(1):107-182.
[12]Barro R.J.,Sala-i-Martin X..Convergenc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2(2):223-251.
[13]、[14]Sala-i-Martin X..Regional Cohesion:Evidence and Theories of Regional Growth and Convergence[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6(40):1325-1352.
[15]Romer P.M..Endogenous Technical Chang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98):71-102.
[16]Barro R.J.,Sala-i-Martin X..Technological Diffu?sion,Convergence,and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7(5):1-26.
責任編輯:方程
Study on Econom ic Grow th Convergence and Influence Path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WU Meng
(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Based on themeasurementof econom ic convergence,the authors discuss the evolution feature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long period from 1995 to 2013,the region of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hasundergone such three stagesof convergence,unconvergence and converge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m is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elements,high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coexistence of industry isomorphism and gradient difference are the main problems.The breakthrough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mainly lies in rational flow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acceleration ofmarketization process,developmentof industrial transferand dislocation.
the region of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coordinated development;econom ic convergence
F127
A
1007-8266(2015)07-0088-07
吳蒙(1985—),女,河北省唐山市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