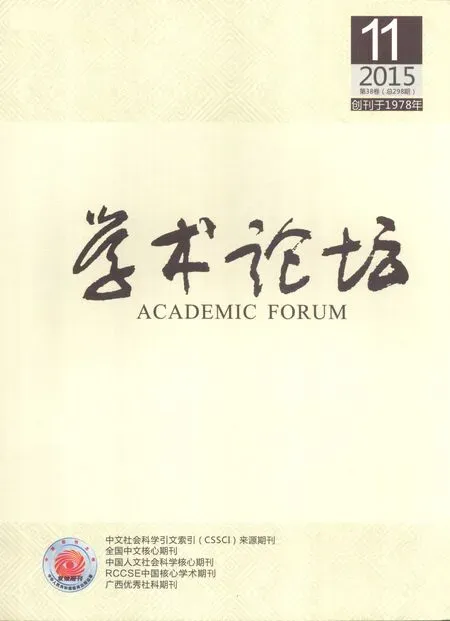基礎設施對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基于空間面板杜賓模型的研究
王 娟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新絲綢之路建設是我國向西尋求發展空間的戰略需要。 “絲綢之路”戰略的核心是加強中國與相關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將分別打通中亞、東南亞和我國主要的經濟區域。 “絲綢之路經濟帶”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其建設有助于加強我國同臨近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保障能源安全也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題中之義,建設經中亞、東南亞國家通往內地的能源運輸路線和油氣管道有助于緩解我國能源進口嚴重依賴途徑馬六甲海峽的海上運輸風險,有助于提高我國的能源安全。 此外,我國西北、西南地區相對沿海地區而言,資源豐富而基礎設施較差,經濟落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能夠緩解當地資源產出豐富而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在全國層面進一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絲綢之路經濟帶”帶來的經濟紅利,也能夠由道路網路輻射周邊地區,拉動沿線經濟發展。對于中國來說,如何擺脫傳統低附加值產品出口的困境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重要課題,“一帶一路”將深挖我國的潛力。例如,我國通過提升產品檔次,提升高端裝備出口規模,將會延續中國出口的競爭力,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可靠的動力。從絲綢之路經濟帶涉及的國家看,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基礎設施普遍薄弱,急需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
大部分針對基礎設施投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作為一種社會先行資本,基礎設施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前提條件,具有外部溢出效應和正外部性 (Eisner,R. ,1991;Holtz-Eakin,1994;Munnell,1992;Hulten,C.2006 )[1][2][3][4],運輸和通訊部門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非常大。Hulten,C.(2006)通過對104 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存量(鋪設公路和鐵路的公里數、電話門數等)的物質估計方法解釋了其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也證實了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國內相關研究也比較多,劉勇(2010)[5]利用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公路水運交通的固定資本存量對中國經濟增長有空間溢出作用,但是隨著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會產生諸如擠出效應等,由此孫早等(2014)[6]認為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倒U 型關系,超過拐點以后,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會大幅減少。 在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同時,基礎設施建設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作用也有部分文獻提及。 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作用體現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基礎設施的發展,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交易障礙,促進貿易的發展。 當然貿易與投資是相輔相成的,貿易和投資的增加促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新貿易理論和新發展經濟學對此都有相關的理論概括。 在實證研究上,國內研究大多針對的是基礎設施建設對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如劉生龍和胡鞍鋼(2011)[7]利用2008 年中國交通部省際貨物運輸周轉量的普查數據,驗證交通基礎設施對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對中國的區域貿易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促進作用。 張美濤(2012)[8]、劉育紅(2014)[9]等研究了基礎設施建設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
整體來看,國內外關于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較多,而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影響的研究較少,僅有的研究也大多對國內區域一體化的視角進行分析,跨國的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研究尚沒有看到。 對于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研究來看,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上。 本文從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視角,分析了基礎設施投資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為促進中國對外開放程度和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提供一種可能的途徑。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測算
(一)測度方法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指標較多,Harris (2000)認為除貿易一體化、投資一體化、金融一體化等外,還包括基礎設施的交通流量、電訊流量、電子郵件流量等。 當然本文的研究中后者屬于基礎設施的指標,我們采用簡單的貿易強度的計算公式,雙邊貿易強度為:

wtt(i, j)為i 國與j 國之間的雙邊貿易強度,右邊的等式是用兩國之間的貿易額除以兩國全部的貿易額,指標數值越高說明雙邊貿易強度越大,兩國的貿易聯系越緊密,一體化程度較高。
根據上述公式,我們還可以設計多邊貿易強度為:

(二)絲綢之路經濟帶經濟一體化程度測度
根據這個公式,我們計算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一體化程度。 對于新絲綢之路涉及到的國家,目前尚沒有統一的界定,古絲綢之路分成不同方向,而現在很多國家經過了變化。 自從中國提出了新絲綢之路以來,得到了中亞、西亞、中東歐和西歐各國的響應,截至2015 年初,已有50 多個國家參與新絲綢之路的建設。 但從實際來看,基礎設施投資尚不足,2007 年我國與中亞七國計劃共同投入192 億美元建設“現代絲綢之路”,2008 年我國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及中亞四國聯合發起絲綢之路區域項目,再為復興絲綢之路投入430 億美元。 因此,我們把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分為3 組:第一組為上海合作組織6 個國家: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第二組是在第一組6 國基礎上再加上土庫曼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總共10 個國家;第三組是在第二組10 國基礎上再添加蒙古、阿富汗、緬甸和土耳其。 當然,我們的研究集中在中亞和南亞國家,西亞國家較少涉及,歐洲國家也沒有包括在內,這主要是基于中亞和南亞國家基礎設施落后,投資于基礎設施的邊際收益較高,也能更好地促進中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水平,再加上這些國家是中國重要的基礎原材料來源國,也是未來中國產品出口的重要市場[3]。

圖1 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三組)
從圖1 的走勢可以看出,三組指標都顯示向上的趨勢,表明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越來越高,但是從總體數值來看,高峰值只有0.3,絲綢之路經濟帶一體化程度難以和發達區域一體化相比較,比如東亞、東南亞、南美和北美等地區,這也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經濟聯系并不緊密。 從實際來看,中亞和南亞等都不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對象,中國出口最多的區域是歐盟、東亞和北美等地區,進口最多的是東南亞、非洲和南美洲等地區,中國與中亞、南亞的經濟聯系主要表現在這些地區是中國的能源和原材料來源地,中國從中亞地區進口能源(原油和天然氣),從南亞地區進口礦產和其他原材料[4]。 而中亞和南亞地區由于經濟并不發達,內部貿易聯系并不緊密,所以整體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并不高。 從三組數據來看,中國與上海組織其它國家的貿易聯系程度較高,這些國家是中國非常重要的能源基地, 也是中國產品出口有潛力的地區,包括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都是中國原油和天然氣的重要來源,中俄雙邊貿易額接近1000 億美元,中國是俄羅斯最大的貿易伙伴,俄羅斯是中國第九大貿易伙伴,中國也是哈薩克斯坦最大的貿易伙伴。第二組中加入的這些國家與中國的貿易聯系也非常緊密,只是在第一組中因有俄羅斯的存在而使指標表現較高。 第二組的印度、 巴基斯坦等與中國的貿易關系也非常緊密,中國是印度、伊朗等最大的貿易伙伴。 第三組加入的國家大多比較落后,對外貿易聯系較少,整體貿易規模小,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較低[5]。
三、基礎設施建設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影響的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定
國內外關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一般是從制度因素分析的傳統計量模型入手,筆者引入基礎設施變量:



空間權重構建方法為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根據兩地之間的地理距離的倒數決定,其假設前提是空間距離隨著距離增加而減少,地理距離是按照兩國首都之間的經緯度的地標距離,這種方法計算簡單而且有效。
(二)變量的選取和數據說明
基礎設施:基礎設施包括的范圍比較廣泛,如交通基礎設施(鐵路里程、公路里程)、信息基礎設施、能源基礎設施等。 我們構建了一個基礎設施指數,主要包含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鐵路里程、人均電力、人均電話擁有量等變量。
對外開放度: 用進出口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
財政支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政府財政支出越多,表明用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金額越多。
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區間為1995年到2013 年,涉及到上文中論述到的14 個國家。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世界經濟發展指標。
(三)空間相關性檢驗
采用空間面板杜賓模型分析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基本形式為:


空間自相關檢驗:各年度的基礎設施和一體化的Moran 值均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基礎設施與一體化之間存在自相關,運用空間計量模型是合適的。然后筆者通過似然比檢驗和wald 檢驗,結果顯示LM Error 值和Robust-LM Eorrer 值分別為3.45 和6.78,均在1%水平下顯著,拒絕原假設,使用選擇空間面板迷行是合適的。 絲綢之路經濟帶涉及到的國家為14 個,樣本數較少,經Husman 檢驗,我們選擇固定效應模型,然后采用動態廣義矩估計法對模型進行估計,空間面板杜賓模型為:

θ 為控制變量系數。
(四)實證檢驗結果
我們實證檢驗考慮空間效應下的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模型1、模型2 和模型3分別對應的是RSEQ6、RSEQ10 和RSEQ14 三組的檢驗結果。
1.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溢出效應。 從W*dep var(REI)的檢驗結果看(見表1),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空間溢出效應,但是方向是負的,這和傳統的貿易理論是相符的。 貿易理論認為,自貿區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具有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 貿易創造效應來自于區域內國家的貿易會增加,而貿易轉移效應來自于減少外部的貿易活動。 雖然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沒有成立自貿區,但在資源既定的背景下,中國對某一國原油或天然氣等原材料需求的增加, 相應的就會減少其它國家的進口。 2008 年之前這種表現并不明顯,因為中國需求顯得無限大,區域內的國家都可以獲得中國足夠多的需求訂單,但隨著中國經濟放緩,對原材料需求下降,這種負的效應就尤為明顯[4]。
2.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直接效應。實證結果顯示,FR 在三個模型中都顯著,且符號為正,表明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運輸設施、電信通訊設施等。 交通運輸設施的發展可以降低運輸成本,擴大雙邊和多邊貿易規模,特別是原油天然氣運輸管道的建設。 中國進口的原油和天然氣來自中東和非洲地區,主要依賴船運,而來自俄羅斯和中亞地區的石油和天然氣,以前主要靠鐵路,目前依賴管道運輸,比如2011 年中俄原油管道建成,目前年輸油1500 萬噸,而中國從俄羅斯年進口原油大約為2300 萬噸,可見能源運輸管道的建設對中俄貿易的影響之大,而原油貿易占俄羅斯對華出口金額的40%以上。 中國首條跨境原油運輸管道——中哈石油管道管自2006 年運營至2014 年底,累計進口原油7523.82 萬噸。2014 年,中哈原油管道進口原油1205.37 萬噸, 哈薩克斯坦對中國原油輸出全部為管道運輸,哈薩克斯坦對中國出口中原油占到50%以上。 其它中亞國家、緬甸、蒙古等也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有效地促進了區域貿易的發展。
3.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空間溢出效應。 從表1 可以看出,基礎設施的空間效應會顯著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水平。 而且我們對影響系數與直接效應的系數進行了對比,可以看出空間溢出效應的系數大于直接效應的系數。 一國基礎設施的完善可以促進其經濟發展,帶動需求的增加,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依賴原材料進口的國家來說,世界第一大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需要充足的原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等原材料的供給,帶動了對中亞、南亞國家此類產品對中國的出口,增加了雙邊貿易額,促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5]。
4.在其他因素中,對外開放程度和財政支出都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有促進作用。對外開放程度較低時, 表示進出口規模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較低,表明對外貿易聯系程度差,關稅等貿易壁壘的程度也較大,隨著各國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入WTO 等貿易便利化的實施,對外經濟聯系程度越來越高,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也增加。而財政支出的結果顯示財政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區域經濟一體化。

表1 區域經濟一體化影響因素的空間權重矩陣模型回歸結果

(續表)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而基礎設施包含的范圍比較廣泛,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郵電、供水供電、商業服務、科研與技術服務、園林綠化、環境保護、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等市政公用工程設施和公共生活服務設施等。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上,按照中國的規劃,交通運輸設施是關鍵,需要大量建造鐵路、公路、管道等。 我們實證檢驗者三種運輸方式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檢驗的樣本為上海合作組織6 國。
從表2 檢驗結果看,不同交通運輸方式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是不同的。 就目前而言,影響最大的是管道運輸,這主要是由于中國與中亞四國及俄羅斯的貿易結構不同造成的,中國從這些國家進口的主要產品是原油和天然氣,占總進口的比例高達52.3%,基本上都是通過管道運輸。 影響第二大的是鐵路運輸,最后才是公路運輸。 中國與俄羅斯其它貿易產品主要通過遠東鐵路進行運輸,與中亞四國的貿易依賴公路。 整體來看,鐵路和公路的運輸能力有待提高。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如何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快速發展,目前學術界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的作用,我國也通過一系列實踐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基礎設施的發展。 但是基礎設施到底對區域經濟一體化起到什么作用,哪些類別的基礎設施需要優先考慮? 筆者依據1995 年到2013 年的數據,基于空間溢出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基礎設施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一體化的作用。 主要結論如下:一是基礎設施可以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一體化的發展,但是作用不可高估。 近年來中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其它國家的經貿聯系越來越緊密,貿易規模逐漸擴大,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逐漸提高。 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也取得可長足進展,中國與世界銀行以及這些國家也都加大了運輸、電力網絡、信息網絡等建設投資力度,有效地促進了區域內國家的貿易聯系。 但是從基礎設施的空間溢出的產出彈性系數來看,其呈現出逐漸變小的趨勢,說明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系數及其空間溢出效應逐漸變小,基礎設施的作用不可高估。 二是就交通運輸設施而言,不同交通運輸方式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是不同的。 管道運輸方式的影響最大,后面依次為鐵路和公路運輸。 當然,這與我們研究樣本的貿易結構有關,中國與中亞及俄羅斯的貿易主要是能源,管道運輸是主要方式。如果是貿易產品結構不同的其它國家,其影響大小是不同的。
本文的研究結論,為制定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
首先,要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對基礎設施建設進行跨區域協調。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國家之間貿易的基礎在于各國要素稟賦的不同,但貿易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運輸成本、通訊成本和其它交易成本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后的實踐證實了這一點。 為了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一體化發展,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勢在必行,特別是經濟尚不發達的中亞和南亞等地區,急需要基礎設施建設。 在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對于鐵路、公路等建設需要加強國家之間的協調,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建設。 但是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基礎設施建設存在拐點,到一定閥值以后其效應會逐步降低,對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要考慮其經濟發展承受能力和未來的經濟發展潛力。
其次,要加強公路和鐵路建設。 從本文的研究來看,管道運輸已經發揮出其效應。 隨著中國經濟逐漸進入“新常態”,對原油和天然氣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長幅度逐漸減少,已經不需要再進行大規模的管道建設,而西亞和南亞地區缺乏大規模鐵路和公路網絡,對鐵路和公路的投資具有較高的邊際收益。 中國具有全球最強的鐵路和高速公路建設能力,加強相關行業的資本輸出,帶動上下游產品的出口。 但是,在高鐵等走出去的同時,要加強風險管理。 西亞和南亞國家基本上都是政治不穩定和依賴原材料出口的國家,其還款能力有待提高。傳統上中國采用的BOT 方式風險較大,可以考慮采用BT 等方式,以其國內的原材料來抵消工程款項,但還需要國內進行協調。
最后,要提高基礎設施建設融資能力。 財政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區域經濟一體化,但經濟發展初期,各國普遍缺乏財政資金,吸引外來資本和國際金融機構的投資尤為重要。 中國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可以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 事實上中國也正在這樣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已經運營,絲路銀行也即將成立。這些銀行在進行基礎設施發放貸款時,不能僅僅考慮政治因素,經濟風險也要綜合考量。
[1] Eisner,R.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Comment [ J].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1991,(9).
[2] Holtz-Eakin,D.,Public-Sector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vity Puzzle [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4,(76).
[3] Munnell,A. H. Policy Watc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 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2,(6).
[4] Hulten,C. ,Bennathan,E. and Srinivasan,S. Infrastructure,Externaliti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tudy of the In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6,20(2).
[5] 劉勇.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區域經濟增長及空間溢出作用——基于公路、水運交通的面板數據分析[ J].中國工業經濟,2010,(12).
[6] 孫早,楊光,李康.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拐點嗎——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 J].財經科學,2014,(6).
[7] 劉生龍,胡鞍鋼.交通基礎設施與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 J].經濟研究,2011,(3).
[8] 張美濤.政府競爭、基礎設施建設與中國市場一體化[ J].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12,(6).
[9] 劉育紅,王曦.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交通基礎設施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基于引力模型的實證研究[ 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