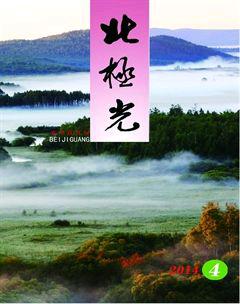憶古源筑路會戰
王修業
1965年3月,七千林業職工奉命從牙克石、伊春、牡丹江、哈爾濱等林區調動,紛紛日夜兼程,潮水般涌入大興安嶺會戰區,參加松嶺林業公司公路建設大會戰。在大興安嶺嫩林鐵路線上爭分奪秒地緊張施工。轟隆轟隆的放炮聲響徹山谷,喚醒了沉睡千年的林海。一個個工地彩旗飄揚,勞動現場你追我趕,熱氣騰騰,大字標語鼓舞著指戰員們劈山開路,冰河架橋,采石挖洞,日夜激戰,會戰到了白熱化程度。
五月中旬,我從嶺北塔河林業辦事處(駐地十八站)乘汽車,經塔源,越過伊勒呼里山,沿鐵道兵修的簡易路趕到古源,加入到從牡丹江來組建塔河林業公司的古源筑路隊伍。指揮部設在山腳下一片松樺混交林的帳篷里,屋里沒有桌凳,只有小桿鋪和木頭墩。公司黨委書記李楓跟我說:“你們在嶺北堅守陣地到頭了!過去開發沒有鐵路,被迫下馬。這次開發鐵道兵修大鐵,林業修公路,一定能勝利。”他滔滔不絕地述說了他帶領工人干部參戰開始的艱苦情景。那時牡丹江來的一千九百多人,三月十日到加格達奇后,轉乘物運汽車,拉著帳篷、糧食、工具、炊具和行李,沿著鐵道兵筑的簡易道到達古源,分成五個中隊,各隊步行到各指定地點,承擔修筑二十五公里運材公路的任務。進點沒有道路,穿森林,踏冰雪,就像紅軍長征一樣,一切物資全憑人背肩扛,真是披荊斬棘,篳路藍縷。一到營地,就入林砍小桿,架帳篷,搭床鋪,壘鍋做飯,刨冰化水。白天架不上帳篷,夜間就得圍著火堆露宿。大家住小布房,睡波浪床,吃高粱米和脫水菜,喝醬油膏湯。開始沒有桌凳,就端著飯碗蹲在雪地上吃。頭碗熱,二碗涼,吃完凍得直篩糠。后來,用小桿和木頭轱轆搭上桌凳,吃飯可以坐下吃。用水,靠化冰雪、小河溝和塔頭甸子的水。生活條件很苦,但沒有人叫苦,也沒有人要求離開的。人們想的是會戰,想早日筑好路,想奉獻,不想得失。 ? ? ? ? ? ? ? ? ? ? ? ? ? ? ? ? ? ? ? ?筑路勞動十分艱苦,沒有筑路機械和運料設備,備料用尖鎬刨沙土,由于地凍未化透,一鎬下去一個白點,震得雙手疼痛難忍,刨十多鎬才刨下一塊。運料全憑土籃加扁擔。人們起早貪黑,爭先恐后地干,展開勞動競賽。有的人一次挑四只土籃,肩膀被壓得腫起來不叫苦堅持干。有的人不僅推獨輪車,還鏟土裝料,搶活兒干。在掄鎬揚鍬、挑土推石等活計中干得生龍活虎,有聲有色。大家迎著工地飛揚的彩旗,你追我趕,一片歡騰。既像延安大生產運動,又像開墾北大荒的場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筑路不僅勞動繁重,而且又有危險。一中隊路段需要開山劈石和填方,工程量很大。隊長于志深率領工人們在十幾米高的山頭上打眼放炮,劈山采石。炮啞了,隊長冒著危險去排除。夏季的大森林酷暑炎熱,中午的工地被烈日曬到零上四十多度,人們的臉膛和臂膀被曬成紫紅色,暴了皮。汗水浸透了背心,就光著膀子干。烈日里瞎蒙叮,陰天里蚊蟲咬,小咬蚊子輪番攻擊,都沒有折磨倒這些人。大興安嶺夏季早晨兩點鐘天就亮了,晚間九點多天還不黑,公司領導率領干部們天天參加筑路勞動。為了多筑路,大家學鐵道兵干十二個小時活兒,吃四頓飯,不休星期天,掄大錘,握鋼釬,抬石頭,推獨輪車,搬運沙石。八磅重的大錘掄十幾下,胳膊就累酸了,大錘砸下去,震得手麻骨痛,我們就換班兒干。為了安全,錘一下下打準,炮一個個放響。從山上炸下的石頭快大,搬不動,我們就用錘和鋼釬再打碎,搬運到填方的地方。我是山東人,在農村干過活兒,擅長推獨輪車,就用車推石頭,用鍬裝石料,也掄錘打鋼釬,天天參加勞動。那時勞動中,分不出誰是干部誰是工人,就連會戰指揮部下去檢查工作的全玉祥、馬恒玉副書記和于錫湘、李春林副部長,都是一到工地就投入到熱火朝天的勞動之中。大家同樣流汗,同樣經受烈日烘烤,同樣受著蚊蟲的叮咬。回到住地,吃同樣的飯,住同樣的小布房。晚間在波浪床上輪流著講故事,唱歌、出小節目。干群關系是那樣的融洽、和諧、密切。干部參加勞動成了制度。“勞動光榮,參加會戰光榮,艱苦奮斗光榮”的思想深入人心,成為會戰精神,貫穿在整個筑路會戰之中。這一點,我記憶猶新,始終不忘,經常向周圍的人們講述當時的情景。
我們這些林業職工盡管不懂筑路技術,大家邊干邊學,集思廣益,解決遇到的難題。施工中,遇到六公里長的塔頭水濕地,是永凍層,如果把塔頭清除再填土方,要到六公里以外去取料,量大,時間長,延長工期。公司領導張丕旭、王 才、孫洪權就發動群眾想辦法,創造了翻扣塔頭保護永凍層再填砂石的辦法,又省料,又省時,很快把“攔路虎”搬掉了。公路穿過一條小河,需要架座鋼筋水泥橋,設計、施工難壞了技術人員。李書記和經理們熱誠地鼓勵技術員到鐵道兵那里去取經,又到兄弟單位借來抽水設備和工具,經過幾十天的精心施工,技術上嚴格把關,工人們艱苦奮戰,二十多米長的鋼筋水泥橋落成了。
深秋九月,我們勝利完成筑路任務,一路上欣賞著大森林五彩繽紛的靚麗風光,奔赴塔河,去建設林業公司未來美好的家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