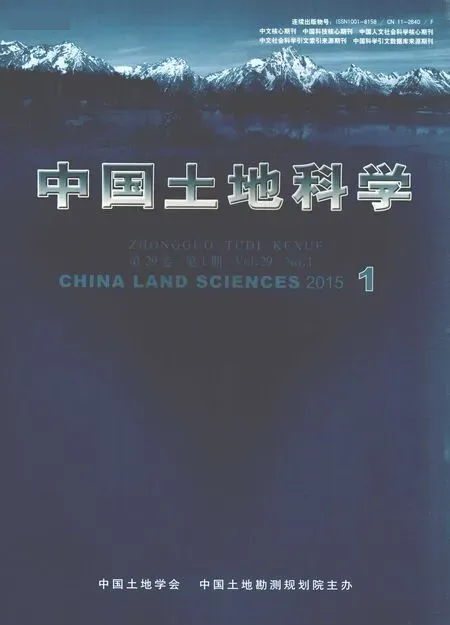農地城市流轉對不同年齡階段失地農民的福利影響研究
彭開麗, 朱海蓮
(1.華中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湖北 武漢430070; 2.湖北農村發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漢430070)
農地城市流轉對不同年齡階段失地農民的福利影響研究
彭開麗1,2, 朱海蓮1,2
(1.華中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湖北 武漢430070; 2.湖北農村發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漢430070)
研究目的:研究農地城市流轉對不同年齡階段失地農民的福利影響,為制定差別化的征地補償政策提供借鑒。研究方法:以武漢市江夏區、東西湖區、新洲區和洪山區為研究區域,將失地農民分為小于45歲、45—65歲、大于65歲三個年齡階段,然后以森的可行能力理論為依據,利用模糊數學法,對不同年齡段失地農民的福利變化進行定量測度。研究結果:(1)農地城市流轉對不同年齡階段失地農民的福利影響存在差異。45—65歲失地農民的福利變化最大,其福利水平下降了18.69%;其次是小于45歲的失地農民,下降了16.62%;大于65歲的失地農民下降了12.74%。(2) 不同年齡階段失地農民的各功能性活動指標在農地城市流轉后的變化方向和變化程度存在不同。失地農民的經濟狀況、居住環境、健康、社會參與功能均有所下降,社會保障和住房條件功能得到了改善,但變化程度不同,而發展機遇和交往與閑暇功能在不同年齡階段的失地農民中變化方向不同。研究結論:根據失地農民年齡特點制定合理細致的征地補償政策,是提高失地農民福利水平、減小福利差異的重要途徑。
土地經濟;農地城市流轉;模糊數學;不同年齡失地農民;福利影響
1 引言
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經歷著城市化,城市居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了2013年的53.73%[1-2],在未來20年內,中國所有的城市仍將處于快速發展階段[3]。與此同時,因不斷受到城市和省級層面景觀城市化和經濟增長的正反饋的推動[4],城市土地需求量不斷增大,為滿足這一需求,政府通過征收或征用的方式將城市附近農村集體所有土地轉變為國有城市土地,學術界將這一過程稱為農地城市流轉[5]。如今,農地城市流轉不僅使土地利用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也對農民的福利水平[6-10]產生了顯著影響。
在中國,失地農民是農地城市流轉中數量巨大的弱勢群體,政府各部門及學術界一直十分重視其福利問題。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失地農民的福利變化[6]、福利影響因素[7]、補償安置問題[8]及社會保障機制[9]等,以農戶或者農戶家庭為研究對象的較多,僅有少量以農村集體或農村社區為研究對象[10]。這些成果均較好地推動了農地城市流轉中的各權利主體福利變化與福利均衡問題研究,但仍需要在制定差別化、細致化的征地補償標準方面進一步完善[1]。同時,以上研究成果均是把同一地區的失地農民作為一個均質主體來看待,沒有從自生轉換因素的角度來進行區分。根據阿瑪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在福利“產生”的過程中,由于個人(如年齡、家庭結構、文化程度、職業)、社會(如社會服務水平、經濟發展狀況)和環境(如區位條件、公共設施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差異,商品和服務向福利的轉換程度和效率也各不相同,這些因素被稱為轉換因素。雖然這些因素不直接產生福利,但在衡量農戶福利的變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1],剖析它們促進或阻礙商品或服務向福利轉換的能力對于進一步分析福利形成過程中各功能性活動的重要程度有著至關緊要的作用[12]。為此,近年來,學者們開始關注農地城市流轉中轉換因素對于農戶福利的影響[13],但相關研究還非常少見。因此,本文試圖從自身轉換因素的角度出發,將失地農民分成不同年齡階段,在森的可行能力理論的基礎上,從經濟收入、社會保障、發展機遇、住房條件、生活環境、交往與閑暇、健康和社會參與8個方面構建失地農民福利評價指標,探索農地城市流轉對不同年齡階段失地農民福利的影響差異,進而結合不同年齡段失地農民的特征,提出完善失地農民福利的細致化的政策建議。
2 理論模型
2.1 失地農民年齡劃分標準
(1)人口學一般將16—64歲期間的人口定義為勞動適齡人口,中國一般規定男性16—60歲,女性16—55歲。由于農業生產是受年齡限制最小的一門職業,本文認為大于60歲(男)或55歲(女)但小于65歲的農民仍能夠從事農業生產。
(2)中國招普工的企業往往傾向于招收35歲以下的農村勞動力,發生民工荒現象之后,招聘普工職位的最高年限上升到40—46歲,一般最高年限為45歲[14]。因此,本文認為45歲以上的有勞動能力的農民在農地城市流轉后很難在城鎮找到合適的工作,農地對于他們的作用較大。
(3)調研發現年齡在45—65歲的失地農民對征地后生活各方面的感受均比其他年齡段的更為悲觀,為了證實農地城市流轉對不同年齡階段失地農民的福利影響是否存在著差異,或者是否對45—65歲的失地農民的福利影響最大,將45—65歲的失地農民劃分為一個群體。
(4)調研發現受訪者中小于35歲和大于75歲農戶僅分別占總樣本數的7.06%和3.53%,因此,為了使樣本分布均勻,把小于35歲和大于75歲農戶樣本分別歸入小于45歲和大于65歲的年齡階段中,其中,小于45歲的失地農民不包括在校學生和待升學者。
2.2 失地農民福利指標體系
森認為給人類帶來福利的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物品給人類帶來的機會和活動,但這些活動和機會也是建立在人的能力之上——可行能力,也就是人有可能實現的所有功能性活動的集合。森提出了5種衡量福利的功能性活動——經濟條件、透明性保證、防護性保障、社會機會以及政治自由[11],自該理論被提出之后,學者們根據自身研究的需要,在其框架上提出了相應的福利指標[6,13]。借鑒前人的研究經驗和調研區域的實際情況,本文用經濟狀況體現經濟條件這一功能性活動,用社會保障和發展機遇體現福利衡量中的透明性保證,用住房條件和居住環境體現福利衡量中的防護性保障,用交往與閑暇和健康體現福利衡量中的社會機會,用社會參與體現福利衡量中的政治自由,最后選取以下8項指標評價失地農戶福利的功能性活動。
(1)經濟狀況。農地城市流轉使得失地農民農業收入減少,生活成本顯著提高。本文選取兩組指標來表示該功能性活動:一組直接衡量失地農民經濟狀況的變化,包括對總收入的影響(X11)和生活成本的變化(X12);另一組是失地農戶對經濟狀況的主觀感受,即對失地后對經濟狀況的滿意度(X13)。
(2)社會保障。土地被征收之后,其附帶的一切保障功能隨之消失。本文選擇是否設立失地農民醫療保險(X21)、是否設立失地養老保險(X22)來衡量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功能。此外,選取失地農民對社會保障的主觀感受(X23)來反映失地后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帶給他們的心理沖擊。
(3)發展機遇。發展機遇主要是指獲得工作的機會以及創業的機會,但這給不同年齡階段的失地農民帶來的效應有所差異。本文選取就業難易(X31)、就業優惠政策(X32)、創業環境主觀感受(X33)和發展機遇主觀感受(X34)來衡量發展機遇功能。
(4)住房條件。住房質量的好壞也對居住者的健康有著重要并長期的影響。本文選取衡量住房條件功能的指標有房屋位置(X41)、房屋結構(X42)、房屋地面材料(X43)、飲用水源(X44)、人均居住面積變化(X45)。此外,選取居住滿意度(X46)作為住房質量功能的主觀指標。
(5)生活環境。農地非農化之后轉變為道路、工廠、居住區等,失去了其原有生態價值,并出現噪音變大、空氣質量變差、固體垃圾增多、綠化情況變差等一系列問題,影響農民的生活。本文選取噪音(X51)、空氣質量(X52)、固體垃圾(X53)、治安情況(X54)、路面粉塵(X55)、綠化情況(X56)作為衡量生活環境功能的指標。
(6)交往與閑暇。人們在滿足了基本的生活之后,開始要求精神的滿足與自我實現,而擁有閑暇時間為實現這些提供了條件,因此,閑暇是一種新型的福利文化[15]。農地城市流轉之后,閑暇時間以及社會交往也發生了變化。本文選取閑暇時間(X61)、社區生活(X62)來衡量交往與閑暇功能。
(7)健康。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制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中指出健康是個人福利的重要指標。農地城市流轉后,一方面生活環境發生了改變,例如工廠廢水排放、固體垃圾增多,同時由于補償標準太低,用于健康的投資減少,這些都影響了失地農民的健康[16]。本文選取自評健康(X71)來反映健康功能。
(8)社會參與。依據馬斯諾需求理論,人除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外還有一些更高層次的需求,如被人尊重與自我實現。在農地城市流轉過程中,社會參與體現在農戶對征收土地補償價格、是否流轉、流轉用途以及安置補償方式的知情權以及監督權。因此,本文選取征地方式(X81)、補償合理性(X82)來體現社會參與功能。
3 福利效應測度方法
3.1 模糊數學基本計算步驟
因為福利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就是一種主觀幸福感[17],本文在衡量失地農戶福利變化過程中所選取的指標大多屬于主觀評價指標,由于其具有模糊性,故采用模糊數學方法。
(1)福利模糊函數。設X為農戶福利狀況的模糊集,農地城市流轉前后可能變化的福利內容為X的子集W,則第n個農戶的福利函數可表示為:

式1中,μ(x)是x對W的隸屬度,其值在0和1之間,x∈X。一般認為隸屬度值越大表示農民福利越好,即當隸屬度為1時,農民的福利狀態最好,為0時最差,為0.5時處于模糊狀態,不好也不壞。
(2)福利隸屬函數。變量一般分為虛擬二分變量、虛擬定性變量和連續變量三類,不同類型的變量有著不同的隸屬函數。本文僅涉及虛擬變量二分變量和虛擬連續變量兩種情況,其中,虛擬二分變量的隸屬函數為:

式2表示,當農民有醫療保險時,xij為1,該指標對于第i個功能子集的隸屬度μw(x)為1;當農民沒有醫療保險時,xij為0;該指標對于第i個功能子集的隸屬度μ(x)為0.5時,表示流轉前后該情況沒有變化。
虛擬定性變量是只能通過語言描述的情況,比如對于目前生活的主觀滿意度分為滿意、一般滿意、不滿意。假設一項研究有m種狀態,一般給這m種狀態等距賦值xij= {xij(1),…,xij(m)},值越大表示福利狀況越好。

式3為這類變量的隸屬函數,其中xijmin和xijmax分別表示xij的下限和上限,分別表示低于或高于該值時,狀況絕對好或絕對差。μ(xij)值越大,說明福利狀況越好。
(3)福利權重函數。在得到初級指標隸屬度的基礎上,需要賦予每個指標一個權重,并進一步將隸屬度匯總成一個綜合指標。由于各項指標的變化對于福利的影響程度不一樣,所以在計算福利的綜合值時不能簡單相加求平均,而應根據理論與實際賦予各指標不同的權重。本文擬采用式4作為權重函數:

這個權重函數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指標的隸屬度增大時,權重值邊際遞減,符合隨著指標權重值增大,該指標對總體福利的貢獻率應該減弱的經濟學規律;第二,指標值單調變化的時候,總體福利也呈現單調變化的規律,保證了總體福利與指標值的變化一致性。
依據指標性質,選擇隸屬函數計算其隸屬度,最后根據權重函數得到失地農民的總體福利函數為:

以上式2—式5中,i、 j和I分別代表功能子集、初級指標和衡量福利的功能性活動的個數。
3.2 數據處理
(1)變量隸屬度賦值。按照式2進行賦值的虛擬二分變量有X21、X22、X32和X81。為了更加精確地描述指標的變化情況,有些虛擬二分變量的備選答案中加入了“和征地前差不多”這個選項,如人均居住面積(X45),若征地后人均居住面積變大了,隸屬度為1;若人均居住面積不變,則隸屬度為0.5;若人均居住面積變小了,隸屬度為0(為了便于計算,用0.0001代替0)。與此類似的指標還有X12、X43、X44、X62、X31、X71和X82。
虛擬定性變量需根據不同情況依次賦值,如農地城市流轉對總收入的影響(X11),受訪的失地農民的回答有:變好了很多、變好了一點、基本沒變、變差了一點、變差了很多,依次賦值5、4、3、2、1。類似的指標還有X13、X23、X33、X34、X46和X61。另外,X51、X52、X53、X54、X55和X56這些指標在調研時分別詢問農地城市流轉前后的狀況,將沒有變化的隸屬度設為0.500,變好了1個等級,隸屬度增加0.125;變好了兩個等級,隸屬度增加0.250;變好了3個等級,隸屬度增加0.375;變好了4個等級,隸屬度增加0.500,即為1,反之亦然。
還有一類變量,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虛擬定性變量,但是可以采用虛擬定性變量的公式來計算隸屬度,如房屋的位置(X41),有“不變、未重新裝修,不變但已裝修,變了、統一搬到還建房或者另批宅基地重建新房”三個等級,若為“不變、未重新裝修”,則記為0.50,每提高一個等級,隸屬度增加0.25,降低一個等級,隸屬度則減去0.25,房屋結構(X42)也是同樣處理。
(2)農戶福利變化百分比計算。本文采用福利變化百分比來測度農地城市流轉前后失地農民的福利變化,不僅有利于分析福利變化方向,也有利于衡量福利變化程度。統一將征地前的農民福利模糊值設為0.5(不好也不壞),然后根據式5算出征地后的福利模糊值,若小于0.5,則說明失地農民福利下降,若大于0.5,則說明失地農戶福利變好了,最后用征地前后變化量除以0.5,得到農民福利變化百分比。
4 實證研究
4.1 數據來源
本文選用的數據來源于2012年12月—2013年2月“農地城市流轉的福利效應”課題組對湖北省武漢市江夏區、東西湖區、新洲區和洪山區的失地農民入戶調研,在這4個區域的城鄉結合部,農地非農化現象非常活躍,且越來越呈頻繁趨勢。調查主要采取隨機抽樣法和直接訪談法,共發放調查問卷267份,得到最終有效問卷255分,有效率為95.51%。樣本分布及年齡特征如表1。

表1 被調查地區樣本分布及年齡特征Tab.1 Sample distribution and ag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urveyed areas
4.2 福利變化的測度結果
依據變量的賦值規則及隸屬度與福利變化百分比的計算方法,分別測算出的小于45歲、45—65歲、大于65歲失地農民的福利變化結果。表2顯示了每一個功能指標的權重、隸屬度以及變化百分比。

表2 不同年齡階段各功能指標的評價結果及變化百分比Tab.2 Evaluate results and percentage changes of functional index for different ages
5 結論與討論
5.1 結論
(1)農地城市流轉使不同年齡階段失地農民的福利水平均有下降,但下降幅度存在差異。下降最多的是45—65歲的失地農民,為18.69%;其次是小于45歲的失地農民,下降了16.62%;大于65歲的失地農民福利下降最少,為12.74%。這說明農地城市流轉對45—65歲的失地農民的福利影響最大。分析其原因發現,農地城市流轉雖然使得45—65歲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住房條件、交往與閑暇三項功能性活動福利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經濟狀況、發展機遇、居住環境、健康和社會參與這5項功能性活動的福利水平均為下降,并且發展機遇與社會參與的下降程度在三個年齡組中最大。這說明,相比于其他兩個年齡組失地農民,45—65歲的失地農民則更容易陷入“農村—城鎮兩難容身”的困境。
(2)在8項功能性活動指標中,各指標變化方向和程度不同,農地城市流轉對不同年齡階段失地農民的總體福利影響不同。農地城市流轉后,經濟狀況、居住環境、健康和社會參與這4項功能性活動的隸屬度在失地后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下降比例最大的為社會參與功能,其次是居住環境功能。社會保障和住房條件這兩項功能性活動都得到了改善,但改善程度有所不同。其中,小于45歲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提高最多,其次是45—65歲和大于65歲的失地農民;住房條件功能提高的程度在三個年齡階段中的排序與社會保障功能相比正好相反。發展機遇和交往與閑暇這兩項功能性活動在不同年齡階段中變化的方向不同。其中,只有小于45歲的失地農民的發展機遇功能有所提高,而45—65歲和大于65歲兩個年齡階段農民均有下降;交往與閑暇這一功能性活動的福利水平只有小于45歲的失地農民下降了,45—65歲和大于65歲的失地農民均有提高。
(3)農地城市流轉對社會參與功能的影響是最大的,該項功能在小于45歲、45—65歲和大于65歲的失地農民中的福利變化百分比依次是-64.46%、-73.22%和-53.76%,是造成其整體福利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失地農民對征地的滿意度不僅僅取決于補償的標準,更重要的是取決于是否享有知情權和參與權[18],因此,提高農地城市流轉過程中農民的參與度就顯得十分重要。此外,改善與提高失地農民的健康狀況、經濟收入與居住環境也是提高所有年齡階段失地農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方面,而促進失地農民充分就業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途徑,因為促進失地農民就業增長、保障失地農民工資收入穩定增長不僅能改善失地農民經濟狀況,而且能夠增強其對健康與居住環境的投資能力[16]。
5.2 討論
(1)由于中國現行的征地補償并不與失地農民的年齡、文化程度及家庭結構等自身特征因素相掛鉤,這就使得同樣的補償方式和補償標準給不同年齡的失地農民帶來的福利效應存在差異。因此,為了維護社會公平,征地補償制度應該盡可能地結合農民的年齡特征,從構成農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動的各方面對失地農民進行多樣化、細致化的補償。除了必要的經濟補償之外,可配合不同的附帶補償措施。例如,針對小于45歲的失地農民,最重要的是解決其就業問題,可以提供非農就業培訓,使其掌握一項生存技能,或提供創業機會以及優惠政策,幫助他們順利完成向城鎮化的轉移,并對其還在接受教育的子女提供一定的教育補償金或免除異地借讀費,以減輕其經濟負擔。對于45—65歲的失地農民,最重要的是通過各種方式轉變其對城鎮生活方式和再就業的認同感,比如通過協調溝通轄區企業,為其提供保潔、物業、綠化等技術含量低的工作崗位,在引進企業時,為其中的貧困群體設立專項扶助計劃。對大于65歲的失地農民,重點是做好醫療以及養老保險,提高他們對未來的安全感,通過建立老年會所、老年協會等豐富其生活,減少其因交往與閑暇時間增多而產生的抑郁。
(2)為了保障失地農民權益,中國各地相繼出臺了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來解決被征地農民的長期基本生活需要。各地政策實施有所不同,一般按照不同的年齡段采取不同的繳費比例。在繳費原則上,應該繼續堅持政府保障為主,個人保障為輔。對于65歲以上的失地農民,可從當地土地征收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資金用于其養老保險費用的支付,個人可不再負擔繳費。對于45歲以下的失地農民,也應從集體獲得的土地補償費用中拿出一部分作為就業培訓專用資金,使其掌握新的勞動技能,加快就業進程,當這部分失地農民進入城鎮就業后,可將其納入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范疇。對于45—65歲的失地農民,應被納入到城鎮靈活就業人員養老保險項目中,并可憑借失地農民身份享受一定的優惠待遇,降低其個人負擔繳費的比例。同時,為了使其有較穩定的經濟來源,應放寬企業招普工的年齡上限,讓不超過城鎮居民退休年齡(男60周歲,女55周歲)的失地農民都可以在通過技能培訓后走上工作崗位,對超過年齡的45—65歲失地農民則主要采取留地安置的補償方式。
(3)森認為同一種商品或服務的組合必定給不同的人們(即使他們的需求函數是相同的)帶來相同水平效用的假定是完全任意的[11]。因此,在客觀環境相同的情況下,由于個體的差異,不同的人會獲得不同的效用水平。今后的研究將繼續關注其他自身特征和社會環境等轉換因素導致的福利水平的差異,從而能夠在實施地區差別化補償政策的同時,針對不同群體的特征采用相應的補償方式,這將對改善失地農民福利狀況、減小福利差異、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
):
[1] Bai X. M., Shi P. J., Liu Y.S. Realizing China’s urban dream [J] . Nature,2014,158(5):158 - 160.
[2] 國家統計局. 2013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3.73% [EB/OL] .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1 - 20/5755331.Shtml,2014 - 01 - 20.
[3] 城鎮化到了轉折時期[EB/OL] . 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2 - 05/15/c_123130280.htm,2012 - 05 - 15.
[4] Bai X. M., Chen J., Shi P. J. Landscape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positive feedbacks and sustainability dilemmas [J] .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2012,(46):132 - 139.
[5] 張安錄.城鄉生態經濟交錯區農地城市流轉機制與制度創新[J] .中國農村經濟,1999,(7):43 - 49.
[6] 胡動剛,閆廣超,彭開麗. 武漢城市圈農地城市流轉微觀福利效應研究[J] .中國土地科學,2013,27(5):20 - 26.
[7] 郭玲霞,高貴現,彭開麗.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失地農民土地征收意愿影響因素研究[J] .資源科學,2012,(8):1483 - 1492.
[8] 聶鑫,汪晗,張安錄.基于公平思想的失地農民福利補償——以江漢平原4城市為例[J] .中國土地科學,2010,24(6):62 - 67.
[9] 馬愛慧,蔡銀鶯,張安錄.耕地生態補償相關利益群體博弈分析與解決路徑[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1(7):114 - 119.
[10] 徐唐奇,李雪,張安錄. 農地城市流轉中農民集體福利均衡分析[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1(5):50 - 55.
[11] 阿馬蒂亞·森. 以自由看待發展 [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12] Ingrid R.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gender inequality:selecting relevant capabilities[J] . Feminist Economics,2003,9(2 - 3):61 - 92.
[13] 高進云,周智,喬榮鋒.森的可行能力理論框架下土地征收對農民福利的影響測度[J] .中國軟科學,2010,(12):59 - 69.
[14] 掃雷鏡.中國民工荒的原因:只盯著30歲以下的,35 - 55歲不要[EB/OL] .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011/277 3/14/05/1 _1html,2011 - 03 - 02.
[15] Bittman M.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family welfare:the money and time costs of leisure[D] .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re,1999.
[16] 秦立建,陳波,蔣中一. 我國城市化征地對農民健康的影響[J] .管理世界,2012,(9):82 - 88.
[17] Harsanyi J. C.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for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J] .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2001,18 (3):387 - 388.
[18] 劉祥琪,陳釗,趙陽.程序公正先于貨幣補償:農民征地滿意度的決定[J] .管理世界,2012,(2):44 - 51.
(本文責編:仲濟香)
The Impacts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on the Welfare of Different Aged Land-lost Farmers
PENG Kai-li1,2, ZHU Hai-lian1,2
(1.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70,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th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on the welfare of different aged farmer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land compensation policies. Taking Jiangxia, Dongxihu, Xinzhou and Hongshan districts in Wuhan city as studying area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land-lost farmers into three age groups: less than 45, 45-65 and more than 65. It selects the functional-activity index of land-lost farmers on the basis of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Finally, by using the fuzzy mathematics method it measures and compares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he three age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1) the overall welfare level of land-lost farmers of all age group declined but with a varying degrees. That is, the welfares of the farmers who are 45-65 years old, younger than 45 years old and older than 65 years old decreased by 18.69%, 16.62% and 12.74%, respectively;2) The effect directions and degrees of functional activity indexes of different groups varied. Living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all age groups decreased while social security and housing conditions increas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communication and leisure have different changing directions in different age stages. These results call for differentiated and tailor-made compensation policies for different aged land-lost farmers, which can improve their welfare levels and reduce the gaps among them.
land economy;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fuzzy mathematics; different aged land-lost farmers; welfare effect
F301.2
A
1001-8158(2015)01-0071-08
2014-05-22
2014-09-2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7100304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2012ZYTS017)。
彭開麗(1975-),女,江西分宜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土地資源經濟學。E-mail: klpeng@mail.hza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