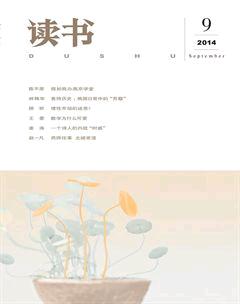公共藝術價值何在?
近些年,隨著中國城鎮化步伐的加快,關于“公共藝術”的實踐和討論都多了起來。事實上,“公共藝術”(Public Art)這個概念也是這些年才從國外移植過來的。以前,學術一點的稱謂叫作“城市雕塑”或“壁畫”之類,文氣一些的人說“接了個工程”,更多的藝術家則比較直白地說“接了個行活(私活)”。因為這類作品大都很難體現藝術家自己獨特的藝術追求,在他們看來,不過是從甲方(一般是政府或企事業單位)爭取到一個靠手藝賺錢的機會而已。在那個當代藝術市場還沒什么起色的年代,正是這類工作使一部分藝術家找到了改善生活的途徑,并率先富了起來。這種甲方決定方向、出錢拍板,乙方圍繞甲方出構思和手藝的模式,可以稱之為公共藝術的“行活模式”。由“行活模式”產生的公共藝術,其“公共性”主要體現在它被放置到公共空間之后公眾被動接受、評論的層面,這與當代公共藝術所強調的注重公民參與創作過程的“公共性”很不一樣。因為公眾只能被動評價,所以就產生了諸如“賽先生還頂個球,德先生球都不頂”之類的關于公共藝術的刻薄段子。顯然,“行活模式”是一種行政集權和藝術家話語霸權的產物,從當代的公共藝術觀念出發,這是一種過時的、應該被摒棄的套路。但是,理想歸理想,現實仍舊是現實。我們所能看到的是,“行活”的風格形式在變,討論和展覽方式在變,但“行活模式”本質上并沒有變。當然,歷史地看,“行活模式”也能夠產生一些在美學上經得住推敲的藝術作品,但問題在于,“行活模式”產生不了真正意義上的藝術的“公共性”,它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公共藝術的創造性和可能性。
籠統來看,當代中國的公共藝術可以分為兩類:其一,便是隨處可見、普遍存在的由“行活模式”產生的公共藝術,這些公共藝術也可冠以“城市雕塑”、“壁畫”或“環境藝術設計”之類的名目,其基本的特點就是西方的大型藝術作品和紀念碑傳統與中國古代“扎彩應景”傳統的結合。紀念碑傳統在威權政治和宏大話語衰落之后,變成了一種空洞的形式,但是這種傳統在當代中國的造城運動中又找到了經濟上的支撐,它與行政和資本權力為伴,頌揚政治的功能被作為美化和裝飾的城市點綴功能所取代。這其實是復活了中國古代社會為了節慶、時令的需要而在城市的重要節點“扎彩應景”的傳統,古代的“扎彩應景”也是裝飾、點綴,強調“熱鬧”、“講頭”,它沒有精神層面上的價值,是短暫的,但有明確的實用功能。也可以說,這類公共藝術,其實是把古代“扎彩應景”的傳統“紀念碑”化了。其二,是展覽和學術意義上的公共藝術,藝術家和策展人把當代藝術方式、方法與藝術的公共性結合在一起,圍繞展覽而推進、基本上只為展覽的時間段而存在的公共藝術。比如近幾年在國內外一些著名的藝術展覽機構、雙年展、藝術節上,以“中國當代公共藝術”的名義展出的一些作品。這種公共藝術,一般更強調觀念和藝術價值,藝術家在進行創作時也常常會使用“行為”、“參與”、“事件”等當代藝術語匯,強調實驗性、學術性和當代性,有時甚至以挑戰“公共性”的方式來推進公民對公共價值的思考。這類公共藝術作品,放在當代藝術展覽中就是“當代藝術”、“實驗藝術”,放在“公共藝術”的展覽中就是“公共藝術”。可以說,這類作品是為了展覽要求而被定義為“公共藝術”的實驗藝術。
紀念碑化的“扎彩應景”公共藝術,與強調客戶市場的設計、實用美術沒有區別,從事這類創作的人可以是有一定藝術追求的藝術家、設計師,也可以是完全以贏利為目的的園林公司、裝飾公司,這類作品給中國當代城市景觀提供的正面價值是美化和裝飾,其反面就是連形式都無法讓人信服的視覺垃圾。這類作品大都是成熟風格或視覺模式的再生產,它幾乎不提供任何有創造性的、批判性的價值觀念。作為展覽的“公共藝術”,會提倡創造性和價值觀上的突破,這類公共藝術一般來說都是藝術家個體思考和創作觀念的延伸。這類作品現在還特別依賴相對獨立的“藝術世界”,脫離了由策展人、美術館(或特定的展場)、媒體等形成的固定氛圍,很難在當下的公共空間中持續地存在并與社區產生有益的對話。藝術家一般也更看重其作為“作品”或“事件”的相對獨特的存在意義。這類公共藝術的所有優點都來自當代藝術,缺點也同樣如此。尤其是當中國的當代藝術越來越被金融化、時尚化和媒體化的時候,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注意這類“公共藝術”所提供的價值對于塑造一個成長中的公民社會是否有積極的意義和價值。抑或說,他們只是在一種高調的自言自語中,以公共藝術的名義不斷重復完成一個個藝術個體的名利場邏輯。
顯然,我們有理由對這兩種公共藝術的存在現狀都表示擔憂。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從事公共藝術創作的主體,仍將是畢業于各種藝術類科系的藝術家和設計師。我們很難脫離當代藝術與設計的語境,脫離藝術教育的現實,在大學里培養出一些與以往的藝術家完全不一樣的“公共藝術家”。因此,我想或許可以在當代藝術哲學和設計哲學的語境中,尋找一些不一樣的思想資源,重新審視當代公共藝術的創作取向和話語路徑。我想說的就是德國觀念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和美國設計師、設計理論家維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他們的思想和實踐對今天的藝術和設計都有深遠的影響,但他們對于公共藝術的價值仍有待我們深入發掘。
博伊斯的重要觀點是“社會雕塑”。所謂“社會雕塑”就是指:“一切由人類構造、發展、創制的事物,以及一切具有生長能力并處于不斷的變化發展之中的思想成果,它們共同從本質上造益于人類的生活。”博伊斯繼承了杜尚的達達主義傳統,把藝術和生活的界限抹平,把藝術引入生活,又把生活轉變為藝術。但他卻揚棄了達達主義者的玩世不恭,把平等、自由、奴役、社會不公和物質主義對自然的破壞等傳統藝術家不怎么關注的問題作為“社會雕塑”去做,力求通過藝術,批判性地建構人類未來的烏托邦。他把藝術與政治、自由、社會等大問題混融在一起,強調思想和觀念的創造性,強調藝術對于社會的建構作用。總之,藝術在博伊斯那里既不是遠離社會的象牙塔里的“念珠游戲”,也不是只給社會提供美化、裝飾的手藝活,而是積極主動地介入到對重要社會問題的關注中去的思維力和行動力。他的“社會雕塑”概念對當代世界的公共藝術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博伊斯在卡塞爾種的七千棵橡樹(該作品全稱為《七千棵橡樹—城市綠化代城市統治》),哪怕是藝術觀念最保守的人也會承認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藝術”。博伊斯認為,長久以來,人類的城市文明是建立在對大自然的侵略和征服的基礎上的。包括“園林景觀”、“公園建筑”在內,人造景觀本質上都體現了人類試圖掌控自然法則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他的“七千棵橡樹”就是要徹底反叛這個傳統。他從一九八一年開始籌劃,經過和卡塞爾市民和市政官員的不斷溝通獲得支持,從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開始正式實施該項目。很快,七千塊象征著原始能量,象征著歷史和過去的玄武巖被運到了卡塞爾市內的弗里德里希廣場。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六日,他在弗里德里希博物館入口處的草坪上栽了第一棵壽命可達八百年、象征未來和進步的橡樹。博伊斯不幸于一九八六年逝世,但是這個藝術項目的目標仍舊被人們堅持了下來。一年多之后,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人們種下第七千棵橡樹。作為“社會雕塑”的“七千棵橡樹”,作品的最終完成,成為獻給卡塞爾市的一份厚禮,也成為該市各市政部門和普通市民用自己的雙手創造更美好的生存環境的永久記憶。endprint
之所以說博伊斯的“七千棵橡樹”是當代公共藝術的一個里程碑事件,我認為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敏感的、宏偉的問題意識。作為德國環境保護運動的先驅,博伊斯所關注的是關系人類生存和未來的大問題,這需要藝術家有大智、大愛,有非凡的洞見和勇氣。其次,他采用了激進的藝術方式。尤為重要的,就是廣泛地發動民眾參與藝術的創作過程,把當地居民的看法意見和日常情感融入到藝術的創作過程中,因為最終這個作品畢竟是在當地居民的家門口,必須得成為社區生活的一部分。在這里,民眾也是藝術的創作者,而不只是藝術的被動接受者。這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當代建筑和設計思想中越來越強調用戶和利益相關方的參與是相通的。
作為“二戰”后最重要的設計理論家之一,維克多·帕帕奈克是可持續設計、通用設計、社會設計和責任設計運動的先驅。他有兩本著作,對當代的設計理論和實踐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一,是《為真實的世界設計:人類生態與社會變革》,該書一九七零年首版于瑞典,包括中文版在內,迄今已被翻譯成二十四種語言,被稱為“責任設計運動的圣經”。一九九五年,帕帕奈克出版了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綠色律令:設計與建筑中的生態學和倫理學》。此書可以說是《為真實的世界設計》一書的“綠色版”,繼續對設計倫理、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第三世界的生存狀況與設計、設計的精神與設計的未來等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可謂集其晚年思考之大成,在西方的設計界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帕帕奈克一生堅持設計的平民政治,強調設計的倫理和精神價值,強調對歷史和自然的謙卑和敬畏,認為設計師必須擔負起他對人類的生存狀況和未來所負有的社會責任。這些設計觀念雖然是在四十多年前提出來的,但許多問題今天依然值得我們深思。
當然,藝術家和設計師的思維方式有很多不同之處,比如帕帕奈克強調腳踏實地的設計研究,強調科學、理性和系統思維的價值,博伊斯則強調頓悟超越,擅長薩滿式的、碎片化的思考(盡管他的思維和實踐也有一以貫之的完整性)。博伊斯令人費解的行為藝術可能是帕帕奈克所厭惡的。但是,作為同齡人,他們的思想都成熟于六十年代,觀念上有許多共通之處。比如,博伊斯說“人人都是藝術家”,帕帕奈克則說“人人都是設計師”,他們都反對形式主義,強調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介入,關注物質主義給社會和自然環境帶來的災難,都強調藝術或設計實踐中的客體參與,強調藝術及行為的平民政治和人道主義關懷,強調藝術或設計的倫理和精神價值。尤其是在環境問題上,他們的見解可謂高度一致。比如,博伊斯在一九七九年的一次談話中曾公開表示:
偉大藝術的標志是它完全沒有自我彰顯的意志,而是完全地融入,甚至是消失在自然造化之中。
十多年后,帕帕奈克在《綠色律令》中談到設計師的工作時也說:
我們必須得解決在暫時和持續、短暫和永久之間似乎存在的矛盾。如果我們整體地觀察這些表面看相反的事物,我們很快就會意識到,任何房屋或建筑,任何工具、物品或人工制品不過都是永無止息的發展長河中短暫的插曲而已。
顯然,帕帕奈克的這個設計觀點與博伊斯的藝術觀點不謀而合。這種類似于中國文化中所講的生生不息、循環往復的道家哲學,與后來美國設計師威廉·麥克唐納(William McDonough)和德國化學家邁克爾·布朗加特(Michael Braungart)提出的“從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的循環設計概念也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
相較而言,當代中國的設計,在很大程度上仍舊深陷于消費主義和市場的逐利生存法則中不能自拔,與自然、社會和文化責任形同路人。而中國的當代藝術,則似乎已經或正在渴望變成金融衍生品,無論是新潮、革命、批判還是艷俗,如今都變成了生意。放眼望去,它們之中究竟有多少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歷史文脈息息相通,又有多少能夠與我們生存在其中的這個“真實的世界”有切膚之痛的關聯?中國未來的“公共藝術”如果仍舊把價值追求建立在這兩者之上,將很難提出對藝術與社會真正有意義、有突破性的議題。當然,中國當代公共藝術思維力的遲滯和幼稚,也與大的思想環境有關系:主流話語過于強大,相比之下,邊緣的、民間的思想盡管活力充沛,創造性和前瞻性卻顯得嚴重不足,且缺乏支持。如果科斯(Ronald H. Coase)所強調的開放、自由的思想市場在不久的將來、在中國真的會出現,包括公共藝術在內,藝術的未來或許才真會有所改觀。
事實上,公共藝術恰恰處在設計與藝術之間,它一方面應該在設計的消費屬性和工具理性之外強調公共價值和公共精神,另一方面,公共藝術又應該為大寫的“藝術自由”提供一種限度,這種限度就是以理性、開明、健康的公民社會的成長為旨歸。我認為,當代中國的公共藝術,無論是作為“藝術”還是作為“設計”,可以從博伊斯和帕帕奈克的這些具有原創性、且彼此具有共通性的思想觀念中得到一些啟發。尤其重要的是對更加人道的、生態的理想社會的追求,對社會議題的思維力和行動力,以及面對“真實世界”的公共精神和責任倫理。在我看來,這些啟示有可能也應該成為中國未來公共藝術實踐和批評的一種新的價值起點。
(《社會雕塑:博伊斯在中國》,王璜生主編,中國青年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為真實的世界設計:人類生態與社會變革》,維克多·帕帕奈克著,周博譯,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綠色律令:設計與建筑中的生態學和倫理學》,維克多·帕帕奈克著,周博、趙炎譯,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