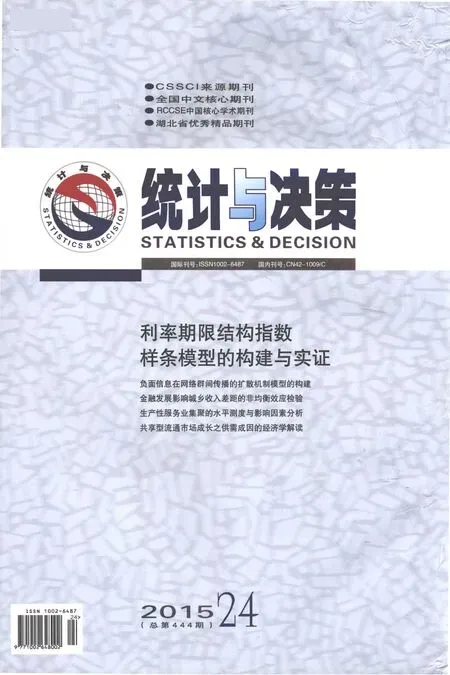我國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波動影響的實證分析
張禮濤
(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西安 710061)
0 引言
需求結構轉變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解釋經濟波動的本質因素。需求結構是否合理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失衡的需求結構對經濟增長存在較強的制約能力,進而影響到我國的投資結構、消費結構,最終導致我國出現較難預測的經濟波動。正如Garavaglia和Malerba等人(2012)所言,若一個國家或地區出現需求結構不均衡狀態,那么它的經濟增長也將變得不穩定,甚至導致經濟出現后退可能,而需求結構均衡化則有利于穩定經濟增長。雖然我國經濟總體上不斷增長,但局部經濟波動仍較明顯,例如2006年、2007年、2010年、2011年經濟增長率保持增加,但2008年、2009年、2012年、2013年均保持了下降。與此同時,國內需求結構不斷調整,特別是消費品需求的調整非常明顯,特別是對交通通信、文教娛樂、醫療保健等的消費支出明顯增加,但對糧食、肉禽等食品的消費支出未得到明顯增加。那么,需求結構調整是否對經濟波動產生影響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入考慮。
縱觀國內研究發現,能夠定量地、系統地研究我國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波動的文獻非常少。基于此,本文對我國需求結構與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分析需求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探究需求結構演進過程中對緩解經濟波動是否具有貢獻。
1 需求結構調整的指標度量
1.1 需求結構合理化度量
單純采用消費率、投資率或者投資消費比率來衡量需求結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借鑒R-C-K模型和Fabricant(1942)提出的結構合理化指標,采用最終需求投資比率來衡量需求結構合理化。最終需求投資比例能有效的判斷需求結構是否失衡,考慮到不同經濟狀態下最優需求結構與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衡量需求結構是否存在失衡現象。通常需求結構合理化通過兩個維度來衡量,一個是需求結構合理化的年度指標;另一個是需求結構化的階段性指標,兩個維度具體的計算公式分別如下:

其中DRFi代表需求結構合理化的年度指標;DRFs代表需求結構合理化的階段指標;DRi代表第i年的最終需求投資比率;DR*代表穩態下最終需求投資比率。
1.2 需求結構高度化度量
本文采用需求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來衡量需求結構高度化指標,用DRH來表示我國需求結構高度化,即采用消費率來衡量需求結構高度化。
一般來說,需求結構高度化指標滿足:0<DRH<1;當需求結構高度化水平越高時,DRH值也就越大;反而亦之。
測算2001~2013年我國整體的需求結構合理化、高度化指標值,結果如圖1所示。由圖可知,我國需求結構高度化水平呈“U型”變化,而需求結構合理化水平則整體上越來越偏離均衡經濟增長的路徑。

圖1 2001~2013年我國需求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變化趨勢
2 模型構造和指標說明
2.1 模型構建
為了更好地分析我國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本文采用了引入控制變量的方法,消除其他影響因素對兩者之間的影響。為了避免控制變量的隨意性,借鑒干春暉(2011)在分析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波動影響的做法,選取需求結構(包括合理化與高度化兩個指標)與經濟波動指標的交互項作為控制變量,具體的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第i個地區;t代表第t年;Yit代表第i個地區第t年區域經濟波動情況;DRFit代表第i個地區第t年區域需求結構的合理化指標;DRHit代表第i個地區第t年區域需求結構的高度化指標;(DRFit×Yit)表示需求結構合理化與經濟波動的交互項;(DRHit×Yit)表示需求結構高度化與經濟波動的交互項;α0為常數項系數;α1、α2、…、α4代表待估計參數的系數;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2.2 指標數據說明
為了擴大樣本容量,增強實證研究的可靠性,本文選取2001~2013年我國30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其中西藏自治區因數據缺失,所以沒有列入樣本。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總量上都存在遞增的趨勢,而在這過程中存在的經濟波動必然是伴隨經濟總量變動的。本文將分別引入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分別檢驗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以及經濟波動的影響。其中,經濟增長指標按照目前學術界慣用的方法,即采用名義GDP的增長率,即為DGDP;經濟波動指標按照目前大多數學者采用的HP濾波方法,消除各省區GDP在變化過程中所時間趨勢波動的成分,得到不含有時間趨勢的周期性波動指標,記為WG。在計算經濟波動指標時,設定年度平滑參數值為100。
3 實證分析
3.1 面板數據平穩性分析
為了使數據分析有效,首先需對面板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LLC的單位根檢驗方法進行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面板數據LLC單位根檢驗結果
由表1結果可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以上所有變量的LLC值都是顯著的,這也表明了所有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是平穩序列。因此,使用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在統計意義上是合理的。
3.2 區域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提高本文研究的準確性,首先對所有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檢驗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整體影響;然后,將面板數據按時間序列進行分組,分別檢驗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體地,首先對2001~2013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然后,以2007年為分界點,分別對2001~2007年和2007~2013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通過Hausman檢驗,這里3個模型都選擇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首先分析2001~2013年整體層面的回歸結果。
由表2可知,需求結構合理化DRF的系數為0.052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我國需求結構合理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名義GDP增長率上升。而需求結構合理化與名義GDP增長率交叉項的系數DRF×DGDP為-0.2521,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我國需求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受到經濟增長水平本身的約束,當經濟增長速度非常高的時候,需求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將明顯減小。這里,有|α1/α3|<1,這就意味在我國需求結構不斷調整的過程中,當需求結構合理化值較小的時候,即使需求結構不合理,也不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明顯的負面作用。

表2 區域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回歸結果
綜合這個回歸結果可知,在我國經濟蓬勃發展的階段,為了實現國內經濟快速增長,可以對需求結構的合理化進行一定程度限制,即允許一定程度的非合理化;但需求結構非合理化程度也存在一定界線,當非合理化程度較高時,將會對經濟增長帶來明顯的負面作用,因此必須實施相應的戰略調整。
與此同時,需求結構高度化DRH的系數為-0.2397,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我國需求結構高度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名義GDP增長率上升。而需求結構高度化與名義GDP增長率交叉項的系數DRH×DGDP為1.784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我國需求結構高度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也受到經濟增長水平本身的約束,需求結構高度化與經濟增長的共同作用可以顯著推進經濟增長速度增加。當經濟增長速度非常高的時候,需求結構高度化對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程度將明顯提高。這里,有|α2/α4|<1,這就意味著除非我國需求結構能短時間內快速高度化,否則較為緩慢的需求結構高度化反而會引起經濟增長速度下滑。
其次分析2001~2007年、2007~2013年的回歸結果。
由表2可知,2001~2007年、2007~2013年需求結構合理化DRF的系數分別為0.0255和0.0627,且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在兩個時間段內我國需求結構合理化程度的提升都促進了名義GDP增長率上升,而2001~2007年需求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明顯弱于2007~2013年。在后一時間段,受金融危機以及經濟新常態影響,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因而需求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所增強,這一論斷與前面的分析相呼應,即當經濟增長速度非常高的時候,需求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將明顯減小。
2001~2007年、2007~2013年需求結構高度化DRH的系數分別為-0.2118和-0.3512,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在兩個時間段內我國需求結構高度化程度的提升都明顯地抑制了名義GDP增長率上升,而2001~2007年需求結構高度化對經濟增長的負向作用要弱于2007~2013年。這也與前面的相關論斷相呼應,即當經濟增長速度非常高的時候,需求結構高度化對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程度將明顯提高。正是由于2001~2007年我國經濟火熱,經濟增速明顯高于2007~2013年,因此需求結構高度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才更能發揮出來。
3.3 區域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波動的影響
同樣地,首先對2001~2013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檢驗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波動的整體影響;然后,以2007年為分界點,分別對2001~2007年和2007~2013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這里,3個回歸模型的面板數據效應也都選擇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區域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波動影響的回歸結果
首先分析2001~2013年整體層面的回歸結果。
由表3可知,需求結構合理化DRF的系數為0.0087,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我國需求結構合理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經濟波動。而需求結構合理化與經濟波動交叉項的系數DRF×WG為-0.1834,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我國需求結構合理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程度受到經濟波動程度本身的約束,當經濟波動幅度非常大的時候,需求結構合理化對經濟波動的抑制作用將得到強化。這里,有|α1/α3|<1,這就意味在我國需求結構不斷調整的過程中,當需求結構合理化值較小的時候,即使需求結構不合理,也不會對經濟波動產生明顯的影響,這與需求結構合理化影響經濟增長的效應基本相似。
綜合這個回歸結果可知,在我國經濟總體蓬勃發展,但經濟波動明顯的階段,需求結構的合理化與經濟波動并未存在完全一致性。這也從側面表明,為了有效緩解經濟波動,除了不斷推進需求結構合理化,還應時刻重視其他方面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以便及時作出戰略調整。
與此同時,需求結構高度化DRH的系數為-0.076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我國需求結構高度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波動產生穩定的緩解作用。而需求結構高度化與經濟波動交叉項的系數DRH×WG為1.472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我國需求結構高度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程度也受到經濟波動程度本身的約束,需求結構高度化與經濟增波動的共同作用則是顯著地為經濟波動滋生動力。當經濟波動幅度非常高的時候,需求結構高度化對經濟波動的引發作用將明顯提高。這里,有|α2/α4|<1,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國需求結構能夠持續地向高度化演進,那么將對國內經濟周期性波動產生顯著的緩解作用。
其次分析2001~2007年、2007~2013年的回歸結果。
由表2可知,2001~2007年、2007~2013年需求結構合理化DRF的系數分別為-0.0066和0.0124,且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在兩個時間段內我國需求結構合理化程度對經濟波動產生了相反的作用。2001~2007年、2007~2013年需求結構高度化DRH的系數分別為1.6008和1.8210,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在兩個時間段內我國需求結構高度化程度的提升都明顯加劇了經濟波動,而2001~2007年需求結構高度化對經濟波動的驅動作用要強于2007~2013年。這也與前面的相關論斷相呼應,即當經濟波動幅度非常高的時候,需求結構高度化對經濟波動的引發作用將明顯提高。

表5 區域需求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正是由于2001~2007年我國經濟火熱,經濟波動力度也高于2007~2013年,因此需求結構高度化對經濟波動的引發作用才更能發揮出來。我國區域需求結構高級化水平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經濟增長速度,表明需求結構高級化水平降低有利于經濟增長(見表5),但要求區域需求結構高級化水平降低要適度。
4 結論及啟示
本文以需求結構合理化和需求結構高度化兩個指標共同反映當前我國需求結構調整情況,并以此為基礎,實證檢驗了需求結構調整是否能夠緩解經濟波動。研究結果顯示:第一,我國需求結構合理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名義GDP增長率上升,但也加劇了經濟波動。第二,我國需求結構高度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名義GDP增長率上升,同時對經濟波動產生穩定的緩解作用。第三,無論是需求結構合理化還是高度化,它們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均受到經濟波動程度的約束。第四,需求結構合理化還是高度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存在一定的動態性,即不同時期的影響存在一定差異。
根據本文研究結果,揭示了以下事實:第一,對于一個經濟體,需求結構在調整過程中與經濟體自身的發展特點以及所處的發展階段都存在密切關系。第二,我國政府在處理需求結構調整與經濟波動關系的同時,應重視需求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實質,以及對經濟波動影響的異同點,爭取強化它們對經濟波動產生明顯的緩解作用。
[1]Garavaglia P,Malerba F,Orsenigo L,et al.Technological Regimes and Demand Structur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J].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12,22(4).
[2]Ramsey,Frank P.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J].Economic Journal.1928,38(152).
[3]Cass,David.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5,32(3).
[4]徐舒,左萌,姜凌.技術擴散、內生技術轉化與中國經濟波動——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J].管理世界,2011,(3).
[5]莊子罐,崔小勇,龔六堂,鄒恒甫.預期與經濟波動——預期沖擊是驅動中國經濟波動的主要力量嗎?[J].經濟研究,2012,(6).
[6]史晉川,黃良浩.總需求結構調整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1).
[7]李永友.我國需求結構失衡及其程度評估[J].經濟學家,2012,(1).
[8]沈利生.最終需求結構變動怎樣影響產業結構變動——基于投入產出模型的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