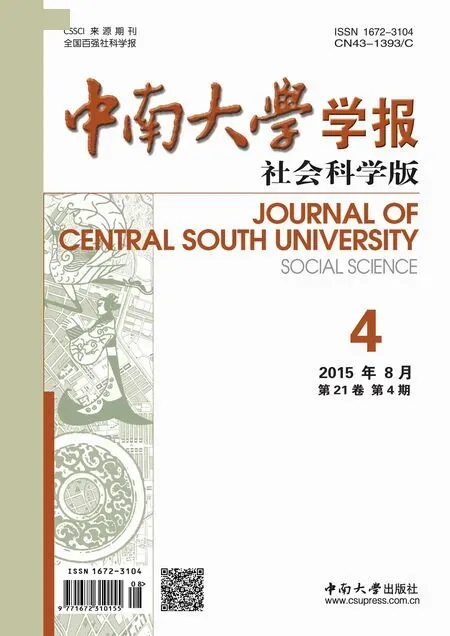土地確權(quán)與國(guó)家德性
——基于《憲法》第10條的法理分析
王進(jìn)文
(中南大學(xué)法學(xué)院,湖南長(zhǎng)沙,410083)
土地確權(quán)與國(guó)家德性
——基于《憲法》第10條的法理分析
王進(jìn)文
(中南大學(xué)法學(xué)院,湖南長(zhǎng)沙,410083)
土地問題是中國(guó)當(dāng)前城市化過程中所面臨的重要問題。1982年憲法第10條關(guān)于土地性質(zhì)的城鄉(xiāng)二元?jiǎng)澐种?guī)定,在法律層面上便會(huì)產(chǎn)生以下問題:一是城市界限不明確,存在無限擴(kuò)大的可能性;二是集體土地所有權(quán)因行政權(quán)力介入而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導(dǎo)致基于集體土地成員身份而產(chǎn)生的身份權(quán)利保障喪失。所以,必須摒棄土地國(guó)有與私有的分析框架,而以土地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屬性為基礎(chǔ),以人地關(guān)系為核心,突出身份權(quán)利的重要性,充分發(fā)揮土地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屬性來彌補(bǔ)其所有權(quán)屬性的不足,進(jìn)而構(gòu)建新的公民身份權(quán)利體系,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德性維度的政治合法性和治理現(xiàn)代化。
土地確權(quán);財(cái)產(chǎn)權(quán)屬性;身份權(quán)利;國(guó)家德性
一、 土地問題的中國(guó)語境與分析框架
中國(guó)全方位改革開放所造就的經(jīng)濟(jì)奇跡,其間一個(gè)不可忽略的前提便是改革前三十年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下工農(nóng)業(yè)之間的剪刀差所帶來的工業(yè)紅利與基于人口基數(shù)尤其是農(nóng)村人口所釋放出來的巨大勞動(dòng)力而形成的人口紅利,兩者的合力在開放社會(huì)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模式下所形成的后發(fā)優(yōu)勢(shì)使得中國(guó)社會(huì)在晚近三十年來得以快速乃至急速發(fā)展。從宏觀角度而言,中國(guó)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恰恰是三個(gè)“化”的過程:第一“市場(chǎng)化”,第二“全球化”,第三“城市化”。大致以十年為期,各完成一化,以1992年所明確的建立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改革目標(biāo)、2001年中國(guó)加入WTO和近十年來的城市化為分階,每個(gè)階段面臨的問題都不一樣。毋庸置疑,在城市化進(jìn)程中,最主要的就是土地問題。而土地問題,在當(dāng)下中國(guó),其表現(xiàn)并不局限于靜態(tài)的土地制度的運(yùn)行,更大層面上是基于現(xiàn)行土地制度或土地政策的改革調(diào)適問題,從而,土地問題就成為了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問題,質(zhì)言之,便是土地改革問題,土地確權(quán)問題。
土地問題之重要性,久已為法學(xué)界所關(guān)注。在憲法學(xué)界引起關(guān)注的是張千帆教授關(guān)于土地二元?jiǎng)澐峙c城市化問題的相關(guān)研究[1, 2],從憲法解釋學(xué)維度對(duì)現(xiàn)行憲法第10條所確立的土地二元結(jié)構(gòu)進(jìn)行了梳理,肯定了土地的使用權(quán)屬性,將其納入財(cái)產(chǎn)權(quán)范疇更是精彩的分析,是針對(duì)土地財(cái)政的現(xiàn)實(shí)所做出的回應(yīng)。而許章潤(rùn)教授之研究雖不是直接針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下的土地問題而發(fā),但其地權(quán)之所指,自不是針對(duì)具有成熟地權(quán)的國(guó)家,面對(duì)國(guó)家德性維度之闕失,其所討論的乃是土地二元結(jié)構(gòu)下的權(quán)屬不明所造成的政治問題。[3]
筆者認(rèn)為,要理解土地問題的具體語境,必須將之放置到現(xiàn)行土地制度確立的六十余年來的歷史情境中去考察,方有可能認(rèn)識(shí)到土地問題的普遍性及其在中國(guó)所表現(xiàn)出來的特殊性。以此為前提,才能進(jìn)一步分析圍繞土地所產(chǎn)生的法權(quán)安排之特殊性與內(nèi)在缺陷,尤其是與土地制度密切相關(guān)的由土地而產(chǎn)生的——個(gè)體或集體——身份權(quán)利及其確權(quán)在城市化進(jìn)程中的重要性。從大歷史角度而言,中國(guó)近現(xiàn)代的核心命題是土地革命,而針對(duì)土地制度所進(jìn)行的改革則表明土地問題是一場(chǎng)未完成的國(guó)民革命。此一革命既表現(xiàn)出中國(guó)土地問題的歷時(shí)性特征,又具有世界歷史的共時(shí)性特征。其歷時(shí)性特征無庸諱言,乃在于中國(guó)革命所要解決的土地集中或兼并問題,以1947年《中國(guó)土地法大綱》①為標(biāo)志,共產(chǎn)黨成功地實(shí)現(xiàn)了革命動(dòng)員,土地革命成為其政權(quán)合法性的來源,具有賦權(quán)性的意義。就其共時(shí)性特征而言,則在于中國(guó)革命所處的世界形勢(shì)是由工業(yè)—商業(yè)資本向金融資本過渡的過程中,各主要國(guó)家均面臨土地制度的改革及隨之而來的基于土地的身份權(quán)利的確認(rèn)問題,該問題的解決不僅有其經(jīng)濟(jì)方面的現(xiàn)實(shí)意義,更具有影響政治的歷史意義。土地問題在中國(guó)現(xiàn)階段所表現(xiàn)出來的特殊性,既與其基于歷史而產(chǎn)生的歷時(shí)性特征相聯(lián)系,并按其內(nèi)在邏輯不斷拓充其外延,又與現(xiàn)階段的城市化問題相銜接,從而必然地要求在土地基本制度方面適應(yīng)該時(shí)代命題,使其原有的內(nèi)涵做出相應(yīng)的調(diào)適。這必然影響到基于土地而產(chǎn)生的人身權(quán)利或身份權(quán)利的規(guī)定,即人地關(guān)系的建構(gòu)問題[4?6],而能否解決后者,便需要我們?cè)谡暚F(xiàn)實(shí)的基礎(chǔ)上提出可行性對(duì)策。
二、中國(guó)土地制度的歷史考察和法理闡析
對(duì)土地制度的歷史考察,涉及到土地制度的分析框架問題。現(xiàn)階段對(duì)土地議題的討論大量集中在土地權(quán)屬制度方面。毋庸諱言,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土地所有權(quán)問題。土地所有權(quán)被理解為土地所有者對(duì)土地的最廣泛和最絕對(duì)的權(quán)力。②對(duì)土地議題的討論也大量集中在土地權(quán)屬制度方面,即土地是否應(yīng)私有化。然而,筆者在此需要著重指出的是,當(dāng)下所秉持的“私有”與“國(guó)有”的概念是很不完善不清晰的,甚至不準(zhǔn)確的,它具有混淆甚至誤導(dǎo)的作用。依據(jù)法理,“國(guó)有”是在國(guó)內(nèi)語境中而言的,它不是一個(gè)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問題,而是主權(quán)的問題。它只有當(dāng)外國(guó)人在場(chǎng)時(shí)才有效,即它所針對(duì)的對(duì)象是外國(guó)人而非本國(guó)人,例如某一建筑是中國(guó)人民的共同財(cái)產(chǎn),那么它的意義在于對(duì)外國(guó)人的排斥與否定,意即外國(guó)人要使用的話就可能要多交錢,或者根本不允許使用。但農(nóng)村集體所有制或個(gè)人所有等概念都具有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內(nèi)涵與屬性。“私有”必須在具有具體指明是何種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時(shí)方才有意義。所有和使用的區(qū)別不是本質(zhì)意義上的,它是類型學(xué)意義上的。例如,在英美法里面便沒有所有權(quán)的重要性,人們注重的是具體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對(duì)于具體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考察而言,該種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產(chǎn)生了什么樣的利益,才是問題的關(guān)鍵。
鑒于國(guó)有與私有概念的話語地位,尤其是其在運(yùn)用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誤導(dǎo),造成掩蓋實(shí)質(zhì)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歸屬的不良后果,筆者由土地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之法律屬性入手③,從其內(nèi)涵與外延出發(fā),引入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具體利益概念,以地租分配制度與土地使用制度為基點(diǎn),闡析土地制度的內(nèi)在邏輯與現(xiàn)實(shí)運(yùn)行中的癥結(jié)所在,并將其與身份權(quán)利的確立做一預(yù)瞻。筆者認(rèn)為使用此一分析框架的優(yōu)點(diǎn)在于,它不僅可以很好地揭示土地權(quán)屬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內(nèi)涵,更有利于我們站在更高的層面上探討現(xiàn)階段因人為劃分城鄉(xiāng)土地而產(chǎn)生的法理困境,即土地流轉(zhuǎn)只適用于城市而非農(nóng)村,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征地、拆遷補(bǔ)償?shù)确删葷?jì)的無力,從而有可能為克服法律規(guī)制層面的局限性與潛在危害性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但是,鑒于目前法律實(shí)踐中土地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屬性是派生于土地的所有權(quán),而又被后者所掩蓋,筆者為分析土地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計(jì),有必要從所有權(quán)角度對(duì)土地二元權(quán)屬的形成歷史做一梳理。
如果我們梳理當(dāng)下中國(guó)土地問題的形成,從立法角度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之前,中國(guó)實(shí)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數(shù)土地屬于私人所有,也有一部分土地屬于國(guó)家所有。[5?7]1949年9月中國(guó)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通過的《中國(guó)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共同綱領(lǐng)》第3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yōu)檗r(nóng)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土地改革法》,與1947年的《中國(guó)土地法大綱》相比,它規(guī)定廢除地主階級(jí)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shí)行農(nóng)民的土地所有制。此外,還規(guī)定了沒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則和辦法。到1953年春中國(guó)大陸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wù)。
很顯然,按照耕者有其田的規(guī)定,農(nóng)民是擁有土地的所有權(quán)的,這也在1954年憲法中得到了體現(xiàn)。該憲法第5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的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主要有下列各種,即國(guó)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勞動(dòng)群眾集體所有制)、個(gè)體勞動(dòng)者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其中的集體所有制、個(gè)體勞動(dòng)者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都屬于私有制。第8條規(guī)定,國(guó)家依照法律保護(hù)農(nóng)民的土地所有權(quán)和其他生產(chǎn)資料所有權(quán)。同時(shí),該憲法第13條還規(guī)定,國(guó)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條件,對(duì)城鄉(xiāng)土地和其他生產(chǎn)資料實(shí)行征購(gòu)、征用或者收歸國(guó)有。之后,中國(guó)確立了土地的社會(huì)主義公有制,同時(shí)憲法明確規(guī)定“任何組織或者個(gè)人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zhuǎn)讓土地”。這就形成了舊的國(guó)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土地?zé)o償使用,二是無限期使用,三是不準(zhǔn)轉(zhuǎn)讓。改革開放以前,中國(guó)城鎮(zhèn)國(guó)有土地實(shí)行的是單一行政劃撥制度,國(guó)家將土地使用權(quán)無償、無限期提供給用地者,土地使用權(quán)不能在土地使用者之間流轉(zhuǎn)。
需要指出的是,從1954年到1975年間所經(jīng)歷的許多“運(yùn)動(dòng)”,很多是針對(duì)土地所有權(quán)的,如農(nóng)村合作化運(yùn)動(dòng)、公私合營(yíng)運(yùn)動(dòng)、私房改造運(yùn)動(dòng)、人民公社運(yùn)動(dòng)等。私有制特別是土地私有制是社會(huì)主義革命的對(duì)象,但在法律上對(duì)于基本土地制度并沒有做更改,城市的土地所有權(quán)經(jīng)過所謂的“社會(huì)主義改造”就變成了國(guó)有,這顯然與1954年憲法規(guī)定不同。而1975年憲法中涉及土地所有權(quán)的條款很少,僅在其第6條中有如下規(guī)定:“礦藏、水流、國(guó)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資源,都屬于全民所有。國(guó)家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條件,對(duì)城鄉(xiāng)土地和其他生產(chǎn)資料實(shí)行征購(gòu)、征用或者收歸國(guó)有。”緊接著,第7條規(guī)定:“農(nóng)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在保證人民公社集體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占絕對(duì)優(yōu)勢(shì)的條件下,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jīng)營(yíng)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yè),牧區(qū)社員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需要注意的是,1975年憲法第6條繼承了1954年憲法第13條的內(nèi)容,事實(shí)上仍然承認(rèn)非國(guó)有土地的普遍存在,規(guī)定國(guó)家只有通過征購(gòu)、征用或收歸國(guó)有的程序,才能將非國(guó)有的土地轉(zhuǎn)變?yōu)閲?guó)有。
不過,1978年憲法與1975年憲法都只承認(rèn)生產(chǎn)資料的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按照1978年憲法第6條的規(guī)定:“礦藏、水流、國(guó)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海陸資源,都屬于全民所有。國(guó)家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條件,對(duì)土地實(shí)行征購(gòu)、征用或者收歸國(guó)有。”接續(xù)這一規(guī)定的內(nèi)在邏輯,第7條則修改為:農(nóng)村人民公社經(jīng)濟(jì)是社會(huì)主義勞動(dòng)群眾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jì),現(xiàn)在一般實(shí)行公社、生產(chǎn)大隊(duì)、生產(chǎn)隊(duì)三級(jí)所有,而以生產(chǎn)隊(duì)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chǎn)大隊(duì)在條件成熟的時(shí)候,可以向大隊(duì)為基本核算單位過渡。在保證人民公社集體經(jīng)濟(jì)占絕對(duì)優(yōu)勢(shì)的條件下,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jīng)營(yíng)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yè),在牧區(qū)還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值得關(guān)注的是,1982年憲法即現(xiàn)行憲法規(guī)定了城市土地的無償國(guó)有化。[8]該憲法第10條的規(guī)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guó)家所有。農(nóng)村和城市郊區(qū)的土地,除由法律規(guī)定屬于國(guó)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國(guó)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對(duì)土地實(shí)行征用。任何組織或者個(gè)人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zhuǎn)讓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gè)人必須合理地利用土地。”由此,通過修改1978年憲法,在1982年憲法中增加了關(guān)于城市土地屬于國(guó)有的規(guī)定,其意義更像是一場(chǎng)革命,即不設(shè)定任何產(chǎn)權(quán)變更及認(rèn)證手續(xù),便實(shí)現(xiàn)了城市土地的國(guó)有化。1982年憲法在城市土地的無償國(guó)有化方面的規(guī)定,在客觀上使政府壟斷了土地所有權(quán)的權(quán)益。這一過程主要是通過1988年憲法修正案、1990年的國(guó)土13號(hào)文④和1995年的《確定土地所有權(quán)和使用權(quán)的若干規(guī)定》⑤等實(shí)現(xiàn)的,將城市私有土地財(cái)產(chǎn)以“自然享有土地使用權(quán)”的形式沿襲了下來。
從1980年代起,中國(guó)開始了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改革主要分兩方面進(jìn)行。一是土地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1986年國(guó)家通過了《土地管理法》,成立了國(guó)家土地管理局。二是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大體思路是把土地的使用權(quán)和所有權(quán)分離。在使用權(quán)上,變過去無償、無限期使用為有償、有限期使用,使其真正按照商品的屬性進(jìn)入市場(chǎng)。⑥按照土地所有權(quán)與使用權(quán)分離的原則,國(guó)家在保留土地所有權(quán)的前提下,通過拍賣、招標(biāo)、協(xié)議等方式將土地使用權(quán)以一定的價(jià)格、年期及用途出讓給使用者,出讓后的土地可以轉(zhuǎn)讓、出租、抵押。這可以說是中國(guó)土地使用制度上有根本性的改革,因?yàn)樗蚱屏送恋亻L(zhǎng)期無償、無限期、無流動(dòng)、單一行政手段的劃撥制度,創(chuàng)立了以市場(chǎng)手段配置土地的制度。1992年進(jìn)一步確立了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和土地市場(chǎng)培育的進(jìn)程。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形成一個(gè)土地市場(chǎng)體系和有效的資源配置體系。1995年的《協(xié)議出讓國(guó)有土地使用權(quán)最低價(jià)確定辦法》,則利出一孔,加強(qiáng)了國(guó)家對(duì)土地使用權(quán)出讓的壟斷。
通過梳理以上歷程可以發(fā)現(xiàn),以1982年憲法為分水嶺,將土地所有制度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gè)時(shí)期,即土地從私有制轉(zhuǎn)變?yōu)閲?guó)有制。然而,私有與國(guó)有概念并不足以作為有效的土地問題分析框架,無法通過文本去認(rèn)識(shí)土地制度的現(xiàn)行運(yùn)作及其癥結(jié)所在,也無法探究土地問題的根源。由于該分析框架與現(xiàn)實(shí)運(yùn)作之間的脫節(jié),導(dǎo)致我們無法認(rèn)識(shí)與理解土地作為一項(xiàng)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法律屬性以及由此法律屬性而產(chǎn)生的身份權(quán)利之特性,尤其是在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與實(shí)踐領(lǐng)域內(nèi),它恰足以掩蓋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內(nèi)涵。
三、土地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屬性之分析
土地作為一項(xiàng)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其核心乃在于地租分配與土地使用兩方面,此即人地關(guān)系的兩個(gè)核心維度。兩者是可以并且必須分開的,這構(gòu)成了土地制度的一體兩面。這也是公(國(guó))有—私有權(quán)屬劃分框架所無法兼顧的。在地租分配—土地使用的分析框架下,無論城市土地還是農(nóng)村土地都可以進(jìn)行分析,從而可以很好地解決公有—私有框架下所掩蓋的內(nèi)容。
臺(tái)灣學(xué)者李鴻毅指出:“土地法者,乃規(guī)范土地關(guān)系之法律。人類社會(huì)之土地關(guān)系,大別有二:一為因使用土地所建立人與人間之土地權(quán)利關(guān)系,即土地分配關(guān)系;二為因使用土地而發(fā)生人與地間之直接關(guān)系,即土地利用關(guān)系。”[9]如果我們對(duì)土地制度做一個(gè)歷史的宏觀列舉,無論是井田制、均田制、占田制、屯田制、村社制、族田制等等,土地制度無論其表現(xiàn)為何種形態(tài),均包含收益分配(地租)和土地利用(使用)兩個(gè)方面。地租的差異源于土地作為財(cái)產(chǎn)的有限性與差別性,而使用制度則是運(yùn)用法律或政策對(duì)前者加以調(diào)整,并以此為基礎(chǔ),形成特殊的身份權(quán)利,即人地關(guān)系的法權(quán)安排。而此種身份權(quán)利的固化與改變(無論是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均是關(guān)系一個(gè)社會(huì)穩(wěn)定與否的重要因素。從而,這也就決定了此種考察的重要性。在此基礎(chǔ)上,我們可以更深入地探討我國(guó)城鄉(xiāng)土地制度存在的問題。
作為土地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屬性的第一個(gè)方面,地租及其分配是土地制度中的根本所在。從歷史經(jīng)驗(yàn)的層面上看,沒有解決好地租分配問題,例如少數(shù)人壟斷土地收益(與收益的壟斷相比,經(jīng)營(yíng)方面的土地集中或兼并其實(shí)并不可怕),社會(huì)矛盾便會(huì)非常尖銳,如果無法解決的話,往往訴諸革命暴力。揆諸歷史,法國(guó)大革命、俄國(guó)革命、中國(guó)革命等由土地問題所引發(fā)的解決斗爭(zhēng)是非常殘酷的。
作為土地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屬性的第二個(gè)方面,土地使用制度從邏輯上講就是地租分配的制度化。它的核心在于土地的流轉(zhuǎn),即土地作為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交換價(jià)值之實(shí)現(xiàn)。這既包括實(shí)物地租的貨幣化,也包括土地使用權(quán)利方式的變更。中國(guó)歷代的土地改革,核心是“收入”增加的實(shí)現(xiàn)。從公元前594年魯國(guó)的“初稅畝”——初次對(duì)土地征稅開始,增加收入之目的貫穿始終。需要注意的是,“畝”是“私田”。[10]這次土地改革,是為增加政府的收入而對(duì)“私田”征“稅”。中國(guó)歷代的土地改革,無論是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唐朝的“兩稅法”、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和方田均稅法、明朝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地,還是開始于改革開放初期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和當(dāng)下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都是為了“收入”。
以地租和土地使用制度來衡量的話,如前所述,我們并沒有從這一維度對(duì)建國(guó)后歷次有關(guān)土地問題的法律進(jìn)行考察,而是集中于權(quán)屬的變更。建國(guó)后的農(nóng)村集體化過程中所建立的是村社土地制度,使用方式是共耕,而實(shí)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后則是均地。原來的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中,基于法律規(guī)定,土地屬于集體所有,則村社成員均享地租收益,即法理意義上的增人必增份,減人必減份。在這個(gè)意義上,實(shí)際上任何人種地都是在向村集體租地種,從而,無論是土地集體所有、國(guó)家所有還是個(gè)人所有都失去其意義。筆者將這種基于村社或村集體成員而產(chǎn)生的享有土地份額的權(quán)利稱之為土地的身份權(quán)利,也即基于該身份而享有的地租收益的權(quán)利。此權(quán)利無論城鄉(xiāng)均適用,只不過是身份權(quán)利指涉的具體對(duì)象不同而已。這種身份權(quán)利是維系社會(huì)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在村集體中,基于對(duì)地租的均享,實(shí)質(zhì)上弱化了成員的承包權(quán)。而基于效率的考慮,同時(shí)也限于規(guī)模,客觀上必然要求土地流轉(zhuǎn),土地流轉(zhuǎn)必然是而且只能是在土地承租人之間流轉(zhuǎn),以便有效解決土地經(jīng)營(yíng)細(xì)碎化的問題。⑦
在城市中,由于居住位置的差異,形成由中心區(qū)域到邊緣區(qū)域土地價(jià)格逐級(jí)落差的情況,而且不同地塊之地租差距較之農(nóng)地間差距更為復(fù)雜,也更為明顯,從而城市地租的分配遠(yuǎn)較農(nóng)村為繁復(fù)。依據(jù)現(xiàn)行憲法及土地管理法等的有關(guān)規(guī)定,城市土地屬于國(guó)有制,這會(huì)造成什么后果呢?它實(shí)際上使得基于城市土地之不同區(qū)位而產(chǎn)生的級(jí)差地租為少數(shù)私人占有,從而出現(xiàn)了土地利用方面嚴(yán)重的行政干預(yù)狀況。如果將城市土地視為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而不是以公有私有等屬性做劃分,則我們可以看到,土地所存在的問題,至少包括如下兩個(gè)方面:一是所有制管制導(dǎo)致行政權(quán)力侵犯經(jīng)濟(jì)產(chǎn)權(quán)。作為一項(xiàng)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無論是區(qū)分為集體所有權(quán)還是國(guó)有產(chǎn)權(quán),按照民法的基本精神,不同所有權(quán)應(yīng)當(dāng)是地位平等的。但我們可以看到,現(xiàn)在的國(guó)有產(chǎn)權(quán)與集體產(chǎn)權(quán)的權(quán)能根本不平等。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對(duì)于城市土地的利用,例如建設(shè)用地等,就必須進(jìn)行土地的征收或征用,把集體所有制的土地轉(zhuǎn)為國(guó)有制的土地。而按照1982年憲法的規(guī)定,集體所有制的土地不能進(jìn)入市場(chǎng)流通領(lǐng)域,國(guó)有土地則可以正常流通。如此,行政權(quán)力事實(shí)上是在侵犯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實(shí)質(zhì)則是對(duì)集體土地地租的壟斷與獨(dú)享,從而,便可以解釋為何在現(xiàn)階段征地補(bǔ)償方面的問題層出不窮。此處需要注意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土地作為一項(xiàng)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它的使用權(quán)的貨幣化實(shí)質(zhì)是將其一定時(shí)間段內(nèi)地租予以貨幣化,征地過程表面上是所有制形式的變更,但實(shí)際上掩蓋了地租權(quán)利的平衡交換與分配問題——當(dāng)然,其終級(jí)原因無庸諱言,乃是個(gè)人土地所有權(quán)或曰土地正義的闕失。
二是基于所有制的不同而呈現(xiàn)出管制過度和管制失效并存的現(xiàn)象。囿于所有制尤其是對(duì)國(guó)有土地的意識(shí)形態(tài)方面的保護(hù),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了極為嚴(yán)格的程序,從流通角度而言,無疑是 “管制過度”;但另一面,則是管制失效,即過于嚴(yán)格的程序在現(xiàn)實(shí)中無法實(shí)施,以致淪為具文。從而,違法現(xiàn)象尤其是違反土地管理法律現(xiàn)象便無法禁止。
以上兩個(gè)方面的問題,如果我們僅從土地性質(zhì)變更的角度去觀察的話,可能只看到表面上的不公平,而難以窺視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回到筆者前述對(duì)于1982年憲法中關(guān)于土地權(quán)屬的規(guī)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guó)家所有”——法律并沒有明確指出城市的邊界,是按行政區(qū)劃還是按自然地理特征來界定?如果按自然地理特征來界定“城市”,例如北京的城市僅限于“紫禁城”,西安的城市僅限于內(nèi)城,則并不具備法律上的可操作性。如果按行政區(qū)劃來界定“城市”,則會(huì)造成憲法不同條款之間的彼此矛盾。在城市化過程中,伴隨著諸如“舊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等名目,事實(shí)上造成了“城市”沒有法律的邊界,處于隨時(shí)隨意地?cái)U(kuò)張的狀態(tài),從而,就呈現(xiàn)出上文所分析的管制過度和管制失效并存的現(xiàn)象。在中國(guó)的法律語境中,除由法律規(guī)定屬于農(nóng)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外,其他的土地均屬國(guó)家所有。甚至我們可以將這個(gè)問題推到極致,全中國(guó)的土地在理論上都有可能全部劃歸為城市,即全部屬于國(guó)有。從而,近年來各級(jí)地方政府經(jīng)常舉著“城市化”的旗幟圈占城郊農(nóng)民的土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獲取農(nóng)村土地國(guó)有化的收益,以填充空虛的地方財(cái)政。因?yàn)椋俺鞘谢本褪浅鞘行姓^(qū)控制的土地面積不斷擴(kuò)大,而農(nóng)村土地一旦歸入城市的范圍,也就自然而然地“國(guó)有化”了。如此,則“城市化”程度越高,土地國(guó)有化程度也越高。伴隨這種國(guó)有化程度趨高過程的是,基于土地而形成的身份權(quán)利的喪失。
筆者之所以反對(duì)公有?私有或國(guó)有?集體所有這樣的權(quán)屬劃分,已如前所述,正是因?yàn)樗赡苷`導(dǎo)甚至掩蓋了土地作為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本質(zhì),從而無法避免也不能解決因城市化進(jìn)程的擴(kuò)張而導(dǎo)致的權(quán)屬變更所帶來的權(quán)利保護(hù)問題。質(zhì)言之,在集體所有的土地向國(guó)有土地轉(zhuǎn)化過程中,或者說是集體所有的土地作為一項(xiàng)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在市場(chǎng)進(jìn)行流通的過程中,因法律設(shè)置的原因而造成其地租收益被獨(dú)占的局面,從而在客觀上造成了基于此種土地關(guān)系而形成的身份權(quán)利被剝奪的現(xiàn)象,最終會(huì)造成一種偽城市化或反城市化,甚至地域與族群沖突等的后果。
四、土地的財(cái)產(chǎn)屬性與身份權(quán)利的法權(quán)安排
在明確了土地具有的地租分配制度與土地使用的內(nèi)在屬性之后,我們將觀察的視角放回到現(xiàn)實(shí)。無論是集體所有還是國(guó)有土地,無論是表現(xiàn)在前者的經(jīng)營(yíng)細(xì)碎化與不規(guī)模化和所謂的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農(nóng)民等的“三農(nóng)問題”,還是表現(xiàn)在后者的個(gè)人房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與土地權(quán)屬的分離,尤其是土地正義的闕失,其關(guān)鍵處都在于以權(quán)屬問題掩蓋土地的財(cái)產(chǎn)屬性問題,忽略或否定在地租分配與土地使用方面應(yīng)做出的法律規(guī)定與法權(quán)安排,從而導(dǎo)致基于土地之利用和分享而形成的身份權(quán)利處于不穩(wěn)定甚至被剝離狀態(tài)。筆者此處所用的身份權(quán)利的概念,并非社會(huì)學(xué)與政治學(xué)意義上的公民身份權(quán)利,實(shí)質(zhì)上可以說是公民身份權(quán)利的下位概念,即基于土地制度而形成的社會(huì)職業(yè)身份所具有的對(duì)地租分配與土地使用得以主張的權(quán)利,該項(xiàng)權(quán)利因其身份而獲得,并由法律保障實(shí)施。例如,在村社體制下,農(nóng)民作為村集體的成員,原來的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或者村社成為一個(gè)地租的收集者。村社成員均享地租收益,“增人必增份,減人必減份”。此種權(quán)利因其身份而獲得,除非拋棄這一身份,否則只要沒有喪失掉身份,便仍可以在村社里面取得地租收益。村社成員的身份權(quán)利乃是一項(xiàng)特權(quán),不妨礙其他公民權(quán)利的獲得。而這種身份權(quán)利在城市化進(jìn)程當(dāng)中,則表現(xiàn)為土地進(jìn)入流通領(lǐng)域后的社會(huì)保障問題,即農(nóng)民向市民之間的轉(zhuǎn)變,這是城市化過程中的當(dāng)然之意。而此種社會(huì)保障的實(shí)現(xiàn),實(shí)際上是地租的貨幣轉(zhuǎn)化對(duì)身份權(quán)利的保障。這一身份權(quán)利的保障才是法理意義上現(xiàn)代社會(huì)政治認(rèn)同的最終完成。
正是基于對(duì)當(dāng)下城市化進(jìn)程中土地尤其是集體土地向國(guó)有土地轉(zhuǎn)化方面存在的現(xiàn)實(shí)問題的考察,例如征地、拆遷等問題無一不在叩問土地制度的合理性與否;鑒于土地問題在中國(guó)的特殊意義,土地作為一項(xiàng)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就其運(yùn)作而言,由于立法領(lǐng)域內(nèi)人為的權(quán)屬區(qū)劃,導(dǎo)致其財(cái)產(chǎn)屬性被虛置,在公有—國(guó)有概念的語境中,土地所有權(quán)的真正歸屬無法在立法層面落實(shí)與突破,從而正如我們?cè)?982年憲法中看到的那樣,城市土地屬于國(guó)有的規(guī)定,客觀上使集體土地處在不穩(wěn)定狀態(tài)之中;作為一項(xiàng)基礎(chǔ)性權(quán)利,它不可避免地指向?qū)τ诠矙?quán)力的邊界的追問,對(duì)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的追問。從而,筆者認(rèn)為,在更深層次的意義上,土地問題事關(guān)權(quán)力本身的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的正當(dāng)性。質(zhì)言之,它是關(guān)乎國(guó)家的德性的問題[3],身份權(quán)利的法權(quán)安排其意義恰在于回答此一問題,并形成對(duì)于政治合法性的判斷,屬于一種政治過程與政治建設(shè)。
自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由于1982年憲法中對(duì)于城市土地國(guó)有性質(zhì)的確認(rèn),使其得以進(jìn)入流通領(lǐng)域,即土地作為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進(jìn)行交換。但必須指出的是,相對(duì)以前的土地政策,公權(quán)力對(duì)于地租的壟斷是顛覆性的,在客觀上否定了自土地革命以來政權(quán)的歷史合法性,進(jìn)而損害了執(zhí)政的現(xiàn)實(shí)合法性。在此過程中,公權(quán)力不是作為服務(wù)者而是作為營(yíng)利者存在的,由于公權(quán)力對(duì)于地租分配的壟斷,便出現(xiàn)了諸如政府進(jìn)行“強(qiáng)制拆遷”的現(xiàn)象,勢(shì)必導(dǎo)致對(duì)公權(quán)力行使的合憲性拷問,公共權(quán)力的邊界在哪里,“公共利益”的范圍等,均大成問題。更具有本質(zhì)意義的是,由于制度設(shè)計(jì)的不當(dāng),整個(g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政府投資所建的公共設(shè)施導(dǎo)致的土地增值,最后歸少數(shù)私人所有。這也是造成地方政府土地財(cái)政的原始沖動(dòng)的制度性病因。土地權(quán)屬變更所形成的土地增值部分本應(yīng)歸公,但實(shí)際上是增值紅利成了公權(quán)力與開發(fā)商之間的分紅。現(xiàn)行的土地政策培養(yǎng)了一個(gè)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階層,一個(gè)專門的地租掠奪者。我國(guó)的房地產(chǎn)業(yè)很大程度上便是建立在貨幣化的地租的尋租模式之上的。
就土地使用制度層面而言,由于1982年憲法對(duì)于城市土地的性質(zhì)界定,“城市”界限的擴(kuò)張?jiān)诶碚撋鲜菬o邊界的。基于兩種土地權(quán)屬性質(zhì)的劃分,公權(quán)力的介入使得“國(guó)有”極易將集體土地納入囊中,而且成本極低。這事實(shí)上是利用行政權(quán)力對(duì)土地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屬性中的地租進(jìn)行掠奪,從而,農(nóng)民基于土地而形成的身份權(quán)利在面臨土地征收時(shí)變得極為脆弱,亦即無法實(shí)現(xiàn)從村民到市民的轉(zhuǎn)化。而原有的村社體系被打破之后,基于村社共同體內(nèi)部共有制而形成的身份權(quán)利喪失,始終無法成為城市化進(jìn)程中的參與者。就城市而言,因憲法規(guī)定土地屬于國(guó)家所有,土地使用者僅僅對(duì)其地上附著物享有所有權(quán),而對(duì)土地并無權(quán)利主張,最基本的土地權(quán)利在法律層面闕如,直接后果便是導(dǎo)致其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脆弱性。例如,“七十年所有權(quán)”之類的論述,恰恰是因?yàn)楣珯?quán)力對(duì)土地所有權(quán)的壟斷,邏輯上導(dǎo)致對(duì)地租的壟斷,從而使土地使用制度客觀上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
上述兩者作為土地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必然內(nèi)涵,因其法理意義上的闕漏,使得身份權(quán)利無從落實(shí),集體土地上的身份權(quán)利面對(duì)國(guó)有土地權(quán)屬擴(kuò)張時(shí)無從自我保護(hù)。這既是因?yàn)榧w土地經(jīng)營(yíng)模式的不規(guī)模性與村社土地權(quán)屬在立法層面的缺陷所致,又是因?yàn)榉伤?guī)定的地權(quán)使用制度中對(duì)于地租的壟斷所致。兩者相互作用,一方面使得村社即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營(yíng)體系瓦解,身份權(quán)利崩潰,另一方面使得城市化進(jìn)程中地租為少數(shù)私人所壟斷,身份權(quán)利同樣處于脆弱狀態(tài),土地財(cái)政的存在又加劇了這一現(xiàn)象。從而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征地拆遷撤村并居的城市化如火如荼,一方面是社會(huì)保障體系的滯后,新的身份權(quán)利沒有建立起來,城鄉(xiāng)沖突甚或有演變成族群沖突的可能性。中國(guó)城市化的真正障礙,很有可能是沒有采取適當(dāng)?shù)氖侄纹骄貦?quán),實(shí)現(xiàn)地租的社會(huì)成員共享均享。
五、成熟地權(quán)與國(guó)家治理
依據(jù)前述分析,現(xiàn)行法律層面關(guān)于土地制度的規(guī)范,足以消解乃至否定地權(quán)的財(cái)產(chǎn)屬性,從而使建立在土地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體系上的一系列權(quán)利均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地租為少數(shù)私人所壟斷,在城市化進(jìn)程中,公權(quán)力以低成本的權(quán)屬變更方式跑馬圈地,打破了原有的社會(huì)保障格局。而土地使用直接受公權(quán)力支配,造成行政權(quán)力對(duì)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宰制,否定與破壞了市場(chǎng)流通領(lǐng)域中作為經(jīng)營(yíng)主體的地權(quán)所有者的主體性,導(dǎo)致權(quán)利救濟(jì)的缺位。這一進(jìn)程所造成的更為嚴(yán)重的后果是使被圈占土地上的身份權(quán)利喪失,而由于土地使用制度的內(nèi)在缺陷,新的身份權(quán)利保障無法建立,救濟(jì)便無從談起。
我們可以看到,展現(xiàn)在現(xiàn)實(shí)層面上的問題是由于土地地權(quán)的不成熟而導(dǎo)致的深層次的城鄉(xiāng)隔閡,社會(huì)保障體系的滯后,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或者放棄農(nóng)業(yè)操作的農(nóng)民工,尤其是那些已經(jīng)習(xí)慣了都市生活、徹底抗拒鄉(xiāng)村的新生代民工,受制于身份權(quán)利的闕失,始終無法被城市接納。同樣由于土地使用制度的法律闕失,失地者無法也不可能分享城市地租,而城市化進(jìn)程在對(duì)鄉(xiāng)村秩序與生活環(huán)境的破壞的同時(shí),因?yàn)橥恋丶t利為少數(shù)私人所獨(dú)享,以至于國(guó)家無力建立起切實(shí)有效的社會(huì)保障系統(tǒng)。我們可以看到,失地農(nóng)民或農(nóng)民工進(jìn)城之后由于無法分享城市化的利益,轉(zhuǎn)而形成了以農(nóng)民工為主體的農(nóng)村,即城市中的農(nóng)村。因此,這就形成了一個(gè)全新的問題,即傳統(tǒng)意義上的農(nóng)村問題,很大程度上集中到了城市。因身份權(quán)利的喪失與城市社保的排斥,可能爆發(fā)城市本土和寄居在、混雜在城市中的農(nóng)村之間的城鄉(xiāng)沖突,甚至地域沖突乃至族群沖突。亨廷頓在其《變化社會(huì)中的政治秩序》中分析革命的城市因素時(shí),曾對(duì)由農(nóng)村轉(zhuǎn)向城市的移民群體做了代際比較,移民第二代較之于第一代因既無法融入城市身份又無法與農(nóng)村保持聯(lián)系而成為不穩(wěn)定的因素,乃是因?yàn)樗麄冊(cè)谏鐣?huì)上缺乏固定的地位。[11]此種地位,即為身份權(quán)利。事實(shí)上,綜觀晚近幾年來的所謂城鄉(xiāng)之間的群體性事件,尤其是具有族群沖突特征的外來農(nóng)民工與城市土著居民之間的沖突,日益呈現(xiàn)出流民問題的跡象。而究其根源,則在于土地制度之非正義性所導(dǎo)致的身份權(quán)利之缺位,土地確權(quán)闕失,法權(quán)安排無從落實(shí),最終指向國(guó)家德性之不足。
因土地制度而形成的身份權(quán)利之所以指涉政治正義問題,原因在于,以土地作為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為基礎(chǔ)而形成一整套的法權(quán)安排,可以開啟合理的政治過程與政治建設(shè)。甚至可以說,良善的土地制度以及有保障的身份權(quán)利是決定城市化進(jìn)程能否成功的最終因素。
從比較視角來看,近代英國(guó)是最早開啟土地問題改革的國(guó)家。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由于圈地運(yùn)動(dòng)而造成大批農(nóng)民失地,但晚近的考察表明,圈地主要針對(duì)公有地進(jìn)行[12, 13],當(dāng)然在此過程中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農(nóng)村土地權(quán)屬的變更和大批失地農(nóng)民。這一方面為機(jī)器大工業(yè)提供了充足的勞動(dòng)力,另一方面,與圈地運(yùn)動(dòng)并行的是,身份權(quán)利的重新確立與保障也成為消弭社會(huì)動(dòng)蕩、促使新秩序穩(wěn)步確立的強(qiáng)有力因素。新的身份權(quán)利的確立是以濟(jì)貧法為主要依據(jù)的。針對(duì)圈地運(yùn)動(dòng)迫使眾多農(nóng)民背井離鄉(xiāng),失業(yè)現(xiàn)象日益嚴(yán)重,1572年英格蘭和威爾士開始征收濟(jì)貧稅,1576年又設(shè)立教養(yǎng)院,收容流浪者,并強(qiáng)迫其勞動(dòng)。1662年斯圖亞特王朝通過《住所法》,規(guī)定貧民須在其所在的教區(qū)居住一定年限者方可獲得救濟(jì)。1723年的濟(jì)貧法更進(jìn)一步規(guī)定設(shè)立習(xí)藝所,受救濟(jì)者必須入所。1834 年英國(guó)通過了“濟(jì)貧法修正案”,即“新濟(jì)貧法”。[14, 15]濟(jì)貧法的實(shí)施,為那些因原有的土地關(guān)系變更而喪失身份權(quán)利的失地者賦予新的身份,經(jīng)由適應(yīng)城市生產(chǎn)方式而獲得市民身份,實(shí)現(xiàn)身份權(quán)利的重塑。而大革命之所以沒有在英國(guó)爆發(fā),很大原因就在于基于土地的身份權(quán)利之重新塑造過程,英國(guó)取得了成功。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國(guó)大革命實(shí)質(zhì)是脫離土地的農(nóng)民——流民革命,而革命后的《拿破侖法典》正是從農(nóng)民和土地問題入手來解決嚴(yán)峻的社會(huì)問題。[16]美國(guó)自19世紀(jì)20年代工業(yè)化進(jìn)入加速期也面臨著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向城市的轉(zhuǎn)移,與美國(guó)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的全面展開是同步的,而美國(guó)的例外與幸運(yùn)之處便在于西部領(lǐng)土的開發(fā),1862年林肯政府頒布《宅地法》,旨在無償分配美國(guó)西部國(guó)有土地給廣大移民,確立了小農(nóng)土地所有制。德國(guó)自19世紀(jì)中葉相繼頒布《職業(yè)自由法》和《遷徙自由法》等法案,為農(nóng)民向城市的流動(dòng)就業(yè)掃清了各種體制上的障礙。而真正的身份權(quán)利的確立則是在19世紀(jì)80~90年代所謂的“俾斯麥型社會(huì)保障模式”建立之后,將脫離土地的工人的身份權(quán)利以社保形式予以保障,從而避免了農(nóng)村與城市之間的隔閡和族群之間的對(duì)立。從這一意義上講,1871年德意志的統(tǒng)一只是完成了政治上的整合,真正的國(guó)家整合與國(guó)家認(rèn)同則是在社保體系身份權(quán)利建立之后。
六、結(jié)論
綜上所述,1982年憲法對(duì)于城市土地權(quán)屬的規(guī)定,將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屬性中的所有權(quán)虛置,客觀上導(dǎo)致了無法通過核析界定權(quán)屬的方式解決因土地變更而產(chǎn)生的糾紛、沖突與對(duì)抗,尤其是當(dāng)公權(quán)力以國(guó)家的名義行使土地確權(quán)之時(shí),由于依權(quán)屬劃分之區(qū)別而造成的土地使用制度具有內(nèi)在的低成本擴(kuò)張傾向。特別是在應(yīng)對(duì)城市化進(jìn)展與分稅制下土地財(cái)政的雙重驅(qū)動(dòng)下,該種擴(kuò)張無論是征地還是拆遷等,均直接造成原有的對(duì)于地租之分享而形成的身份權(quán)利的破壞,進(jìn)而更為嚴(yán)重的是,它形成了對(duì)公權(quán)力合法性與正當(dāng)性的否定,將建立于土地革命基礎(chǔ)上的歷史合法性流失殆盡,同時(shí)現(xiàn)實(shí)合法性無從建立,國(guó)家德性便無從談起了。
土地制度及由其引生出來的身份權(quán)利從邏輯上指向了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而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保障與落實(shí)又指向了政治層面的合法性與國(guó)家治理的正當(dāng)性維度。由于土地具有內(nèi)在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屬性,事實(shí)上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gè)極具操作性的破解此種法律僵局的切入點(diǎn),即以地租的享有與土地使用制度的合理化設(shè)置為基礎(chǔ)塑造新的身份權(quán)利,消弭因土地權(quán)屬劃分所造成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啟動(dòng)政治正義的建設(shè)過程,從而得以政治正義化解具體法律正義(立法)不足引發(fā)的公權(quán)力正當(dāng)性不足問題,進(jìn)而以迂回側(cè)擊的進(jìn)去方式實(shí)現(xiàn)法權(quán)安排。
因此,如果從土地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屬性入手,以具體的制度性安排,例如土地承包權(quán)的固化和城市地租的均享等的技術(shù)理性措施,為法律層面的突破提供制度資源與技術(shù)積累,從而漸次將轉(zhuǎn)變?yōu)榭刹僮鞯募夹g(shù)問題,不失為一種解決之道。那么,規(guī)制意義上立法的局限性與潛在危害性(此種危害性已顯現(xiàn))完全可以通過能動(dòng)性的司法方式加以解決。最終,通過建立成熟的土地權(quán)利,實(shí)現(xiàn)良善的國(guó)家治理。
注釋:
① 《中國(guó)土地法大綱》確立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參見中央檔案館編.解放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土地改革文件選輯.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1: 84-88.
② 在德國(guó),土地所有者對(duì)土地的最廣泛和最絕對(duì)的權(quán)力,是與土地的社會(huì)責(zé)任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參見《德國(guó)民法典》第903條和德國(guó)基本法第14條第3款。
③ 關(guān)于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參見[美]H·登姆塞茨.“關(guān)于產(chǎn)權(quán)的理論”、[美]A·A·阿爾欽.“產(chǎn)權(quán):一個(gè)經(jīng)典注釋”,[美]R·科斯. A·阿爾欽、D·諾斯.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與制度變遷:產(chǎn)權(quán)學(xué)派與新制度學(xué)派譯文集.劉守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6-112.166-178.
④ 參見《國(guó)家土地管理局關(guān)于城市宅基地所有權(quán)、使用權(quán)等問題的復(fù)函》(1990年4月23日國(guó)家土地管理局 國(guó)土(法規(guī))字〔1990〕第13號(hào)). http://china.findlaw.cn/fagui/p_1/289961.html. 2012-12-5.
⑤ 參見《國(guó)家土地管理局關(guān)于印發(fā)〈確定土地所有權(quán)和使用權(quán)的若干規(guī)定〉的通知》(1995年3月11日國(guó)家土地管理局[1995]國(guó)土[籍]字第26號(hào))。該《規(guī)定》“第二十七條:土地使用者經(jīng)國(guó)家依法劃撥、出讓或解放初期接收、沿用,或通過依法轉(zhuǎn)讓、繼承、接受地上建設(shè)物等方式使用國(guó)有土地的,可確定其國(guó)有土地使用權(quán)。第二十八條:土地公有制之前,通過購(gòu)買房屋或土地租賃土地方式使用私有的土地,土地轉(zhuǎn)為國(guó)有后迄今仍繼續(xù)使用,可確定現(xiàn)使用者國(guó)有土地使用權(quán)。”需要注意的是,該規(guī)定部分內(nèi)容已被《國(guó)土資源部關(guān)于修改部分規(guī)范性文件的決定》(2010年12月3日國(guó)土資源部 國(guó)土資發(fā)〔2010〕190號(hào))所修訂),http://china.findlaw.cn/fagui/p_1/288465.html. 2012-12-5.
⑥ 1982年,深圳特區(qū)開始按城市土地等級(jí)不同收取不同標(biāo)準(zhǔn)的使用費(fèi)。1987年4月國(guó)務(wù)院提出使用權(quán)可以有償轉(zhuǎn)讓,同年9月,深圳率先試行土地使用有償出讓。研究者普遍認(rèn)為這已具有了土地財(cái)政的雛形。
⑦ 關(guān)于這一問題,可參閱蕭錚其他論著及黃俊杰.中國(guó)農(nóng)村復(fù)興聯(lián)合委員會(huì)史料匯編.臺(tái)北:三民書局,1991:395-423.
[1] 張千帆. 城市土地“國(guó)家所有”的困惑與消解——重新解讀憲法第10條[J]. 中國(guó)法學(xué), 2012(3): 178?190.
[2] 張千帆. 城市化不需要征地——清除城鄉(xiāng)土地二元結(jié)構(gòu)的憲法誤區(qū)[J]. 法學(xué), 2012(6): 19?24.
[3] 許章潤(rùn). 地權(quán)的國(guó)家德性[J]. 比較法研究, 2010(2): 104?119.
[4] 達(dá)馬熙克. 土地改革論[M]. 張丕介, 譯. 北京: 建國(guó)出版社,1947: 63?68.
[5] 蕭錚. 中華地政史[M]. 臺(tái)北: 商務(wù)印書館, 1984.
[6] 趙岡, 陳鐘毅. 中國(guó)土地制度史[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97?132.
[7] 陳登元. 中國(guó)土地制度[M]. 上海: 上海商務(wù)印書館, 1932: 425?428.
[8] 王維洛. “1982年的一場(chǎng)無聲無息的土地‘革命’——中國(guó)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國(guó)有化的?”[J]. 當(dāng)代中國(guó)研究, 2007(4): .
[9] 李鴻毅. 土地法論[M]. 臺(tái)北: 三民書局, 1984: 1.
[10] 程念祺. 國(guó)家力量與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歷史變遷[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60?62.
[11] 塞繆爾·P 亨廷頓. 變化社會(huì)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華, 劉為, 等譯. 上海: 上海世紀(jì)出版集團(tuán), 2008: 234.
[12] 咸鴻昌. 圈地運(yùn)動(dòng)與英國(guó)土地法的變革[J]. 世界歷史, 2006(5): 61?68.
[13] 王田田. 英國(guó)圈地運(yùn)動(dòng)中的法律規(guī)制[J]. 求是學(xué)刊, 2009(1): 92?96.
[14] 尹虹. 近代早期英國(guó)流民問題及流民政策[J]. 歷史研究, 2001(2): 111?123.
[15] 尹虹. 論十七、十八世紀(jì)英國(guó)政府的濟(jì)貧問題[J]. 歷史研究, 2003(2): 128?143.
[16] 馬克?布洛赫. 法國(guó)農(nóng)村史[M]. 余中先, 張朋浩, 等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 2008: 172?218.
Establishing right of the land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WANG Jinwen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he dual land system of the urban and rural stipulated by the 10th articl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PRC 1982 gives rise to the following results. On the one hand, the city’s boundary is not clear, and there exists the possibility of unlimited expan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llective land is in an unstable state because of the involvement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so that problems occur such as the loss of the owning right of the land. This essay analyses the constitutional change about land ownership from 1954 to 1982, holding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state-owned land and private land should be abandoned, that a new on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operty right of the land with person-land relation as the core. In this way,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ty right can be constructed so that the proprietary right of the land can be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ownership property, to establish a new system of status right and to actualize the legality and justness of modern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the dual land system; proprietary right; status right;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D90-059
A
1672-3104(2015)04?0053?08
[編輯: 蘇慧]
2015?04?08;
2015?05?18
國(guó)家社科基金青年項(xiàng)目“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流轉(zhuǎn)視角下的社會(huì)公平正義研究”(10CFX009);國(guó)家社科基金重大項(xiàng)目“加快建設(shè)法治中國(guó)研究”(13&ZD032);中南大學(xué)科學(xué)研究基金(2014JSJJ044)
王進(jìn)文(1980?),男,山東濰坊人,法學(xué)博士,中南大學(xué)法學(xué)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