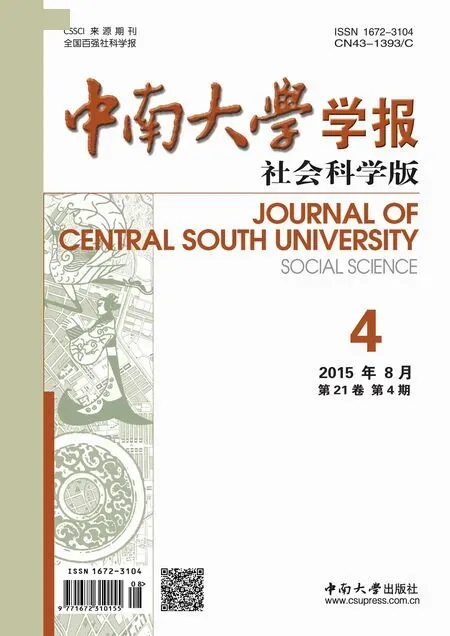行政處罰功能定位之檢討
陳太清,徐澤萍
(南京理工大學(xué)法學(xué)系,江蘇南京,210094;江蘇億城律師事務(wù)所,江蘇南京,210013)
行政處罰功能定位之檢討
陳太清,徐澤萍
(南京理工大學(xué)法學(xué)系,江蘇南京,210094;江蘇億城律師事務(wù)所,江蘇南京,210013)
學(xué)界通常將行政處罰功能定位為懲罰,以示與其他行政行為乃至他類法律制裁的區(qū)別。然此等功能特征有其既定疆域,即以非制裁行政行為作為參照系。一旦沖破該疆域,將懲罰拔高至處罰與他類法律制裁在功能上的分野,超損害之懲罰論勢(shì)必走上前臺(tái),造成懲罰與補(bǔ)償?shù)膶?duì)立。懲罰的“超損害性”解讀,存在報(bào)應(yīng)不公、放縱違法、前提可疑、操作困難等諸多缺失。為維護(hù)法律制裁的體系統(tǒng)一性與功能完整性,保障行政處罰違法阻卻與公益損害救濟(jì)雙重作用的發(fā)揮,對(duì)處罰的懲罰功能宜界定為第二性行政義務(wù)的科加,并僅限于用以區(qū)分行政處罰與非制裁行政行為。
行政處罰;法律制裁;懲罰性;補(bǔ)償性
耶林曾指出,目的是“整個(gè)法的創(chuàng)造者”[1](234)。功能往往與目的具有相同的含義①,合理的功能定位是制度設(shè)計(jì)必須首先解決的問(wèn)題。現(xiàn)有行政處罰理論非常重視處罰功能研究。通說(shuō)認(rèn)為,行政處罰的功能旨在懲罰違法相對(duì)人。為行文之便,本文將此論稱為“懲罰論”。以主張之苛緩程度之不同,“懲罰論”又可分為廣義“懲罰論”與狹義“懲罰論”。前者認(rèn)為,任何對(duì)行為人依法施加的任何不利后果均為懲罰。后者認(rèn)為,僅在對(duì)行為人所施加的不利后果超過(guò)違法損害時(shí)方為懲罰。廣義“懲罰論”的提出,本是基于區(qū)分行政處罰與其他行政行為的需要。然而,自該論提出之后,其使用出現(xiàn)了擴(kuò)大化趨勢(shì),即不再限于行政行為的內(nèi)部,而是擴(kuò)大到行政法領(lǐng)域之外,用于區(qū)分行政制裁與其他法律制裁,特別是民事制裁。②可是,廣義的“懲罰論”卻無(wú)法有效地把行政處罰與他類法律制裁區(qū)分開(kāi)來(lái)。于是,出于滿足這一主觀動(dòng)機(jī)的需要,狹義“懲罰論”便在不經(jīng)意間走上前臺(tái)。
令人遺憾的是,狹義“懲罰論”打破了法律制裁功能配置上的既有平衡,客觀上導(dǎo)致了懲罰與補(bǔ)償?shù)亩獙?duì)立,給行政處罰理論與實(shí)踐帶來(lái)不小紛爭(zhēng)與困擾。伴隨著行政處罰的高頻運(yùn)用,諸如罰無(wú)定數(shù)、罰不止禁等問(wèn)題日益突出,處罰正當(dāng)性倍受拷問(wèn)。行政處罰社會(huì)觀感不佳,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其中,處罰功能定位失當(dāng),是造成這種尷尬境遇的重要原因之一。對(duì)行政處罰傳統(tǒng)功能定位——“懲罰論”進(jìn)行檢討,既是梳理和澄清理論歧見(jiàn)的需要,也是回應(yīng)處罰實(shí)踐、探尋處罰完善之道的邏輯起點(diǎn)。
一、行政處罰“懲罰論”及其類型
(一)“懲罰論”的形成
學(xué)界在研究行政處罰時(shí),通常先從內(nèi)涵上對(duì)處罰下一個(gè)定義,爾后從不同視角進(jìn)一步揭示其外延上之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功能上之特征。學(xué)者對(duì)于行政處罰功能之提煉,大多以其他行政行為作為參照,圍繞其法律制裁屬性加以展開(kāi)。雖在內(nèi)涵上并無(wú)大的不同,但在表述方式上主要有三種:制裁性[2?3],懲罰性[6?10],懲戒性[11](282)。
鄭玉波先生認(rèn)為,“法律之制裁者,乃國(guó)家為確保法律之效力,而對(duì)于違法者,所加之惡報(bào)也。惡報(bào)對(duì)于善報(bào)而言,善報(bào)所以勸善,惡報(bào)旨在懲罰。”[12](77)王利明教授在闡釋侵權(quán)行為法的功能時(shí),也指出“救濟(jì)功能、預(yù)防功能、制裁或懲罰功能,基本上概括了侵權(quán)責(zé)任法所應(yīng)當(dāng)具有的規(guī)范功能”[13](104)。可見(jiàn),制裁其實(shí)就是懲罰。從修辭學(xué)的角度看,以懲罰性來(lái)指代制裁之特征是沒(méi)有問(wèn)題的;反之,以制裁性作為特定制裁形式的行政處罰之特征,似有循環(huán)定義之嫌。懲戒與懲罰僅一字之差,“懲戒”包含有通過(guò)懲罰來(lái)勸誡與預(yù)防違法的意思,而對(duì)違法的勸誡與預(yù)防乃懲罰的應(yīng)有之意。懲戒將懲罰與告誡并立,有顯冗贅。此外,在行政法學(xué)科之外,一些學(xué)者為了說(shuō)明本部門法律制裁功能特征,也將行政處罰作為行政制裁之代表,給其貼上懲罰性的標(biāo)簽。[14, 15]
由此,無(wú)論是行政法領(lǐng)域之內(nèi)還是之外,將行政處罰功能定位為懲罰,即“懲罰論”,已成為理論界大多數(shù)學(xué)者約定俗成的表述。
(二)兩種懲罰觀
盡管學(xué)界對(duì)于將懲罰作為行政處罰的功能特征并無(wú)大的爭(zhēng)議,但對(duì)此等懲罰內(nèi)涵之解讀卻分化為兩種不同的主張。
一是廣義“懲罰論”,認(rèn)為懲罰即不利后果的科加,以楊建順、湛中樂(lè)教授為代表。楊建順教授認(rèn)為,“行政處罰是對(duì)違反行政法律規(guī)范尤其是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相對(duì)人的人身自由、財(cái)產(chǎn)、名譽(yù)或者其他權(quán)益的限制或者剝奪,或者對(duì)其科以新的義務(wù),體現(xiàn)了強(qiáng)烈的制裁性或者懲戒性。”[16](272)湛中樂(lè)教授認(rèn)為,行政處罰的懲罰性體現(xiàn)在“對(duì)違法相對(duì)方權(quán)益的限制、剝奪,或?qū)ζ淇埔孕碌牧x務(wù);這點(diǎn)使之既區(qū)別于刑事制裁、民事制裁,又區(qū)別于授益性的行政獎(jiǎng)勵(lì)行為與賦權(quán)性的行政許可行為”[2](228)。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湛中樂(lè)教授認(rèn)為此種懲罰不僅用于行政行為內(nèi)部區(qū)分,也可用于識(shí)別行政制裁與其他性質(zhì)法律制裁。
二是狹義“懲罰論”,主張只有“超額”制裁才是懲罰,代表學(xué)者主要有胡建淼、李孝猛教授等。胡建淼教授認(rèn)為,行政處罰的懲罰性在于當(dāng)事人必須為其違法行為付出比補(bǔ)償(或修復(fù)行為)更多的“代價(jià)”。[17, 18]李孝猛教授認(rèn)為:行政處罰的目的是為了懲罰,使相對(duì)人在一般法律義務(wù)之外承擔(dān)額外的義務(wù)。[19]二者均將責(zé)令類行為作為比較對(duì)象,強(qiáng)調(diào)處罰所施懲罰之“超額性”,主要分歧是一個(gè)將違法損害作為判斷“超額”與否的標(biāo)準(zhǔn),另一個(gè)則選擇了原行政義務(wù)。
實(shí)際上,違法損害與原行政義務(wù)在本質(zhì)上并無(wú)不同。行政主體實(shí)施行政處罰這種制裁,是因?yàn)橄鄬?duì)人違背其依法負(fù)有的行政義務(wù)。而行政法律規(guī)范之所以將這些事項(xiàng)確定為行政義務(wù),是基于對(duì)前述事項(xiàng)的違反將造成損害這一主觀判斷。簡(jiǎn)言之,違法損害是確定行政義務(wù)的原因,也是相對(duì)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行政義務(wù)的可能后果。由是,行政義務(wù)是一種主觀設(shè)定,違法損害則系一種客觀后果。
二、狹義“懲罰論”之缺失
懲罰論的提出,主要是建立在行政處罰與其他行政行為的區(qū)分上。一旦將行政處罰這一功能特征進(jìn)行擴(kuò)大化使用,即用以區(qū)分行政制裁與其他法律制裁,尤其是民事制裁,勢(shì)必導(dǎo)致狹義“懲罰論”的出現(xiàn),并產(chǎn)生廣泛而深遠(yuǎn)的影響。狹義“懲罰論”的懲罰主張,恰與以“等額性”為特征之補(bǔ)償相對(duì)應(yīng),不僅承襲了公私法劃分的二元主義立場(chǎng),而且與民法帝國(guó)關(guān)于賠償、違約金的類型劃分路徑一致,具有相當(dāng)?shù)奈ΑM瑫r(shí),廣義“懲罰論”者認(rèn)為懲罰包括施加新的義務(wù),在某種意義上部分承認(rèn)了狹義“懲罰論”者的主張。因此,對(duì)行政處罰功能定位的反思,關(guān)鍵是檢討?yīng)M義“懲罰論”。
將狹義“懲罰論”置于法律制裁體系、處罰類型與實(shí)踐操作等語(yǔ)境下進(jìn)行考量時(shí),可發(fā)現(xiàn)其存在諸多難以自圓其說(shuō)的缺失。
(一)違背法律制裁報(bào)應(yīng)觀,助長(zhǎng)主觀化積弊
法律制裁的正當(dāng)性基礎(chǔ)在于報(bào)應(yīng)與預(yù)防。報(bào)應(yīng)就是要將違法行為造成的損害反加諸行為人,而作為法律制裁的功利目的的預(yù)防須在報(bào)應(yīng)限度內(nèi)予以實(shí)現(xiàn)。公平報(bào)應(yīng)乃法律制裁之根基,已為現(xiàn)代法治所接受,如民事制裁以等額補(bǔ)償、刑事制裁以罪刑相適應(yīng)、行政制裁以過(guò)罰相當(dāng)為原則。狹義“懲罰論”,無(wú)論是以損害還是義務(wù)為標(biāo)準(zhǔn),均與過(guò)罰相當(dāng)原則抵觸,構(gòu)成了對(duì)公平報(bào)應(yīng)觀的違反。③這一違反可能導(dǎo)致行政處罰失去限度,助長(zhǎng)主觀化積弊,進(jìn)而動(dòng)搖其存在的正當(dāng)性根基。
(二)與“任何人不得從違法中受益”的法理沖突,無(wú)助于遏制違法
法諺云:“任何人不得從違法中受益。”“任何人”除了行為人外,理應(yīng)包括受害人。因?yàn)槿绻芎θ丝赏ㄟ^(guò)他人違法得到更多收益,那么他可能會(huì)放縱違法,社會(huì)成本也會(huì)隨之增加。[20]在行政處罰中,政府作為受損公益之代理人受領(lǐng)罰沒(méi)款物。而根據(jù)公共選擇理論,政府也是“經(jīng)濟(jì)人”,同樣存在利益最大化的驅(qū)動(dòng)。如果罰沒(méi)款物必須在價(jià)值上超出受損之公益,那么政府職能部門勢(shì)必放縱違法,導(dǎo)致公益與私益更為激烈的沖突。
(三)理論預(yù)設(shè)非一般性主張,結(jié)論可信度不高
結(jié)論要可信,立論前提須可靠。狹義“懲罰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行政處罰與責(zé)令類行為的比較。這一論證路徑,潛藏著責(zé)令類行為不屬于行政處罰的理論預(yù)設(shè)。然責(zé)令類行為與行政處罰的關(guān)系,無(wú)論是在立法還是學(xué)理上均存爭(zhēng)議。不少行政法律規(guī)范④,就是將責(zé)令類行為作為行政處罰具體類別加以規(guī)定的。學(xué)理上,至少有救濟(jì)罰說(shuō)[21](214?215)、申誡罰說(shuō)[22](119)、行為罰說(shuō)[23](27)等三種主張將責(zé)令類行為界定為行政處罰的具體類型。正因?yàn)橛腥绱酥嗟臓?zhēng)議存在,不宜將責(zé)令類行為不屬于行政處罰作為一般前提。
(四)“超額”與否,難以判斷
“超額”本是一種數(shù)量判斷,其能否順利進(jìn)行取決于用于比較的兩個(gè)事物是否可以量化或者是否具有同質(zhì)性。狹義“懲罰論”,無(wú)論選取違法損害,還是第一性義務(wù)作為判斷基準(zhǔn),均存在操作上的困難。行政違法所致的公益損害往往是一種無(wú)形損害,在很多情況下難以金錢計(jì)量。而且,處罰所施加的第二性義務(wù)與公益損害、第一性義務(wù)同質(zhì)的情形,在實(shí)踐中并不普遍。如此以來(lái),“超額”與否,難以進(jìn)行有說(shuō)服力的判斷。
三、“懲罰”之應(yīng)然內(nèi)涵
如前所述,行政處罰“懲罰論”是建立在其作為法律制裁屬性基礎(chǔ)之上的。而法律制裁除了行政制裁之外,尚存在諸如民事制裁、刑事制裁等形式。由此,不妨跳出行政法學(xué)科視野,站在法律制裁體系的高度來(lái)追尋懲罰的應(yīng)然內(nèi)涵。
(一)幾種常見(jiàn)的“懲罰”見(jiàn)解
除行政法學(xué)科外,對(duì)懲罰內(nèi)涵有較多涉及的學(xué)科還有法理學(xué)與民法學(xué),它們關(guān)于懲罰的見(jiàn)解或者判斷標(biāo)準(zhǔn)主要有以下幾種。
1. 不利后果論(或稱第二性義務(wù)論)
由于懲罰與法律制裁或者法律責(zé)任聯(lián)系十分密切,法理學(xué)者在研究后者時(shí),或多或少地會(huì)對(duì)懲罰的含義進(jìn)行探討。從總體上看,該領(lǐng)域?qū)W者對(duì)懲罰(性)的詮釋多持廣義立場(chǎng),認(rèn)為懲罰即對(duì)違反法律義務(wù)的行為人追加的一種不利后果(或者第二性義務(wù)),刑事制裁、行政制裁與民事制裁均具有懲罰功能。[24?27]
2. 過(guò)錯(cuò)歸責(zé)論
該說(shuō)認(rèn)為如果某一法律責(zé)任包含了對(duì)行為人主觀惡性的考量,那么它就是懲罰性的。這一觀點(diǎn)受到王澤鑒、王利明、崔建遠(yuǎn)、貝勒斯等具有相當(dāng)影響的域內(nèi)外學(xué)者采納。王澤鑒教授認(rèn)為,損害賠償?shù)哪康牟辉趹土P,因其基本上不審酌加害人的動(dòng)機(jī)、目的等。[28](7)換言之,是補(bǔ)償還是懲罰,似乎取決于是否考慮行為人的主觀狀態(tài)。王利明教授將制裁等同于懲罰,并認(rèn)為其最核心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當(dāng)為過(guò)錯(cuò)。[13](113)崔建遠(yuǎn)教授認(rèn)為:“過(guò)錯(cuò)責(zé)任以過(guò)錯(cuò)為主觀要件,故其必然具有懲罰性。”[29](320)美國(guó)學(xué)者貝勒斯認(rèn)為,“只要被告的責(zé)任以道義過(guò)錯(cuò)為基礎(chǔ),那么,使他們支付賠償金便是對(duì)不法者實(shí)施了懲罰。”[30](258)
3. 為他人行為承擔(dān)或非過(guò)錯(cuò)歸責(zé)論
曾世雄教授認(rèn)為,損害賠償之懲罰功能,可從下列事項(xiàng)獲得印證:違反私法義務(wù)往往伴隨著公法制裁;私法主體為他人行為承擔(dān)責(zé)任;不違法也無(wú)過(guò)失的危險(xiǎn)責(zé)任。[31](8)在曾教授看來(lái),不僅公法制裁是懲罰性的,而且私法制裁中為他人承擔(dān)責(zé)任以及嚴(yán)格責(zé)任也具有懲罰性。
4. 強(qiáng)加之不利益論
同樣是曾世雄教授,他對(duì)懲罰還有另外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即“蓋懲罰必具兩個(gè)特質(zhì):一即非出自意愿,二即加諸不利益。兩個(gè)特質(zhì)缺一不可。懲罰性之違約金,其存在仍須契約當(dāng)事人之合意。即有合意在先,應(yīng)與非出自意愿有別”。[31](8注釋1)
(二)初步歸納:懲罰與補(bǔ)償對(duì)立論并非主流
從上述學(xué)說(shuō)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理論界占主導(dǎo)地位的不是狹義“懲罰論”,而是廣義“懲罰論”。法理學(xué)者基本上主張廣義“懲罰論”,民法學(xué)者持同樣立場(chǎng)者也不在少數(shù)。但必須看到,即便是廣義論者在論證中也摻雜著一定狹義論成分。如:高其才教授認(rèn)為,懲罰功能是法律責(zé)任的首要功能,懲罰包括所有性質(zhì)的法律責(zé)任,卻又依責(zé)任實(shí)現(xiàn)方式為標(biāo)準(zhǔn)將其分為懲罰性法律責(zé)任與補(bǔ)償性法律責(zé)任;[25](172)魏振瀛教授認(rèn)為法律責(zé)任具有補(bǔ)償、懲罰、預(yù)防、教育等功能的同時(shí),又指出民事責(zé)任側(cè)重于補(bǔ)償,一般不具有懲罰性。[32](41)至于(非)過(guò)錯(cuò)說(shuō)、責(zé)任原因說(shuō),雖有一定道理,但因與本文主旨關(guān)聯(lián)不大,故在此不作評(píng)述。
(三)懲罰含義之取舍
懲罰內(nèi)涵理論歧見(jiàn)的形成,主要源于參照系的選擇、對(duì)待約定俗成的制裁形式分類的立場(chǎng)以及對(duì)于懲罰與補(bǔ)償關(guān)系的認(rèn)知差異。確定“懲罰”的應(yīng)然含義,需對(duì)上述三個(gè)爭(zhēng)論焦點(diǎn)進(jìn)行正面回應(yīng)。
1. 確立懲罰內(nèi)涵的立足點(diǎn)是特定制裁形式,還是整個(gè)法律制裁體系?
目前有關(guān)懲罰的學(xué)說(shuō),有的來(lái)源于個(gè)別制度,有的則立足于整個(gè)法律制裁體系。要厘清懲罰的含義,首先應(yīng)確定適宜的參照系。筆者認(rèn)為,相對(duì)于特定制裁形式,法律制裁體系才是一個(gè)更為合適的參照系。其一,懲罰在理論上是一個(gè)用來(lái)揭示法律制裁功能的范疇。對(duì)懲罰含義的理解,必須從作為源頭的法律制裁入手。其二,囿于學(xué)科視野,是上述主張沖突劇烈而交鋒甚少的根源。雖然現(xiàn)有學(xué)說(shuō)大多是從法律制裁視角出發(fā)闡釋?xiě)土P的,但其立足點(diǎn)主要還是具體的制裁類型。這樣很容易導(dǎo)致一葉障目,不見(jiàn)泰山。只有跳出學(xué)科視野,回歸整個(gè)法律制裁體系,方有整合和統(tǒng)一各種學(xué)理主張之可能。
2. 特殊語(yǔ)境下懲罰內(nèi)涵是作為對(duì)懲罰解讀的依據(jù),還是作為其一般內(nèi)涵的例外?
雖然狹義“懲罰論”不是主流學(xué)說(shuō),但是現(xiàn)行理論對(duì)于一些具體制度,如賠償、違約金的分類上,切實(shí)存在著懲罰與補(bǔ)償?shù)亩獙?duì)立。這些特定語(yǔ)境下的懲罰是作為確立懲罰一般內(nèi)涵的依據(jù)還是例外,可能會(huì)產(chǎn)生完全不同的結(jié)果。倘作為依據(jù),則需要改造一般懲罰理論,使二者得以兼容。否則,僅需堅(jiān)持一般主張即可。實(shí)際上,懲罰性賠償中懲罰所顯現(xiàn)出的超額性,只是相對(duì)私益損害而言,如果將公益損害考慮在內(nèi),賠償數(shù)額可能仍然沒(méi)有超過(guò)損害總量。⑤同樣,懲罰性違約金并不一定意味著守約方獲得了超額補(bǔ)償,因?yàn)槔^續(xù)履行可能不能完全彌補(bǔ)守約方所受之損害。考慮到上述提法已約定俗成,沒(méi)有必要去加以推翻或重構(gòu)。至于由此對(duì)懲罰所作的“超額性”解讀,宜作為懲罰一般理解的例外。⑥
3. 懲罰與補(bǔ)償是對(duì)立的,還是辯證統(tǒng)一的?
在日常生活,甚至學(xué)理研究中,人們對(duì)于懲罰與補(bǔ)償關(guān)系的認(rèn)知,存在著一個(gè)很大的誤區(qū):想當(dāng)然地把狹義“懲罰論”所持的懲罰與補(bǔ)償對(duì)立論作為一般觀念加以接受。這種對(duì)立論往往將懲罰或補(bǔ)償與特定的制裁形式相關(guān)聯(lián),試圖將法律制裁的某一功能與特定制裁形式進(jìn)行一一對(duì)應(yīng)。懲罰與補(bǔ)償對(duì)立的主張,由于順應(yīng)了與公私法二元?jiǎng)澐值乃季S偏好,不僅在狹義“懲罰論”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而且在廣義“懲罰論”中也可看到它的魅影。從法律制裁體系出發(fā),懲罰的目的就是要讓行為人承擔(dān)不利后果。基于社會(huì)調(diào)控的需要,任何制裁形式均應(yīng)當(dāng)具有懲罰性,私法制裁概莫能外。懲罰據(jù)以實(shí)現(xiàn)的方式眾多,包括事前的預(yù)防、事中的制止與事后的補(bǔ)救措施,而補(bǔ)償僅僅屬于事后的補(bǔ)救措施之一種。可以說(shuō),補(bǔ)償是實(shí)現(xiàn)懲罰的一種手段,補(bǔ)償乃懲罰的下位概念。
在對(duì)行政處罰懲罰功能解讀上,筆者支持廣義“懲罰論”,贊同將懲罰與法律制裁聯(lián)系起來(lái)理解,把懲罰界定為法律制裁的一般功能。至于在廣義“懲罰論”之下,是選擇否定評(píng)價(jià)論,還是選擇第二性義務(wù)論,抑或不利后果論,取決于對(duì)于法律制裁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否定評(píng)價(jià)論將法律制裁視為從法律價(jià)值出發(fā)對(duì)某種行為所作的否定性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過(guò)于寬泛,無(wú)法揭示法律規(guī)則與道德、宗教、紀(jì)律規(guī)則等的區(qū)別。不利后果論強(qiáng)調(diào)法律制裁作為一種結(jié)果對(duì)行為人的不利益性,而第二性義務(wù)論則強(qiáng)調(diào)法律制裁與第一性義務(wù)之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然不利后果論帶有價(jià)值判斷,由于強(qiáng)調(diào)結(jié)果的不利益性,大大壓縮了懲罰適用空間,而且可能給懲罰的運(yùn)用帶來(lái)一些不必要的困擾。如違法所得因其本不屬于行為人之利益,對(duì)它的剝奪很難說(shuō)在價(jià)值上是不利的。此外,還有一些制裁不僅不是對(duì)當(dāng)事人不利的,而且是有益的。比如,依據(jù)《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七十二條第三項(xiàng)的規(guī)定,對(duì)吸食、注射毒品的行為人可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此等拘留,可保證行為人在一定期間內(nèi)遠(yuǎn)離毒品的傷害。從這種意義上說(shuō),其總體上對(duì)行為人是有利的。相反,第二性義務(wù)論則實(shí)行價(jià)值中立,包容性更強(qiáng),能夠涵蓋更多的處罰措施,適用更多的情形。因此,行政處罰中的懲罰,詮釋為施加第二性行政義務(wù)似更為妥當(dāng)。
必須指出的是,行政處罰廣義“懲罰論”固然可取,但對(duì)其適用范圍必須加以限制,即僅限于區(qū)分具有法律制裁性質(zhì)的行政處罰與其他行政行為,而不宜拓展到行政處罰與其他性質(zhì)的制裁,特別是民事制裁的比較上。
四、結(jié)語(yǔ)
無(wú)論是從使用的廣度還是深度上看,懲罰已構(gòu)成一個(gè)基本的法學(xué)范疇。但懲罰卻是一個(gè)被“用濫了”的概念,而且其中很多用法屬于誤用。狹義“懲罰論”將行政處罰之懲罰功能解讀為一種“超損害性”制裁,并用以區(qū)分行政制裁與其他制裁,就屬于一種典型的誤用。這種誤用實(shí)際上將法律制裁的懲罰功能與補(bǔ)償功能對(duì)立起來(lái),并把它們與特定的法律制裁形式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不能以行政處罰具有懲罰功能為由,否認(rèn)其可能具有的補(bǔ)償功能。公益如同私益一樣,也存在被侵犯的危險(xiǎn),也有救濟(jì)的必要。而在諸多救濟(jì)手段中,由于補(bǔ)償性救濟(jì)的目的在“范圍上比起懲罰目的與預(yù)防目的來(lái)都要寬泛得多”[30](256)。行政處罰作為公益的主要救濟(jì)手段之一,其補(bǔ)償功能不能也不應(yīng)當(dāng)缺位。
基于公私法二元?jiǎng)澐侄贸龅摹靶姓幜P是懲罰性的,而民事責(zé)任是補(bǔ)償性的”認(rèn)識(shí),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觀察視角之不同。臺(tái)灣學(xué)者黃立就指出:“損害賠償要賠什么,并不是依處罰原則,也不依阻嚇原則,而依據(jù)‘均衡之考量’。此種考量系以受害人之利益為準(zhǔn)則,不以賠償義務(wù)人之行為作基準(zhǔn)。”[33](371)由此,可作進(jìn)一步推論:補(bǔ)償是相對(duì)受害人而言的,而懲罰則是從違法行為人角度考量的結(jié)果。這種視角上的偏好,是建立在個(gè)人主義基礎(chǔ)之上私益中心的產(chǎn)物。
對(duì)行政處罰功能定位之省思,有助于重新構(gòu)建懲罰功能與補(bǔ)償功能之間的關(guān)系。將行政處罰的懲罰功能在闡釋為科加第二性行政義務(wù)后,其可能具有的補(bǔ)償功能就不會(huì)被人為地否認(rèn),從而為發(fā)掘具有補(bǔ)償功能的行政處罰手段消除觀念障礙。這樣一來(lái),不僅為透過(guò)處罰手段的優(yōu)化配置推動(dòng)公益法律保障水準(zhǔn)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為在行政處罰中引入相對(duì)成熟的民事制裁方法、促進(jìn)行政處罰客觀化提供了可能。
注釋:
① 學(xué)界經(jīng)常把功能與目的等同。參見(jiàn)王澤鑒:《侵權(quán)行為法》(第一冊(cè)),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yè);曾世雄:《損害賠償法原理》,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yè);[澳]彼得?凱恩:《侵權(quán)法解剖》,汪志剛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頁(yè)。
② 凱爾森認(rèn)為,一個(gè)人在法律上對(duì)一定行為負(fù)責(zé),或者他為此承擔(dān)責(zé)任,意思就是他作相反行為時(shí),他應(yīng)受到制裁。基于法律制裁與法律責(zé)任的緊密聯(lián)系,本文對(duì)二者不加區(qū)分,在同等意義上使用。參見(jiàn)[奧]凱爾森:《法與國(guó)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shū)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頁(yè)。
③ 報(bào)應(yīng),通俗地說(shuō)就是懲罰。懲罰的正當(dāng)性與倫理學(xué)基礎(chǔ)在于公正。懲罰是一切法律責(zé)任的首要功能,民事責(zé)任也同樣執(zhí)行懲罰的功能,具有懲罰的內(nèi)容。參見(jiàn)張騏:《中外法學(xué)》,1999年第6期,第28-34頁(yè)。
④ 如《安全生產(chǎn)違法行為處罰辦法》第5條、《著作權(quán)法》第48條、《城鄉(xiāng)規(guī)劃法》第64條等。
⑤ 受害人之所以能夠受領(lǐng)此等賠償,主要是因其通過(guò)法律的私人實(shí)施維護(hù)了公益,在制度安排上將本屬于對(duì)公益損害賠償?shù)囊徊糠忠元?jiǎng)勵(lì)的形式授予該法律實(shí)施者。對(duì)此,筆者將另文詳釋。
⑥ 如有學(xué)者認(rèn)為,懲罰性賠償實(shí)質(zhì)上是公法私法二分體制下以私法機(jī)制執(zhí)行由公法擔(dān)當(dāng)?shù)膽土P與威懾功能的特殊懲罰功能。可見(jiàn),懲罰性賠償無(wú)論是相對(duì)于公法制裁,還是私法制裁,均具有“例外性”。參見(jiàn)朱廣新:《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演進(jìn)與適用》,《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14年第3期,第104-124頁(yè)。
[1] 魏德士. 法理學(xué)[M]. 丁曉春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2] 羅豪才, 湛中樂(lè). 行政法學(xué)(第三版)[M]. 北京: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2012: 228
[3] 胡錦光. 行政法專題研究(第二版)[M]. 北京: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06: 202.
[4] 莫于川. 行政法學(xué)原理與案例教程[M]. 北京: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07: 211.
[5] 張尚鷟. 走出低谷的中國(guó)行政法學(xué)——中國(guó)行政法學(xué)綜述與評(píng)價(jià)[M]. 北京: 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 1991: 225.
[6] 應(yīng)松年. 當(dāng)代中國(guó)行政法(下卷)[M]. 北京: 中國(guó)方正出版社, 2005: 1566.
[7] 楊解君.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上)[M]. 北京: 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9: 258
[8] 楊海坤, 章志遠(yuǎn). 行政法學(xué)基本論[M]. 北京: 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 2004: 169.
[9] 葉必豐.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二版)[M]. 北京: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07: 134.
[10] 章劍生. 現(xiàn)代行政法基本理論[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227.
[11] 周佑勇. 行政法原論[M]. 北京: 中國(guó)方正出版社, 2000.
[12] 鄭玉波. 法學(xué)緒論[M]. 臺(tái)北: 三民書(shū)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8.
[13] 王利明. 侵權(quán)責(zé)任法研究(上卷)[M]. 北京: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10.
[14] 王利明. 民法(第三版)[M]. 北京: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07: 718.
[15] 李昌麒. 經(jīng)濟(jì)法學(xué)(第二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674.
[16] 姜明安.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五版)[M]. 北京: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17] 胡建淼. “其它行政處罰”若干問(wèn)題研究[J]. 法學(xué)研究, 2005(1): 70?81.
[18] 胡建淼, 吳恩玉. 行政主體責(zé)令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的法律屬性[J].中國(guó)法學(xué), 2009(1): 77?87.
[19] 李孝猛. 責(zé)令改正的法律屬性及其適用[J]. 法學(xué), 2005(2): 54?63.
[20] 柳硯濤. 行政相對(duì)人違法行為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分析及預(yù)防對(duì)策[J].理論探索, 2013(4): 107?110.
[21] 江必新. 行政程序法概論[M]. 北京: 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1991.
[22] 馮軍. 行政處罰法新論[M]. 北京: 中國(guó)檢察出版社, 2003.
[23] 楊小君. 行政處罰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24] 沈宗靈. 法理學(xué)(第三版)[M]. 北京: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2009: 339.
[25] 張文顯. 法理學(xué)(第三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2007: 175?176.
[26] 孫國(guó)華, 朱景文. 法理學(xué)(第三版)[M]. 北京: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10: 340.
[27] 劉作翔. 法理學(xué)視野中的司法問(wèn)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82.
[28] 王澤鑒. 侵權(quán)行為法(第一冊(cè))[M]. 北京: 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 2001.
[29] 崔建遠(yuǎn). 合同法(第二版)[M]. 北京: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2013.
[30] 邁克爾?D?貝勒斯. 法律的原則——一個(gè)規(guī)范的分析[M]. 張文顯. 北京: 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shū)出版社, 1996.
[31] 曾世雄. 損害賠償法原理[M]. 北京: 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 2001.
[32] 魏振瀛. 民法(第五版)[M]. 北京: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33] 黃立. 民法債編總論[M]. 北京: 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 2002.
On the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CHEN Taiqing, XU Zeping
(Department of Law,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Jiangsu Fides Law Firm, Nanjing 210013, China)
The punitive character 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administration penalty in theory relative to other administrative deeds, even to different sanctions. But this character can be used only to discriminate relevant behaviors. If exceeding above scope, the punishment will be interpreted to impose excess obligation. However, there are lots of defects in thus theory, such as unfair retribution, invalidity to prevent illegal activities, suspect precondition, absence of operability etc. In order to uphold the integrity of legal sanctions, the generalized comprehension imposing the second duty should be accepted by u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limit the employ range just to compare administrative actions.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egal sanction; punishment; compensation
D912.1
A
1672-3104(2015)04?0061?05
[編輯: 蘇慧]
2014?11?28;
2014?12?21
司法部國(guó)家法治與法學(xué)理論研究項(xiàng)目“罰款治理的困境與出路——基于公益損害補(bǔ)償?shù)囊暯恰?12SFB501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è)務(wù)費(fèi)專項(xiàng)資金資助項(xiàng)目“行政罰款功能創(chuàng)新研究”(30920130132017);江蘇服務(wù)型政府建設(shè)研究基地(南京理工大學(xué))開(kāi)放基金資助項(xiàng)目“行政公益損害救濟(jì)問(wèn)題研究”(2012FWZF015)
陳太清(1975?),男,湖北安陸人,法學(xué)博士,南京理工大學(xué)法學(xué)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學(xué);徐澤萍(1975?),女,江蘇無(wú)錫人,江蘇億城律師事務(wù)所律師,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