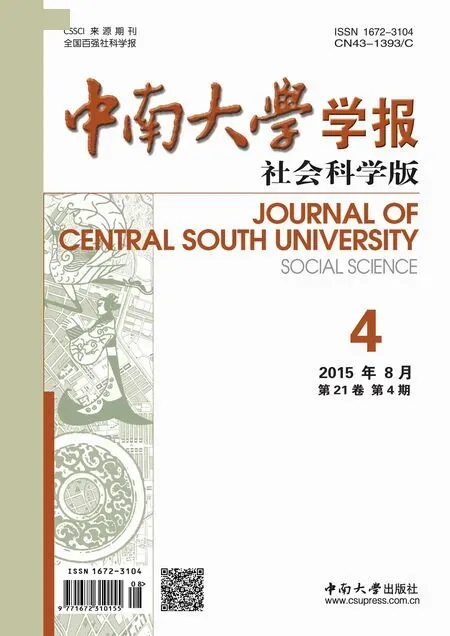從空間表征到文化實踐:對電子地圖的批判性反思
楊致遠
(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陜西西安,710128)
從空間表征到文化實踐:對電子地圖的批判性反思
楊致遠
(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陜西西安,710128)
基于網絡和移動信息新技術發展起來的電子地圖不僅是傳統地圖的延伸和擴展,還是一種全新的空間表征形式和媒介文本。它典型地體現了后現代時期“時空壓縮”這一現象,其中,消費文化在技術的主導下介入這一空間的再現/表征形式,使其具有隱含的生產性:電子地圖激發個體的空間想象和消費實踐,推動個體的身份認同,并通過權力分配、欲望塑造等途徑對個體的主體性的再生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電子地圖;空間表征;空間想象;主體性
一、反思地圖
人類為了“確立‘世界之形象’”創制了地圖,而且,“只有當文化的發展到了能夠在相當程度上具體地構想出一個‘世界的形象’(即便是想象的)時,這個‘世界之地圖’才有可能出現”[1]。就此而言,地圖的最主要功能是表達人們對空間的認識并對人們生活其中的現實空間進行摹擬再現。尤其到了啟蒙運動時期,數學、地理、天文學等學科的快速發展使“地圖剝去了一切幻想的和宗教信仰的因素,也剝去了涉及到它們之產物的一切經驗符號的因素,已經成了對空間現象進行實際安排的抽象和嚴格的功能體系”[2](312)。科學的推進和技術的發展讓地圖的認識、摹擬能力得以極大提高,例如,地理信息更為豐富、其標示更為精確……地圖作為地理空間再現的主要形式,其指示作用越來越為人們的生活所倚重。
毫無疑問,地圖是一種圖像類型。然而,“圖像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現實”[3]。在批判理論、符號學、文化研究等當代理論的討論中,圖像的再現危機成為一個焦點。圖像不是一個自然的存在,圖像與其指示物之間并非存在天然、穩固的關系,而是包含了認識型、權力關系等一系列復雜的因素。雖然地圖是一種高度再現型的圖像類型并直接為人們的空間認知提供直接的指導,但這種危機同樣存在。首先,地圖信息的可靠性大可受到質疑。“地圖是從偶然的地理狀況的特定細節中挑選出來并抽象而成的,……卻要充當‘地理現實’的‘完整’表現,從而成為這個世界的真實寫照”[4](179)。此外,地圖信息的表征方式也存在問題。地圖必然包含了特定的繪圖法,而“繪圖法(制作地圖的科學和藝術)要使現實變成可見之物,除了扭曲它之外別無選擇”[4](177)。地圖不僅是一種空間的再現——對各種基本地理要素(如山川河流、地形交通、居民點)的標示,還是一種空間的表征。“表征不只是簡單地復制世界,它們也生產著對于世界的一種看法。”[5]因此,繪制地圖即是話語的操作過程,涉及到對地理信息的安排、分配,涉及到對某些事物的呈現與對另一些事物的隱藏,涉及到通過信息的安排從而影響使用者的空間認知。簡言之,地圖圖像體現了某種權力的運作策略。
將對地圖的批判性思考延伸至電子地圖,我們該如何分析認識網絡電子地圖?它的表征形式有何特點?其表征形式為個體帶來了怎樣的信息交流關系?之下又隱含著怎樣的文化意義或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對個體又造成了怎樣的內在影響?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從媒介文化角度審視電子地圖這一新事物時必須去解答的。
二、電子地圖:一種新的空間表征
電子地圖基于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出現。Web 3.0時代的到來和移動通信技術的廣泛應用使電子地圖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關聯更為緊密。相較于傳統地圖,電子地圖的信息在如下幾個方面表現出新異性。首先,電子地圖通過新的媒介進行信息呈現。如果說以往的地圖主要是通過物質性的媒介呈現信息,那么電子地圖則是通過數字化的網絡通訊技術將信息呈現出來。其次,電子地圖的信息形態更為新穎。由于借助物質化的媒介呈現信息,傳統地圖主要是一種固態平面信息,一旦繪制完成,很難再進行修改、添加和拓展,而由于擺脫了物質性載體并借助于網絡互連技術及數字存儲技術,電子地圖的信息則呈現出流動化、立體性、可重構性的特點,隨著真實空間信息的變動,電子地圖的信息可以隨之進行改變和豐富。最新的衛星視圖、實時交通路況信息、2D平面圖、3D俯視圖等不同的地圖類型,可進行立體化層級處理。此外,飲食、出行、購物、住宿等日常性服務信息也能隨著顯示比例的變化而呈現。
最后,電子地圖的信息具有海量性、交互性的特點。傳統地圖的信息載負能力十分有限,而電子地圖借助移動通信技術能提供極為豐富的空間信息,而且越來越向即時交互性發展,各種信息既可以通過生產商也可以通過用戶被添加進去。它的查詢搜索功能、GPS實時定位都能很好地滿足用戶需求。同時,用戶能在電子地圖上進行信息標記、添加圖像及事件,以創造個性化的地圖空間。此外,交互性還體現在電子地圖與網頁或各種App的功能連結上:其他服務能向電子地圖添加內容信息;電子地圖能嵌入到網頁或其他App中,以滿足用戶通過其他應用程序搜尋信息時對電子地圖的即時調用。
地圖通過標記再現空間,在這個意義上,電子地圖可以被看作是當前最新、最典型的一種空間表征形式。西方新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戴維·哈維用“時空壓縮”這一概念來指稱現代社會中個體在時空維度上體驗到的勢不可擋的變遷感。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周轉流動的加速導致“決策的時間視野大大地縮短,生活方式的時尚迅速地改變。所有這些都伴隨著對時空關系的徹底重組、對空間障礙的進一步消除以及新的資本主義發展地理學的出現”[6](135)。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某種新的再現方式,通過這些方式,這種相互連接的世界得以再現”[6](133)。在他看來,福樓拜的小說語言和馬奈的繪畫技法就是這種新的時空再現模式的體現。
根據哈維的觀點,電子地圖可被視為將“時空壓縮”體驗推至一個前所未有的極限。電子地圖對空間的直觀展現具有高度的擬真性。2D平面圖、3D立體俯視圖、室內圖及衛星視圖為人們提供了切近、感知空間不同層面的途徑,無論哪種圖型,其對地理空間的令人驚嘆的精確標記不免會使人將之看作是真實空間的完美復制,尤其是可以自如縮放的衛星視圖,更像真實地理面貌的自然呈現。當前還有電子地圖生產商開發出全景地圖,利用攝像車記錄一些城市的街道實景圖像,用戶通過網絡獲取這些流動的六維空間的圖像,仿佛親自置身現場。即時查看并能隨需獲取的動態地理信息呈現出不斷的流動狀態,讓人能輕易跨越固有的地理疆域劃分。空間可以隨時呈現在眼前,人們所需做只是盡快決策去克服實體空間對人的限制,這正印證了哈維所說的“通過時間消滅空間”[2](367)。
在人類學意義上,電子地圖所表征的虛擬空間與真實空間的高度交融或許可被視為體現了長久以來人類的一種心理渴望:盡可能真實、全面、立體豐富地捕捉、再現生活空間。從繪畫圖像到文字符號,從客觀描摹到主觀表現及抽象,從人為創作到機械復制,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心理渴望的存在。如上所述,電子地圖提供的衛星視圖、城市實景圖等諸多空間模式讓其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強大再現能力。此外,吃、住、行、購物、休閑娛樂、公共服務等構成人們生活世界主要領域的海量信息的添加,更是使電子地圖對生活世界的再現趨于極致。
電子地圖的空間表征還為個體提供了一種創造可能。個體不僅可在動態化的海量空間信息中隨意調取所需信息以滿足特定生活需求,還能運用收藏、標記、添加等功能或保存曾經的移動路徑,或指導當前的行進路線,或規劃未來的出行路線。在這些路線上,個人可以添加圖像或文字,記錄他們曾經參與這些空間(如景點、購物場所等)的痕跡或體驗,或表達對其上某個場所、組織的評價認識(如對某個餐飲的口味或娛樂場所的服務的評價),通過這樣的途徑,他們可以在電子地圖上創造出自己具有獨特性和差異性的空間。更進一步,他們還能發布這些個性化的信息或對他人的信息進行評論,以實現空間信息、體驗的分享。電子地圖成了一個人們可以交流、共享信息的公共空間,在其間添加、創建公共符號,即是創造個性化自我空間的一個重要方式。
現代性進程與世界及事物的可視化密不可分。馬丁·海德格爾曾對“世界成為圖像”這一現象作出哲學分析,他認為,“世界成為圖像和人成為主體”是對現代歷史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兩大進程,而“現代的基本進程乃是對作為圖像的世界的征服過程”,“這一進程的一個標志是,龐大之物到處并且以最不相同的形態和喬裝顯現出來。在這兒,龐大之物同時也在愈來愈細微的方向上顯示出來。龐大之物在某種形式中突現出來,而這種形式表面上看來恰恰是使龐大之物消失”[7](904)。顯然,空間,這一龐大之物,已在電子地圖上獲得了完美的可視化存在,并通過其中各種各樣細微的生活化信息形態喬裝、退隱。電子地圖置身前臺,代表了當代對空間可視性的最新征服和表征。
三、建構消費空間:從想象到文化
對空間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在思考空間問題時指出,“空間是社會性的;它涉及到再生產的社會關系……也牽涉到生產關系,亦即勞動及其組織的分化。”[6](25)他還區分出了“再現的空間”(比如購物中心和百貨公司)和“空間的再現”(在廣告和其他媒體里),并認為無論哪種空間形式,都具有根本上的生產性。大衛·哈維在闡述“時空壓縮”這一概念時,也注意到新的空間表征模式背后所蘊含的生產性:“地方和空間之間的明顯緊張關系,呼應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內部的張力;它需要一種特別的空間組織形式來消滅空間,需要長期周轉的資本來推動其他資本的快速周轉。”[6](135?136)那么,電子地圖作為一種“空間的再現”形式和新的時空表征模式,它的生產性體現在哪里?
消費文化是當代文化的主導范型。消費成為分析當代社會各種現象時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人們對“生產—消費”之間關系的認識由傳統的“生產視角”轉向“消費視角”,由此形成的共識是:消費并非生產的終端或補充,而是啟動再生產的關鍵步驟和力量,消費本身即具有強大的生產性。在消費領域,休閑服務方面的消費成為經濟的主要增長點和推動力。通過前面對電子地圖具體表現形式的分析可以看出,電子地圖上的信息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密切相關,餐飲、出行、觀光、購物、住宿、休閑娛樂等生活服務信息可以讓人們從上面輕易獲取,并獲得可視化呈現。人們獲取這些信息的一個重要指向便是消費。因此,電子地圖的生產性就在于它對消費行為的召喚、調動與支持。在這個意義上,電子地圖可以說是當代消費文化的一個實踐領域,為人們建構了一個嶄新的消費空間。
那么,進一步的問題在于:電子地圖作為消費實踐的內在動力何在?
“消費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記號和符號商品,它們體現了夢想、欲望和離奇幻想。”[8]費瑟斯通的這一論述談及了當代消費實踐中的兩個重要方面:影像符號和想象。想象“本質上被認為是一種再現或者創造的能力。作為再現的能力,想象是對業已存在的現實的復制或表現。作為創造性的能力,想象本質上是生產性的:想象創造出超越已有事實之上的、原創性的或者真實的影像”[9](231)。也即是說,想象的能力源于事物的缺席。前現代時期,想象的場所主要在于文字及繪畫等文本形態中,隨著機械復制和數字傳播時代的來臨,想象的來源和場所也發生了歷史性的遷移:視覺圖像越發成為刺激、推動人們想象的主要文本形態,甚至是最終形態。由于視覺圖像具有直接、明晰、具體等特點,它天然地成為消費活動中展示產品形象的載體。在此,消費與想象達成了聯姻。在消費過程中,商品信息通過視覺圖像的方式得以展示、傳播,圖像本身對消費者形成視覺刺激,在后者那里激發起關于商品的各種相關想象——具體形態、性能、質感、身份、體驗等等,召喚后者的消費行為。因而,“想像乃是一種社會實踐”,它的作用“是一個論辯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個人和群體試圖把全球性融入到他們自身對現代性的實踐之中……普通人已經開始在他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展開想像”[10]。想象的生產性正是在此得以顯現。
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城市文化史學者劉易斯·芒福德就敏銳地指出了地圖制作在促進人們進行空間生產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在畫家和制圖家所建造的基礎之上,人們產生了對空間的興趣,對運動的興趣,對旅行的興趣。……于是想要利用時間和空間的渴望爆發了,時空一旦與運動協調起來,就可以加以縮短或伸長:人們開始征服時空了。”[11]就當時而言,地圖成功刺激了殖民、探險等活動,并引發了道路、交通工具、定向工具等一系列事物的革新,其生產性體現在權力、空間范圍、物質性等方面。
可以肯定的是,電子地圖激發的空間想象較傳統地圖更為強烈,其中包含兩個重要原因。其一,電子地圖借助于網絡的存儲及鏈接技術,實現了地理、空間信息的動態化及海量化呈現,人們可以更為便捷、迅速地接觸到豐富的空間圖像,由此可能產生更頻繁、強度更大的空間想象;其二,移動通信技術的廣泛應用,使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端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電子地圖中空間信息與各種生活消費、服務信息的相互滲透讓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消費導向。技術的介入讓電子地圖成為消費活動展開的重要陣地。電子地圖通過將地理空間快速建構為一個充滿了各種生活消費信息的動態化可視圖像,刺激了我們關于消費空間的想象,將我們的生活不斷納入到越來越頻繁的消費浪潮中去。因為從根本上看,消費活動即是占有某個空間的一種象征形式,通過在某個具體場所進行的消費行為,我們對于該場所的空間想象得以滿足。
電子地圖對人們的消費行為的調動除生產意義之外,還具有文化上的意義,這是由于消費行為及推動該行為的想象實踐,在構建當代人的身份認同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一方面,作為個體心理幻想的一種,想象“是自我建構和他者導向的媒介”[12](71)。在我們與各種文本信息的意義交流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想象的維度。想象激發并引導我們的情感投入,讓我們遭遇他者的存在,進而確立起自我存在的邊界和身份形象。這一心理過程在消費行為中同樣存在:“……各種形象會撩起人們對于那個遙遠地方的向往,而這種不能滿足的需要或‘空缺’可以通過某一產品來彌補。這種產品被認為是代表了欲望中的各種品質。因此,如果我們買了這一產品,就等于買了一個夢想。”[13]另一方面,消費行為包含并再生產我們的情感心理,創造我們關于生活世界的意義感受。如果說“購物得以來界定作為個人,我們是誰,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想要變成什么樣”[14],那么一般性的消費行為發揮著同樣的作用。選擇什么樣的商品或消費行為,決定著我們認同怎樣的生活倫理意義:我們選擇不同的場所展開我們的消費活動,生成日常生活的體驗和意義;我們購買各種各樣的商品,構建起日常生活的面貌和空間;我們在消費活動中與他人發生關聯,從而實現社會化的互動,建構公共生活。消費為我們提供了情感和想象的空間,而“如果公民身份概念不僅僅是權利和義務的總和,它就需要有這種情感和想象的空間,這個主觀領域可以恰當地稱之為人類主體向其所處的社會現實世界的投入。盡管這些投入可能是情感的和非理性的,但由于‘文化’公民身份必須與誰被允許做什么或者誰可享受什么這種形式上問題相聯系,所以它與這些東西有著重要的關系”[12](87)。總之,人們通過消費選擇生活方式,進而構建了自我身份。
因而,電子地圖在促進人們的身份認同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更進一步,由于帶有社會意義的空間能塑造個體對自身的認同感,由于電子地圖的“時空壓縮”帶給人們一種全新的時空體驗,因此,在電子地圖推動下的身份認同不可避免地帶有典型的后現代特征。傳統上比較穩定、統一的時空感塑造的相對穩固的自我身份經受著技術加速度的沖擊,變得越來越多元、流動、虛擬。“后現代生活是片段的,一個分裂了的而且還在分裂中的世界,沒有連續性,也無法構成意義的聯系。……由于新技術和電子技術的發展,想象似乎空前地高漲了。……我們現在擁有的這些技術宣告了不同種類的快樂、不同思想和感情、以及不同想象存在的可能。”[12](71)電子地圖呈現出流動的地理空間圖景,給我們越來越快的欲望提供充分的想象空間和選擇可能,這也暗示了我們的身份認同存在的多種可能。生活的時間與空間由單一、穩固變為開放,“認同轉換成了若干個事件,成了一系列漂移的時刻,成了永恒的現在和轉瞬即逝的偶遇。”[12](70)這正符合后現代理論家詹姆遜所說的后現代主義的兩個基本特征:“現實轉化為影像、時間割裂為一連串永恒的當下。”[15]
不可否認,這種“當下”“碎片”式的身份認同代表了后現代時期個體身份的生成策略,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對個體自由選擇的尊重,是對個體生存價值的肯定。然而,這些身份認同的新變化也可以被視作是一種困境和危機:“社會空間朝向我們內爆的感受所引發的預感轉化成一種身份危機。我們是誰?我們屬于哪個空間/地方?”[6](135)個體的身份感變得破碎,其生存似乎被編織進了某個無法逃避的網絡。
四、欲望的空間旅行:電子地圖與當代主體性的生產
身份認同是個體主體性的一個重要表現層面。在文化研究的理論視域中,文本或話語對主體性的生產作用已得到充分的重視。其中,“文本決定論”者主張,“某種文本或話語不管使用什么指涉術語,當它在閱讀或言說活動中得到復現之際,其主體都是讀者或言說者。于是,文本與話語就成為社會與個體之間的關系借以溝通的方式。……文化產品如何利用文本化的手段與策略,如觀點、說話方式、敘事等以提出或固定某種主體立場,通過這種立場它們才能在解讀之際獲得意義,……解讀行為只是一個占據這種文本所提供的‘空間’之過程。因此,在這個領域就存在一種趨勢:文本由于作為我們主體性的建構者或生產者而被賦予特權;而個體則多少被視為‘消極的意識形態之主體’,不斷地被改編到他們所棲居的任何話語形象之中。”[16]這就意味著,任何文本或話語都對信息接受者進行主體性的召喚,其中文本或話語的框架發揮了重要的意義定位、引導作用。個體解讀文本意義的過程,就是想象性關系作用于個體、將個體塑造成主體的過程,相應地,個體成為主體則是文本意義得以實現的必要保證。
地圖力求精確、客觀地再現地理空間面貌。然而,這僅僅是一個幻覺。地圖是一種文本,一種關于空間的陳述話語。“地圖把空間歷程與空間描述豐富的多樣性同質化和具體化了”[2](15),作為文本,它的意識形態功能也逐漸浮現。“地理學上的地圖從來就沒有完全中立、客觀地再現過空間,因為它們力求以系統的方式把世界理性化,并固定在穩定的意象世界里,而意象世界實際上是變動不居的。然而,地圖經常以精確的面目出現,目的是賦予我們的空間感以永恒的意義,讓我們產生幻覺,以為空間是能夠被徹底地探索和控制的。地圖不僅描繪這個世界,事實上,它們還根據特定的文化需求構筑了這個世界,并因此成為重要的意識形態工具。”[4](178)
至此,地圖這一文本/話語與主體(性)塑造之間的作用關系是最后的焦點所在。前引芒福德·劉易斯的論述中,他已經談及現代早期傳統地圖如何將某些個體塑造為殖民主體的問題。在當前信息技術成功推動了全球經濟、文化形成的語境下,新的社會形態、生產關系及社會實踐使得主體性發生了整體性的歷史變遷。電子地圖既作為傳統地圖的延伸,又作為一種高度技術化的新型媒介文本/話語,它對當代主體(性)的生產與形塑必然呈現出新的特征。
如前所述,雖然電子地圖呈現出全新的空間表征形式,似乎無限地接近了“精確客觀再現地理空間”這一目標,并為人們提供了創造個性化生活空間的可能,但總體上看,由于當代消費文化對日常生活的全面滲透,個體的創造性似乎難以逃脫消費文化設立的界限。電子地圖中的海量生活信息及其圖像式再現作用于個體,極有力地刺激著個體的消費想象,使個體的心理結構很大程度上被社會的主導文化形態所塑造。因而,電子地圖更傾向于將個體塑造成一個消費主體,而非生產性主體。電子地圖快速流動的海量信息及多樣的空間表征方式有助于引發頻繁的消費行為,從而潛在地推動短暫化、破碎化的身份認同,最終造就一種“最小限度的自我”。“這種新的自我是被抽掉了自我力量和自主的自我,是僅把目光集中在‘某日某時’生活經歷的自戀的自我。它把現實理解為‘連續出現的微不足道的突發事件’。日常生活,在后現代語境下,變成了不斷變化的焦急和漂浮不定的憂慮,總是變化著,總是一個個小片段。”[12](70?71)在電子地圖持續流動的空間圖像中,主體關于空間的想象和消費欲望相互激發,不斷生成,個體成了在短暫、破碎體驗與渴望永恒、完整之間、在自戀與自卑之間不斷擺蕩的焦慮型主體。
電子地圖中隱蔽的文本修辭策略是塑造主體性的重要途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電子地圖作為話語對空間信息的配置與安排,這涉及到它企圖顯現什么、隱藏什么的問題。即是說,電子地圖的圖像呈現必然處于一種可見物與不可見物的機制設計中。為何各種生活消費信息得到了突顯?而哪些信息沒有在其中得到展現,而它們對于我們可能恰恰是極為重要的?這種信息的隱與顯的配置對我們感知現實會產生怎樣的作用?這些疑問會將電子地圖召喚個體為消費主體的意圖揭示得更加明顯。此外,電子地圖呈現信息的視角也與主體性塑造密切相關。換句話說,電子地圖這一文本是如何將信息敘述出來的,直接影響到使用者的主體性體驗。電子地圖的視角主要有以下幾種:俯瞰式瀏覽;地理空間的圖像比例的靈活縮放;虛擬的地理位置能自由變換移動。這些可被總稱為“上帝視角”,借助這種視角,我們如上帝一般俯瞰整個地理空間,并于其中相當自由地“移動”。在這種視角作用下,我們難免會產生一種“空間是能夠被徹底地探索和控制的”感覺,產生一種權力的幻覺。在手指的操作或鼠標的點擊中,地理空間在我們手中翻轉、變化,我們似乎可以擺脫身體和實際空間的限制,抹消真實地理空間中此地與他國、異鄉之間的存在的隔閡、阻礙,抹消自我與他者生活空間的差異,擬真式地“介入”一個個“他異空間”,自在地遨游。這一幻覺讓人滿足,因為權力能給予主體以撫慰。
路易·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的著名論述指出了“個人與其實在生存條件之間的想象關系”[17],正是借助于這種想象性關系,意識形態得以悄悄地將個體“召喚”為主體。那么,問題便在于:我們如何才能避免這種“想象關系”的歪曲去認識“真實”?或許,在尋找問題答案前我們必須先面對如下幾個問題:在想象性的作用下,認識“真實”是可能的嗎?“真實”與想象是否能被絕對地加以區分?如果“真實”只是話語的一種效果,如果“隨著大眾傳媒的復制技術的出現,‘真實’的話語本身開始失去了意義”[9](231),那么對“真實”與想象的區分是否還有意義?這些問題可以引發持久的討論,也很難得出一個絕對正確的結論。然而,處于現實結構中的主體完全可以在批判式反思的推動下對事物進行超越性的思考,去挖掘其可能蘊含的意義空間。
因此,挖掘電子地圖這一媒介文本的意義空間即是關注主體的當代處境。借助于社會經濟、技術及文化的共同支配作用,電子地圖在精確再現的偽裝下努力將現實塑造為一個帶有強烈消費文化色彩的單一感知結構,召喚個體向消費主體的自然轉變。表面上個體對信息的自由獲取與內在層面上資本、技術對個體的隱形支配將主體推至羅蘭·巴特所說的那個“重要的歷史悖論”面前:“技術越是促進信息(最明顯的乃是種種影像的)傳播,它就越是提供了手段,把被構成的意義隱藏在天賦意義的表象之下。”[18]技術的作用使我們生活的世界空間這一龐大之物似乎成為可計算的、可操控的,我們于其中感受到了自由主體的某種幸福。然而,與這種幸福感緊密相伴的是一種始終籠罩在主體存在上方的陰影。恰如海德格爾所言:“一旦在計劃、計算、設立和保證過程中的龐大之物從量突變為某種特有的質,那么,龐大之物和表面上看來總是完全能得到計算的東西,恰恰因此成為不可計算的東西。后者始終是一種不可見的陰影;當人成了主體而世界成了圖像之際,這種陰影總是籠罩著萬物。”[7](905)
五、結語
當前,新媒體、自媒體已然成為人們獲取信息、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其易攜、快捷、全面等諸種便利性,它們與日常生活已經實現了高度融合,并不斷重塑著后者的面貌形態。“新的傳播媒介的引進和廣泛使用,可能重建大范圍的場景,并需要有新的社會場景的行為。”[19]隨著網絡信息技術及移動通信技術十多年來在國內的迅猛發展,電子媒介顯著地影響著中國的社會化進程及人們的社會行為,這一點尤其可以被清晰而強烈地感知到。各種智能手機App的開發和應用讓我們不斷地應對新的社會場景,并生產出新的行為方式。微信、QQ等通訊軟件改變了我們的社交方式;電子游戲、影音客戶端等應用改變了我們的娛樂方式;美團、滴滴打車等軟件塑造著我們新的生活消費方式……新的信息技術及方式營造出新的媒介環境,二者又共同培育出新型的消費者。可以預見,當這些年輕的新型消費者全面成長起來并成為社會的主要消費力量時,新的社會場景及新的社會行為會占據絕對性的優勢位置。
電子地圖在培育新型消費者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通過提取生活消費方面的空間信息并將之置入文本結構,通過將文本呈現為高度摹擬性的圖像形態,電子地圖成功地將空間表征為真實、可信、全面、動態,吁求個體參與到以消費為導向的諸種社會實踐中,并將被建構起的消費空間內化于個體的主體性之中。目前,這種培育效果已經在電子地圖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中凸顯出來。數據顯示,2014年初,中國手機地圖導航App市場累計賬戶已達13.3億戶,地理信息產業產值已達到2 000億元,預計到2020年該產值將超萬億元。[20]百度、高德、搜狗等占據了市場主要份額的電子地圖在完善平臺化功能的同時,在進一步向渠道化發展,努力為各個商家提供擴展和增殖服務。消費服務信息與電子地圖的交融還在繼續深化。
年輕一代熱情地擁抱新媒體,新媒體帶給他們各種消費快感及文化體驗。然而,站在經濟、文化樂觀態度之外的批判性反思的立場上,不難發現,對于當前中國的社會現實而言,以電子地圖為代表的新媒介技術帶來的悖論是雙重的,并引發了一系列問題。一方面是新的信息技術、信息方式與社會發展、個體自由之間的悖論。新技術推進、加速社會發展,同時又導致社會“熵值”的不斷增加,那么,我們該如何對待技術?資本與技術的聯姻使消費文化成為強勢文化形態,并威脅到了其他文化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平衡諸種文化之間的平衡?最后,消費文化浪潮之中的個體的創造性有多少可能?信息技術是激發了個體的創造性還是將其更牢固地束縛?該如何評估技術“意識形態”對個體的影響?
另一悖論體現為,在信息技術導致的不斷加速的全球化浪潮中,本土傳統文化、地域文化遭遇到全球性視覺文化、消費文化時的發展困境。全球化進程造成了文化之間的相互碰撞,“時空壓縮”的加劇,使強勢、主流文化勢必同化、吞噬弱勢、少數文化的發展空間,在這一危機時刻,如何保護弱勢文化不受侵蝕?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樣性并使不同文化都得到發展?如何讓不同的文化為人們提供身份認同的多元選擇可能?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持續性地思索。
[1] 海野一隆. 地圖的文化史[M]. 王妙發譯.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13.
[2] 戴維·哈維. 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M].閻嘉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3.
[3] 雅克·朗西埃. 圖像的命運[M]. 張新木譯.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9.
[4] 丹尼·卡瓦拉羅. 文化理論關鍵詞[M]. 張衛東, 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
[5] 阿雷恩·鮑爾德溫, 布萊恩·朗赫斯特,等. 文化研究導論[M].陶東風, 等譯.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5.
[6] 薛毅. 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讀本(三)[M].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8.
[7] 孫周興選編. 海德格爾選集[M]. 上海: 三聯書店, 1996.
[8] 邁克·費瑟斯通. 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 劉精明譯. 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00: 39.
[9] 維克多·泰勒, 查爾斯·溫奎斯特. 后現代主義百科全書[M].章燕, 等譯.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10] 尼古拉斯·米爾佐夫. 視覺文化導論[M]. 倪偉譯.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 35?36.
[11] 劉易斯·芒福德. 技術與文明[M]. 陳允明, 等譯. 北京: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2009: 21.
[12] 尼克·史蒂文森編. 文化與公民身份[M]. 陳志杰譯.長春: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07.
[13] 邁克·克朗. 文化地理學[M]. 楊淑華, 等譯.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172.
[14] 莎朗·佐京. 購物點—購物如何改變美國文化[M]. 梁文敏譯.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1: 7.
[15] 詹明信.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M]. 陳清僑譯. 北京: 三聯書店, 1997: 419.
[16] 約翰·費斯克等編.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M]. 李彬主譯. 北京: 新華出版社, 2004: 283?284.
[17] 陳越編. 哲學與政治: 阿爾都塞讀本[M].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353.
[18] 羅蘭·巴特. 影像修辭學[M]. 陳越譯. 世界電影, 1997(4): 197.
[19] 約書亞·梅羅維茨. 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M]. 肖志軍譯.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2: 32.
[20] 大數據如何駕馭地圖導航App[EB/OL]. http://www.cnii. com.cn/mobileinternet/2014-09/23/content_1448873.htm.2014-09-23.
From spatial representation to cultural practice: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net electronic map
YANG Zhiyu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Based on the network and mobil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electronic map is not only the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traditional map, but also a new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media text. It is a typical phenomenon of the post-modern era “Time-space Compression,” in which consumption culture starts to intervene in the form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 with the dominance of technology so that it has a productive implication: electronic map stimulates individual space imagination and practice of consumption, promotes the individual ident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producing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through power distribution, desire characterization and so on.
electronic map; spatial representation; space imagination; subjectivity
G07; G206.3
A
1672-3104(2015)04?0209?07
[編輯: 胡興華]
2015?03?25;
2015?06?22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空間批評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12CZW001)
楊致遠(1980?),男,陜西西安人,文學博士,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影視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