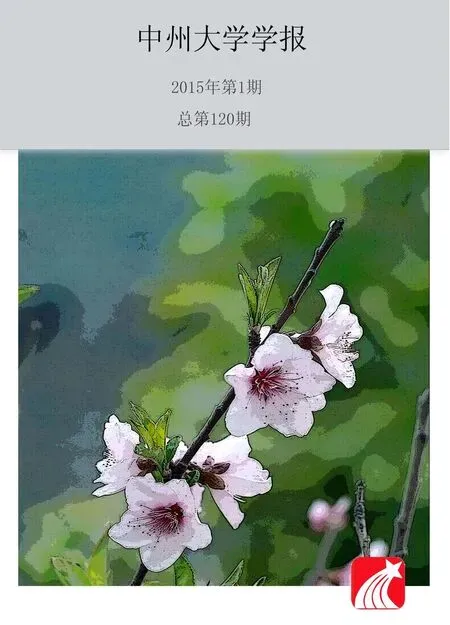未完成的突圍:形式論視野中的晚清“三界革命”
肖翠云(閩江學院中文系,福州350007)
未完成的突圍:形式論視野中的晚清“三界革命”
肖翠云
(閩江學院中文系,福州350007)
晚清“三界革命”對散文、詩歌、小說三種文學體裁的文學形式(語言和文體)進行革新,以期突破傳統的形式規范,形成嶄新的語言和文體。但從實際結果來看,并未達到預期目標:既未實現語言形式的“言文合一”,也未完成文體形式的變革,從而未能實現中國古代文學的現代轉型。
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語言;文體
晚清白話文運動為了實現社會功利“開啟民智”和政治功利“強國保種”,選擇書寫工具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力圖改變中國文學“言文分離”的局面,使文學書寫朝著“言文合一”的目標邁進。為此,在文學領域掀起了三場聲勢浩大的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對散文、詩歌、小說三種文學體裁的文學形式(語言和文體)進行革新,以期突破傳統的形式規范,形成嶄新的語言和文體。但從“三界革命”的結果來看,并未達到預期目標,理想與現實之間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一、文界革命:以淺近文言書寫的“新文體”
晚清時期,在文壇占統治地位的仍是桐城派古文,桐城古文以“義法、考據和辭章”來糾正八股文內容空疏、形式僵化之弊端,但其本身也存在盲目模仿、矯揉造作、內容空洞、義法繁復、用詞典雅等缺陷。正如梁啟超所說:“然此派者,以文而論,因襲矯揉,無所取材;以學而論,則獎空疏,閼創獲,無益于社會。”[1]3093這樣的文章只適合上層社會把玩欣賞,于當時內憂外患的社會是無濟于事的。因此,出于政治宣傳的需要,梁啟超選擇了報章這一新型大眾傳播媒介,身體力行,撰文寫作,形成了風格獨特的“報章體”(又稱“新文體”)。梁啟超不無欣喜地看到“自報章興,吾國文體為之一變,汪洋恣肆,暢所欲言,所謂宗派家法,無復問者”[2]。“汪洋恣肆,暢所欲言”打破了八股文和桐城古文嚴格的文體規范,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文學的自由抒寫。這種文學表達方式能夠契合當時社會對民眾進行宣傳、教育和啟蒙的訴求,很快就風靡開來,梁啟超以此為基礎提出了“文界革命”的主張,并從形式層面闡述了“新文體”的主要特征:“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1]3100具體而言有如下特征:
(一)書寫語言平易暢達
要做到這一點,須采用淺近的文言,并“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俚語韻語”是具有口語性質的方言俗語,與民眾的關系最為密切,若加以采用,顯然能柔化純文言書寫的正統面孔,使文學表達更具親和力。“外國語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引進外來的新詞語,以適應時代變革的需要;二是采用外來語的詞法和句法,為文學寫作輸入新鮮的表達方式。這一思路源于梁啟超對日本文的考察:“德富氏為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于是也。”[1]1200他在日本文中看到了歐西文思的力量,認為中國的文界革命也應該融入外來的文學資源,為文學注入新的素質和活力。“新文體”在語言上的亮點正在于西方“新名詞”的大量引入。
不過,從“雜以”二字來看,梁啟超雖然提出要在“新文體”中加入方言俗語以及外國語法,但這些新的成分在“新文體”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當時“新文體”的語言并不像白話報刊那樣主要采用接近口語的官話(或方言),“俚語韻語”“外國語法”只是摻雜其中,加以點綴。這表明,“新文體”的主要語言形式仍是文言,但選擇的是明白曉暢、通俗易懂的文言,而非桐城古文淵雅深奧、佶屈聱牙的文言。
(二)文體縱筆所至而又條理明晰
要做到這一點,須打破桐城古文所制定的各種“義法”,解除散文寫作上的條條框框,筆隨心至,自由抒寫;但又非漫無邊際、天馬行空式的胡涂亂抹,在縱筆之時也須講究文章的條理,實踐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文體理念。這種文體要求在“新文體”中表現為句式多變,常使用排比句、對比句、重復句、反問句、感嘆句等形式;長短不拘,短句與長句、散句與整句交錯使用,文章富于起伏變化之美。
上述兩點形式特征皆可證之于梁啟超的政論散文,現以梁啟超論《英雄與時勢》的第一段為例(文字有刪節)加以說明:
或云英雄造時勢,或云時勢造英雄,此二語皆名言也。為前之說者曰:英雄者,人間世之造物主也。……故有路得然后有新教,有哥倫布然后有新洲,有華盛頓然后有美國獨立,有俾士麥然后有德國聯邦。為后之說者曰:英雄者,乘時者也,非能造時者也。……雖無哥白尼,地動之說終必行于世;雖無哥倫布,美洲新世界終必出現。余謂兩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既有英雄,必有時勢,既有時勢,必有英雄。嗚呼!今日禹域之厄運,亦已極矣!地球之殺氣,亦已深矣!……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菲薄乎?[1]341
由上述可以看出:①引文在語言上以文言為主,但擯棄了古奧難懂的文言詞匯,采用的是淺近易懂的文言詞匯,理解起來沒有什么障礙,并加入了很多外國新名詞,如“哥倫布”“路得”“聯邦”“美洲”“哥白尼”“地動”等,為讀者帶來了嶄新的知識和視野。但從整體上看,仍沒有脫離文言文的表達習慣,文言詞匯和文言語法仍占主導地位。
②引文在表達方式上綜合使用了多種句式,有排比句、對比句、、感嘆句、反問句等,句式多樣,靈活多變,呈現出“汪洋恣肆”的自由與奔放的風格。
③引文在結構上采取了“總—分—總”的格式,先總論兩種觀點“英雄造時勢”和“時勢造英雄”,然后分別論之,最后總結“兩說皆是也”,并結合現實加以延伸。整段文章思路清晰,層次分明,條理順暢,論據充足,強有力地論證了英雄與時勢不可分離的關系。
可見,“文界革命”主要從語言和文體兩個方面對晚清散文的形式進行改革,使晚清散文在詞匯、句式、結構等方面都呈現出嶄新的氣象。正如鄧偉所說:“文界革命的語言學意義遠遠大于文學意義。在異域的視野下,新文體以報章為媒介,實質性代表了文言新的發展:它融入許多日本、歐洲文體的因素,基本上突破了所謂‘義法’、‘辭章’等古文規定,富于社會激情,以情感為內核造就了文體解放的氣象。”[3]50但同時也應該看到,“文界革命”側重于文體上的革新,對文學語言的變革力度并不大,“之乎者也”式的文言詞匯及文言句式仍是“新文體”最主要的表達方式,這在梁啟超的政論散文中即可窺見。
二、“詩界革命”:在口語和“新語句”中徘徊的舊詩體
晚清詩壇和文壇一樣,籠罩著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氛圍,雖有龔自珍、魏源等人開辟的新詩風,但占統治地位的仍是宋詩派和湖湘派的復古詩,這些詩人們每天在故紙堆里討生活,做著復古主義的詩夢。對此,“詩界革命”的先驅黃遵憲大膽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口號,要求詩人擺脫古人的束縛,遵從自己內心的需求進行暢快的表達。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的原因之一也是“詩之境界,被千余年來鸚鵡名士(余嘗戲名家詞章為鸚鵡名士,自覺過于尖刻)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1]1219。梁啟超對詩壇人云亦云、因襲模擬的詩風深感痛恨,要求擺脫束縛,力求創新。
面對擬古主義,黃遵憲要求“我手寫我口”,用“口說語言”作為“書寫語言”的形式,怎么說就怎么寫,實現手口一致。不過“手口一致”是很難做到的,這個理論命題忽略了“口說語言”向“書寫語言”轉化過程的復雜性,譚學純對此有過精到的分析,此不再贅。[4]但在當時,黃遵憲沒有認真考慮這些問題,僅在“新穎通俗”的層面來要求書寫語言“適用于今、通行于俗”[5]。從黃遵憲的詩歌創作來看,用詞大多較為平實。如《今別離》詠“電報”:“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已極,云是君所寄。”《錫蘭島臥佛》:“大風西北來,搖天海波黑。茫茫塵世界,點點國土墨。”《登巴黎鐵塔》:“一覽小天下,五洲如在掌。”《番客篇》寫南洋華僑:“余皆閩粵人,到此均同鄉。”這些詩歌相較于晦澀的文言古詩,確實通俗易懂,但與口說語言仍有很大差距,許多詞匯仍是文言,如“朝、暮、云、余、皆、均”等,尤其是在詞與詞的組合(句法)上,與口說語言的距離更為明顯,如“一覽小天下”顯然不符合口語表達的習慣。這說明,詩歌表達的通俗化不只是要做到語言的通俗,還要做到表現方式的通俗。這一點,黃遵憲也有涉及。1902年,在《新小說》籌辦期間,黃遵憲給梁啟超寫了一封信,主張吸收民間詩歌養料,借用山歌、歌謠等形式來實現詩歌表現方式的通俗化:
報中有韻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樂府》,尤西堂之“明史樂府”,當斟酌于彈詞、粵謳之間,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長或短,或壯如《隴上陳安》,或麗如《河中莫愁》,或濃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或俳伎詞,易樂府之名而曰雜歌謠,棄史籍而采近事。[5]432
在信中,黃遵憲對詩歌的文體變革提出以下要求:在體裁上,不再模仿樂府,而采用民間彈詞、歌謠形式;在句式上,擺脫律詩、絕句的限制,不拘長短;在風格上,追求多樣化,或雄壯、或絢麗、或濃厚、或古樸,從而大大解放了詩歌的形式要求,尤其是體裁和句式上的解放,為詩歌能夠實現“我手寫我口”提供了可能。從黃遵憲的詩集《人境廬詩草》來看,他的詩歌創作基本上踐行了自己的詩學追求,擺脫了近體詩謹嚴的格律束縛,不講平仄,不拘句數,少則四句,多則幾十句,根據表意的需要自由選擇,大大拓展了詩歌的表現空間,這是值得肯定的。但黃遵憲的詩雖不注重平仄、格律,卻仍講究押韻和字數,字數基本上都局限于五言或七言,這與古詩、樂府很相近,與字數長短不拘的民間歌謠有差距。黃遵憲跳出了近體詩的格律規范,卻沒有跳出古體詩的形式要求,所以,他的詩歌給人的印象仍是古詩,而非新詩。盡管黃遵憲曾在理論上大聲疾呼“今之世異于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強調詩人要保持自我的主體性和獨立性,不必受古人的約束和制約,但在自身的詩歌創作實踐中深刻體會到“欲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為古人所束縛,誠戛戛乎其難”。因此,他在強調當今詩人要保持獨立性和創造性的同時,也要求今人繼承古人的優秀成果,如“復古人比興之體”“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5]68-69等。這些優秀成果都融化在黃遵憲的詩歌創作中了。
梁啟超對擬古主義采取的策略是重視“新語句”在“新詩”創作中的地位。他提出“詩界革命”的原因之二是對當時的“新詩”創作感到不滿意,在他看來,黃遵憲雖然能創造新意境,“然新語句尚少”;夏曾佑、譚嗣同等人雖然“善選新語句”,但“其語句則經子生澀語、佛典語、歐洲語雜用”,“已不備詩家之資格”[1]1219。“文界革命”要求在淺近的文言中雜以外國新詞語相同,梁啟超的“詩界革命”同樣將“新語句”作為“新詩”的內涵和標準之一。在梁啟超看來,“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后成其為詩”[1]1219。但梁啟超對外來“新語句”不是照單全收,而是有所要求,從他對夏曾佑、譚嗣同等人的批評來看,他所心儀的新語句不應艱澀難懂,而應明白通俗。
由于“新語句”大多屬于外來語,雖然新穎,但畢竟陌生,加上音譯等原因,使“新詩”在表達“新意境”的同時亦具有晦澀難懂的特點。而梁啟超又要求“新語句”必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這就必然造成“新語句”的自由表達與“古風格”的格律規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1902年以后,隨著“詩界革命”的推進,梁啟超也意識到“新語句”與“古風格”的矛盾,遂逐漸淡化了對“新語句”的要求,將“詩界革命”的內涵簡化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并認為“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明確否定了“新語句”這一形式革命。在《飲冰室詩話》中,他說:“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茍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不爾,則徒示人以儉而已。”[1]5327這時的“新名詞”已經不再是最初倡導時的必備條件,而是可有可無的,所以,當梁啟超用“舊風格含新意境”來替代“三長”,并將其作為“詩界革命”的主體時,“詩界革命”的內涵已發生了重大轉變:“新語句”被刪除,“舊風格”取代“新意境”躍居第一位,并以前者來涵蓋后者,一個“含”字,表明“舊風格”主導地位的確立。從梁啟超所寫的詩歌來看,第一,“新語句”出現頻率確實不高,有時為了適應整首詩的詩體要求,不得不對新語句進行簡縮,如“孕育新世紀,論功誰蕭何?華拿總馀子,盧孟實先河。”(《壯別》)詩句中的“華拿、盧孟”都是人名的簡縮,指華盛頓、拿破侖、盧梭和孟德斯鳩。如果沒有注釋,很難理解其含義。第二,梁啟超心目中的“舊風格”主要是古體詩、樂府詩的風格。梁啟超詩作中很少有近體詩,絕大多數是以七言為主的雜言體詩,具有離騷體、歌行體的特征,不拘句式字數,不講平仄押韻,與黃遵憲的詩作相比,顯得更為靈活,體現了他對“古風格”的重視。
黃遵憲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古風格”(或“舊風格”)這一概念,但也強調要繼承古詩的優秀成果。這種對“古”“舊”的強調,極大地限制了“新詩”詩體的發展,使得“新詩”難以突破舊詩體的形式束縛。雖然“詩界革命”后期也表現出吸收民間歌謠、彈詞的通俗化傾向,但并未完全觸動中國古典詩歌的體制,詩歌的文體面貌并未發生多大的改變,加之通俗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啟蒙宣傳,對詩歌理論并無多大興趣,且創作規模不大,因此“似乎也還談不上具有整體突破傳統詩體的意義”[3]187。
總的來看,“詩界革命”雖然沒有突破中國古典詩歌的詩體,但也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其一,詩歌語言走出古奧典雅的文言傳統,向簡潔淺近的文言和通俗易懂的白話靠近,發揚了樂府詩辭的清新平實的風格,為“五四”新詩的白話寫作奠定了基礎。其二,外來“新語句”的出現打破了傳統詩歌文言寫作的局面,促使詩人開始思考“新語句”與“舊風格”的關系,盡管思考的結果是刪去“新語句”,保留“舊風格”,但畢竟為“五四”學人重新考量詩歌的發展路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三、“小說界革命”:文白參用的古典章回體
在晚清“三界革命”中,“小說界革命”的影響最大、最深遠。它不僅改變了中國古典文學既有的雅俗格局,將處于“街談巷語”的小說提升到“文學之最上乘”的地位,而且推動了中國文學語言由文言向白話的轉變,為“五四”白話文運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從語言形式上看,“文界革命”和“詩界革命”以淺近文言為主,夾雜白話和新詞語,而“小說界革命”則力倡“俗語”。1897年,嚴復和夏曾佑以幾道、別士的署名在《國聞報》發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從文學傳播角度論述了小說采用口說語言的必要性:“若其書所陳,與口說之語言相近者,則其書易傳。若其書與口說之語言相遠者,則其書不傳。”[6]25梁啟超則從文學進化角度論述了俗語的重要性,他認為:“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并斷言:“小說者,絕非以古語之文體而能工者也。”[6]82狄平子(即楚卿)也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看到了俗語文的優勢,并預言中國文學“若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剝去鉛華,專以俗語提倡一世,則此后祖國思想言論之突飛,殆可未量。而此大業,必自小說家成之”[6]80-81。嚴格來說,“口說語言”(即口語)、“俗語”、“白話”三者的內涵并不一致,“口語”相對于“書面語”,“俗語”相對于“雅言”,“白話”相對于“文言”,三者雖有交叉,但絕不等同。對此,“小說界革命”的倡導者們并沒有加以明確辨析,而是采取模糊處理,將它們視為同一,基本上是在與“文言”對立的語境中來使用“俗語”“口語”和“白話”的。
盡管晚清仁人志士對小說應該采用俗語具有理論上的高度自信,但經不起小說寫作實踐的檢驗。梁啟超本人親自創作了白話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但只寫了五回,就寫不下去了。究其原因,除了客觀上梁啟超“身兼數役,日無寸暇,更安能以此余力及此”外,更多的恐怕還是不能很好地把握這種小說的語言和文體。在《新中國未來記·緒言》中,梁啟超坦言了自己的不足,認為它在文體上“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在語言上“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篇累牘,毫無趣味”[1]5609。由于小說中大段引用其他文體的語言,并穿插大量游離小說情節的議論,所以,藝術相當粗糙,注定了它的難產。
另外,梁啟超在翻譯外國小說的過程中也深刻體會到新小說語言建構的艱難。在《十五小豪杰》“譯后語”第一回中,梁啟超對自己的翻譯充滿自信:“今吾此譯,又純以中國說部體段代之,然自信不負森田。”但譯到第四回,梁啟超則有力不從心之感:“本書原擬依《水滸傳》《紅樓夢》等書體裁,純用俗話,但翻譯之時,甚為困難。參用文言,勞半功倍。……譯者貪省時日,只得文俗并用。”[1]5674此時這種“只得”之情與開始時的“自信”之情相比,顯得帶有更多的迫不得已的無奈色彩。
不惟梁啟超有這種無奈之情,狄平子、姚鵬圖等也深有同感。狄平子在文學發展中看到了俗語文體的優勢,但也看到了晚清新小說所面臨的語言困境:“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故言文分離,此俗語文體進步之一障礙,而即社會進步之一障礙也。為今之計,能造出最適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參半焉。此類之文,舍小說外無有世。”[6]78顯然,在狄平子提出的兩種“為今之計”中“造出最適之新字”不太可能,唯有“言文參半”比較可行。姚鵬圖也以親身經歷講述了純用白話的難度:“鄙人近年為人捉刀,作開會演說、啟蒙講義,皆用白話體裁,下筆之難,百倍于文話。其初每倩人執筆,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書。然總不如文話之簡捷易明,往往累牘連篇,筆不及揮,不過抵文話數十字、數句之用。”[6]152對于身處強大的文言傳統中的晚清學人來說,要想完全拋棄使用習慣的文言,改用生疏的純白話,是需要時間來調整和適應的,而在這一磨合期中,文言與白話參用是其必然之選擇。
可見,“小說界革命”的同仁們雖然在理論上認識到新小說應該純用俗語或白話,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則很難做到,形成了文言與白話參用并行的局面:一方面,在同一篇小說中,文言與白話兼用;另一方面,在同一本雜志中,文言小說、文言與白話參用的小說也能和平共處。這說明,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中,純用白話來寫新小說還有相當的難度。從晚清白話小說的最高成就“清末四大譴責小說”來看,雖標明“白話小說”,實際上也是文言與白話參用。陳平原對此有一個評價:“李伯元的文體最為通俗,其中雜入諧文的成分,嬉笑怒罵,淋漓盡致,最能體現譴責小說的文體特征。曾樸的小說‘文采斐然’夾有不少文言辭藻,文人趣味較濃,可不時有掉書袋、炫耀文墨的毛病。吳趼人和劉鶚的文體介于李、曾之間,不太文也不太白。”[7]769“夾有不少文言辭藻”“不太文也不太白”等說明晚清白話小說在語言上仍然很難完全擺脫文言傳統的影響,文言字詞、文言句式及文言腔調等在晚清白話小說中仍占有相當的比重,但在朝著淺近易懂的方向發展。
此外還需辨析的是,“文白參用”中“白話”本身也存在官話與方言的糾葛。一般來說,為了更好地宣傳和普及,晚清白話小說多采用“官話”,因為“官話”使用的范圍廣,易于被廣大民眾所理解。這對于身處官話區的作者來說自然比較容易,但對方言區的作者來說,則有如何將方言轉化為官話的困難。如海天獨嘯子創作《女媧石》時就有這種感受:“小說欲其普及,必不得不用官話演之。鄙人生長邊陲,半多方語。雖力加效顰,終有夾雜支離之所,幸閱者諒之。”[6]148對大多數方言區的作者來說,在方言與官話兩種語言中自由轉換是相當不易的。因此,有的作者為了省去轉換的麻煩,干脆以本地方言為主進行寫作。如韓邦慶用吳語創作長篇小說《海上花列傳》,他在書中“例言”里指出:“蘇州土白,彈詞中所載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之,故仍用之,蓋演義小說不必沾沾于考據也。”[8]162為了便于讀者的理解,作者在小說的后面附有“《海上花列傳》方言簡釋”,對文中出現的方言詞進行解釋。程宗啟《天足引》運用的也多是杭州方言,作者指出:“做白話的書,大概多用官話。我做書的是杭州人,故官話之中,多用杭州土音。想我這部書做的很不好,能彀杭州女人家大家看看,已是僥幸萬分了;若是外府外縣的女人,能賞個臉兒,看我這部書,想來土音雖不同,究竟也差不多的,又何必慮他呢!”[6]215
但這些用方言創作的小說,也不是純方言小說,因為方言與方言之間,讀音雖然差別很大,但書寫形式差別不是太大,對讀者的理解不會構成太多的障礙。程宗啟之所以敢用杭州土音來寫小說,除了將讀者群主要設定為“杭州女人家”外,更多的是考慮到“土音雖不同,究竟也差不多”,正因為如此,所以,才希望此書能得到“外府外縣女人”的青睞。而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之所以用吳語創作,也是因為“所載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之”。這種看法與當時的白話報刊不謀而合。晚清白話報刊雖多以地方命名,但大都以通行的官話為主,夾雜地域方言,以擴大其影響。白話小說多刊載于白話報刊,因此,語言上的要求趨于一致。
晚清開創了小說發展的盛世,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小說繁榮景象。小說的內容與時代緊密互動,小說的類型層出不窮,大大突破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書寫范圍。但從小說文體上看,與“詩界革命”未能完全觸動中國古典詩歌的詩體一樣,“小說界革命”也未能從根本上觸動中國古典章回小說的體制,新小說在舊章回體的格局中難以突圍。從《中國近代文學大系·小說集》(共七卷)中所選錄的小說來看,章回體小說占了絕大多數,只有少數幾篇打破了章回體格局,如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徐枕亞的《玉梨魂》等,采用了“第一章”“第二章”的現代小說形式,不再采用“話說”“卻說”的開頭方式和“正是……”“請聽下回分解”的結尾方式,盡量消除和淡化章回體小說的影響。盡管如此,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仍殘留著章回體小說說書人的痕跡,小說中常常使用“讀者試想”“讀者思之”“讀吾書者”“吾讀者”等詞語,并用第一人稱“余”與之對照,形成面對面即時交流的生動圖景。[9]這種與讀者進行交流的“談話的口吻”實則延續了中國古代話本小說和章回體小說的說書人口吻,其目的是為了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加強與讀者的情感交流。這樣看來,蘇曼殊等人的抒情體小說雖然擺脫了古典章回體小說的外在形式,但由于其文言式的語言和穿梭于文本中的說書人口吻,仍然不能從根本上實現晚清新小說文體的變革。
晚清新小說文體難以突破舊章回體的原因在于,晚清對小說地位的提升和對小說的重視,主要是從社會功用角度出發,而不是從小說文體自身發展考慮的。由于將注意力集中于小說的社會功用,所以對小說語言和文體的關注也是出于宣傳和啟蒙的需要。從語言上看,小說語言應該純用白話或者俗語的要求,是因為白話相比文言,更通俗易懂,更容易為普通民眾所接受,也就更能實現“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新小說》第一號)的政治理想。從文體上看,小說采用章回體形式,是因為章回體為民眾所熟悉,尤其是其中的說書人傳統更為民眾所喜愛,這對于小說的傳播和普及是十分有利的。晚清新小說在“文學之最上乘”(梁啟超)與“社會之藥石”[6]148之間更傾向于后者,注重小說的社會作用,而忽視小說的文學審美作用。因此,梁啟超雖然將小說從不入流的小道提升為最上乘的文學,“觀念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可思維方法和審美趣味并沒有改變”[6]6。這也決定了晚清新小說在文體上不可能超越古典章回體小說,而只可能在舊有的體制中做語言上的微調,在文白參用中,使用淺近的文言和白話,并加入方言土語和一些外來新詞語,促使小說語言朝著理論預設的白話化(俗語化)目標發展。
四、結語
從文學形式角度來看晚清“三界革命”,可以發現:
1.在語言上,“三界革命”都對淵雅古奧的文言進行了改革,采用淺近通俗的文言,并加入當時的俗語、方言和外來新詞語,但在文言與白話的使用比率上不太一樣,散文和詩歌以淺近文言為主,白話摻雜其中;小說則形成文言與白話參用并逐步向白話過渡的語言格局。
2.在文體上,“文界革命”的改革力度最大,突破了桐城古文的“義法”,能夠進行“汪洋恣肆”的半自由書寫,形成了“報章體”的風格,但整體上仍延續了文言文的表達習慣。“詩界革命”次之,在以舊詩體為主的同時,也吸收民間歌謠體形式,雖不講究句式、平仄,但在字數、押韻等方面仍保留著古體詩的特點。“小說界革命”雖然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小說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實現了小說語言由文言向白話的轉變,但對小說的文體未能進行有力的變革,仍拘束在中國古典章回體中。
“三界革命”是晚清白話文運動在文學領域中的實踐,初步實現了“改革文言、言文合一”的目標,但離梁啟超“專用俚語”、裘廷梁“崇白話而廢文言”的愿望還有相當的距離。晚清白話文運動并沒有實現用白話完全取代文言的理想,文學語言的整體格局是文言與白話并行。在文體上,盡管對散文、詩歌、小說三種文學體裁進行了革命,但都未能完全突破這些體裁原有的形式規范,只是作了局部的調整和改革。與“三界革命”響亮的口號相比,調整和改革的力度顯然過于微弱。
“三界革命”未能在語言和文體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除了時代的局限之外,或許還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1.“三界革命”沒有與語言學界的語言改革運動相結合。晚清白話文運動除了文學界的改良運動之外,還有語言學界的語言改革運動(如勞乃宣的“切音新字”、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國音統一、國語研究會等),但這兩個場域的變革各行其是,未能進行有效的溝通與對話。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只關注“言”(口頭語言)與“文”(書面語言)的統一,卻忽視了“言”自身的“讀音統一”和“國語統一”,因此,“三界革命”在向“言文合一”的目標邁進時,往往因“言”的不統一而受阻,從而延緩了文言向白話轉變的進度。加上晚清學人都有著深厚的文言傳統,很難完全擺脫文言的羈絆,這也增加了文言向白話轉變的難度。胡適在總結“五四”白話文運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時,曾把與當時的國語運動合流作為重要的原因之一,從中也可反觀晚清白話文運動在這一方面的缺失。
2.“三界革命”具有濃厚的政治功利,其目的是宣傳思想,啟蒙大眾,以實現政治變革。因此,文學是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而受到關注的,語言是作為文學表達和教育民眾的工具而受到重視的,文學及語言自身的意義和價值被忽略了。由于局限于工具論視野,晚清學人只有在面向普通民眾時,才努力采用淺近的文言和白話,以便于民眾理解和接受;在其他時候,寫詩作文都使用文言。晚清白話文運動的核心人物黃遵憲、梁啟超、夏曾佑等人所寫的詩文都以文言文為主;裘廷梁雖然大膽呼吁“崇白話而廢文言”,但他的檄文《論白話為維新之本》通篇均是文言。可見,白話在晚清只是作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用來進行政治宣傳、開啟民智的一種權宜之計,只是在通俗好用的工具價值層面被關注,其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基本上被忽視了。這必然阻礙白話在晚清的發展,也必然影響白話在“三界革命”中的運用。
3.從現代語言哲學所倡導的語言本體論來看,語言不僅是思維的工具,也是思維本身;語言不僅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本身,語言與思維、文化具有同一性。選擇一種語言,也就選擇了與這種語言相對應的思維方式和表述方式。深受傳統文言影響的晚清學人,選擇了文言作為主要的書寫形式,也就受制于文言這種語言系統所具有的思維方式和表述方式,這就決定了晚清“三界革命”的文體變革難以突破固有的形式規范。正如高玉所說:“晚清黃遵憲、梁啟超等人也試圖對中國傳統文學進行變革,但中國古代文學終于沒有在晚清發生轉型,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語言以一種巨大的力量所產生的無形限制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他們也試圖超越傳統、反抗傳統,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古代漢語體系以及隱含在這語言體系中的思想體系的原因,他們的反抗終歸是在語言體系內的左沖右突,終歸是在傳統限度內的反抗,語言就像一道魔障,使他們無法超越傳統,使他們的反抗歸于無效。”[10]85
[1]梁啟超.梁啟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梁啟超.中國各報存佚表[J].清議報,1901(100).
[3]鄧偉.分裂與建構:清末民初文學語言新變研究(1898—1917)[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4]譚學純.百年回眸:一個詩學口號的修辭學批評[J].東方叢刊,2004(2):107-122.
[5]陳錚.黃遵憲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5.
[6]陳平原,夏曉虹.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7]陳平原.陳平原小說史論集[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8]吳組緗,端木蕻良.中國近代文學大系1840—1919:小說集(一)[M].上海:上海書店,1994.
[9]黃軼.現代啟蒙語境下的審美開創:蘇曼殊文學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高玉.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責任編輯劉海燕)
“The Three-bound Literary Reform”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ism
XIAO Cui-y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injiang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The Three-bound Literary Reform”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forms the three types of literature,poetry,prose and fiction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norms,forming a new language and style.However,it does not reach the expected goal:the union of linguistic form and the reform of stylistic form.Therefore,it fails to realiz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reform;poetic reform;reform in fiction;language;style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1.011
I207
A
1008-3715(2015)01-0050-07
2014-12-10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中國語言學批評研究”(10CZW013)
肖翠云(1978—),女,安徽寧國人,文學博士,閩江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語言學、文藝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