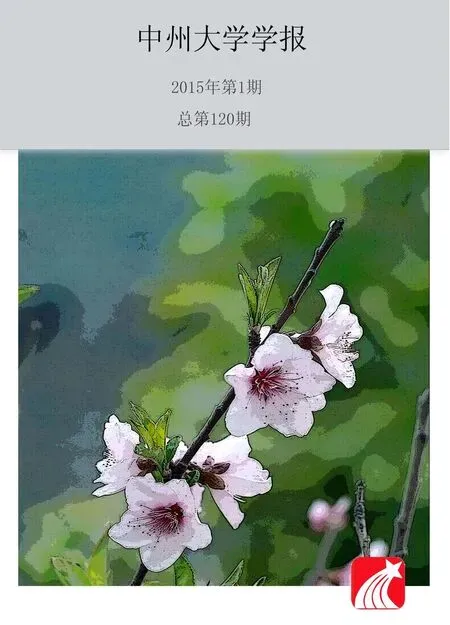性別世界的進化
張月(鄭州大學文學院,鄭州450001)
性別世界的進化
張月
(鄭州大學文學院,鄭州450001)
性別的進化總有權力的滲透,權力造就了性別的所謂優劣與等級化,因其性別特征差異,一方占據支配地位,另一方屈居從屬地位。性別特征究竟是生理結構功能在進化過程中的自然顯現,還是社會文化的建構之物?多數男性學者傾向于生物決定論,而女性學者則堅持文化建構論。本文選取瑪格麗特·米德、西蒙·德·波伏娃、伊麗莎白·戈爾德·戴維斯與愛德華·O·威爾遜、約翰·莫尼、渡邊淳一、皮埃爾·布爾迪厄等作為雙方代表性人物,展示其各自的論點、主張及論據,并作為第三方指出性有差別,但無優劣,壓迫性的性別等級制與性別無關,與權力的機制相關。在進化的過程中,男女皆展示了自己的存在價值及不可或缺的功能和意義。
性別差異;進化;生物決定論;文化建構;男權社會
什么可以將男女兩性最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顯而易見,答案是愛情。在愛的實踐活動中,男女既顯現出共性,也因個體差異,表現出彼此獨具的特性。渡邊淳一的《失樂園》中的男女主人公,為了捍衛他們凄美的愛情,不惜同飲毒酒,擁抱而亡,以致鑒定死因的法醫也無法將他們相互緊抱的身體掰開;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的作家風流成性,而女主人公卻癡愛著他,矢志不渝;在《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杜十娘對李甲情真意切,換來的僅是李甲的薄情寡義;《鶯鶯傳》里的鶯鶯對張生一往情深,卻遭多情才子張生遺棄;在《霍小玉傳》中,女主人公對擅長詩文的狀元郎李益情深意切,可她所癡愛之人同樣也是個負心之人。
矢志不渝還是多情善變,實在因人而異。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女子癡心,男人負心”的現象時有發生,似具有某種規律性,對此,文藝作品亦多有表現。這就使人不得不相信,男女在愛情方面的確存在著性別差異,此類差異既顯現在行為活動層面,也顯現于精神世界層面。依據對現實的觀察,結果顯示,男女的差別不僅表現在愛情上,也表現在生活的諸多領域里。生物學家、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等為此著書立說,對兩性的差異展開認真嚴肅的探討,并根據自己的考察,對彼此的性別特征進行描述與論證,他們所列出的一系列特征通常具有顯著的二元性:如男人理性,女人感性;男人強悍,女人柔弱;男人主動,女人被動等,并試圖將其解釋為兩性恒在的乃至與生俱來的特征。
針對這類帶有固化特征的主張,不少學者發出了截然不同的聲音,他們絕不認可,其中以女性學者為甚。反對固化主張的學者也承認,其所列舉的此類特征在現實中的確存在,但他們對其釋義完全不予認同,對其歸因更是拒絕接納。在這些學者尤其是女性學者看來,多數所謂的女性特征并非女人天性使然,實為社會造就。女性學家希爾·海特依據其團隊的調查得出結論說:男人總是要求女人應該是什么,而不在意她們原本是什么;西蒙·德·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公開宣稱: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瑪格麗特·米德則通過對三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的實地考察,證明性別特征并非皆源于天性,其大多為社會、文化及習俗所塑造;伊麗莎白·戈爾德·戴維斯更是在其《第一性》中坦言,女性作為源頭本來就具有所有的特質,男性僅是其原質的突變產物。毋庸諱言,就對男女性別特征的認識而言,女性學者西蒙·德·波伏娃、瑪格麗特·米德及伊麗莎白·戈爾德·戴維斯等與約翰·莫尼、H·穆薩弗、愛德華·O·威爾遜、渡邊淳一等持守生物決定論觀點的男性學者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一
瑪格麗特·米德系杰出的女人類學家,是持守文化塑造性別性格、行為模式及生存樣式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著述甚豐,其《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系闡發這一主張的代表作。在此著作里,她詳盡記述了其對阿拉佩什、蒙杜古馬和德昌布利三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的實地考察的情況,用實例印證其研究成果。通過對三個部落的深入觀察與系統比較,她發現:人們通常所認定的命中注定的性別特征并非天生,而是社會文化塑造的結果,抑或更直截了當地說,是社會強加給不同性別的結果。“一個性別中的某些成員所表現的特征往往被強加給該性別所有成員。表現在這個成員身上的特征不允許表現在另一性別成員身上。性別差異的界定史告訴我們,社會文化在這方面是專斷的,這種按社會意志的編排,在學術和藝術領域尤為突出。”[1]272那種被認為是天性的東西,在米德看來,原來明明只是一種假定,卻被認定成與生俱來、恒定不變的存在。無論這種認定是有意還是無意,它都會令人們形成關于性別的刻板意識與觀念。
毋庸諱言,將性別差異固定化,將有助于社會對不同性別的人進行有效的管理與控制,將之納入相對固定的精神領域與現實領域。瑪格麗特·米德根據深入的觀察,發現原始部落社會就已經注意到了性別差異具有的價值,這些部落社會依據自己的需要,對不同的性別進行氣質及人格上的設定,以德昌布利部落社會為例,她對此做了具體說明。“德昌布利社會至少已經意識到了性別差異的重要意義。他們根據鮮明的性別差異去編排、塑造社會人格。當然,相對我們而言,他們正好是一幅倒置的性別差異圖景。”[1]274之所以說是一幅倒置的性別差異圖景,她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德昌布利男女的性格與行為,與我們已知的絕大多數社會中的男女的性格與行為截然相反;她并不認為,這與他們生物性的身體結構有任何必然的關聯,相反,她堅信認為這完全是文化與傳統的造物。
瑪格麗特·米德相信自己的眼光,并給予了具體的說明:“完全有理由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徳布昌利女人生來就是盛氣凌人、樂于支配他人的;也不是生來就有組織能力、管理氣質的……但是,很多德昌布利的女孩子長大成人后總要表現出這些特征。這種情形說明,徳布昌利的性別人格觀念與我們傳統社會的通常設定恰恰相反。所以,顯而易見,徳布昌利文化也是專斷地把一些人格特性規定在女性身上,同時把另一些人格特性規定在男性身上。”[1]274
從上述瑪格麗特·米德的表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她認定性別特征并非先天所賜,而是社會、部落文化塑造的產物,在她眼里,人類天性無比柔順,極具可塑性,可極為精確地應答周圍多變的文化環境刺激。性別特征的成因不能用種族、地域飲食、自然選擇等理論來解釋。根據所收集的資料,她立論說:“兩性人格特征的許多方面(雖不是全部方面)極少與性別差異本身有關,就像社會在一定時期所規定的男女的服飾、舉止與生理差別無關一樣。”[1]266
瑪格麗特·米德在書中提供了大量支持其主張的具體例證,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她沒有說明也無法說明的是:為何徳布昌利人的生存樣式與性別特征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普遍存在的則是與之相反的模式?
或許這一問題涉及更多復雜性的因素,如生命深層的機制、生存斗爭的取向、人的進化、社會的選擇等,關聯度最高的應該是兩性差異的內在性、各自體能上的優勢、勞動分工、兩性之間的合作與對抗、權力角逐與社會角色約定等。但無論如何,瑪格麗特·米德提供的支撐其主張的例證,畢竟只是一種特例,用她的語匯來說,是“一幅倒置的性別差異圖景”。在世界范圍內,未被倒置的性別差異圖景,是絕大多數社會中最為常見的圖景,這種圖景如何構成,又如何成為最為普遍存在的圖景,需要人們進行更為深入的考察,給出更具說服力的分析與解釋。
二
在性別特征的釋義上,男女學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男性學者多傾向于將兩性的特征視為生物—社會—歷史發展進化的必然產物,而絕大多數女性學者卻更傾向于將其看作是文化塑造、文化規訓與文化順應的結果。男性學者相信,從合子即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就一次性地決定了男女生理的結構、生命功能和身體外形上的差異。這既是男女身體結構、體能差異的起始點,性別特征形成的基本條件,性別勞動分工的根據,亦是性別差異性審美的始基。男性與女性的許多性別特征,皆可從生物學上找到解釋的終極依據。可女性學者不贊成這樣的研究導向,她們認為,男女之間的差異源自文化的“監制”,所謂男女性別特征,是人所創造的文化產物,是人為的結果,而非所謂歷史的必然,那種過度強調性別特征的生物基礎的主張實際上是生物決定論,排斥文化在性別特征塑造上所起的關鍵性作用。
究竟是什么因素在性別特征形成的過程中起著關鍵性作用?不同的研究者給出的回答皆不相同,而每一種研究都有支撐其觀點的證據。瑪格麗特·米德的文化建構論,依據的是自我親歷的有效的同時又是有限的人類學實地考察。而性別研究專家約翰·莫尼、穆薩弗等人則根據廣泛的研究與社會觀察,提出自己的主張,他們給出的說法是另一種模樣。關于男女差異的性別特征,約翰·莫尼在《人類性別和性角色的確定因素》中有著這樣的表述:“男人用一種方式行事,女人用另一種方式行事。這種與性別有關的行為范圍很廣,從服飾到工作常規和謀生方式,從禮節和儀式到家庭勞動分工。這種多種多樣的立體式的男人怎樣女人怎樣的差別,最終可能是源于最基本的性別的差異,但常規本身也受習慣的制約,也可能具有隨意性,還可能隨時突然變化或隨著文化類型的變化而緩慢地變化。”[2]78他的表述相對委婉、含蓄,且注重描述,雖然也提到了習俗、文化與時尚的作用,但他還是傾向于將男女不同的行事方式歸因為基本的性別差異,而這種差異根植于身體的內部結構。
如果從還原的角度入手,追根溯源,男女性別特征的差異的歸因,總是要回到生物學的層面。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O·威爾遜在其著述《社會生物學》中一開卷就寫道:“文化進化實質上建立在生物特征的基礎上。”[3]4以此為基礎,他也談到了生物進化與社會的互動:“大腦的生物進化,特別是大腦皮層的生物進化,受制于一定的社會背景。”[3]4一些文化學者與女權主義者都排斥這種觀點,他們更愿意相信文化建構論,相信文化強悍的塑造力量,他們堅持認為,人有無限的可能性,男女性別特征完全由文化塑造,他們拒絕承認文化塑造得以實施的生物學基礎。然而,事實并非因人拒認而不存在,實際生活中存在著的男女差異始終具體而鮮活,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時時看到明顯存在著的兩性差異。
與女人相比,男人天生體格高大,身體強壯,肌肉發達,體能、體力上優于女人,在體力占主導地位的生命實踐活動中,發揮著主導性的重要作用。耕種、狩獵、爭奪領地的角逐、戰事等活動,對體能有著較高的要求。在此類活動中,男人扮演著主要角色,他們保衛自己的疆土,獲取食物,保護女人和孩童。在漫長的生存活動與生命實踐中,勇敢、堅定、強悍、威猛、富于競爭性、勇于擔當,逐漸成為他們的性別特征。
與男人相比,女人的優勢是生命力旺盛,身體平衡系統好,耐受力好,在新生兒中,女童的成活率高于男童,在無需體力優勢的活動領域,女人的作為如果不優于男人,也絕對不亞于男人。在母系氏族社會里,女性一度成為人類社會的主導者,其歷史功績已載入史冊。但隨著體能、體力甚至蠻力在生命實踐活動中變得越來越重要,男人逐漸成為主角,取代女人原有的統治地位,從此,父系氏族社會拉開了帷幕,男權開始了其征程。在其漫長的征程中,男人進入社會生活,在領地的擴張、資源的爭奪、利益的角逐、權力的捍衛中,越來越多地訴諸于理性與實效,依據理性與功用行事。
女人在強力主宰的世界失勢,被迫從社會生活離場,退避到家庭中,成為孩童的生養者、哺育者、家庭成員的呵護者。與此同時,她們更為充分地展示自身的優勢——自然天成之美與以直覺形態顯現的智慧,并以此作為路徑,獲取權力與卓越地位。與動物界雄性比雌性美的情形相反,女人天生就是美的載體。美讓女人成為魅力的化身,令男人迷戀、陶醉。男人靠強力征服世界,女人用魅力征服男人,男人將征服的世界心甘情愿地奉獻在女人面前。
無論在家庭還是在維系美的世界中,女人更多使用的是豐富的感性,而非理性。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女人的感性變得高度發達,愛美、敏感、感悟能力超強、富于同情心、仁慈、堅韌、樂于傾聽、善解人意等,遂成為其正面的性別特征。
若從社會分工、生產方式與生產力發展的進程分析,男女活動領域的分化、各自的側重及自我發展,既是社會的歷史性選擇,也是性別合作的自然選擇,這類選擇基于各自的性別優勢,基于男女雙方各自不可替代的能力與屬性,以及男女源自生命深層的聯合。與種系繁衍密不可分的生命孕育、哺乳是男人天生無法承擔的重任,與此毗連的生命領域自然也屬女性掌管,而男性則更多地馳騁于以力量取勝的天地之間,追逐權力,獲取人生的資源與財富,保護婦孺與部族,捍衛家園。
傳統之中的男女組合無論是“英雄與美人”,還是“野獸與美人”,強調的無一不是男人的力量和女人的美。在文藝作品中,藝術家總是側重表現男性的力量,女性的美、愛與溫情。在注重體現美感的造型藝術中,尤其是在以表現人為中心的西方造型藝術中,女性成為絕對的主角,絕大多數藝術作品表現的都是以女性美為中心的主題。中國的文藝作品同樣也表現“英雄與美人”的主題,但在中國,才智在價值上的定位不亞于力量,甚至更高,在許多情境中,為了體現才智的價值,藝術家將男性的力量置換為才智,同時也將女性的美處理得更為表層化,于是“英雄與美人”就轉換成了“郎才女貌”。中國傳統藝術的表現主題,除了“帝王將相”之外,就是“才子佳人”。
在現實社會里,男人似乎總是置身于征服大世界的主戰場,而女人是人類生命的養育者,是男人生命的港灣與溫柔之鄉。女人仿佛永遠可以用美來征服男人,她們是男人永久的誘惑與創造的靈感,她們關愛男人,教導男人,是男人生命躍遷的引領者。雖然有不善于與女性交往的男人表達對女性的不滿、敵意與畏懼,但多數男性還是愿意將女性視為理想的人生伴侶,認同歌德在《浮士德》結尾處對女性的崇高定位:“永恒的女性,引我們飛升。”[4]496而男性的力量令女性似乎天生認定,男人能給她抵御外部殘酷世界的安全感,將男人視為自己的呵護者與保衛者,看作是自己的人生依靠。所有這些男女現實世界的表象之形成,從終極的意義上來看,皆與生物的內在生長趨勢與社會進化有著不解之緣。
三
男人和女人共同擁有這個世界,他們感受著對方擁有的力量,體驗著對方給自己帶來的感受,并不斷地為對方進行定位,他們都自以為了解,他們的自以為是卻讓彼此深深地誤解對方,相互之間戰火不斷,紛爭不息,使得曾經是自己另一半的人變成了親密的陌生人,互生怨恨,變成又愛又恨、卻彼此無法真正分離的歡喜冤家。
彼此了解是男女雙方的共同愿望,可他們彼此卻往往深陷于誤解的陷阱之中,原因固然多種多樣,但我們可以嘗試從被情緒遮蔽、被道德審判拒斥的真相入手,暫時中止對彼此品行的倫理評判,去除遮蔽,直面真相,并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立場上,真正地理解對方,而非審判對方,無論對方曾經是多么令人失望,令人心痛,甚至令人心生怨恨。
男人對女人失望,女人也對男人失望,且女人對男人的失望尤甚。觀其緣由,不外乎尋常可見的男人對女人的背叛,其中包括情感上的背叛與肉體上的背叛。文藝作品著墨最多的世界是男女的世界,而“癡心女子負心漢”又是文藝作品著力表現的主題之一。在中國,從《衛風·氓》《邶風·谷風》,敦煌曲子詞《望江南·天上月》,賀鑄的《生查子·陌上郎》,到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等,表現這一主題的作品可謂不計其數。從某種意義上看,這也是實際生活的一種寫照。男人似乎總是辜負女人的一往深情,這讓女人對男人極度失望、怨恨,以致大加討伐。的確,男人的負心與多情理應從道德上加以譴責,文藝作品的立意原本也在于此。
然而,道德譴責無助于解釋這一現象何以經常發生。要揭示男人的負心與多情,除了要留意其注重功利、耽于享樂、四處留種、患得患失外,更要關注其負心多情行為背后的生理及心理機制。
從生物學的維度考察,我們必須承認,男性既是有性的人,也是雄性動物。動物學研究表明,作為雄性的哺乳動物,其天生就具有四處傳遞自己遺傳基因的本能,他們隨機播撒自己的種子,以增大繁育后代的幾率。據動物研究者的統計,在哺乳動物中,有超過80%的雄性擁有多個異性伴侶,人雖然比其他哺乳動物進化程度更高,但其作為動物的本能始終未有改變:復制自我、繁衍后代的原始沖動始終永居第一位。男性的多情與風流看似品行不端,實則亦是其受動物性本能驅使而未加自我控制的一種行為結果。男人作為雄性動物的多戀取向極有可能導致其到處播種,四處留情,貪戀多個有吸引力的異性伙伴。男性的這種所作所為,實在令女人難于理解與接受。但這與增加繁育后代幾率的生命內驅力高度相關。
在莎士比亞的筆下,人被譽為“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5]25但其始終未能脫離動物界。男女的世界中彼此雖有“海枯石爛永不變心”的山盟海誓,有永遠忠實于對方的愛之神圣律法,卻總也抵擋不住來自本能巨大力量的沖擊,從兩性的理想關系的最高點,跌入動物性王國的深谷;兩性對等的神圣權利承諾,換來的往往是某一方的失信,通常是男方的毀約與背叛。
究其原因,恐與人的生物進化的歸路密切相關。威爾遜指出,人類基因型和其進化的生態系統都是在極不公平的情況下形成的。有著公平、權利對等內涵的道德是文明世界的產物,其出生時間較晚,良知自律雖有內生性依據,可大于良知的道德尤其是社會性道德他律的主要構成是外源性的,道德本身帶有強烈的社會理想色彩,盡管頗具感召力,可與本能的力量相遇時卻無法與之抗衡,在本能面前通常顯得力不從心。
社會性道德,往往與人未曾規訓的原始生命感受與體驗相左,甚至相矛盾與對立。社會性道德要求的常常是一種缺乏內心真實驅力的所謂善舉,藝術家尤其是男性藝術家,將這種訴諸于善舉但與本能的真實相違的道德,斥之為偽善,認定為是對自己的肉體所撒的謊言。男性藝術家對本能真實的強調,常常與社會性道德相背離;而他們對本能真實的堅守,會讓社會將其置于一種道德上的劣勢,令社會將藝術家視為非道德的人,甚至是反道德的人。事實上,藝術家十分看重道德,只是他們注重的是內源性維度的道德,即人類的良知,他們厭惡謊言,哪怕這種謊言能帶來好的實效。藝術家選擇直面生命的真相,哪怕這種真相令人難于承受。在社會領域如此,在兩性的領域同樣也如此。
有著醫學博士背景的日本知名作家渡邊淳一,喜歡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解析男女兩性的生命樣式,他注重生物譜系的整體性與生物性本能的功能,承認性別的原初差異與各自選擇傾向的合理性。“所有的雄性動物,從其本能上說都希望將自己的種子廣泛播撒以延續自己的遺傳因子;與此相反,雌性動物為了確保生育出具有優良遺傳因子的后代而對其交配對象嚴加挑選。兩者互補平衡,使得物種得以綿延不斷。人類作為自然中的一員,理所當然也具有這種本能,如果單單只是從道德的層面對此進行非難,等于否定人類也是動物這一基本事實。”[6]66-67
渡邊淳一的觀點表述得十分明確:我們必須承認事實,盡管從道德的層面看,這種事實令人感到不快、失望甚至絕望。但事實終歸就是事實,無論我們是否承認,事實始終存在。按照一夫一妻制對男女雙方規范行為的要求,作為雄性動物的男人的行為顯而易見是不道德的,但從種系自我持存,增加繁衍成功幾率的角度來看,其行為與這一目標的實現高度一致,符合生物種系繁衍的自然倫理。
男女的差異甚至在新生命誕生的過程中就已顯現出來,“通過顯微鏡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精子都具有進入卵子的本能,而卵子則有著從無數精子中選擇其一的本能”[6]67。渡邊淳一將其視為男女差異的“性的原點”。
男性進取性的欲求,多元化的愛欲行為,與其內在的復制自我、繁衍后嗣的原生驅力息息相關。這驅力源自生命的原結構,“男人的性欲望,可以說是先天被注入雄性DNA中的一種本能。當然,由于人類受到種種限制與道德制約,其行為不可能像其他動物那樣隨心所欲,但是我們仍應清楚地認識到,男人的性好奇以及挑戰欲望都源自于這一本能”[6]67-68。
威爾遜的研究成果,也對上述觀點形成了支撐,“多偶制在哺乳動物系統中是常規,而常見的是其中的‘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相對罕見”[3]428。
從科學認知的目標出發,暫且終止道德判斷,回到生物的層面尤其是回到物種繁衍的層面,從生物學的維度觀看,我們可以看到,男性的多配偶的行為取向與女性對配偶的精挑細選,以及由此而生的男人的進取性、攻擊性和女人的持守性、養育性為主的性別特征,實乃出自造物主的設計;男女之間看似對立沖突的行為傾向,恰恰引致了一種絕配的互補平衡,使物種得以綿延不息,亙古不斷。
然而,在物種繁衍這一事件中,男女的付出絕不對等,女性付出的代價大得驚人。在具有生育能力的年齡段,未孕女人每月僅產一次卵子,男人每月生產的精子則不計其數。卵子比精子大許多倍,遠較精子稀缺,且合子形成后要在女人體內孕育10個月之久。從嬰兒誕生到斷乳前,女人需一直對其哺乳喂養。在整個孕育過程中,女人為此付出心血和時間,有時甚至是生命。相比之下,男人的付出可謂微不足道。
生育對女人來說,如同造化之手設下的陷阱,令其深陷其中。好在這種對女人極不公平、將幾乎所有苦難與重負都加諸于女人身上的繁衍活動只是一種活動。伴隨著文明的進化,人類兩性之間的關系早已跨過這種只限于繁衍活動的關系形態,在超越生育的愛情活動中,女人享有與男人同等的自由與選擇。造物主為了補償女性,賦予女性享受性愛歡樂更多的可能性,讓性感帶與動欲區廣布于其身體的多個可觸及部位。如此一來,她們的身體可在極樂體驗過程中始終有能力享受快樂,“正是女性而不是男性能處于連續高潮的巔峰狀態”[7]102。除此之外,女性身體與心理的敏感性顯然高于男性,女性的動情區或性感帶的廣布,也使其享有比男人更多的性娛的歡樂。
男人盡管有動物性,卻畢竟更是文化的動物,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雖不時會經受本能的困擾,為其所驅使和奴役,可無數個世紀的道德規訓與文化塑造的結果依然卓有成效,不斷地在令其發生著令人欣喜的改變,造就出了為數眾多的令女人喜愛的男人。在文學作品中,既有東方好色的登徒子,西方放蕩不羈的唐·璜,也有東方坐懷不亂的柳下惠;有終生只愛祝英臺的梁山伯,癡情于林妹妹的賈寶玉,也有西方與朱麗葉共生死的羅密歐;更有現實版的用愛創造奇跡、令癱瘓多年的愛侶伊麗莎白·芭蕾特·布朗寧重新站起來的英國詩人羅伯特·布朗寧。
四
文明世界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溫文爾雅,理智而有節,雖友善卻流于表面,彼此之間深層意義上的理解幾乎難于達成,對其間橫亙著一條性別之溝的男女而言就更是如此。女人無法理解,男人何以能夠把愛與性分開;而男人則覺得女人的內心世界神秘莫測,難于捉摸,其性情時時變化無常,其想法不可理喻。在與之共處的世界里,男人對女人的感情復雜而矛盾,雖然自覺在理性與控制力上勝女人一籌,但女人的非理性的感知覺能力、直覺的智慧令其感到望而興嘆,自愧弗如。他們為此既感到焦慮,又深感恐懼,這種焦慮與恐懼經常通過其文化所塑造的諸多先知先覺的女巫形象顯現出來,在《麥克白》中,莎士比亞所刻畫的三個女巫可謂其典型。令人感興趣的是,文化藝術中不時現身的女巫皆具非凡的預言能力,可似乎總與厄運攜手。
除女性的直覺外,更令男人感到焦慮與恐懼的是女性與生俱來的美與性的魔力。西方男性文化塑造的“致命的女人”形象,即是其焦慮與恐懼的集中體現。而男性文化塑造的以“紅顏禍水”著稱的妲己、楊玉環、潘金蓮等形象,可謂西方“致命的女人”的東方翻版。
文學藝術中有著大量表現令男性焦慮與畏懼的女性形象,遠至《希臘羅馬神話》中的復仇女神阿勒克圖、墨紀拉和底西福涅、蛇發女妖美杜莎、海妖塞壬,《圣經》中希律王的女兒莎樂美,近至科克托在《俄耳甫斯》中塑造的將俄耳甫斯帶向毀滅的女人,19世紀木刻畫表現的洛瑞蕾(條頓神話中用歌聲引誘男人走向死亡的水妖),還有現代繪畫中表現的露薩爾卡們,她們是斯拉夫神話中溺水而亡的女孩的靈魂化身,魅惑路過的男人并將其淹死。“在世界各地,皆有著諸如此類的神話傳奇,現身于其間的,是一位‘有毒的少女’(在東方他們這樣稱呼她)。她是美麗動人的尤物,嬌軀里藏匿著武器,抑或隨身攜帶著秘制的毒藥,在她與戀人一起共享歡情的第一夜,將戀人殺死。”[8]190榮格派的分析心理學家弗朗茲在對各地神話傳奇做過詳盡的研究后,得出如此的結論。
有關對女人的態度,男人始終是雙向矛盾的,他們將最好的與最壞的屬性同時賦予了女性,其內心深處有關女人的“圣母—娼妓”“天使—蕩婦”“明星—婊子”等之類矛盾情結總難消解。漢字中表現美好意義的詞語多用“女”字做偏旁,與此同時,許多意義不好的也用“女”字做偏旁,甚至用三個“女”字做成了“奸”的繁體字“姦”。男人既將女人偶像化,又將其玩偶化,將其矮化,甚至妖魔化、污名化。一方面,女人在體能上不如男人,在情感上由于過于充沛而常顯出脆弱之相,在實際生活中,女性也較依賴于男人;另一方面,她們又有其自身的優勢,其獨特的能力與魅力經常超出男人的控制領域,令男人心存畏懼。
經驗是觀念的支撐,實際生活中也確有可用來顯示男性優越的所謂證據,如堅強、理性,具有原創性、責任感等。盡管并不充分,但與之相比,女人在這些方面似乎處于劣勢。亞里士多德曾溫和地表達了男性相對于女人的優越,莎士比亞則在其《哈姆雷特》中借哈姆雷特之口說出:“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5]25并塑造哈姆雷特的母親葛楚德和戀人奧菲莉亞等柔弱的形象,以圖解女性的脆弱。尼采、魏寧格、斯特林堡更是不予余力地宣揚男性優于女性,斯特林堡甚至在其表現心路歷程的《狂人辯詞》中聲稱,女人是被閹割的男性。古往今來,男人矮化、妖化女人的作品比比皆是,在《危的性——女性邪惡的神話》一書里,海斯讓我們見識了男性如何系統地將其內心的焦慮與恐懼投射于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之中,如何有意無意地將女性妖魔化與污名化。
針對男性的誤視、誤讀與污名化,為數眾多的女性學者給予了有力的回應。伊麗莎白·戈爾德·戴維斯在其著述《第一性》中,通過對生物學、神話學、人類學及大量史料與文獻的考察,證明女性非但不弱于男性,而且優于男性,女性是第一性,而非第二性。她指出,女性系本源,生物學意義上的男人是女人的一種突變異種,Y染色體是發育不良的X染色體;歷史上人們最早膜拜的神,是女神,女性最早發現了藝術與科學,最早行進在朝向文明的征途之上。
戴維斯歸集了大量的資料,首先從神話學的角度討論了女性的優越性:“在全世界各地的神話中,從太陽升起的最為遙遠的亞洲海岸,到太陽落山的浩瀚太平洋最遠端西方的群島,所有地區神話的造物主都是女神。在后來的神話里,她被男神置換——時常是有意為之,如同耶和華取代阿娜特;有時名字不變,但故意改變其性別,像是敘利亞的伊婭神,印度的濕婆神,波利尼西亞的阿提亞神;有時則是發生一種漸進的轉換變形,如墨提斯轉換變形為菲尼斯。”[9]33
隨后,戴維斯引用了生物學的一個事實,來說明阿里斯托芬關于雌雄同體隱喻本身具有的合理性,同時也暗喻《圣經》里有關亞當與夏娃的說法是顛倒了的不實之詞。其實,夏娃并非由亞當的一根肋骨做成,反倒是亞當實乃夏娃突變與劣質化的產物。“蘇珊·邁克爾墨描述過一種鳥,其雌性同時具有卵巢與睪丸,在各種各樣的情境中,兩種器官都可變得活躍。這一現象暗示人類身體的組織構造——男性與女性存在于同一個女人身體內。當其一半被分離時,兩種性別出現。柏拉圖有關人類性別分離的種族記憶之說,或許象征性地表述了那一災變:它引致了男性的突變,造成X染色體的斷裂,抑或發育障礙,進而形成形變的Y染色體。”[9]35
與傳統中將女性貶為第二性的觀點相對立,戴維斯堅持女性為第一性的觀點,她認為男人并不比女人優越。相反,女人應該比男人優越,對此她說明了其中深層的緣由:“最初的男性是突變的產物、非常態之物,由疾病抑或太陽輻射撞擊引發的基因的某種損傷所致。如果說Y染色體是X染色體的劣質化與畸變,那么男人就是劣質化和畸變的女人。”[9]35既然決定男人性別的Y染色體是劣質化的女人性別的X染色體,那么男人優于女人的生物學上的依據也就根本不存在。
不僅如此,根據其長時間查閱的大量文獻與資料,戴維斯還發現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化之中,女性皆處于顯要的地位。女人接受著來自各方的贊美與膜拜,一種尊崇女性的傳統隨之形成,并四處流傳。“在古代世界的各地,流行著這樣一種傳統:女人掌握著自然的種種奧秘,她們是通向智慧和知識的唯一途徑,通過她們,世世代代的智慧和知識源源不斷地流淌涌出。女性神諭、女預言家、女祭司、西比爾的女巫、女通靈師等的高居首位,將這一傳統信念體現出來。”[9]39
最終,戴維斯依據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出結論說:“女人是一切文化的原創者及豐富寶藏,是初始文明的源頭。”[9]40大量的文獻與實物表明:“神話、傳奇以及傳統皆將裝飾性藝術的發明歸于女性,考古學與人類學證實這一做法正確無誤。與之相似,神話的研究也將音樂、歌唱、制陶、舞蹈的源頭追溯至遠古時代的女性。”[9]46
依照文明進化的理論邏輯,人類社會應該朝向更加開明、更加理性同時也更加人性化的方向發展,女人在歷史上曾經做出過巨大的貢獻,理應繼續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然而,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女人不僅沒有優于男人的社會地位,反而位居男人的地位之下。戴維斯認為,根本原因在于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野蠻化與叢林化。女性從第一性淪為第二性,源于歷史上人類的野蠻化過程。
文明的進化理應沿著理性與開明的路徑展開,可它時常會遵循另外一種法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社會的叢林化使男人在生存實踐中占得先機,體能上的優勢令女人退居其次。依靠強力,男人在各個領域進行征戰,全方位地獲取勝利,奪得盡可能多的社會空間,占據絕對的優勢地位,并編造男性優越的神話,最終成功地運用父權制在實踐領域與精神領域實現了對女性的雙重統治。
男性的獲權憑借的不是智慧,而是強力,甚至是蠻力與暴力。這就是為何戴維斯說女人地位的淪落源于社會進化過程中的野蠻化與叢林化。事實上,盡管人自詡為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但他始終是動物,雖然是文明化的動物,其動物的屬性永遠無法從根本上加以改變,文明化只是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人的獸性,卻無法完全消除人的獸性。歸根到底,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遵循自然界的法則,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人從叢林里走出來,卻不時會重返叢林。
若論智慧,兩性之間應該不存在質的的差異。已有的差異應是兩性獲取的智慧顯現機遇的差異造成的。公平而言,女人的智慧并不在男人之下。不僅在生命活動中,在《圣經》中亞當夏娃偷食禁果的寓言換種角度解讀也可得出這種結論。原有的敘述是:在撒旦的誘惑下,夏娃吃了禁果,她又讓亞當食了禁果,犯下所謂原罪。然而,撒旦原名路西弗(Lucifer),是大天使之首,天界的啟明星、智慧的引領者,夏娃接受引導,先于亞當食用了智慧之果,隨后她將智慧之果給了亞當。由此可以看出,女人的智慧的獲取先于男人,女人是男人的引領者與啟蒙者。
五
女人淪為第二性,是歷史上業已存在的事實。女權主義多年來一直為之奮斗的,即是如何改變女人所處的第二性的悲慘境地,全面獲得應有的權利。關于這一淪落,曾有多種不同的解釋。男權社會將此淪落視為歷史發展的必然,女權主義者則采取了與男權社會全然不同的立場,但她們之間彼此也有差異。
與女人的淪落源于文明的野蠻化與叢林化的主張不同,法蘭西最為知名的女權主義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引入了另一種解釋視角,她認為,女人的本質由選擇決定,女人的性別,尤其是其社會性別,當由其自主意志與存在境遇塑造。父權制以降加諸于女人的政治、經濟、文化、習俗、觀念等種種社會束縛,使女人只能在其限定的范圍內進行選擇,無法單獨成就偉業。假如能清除所有這些束縛,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進行選擇,其潛質必能得以釋放,她們定將擁有全然不同的性別身份與命運。當前女性表現出的形象,完全是男人將其主權強加給女人的一種結果。掙脫諸種束縛是女性解放的必由之路。
言及性別的本質,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被譽為“女性的《圣經》”的《第二性》中明確指出:“女人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經濟上,沒有任何命運能決定女性在人類社會中的形象。決定這種介于男性與閹人之間的、所謂具有女性氣質的,是整個文明。”[10]309她認為,所謂的“女人特質”“女人的被動性”“女人化特征”與生物學事實根本無關;與之相關的是規訓女人的文明,文明按其所需通過規訓,讓女人具有了所謂女性應有的屬性,并令其位居男人之下。簡言之,將女性貶為第二性,是體現男權制文明的規訓者與男權社會強加給女人的命運。
為了讓女人心悅誠服地接受男權社會安排的命運,男權制社會還通過其刻意的構造,制造合理性證據,以期完成“一種統治的社會關系的軀體化”[11]28。關于這一點,皮埃爾·布爾迪厄曾做過透徹的說明:“男女身體及其用途與功能在生物學再生產方面的任意構造,使性別勞動的劃分和勞動的性別劃分這一男性中心觀念顯得十分自然,并由此使整個宇宙也具有這種特點。”[11]27-28他指出,如此做派是要達成從身體上到精神上對女性進行雙重奴役的目的。
與男人相比,女人在近現代社會中取得的成績確實不那么光彩奪目。然而,男人在社會多重領域中取得的豐功偉績,亦不足以成為他們優于女人的充分證據。女人所取成就較少,決非因女人低能,實乃因為男權社會對其實施了社會性剝奪,未予其釋放能量的天地,將其變為了附庸,故造成今日之局面。“使女人注定成為附庸的禍根在于她沒有可能做任何事這一事實;所以她才通過自戀、愛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勞地追求她的真實存在(Being)。”[10]771而一旦時機允許,“當她成為生產性的、主動的人時,她會重新獲得超越性……”[10]771-772換言之,女人即能以嶄新的風貌佇立在世界的舞臺上。
女權主義運動的核心要義在于,重新獲取原本女性自己的公平正義,討回屬于她們的天賦人權,像男人一樣自由、獨立,擁有尊嚴,能夠自主地選擇自己的命運。文學、藝術的本質體現為自由與創造,其對自由與創造、對人的權利、人的尊嚴的維護,既為男人帶來生命價值的啟示,也為女人開啟心智、創造未來提供了路徑。“藝術、文學和哲學,是試圖以人的自由、以創造者個人的自由,去重建這個世界……教育和習俗強加給女人的種種束縛,正是限制著她對世界的把握……女人首先要痛苦地、驕傲地開始她在超越方面——即在自由方面的實習。”[10]805-806
從原初的意義上說,性別原本并無優劣,也無第一性與第二性的等級之分。只是由于歷史進化的某種起因,男性顯現出優勢,繼而獲得主導地位,并一直試圖維持這種地位。在文學藝術的世界中,我們憑直觀得到的印象是,女性少有原創性,其成就多體現于表演藝術領域,原創藝術家多為男性。然而,此一表面現象遮蔽了另一種真實:男權社會的諸種清規戒律,壓抑、限制女性的原創力展示的地界,同時將表演藝術領域向女性開放,進而造就了大量的女性表演藝人。然而,一些女性不甘于此,她們頑強地展現自己的原創力,并成為與男性齊肩的杰出藝術家,薩福、紫式部、弗吉尼亞·伍爾芙、艾米麗·狄金森、伊莎朵拉·鄧肯皆為其中的佼佼者。自諾貝爾文學獎頒發以降,加上2009年得獎的赫塔·米勒,諾貝爾文學獎女性得主已有十幾位之多。
女性的原創力其實并不低于男性,只是女人常止步于幕后,人們不知真相而產生男人更具原創性的錯覺。世人皆知創立著名的戲劇表演體系的布萊希特才華橫溢,卻不知他的劇作的靈感與構思大部分來自他的女性伴侶伊麗莎白·霍普特曼、瑪格麗特·斯德芬等人;人們都知道古代希臘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演講舉世聞名,卻鮮有人知道其大部分演講稿的撰寫者是其美艷而聰穎過人的情人阿斯帕西婭。據稱,不僅伯里克利是阿斯帕西婭的學生,西方最為著名的古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也是阿斯帕西婭的學生。而且,她不僅是二人在學識方面的導師,更是他們在研習愛之藝術方面的卓越導師。
假如讓女人從后臺走上前臺,在享有與男人同等權利的人生舞臺上一顯身手,歷史將會被重寫。女人可以向世人宣示,她們在各個領域中取得的輝煌成就,可以在人類新紀元建立起她們的不朽功勛。
[1][美]瑪格麗特·米德.三個原始部落的的性別與氣質[M].宋踐,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美]約翰·莫尼,H·穆薩弗.性學總覽[C].王映橋,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3][美]愛德華·O·威爾遜.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M].毛盛賢,等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
[4][德]歌德.浮士德[M].綠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5][英]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第9卷[M].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6][日]渡邊淳一.男人這東西[M].陸求實,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7]馬曉年.性的學習[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
[8]Carl G J,von Franz M L.Man and His Symbols[M].Dell Publishing,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September,1968.
[9]Elizabeth Gould Davis.The First Sex[M].Penguin Books Inc.,Baltimore,Maryland,1973.
[10][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11][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男性統治[M].劉暉,譯.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劉海燕)
The Evolution of World of Sex
ZHANG Yue
(Literature Schoo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The evolution of sex is always penetrated by power,which molds the so-calle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ender and the hierarchy of sex.One sex becomes dominant,while the other reduces to a subordinate ow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sex characteristics.Are sex characteristics the natural manifestation of biologic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r the produc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Most of male scholars tend to hold fast biological determinism,whereas the woman scholars adhere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vism.By selecting M.Mead,Simone de Beauvoir,E.G.Davis and E.O.Wilson,Junichi Watanabe,John Money,P.Bourdieu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parties,the text intends to demonstrate their ideas,propositions and the evidences they render,and points out as the third party that sex contains differences without good points and bad points,the oppressive sex hierarchy is irrelevant to sex differentials,but relevant to the power mechanism.Both man and woman have been demonstrating their existential values,necessary functions and the indispensable significance in the course of evolution.
sex differentials;evolution;biological determinism;cultural construction;patriarchic society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1.013
F016;H0-05
A
1008-3715(2015)01-0061-09
2014-12-20
張月(1959—),男,河南開封人,社會學博士,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藝術學、文藝學學科帶頭人,研究方向:藝術社會學,組織社會學,并從事西方經典作品和人文思想的翻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