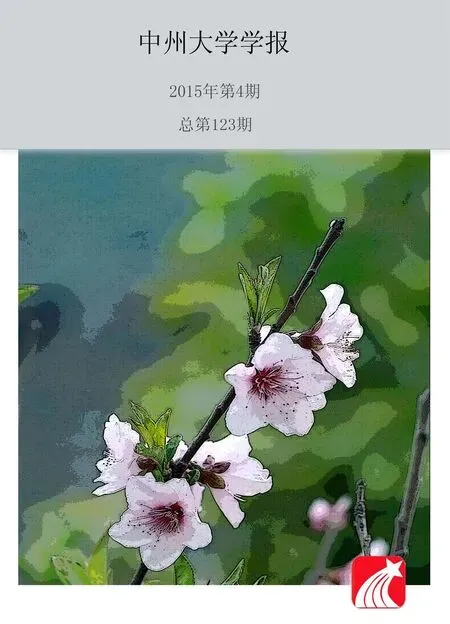城市與自然 ——論卡爾維諾作品中的建設性后現代生態觀
城市與自然
——論卡爾維諾作品中的建設性后現代生態觀
岳芬
(蘇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蘇州215021)

摘要:伊塔洛·卡爾維諾的作品以生動的形式展現了人類從現代走向后現代的精神歷程。在他的小說中,城市既是重要的元素和組成部分,也承載了作家的精神旨歸。卡爾維諾對城市以及居住于城市中的人的描繪,在思想上為新的文學批評范式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卡爾維諾的作品是對后現代哲學思想的一次生動闡述,他作品中的城市意象包涵了豐富的建設性后現代生態思想。
關鍵詞:伊塔洛·卡爾維諾;建設性后現代生態觀;城市;自然
收稿日期:2015-05-24
作者簡介:岳芬(1983—),女,山西太谷人,蘇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文藝學跨文化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4.019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715(2015)04-0087-05
Abstract:Italo Calvin’s works lively shows the spirit course of human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In his novel, city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and elements, but also carries the writer’s spiritual orientation. Calvino’s depiction of cities and people who live in the city, provid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new literary criticism paradigm in thought. The works of Calvino vividly elaborate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city image is full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ecological thought.
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是意大利當代文學史上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他在文學語言、小說結構以及作品思想等方面開創了“獨特的后現代風格”[1]。他向世人展現了他的洞察力和寬廣的視野。他的作品以生動的形式展現了人類從現代走向后現代的精神歷程,他用令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手段建造了一個與現實息息相關、又超越于現實之上的完美世界。在這個獨特的奇幻世界中,城市既是重要的元素和組成部分,也是承載卡爾維諾思想和精神旨歸的所在。
卡爾維諾對城市以及居住于城市中的人的描繪,在思想上為新的文學批評范式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他試圖在后現代精神中尋找某種解決的可能。他的思考同后現代哲學家大衛·格里芬等人的觀點不謀而合,在哲學層面,它們為卡爾維諾對城市的塑造和思考提供了佐證,并支持了卡爾維諾對未來的預見。在卡爾維諾看來,城市最終應當向精神生態復歸。城市實體及其存在的意義不應當高于自然精神之上,相反,城市的精神性存在才是現代都市文明的真正歸宿。同現代科技和理性相比,精神生態也是解決城市精神危機和生態危機的有效方式。
城市的自我消解為人類文明帶來的危機是深重的,卡爾維諾詳盡地描繪了這一危機。從遠古城市到現代都市,城市的外在規模不斷膨脹,內核卻在逐漸變得空虛、脆弱和萎縮。現代城市更像是一個個逐漸擴大即將爆炸的氣球,欲望幾乎要將其壓垮,城市居民也在不可自拔的沉淪中每天都過著惶恐的生活。向祖先存在方式的復歸,成為卡爾維諾小說塑造城市意象的基本方式,這一方式具有隱喻的性質和精神的內傾趨勢。
就像菲朵拉城那樣,現代都市的存在狀態原本包涵了多種可能性,但實際建成的城市卻都不是最理想的狀態:
“在每個時代里都有某些人,看著當時的菲朵拉,想象著如何把她改建成理想的城市,然而當它們制作理想城市的模型時,菲朵拉已經不再是從前的城市,而是那個直至昨日還是坑的未來城市,也就只能成為玻璃球里的一件玩具。”[2]31
一
卡爾維諾的作品趨向于后現代的思考模式,他甚至不斷地嘗試改變小說的敘事結構來配合思想和觀念的轉變,其目的在于為城市尋找一個最佳的存在狀態。他在祖先的城市中搜集到一些可行的經驗,為現代城市勾畫出回歸自然的路徑,他希望能夠建造一座擺脫沉重欲望的輕盈之城,如同一座蜃景之城。
在現代城市文明面前,卡爾維諾的思想顯得不合時宜,他幾乎否定了現代都市文明引以為豪的各種驕傲和成就。但是,在建設性后現代哲學那里,他的思想卻找到了知音。例如,大衛·格里芬等人在現代文明重構等方面提出了卓有見地的思想,這些觀念對于卡爾維諾在其作品中塑造的城市意象來說格外重要,他們為卡爾維諾作品中的城市提供了更多、更為合理的可能性空間。
卡爾維諾希望找到某種方式來解決城市的精神危機和生態危機。和一些現代城市社會學家不同[3],卡爾維諾將他的視野轉向“祖先之城”——祖先的生活方式為處在危機(尤其是精神危機)中的現代生活提供了借鑒。相應地,在現代生態批評理論中,回歸思想也是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觀念,它為理解卡爾維諾的生態理想提供了更多支持。
無論是古代城市還是現代城市,對回歸的追尋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記憶的復現,都會出現在每一個不經意的角落。它們對于城市的象征和意義體現在諸多方面,例如城郊的墓碑。這些無法被忘卻的遺跡,往往昭示著城市的過去,“一個旅行者,當他來到一座古希臘或古羅馬城市時,他首先見到的便是一排排的陵墓,和通往城市的大道兩旁的許多墓碑”[4]5。墓地顯示城市的過去,象征城市在歷史中逐漸改變自我的愿望,它曾經是城市對未來編織的夢想。但是,人類歷史卻不斷證明,城市的變化只是存在于形態上的擴大和規模上的機械疊加,在精神層面并沒有太大改變。歷史經驗被刻意忘記,并深藏在城市邊緣,有些甚至被當作垃圾一樣拋棄。
“城市就像一塊海綿,吸汲著這些不斷涌流的記憶的潮水,并且隨之膨脹著。對今日扎伊拉的描述,還應該包含扎伊拉的整個過去。然而,城市不會泄露自己的過去,只會把它像手紋一樣藏起來,它被寫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護欄、樓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線和旗桿上,每一道印記都是抓撓、鋸銼、刻鑿、猛擊留下的痕跡。”[2]9
城市寄托了太多的欲望,記憶隱匿于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欲望的城市”與“輕盈的城市”剛好是相互矛盾的對立面,欲望之城就像一個欲壑難平的胖子,沉重得連轉身都十分困難;輕盈之城卻不斷上升,擺脫一切不必要的重量,輕盈之城中的居民能夠充分認識自己,并獲得精神上的自足。
卡爾維諾渴望賦予城市以生動的形象和復雜的象征意義。在他看來,城市應當是一個流動的時間,而非固定不變的空間。城市的功能不應當僅僅服務于狹隘的目的,“古代城市在形成的時候,把人類社會生活的許多分散的機構集中在一起,并圈圍在城墻之內,促進它們的相互作用與融合過程”[4]579。城市應該服務于一個更大的宇宙共同體。而現代城市卻在嘗試各種形式和可能性來滿足欲望的滋生,在時間的流轉中不斷迷失。城市居民開始對現代城市生活感到厭倦,因為他們每天都要面對同樣模式、同樣時空的單調、刻板的生活,它仿佛是一個馬可·波羅式的樣板城[2]69-70,由它演變出的所有可能性最終又回歸于同一種形式。
現代城市正是這樣一種取消個性和傳統的潮流,席卷了地球的每一個角落,用理性的唯一標準統治每一個城市,將它們變得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只是機場和車站的名字。形式替代了風俗、地域和時空,抹殺了差別,現代城市是將城市居民的靈魂裝進貼了標簽、外表完全一樣的罐子里,他們被強迫發出同一種聲音、思考一樣的問題、經歷相同的生活。每一條街道、每一個社區都具有相似的功能,街道的名字只用于區分枯燥的地理位置,它們不再指示傳統、歷史和差異,也不再銘刻傳說和故事,根據名字,你無法判斷這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還是一座新興之城。“記憶中的形象一旦被詞語固定住,就給抹掉了。”[2]87
只有祖先之城能夠留住自然的烙印和歷史的記憶,它們將這些記憶刻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而不是記入塵封的史書。祖先之城始終為它的居民和來訪者提供精神和思想的指引。穿過大街小巷,陳舊的櫥窗、斑駁的路面以及生動的地名,都能夠引起觀賞者的思考。面對枯燥和煩悶的現代城市生活,尋求精神的棲息地已成為最高的理想,它遠遠超過人的本能欲望,就像梭羅那樣,更多的人愿意走向過去而非現代,甚至愿意走向荒野而非鬧市。“如果有人可以首先選擇,那么,寧可選擇精神的原始森林,而不是精神的荒原。”[5]28很多人愿意像梭羅那樣,從令人絕望的現代城市中分離出來,從異化中逃離。“現代人是分裂的、殘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敵對;馬克思稱之為‘異化’,弗洛伊德稱之為‘壓抑’,古老的和諧狀態喪失了,人們渴望新的完整。這就是我有意置放于故事中的思想—道德核心。”[6]94因此,在精神和觀念上,祖先之城為現代城市提供了參考。
二
現代人對個體精神完整性的追求同他們對現代城市逃離的動機相呼應。城市居民更愿意過柯希莫式的生活——靈魂能夠自由地在變化、激情和自然中徜徉,如同水城斯麥拉爾迪那的居民那樣:
在水城斯麥拉爾迪那,一張運河渠道網與街巷道路網相互交織著。從一處到另一處去,你總有陸路和水路可選擇。……于是,斯麥拉爾迪那的居民就省卻了每日行走相同路線的厭倦。不僅如此,行走的路線絕不只限于一個層面上,而是一路上有上上下下的臺階,有駐足的平底,有驢背式的羅鍋橋,還有架空的路。各段不同層面的路線組合變化,能使每個居民每天去同一地點時觀賞不同路線的景色。在斯麥拉爾迪那,最平常最寧靜的生活也不會千篇一律。[2]89
在卡爾維諾作品里的城市世界,斯麥拉爾迪那應當是祖先城市的代表,它永遠與單調和沉悶截然對立,它證明城市存在的復雜性及其意義。斯麥拉爾迪那的居民可以創造出無數種選擇,完全由其天性和喜好來決定。他們更適應自己的生活以及周邊環境,他們能夠更好地融入到整個生態系統中去。
祖先之城似乎更符合城市的定義,“城市就是一種使人類適應更大環境的機制”[6]53。準確地說,城市的目的應當是使其居民融入到完整的自然中去,而不應使其脫離自然,甚至與自然相對立。作為人類歷史選擇的永久棲息地,城市應當為居住者的精神提供保障,而不是讓居民時時感到緊張和壓抑。現代城市能夠阻擋那些可能來自于外部荒野的種種威脅,卻無法避免來自內部的惶恐。祖先的城市能夠讓居住者記住它的歷史以避免后來者重蹈覆轍,柯希莫們永遠不會走回頭路,因為他了解并銘記犯過的錯。
在卡爾維諾的小說里,城市兼具雙重品格,相比而言,他更贊賞《看不見的城市》里的那種祖先的生活方式。現代城市最終形成了連綿不斷的景觀,所有的城市全部連接在了一起,每一種活著或是死了的元素構成了城市的多重意象。但是,這些連綿的城市并沒有給自然帶來任何益處,相反,它們擠占了其他生物的空間,它們占據了整個世界。它們不再只是名稱和符號,而是負擔和壓力。卡爾維諾對現代城市的描繪總是在記憶與現實之間徘徊,他試圖證明記憶的價值和歷史的意義,并引起“關于現代城市的討論”[2]6。他喚起讀者對于潛意識深處某種記憶的咀嚼,或是刺激集體靈魂深處的某種思考。
回到祖先的居住方式是卡爾維諾的最大理想,他在“我們的祖先三部曲”中描繪了這種可能性。他甚至希望通過某種方式將現代城市轉回到某個可行的、固有的傳統中去,并讓城市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在他的作品中,集中了大多數人口的城市是對古老城市的延伸,它的理念和基本功能并沒有因為人口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而改變,相反,某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愿望卻被表現得更為明顯,甚至記憶本身就是回溯式的,“似乎是對一個古老城市的回憶”[2]6。卡爾維諾更愿意把現代城市描寫得如同森林那樣,而不是鋼筋混凝土和霓虹燈,他努力在現代城市中不斷尋找古代城市的遺跡,并不斷加深對現代城市的理解。
總之,卡爾維諾把回歸的意義植入城市意象之中。“現在看來,人們應當對于人類自己走過的歷史進行深刻的反思。存在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僅從數千年的有文字記載的人類發展史來看……在日益險惡的地球生態危機面前,如果我們繼續盲目樂觀、一意孤行,那簡直就是一種犯罪了。”[7]226卡爾維諾讓現代城市轉過頭來重新審視自己的過去,讓城市中的每一個居民認識到自身的困窘及其由來。他有意識地把城市的歷史和謬誤全都寫進小說里,讓它們在城市地下醞釀、發酵,并從廣場、街道、水溝、紀念碑以及每一處住宅的深處、那些不為人注意或是故意忘卻和拋棄的地方慢慢升騰,它們不斷滋長,逐漸替代原本籠罩在現代都市空氣中的塵埃和煙云,讓居住于城市中的生命內心體驗罪愆,并思考如何獲得心靈安寧的方式。
三
無論在敘述方式,還是作品的形式、結構等方面,卡爾維諾的寫作都應當被歸入到后現代范式中,他不僅超越了傳統小說寫作程式的窠臼,而且在觀念上也大膽地引入了豐富的后現代思想。
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卡爾維諾表達了與后現代哲學在觀念上的某種一致性,“馬可·波羅的回憶就像是對記憶的最初原型的回歸……”[2]8他希望能夠找到精神的救贖之路。卡爾維諾的思想同大衛·格里芬等“建設性后現代生態哲學家”[8]不謀而合。可以說,卡爾維諾的作品及其思想為格里芬等人的后現代生態觀提供了充分的證據。
在現代都市生活中,感性經驗完全被邊緣化,人的情感被掩蓋在鋼筋混凝土的輝煌之下,自我中心主義成為現代都市生活的思想主流,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在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未曾如此冷漠。為了解決現代文明面臨的精神危機和生態危機,以格里芬、小約翰·E·柯布等人為代表的建設性后現代哲學家提出一系列觀點——后現代精神觀。在他們看來,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和生態危機之間是密切聯系的,生態危機是人的精神走向崩潰邊緣的寫照,人類對自然的瘋狂攫取正是靈魂迷失、心靈扭曲以及思想荒蕪的表達。因而,建設性后現代哲學觀同宗教精神緊密相連,它是一種思想和觀念上的“返魅”或“復魅”。建設性后現代哲學家則在思想領域掀起了一股潮流,他們希望于精神層面獲得更多認同,他們的觀點對于精神生態的建構和人類精神的重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格里芬在他的《后現代精神》中借批評現代范式對后現代生態論存在觀進行了闡述,他強調人的存在與生態系統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重要意義:“生態論的觀點認為,個人彼此內在地聯系著,因而每個人都內在地由他與其他人的關系以及他所做出的反應所構成。”[9]214格里芬更愿意讓信眾明白人類的存在及其同周邊生物的關系是組成整個生態系統的基礎,人和自然并非是互不相干的。人類存在的目的是為生態系統提供更多元的關系,而非超越、甚至控制自然。并且,人本身也是由關系構成的,人類社會則是一個復雜的、相互影響又相互依賴的關系的共同體。這個體系不僅具有功能性意義,而且是構成整個世界的基礎,沒有哪一種存在物能夠超越這個體系之外單獨存在。那種“認為自己完全是獨立、自主的個體”[9]215的思想是同生態觀相違背的。
城市居民與整個生態環境的關系是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中所表達的重點,他向讀者灌輸一種觀念:每一個城市不只是一個觀念和符號,它并非單一的存在體,而是由無數種內在和外在的關系組成的、包括城市居民在內的、連綿的景觀。卡爾維諾小說中相互聯系的觀點,不僅為讀者開拓了思考的空間,也向讀者展示了其生態思想。
卡爾維諾不僅揭示了城市的現狀和精神問題,他還關注城市的未來和自我救贖之路。城市的無數種可能性反映了他對人類未來的期待。卡爾維諾的理想同格里芬在他的《和平與后現代范式》一文結尾表達的殷切希望如出一轍:
后現代思想成了后現代范式的基礎(就像笛卡爾、牛頓和其他人的實體思想成了現代范式的基礎那樣),未來幾代人將不會再把建立在強制力量基礎上的關系視作處理問題的‘自然的’和唯一的‘現實的’方法;他們將不會再把自然看作與我們疏遠的、其價值只在于作為我們的一種‘自然資源’的‘祛魅的’領域;他們真正的宗教動機不是去統治自然獲取物質利益;他們不再相信人的滿足感主要來自于金錢和用金錢買來的東西,不再認為經濟方面的考慮是我們公共生活中首屈一指的事情;他們不再把世界看作是由自主的原子構成的,因而不會設想用零打碎敲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不再認為個人或社區的利益可以脫離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而獲得;它們將會感到神滲透在所有事物之中,并為了整體的利益在各部分中發揮著作用;他們效仿神圣性的宗教動機,促使他們把合作性的勸服當成主要的工作方法,并自然而然地去尋找把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結合起來的方法。[9]217-218
格里芬的生態觀帶有神學的濃郁色彩,他試圖通過“復魅”的方式來誘導人們從現代主義的狂歡和欲望的無限膨脹中解脫出來,重新回到敬畏自然、熱愛自然的狀態中去。他反對自韋伯以來現代社會對“祛魅”的追逐,因為現代性的“祛魅”是對自然地位的削弱,并為人主宰世界提供合法性和理論保障,同時,“祛魅”也將人類對個體的追求推向巔峰,甚至否定作為自然整體一部分的人類應當承擔的生態責任。這也是大多數堅持城市生態觀的學者們的一致認識,“時至今日,我們還如此堅定地信奉19世紀工業技術的信念,以致不能完全感覺到它的反常和變態。我們中很少有人能正確估計礦業帶給每一活動領域的破壞性,它是反生命,反有機物的”[4]465。礦業是現代都市破壞生態系統完整性的手段之一,它象征了現代城市的破壞力。現代城市對“祛魅”的推崇是對作為生命體的自然的否定,和對工具理性的盲目樂觀。格里芬主張人不僅應當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且應該充分認識自身的價值和存在的地位。他的思想對于城市居民來說尤為重要,宗教信仰雖然不能夠完全替代理性和科學在現代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宗教情感卻是人類進入現代以來最為缺乏的精神要素。后現代哲學思想始終強調人的精神尤其是個人精神的實現,在社會整體發展的大背景下,個人的精神狀態和思想意識往往被忽略,甚至被拋棄,這種狀況在卡爾維諾對城市的描繪中屢屢出現。卡爾維諾寄希望于在生態觀中尋找某種救贖的方式,以實現城市精神的融通和城市的延續。很明顯,他在后現代生態哲學世界里找到了答案。
卡爾維諾對城市的理解符合建設性后現代生態思想,在他的作品里,生態精神成為現代城市的思想基礎,城市居民對城市以外世界的恐懼和懷疑都能夠在這樣的精神指引下走向緩和。在后現代哲學思想家看來,現代工具理性對自然的超越成為現代城市建立的基礎,也是促使現代城市走向精神荒漠的原因。卡爾維諾在描繪城市時,極力渲染了現代工具理性對城市居民靈魂的破壞力,現代都市對“祛魅”的癡迷,讓一切直覺體驗和感性經驗都失去了意義。城市居民對知覺的重新認識有助于現代城市的生態回歸,當城市重新融入自然時,柯希莫這樣的離經叛道者選擇的生活才會被人所接受。
四
卡爾維諾的作品是對后現代哲學思想的一次生動闡述,他的城市意象包涵了豐富的建設性后現代生態思想。尤其是在《煙云》《看不見的城市》等作品中,卡爾維諾從生態角度對城市進行了深度思考,他清楚地看到在反生態思想控制下,社會的虛偽和城市的精神危機。現代城市對自我的修正,實際上是人類對自身存在方式的救贖,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認識。建設性后現代生態觀為現代城市問題提供了最為切實可行的方案。城市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實體,它不僅要融入到整個社會之中,而且要融入到周邊環境之中。城市是構成自然的組成部分,每一個城市之所以應保留其獨特個性,正是緣于自然的變化和環境的相異性。因此,城市精神是符合生態系統的內在關系的集合體,是在自然與人兩者的長期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溝通的橋梁。
在后現代生態觀的影響下,卡爾維諾以極大的勇氣揭示了現代城市的全部陰暗,以及城市居民絕望的精神狀態。他對人性的理解要比象征主義時代更加透徹,也更深沉;他關注城市的未來,他對構建后現代生態城市充滿了激情。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卡爾維諾的作品中,隱藏著一座令人向往的生態的蜃景之城。
參考文獻:
[1][美]加布理爾·施瓦布.理論的旅行和全球化的力量[J].國榮,譯.文學評論,2000(2):141-147.
[2][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M].張密,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3][美]安東尼·奧羅姆,陳向明.城市的世界:對地點的比較分析和歷史分析[M].曾茂娟,任遠,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美]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M].宋峻嶺,倪文彥,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
[5][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現代文化[M].毛怡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6][意]伊塔洛·卡爾維諾.分成兩半的子爵[M].吳正儀,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7]魯樞元.文學的跨界研究:文學與生態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
[8]王治河.后現代主義辭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9][美]大衛·雷·格里芬.和平與后現代范式[C]//后現代精神.王成兵,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劉海燕)
City and Nature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Ecological View of Calvino’s Works
YUE Fen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Jiangsu 215021, China)
Key words:Italo Calvino;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ecological view; city;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