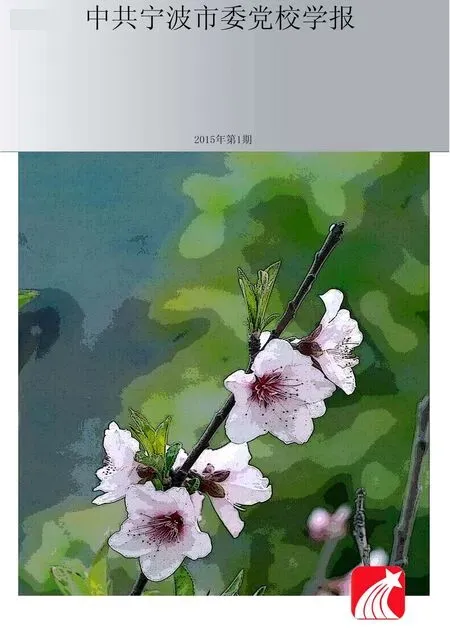展露解釋馬克思哲學存在論境域:重申對象性的活動原則
——關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釋義
張文喜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100872)
展露解釋馬克思哲學存在論境域:重申對象性的活動原則
——關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釋義
張文喜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100872)
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一直引發不少的熱議。在我們看來,馬克思是在《手稿》中表現出他的哲學獨創性的,在那里,他背離了德國古典哲學的規定,并且反對它們想象中的存在論—知識論的王國,直接為對象性的活動的存在意義獲得釋義學處境和方法論特征。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存在論;對象性的活動
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解讀方法一瞥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下稱《手稿》)這部書是有名的難讀,難度甚至還要超過《資本論》。用阿爾都塞的話說:“這部著作實際上是要用費爾巴哈的假唯物主義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顛倒’過來”,青年馬克思實際上“首先是康德和費希特派,然后是費爾巴哈派”。因此,“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離即將升起的太陽最遠的著作。”當然,這些德國古典哲學家的著作難讀也是出了名的。所以,根據這種觀點,《手稿》也難讀。像國內著名的康德、黑格爾專家研究一輩子康德、黑格爾,他們大多也只能“掠影”、“解讀”或“釋義”一下,很難將一個完整的康德、黑格爾從一個人腦子中完全傳送給另一個人。但是,像阿爾都塞這樣一個執迷于“認識論斷裂”的批評家,這個關于馬克思的評論顯然不怎么可靠:為了玩味《精神現象學》,馬克思確實不需要成為黑格爾派成員,或者說,但另一個事實同樣成立,即為了批判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馬克思確實不需要成為人道主義者。
下面我們要來看一看《手稿》的讀法,想必有跟別的經典著作有所不同的讀法,而關于這些讀法,版本也是五花八門。舉其要者,大概有這么幾種讀法。
一是,要一句一句理解、解釋一遍,馬克思這本書究竟有什么樣專門屬于它的財富,一句一句給弄弄清楚,用鄧曉芒的說法,就是“句讀”。到目前為止,對《手稿》進行句讀的作品,我還未曾見過。這種讀法的好處在于,不會漏掉你不懂的地方,一字一句讀,只要有時間,總是能夠搞懂這150多頁中文書的,但是我自己感覺這種一字一句的“句讀”沉悶無趣,似乎沒有什么目標。既不關心精神內涵,也不思慮啟迪心智,只是每讀一句話與精神錯亂地每三秒鐘嗅一下鞋油相類似,或者樂于拘泥于細節。不支持這種讀法的一個堅強理由是,你很難知道馬克思在寫《手稿》時的“初始經驗”是什么,因此也很難知道你是否在自己的腦子中正確地重新建構了它。你所擁有的是大量讀者對此著作的“讀法或體驗”,在這種情況下,你就面臨這樣的危險: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個《手稿》。現今的解釋學承認,現在我們已經無法得到像馬克思那樣哲學家的“初始經驗”,因此“初始經驗”不過就是不同讀者對它的閱讀的經驗總和。
二是,挑出一些難點、重點,做一些句讀的功夫,相對地采取大而化之的方式,因而在時間的運籌中,可以加入一些我們的思考,我們把此種讀書法看作是一種集體創作,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容易分散馬克思究竟是如何考慮他的主題的——比如說,在《手稿》中,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是非常有力的,黑格爾的問題在于,他雖然反對那種搞一個框架,并在同一個框架里,不斷地去裝別的東西,這個框架還是這個框架,它沒有任何變化,但是他的《精神現象學》用得正是上帝創造世界這樣一種基督教的框架,去篡改黑格爾自己寫《精神現象學》的初衷。也就是說,對黑格爾來說,我們看到的綠色的樹、紅色的花,陽光、空氣,一個運動操場有多少米,一個高個子有多少高等等,所有這些規定的東西都是邏各斯自己一步步發展演變出來的,黑格爾最開始并沒有用一個邏各斯的框架去把這些東西裝進去,但黑格爾為什么基本上不提這是他自己的看法。在《精神現象學》中為什么很少提人的名字,無論是國家、人名還是事件?黑格爾夸夸其談要把理性絕對化,又以最堂皇的理由解釋他的邏輯學碰巧跟上帝神交——這樣的借口只有他自己才會相信。馬克思揭示出,實際上這個世界的結構只是在他的主觀精神里,黑格爾就是從主觀精神建立起客觀精神、客觀理性的。馬克思稱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的表面上的誕生地是《邏輯學》,即神學。馬克思其實已經說得很客氣了。如果黑格爾——你就是從你自己、你的意識、自我意識和理性的歷史進程出發,你搞出一套體系,你卻說它是世界的結構,這跟占星術無疑差不多,而你又要讓所有人都相信,那么你憑什么要求人家相信?《邏輯學》中有一種怪異的自我陶醉,在它看來,對我們自己(自我)的所有說明都間接地說明了世界。這是一個錯誤。人們永遠不可能知道黑格爾究竟有多相信自己小心翼翼培育出的謬論,或者甚至無法理解這兒所說的“相信”究竟是什么意思。一方面,他說無中生有,從虛無中產生出存在,本來什么都沒有,但是最開始有一個存在,你也可以說每一次穿越中關村大街對你來說都是一次冒險,每一次穿越沒有被車撞,是上帝存在;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說是邏輯學里面的存在范疇、存在概念,有、是,這樣一個概念,就像傳說中的小妖精,它雖然還什么都不是,卻會不停地變化,一步步地搞出花樣翻新的事物來。所以,馬克思看到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暗中包含著唯心主義所發揮了的人的能動性的主體性。黑格爾的例子表明,那些看起來好像是對世界的關注,實際上卻是對關于世界的意識的關注,是對主體的關注;至于,黑格爾是否真的相信上帝,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信仰是否在他的理論體系里實現了某些事。所以,馬克思讀《精神現象學》就是要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過來,要求主觀精神和客觀基礎聯系起來。這是馬克思的方法論。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為我們解讀他的《手稿》提供了范例。
三是,介紹國內外學者講人生、講百家講壇式的方式。這種方式認為,思想是一種“心境指示”,也許在此種觀點中,人們可以心滿意足地避免原因、本質、本體、屬性、偶然等等這些形而上學的范疇。也許對中國學者而言,重要的是話語的力量或“姿態”,是像《手稿》中明確的要旨,而不是其光禿禿的邏輯結構。但是,有的人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說,你今天讀到《手稿》,但是別人說,有一本書比方說《存在與時間》你還沒有讀過,所以你的觀點還成立不起來,但是我究竟讀了哪些書才算成立了呢?這都是偶然的情況,你的經驗只不過是某些書的經驗,就好像你估計自己會胃疼的時候就真的胃疼了。如果要盡可能避免這種偶然性,就要依靠邏輯的方式。對我們來說,任何理論都是僵化固執的敵人。要堅持你自己的獨立思考,而不是訓導出來的思考。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從普通常識的立場看,我們在讀《手稿》的時候,每一句話你都要憑著更好地鑒賞復雜性和靈活性,也就是說,每一句話你都幾乎不能當有一個固定的意義,你不要把它教條化了。其實,就話語來說,馬克思的話你也不能死磕,你死磕了,那你可能就跑偏了。否則,除了簡單重復之外,你就很難知道如何描述話語背后的心靈活動。很顯然,《手稿》這兒的說法是由張力和極性組成的。換句話說,如果引用馬克思的說法,認為紙面上的詞句的發言權是有限的,那么這能夠將我們隔離在意識形態最邪惡的可能性之外。
四是,一個成功的解讀就在于產生一個成功的交流行為——比如說,理解黑格爾的邏輯學就要理解上帝就是邏輯,至于黑格爾憑什么能夠站在上帝的立場、神的立場來宣稱“絕對理性”,就在于他講的“理性”是“無人身的”(馬克思語)。上個星期五,上帝沒有迫使我打扮成一個教師的樣子,也沒有迫使我叫自己張文喜;但是無所不知的上帝知道,我會,我也能在腦海里很好地搭建起他的宇宙構架,同時,有上星期五張文喜的一些事情。在今天,它就以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形式出現的文化理論中,仍然流行著這種使身體客觀化的談論,仿佛這不是“我”自己的身體。不過,人類的身體確實還是一個物質客體,它是我們實現所有歷史創造的前提要素。身體使我容易受到剝削或歧視,同時它也是所有增進人類關系互動的可能性的基礎。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問題在于,黑格爾由于某種異化感將所有的客觀化等同起來。像這些問題都需要塞進解讀《手稿》當中來討論。有人認為,課堂討論的環節,這么多學生講得總有比老師講得有見地的地方。可是即使如此,很多人還是會認為,老師是一個心靈上的集權主義者,有時也是一個垃圾處理員。課堂討論盡管有意思,但通過課堂討論獲得真理同樣也僅僅是一種保證。你不要當真,你不要以為“我”說的就是真理了,就像你認為你說的就是真理了。我保證我說的是對的,但這還是僅僅是保證,我們還得走著瞧。盡管我和你都在閱讀《手稿》,但是我們的閱讀目標也都是在于“對話”,從中受益。
五是,說從作家本人的哲學觀點出發,結合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的方式。因而需要在解讀中加入許多材料。如此等等。我們覺得,經典著作究竟要怎么樣讀的問題常常被提及,但從來就沒有得到過滿意的解決。我們不妨承認,對于解讀《手稿》的基本需要,提及的這種那種讀法都行之有效,因為從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了人類對精神財富可能占有的方式,以及無論這種那種讀法是多么有所欠缺,它們都可能各得其所。知道這一點就夠了。
二、依對象性活動原則解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結構
大體說來,《手稿》的論述比較繁復,加之它本身并沒有最后完成,對一個不是精通經濟學哲學的人來說,要把其中主要論點提綱挈領地敘述出來,未免有些困難。但是《手稿》的內容還是非常明確和集中的。它的主線是貫徹“對象性活動”的原則,而這種貫徹如同百川歸海那樣,指向存在論問題的優先地位。無論是馬克思的追隨者還是他的反對者,都心服口服地承認《手稿》它是一部開啟存在論新的境域的作品。此外,我們應該對《手稿》幾部分內容有很好的理解。我把我在上述講述中所要指出的總問題概括為:勞動問題。大體上講,馬克思嘗試從兩個角度展示異化勞動產生、發展和結束的歷史道路。指明,勞動究竟為什么是人在一個不屬于他的世界里的自我異化。我們可以很適宜地分出三個分問題,這三個分問題決定了《手稿》的根本內容,我們可以稱之為人的本質的哲學規定,異化勞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再沒有像異化勞動存在的共產主義學說。這一點是明擺的。
第一,馬克思的這部著作是“問題的時代”之中問題感很強的著作。每一個翻閱它的每一頁文字中,讀者都可以感覺到,這個資本主宰的社會從根上就有毛病。可以很確定地說,這里,只有當你問“哪一條根?”時,你才開始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存在論立場。大家知道,在寫作《手稿》之前,馬克思打算寫一部法哲學著作。原本像康德的《法學的形而上學的基本原理》那樣搞出一部他自己的“法的形而上學”著作。他自己的設想是,在法哲學的第一部分的“法的形而上學”中,搞出一套類似于費希特那樣脫離法的實際的形式的原則、思維、定義等等,但是,很明顯的一點是,這也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基本特征。它的起源在柏拉圖主義,它最充分的表達則是在現代技術的本質中。在現實面前,馬克思深刻感到不能淪落到與費希特為伍的地步,他隱隱感到沒有深入經濟學領域,他根本不可能把青年時期的浪漫色彩的理想主義貫徹到法哲學研究當中,他所做的至多是在模仿脫離實際的費希特的那一套而已。
顯然,說這些話的并不是我們,而是馬克思自己。在他幾個月之前動筆,之后又放棄寫作法哲學巨著。他會告訴我們,作為費希特《知識學》的“自我”喚醒如法國革命般的實現變革的行動是無稽之談,因為變革從未發生過。目前馬克思自己的任務是打敗先驗主義。他認為,一個天賦過人的作家,不應該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以上,唯一的工作就是“全憑空想編造、現有的東西和應有的東西之間完全對立。”馬克思在思想魅力方面之所以更加迷人,是因為現實感的影響勢必會擴大。1843年12月,海因里希·海涅在巴黎認識了馬克思,他被馬克思迷住了,他也像1841年時的莫澤斯·赫斯那樣成為馬克思的“粉絲”。赫斯這樣說:“馬克思博士,我的偶像就叫這個名字,還是一個十分年輕的男子……他將最尖刻的幽默與最深刻哲學的嚴肅聯系在一起;”盧梭、伏爾泰、霍爾巴哈、萊辛、海涅和黑格爾這些頭腦加在一塊,這就是馬克思。弗·科本在1841年給23歲馬克思的信中,更把馬克思描述為“思想的倉庫和制造廠”或“思想的牛首。”這些贊揚都表明馬克思不僅僅博覽群書,每年讀的書若一頁一頁鋪開,我估計能夠鋪幾里地。而且,馬克思是對當時歐洲人的精神危機特別有感覺的人。
對一般人來說,年輕的馬克思只不過抓住康德、費希特哲學這個或那個的軟肋,揭露它,把它拖拽到理性的光天化日之下,送到哲學史的審判庭,一切就萬事大吉了,這畢竟就是一般人理解。這也是錯覺。之所以有這樣的錯覺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馬克思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新問題,它不是在西方形而上學內部提出,而是針對這個形而上學本身。馬克思也從來沒有幻想過僅靠割掉小膿包就能根治西方精神毛病。而且,正如馬克思本人的行動所表明,他毅然決然地把自己寫滿三百印張的法哲學巨著“處決”了。后來,為了尋找思想的出路,馬克思又把自己投身到文學藝術之中,馬克思也創作了不少作品,但同樣當他發現作家的文學人格同其個人性格非常矛盾時,他就果斷地燒掉了自己的詩歌和小說文稿。文學創作所帶來的煩惱,以及搞法的形而上學體系的困難,都促使馬克思回心轉意“渴望專攻哲學”。因為在馬克思看來“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也許可以說,從1841年3月完成題為《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的博士論文到1844年春夏完成的《手稿》,馬克思的思想似乎繞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點。從許多方面看,《手稿》回歸到了最初的風格和哲學理想。但是,這已經完全不是康德—費希特—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那一套了。任何人只要認真閱讀過《手稿》都會有這種感覺。
第二,就“存在論”一詞所蘊含的一般意義來看,馬克思也并不是傳統西方存在論的擁躉。不過,他的立場卻需要好好界定一番。不管馬克思會被認為是哪一類哲學家,他都不能算是為了拯救什么“絕對知識”而寫作的人。他不是心里似乎已經知道“存在是什么”,又頭頭是道熱衷于討論“某某東西是否存在?”“我們如何證明它們的客觀存在?”的癡人,更不會簡單地認為如果對一些哲學內部的規章制度加以改進和糾正,再廢除一些“是否有身體存在”之類的反常問題,哲學世界就會變得完美無缺的真理福地。
在這里,有必要把他跟德國古典哲學家做一點比較。德國古典哲學對我們今天學習《手稿》來說很重要,有很多東西都可以相通。從康德—費希特—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德國古典哲學來說,按照馬克思,這些人里面,算黑格爾哲學最集大成。就是認為“他能把哲學的各個環節加以總括,并且把自己的哲學描述成這種哲學。其他哲學家做過的事情……黑格爾則認為是哲學所做的事情。”隨著黑格爾的出現,哲學的傳統也就因此走到頭了。就像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最明確地宣布的那樣,在哲學討論的,正是一種哲學的終結。黑格爾說:“真理就是所有的參加者都為之酩酊大醉的一席豪飲,而因為每個參加豪飲者離開酒席就立即陷于瓦解。”原來真理就是酗酒后的踉踉蹌蹌,在真理的酒席上,大家都酩酊大醉,都互相滲透,不分彼此,不論什么身份,也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醫生、保險公司推銷員、公務員、歌劇男高音,大家既然來了,就得一醉方休,大家融化在一種一團和氣的氣氛中。一旦每一個人一離開酒席,真理就沒有了。大家都參與的時候才是真理,這個整體就是最后的真理。只有在喝醉的時候才能做到。但是,在大家清醒的時候,就要分出彼此,誰是主賓,誰是陪同。所以,當時德國從來沒有過這么多閑適的社交聚會,在柏林,俱樂部、協會、聚餐和小型舞會,突然冒了出來。黑格爾也時不時參與這類活動。但是,聚會本身牽涉到主體相互之間確認,他們想確認自己站在堅實的地面上。這種大家不分彼此的酩酊大醉,能在黑格爾的課堂上很好地顯現,所以,各色人等,都蜂擁而至,聆聽黑格爾的講演。盡管大家不一定聽懂黑格爾的思想,但黑格爾給人一種能夠領會一切的感覺,而且也許他真的起到了改變輿論的作用。不過,現有與應有的矛盾,讓馬克思看透現有哲學的形式下那些不可能得到改變的現實,這是黑格爾望塵莫及的。
1840年代的馬克思做的最根本性的大事便是從黑格爾那里解放出來。如果是這樣的話,存在論原理就得改寫為:存在決定意識。但什么是這個——存在?我們知道,從康德到黑格爾這條路線是按照對“人”的“精神世界”、“理性世界”的理解一路走來的。其突出的特點是,自我意識地表達存在。具體地說,“人”已經將自己的“自然”方面“擱置”起來了。這是一個理解意識決定存在這一原理的前提。當人將自己的“自然”方面暫時“擱置”起來再來看“精神世界”,或作為“理性”的“人”,它的“世界”和“能動性”問題就不一樣了。因為重要性的問題不再是吃喝住穿這些物質生活問題,毋寧說這些方面不重要,才可以理解人將自己的“自然”方面擱置起來,才可以理解歷史和自然之生命過程的能動性,只有人們以自我的方式思考真理整體才能領會,才可以理解人之為了理想而“殺身成仁”的問題。
但問題是,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態度從根本上來說絲毫不具有革命性。沒有跡象表明,他們希望推翻現有秩序,也沒有跡象表明他們相信如果推翻現有秩序的話,社會將發生重大轉變。實際上,他們的哲學目標根本不是社會,而是所謂“人性”。很難在他們的書里找出哪一段來清楚表明,經濟制度作為一種制度是錯誤的。例如,黑格爾關于勞動是人的本質的說法,不過是說人在他的環境中很少找到直接對他有用的原料。他唯一只有通過勞動才能獲得滿足自己需要的手段。以這樣的基礎形成的經濟體系,就像星球體系形成一樣,存在著一定的規律。政治經濟學,黑格爾把它叫做“國家經濟學”,這種叫法就已經告訴我們,黑格爾不可能對私有財產制度發表攻擊性言論。黑格爾還說:“文化的開端”,就是“人們剛開始爭取擺脫實質生活的直接性的時候。”更確切地說來,對于德國古典哲學來說:存在并非其他,根本就是自由之態。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認為,黑格爾哲學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之間有一些共同點。最突出的一點是,黑格爾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現代國民經濟學家也把勞動和資本的結合看成人間天堂。黑格爾比國民經濟學家更加深刻。他的自我意識哲學給資本主義世界原理涂抹上了幾絲圣輝,幾絲能夠足以贏得國民經濟學家滿腔同情的圣輝。而且在某些方面更加強調勞動的積極方面。在這個意義上,懂得黑格爾哲學才能理解國民經濟學的前提和出發點。原因也是因為,黑格爾哲學對國民經濟學的前提和出發點表示哲學方面的支持。當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你可以為你自己在讀黑格爾著作時得出與馬克思相近的這個結論,而且你確實可以從黑格爾哲學的全部作品中得出他的自我意識哲學的確有些替資本主義世界說話的意味。
但是馬克思并沒有作此結論。如果說黑格爾哲學有立場的話,這立場則是擁護資本主義的,因為它的道德訓誡就是,勞動是有積極意義的,工人應該勞動,而不是說工人應該反叛資本家。讀者能從馬克思《手稿》中吸取的黑格爾的社會批評也就是這些了。從社會批評的角度來看,《手稿》中不斷出現的是“忌妒心”、“貪財欲”、“工業的太監”、“誘騙”、“墮落”、“腐化”這樣一些表征資本主義社會的詞匯,這些詞匯像一根絲線一樣貫穿于馬克思的這部著作中。可以看見,在資本主義社會成天拿著金錢送人的“有錢的好人”是不敢想像的。從亞當·斯密開始,對樂善好施的現象就排除在經濟領域而轉移到倫理領域。而馬克思則不會認為個人的仁慈能夠成為包治社會病的良藥。這個變化意義重大。它是觸及到存在論的真正的問題。因此,什么是這個——存在?在馬克思那里,這個——存在,決不是擱置自然“精神—自由”的問題,這個——存在,是與自然進行物質代謝的人,這是勞動著的并通過勞動而社會化的人,人在勞動中表明他的本質力量,創造自身和社會。
第三,“對象性的活動”提示馬克思哲學的存在論根基。在《手稿》有“對象性的活動”這一提法。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基本存在論概念使用如下這樣一些詞匯:“人”、“對象性”、“感性活動”、“感性意識”、“異化”、“勞動”、“實踐”、“自然”、“歷史”、“社會”。這些概念只是《手稿》的一部分詞匯而已。它們會把人們直接送入德國古典哲學的境界當中。沒有這些舊詞匯,傳統這部機器就轉不動。比如,費爾巴哈常常用“感性”概念。它是與“理性”相對立的。也就是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相互對立。對于費爾巴哈來說,感性直接提示著實在性。也就是說,實在性就是感性。費爾巴哈的第一原則就是“感性”原則。譬如,他稱呼身體的感官為“絕對的器官”,“人與人——‘我’和‘你’的統一是上帝。”
所以,要對馬克思的“對象性的活動”這一提法作出說明常常是同德國古典哲學聯系起來,其要旨在于質疑作為自我意識的活動和主體的起源。在這么一種關聯中,在馬克思之前,所謂“活動”充其量只是理性的目的論的一個主題,一個哲學和內在性問題的主題。黑格爾說,自笛卡爾開始,“哲學的原則是從自身出發的思維,是內在性”,“按照這個內在性原則,思維,獨立的思維,最內在的東西,最純粹的內在頂峰,就是現在自覺地提出的這種內在性。”或者說在傳統哲學中,首先要確立一個主體,它是一個對象性的、固定的基礎。然后,這個固定的主體現在變成進行認知的自我本身,是各種賓詞或范疇的聯結活動。而在馬克思那里,人們再也無法從此種“活動”中取得什么?而之所以無法,是因為德國古典哲學家給出了結論,但是尚未澄清前提。他們的結論是,“一切都處在運動中,活動著。”費希特會說:“我們想到這點,但更多的是:我們在自身的活力中感覺這點。世界以一種行動開始,要是我們說出自我,一種行動也開始。”“我創造作為我的自我。因而我是”。不過,這種創造是如何進行的?我們簡單用黑格爾的兩句話來講: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爾的這兩句話其實是一句話。只不過有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一切符合道理的事情都會成為現實的;另一方面,一切現實的東西都可以從道理上去理解它,它的存在,是有一定理由的,并不僅僅是為現存事物“辯護”的意思。
當時的教育部長阿爾滕施泰因以這樣的話對黑格爾表示祝賀:“您賦予……哲學……對于現實的惟一正確的立場,您肯定會成功,保護您的聽眾不受有害的自負的損傷,這種自負鄙棄未被認知的現存事物,尤其在涉及國家方面,它喜歡以任意提出內容空虛的理念來賣弄自己。”這樣的主體是一個現實的創立活動的概念。它成了最重要的哲學主題。
事情會愈來愈清楚,對于德國古典哲學來說,誰要想成為一個哲學家,誰就要了解構成知識的科學體系。近代以來,哲學特別著重探討自我意識的精神是什么,作為認知它是什么。這個“是什么”也就是關于它自己的存在的問題,從亞里士多德以降,存在是什么?一直到近代,哲學主要探討是存在論,存在論是一種知識。自我意識的精神特別繼承了這樣一個存在論的話題。弗·施萊格爾甚至把費希特的知識學和法國大革命、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相提并論,稱之為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三大成就。
我們一定知道馬克思在哲學中所做的革新,以及對傳統哲學知識論所持的批判態度。馬克思無疑不會在知識論或自我意識或德國古典哲學的主體概念的意義上建立和發展他自己的對象性活動的哲學學說;與現實的創立活動相比,康德的“純粹活動”、費希特的“活動本身”、謝林的“無限活動”和黑格爾的“自我活動”在哲學事業上添加的不僅僅是一種危險,而且是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馬克思認為,這些都是“在純粹的思想領域中發生的”。
這個說法很有說服力,情況也的確是這樣的。舉例來說,在耶拿有一個關于費希特“有活力的自我”的傳說:費希特如何在學校的課堂上要求學生,目視對面的墻壁,同學們,請思考墻壁,費希特說,然后請思考自身,作為與墻壁相異者。“人們嘲笑地為那些有抱負的大學生感到惋惜,什么也發覺不了,因為他們想不起本己之我。但是,費希特想以他的墻壁例子,讓通常的意識從它那自我的僵化和自我的物化中得到解脫,因為,他習慣于這么說,人更容易受到誘導,自視為月亮上的一塊熔巖,而非一個活生生的自我。”費希特認為,不對!主體,那個活動的進行辨識的自我,是建立基礎的事物。不存在任何超越這個自我之絕對論的事物,但一切都要進入這個絕對論。席勒和歌德針對費希特開起玩笑。費希特和大學生組織發生了一次爭執,大學生半夜砸他的窗戶,歌德給他的大臣同事寫道:“您見到了這個絕對的自我身處巨大的窘境,東西當然從那些被人設定的非我那里,極不禮貌地穿越了玻璃。”在后來歌德給霍芬的一封信里稱費希特是“康德之后本世紀最偉大的思辨性哲人:世界對他僅僅是個球。自我將它扔出,又在反思時將它重新接住。”
另外,說到對象性原則應當提到一個人,這就是費爾巴哈。1839年時的費爾巴哈在其《黑格爾哲學批判》中寫道,人的具體的、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必須也在哲學中肯定為思維的基礎。過了兩年,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中主張,上帝觀念乃是人的自我意識的異化形態,因而作為人關于自己的真實的自我的表象投射在虛構的天國的結果。這些說法依然很有說服力。但是認為馬克思對費爾巴哈這個觀念有過度依賴,這純粹是學院化或公式化了的馬克思哲學研究的想像。恰恰相反,馬克思只有無情地譏諷費爾巴哈用感性的整體來克服黑格爾的純粹思維,才能真正創立“對象性活動”原則。不管怎么說,馬克思都是以一種共產主義社會發言人的身份來提出這一原則的。
三、結語
馬克思所處的時代不僅跟我們這個時代相通,而且像黑格爾這樣的偶像級哲學家,很好地扮演了時代的兒子的角色。我們這個時代一方面表現為滿足于鞏固歷來的定在和表象,我們不知疲倦地倡導已經被定住了的那樣一些存在方式比方說尊重科學、尊重傳統道德觀念,這是屬于去“接受”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更注重去創新、去“給予”,去給科學知識立下法規。所以這本書也被一個概念所支配,即創造。所謂創造就是在某些原始的虛無中撕裂出一個傷口。本來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東西,因此要創造就必然要損害那種純粹。馬克思《手稿》對“對象性活動”原則的擁護,或者其對“創造”或“給予”的專心追求,也是繼承了德國古典哲學精神。如果我們摒棄“對象性活動”之傳統意義上所謂的概念性質,那么,《手稿》的核心問題就是勞動與異化勞動的對應。
[注釋]
責任編輯:朱明
B0-0
A
1008-4479(2015)01-0010-07
2014-09-28
張文喜(1961-),浙江東陽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