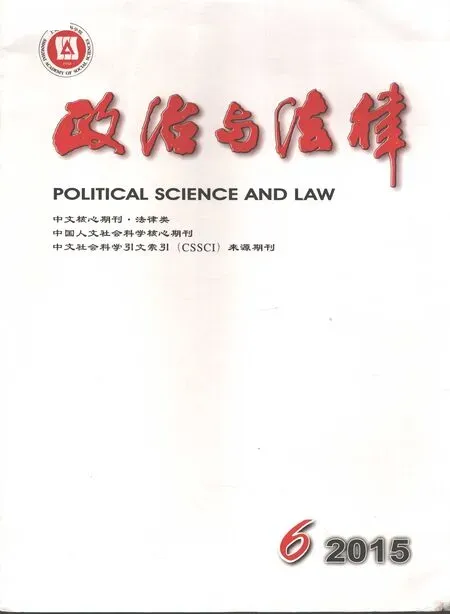法益過度精神化的批判與反思——以安全感法益化為中心
劉 烔
(廈門大學法學院,福建廈門361005)
一、風險社會下的法益精神化
無論是在何種社會背景之下,刑法的核心使命始終是法益保護。法益保護是刑法運作的目標驅動,也是刑法介入的判斷標準。但作為刑法根基的“法益”,其概念本身并不清晰,具有多重含義。關于法益概念的學說也聚訟不止,“利益說”、“價值說”、“狀態說”等各自為營,但究其主要分歧,則在于是否承認法益概念精神化的問題。①陳家林:《析我國刑法的基本立場》,《現代法學》2008年第3 期。正如臺灣刑法學者陳樸生指出:“法益概念之內容,從其發展過程而言,始由物質化,進而精神化。”②舒洪水、張晶:《法益在現代刑法中的困境與發展——以德、日刑法的立法動態為視角》,《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7 期。德國刑法學者麥茲格甚至認為,精神化是法益概念自身的本質,“如果沒有精神化,就不可能利用法益概念”。③陳家林:《德國的不能犯理論及對我國的啟示》,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20 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39 頁。而是否接受法益精神化,則成為區分“法益侵害說”與“規范違反說”的試金石:要么接受法益精神化的概念,要么放棄法益侵害說。④王安異:《法益侵害還是規范違反》,載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第11 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 頁。通過對法益學術史的梳理,“不管是行為無價值論,抑或是結果無價值論,多數學者主張抽象的、精神化的法益概念”。⑤同上注,趙秉志書,第295 頁。法益從“具體”到“一般”,從“實物”到“觀念”,也成為法益精神化的重要表征,⑥但也有學者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這一觀點雖然應和了法益理論在德國理論界和實務界的某些遭遇,貌似賦予了法益順應社會發展的時代精神,實則無視法益的歷史發展及其具體內涵。參見楊萌:《德國刑法學中法益概念的內涵及其評價》,《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 期。這一趨勢在風險社會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風險社會下的刑事立法和解釋都已經遠遠突破了法益的物質化限制。盡管面臨種種指責與質疑,但仍然無法阻擋法益日益精神化、抽象化的趨勢。⑦同前注②,舒洪水、張晶文。“危險社會與刑事立法之間的對應關系,其中最令人注目的表現之一,就是法益觀念之抽象化問題。”⑧舒洪水:《危險犯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 頁。更有甚者指出,法益精神化擺脫了物質法益觀對風險刑法的羈絆,并且開拓性地將“普遍的社會安全價值觀”這一精神化的法益作為一個規范評價原理運用到風險刑法之中。⑨董澤史:《風險刑法理論來源之證實》,《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2年第3 期。而在具體的刑事立法技術上,有論者主張,風險刑法應當致力于保護更廣泛的利益,危險犯的存在范圍還應包括精神和社會秩序的損害性。⑩薛進展、王思維:《風險社會中危險犯的停止形態研究》,《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5 期。也有觀點主張通過增設社會恐慌類的危險犯的手段來防范風險和保障公共安全,將無形的精神性損害結果也納入到危險犯中來。?華關根、王媛媛、馮云:《論危險犯在我國刑事立法中的適度擴展》,《法學》2009年第5 期。既然風險社會下法益精神化趨勢在所難免,問題的關鍵便在于如何科學認識與正確把握“被精神化后”的法益概念。相對于“身體”、“健康”、“財產”等現實法益的“看得見、摸得著”,“名譽”、“信用”、“秩序”等精神法益的保護界限究竟如何劃分則更值得深思。因為,法益過度精神化可能會使法益概念喪失應有機能,可能導致基于政治的、倫理的考慮來界定法益,也可能導致刑法成為國家保護法。?參見韓瑞麗:《刑法法益的精神化傾向及其限定原則》,《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 期。
二、安全感是一種法益嗎
人們通常認為,“安全感是公眾(包括法人)通過客觀行為(包括語言的評價)表現出來的對一定時期和空間下的社會治安破壞力和制控力狀況的綜合主觀心理感受”。?林蔭茂:《公眾安全感及指標體系的建構》,《社會科學》2007年第7 期。但也有學者認為:“一般的安全感或信賴感是指社會成員感受到應該相互遵守的社會生活上的規范或規則被遵守。”?[日]伊東研祐:《現代社會中危險犯的新類型》,鄭軍男譯,載何鵬、李潔主編:《危險犯與危險概念》,吉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 頁。這實際上是把“事態發展的預測可能性或所依賴之社會系統發揮正當機能以一般的信賴利益之形式進行了法益化”。?同上注,伊東研祐書,第190 頁。與此相似,德國刑法理論中的“印象理論”也認為,如果將法益作精神化的理解,就應當承認國民對于法秩序的信賴感也是法益的內容。?陳家林:《德國的不能犯理論及對我國的啟示》,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20 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63 頁。社會系統基本規范或規則被遵守,是社會系統內部成員參與社會互動交往的重要前提,也符合社會成員基于法律系統的保障機能而產生的對法秩序的信賴與期待。這種信賴利益的主觀化描述,實則是規范的平穩運行狀態在心理層面上的反映。這種期待感也好,信賴感也好,其感受對象是社會規范本身。而這與通常意義上的安全感在感受對象上有顯著區別。真正值得刑法關注的安全感,其感受對象應當是可能被犯罪行為所破壞的社會治安情況。類似的說法如日語中的“體感治安”一詞。“體感治安的低下”通常意味著“不安感的增大”。如大谷實指出,體感治安乃指國民對于治安所抱持的一種想象或意識,特別是面臨大白天也會隨時遭到搶劫、電話詐騙隨地發生,難免會讓人加深犯罪恐懼感。再加上社區鄰里犯罪抑制功能的消失,并也反映出國民對于治安的不安。?參見[日]大谷實:《刑事政策講義》,弘文堂2009年版,第26-28 頁。同樣,其感受對象也是與犯罪現象相關的整體治安情勢。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學術領域中,對“安全感”詞義的表達,更多傾向于“犯罪恐懼感”(fear of crime),即在面對犯罪現象時所生之恐懼心理,害怕自己就是下一個受害者。由此可見,安全感的感受對象多指犯罪現象及其背后的社會治安狀況,這不僅僅是刑事法學學術研究所采之通行觀念,也是公共決策與警務工作中安全感的真正所指。
在當下,法益精神化在順應日益高漲的安全呼聲同時,也埋下了過度精神化的理論隱憂。其典型表現即在于主張將“安全感”納入到法益保護的范圍之內。筆者將其概括為“安全感法益化”。如有學者認為,風險社會下刑法的任務已由保護法益轉向保護國民的安全感。?齊文遠:《刑法應對社會風險之有所為與有所不為》,《法商研究》2011年第4 期。也有學者以我國刑法相關罪名為例(第219 條之一),主張在不侵犯個人自由的前提下,也有必要適當設立抽象危險犯以保護國民的安全感、信賴感。?呂英杰:《風險刑法的法益保護》,《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4 期。應當說,上述觀點在風險社會中不難覓得供其棲身的理論市場,?據介紹,當今對安全感(Innere Sicherheit)的研究,超越了“安全”本身,成為一個熱點話題。Vgl.Valentin Golbert, Innere Sicherheit in unterschiedlichen gesellschaftlichen konterxten,LIT Verlag,2003.轉引自陳金林:《積極一般預防理論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 頁。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保障社會安全的公共政策走向。因為,在風險社會中,不安全已經滲入到了人們生活的結構中,破壞了個人的生活,也破壞了自我價值和自尊,產生了讓人無法忍受的恐懼、焦慮、無望和無力(J·維爾語)。?王俊秀:《面對風險:公眾安全感研究》,《社會》2008年第4 期。因此,風險感知總是與不安相伴,風險景象亦總是與恐懼相聯。于是,“風險意識加劇了公眾的焦慮感和危機感,如何為個人的存在提供制度上的安全保障開始支配公共政策的走向,面對周圍世界如此多的挑戰與不確定性,不僅個人需要不斷地進行風險管理,現代國家也必須更多地以管理不安全性為目標”。?[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趙旭東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 頁。刑法當然也深受此目標之影響,但在此更值得追問的是,“安全感”本身是否可以作為一種法益?我們應當對“安全感”抱以何種態度?這也是風險社會下刑法面臨的新問題之一,需要學界予以深入研究。
三、對“安全感法益化”觀點的整體批判
一項生活利益應否受到刑法保護,能否上升為法益,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與標準。法益理論認為,界定法益概念的原則主要有:(1)必須與利益相關聯;(2)必須與法相關聯;(3)必須與可侵害性相關聯;(4)必須與人相關聯;(5)必須與憲法相關聯。?參見張明楷:《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7 頁。此外,法益還應具有刑事政策機能、違法性評價機能、解釋論機能、分類機能等。?同上注,張明楷書,第196-203 頁。其中,刑事政策機能對于安全感能否成為法益的判斷尤其重要。根據法益理論的基本原理,筆者認為,“安全感”不宜作為法益予以保護,安全感法益化的觀點并不可取,具體理由如下。
(一)不具有法益應有的機能
盡管利益有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之分,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都可能成為法益,尤其是精神利益。“法益概念進行抽象化、精神化理解,那么即使不存在現實、客觀的法益侵害或威脅,也可以動用刑罰。這意味著法益概念已淡化了其限制刑罰、保護自由的機能,而且所謂侵害‘法和平’、‘法觀念’等只能是司法者的主觀理由而已”。?同前注④,王安異文,第298 頁。類似觀點也指出:“法益概念過度抽象化,甚至精神化、觀念化,雖然能夠增強法益概念的解釋力和涵蓋度,卻導致其喪失了理論批判機能。”?劉軍:《為什么是法益侵害說一元論?——以法益的生成與理論機能為視角》,《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1年第10 期。換言之,法益精神化使得其構成界限機能降低,這一點對于安全感來說更是如此。
1.安全感的主觀性削弱了其作為法益的定型性
如前所述,安全感是一種集體情緒狀態,是風險社會集體心理特質的主觀表征。常表現為無形的恐懼感(formless fear)等個人情感。但“法益是一種客觀存在,是生活利益,而不是價值觀或其他純觀念現象或純思維現象,所以法益是否受到侵害與威脅,可以根據客觀因果法則進行認定”。?同前注?,張明楷書,第203 頁。
某一生活利益要想上升成為一種法益,必須具有相當的客觀性與顯著的定型性,并能夠籍由因果法則的邏輯推論判定其是否受到損害。正如Michael Marx 所言,法益必須具有客體性,必須是實在存有的要素,法益存在于外界的實際之中,而絕對不是主觀之中。?陳志龍:《刑法的法益概念(上)》,《臺大法學論叢》1986年第1 期。但對于安全感而言,必須坦承的是,無論何種理論說辭,都無法否認其濃厚的主觀性。
2.安全感的模糊性沖擊了其作為法益的界限性
得益于清晰的內涵與外延,法益才具有明確刑法處罰界限的機能。但安全感卻并不具有如此清晰的內涵與外延,且其極易受到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擾與影響。在“風險的社會”放大效應下,大眾媒體的渲染與社會輿論的傳播都可能導致安全感的信號輸出失真,各種形式的遮蔽與夸大,都很難讓風險規制主體能夠依據安全感的真實情況,作出最有效率的風險決策。
在此情況下,倘若認定安全感為法益并據此劃定刑法處罰界限,勢必突破刑事歸責中因果關系的科學限定與責任原則的合理范圍,行為主體完全可能脫離行為本身而為他人的不安與恐懼“買單”。即“無法精確辨別由行為人的行為所引起的具體損害,與經由其他社會事實因素或存于潛在被害人自身的主觀情狀所引起的損害,導致行為人可能必須對非自己行為所引起的部分不安情緒負責”。?周漾沂:《論“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令”之處罰理由》,《臺大法學論叢》2008年第4 期。如此一來,“在普遍的社會恐懼之下,各級政府機關能否保持克制而嚴格依法辦事、司法機關能否嚴格控制刑事打擊范圍,就會成為令人憂慮的問題”。?曲新久:《“非典”時期的“典型”反應——評“兩高”的一個刑事司法解釋》,《政法論壇》2003年第7 期。還有學者直陳,當社會陷入集體的不安情緒時,以保護公眾安寧秩序或安全感為中心的恐嚇類犯罪,就會出現成罪門檻過低,而有過度擴張處罰的問題。?參見謝煜偉:《群眾恐慌下的恐嚇公眾危安罪:北捷隨機殺人案后續事件解析》,《月旦法學教室》2014年第9 期。
可見,肯定與支持安全感法益化無疑是在誘發法益的膨脹化與擴張化,而這一趨勢將不自覺地擴大刑罰處罰范圍,導致法益限制刑罰發動的功能日漸萎縮并淪為刑事政策的工具。?同前注②,舒洪水、張晶文。對此,日本刑法理論中“危懼感說”的“曇花一現”可謂是前車之鑒。此說一出現就“受到了學界的強烈批判,被認為輕視法益侵害,淡化責任要件。即使在支持行為無價值論的學者之中這一觀點也未能被廣泛接受”。?[日]山口厚:《日本刑法學中的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金光旭譯,《中外法學》2008年第4 期。除少數學者(藤木英雄、植松正、石堂功正)固守該理論外,其他大多數學者均持批判態度。此外,該說不單在學界應者寥寥,在日本的判例中也常受排斥。“如在白石中央醫院火災事件中,上訴審判決就否定了第一審所采取的以危懼感說為基礎而論處醫院院長責任的判決,而改采具體的預見可能說將第一審判決撤銷。又如川崎崩塌實驗事故確定決中明白指稱:危懼感說使業務上過失責任的成立范圍不當擴大,并失去明確的確定基準,故不足采。”?黃丁全:《過失犯理論的現代課題》,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7 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79-481 頁。
究其根源,危懼感與安全感一樣,作為一種主觀感受,其過度觀念化的內涵與純粹精神化的性質導致在實踐中難以進行準確判斷與實際操作。“如何判斷行為人應否產生不安感,是否產生了不安感,是極其困難的。”?張明楷:《刑法格言的展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 頁。進而難以有效限定刑法處罰的合理界限,難以獲取持續而長久的實踐生命力。對此,日本刑法學者大谷實批評道:“以一般人具有危懼感、不安感為前提予以處罰,則是過度行使刑罰權的表現。”?舒洪水:《危險犯中危險狀態的判斷》,《法律科學》2012年第5 期。我國也有學者指出:“將極為抽象的‘危懼感’作為刑事責任的依據,必將會使得刑事責任變得不可捉摸。一旦‘危懼感’成為一種責任標準,國家權力的適用無異于如虎添翼。”?孫萬懷:《風險刑法的現實風險與控制》,《法律科學》2013年第6 期。
一個以模糊多變的主觀概念為建構基礎的刑事歸責理論,在責任主義原則與人權保障理念的雙重拷問下,勢必難以獲取其正當性。正如有學者評述一般:“危懼感說過度擴大過失責任的范圍,幾與英美法中的嚴格責任或絕對責任無異,違反刑法基本原則‘責任主義’,而且不安感、危懼感本身很難用科學法則、經驗法則加以確定,是極為曖昧的概念,其以未知的危險作為承認責任的論據,由企業監督者負擔個人的責任,超越罪刑法定主義及個人責任原理,不免有侵害人權之虞。因此在日本除了森永奶粉事件,刑法學界的反應是極為冷淡的,其不足釆取是不言而喻的。”?同前注?,黃丁全文,第480-481 頁。
3.安全感的一般性泛化了其作為法益的特定性
刑法所保護的利益應該具有某種意義上的具體性,太過抽象的保護對象不是法益。如德國刑法學者羅克辛就認為,“抽象的保護對象不能是法益(如公共安寧等)”。?蘇青:《法益理論的發展源流及其啟示》,《法律科學》2011年第3 期。比較而言,心理安全感是安全感(情感),是一種特質,而社會安全感是安全感(情緒),是一種狀態。?姚本先、汪海彬:《整合視角下安全感概念的探究》,《江淮論壇》2011年第5 期。安全感法益化更多是在后一意義上使用安全感一詞(如國民的安全感)。也就是說,安全感的面向需要從社會層面加以把握,它是具有一般性的集體心理感受范疇,是所有犯罪行為都可能對社會平和氛圍所造成的無形損害。
現代刑法并不反對法益從“具體”到“一般”的轉向,正如其已經逐漸接受了集體法益的概念。但“公共安全”這一集體法益的證成,并不代表“公共安全感”必然亦可化身為法益成為保護對象,更不是所有的公共安全感損害(社會恐慌)與威脅(人心惶惶)都必須籍由刑法手段給予高強度保護的。這是因為,所有犯罪行為都可能對社會治安情況造成負面影響,而公共安全感的感受對象正是整體的社會治安情況。打擊犯罪行為,維護社會治安,提升安全感,三者之間是正相關的邏輯關系,三者均有機統一于刑法的保護機能之中。具體而言,打擊犯罪行為是刑法的主要功能,維護社會治安與提升安全感是刑法打擊犯罪行為的實際后果。“消除一般國民主觀上的不安,這是客觀抑制犯罪所產生的事實上的歸結(效果),不應將其本身視為直接的刑罰目的。”?[日]松原芳博:《日本刑法總論研究(三)》,王昭武譯,載周永坤等主編:《東吳法學》(總第25 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 頁。
既然如此,就不能將某一特定行為的犯罪化依據歸咎于與所有犯罪行為相伴相生的公共安全感,更不能將安全感視為將某一生活利益提升為法益的主要理由。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需要重點考察的是該行為是否致使某一相對具體與獨立的法益遭受嚴重損害或威脅。舉例來說,某地殺人案件頻發,社會治安情況惡化,一時間全城內外人心惶惶。相信不會有人反對,在此需要刑法評價與保護的法益絕不是因此而減損的社會安全感(泛化的利益),而是殺人行為可能侵害的生命法益(特定的利益)。同樣,在扒竊犯罪所侵法益是否包括安全感的問題上,?如有論者指出:“扒竊行為單獨列出并予以嚴懲的原因是其發生在公共場所,除了侵害公民的財產權之外,更使得民眾人人自危,從而降低社會安全感,因此產生較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只有發生在公共場所,才能使不特定民眾看到并感知,從而轉化為對己財產安全的擔憂,進而轉變為整體社會安全感的降低。換言之,這種較一般盜竊更嚴重程度的危害性,只有發生在公共場所方能得以彰顯。脫離了公共場所這樣特定的條件,盜竊行為尚不足以造成上述危害。”吳加明:《刑法修正案(八)中“扒竊”的司法實踐認定》,《中國檢察官》2011年第7 期。上述判斷規則的正確運用有助于我們得出較為科學的結論。正如有學者所言:“面對已經或可能發生的犯罪而自危,這是任何一種違法犯罪行為都會給社會公眾帶來的感覺,不是盜竊罪所獨有的,更不是扒竊的特征。一個能夠在所有的盜竊案乃至所有的犯罪行為中都會出現的‘不安感’或‘自危感’顯然無法支撐公共場所成為扒竊概念的本質特征的觀念,更不能提供有別于其他盜竊行為的區別尺度。”?車浩:《‘扒竊’入刑:貼身禁忌與行為人刑法》,《中國法學》2013年第1 期。因此,需從社會面向予以整體把握的安全感,不能成為某一行為犯罪化的實質依據,更不能被當作某一行為中受損利益不法內涵提升的立法產物(法益)加以保護。
(二)不符合刑法明確性要求
法益的精神化必然伴隨著法益的模糊化,這無疑將降低法益的界限機能。“安全研究在面上伸展到包括每一種可以想象得到的威脅,則有可能使‘安全’概念失去作為分析工具的效用和價值,使其日益泛化和空洞化。”?任曉:《安全——一項概念史的研究》,《外交評論》2006年第5 期。而安全概念自身的泛化與空洞更是加劇了安全感的模糊與易變,風險不論是具體或抽象描述的事實狀態,或者只是純粹心理的恐懼感受等,皆不斷被轉譯成簡化的安全概念。?古承宗:《風險社會與現代刑法的象征性》,《科技法學評論》第10 卷第1 期。眾所周知,刑法意義下的法益概念必須具體、明確。安全感要想通過刑法明確性要求的考驗幾無可能,也更難以發揮規范引導機能為一般民眾所事先預見。
作為心理狀態的“安全感”,雖說可以借助社會心理學的認知框架與評估工具進行觀測與量化,但這種評估的困難之大以至于立法者在立法時也將其視為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即立法者根本不可能、事實上也沒有開展這項工作。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安全感”是一個“有待明確但又無法明確”的概念,而這與刑法明確性要求相去甚遠。更何況,“公眾的主觀感受具有相當程度的敏感性,很容易受到周邊環境以及集體相互渲染的影響,同一事實因素,在不同社會環境條件之下未必會引起相同程度的感受。亦即,這種套上‘公共和平’法益的理性外衣,而實際上以不安全感為內涵的負面情緒是一種非理性的群體情緒反應,其發生與否、強度以及在群體中擴散的范圍在經驗上都不能確定,也無法事先預見”。?同前注?,周漾沂文。由此導致的負面結果便是,以犧牲法治國的原則為代價來換取大眾的安全感。“放棄行為客觀影響的可檢驗性,搭配刑度范圍擴張,讓法官的裁量空間大增,但又沒有損害結果可審查比例性。明確性也在此被放棄,因為構成要件被訂得彈性又全面,才能實時應付各種變化。”?鐘宏彬:《法益理論的憲法基礎》,臺灣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35 頁。
(三)易導致非理性刑事反應
安全感的難以把握,也注定了以安全感為指向的刑法立法追求將會墜落于虛空之中。如此一來,依據面目模糊的安全感而為的刑法舉措往往是非理性的,象征性立法與應急性立法便是適例。正如有學者所言:“通常一個象征立法背后所代表的,有可能只是立法者基于特定政治目的,所形成的價值偏好,或者只是單純反應出某個時空背景點下社會的集體心理情緒。”?同前注?,古承宗文。前者把“通過刑法進行的犯罪控制作為純粹的安慰劑”?[德]哈塞默爾:《面對各種新型犯罪的刑法》,馮軍譯,載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編寫:《刑事法學的當代展開》(上),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67 頁。來使用,意在“制造問題已被認真對待且已適當處理的印象”。?齊文遠:《應對中國社會風險的刑事政策選擇——走出刑法應對風險的誤區》,《法學論壇》2011年第4 期。而后者的目的“通常只在于舒緩公眾怒氣、安撫公眾和恢復刑事司法體系的可信度,與所要解決的問題無關”。[51]勞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的刑法》,《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3 期。即立法者在明知制定特定規范于事無補或收效甚微的情況下,仍樂意像救火隊員一般通過定罪處刑的方式宣泄社會公眾對于犯罪行為的憤怒情緒,在最短時間內最大限度地迎合公眾的期待。
具體至安全感方面,“維護公共安全不等于維護公共安全感,刑法的任務是讓社會共同生活成為可能,而不是讓社會大眾感到心情愉快。單純的以穩定群眾的集體意識狀態作為刑法的目的任務,將會使犯罪行為對于公民共同生活的侵害意義從社會性層面遁入心理學的層面,而錯失了法的原初意涵”。[52]同前注?,周漾沂文。如果任由“安全感”代替“安全”作為法益,那么顯然很難說刑事立法已經準確領悟和把握了法治的實質精神與理性內涵。
“當今社會,大眾情感極大地左右著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焦點從犯罪人(即犯罪原因)轉移到被害人(即犯罪結果)和潛在的被害恐懼感,并以剛剛發生的事件為基礎。‘后現代社會的刑事政策由政治體制所支配,目標在于始終代表大眾情感,隨時為每一個人提供充足的保護和安全感(即自由)。’每當惡性案件發生后的應急立法、報復性立法就是這種原因的結果。”[53]同前注?,齊文遠文。也有學者對此表示擔憂,“為了因應民眾的犯罪恐懼感及重視被害者與社會情感,刑罰的民粹主義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導致現行刑事政策有朝向管理、監控、隔離的趨勢而行”。[54]許福生:《風險社會與犯罪治理》,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2 頁。立法者與政治人物所采取的“民粹式的嚴罰”政策便是透過公共輿論,如傳播媒體與各式組織來達成,透過霸權式的共識模式說服一般民眾亂世用重典才是解決治安的根本問題。[55]參見Bottoms, A.E.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Punishment and Sentencing. In Christ Clarkson and Rod Morgan (eds.)The Politics of Sentencing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轉引自許華孚:《監獄與社會排除:一個批判性的分析》,《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2005年第9 期。
“以預防為借口,肆意擴展國家刑罰權,使得侵害刑法淪落為危險刑法、并最終淪落為意思刑法的場面,這種立法現象在現代社會,并不鮮見,對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56]黎宏:《法益論的研究現狀和展望》,《人民檢察》2013年第7 期。可以說,以安全感為驅動的刑事政策模式給我們提供了歷史的經驗與教訓,1983年嚴打刑事政策的出臺便是一個明證。據時任公安部部長劉復之回憶,中央做出嚴打決定的一個重要社會背景是,“當年不少地方發生流氓團伙在大白天劫持強奸女青年,公開侮辱婦女,攔路搶劫和結伙打砸搶等惡性案件。許多地方公共場所秩序混亂,婦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牽掛兒女,群眾失去安全感,黨內黨外反映強烈”。[57]劉復之:《“嚴打”就是專政——記小平同志對“嚴打”的戰略決策》,《中國檢察報》1992年1月13日,第1 版。固然安全感既是社會治安晴雨表,又是立法、決策參考表,嚴打刑事政策在特定歷史時期也發揮了相應的作用,但總體來說,基于安全感而發動的嚴打刑事政策并非犯罪治理的最佳政策模式,因此也逐漸為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所替代與補足。
不單如此,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刑法立法動態中也存在此種非理性現象,[58]但也紛紛受到了學界的質疑與批評。如日本刑法學者大谷實指出,近年來日本對于治安的強化作為,與其說是根據犯罪的實際情況,倒不如說是根據“體感治安”而來。[59]同前注?,大谷實書,第26-28 頁。再如日本刑法學者松原芳博也指出,以“國民生活的平穩”為立法理由的《有組織犯罪處罰法》等法律試圖保護國民的“安心感”,但實際上卻并未保護“國民的實際的具體的利益”,其作為象征立法的色彩要更濃一些。[60][日]松原芳博:《刑法總論專題研究(一)》,王昭武譯,《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年第3 期。再如,臺灣刑法學者黃榮堅就結合臺灣地區刑法修正動向痛斥了為迎合安全感等情緒反應所為的非理性立法:“從立法者對于不能安全駕駛罪之加重結果犯規定及法定刑的一再提高,似乎可以見到立法者響應社會人民對于維護生命安全的要求,問題是,對于生命安全之要求的響應應該是出于具有客觀性與體系性的理論系統,而不應該僅僅是一個局部性的情緒反應。”[61]黃榮堅:《2011年刑事法發展回顧:法律說詞與說詞之外》,《臺大法學論叢》(第41 卷特刊),第1554頁。
四、社會恐慌:作為法益的“公眾安全感”
盡管筆者主張從理論層面視之,安全感并不能成為刑法所保護的法益,但安全感在刑法條文中的身影卻不難尋覓,也有不少涉及安全感的犯罪類型(多為社會恐慌類犯罪),主要包括恐怖活動類犯罪與有害信息類犯罪。那么,就不再局限于與犯罪整體現象相對應的安全感而言,在上述具體犯罪類型中,公眾安全感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社會恐慌又能否成為一種具體的法益?這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一)恐怖活動犯罪的法益解讀
對于恐怖活動犯罪,涉及的主要罪名有: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第120 條),投放虛假危險物質罪(第291 條之一)。根據相關規定,恐怖活動是指以制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脅迫國家機關、國際組織為目的,采取暴力、破壞、恐嚇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圖造成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公共設施損壞、社會秩序混亂等嚴重社會危害的行為,以及煽動、資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協助實施上述活動的行為。而近期中國爆發的暴恐事件無一例外地表明,暴恐分子的瘋狂舉動旨在最大程度地制造社會恐慌,實現他們所謂的影響力。暴恐事件中這種反人類、反社會的“無差別殺戮”,勢必會在社會上制造出直接、強烈、持續的恐懼感。可見,制造社會恐慌是恐怖活動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犯罪主觀方面(目的恐怖性)的外化體現。“這里所謂的‘社會恐怖’,是指由恐怖活動犯罪所造成的,在犯罪行為直接受害人以外的一般社會公眾中普遍存在的,以嚴重擔心、害怕類似的犯罪會繼續發生為主要內容的恐怖心理。”[62]陳忠林:《我國刑法中‘恐怖活動犯罪’的認定》,《現代法學》2002年第5 期。照此理解,恐怖活動犯罪企圖制造的“社會恐慌”從本質意義上來講就是因恐怖活動犯罪而產生的“犯罪恐懼感”。而如前所述,此種單純的“社會恐慌”(犯罪恐懼感)并不足以成為一種法益由刑法予以保護。
盡管有觀點指出,恐怖主義犯罪在摧毀物質性犯罪客體的同時也摧毀非物質性犯罪客體——民眾的安全心理,此種無形損害具有明顯的變異性、社會性、沖擊性與沉積性,這種損害具有“聯想空間”,其造成的社會恐慌,遠大于對物質性犯罪客體的打擊和損害。[63]葉海輝:《對恐怖主義犯罪客體的研究》,《法學雜志》2003年第11 期。但筆者認為,其所謂的“聯想空間”無外乎是“由此及彼”的犯罪恐懼感,即“聯想”到自己可能成為下一個犯罪被害者。同樣,其也難以成為法益。此外,類似觀點認為:“判定是否構成恐怖主義行為罪的標準應是行為人的危害行為本身是否會直接引起大范圍的社會恐慌。”[64]莫洪憲:《略論我國的金融反恐》,《法學評論》2005年第5 期。但必須強調的是,“社會恐慌”這一群體心理現象的事實確認與程度認定仍需借助“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公共設施損壞、社會秩序混亂”等現實法益的具體受損情況予以判定。
同樣,投放虛假危險物質行為雖非真正的恐怖主義行為,但由于其足以在群眾中制造恐怖氣氛,擾亂社會秩序,故刑法將達到“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程度的該類行為予以犯罪化。司法實踐中也有將公共場所針刺犯罪等案件以本罪定罪處罰的做法。應當說,本罪中的社會恐慌不應該被理解為對“公共安全”的侵害,而是對“公共秩序”的侵害。但卻有觀點進一步指出,本罪的犯罪客體是一定的社會心理秩序。[65]張波:《論投放虛假危險物質罪——以案例分析為視角》,《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 期。對此,筆者不能贊同,理由是,“公共秩序與社會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保護法益的抽象化必然導致對構成要件的解釋缺乏實質的限制,從而使構成要件喪失應有機能”,[66]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35 頁。若將此處的社會秩序僅僅理解為“心理秩序”,視為一種單純的犯罪恐懼感,過于強調其無形的一面,則更是降低了其構成要件之機能。完全脫離社會有形秩序的心理秩序,說到底是一種幾乎無法準確描述與客觀測量的觀念產物,因而也不能成為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對象。
(二)有害信息犯罪的法益解讀
對于有害信息犯罪,涉及的主要罪名有:編造并傳播證券、期貨交易虛假信息罪(第181 條第1款);編造、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第291 條之一);誹謗罪(第246 條)。其中,以編造、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最為典型。“虛假恐怖信息”,是指以發生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劫持航空器威脅、重大災情、重大疫情等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的事件為內容,可能引起社會恐慌或者公共安全危機的不真實信息。自《刑法修正案(三)》(2001年)增設該罪以來,其一直較為引人關注。
一般認為,該罪系結果犯。其主要社會危害體現在制造恐怖氣氛,引起社會恐慌,擾亂社會秩序,通常情況下造成人們一場虛驚。為防止不當擴大打擊面,刑法規定本罪必須造成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后果,才能構成犯罪。[67]呂廣倫、王尚明、陳攀:《〈關于審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人民司法(應用)》2014年第1 期。需要探討的是:該罪中“社會恐慌”與“社會秩序”均為本罪所保護之法益?還是僅有“社會秩序”堪稱本罪法益?
對此問題的回答,尚需回歸該罪條文的立法旨意。來自立法部門的專家指出,該罪的主要目的旨在打擊編造、傳播虛假恐怖信息行為,即避免行為人借助此種手段在社會上制造恐怖氣氛,引起社會秩序的混亂。因此,“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而所謂“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主要是指引起社會恐慌,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活動無法正常進行。[68]黃太云:《〈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的理解與適用》,載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編:《法律應用研究》(第1 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17 頁。上述司法解釋的制定說明中也指出:“在公共場所人員密集地區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極易引發恐慌情緒,造成踩踏事故等嚴重后果。”[69]同前注[67],呂廣倫、王尚明、陳攀文。可見,社會恐慌僅是危害行為的表層結果,常與公眾的生命、健康密切相連,是該類犯罪客觀產生的群體心理情緒(或社會氛圍),也是導致社會秩序陷入混亂的直接原因。正如有學者指出,公共秩序混亂就是指破壞了平穩與安寧的狀態,其表現之一就是行為人的行為導致公眾基于恐懼或其他心理而不能再進行正常的生活勞動。[70]孫萬懷、盧恒飛:《刑法應當理性應對網絡謠言——對網絡造謠司法解釋的實證評估》,《法學》2013年第11 期。
一般認為,公共秩序是指社會公共生活依據共同生活規則而有條不紊進行的狀態,既包括公共場所的秩序,也包括非公共場所人們遵守公共生活規則所形成的秩序。[71]高銘暄主編:《新編中國刑法學》(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 頁。而“秩序使人們具有預測可能性,給人們帶來了安全感。在此意義上說,秩序也是一種生活利益”。[72]張明楷:《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 頁。由此可見,秩序這種生活利益也可能基于特定的原因被提升為某類法益。因為,社會秩序的平穩運作與平和狀態,有助于公眾保持對社會秩序的一貫信賴,不必因社會秩序的紊亂與脫軌而心生恐懼,進而失去社會安全感。一旦社會秩序的安寧狀態被犯罪所破壞,則將直接影響到公眾對于社會秩序的穩定印象。故在本罪中,社會秩序才是社會恐慌背后的深層結果,也才是本罪名副其實的法益保護對象,即通過刑法干預的手段減少社會恐慌,避免出現由上述情緒氛圍所導致的“社會失序”現象(如突發事故、經濟損失等)。對此,除了可從司法解釋關于本罪認定的相關規定得到印證,也可以本罪的章節歸屬情況(隸屬于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輔以說明。
當然,除了上述兩類犯罪之外,還有一些犯罪也涉及社會恐慌。如危害食品與藥品安全的犯罪也易誘發社會恐慌,但這些犯罪并非典型的社會恐慌類犯罪,其法益保護對象都非常明確清晰,少有人會將其與社會恐慌相混淆,故不再對其做專門解讀。
綜上,“社會恐慌涉及對犯罪的主觀而可能的反應(subjective and contingent reaction),而不是犯罪的客觀嚴重性(objective gravity),這一概念似乎如此模糊與主觀,以致不可能一致地或公認地適用它”。[73]馬偉陽:《國際刑事法院受理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 頁。可見,社會恐慌只是犯罪行為的反射效果,是生活秩序遭受動搖的社會感知,是對規范保持平穩的信賴落空,其主觀模糊注定其無法代替社會秩序成為該類犯罪的法益,公眾安全感也并非上述法條法益保護的真正目標所在。
五、恐嚇犯罪:作為法益的“個體安全感”
如果說與“社會恐慌”直接對應的“公眾安全感”無法成為法益,那么,對于“個體安全感”來說,其在恐嚇犯罪中又能否成為刑法法益?這一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通過對域外恐嚇犯罪的刑事立法考察可知,有不少國家或地區在刑法中針對恐嚇行為做出了專門的規定。上述恐嚇犯罪的法益究竟為何?以恐嚇危害安全罪的法益為例,有論者在總結諸多爭論后指出,個人因受法律秩序之保障而發生安全感,無慮暴力威脅或其他不法干擾,實為重要利益所在。本罪的設立旨在處罰行為人對個人日常生活之安全平穩之妨害。故本罪的保護法益應系指個人日常生活之安全平穩之狀態。[74]王舒俞:《刑法第305 條之理論與實務》,高雄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0 頁。但該觀點又幾乎將其與“個人生活上之安全感”(個人生活狀態的平穩感)相等同,并指出本罪所危害之安全,無論是學界通說,還是實務見解,皆認為其系指“個人心理上的安全感”,亦即其在社會生活之安全感、穩定感。[75]同上注,王舒俞文,第71 頁。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有混淆“狀態”與“感受”之虞。作為法益的“狀態”,是客觀的現實存在,可被具體感知并能在因果關系中被侵害,這樣一來,狀態才能實現法益的界限機能。故在此意義上,德國刑法學者曾將法益定義為“能夠被損害并受到保護的狀態(Zustand)”,是“受法律保護的社會秩序中的抽象價值”。[76]同前注⑥,楊萌文,第66 頁。可見,狀態作為一種法益不足為奇。如日本刑法學者関哲夫就主張將“各個職員基于該建筑物的利用目的而平穩而且順利地實現業務的、事實上的平穩狀態”視為“住居侵入罪”(日本刑法第130 條)的保護法益。[77][日]関哲夫:《法益概念與多元的保護法益論》,王充譯,《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3 期。但“感受”則不然。對個人生活狀態所生之平穩感,歸根結底還是一種主觀層面的模糊感受,且其內容常因人而異,因此也喪失了法益的界限機能。較之于公眾安全感,個體安全感雖能指向單獨的社會個體,可能具有成為某一犯罪法益的特定性,但其仍擺脫不了安全感的主觀性與模糊性,故仍難成為一種法益。犯罪的實質危害在于侵犯法益,刑法的核心目的在于保護法益。將心理感受作為刑法的保護對象,明顯有悖于刑法目的,且易遭致主觀歸罪之批評。故刑法保護的并非是一般人的安全感自身,而是法益。“對于連這種完全不伴有客觀危險性的不安感都要作為處罰的對象是不必要的”。[78][日]前田雅英:《刑法總論講義》,東京大學出版會2006年版,第152 頁。由此可見,在恐嚇危害安全罪的法益問題上,其法益也應是“個人生活之平穩狀態”,[79]當然,也有觀點認為,本罪的法益是“個人內在意思形成與意思活動的自由”,經由意思形成與意思活動的保護宣示,外顯為個人社會生活之精神上安心領域的存在。參見李圣杰:《嗆聲——惡害通知的思考》,《月旦法學教室》(別冊·刑事法律篇),2011年,第87頁。盡管該觀點與本文觀點不盡相同,但都不同意將個人精神安寧這一外化感受視為本罪法益。而不能將其任意等同與隨意類推為“個人對該狀態所產生的平穩感受”。
相比而言,我國雖并無以“恐嚇罪”直接命名的刑法條文,但是以“恐嚇”為犯罪手段的罪名不在少數(如搶劫罪、敲詐勒索罪、綁架罪等)。盡管上述犯罪之被害人會因恐嚇手段而陷入恐懼與不安,但上述犯罪之法益保護對象可謂相當明顯,基本不會據此主張其個體安全感為上述犯罪的具體法益,也無須對恐嚇行為另作單獨的刑法評價。唯有疑問的是:在單純恐嚇(以使他人陷入恐慌為目的的恐嚇)即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個體安全感又能否被視為刑法保護之法益?
通觀我國刑法,僅有尋釁滋事罪(第293 條)在條文中明確了“恐嚇”。該罪系1979年刑法“流氓罪”之分解產物,原條文中也僅限于“追逐、攔截、辱罵”等行為,遲至《刑法修正案(八)》(2011)才在此基礎上增設“恐嚇”。隨著信息網絡時代的來臨,網絡空間中的恐嚇行為不斷出現,為了有效應對此類情況,新出臺的《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3)中還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亦構成尋釁滋事罪。基于此,職業修評師等恐嚇行為有望得到刑法規制。
一般認為,本罪的保護法益是公共秩序或社會秩序,具體來說是社會一般交往中的或與社會公共秩序相關聯的人身安全、行動與意思自由、名譽,以及與財產有關的社會生活的安寧或平穩。[80]同前注[66],張明楷書,第935 頁。但也有學者認為,恐嚇行為的侵犯法益是雙重法益,既有個人的精神安寧,又有社會管理秩序。其中,恐嚇行為侵犯的法益首先是被害人的精神安寧。[81]陳慶安:《恐嚇類尋釁滋事罪的客觀要件研究》,《政治與法律》2013年第7 期。早年也有學者指出,對公民的精神權利(意思自由)的侵害是單純恐嚇行為應當構成犯罪的主要理由。[82]劉白駒:《關于處理恐嚇行為的立法建議》,《法律學習與研究》1989年第4 期。
那么,將公民個體的“精神安寧(權利)”視為本罪法益又是否妥當?筆者認為,刑法法益的內容范圍當然可以涵蓋思想或精神上的對象(如名譽)、也有相關罪名對此予以專門保護(如侮辱罪)。但在本罪的法益問題分析上,尚需結合刑法如何保護心理感受利益予以綜合判斷。有學者指出,只有能被固化的心理不良感受,才能成為一種權利,方有可能獲得刑法的保護。[83]楊春然:《冒犯型犯罪的根據:傷害原則對法益保護原則的一次超越——兼論犯罪的本質》,《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年第2 期。如果說恐嚇他人侵犯到了他人“免于恐懼”的精神權利,那么,按照Joel Feinberg 的說法,此種精神權利貌似亦可成為刑法應當保護的安寧利益。[84]范氏認為,安寧利益是人們實現其生活目標不可或缺的物質條件。其就包括身心健康、情緒的穩定等。參見Joel Feinberg .Offense to Others: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37. 轉引自楊春然:《冒犯型犯罪的根據:傷害原則對法益保護原則的一次超越——兼論犯罪的本質》,《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年第2 期。但是并非所有安寧利益都可以成為法益,只有維持人類生存最低水平的安寧利益,才能進化成權利,獲得法律的保護,甚至是刑法的保護。[85]同上注,楊春然文。例如,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法益保護對象(住宅安寧權)就是此種值得刑法予以保護的安寧利益。這是因為,法益應當以“特別重要及特別有價值”為限。基于刑法的最后性與刑罰的經濟性,唯有刑罰制裁的必要性被肯定時,才容許刑法予以適度干預。而個人單純的驚恐與不安,盡管也會破壞生活之平穩狀態,但能否一概視為威脅人類最低生存水平的安寧利益被作為法益予以保護則存有疑問。
況且,在我國刑法既定性又定量的犯罪構成模式下,單純的恐嚇行為(定性)尚不足以成為犯罪,構成本罪還需要求具備“情節惡劣”(定量)。在相關司法解釋中,“情節惡劣”又多體現在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如“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再如“嚴重影響他人的工作、生活、生產、經營的”。不難發現,主張本罪法益應為公共秩序的觀點仍占據上風。此外,值得特別強調的是,此處“公共秩序”指的是“物理秩序”而非“心理秩序”,即“混亂單純造成人們心理恐慌、憂慮,或者單純導致人們心理失衡、心理秩序混亂的,不可能屬于造成公共場所秩序混亂”。[86]張明楷:《網絡言論自由與刑事犯罪》,引自“2014 互聯網刑事法制高峰論壇(北京)”主題發言材料。
因此,對于損害個人“精神安寧”的恐嚇行為,只要未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破壞,并未導致社會物理秩序嚴重混亂,只需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或其他法律手段進行制裁即可。未必非得在此情況下就匆匆祭出刑法這一終極武器,將所有對損害個人精神安寧的恐嚇行為犯罪化,因為刑法手段顯然并非解決此類問題的最佳方案。也就是說,個人的精神權利當然值得法律保護,無形的精神損害亦需得到法律關注,但基于刑法謙抑精神的考慮,在無充分理由的情況下,該安寧利益即使可以成為一般法益,其不法內涵程度也遠遠未達到刑法法益的要求。綜上所述,個體安全感也不應被視為法益。
斯故,雖然日本刑法學者伊東研祐認為,在現代社會日益復雜化的背景下,社會成員的精神(心理)負荷在不斷提高,作為對“在所謂象征性事中謀求心理上的或精神上的安全感的立法壓力”的回應,有必要以保護安全感和制度信賴感的方式來防止犯罪行為對心理的或精神上的平和或安定實施侵害的危險。[87]同前注?,伊東研佑文,第182-184 頁。不過,其在最后的分析中也坦誠道:“關于擔保一般的安全感或信賴感,設立容許標準則是困難的。一般的安全感或信賴感只是規范正當狀態的心理反映,因此將其作為法益是存在問題的。”[88]同上注,伊東研佑文,第190-191 頁。
六、結語:警惕法益過度精神化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無論是對安全感法益化的整體性批判,還是對社會恐慌類犯罪的具體解讀,抑或是對恐嚇犯罪的個罪分析,“安全感”均不能代替“安全”,在一字之差中搖身一變成為一種法益。即便是在社會恐慌類犯罪之中,社會恐慌也只是犯罪行為的反射效果,社會秩序才是該類犯罪的真正法益。而恐嚇犯罪中的法益也應是個體生活之平穩狀態而非個人安全感。
正如日本刑法學者松原芳博所言:“在國民的不安反映了客觀事實的場合,就應該認為,作為不安的對象的生命、身體、財產等具體利益本身才是保護法益。如果這些利益得到了保護,其結果就是,會給國民帶來安心感。”[89]同前注?,松原芳博文,第65 頁。然而,當下學界卻不乏將二者相混淆的錯誤觀點。如認為:“法益概念中既包含了物質性的保護對象,也包含了精神化的保護對象(例如個人的名譽、自由、恐懼感等),這些保護對象都具有某種意義上的具體性,因此,法益概念完全可以將公共信用、貨幣的真實性、環境、安全等集體法益(例如信賴、健康、安全等精神化的保護對象)包括進來。”[90]王永茜:《論現代刑法擴張的新手段——法益保護的提前化和刑事處罰的前置化》,《法學雜志》2013年第6 期。很明顯,在精神化法益問題上,論者由最初的“恐懼感”到最后又不自覺地滑向了“安全”,其前后邏輯不一致,且最終偏向了“安全”這一集體法益。
風險社會之下,社會大眾對于犯罪的恐懼總是遠遠超過實際被害之可能。正是以“犯罪恐懼感”為代表的社會大眾的不安全感,催生出所謂的“風險厭惡”(risk aversive)社會。即在風險日增的情況之下,“縱使許多人可認知風險的存在,但仍無法接受風險結果的發生,促使逐漸傾向對加害者采取嚴厲措施藉以回避風險”。[91]同前注[58],守山正、安部哲夫書,第48 頁。所以,一旦恐懼像野火一樣被點燃,作為風險控制利器的刑法便理所當然地呼之欲出并被寄予厚望。“然而,這樣的刑法系統與刑事司法系統,除了可能在不知不覺中禁錮了人們內心深處的自由外,其實更是一種全社會中的刑法暴力。”[92]參見李承興:《風險管理作為刑法系統核心?——對臺灣近來犯罪控制與刑事政策的若干反思》,中正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因此,對于風險社會的現代刑法而言,一方面,我們應當與時俱進,肯定法益精神化的大勢所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保持理性,警惕法益過度精神化的危害,特別是需要警惕以追求“安全感”為唯一價值導向的非理性刑法應對,更不能在過于模糊的“安全感”下誤入偏離法治軌道的歧途。只有立足于法治國的基本立場,才能防止慣用刑法的立法者將消除現代風險的其他控制手段棄之不用,而將維系社會安全感問題的社會解決對策完全強加給刑法。
任何心理上的安全感往往只是一種相對性的情緒程度,亦即這種感覺有可能只是訴諸于道德要求,或者只是訴諸于部分人的個案經驗而已。社會安全感也是如此,很難說單純依靠刑法就可以消除公眾對現代風險的恐懼。不能跟著“感覺”走,這才是現代刑法應有的態度。即便是在風險預防的思想指導下,現代刑法在應對風險社會之時,“法益”的城門也不應被“安全感”輕易地洞開,人權保障的堡壘更不應在法益過度精神化的猛烈攻勢之下被輕言舍棄。對此,日本憲法學者大沢秀介的告誡或許值得我們認真思量與反復揣摩:“為了取得微不足道的安心和安全利益,沒有合理的依據而過度強調危險的恐懼和不安,莽撞地構建安全、安心體系,可能會導致犧牲迄今為止所取得人權保障的成果。”[93][日]石塚迅:《安全、安心與人權:日本的情況》,額爾敦畢力格譯,載周永坤主編:《東吳法學》(總第26 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