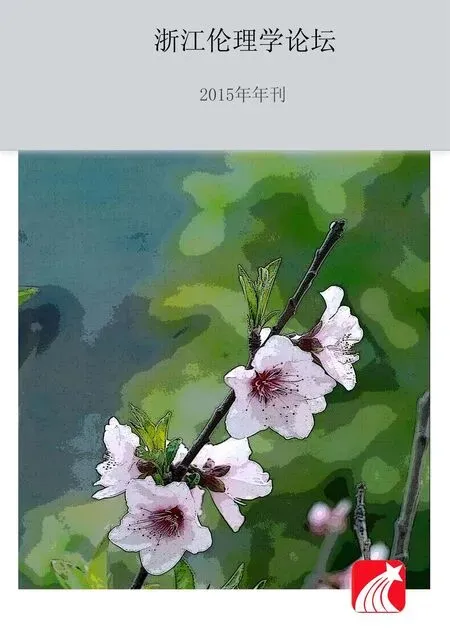論道德教化①
肖會舜
論道德教化①
肖會舜②
教化不僅在于使人成其為人,更在于使人超越其個體性,成為普遍性的精神存在,從而獲得真實的自由。筆者追溯中西方語境中的教化概念,明晰教化的實質(zhì),對傳統(tǒng)道德教化與現(xiàn)代性道德教化進行批判性分析,旨在尋求適應(yīng)現(xiàn)代倫理精神的道德教化。
教化;倫理實體;現(xiàn)代性
教化,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源遠流長:一方面,由于個人只有經(jīng)過教化方才與動物區(qū)別而成為人;另一方面,也只有經(jīng)過教化才能使人脫離孤立的個體,即塑造具有普遍性精神的個體。教化實際上就是使主體實體化和實體主體化,把個體塑造成具有精神性的類存在,從而進入人道或人文的世界。
一、中西方語境中的教化
在中國古代,教化首先是指一種政治—倫理舉措,所謂“明人倫,興教化”是也。《說文解字》釋“教”為:“上所施,下所效也。”即是說,教化是通過政治教化來實現(xiàn)的,它要求統(tǒng)治者有一種較高的道德情操并承擔(dān)一種先知覺后知、先覺覺后覺的道德責(zé)任,所謂“君子之德風(fēng),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fēng)必偃”(《論語·顏淵》),“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荀子·王霸》)。所以董仲舒說:“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wù)。立太學(xué)以教于國,設(shè)癢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jié)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xí)俗美也。”(《漢書·董仲舒?zhèn)鳌?因此,從教化的目的來說,一方面,教化是為了維系傳統(tǒng)社會的正常秩序并使人和諧相處的重要舉措;另一方面,也更為重要的是,教化具有人文意義,即通過教化使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人之所以能夠從動物界抽身,就在于人能夠創(chuàng)制規(guī)范并賦予這種規(guī)范以生命的意義與人道的價值。人對于整個自然宇宙來說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只有通過道德教化,開辟一個內(nèi)在的人格世界,才能開啟人類無限融合及向上提升自我的向度。“人只發(fā)現(xiàn)自身有此一人格世界,然后才能夠自己塑造自己,把自己從一般動物中,不斷地向上提高,因而使自己的生命力作無限的擴張與延展,而成為一切行為價值的無限源泉。”①徐復(fù)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61頁。自然性的人是有限的,但通過道德教化所開創(chuàng)的人格世界是無限的,它能夠通過對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天道”“天理”的契合而實現(xiàn)與“天地參”。
從教化的內(nèi)容來看,“教”不是灌輸抽象的客觀知識和形式規(guī)范,而是“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教以人倫”就充分體現(xiàn)了德性生成條件的各種人倫關(guān)系之間的互動,倫常禮俗不僅具有超越性,更具有現(xiàn)實性與客觀性。如果說“教”體現(xiàn)的是人的向上的維度,那么“化”則指向道的下貫維度。沒有“化”之一維,則“教”必流于空疏。“道”化而成“德”,“道”以“德”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方可謂“化”也。《說文解字》釋“化”為“教行也”,可謂精當。“化”是通過政治—倫理措施使“道”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得到落實,使生活于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受到共同體價值的型塑與精神氣質(zhì)的改變,暢行于社會的人倫規(guī)范、政教措施獲得了理性的認肯與情感的支持,并進駐人的心靈,甚至作為一種無意識或潛意識而成為人的“第二天性”,正所謂“化民成俗”是也。教化是關(guān)乎人的整個倫理性存在的,它是人的心靈感受到共同體的普遍價值并以這種公共本質(zhì)提升個體性的存在,獲得生命的意義。“個人全部內(nèi)在的經(jīng)驗、感覺、情緒和思想在接觸外界的過程中,與外在的即他人的經(jīng)驗、感覺、情緒和思想等等聯(lián)系了起來,個人的這一切內(nèi)在之物必須讓他人意識到,它以擴展了的形式顯示著完整的人類本性,因為它本身即已為精神力量的種種擴展的、具體的努力所滲透。”②[德]威廉·馮·洪堡:《論人類語言結(jié)構(gòu)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fā)展的影響》,姚小平譯,商務(wù)印書館1997年版,第30頁。因此,教化不是單純的對人的理智進行教化,而是對人的整個存在特別是人的情感進行引導(dǎo)和塑造,并固化為人的精神品質(zhì)。“教”的目的在于“化”,“化”是指人的內(nèi)在氣質(zhì)、欲望品質(zhì)得到了徹底的轉(zhuǎn)變,即人的情感、理智、意志能夠以某種普遍性的價值為指引,“從而被塑造成型了一種深厚的、有著超出本能的個別性狀態(tài)的、與他人甚至外物相通的曠達胸襟的精神品德,而且還截斷了倒退到野蠻、粗鄙狀態(tài)的回路”①詹世友:《道德教化與經(jīng)濟技術(shù)時代》,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恰如荀子所說:“長遷而不返其初則化矣。”(《荀子·不茍》)管子也說:“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xí)也,謂之化。”(《管子·七法》)由此我們可知,從本質(zhì)上講,教化乃是對人的情感的教化,使個別性的情感秉持理性的普遍性。當然,情感、欲望并沒有因理性化、普遍化而喪失自身,而是使之具有與人相通的向度。這就說明教化不是單純的理智教化,而是融理性于其中的情感教化。
古希臘的思想家們也認為德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通過學(xué)習(xí)和教化獲得的。教化的希臘詞“paideia”就是教人以德行,使某種普遍性的價值支配著人的思想和行動的意思,“教化的基礎(chǔ)是一般意義上的支配人們生活的價值意識”。據(jù)詞源學(xué)的考察,“paideia”最初的涵義是“兒童的教養(yǎng)”(child-rearing),“它通常指人類身心一切理想的完美,一種完全的kalolagathia,即nobleness(高貴)和goodness(善),在智者時代,這個概念用來意指真正的理智和精神文化”②杜麗燕:《人性的曙光——希臘人道主義探源》,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頁。。總體上講,西方語境下,教化更強調(diào)一種“形式”(form)并賦型于人心之上,因此在教化方式上,它更強調(diào)一種理智教化。因為在他們看來,理性與經(jīng)驗、感覺、欲望是絕對對立的,這種二分結(jié)構(gòu)導(dǎo)致其主張通過理性對激情、欲望的絕對統(tǒng)治來獲得靈魂的提升。德語“Bildung”一詞也充分展示了教化的意義。史密斯(John H. Smith)通過對赫爾德關(guān)于“Bildung”概念的追溯,指出教化概念的意義與范圍主要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1)單個事物形式(form)的提升;(2)教育(education); (3)人類文化形成(the formation of human cultures)的過程和成就;(4)“人性”概念的歷史演變(the historical unfolding of“humanity”);(5)通過按照每一存在者都爭取它的理想的有機形式的原則(principle)統(tǒng)一所有自然世界的科學(xué)的觀點。③John H.Smith:The Spirit and Its Letter:Traces of Rhetoric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Bildung,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48.
可見,“Bildung”的主要含義是通過一種普遍性的形式對人的自然性的提升,使這種自然性符合人性和理性普遍性的概念。伽達默爾指出,“教化”一詞從詞源上說,最初起源于中世紀的神秘主義,以后被巴洛克神秘教派所繼承,再后通過克洛卜施托克那部主宰了整個時代的史詩《彌賽亞》而得到其宗教性的精神意蘊,最后被赫爾德從根本上規(guī)定為“達到人性的崇高教化”(Emporbidung zur Humanit?t,英文為reaching up to humanity)。①[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版,第19—20頁。可見,教化本身就是一個賦形的過程,人最初是本于神所造就的,因此,對于人來說,教化就是使人性通過改變、提升以分有或合乎神性。不過,經(jīng)歷文藝復(fù)興和啟蒙運動之后,神性下墮為人性,而且人性喪失了精神的豐富性和完整性,因為人性要么直接等同于人的自然欲望,要么通過科學(xué)理性或工具理性來認識人的存在,從而把人肢解為沒有任何精神和高貴氣質(zhì)的動物,法國啟蒙思想家拉美特利的格言“人是機器”可謂道出了近代啟蒙思想的人性觀。神性或超越性的失墜,使得教化由此喪失了其根基,自由與必然陷入了二律背反的矛盾之中。德國人文主義者(如歌德、席勒、施萊爾馬赫、赫爾德以及洪堡等)敏銳地意識到“Bildung”概念在人文科學(xué)或精神科學(xué)中的重要地位。洪堡指出:“當我們講到德語Bildung(教養(yǎng))這個詞的時候,我們同時還連帶指某種更高級的、更內(nèi)在的現(xiàn)象,那就是情操(Sinnesart),它建立在對全部精神、道德追求的認識和感受的基礎(chǔ)之上,并對情感和個性的形成產(chǎn)生和諧的影響。”②[德]威廉·馮·洪堡:《論人類語言結(jié)構(gòu)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fā)展的影響》,姚小平譯,商務(wù)印書館1997年版,第36頁。這樣,教化(Bildung)就不僅只是形式(Gelild),而是內(nèi)在地包含著“形象”(Bild),形象既可以指摹本(Nachbild,英文為image),又可以指范本(Vorbild,英文為model),而形式概念則不具有這種神秘莫測的雙重關(guān)系。③[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版,第21頁。
正如伽達默爾所認為的那樣,“教化”概念在精神科學(xué)中有著核心的地位。因為從本質(zhì)上說,精神的存在是與教化觀念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人之為人的顯著特征就在于他能夠從其動物性的生蠻狀態(tài)走出來,脫離直接性與本能性的東西。而且,人還應(yīng)該從其個別性的狀態(tài)中走出來,使其精神的各個方面都習(xí)得一種普遍性,他不應(yīng)該沉湎于他天生所是的那樣子,而應(yīng)成為他所應(yīng)是的那樣。“人類教化的一般本質(zhì)就是使自身成為一個普遍的精神存在。誰沉湎于個別性,誰就是未受到教化的。”④同上,第23頁。教化之所以能夠從其直接性的本能存在中抽身出來,就在于它本質(zhì)上具有精神的理性。不過,精神的理性是一種教化的理性或生命的理性,它并不是通過理智而把“感覺”抹殺掉,而是使人的感覺欲望獲得一種普遍性的形式,即獲得一種“普遍的感覺”。也就是說,教化“它是一種這樣的教育,引導(dǎo)個體把多樣的特殊經(jīng)驗內(nèi)在化,以便通過系統(tǒng)化并作為一般概念來表達并超越它們的特殊性。”①John H.Smith:The Spirit and Its Letter:Traces of Rhetoric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Bildung,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19.
二、教化的實質(zhì)
上文已經(jīng)追溯了“教化”概念在中西方語境中的內(nèi)涵。那么,“教化”的實質(zhì)是什么?或者說“教化”要成就什么?黑格爾一語中的:“教化的意思顯然就是自我意識在它本有的性格和才能的力量所許可的范圍內(nèi)盡量把自己變化得符合于現(xiàn)實。”②[德]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下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wù)印書館1979年版,第44頁。黑格爾所謂的“符合現(xiàn)實”實際上指的就是具有精神的普遍性,即要盡可能地把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智、情感、意志提升到普遍性的層次。但是這種普遍性的提升并不是要把人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性根除殆盡,而是借助于教化所提升普遍性層次使其能夠與他人、社會、歷史在精神上進行溝通。自然性并沒有丟失,而是保存在普遍性當中,在特殊性中將普遍性體現(xiàn)出來。人只有經(jīng)過教化才能獲得現(xiàn)實性,個體不再是作為單獨孤立的個體而存在于世,因為人乃一社會性的存在,即我是作為“我們”之一員而存在的。“我們個體存在的個別性、特殊性、獨立性只是相對的個別性,它不僅產(chǎn)生于包容它的統(tǒng)一性中,而且只能存在于其中。”③[俄]C.謝·弗蘭克:《社會的精神基礎(chǔ)》,王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第58頁。沒有絕對的個體,個體總是受社會共體的熏染而成為定在和現(xiàn)實的,社會共體既是個體成長的基點,但成為社會的個體也是其歸宿。黑格爾也指出:“個體的力量在于它把自己變化得符合于實體,也就是說,它把自己從其自身中外化出來,從而使自己成為對象性的存在著的實體。因此,個體的教化和個體自己的現(xiàn)實性,即是實體本身的實現(xiàn)。”④[德]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下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wù)印書館1979年版,第44頁。實體的普遍性和公共性是個體的本質(zhì),個體只有成為實體的一部分才是其自我實現(xiàn)。
不可否認的是,在具體的教化方式上,中西方文化之間甚至各學(xué)派間存在著差異,有的認為人只有通過朝向不變的存在即理念或神才能獲得教化,而有的則從經(jīng)驗、歷史的角度出發(fā),強調(diào)對情感、欲望的節(jié)制,使欲望的滿足獲得一種合理性與內(nèi)在價值的支持。不管怎么樣,道德教化都是通過對人的感性直接性的一種延遲、反思,使人獲得一種普遍性的視野,從而使人能夠站在一個超出自身即具有“他者”的向度來安排自己的個人生活與社會交往,并在社會交往的過程中,獲得社會的認肯以及個人德性的提升。伽達默爾指出:“教化作為向普遍性的提升,乃是人類的一項使命。它要求為了普遍性而舍棄特殊性。但是舍棄特殊性乃是否定性的,即對欲望的抑制,以及由此擺脫欲望對象和自由地駕馭欲望對象的客觀性。”①[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版,第23頁。可見,教化所實現(xiàn)的普遍性其實是自由的表現(xiàn),人不再受自然性的宰制,而是能夠以精神的普遍性價值來決定并創(chuàng)造自我。此外,教化是沒有自身之外的目的,因而“也不存在任何服務(wù)于達到道德目的的單純合目性的考慮,而手段的考慮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的考慮,并且自身就可以使決定性目的的道德正確性得以具體化”②同上,第437—438頁。。在教化這里,手段和目的的關(guān)系是內(nèi)在的、有機的。這與對天賦的自然素質(zhì)(talent)單純的培養(yǎng)不一樣,自然素質(zhì)的訓(xùn)練和培養(yǎng)只是一種達到目的的單純手段。而經(jīng)過教化的東西,已然成為人自己的東西了,它已融入了人的存在。黑格爾說:“個體在這里賴以取得客觀效準和現(xiàn)實性的手段,就是教化。個體真正的原始的本性和實體乃是使其自然存在發(fā)生異化的那種精神。因此,這種自然存在的外化既是個體的目的又是它特定存在;它既是由于在思維中的實體向現(xiàn)實的過渡,同時反過來又是由特定的個體性向本質(zhì)性的過渡。這種個體性將自己教化為它自在的那個樣子,而且只因通過這段教化它才自在地存在,它才取得現(xiàn)實的存在;它有多少教化,它就有多少現(xiàn)實性和力量。”③[德]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下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wù)印書館1979年版,第42頁。可見,正是通過教化,人的個別性存在向其本質(zhì)性提升,而人的自在的本質(zhì)也是通過個別性表現(xiàn)出來從而獲得實在性和現(xiàn)實性,但教化后的個別性,就不僅僅只是個別性而已,而是體現(xiàn)了實體性的個別性。
其實,教化就是揚棄自然的自我從而獲得現(xiàn)實性。但不幸的是,人們以為自然的特殊性或個別性的存在才是現(xiàn)實的,才是“我”的。現(xiàn)代性及其后現(xiàn)代性就是強調(diào)一種感性上的充分自我感,并把這種自我感看成真實的自我。個性在他們眼里就是特殊性,就是標新立異,就是與一切實在、他人相區(qū)別,并且竭力使這種特殊性取得實在性。其實這毋寧是取消了“我”性,因為“我們的精神生活只有通過交流、通過為我們及其他人所共有的精神要素的循環(huán)才能實現(xiàn)”④[俄]C.謝·弗蘭克:《社會的精神基礎(chǔ)》,王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第59頁。。沒有他人意識的滲透,單純的自我感只能是虛幻的,自我意識只有借助于交流才能得到豐富并獲得現(xiàn)實性,個性不在于與他人格格不入,而恰恰在于能夠被他人理解并接受。所以黑格爾說:“如果個體性被錯誤設(shè)定為由自然和性格的特殊性構(gòu)成的,那么在實在世界里就沒有一個一個的個體性的性格,而所有的個體就都具有彼此一樣的存在了。”他還說:“自我的目的和內(nèi)容則完全屬于普遍的實體本身,只能是一種普遍的存在。一個自然的特殊性,如果竟然成為目的和內(nèi)容的話,那也只有是無力量的和不現(xiàn)實的東西。”①[德]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下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wù)印書館1979年版,第43、42頁。這一點,C.謝·弗蘭克也指出,即使是我們自己創(chuàng)造的某個東西、那個表現(xiàn)了我們個人的“我”之最根本、最獨特的東西也并非來源于孤立的“我”這個封閉的、獨立狹小的范圍,而是來源于精神深處,在那里我們與其他人在一個終極統(tǒng)一體中融合在一起。俗語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一點對于單個的個人也同樣適用,最有獨創(chuàng)性的、出類拔萃的人也是最具“全人類”性質(zhì)的人。只有拙劣的藝術(shù)家才在作品中處處突出其特異性、單純的“我”性,這是一種“偽”個性,真正的藝術(shù)家乃是在作品中展現(xiàn)人性中真正普遍的東西,即“我們”性的東西。
對于個人來說,其心靈情感受到教化即指個人的整個精神氣質(zhì)得到了具有普遍性的倫理規(guī)范和價值理念的型塑,這種型塑不是暴風(fēng)驟雨式的,而是潛移默化式的。性與習(xí)成的方式使這種普遍性的價值成為了人的第二天性。“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禮記·經(jīng)解》)“化”就是一種工夫,“化”實際上是使人的心智秩序得以確立,人的整個靈魂、心靈狀態(tài)得到了徹底的改變,(廣義的)理性在心靈各部分中居統(tǒng)帥地位,能夠協(xié)調(diào)好與情感、欲望的關(guān)系,使整個的心靈不再拘于“意”“必”“固”“我”,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情理,克服、戰(zhàn)勝了個別性的狹隘私欲,能夠站在與他人甚至天地相“通”的立場來看待自我,獲得“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醉名》)的博大胸襟。“化”更是一種成就,它使人的德性結(jié)構(gòu)化為人的精神品質(zhì)和性格質(zhì)素而不是淪為一種偶然的善行,偶然的善行在受到極大利益誘惑或威脅逼迫時就會返回到受教化前的粗鄙狀態(tài)。而由教化獲得的“通”感是一種圣人氣象,《說文解字》釋“圣”為“通”,實為確當。孔穎達疏:“圣者,通也。博達眾物,庶事盡通也。”有學(xué)者稱:“儒學(xué)所謂‘性與天道’的形上本體,乃是在實存之實現(xiàn)完成歷程中所呈現(xiàn)之‘通’或‘共通性’,而非認知意義上的‘共同性’。因此,這‘通’性,非抽象的實體,而是一種把當下實存引向超越,創(chuàng)造和轉(zhuǎn)化了實存并賦予其存在價值的創(chuàng)生性的本原。”①李景林:《教化哲學(xué)》,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緒言第14頁。故而可見,教化并不是要把個體的特殊性泯滅,而是提升著人性,使人性具有更為豐富的內(nèi)涵,“內(nèi)得于己,外得于人”(《說文解字》)。受到教化的心靈在世界中不再被物役所宰制,而是獲得了一個無限性或不朽,它把自我投身于宇宙大化流行當中以獲得無限大全的背景支持。教化就是要達到“自己把握其自己的自我”,“它不是把握別的,只把握自我,并且它將一切都當作自我來把握,即是說,它對一切都進行概念的理解,剔除一切客觀性的東西,把一切自在存在都轉(zhuǎn)化為自為存在”②[德]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下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wù)印書館1979年版,第40頁。。而且,教化的真理是獲得自我意識與實體的統(tǒng)一,或者說是普遍的自我意識。自我意識的真理不是單個的存在物,而是單一物和普遍物、個體性和實體性的統(tǒng)一,或者說必須既是自為存在也是自在存在。
最后,我們還必須指出,由教化而獲得的人格是一種健全的人格,它是一種“有生命的平衡”。也就是說,教化的目的是使人心中的情感和理智相互滲透,是情感化的理性或理性化的情感。沒有理性的情感是自私的、狹隘的,無法與他者的情感相通,但沒有情感的理性是沒有生命、沒有靈性的。單純的理智必然是機械而抽象的,沒有生命情感的灌溉,理性必然會退化成為毫無生氣的邏輯形式。健全的理性必然是要照亮(enlighten)生命的。所以黑格爾指出現(xiàn)在道德教化的工作在于揚棄那引起固定的思想從而使普遍的東西成為現(xiàn)實的有生氣的東西。因此,現(xiàn)代教化的實質(zhì)在于如何使這種抽象的理智概念重新煥發(fā)出靈性的躍動和生命的情感感受,使我們的精神不再由于缺乏理性而狹隘,也不再由于缺乏情感而干涸。所以,教化的目的是成就一種健康的精神。這種精神的特點用弗洛姆的話說就是:“有愛與創(chuàng)造的能力……有自我身份感,這種身份感來自自身的經(jīng)驗,即自己是力量的主體和主動者的經(jīng)驗;能理解自身之內(nèi)及之外的現(xiàn)實,即能夠發(fā)展客觀性及理性。”③[美]E.弗羅姆:《健全的社會》,孫愷祥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頁。
三、超越“倫理的專制”和“道德的獨裁”
傳統(tǒng)的道德教化有其強大的歷史根基。社會秩序與心智秩序的同構(gòu)性使得傳統(tǒng)教化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從文化傳統(tǒng)、生活實踐、人性自然的地基上進行的,日夕熏染,習(xí)于向善,進而成就善德。因為作為傳統(tǒng)社會規(guī)范性力量的“禮”不是理智思慮的結(jié)果,它是充分體現(xiàn)了倫理精神的典章制度,“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天降也,非地出也”,而是本于人情、人性的,“禮作于情”是也。而且,傳統(tǒng)社會中倫理生活的整體性與連續(xù)性也使其教化范式表現(xiàn)出“潤物無聲”的特點。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傳統(tǒng)的道德教化范式有其自身的弊病,必須向現(xiàn)代教化范式轉(zhuǎn)化以適應(yīng)時代狀況及其要求。傳統(tǒng)道德教化總體上體現(xiàn)出一種較強的道德觀,這種較強的道德觀人為地制造了人倫規(guī)范(義)與肉身欲求(利)的二元對立。而且,在傳統(tǒng)社會中,“我們”具有絕對的統(tǒng)治力,以至于“我”的合理性要求也被剝奪了。“我們”在傳統(tǒng)社會中無所不在,而“我”卻始終處于缺席的境地。而且,傳統(tǒng)倫理更多地具有自在的、直接的性質(zhì),它還沒有與自為意識結(jié)合起來,亦即還沒有在倫理自身內(nèi)經(jīng)歷分裂,沒有與特殊性結(jié)合,還處于“自然性倫理”階段。
現(xiàn)代性道德教化在于從“我們”中解救出了“我”,這不能不說是啟蒙以來的一項成就。“我”不是由“我們”得以說明和確立的,“我們”卻是由“我”而獲得存在的合理性。“我”與“我們”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我們”之間不存在著一條神圣的存在之鏈,也就是說,“我們”不是“精神性”的存在,而只是“無內(nèi)容的單純自我相關(guān)”。正是在這一思維的支配下,道德完全成為自我決定的東西,它沒有任何特定的內(nèi)容,只是一種“自為的、無限的、形式的自我確信”。因此,在道德中,“我”也只是一意識主體,沒有任何規(guī)定性,也不達到任何定在,這樣一種形式的自我確信也容易從普遍性過渡到特殊性,因為這里所謂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本身同出一源。“當自我意識把其他一切有效的規(guī)定都貶低為空虛,而把自己貶低為意志的純內(nèi)在性時,它就有可能或者把自在自為的普遍物作為它的原則,或者把任性即自己的特殊性提升到普遍物之上,而把這個作為它的原則,并通過行為來實現(xiàn)它,即有可能為非作歹。”①[德]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wù)印書館1961年版,第142—143頁。所以,當普遍性本身只是自我自為意識單獨決定時,它又有可能造成一種“道德的獨裁”。“道德的獨裁”是自以為純潔,并將自我特殊性的意志提升到普遍性之上,要求他人也遵循這種虛假的普遍性,而當他人不服從時,則以道德之名對他人進行強制。導(dǎo)致“道德的獨裁”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的觀點不要求任何定在或好的后果,因為任何定在如果不是對道德真純的玷污的話,至少任何定在并不構(gòu)成道德的實質(zhì)規(guī)定或必然要素。
傳統(tǒng)的自在倫理可能導(dǎo)致“倫理的專制”,因為它缺乏個體自我意識的反思,亦即缺乏特殊性環(huán)節(jié),甚至把特殊性看作與倫理普遍性截然對立的東西;而自為的道德卻也可能導(dǎo)致“道德的獨裁”,因為它只是個體自我意識的反思,僅僅把道德停留在隱密的內(nèi)心世界,它不要求有好的定在或后果,但是這種抽象的良心只是自己知道自己、自己決定自己,它是他人所無法洞徹的。所以當把特殊性提升到普遍性之上并要求它實現(xiàn)時,就可能無視他人的特殊性而導(dǎo)致“道德的獨裁”。“倫理的專制”主要就是表現(xiàn)在傳統(tǒng)社會,在那里,個體沒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它必須成為實體的一員才有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實體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它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對自然倫理的反思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所以在倫理專制的社會,個體的特殊性是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沒有個體的特殊性環(huán)節(jié),自在的“真實的精神”永遠只能是處于渾沌未萌的狀態(tài),即“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層次。更為可怕的是,倫理的專制使得個體僅僅具有偶性而已。所以,強調(diào)對自在倫理的絕對服從肯定不是教化,因為人在那里是沒有自我意識的,這無論如何都是對人性的戕害。從自在的倫理世界中走出并進入自為的道德世界就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一種進步,因為個體的自我意識第一次真正覺醒了。一切自在的東西都必須放在理性的考量之中,只有經(jīng)得起理性普遍性檢驗的才有存在的合理性,自然性的倫理在科學(xué)理性的考量下喪失了其天然的合理性。但是這并不是說單純自為的意志就能實現(xiàn)真正的自由,因為經(jīng)過理性反思而建構(gòu)的道德原則或道德規(guī)范并不一定是周全的,而且當理性與情感感受處于絕對對立的立場時,道德也就成了“心懷厭惡之感而去做道德之事”了。在個體理性的反思下,“道德”確實獲得了普遍性,因為它必須經(jīng)受住邏輯的不矛盾律,但是,形式的普遍性卻也忽視了個體的情感。這樣一來,道德原則或道德規(guī)范又變成一種沒有生命、沒有精神的東西了,這也就是為什么現(xiàn)代以來的道德教化總體上說是失敗的:一方面,在道德世界觀中,只要個體有良好的理性反思能力就必然能夠做出合理的行動似的,所以道德教育也僅只是“脖子上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neck up)。殊不知,“脖子上的教育”只能造就沒有“心肝”(heart)的道德知識專家,而無法塑造一個具有普遍性的靈魂。這里所說的普遍性不是形式上的普遍性,而是一種“品質(zhì)的普遍性”①詹世友:《道德教化與經(jīng)濟技術(shù)時代》,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頁。,即情感、氣質(zhì)的普遍化:個體的情感受到了普遍性價值的型塑,使得個體的情感與理智能夠相互滲透乃至化通,從而使個體的生命變得更深厚與靈慧,他能夠感他人之所感、想他人之所想,也就是說,能夠以寬容、開放、平等的姿態(tài)與他人溝通、交往。而現(xiàn)代性的道德教化乃是沒有情感的,因為情感在他們看來是無法普遍化和通約的,而作為特殊性表現(xiàn)的情感也只能是無尺度的,所以知與行的分裂乃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沒有倫理實體的環(huán)境支持,道德就僅僅作為主觀性的東西,而這種主觀性如何獲得普遍性以及客觀性本身就是可疑的了。這樣一來,道德也只能是以規(guī)范的形式出現(xiàn),而且道德也可以說只是一種懲戒性的規(guī)范。所以這也導(dǎo)致現(xiàn)代道德教育只是培養(yǎng)個體機械地遵循規(guī)范,而不是把個體的生命提升到一個普遍性的層次,培養(yǎng)一種普遍性的道德人格,使個體在盡義務(wù)的同時自然而然就能做到行為合宜、情感合度。最后,“道德的世界觀”只不過是一種否定的自由,它所要實現(xiàn)的無限不是在有限的基地上進行揚棄之而實現(xiàn)的,所以它也就根本不考慮人性的有限性以及環(huán)境的復(fù)雜性,只是為盡義務(wù)而盡義務(wù)。
正是基于對傳統(tǒng)“倫理世界觀”與現(xiàn)代“道德世界觀”的分析,我們認為必須實現(xiàn)倫理與道德的辯證統(tǒng)一,即倡導(dǎo)一種走向倫理精神的道德教化,也就是說,自然性的、直接性的倫理世界經(jīng)歷自我意識的道德教化而向自身返回,從而實現(xiàn)一種自由性的倫理世界。只有在這樣一種倫理世界中,才能實現(xiàn)了意志與其概念的同一。正如黑格爾所說,“倫理是客觀精神的完成,是主觀精神和客觀精神本身的真理。客觀精神的片面性在于,它部分地直接在實在里,因而在外部東西、即事物里,部分地在作為一種抽象普遍東西的善里具有其自由;主觀精神的片面性在于,它同樣與普遍東西抽象地對立而在其內(nèi)在的個別性里是自我決定的”①[德]黑格爾:《精神哲學(xué)》,楊祖陶譯,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頁。。所以,作為主觀精神與客觀精神統(tǒng)一的“倫理”既擺脫了自然性倫理的自在性,又擺脫了主觀性道德的自為性,從而實現(xiàn)了自在自為的自由。相比較而言,現(xiàn)代性道德教化的最大任務(wù)也許并不在于使人擺脫“野人”狀態(tài),而在于使人擺脫“蠻人”狀態(tài)②“野人”和“蠻人”的區(qū)分出自席勒。席勒認為,人可以以兩種方式使自己處于對立的狀態(tài):一種方式是“感覺支配了原則”而成為“野人”,另一種方式是“原則推毀了感覺”而成為“蠻人”。“野人”視自然為他的絕對主宰,而“蠻人”則嘲笑和謗瀆自然,他總是成為他奴隸的奴隸。所以在席勒看來,“蠻人”比“野人”更可鄙,因為有教養(yǎng)的人總是把自然當作自己的朋友,尊重自然,只是約束自然任性而已。(可參見[德]席勒:《審美教育書簡》,馮至、范大燦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6頁。),因為“蠻人”是無法獲得與他人、與社會的內(nèi)在精神統(tǒng)一的。現(xiàn)代社會是特殊性支配著普遍性,從而以形式的普遍性來確保特殊性的實現(xiàn)。正如黑格爾在分析市民社會階段時所指出的,具體的人作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且特殊性原則只有在普遍性原則中才達到其真理性和現(xiàn)實性,因為市民社會“相需相求”的結(jié)構(gòu)要求個別性的滿足以他同時滿足其他人的欲望為前提,所以在市民社會中,特殊性是受到普遍性限制的,而且個體也自覺到了這種限制并努力促成普遍性的實現(xiàn)。雖然特殊性原則與普遍性原則是結(jié)合在一起了,但這種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tǒng)一并不是“倫理性的同一”,因為它不是作為自由,而是
作為必然性而存在的,因為特殊性若不與普遍性相結(jié)合,特殊性是無法實現(xiàn)自身的。由此可見,重建“倫理性的同一”乃是當今道德教化的重中之重。傳統(tǒng)共同體已一去不復(fù)返,我們現(xiàn)在要做的只能是重構(gòu)“倫理性的同一”;它是一種“精神性”的東西,而且精神性的大全只有通過特殊性才能實現(xiàn)自身。所以我們現(xiàn)在就是要在社會利益高度分化中重建人的心靈的秩序,培養(yǎng)一種人的“品質(zhì)的普遍性”。這種“品質(zhì)的普遍性”就不僅是對規(guī)范、制度在形式上的遵循,更是秉持一種普遍性的價值覺察和人道情懷,使人能夠在一切具體領(lǐng)域的具體活動中實現(xiàn)道德精神和價值內(nèi)容。
①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青年項目《道德自我的倫理根基——教化論視野下的現(xiàn)代性道德哲學(xué)批判》(編號12YJC720041)階段性成果。
②肖會舜,哲學(xué)博士,紹興文理學(xué)院法學(xué)院教師,主要從事倫理學(xué)原理、政治哲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