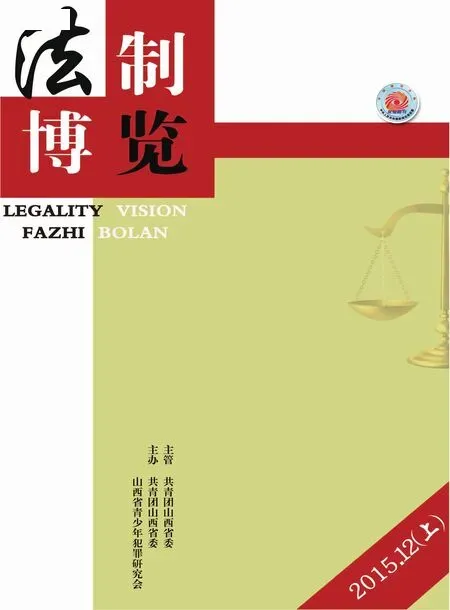淺析網絡謠言的刑法規制問題研究
張曉軒 黃丹娜
1.廣東華諾律師事務所,廣東 汕頭 515000;
2.廣東特力律師事務所,廣東 汕頭515000
一、網絡謠言的基本內涵
(一)網絡謠言概念的厘清
網絡謠言雖然伴隨著網絡的普及而出現,但是至今對于網絡謠言并沒有一個確切的法律層面上界定。在分析和探討刑法對于網絡謠言的規制之前,必須要對網絡謠言有一個明確的概念。當前有學者認為:網絡要求就是在網絡平臺發布的虛假信息,也有人指出網絡謠言是“在網絡上生成或發布并傳播的,沒有事實根據或捏造的虛假信息。”還有人指出網絡謠言是“利用網絡技術以及網絡媒介所傳播的對公眾感興趣的事物、事件或問題未經證實的闡述或詮釋。”等等。雖然以上幾位學者對于網絡謠言進行了相關定義,但尚不夠具體和全面,并未細致性的概括出網絡謠言的特征。根據個人理解,對于網絡謠言的定義的重點在于“謠言”而非網絡,因為后者僅僅是提供了發布的途徑,是謠言發布的一種媒介而已。因此,在網絡謠言概念的界定上,應當優先確定“謠言”在法律概念上的界限。根據《現代漢語詞典》中對于謠言的解釋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消息。”我國《刑法》中所指“謠言”有“捏造事實”之意。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所指“謠言”作“散布”之解。綜上,應當將網絡謠言的概念歸納為:沒有相應事實基礎而被故意捏造出來并通過網絡媒介進行傳播的言論。
(二)網絡謠言的基本特征的界定
網絡信息能否構成網絡謠言,可從一下幾個方面進行判定:
1.行為人主觀捏造與傳播也即行為人明知是虛假信息但卻故意進一步捏造并通過網絡途徑進行傳播,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就故意而言,指的是行為人知道虛假信息可能會造成一定的危害但卻希望并放任該危害的發生。網絡謠言的制造者與傳播者,大都具備此種心理。如果當事人的心理態度為過失,并在此主觀因素的支配下制造或傳播了網絡謠言,其言論不構成網絡謠言。例如:行為人不知言論是被捏造而進行傳播擴散的就不應當被認定為網絡謠言的制造者。
2.傳播途徑為網絡平臺。在現實生活中,謠言的傳播有多種途徑但唯有通過網絡平臺發布的虛假信息或惡意中傷信息才能被定義為網絡謠言。由于網絡平臺的開放性,任何人均可以通過互聯網發布各類信息,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和高效性,由此決定了網絡謠言的發布必定會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危害。
3.網絡謠言受眾范圍較大。網絡謠言的危害性與其受眾范圍息息相關,呈現正比例關系。網絡謠言的發布唯有具備一定程度上的受眾才能產生一定的危害性,受眾范圍越大,則意味著其危害性越大。此外,在實際生活中對于網絡謠言危害性的判斷還需要綜合行為人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和判定。例如,網絡謠言行為人雖然捏造了一定的虛假信息但僅僅是發布在了只能自己瀏覽的網絡平臺,其他人無法瀏覽的話,此時該行為并不具備社會危害性,對于他人的權益并未造成損害。
二、刑法規制網絡謠言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
(一)刑法中未對相關網絡謠言犯罪進行法律規制的情形
例如,2011年在網絡上盛傳的《內地“皮革奶粉”死灰復燃長期食用可致癌》一文中,一經發布即刻被眾多大型網絡平臺媒體所轉載,直接導致了我國多家牛奶制造廠商股價的下跌,尤其是蒙牛股價下跌幅度高達3.3%。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規定:編造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然而此類網絡謠言之內容并不屬于“虛假恐怖信息”的范疇,因此不能適用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由于此類網絡謠言所針對的是不特定的對象,故誹謗罪與損害商業信譽罪亦不能規制此類網絡謠言。
(二)刑法中已對相關網絡謠言犯罪進行法律規制但存有缺陷的情形
例如,在誹謗型網絡謠言事件的犯罪認定存在一定的缺陷。所謂誹謗罪指的是故意捏造某種事實并故意傳播而且能夠敗壞受害人的名譽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未發布該司法解釋之前,我國《刑法》中誹謗罪的認定標準為“情節嚴重”,但該認定標準無論在內涵上還是外延上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法官在辦理該類案件的過程中只能通過自己對于案情的分析與判斷來進行裁決,其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自由裁量權過度使用或權力過大必定造成在案件的判定上出現各類問題,尤其是影響到案件的定性以及出發力度。
三、刑法規制網絡謠言的進一步完善
(一)刑法規制網絡謠言的前提——保證言論自由的正常行使
在當代社會網絡謠言是不可避免,也同樣遭人痛恨,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網絡謠言均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一旦將所有的網絡謠言通過法律進行規制的話,勢必會對公民的權益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損害,尤其是言論自由權。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的自由。就言論自由而言,其內容應當是遵從我國基本國情而且是有利于社會穩定與發展的自由表達,與造謠內容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因此,對于網絡謠言,我國刑法應當將之限制在某一合理的范圍之內,唯有當網絡謠言達到了規定的范圍或程度方可運用法律進行規制和制裁。
(二)遵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保證刑法適度
運用刑法規制網絡謠言應當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其處罰的依據應當綜合網絡謠言的危害大小、受眾范圍大小、受害人受到的損害程度大小、能否進行事后補償等多種因素加以判定,而非一概而論的運用刑法手段進行處理。謙抑性是刑法的特點之一,由于刑法的強制力最大,因此在刑法的運用上應當慎之又慎,唯有達到一定程度方可使用以避免對公民造成不必要的損害。例如,在2013年9月14日的,楊某通過個人微博發布了一條消息,內容是張家川9·12 殺人案發生后警方不作為,民眾多次舉報不受理而且與民眾之間發生沖突。在當天晚上,其又繼續發布了警方強制拘留家屬的消息并再次與民眾發生了爭執。隨后,該信息引起了張家川警方的高度重視,經過調查發現純屬了惡意造謠,隨后楊某被拘留,等待進一步的處理。楊某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抹黑了張家川警方,對其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上負面影響,但是此行為只需要警方仔細調查即可將謠言不攻自破,是否需要運用法律進行制裁有待商榷,與法律的謙抑性原則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
(三)拓寬誹謗類網絡謠言犯罪的追訴途徑
誹謗類網絡謠言所面臨的司法困境主要表現在當事人的取證能力上。公權力是否介入、介入的時機以及介入的方式都將成為認定和懲罰誹謗類網絡謠言犯罪的關鍵,但是當前的法律卻沒有給予明確的規定,導致當事人處于尷尬的境地。就此而言,必須要立足現狀不斷拓寬當事人的自述的通道。自訴程序的運用,是將國家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兼顧起來,在保障受害人權益的同時給與行為人自我申訴的機會,以保障法律的公正公平性。尤其對于對受害人造成了輕微損害的犯罪是否運用刑法加以制裁,可由被害人去行使。對于受害人在受到網絡謠言攻擊時,但并不想通過刑法去追責時,公權力可無需進入;反之,當受害人欲主站自身權益,希望通過刑法進行追責時,公權力則應及時進入。
[1]謝耄宜.試析社會轉型期網絡謠言的防治策略[J].法制與社會,2014(8).
[2]桑麗.轉型期中國網絡謠言的形成機理探析[J].中國青年研究,2014(11).
[3]李麗.網絡謠言問題的詮釋學結構分析[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