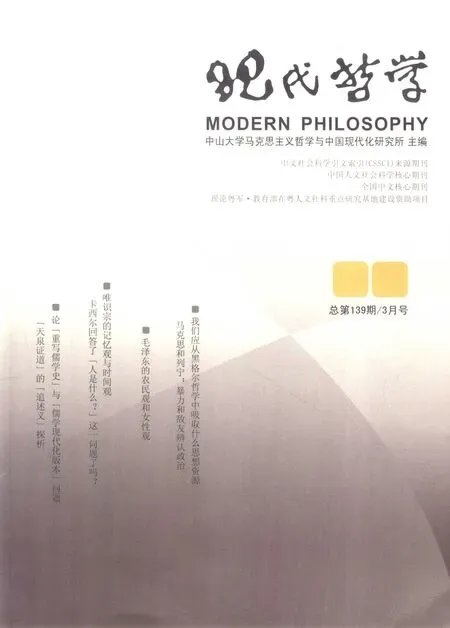范恩論本質的模態主義解釋*
何朝安
范恩論本質的模態主義解釋*
何朝安**
針對本質的模態主義解釋,范恩發展了一個著名論證來反駁它。范恩試圖證明,成為必然屬性是成為本質屬性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通過對范恩的論證給出新的分析,文章將表明,范恩的反例都建立在“對象反身性”屬性的構造上,其論證貫穿著“同一性本質”和“識別性本質”的混淆,從而其針對模態主義解釋的挑戰是不成立的。
范恩;本質;模態主義;對象反身性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關于本質(essence)的哲學分析就成為一個有持續重要性和活力的哲學議題。但是,直到量化模態邏輯興起以來,關于本質的形而上學研究才得以開始嚴格地以模態概念來刻畫本質屬性。對象X的本質屬性被刻畫為X的必然屬性,這一觀念具有相當強的直觀基礎。因為如果P是X的本質屬性,則P是使得X成其為自身的要素(之一)。換句話說,在任何情況下(即在任何可能世界中)只要X存在,則X都具有P。反之亦然,如果X無論如何也無法失去屬性P,那么P必定“根植于”X的本性(nature)之中,從而X本質上具有屬性P。如此一來,我們有了關于本質的模態主義解釋:P是X的本質屬性當且僅當P是X的必然屬性。
針對本質的模態主義解釋,范恩(Fine)發展了一個著名論證來反駁它。①Fine,K.,1994,“EssenceandModality”,inPhilosophicalPerspectives8.范恩試圖證明,成為必然屬性是成為本質屬性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亦即,就某特定對象而言,它的某些必然屬性并不是其本質屬性——盡管其任何本質屬性都是其必然屬性。針對模態主義解釋,范恩主張反其道而行之,以本質概念來定義必然性(而不是相反),并以此為基礎,發展了一種回歸到亞里士多德的新本質主義。范恩這一令人出其不意的工作引發了廣泛關注和爭論。科斯力基認為范恩恰當揭示了本質性與必然性之間的某種非對稱性②Koslicki,K.,2012,“Essence,NecessityandExplanation”,inT.Tahko(ed.),ContemporaryAristotelianMetaphys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查爾塔認為范恩的挑戰不僅成立,而且還有進一步推進的空間和必要性③Zalta,E.,2006,“EssenceandModality”,inMind115.;科雷亞認為某種獨特版本的模態解釋可以避免范恩的反例④CorreiaF.,2007,“(Finean)essenceand(priorean)modality”,inDialectica,61.;而扣玲則認為范恩的反例建立在對本質(essence)和本性(nature)混淆之上,從而是不成立的。⑤Cowling.S.,2013,“TheModalViewofEssence”,inCanadianJournalofPhilosophy43.
相關爭論顯然還沒有完結的趨勢,但我們認為這些既有爭論對范恩反例之根源的認識并不充分。本文擬就范恩的論證給出新的全面分析,并對其有效性給出評估。我們將看到,范恩的反例都建立在我們將稱之為“對象反身性”(objectreflexive)屬性的構造上,其論證貫穿著“同一性本質”(identity-essence)和“識別性本質”(identification-essence)的混淆,從而其針對模態主義解釋的挑戰是不成立的。
一、范恩對模態主義的挑戰
范恩構造了四組反例來挑戰本質的模態主義解釋,其基本目標是證明存在某些不是本質屬性的必然屬性。⑥第一組可稱之為“非對稱性反例”。由于“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是必然真理,因而,〈{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這一屬性是蘇格拉底的必然屬性。①在本文中,我用{x}表示以x為元素的集合,以〈y〉表示表達式“y”所表達的屬性。但是,范恩認為〈{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卻不是蘇格拉底的本質屬性,因為蘇格拉底的本性并不要求他屬于某個集合,甚至并不要求存在任何集合。但其對稱的情況卻完全不同,〈包含蘇格拉底作為其唯一元素〉這一必然屬性卻是{蘇格拉底}的本質屬性,因為集合的本質恰好在于其元素的構成情況。也就是說,在蘇格拉底和{蘇格拉底}之間存在某種非對稱性:同一個必然真理僅僅揭示了{蘇格拉底}的本質屬性,而無法揭示蘇格拉底的本質屬性。
第二組反例可以稱之為“無關性反例”。根據個體化原則,蘇格拉底必然與其它任何個體都不同一,因此“蘇格拉底不同于埃菲爾鐵塔”是必然真理。從而〈不同于埃菲爾鐵塔〉是蘇格拉底的必然屬性。但是它卻似乎不是蘇格拉底的本質屬性,因為蘇格拉底的本性并未以任何方式與埃菲爾鐵塔相關聯,否則的話,不光埃菲爾鐵塔會與蘇格拉底的本性關聯起來,甚至任何東西都將與蘇格拉底的本性相關聯——只要把〈不同于埃菲爾鐵塔〉中的埃菲爾鐵塔換成任何東西(除蘇格拉底)都將獲得一個蘇格拉底的必然屬性。這意味著要了解蘇格拉底的本性,我們必須先行了解所有的東西,而這顯然不符合直覺。
第三組反例可以稱之為“平乏性反例”。“蘇格拉底是如此這般使得2+2=4”(Socratesis suchthat2+2=4)是一必然真理。因而,〈如此這般使得2+2=4〉是蘇格拉底的一個必然屬性,但它顯然不是蘇格拉底的本質屬性。與“無關性反例”類似,“2+2=4”這一算術真理與蘇格拉底的本性完全不相關,否則的話,任何必然真理都將成為蘇格拉底的本質屬性的構成要素了。
第四組反例針對模態主義解釋的一個限定性版本展開,本文暫不作討論。
關于前三組反例之所以存在的根源,范恩本人作了簡要分析。他認為,只有當某必然真理T具有關于對象X的根源敏感性(source-sensitivity)時,它才能夠用于展現X的本質。所謂關于X的根源敏感性,是指T的真奠定于X的同一性之中。“蘇格拉底是哲學家”的真奠定于蘇格拉底的同一性之中,因而它具有關于蘇格拉底的根源敏感性。但是“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的真卻并不奠定于蘇格拉底的同一性之中,而是奠定于{蘇格拉底}的同一性之中。因此,那個真理只能展現{蘇格拉底}的本質屬性,卻不能展現蘇格拉底的本質屬性。范恩認為,必然性真理一般不具有根源敏感性,而本質性真理必須具有根源敏感性。這一差異解釋了非對稱性現象的存在,也解釋了為何本質屬性無法通過必然屬性得以完全刻畫和捕捉。
關于范恩的這一分析,存在一些疑點。首先,并不清楚為何“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的真僅僅奠定于{蘇格拉底},而不奠定于蘇格拉底。實際上,“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表達某種二元關系:“蘇格拉底和{蘇格拉底}具有如下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唯一元素”,其邏輯形式是R(a,b)。根據關于二元關系的一般性理解,對于R是否成立而言,a和b同樣重要且缺一不可。似乎并無特別理由認定R(a,b)的真僅僅奠定于其中一個元素,而非另一個。實際上,如果蘇格拉底不保持其同一性,那么“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在某些情況下為假。這是因為,只有那個唯一的蘇格拉底S才具有〈{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這一屬性。如若蘇格拉底失去其同一性,則它就“變成”了另一對象S’,而S’不可能具有那一屬性。由此看來,“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的真必定奠定于蘇格拉底的同一性之上。
其次,根源敏感性的概念似乎掩蓋了前三組反例之所以看上去存在的真正根源。這一根源最直觀地體現于第二組反例中:如果“蘇格拉底不同于埃菲爾鐵塔”這一必然真理展現了蘇格拉底的本質屬性,那么對蘇格拉底之本性的展示和說明將不得不訴諸埃菲爾鐵塔。但直觀上,埃菲爾鐵塔與蘇格拉底毫無關系,即使埃菲爾鐵塔不存在,蘇格拉底的本性也絲毫無損,從而對蘇格拉底本性的說明不應該訴諸這一完全不相關的東西。同樣的無關性也體現在第一組和第三組反例中,蘇格拉底的本性似乎與任何集合的構成性或必然真理并不相關。從而通過訴諸這些不相關的集合和真理來說明蘇格拉底的本質,必將導致反直覺的后果。因此,與其說三組反例的存在源于根源敏感性的差異,還不如說源于這種無關性。
接下來,我將嘗試闡明:“無關性”主要是在本質屬性歸屬的認識論意義上而言的,它的存在與本質屬性在形而上學上的合理歸屬并無沖突。通過區分本質屬性的兩層含義,既可以從認識論上說明“無關性”的直觀根源,也可以保留其在形而上學上的“相關性”,從而表明本質屬性的模態主義解釋在形而上學上仍然成立——盡管在認識論上不盡恰當。第二節的討論將重點闡明這一區分及此區分下的認識論不相關性,以容納范恩反例呈現出的基本直覺。第三節將從正面說明為何在形而上學上而言,看似不相關的本質屬性歸屬實際上具有相關性。
二、兩種本質屬性的區分
關于本質屬性的理解和界定,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就存在諸多爭議。但幾乎沒有爭議的是:本質是一個形而上學概念。一個對象的本質被認為是“使得它成其為自身”、“保持其同一性”、“使之不同于其它東西”的東西。由于一個對象的本質是造就對象同一性和獨特性的根源,并使得它不同于任何其它東西,本質具有某種認識論的意義:它可以使得我們將此對象與任何其它東西區別開來。只要我們把握了對象的本質,我們就在認知上獲得了某種區分性能力——使得任何兩個無論區別多細微的東西都可以得以區分和辨識。
但是,認識論意義上的本質屬性往往并不與形而上學意義上的本質屬性重合。正如要從一群嫌疑犯當中辨別出兇手來,通常我們不必將〈人〉、〈成年男性〉、〈具有雙腳〉等平乏特征納入考慮,需要介入的是〈時間t時出現在現場〉、〈與被害人有利益關系〉、〈作案兇器上有其指紋〉等有效特征。在此情況下,大量“不相關”的本質屬性不必介入,需要介入的僅僅是那些具有區分性意義的本質屬性。
盡管在認識論意義上,很多屬性不必作為辨別性屬性介入,但在形而上學意義上,它們仍然不失為本質屬性。恰如〈人〉、〈成年男性〉、〈具有雙腳〉、〈會說話〉等特征不必介入到對兇犯的辨識中來,但它們仍然是兇犯的本質屬性。于是,我們可以將本質屬性區分為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同一性本質”和認識論意義上的“識別性本質”。在某種意義上,識別性本質是同一性本質的“顯性”構成部分,它在各種認知情形中顯著地成為對象的識別性特征。當然,哪些同一性本質成為識別性本質是取決于不同情形下的不同認知訴求的。
當然,本質的概念在根本上而言是一個形而上學概念,因此談論認識論意義上的本質似乎從一開始就不免顯得有些矛盾。但是,我們認為“識別性本質”這一概念恰當地捕捉了范恩反例下的樸素直覺,使用這一認識論概念對于澄清本質屬性歸屬的直觀恰當性極為貼切。恰如,一位偵探在經過大量探查和深思熟慮后說“兇手一定是人”會多少顯得不恰當一樣,當我們需要通過訴諸本質屬性來辨識蘇格拉底是誰的時候,被告知“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時會顯得不恰當。這一不恰當性正好源于“識別性本質”的缺失。因為盡管這些非識別性本質的歸屬是真的,但卻絲毫無助于相應的辨識要求——他們顯得“無關”!
因此,與同一性本質與識別性本質的區分相對應,我們可以作出“真的本質屬性歸屬”與“恰當的本質屬性歸屬”的區分。本質屬性的歸屬是否為真僅僅取決于被歸屬對象是否在形而上學上具有那一屬性,而本質屬性歸屬的恰當性不僅要求它是真的,還要求這一屬性有助于在認識論上將被歸屬對象“凸顯”出來。于是,關于范恩反例下所呈現出的“不相關性”,我們給出如下解釋:范恩的三組反例所涉及的本質屬性歸屬都是不恰當的,而這種不恰當性正是“不相關性”的源頭。〈是{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等屬性絲毫無助于“凸顯”蘇格拉底的獨特性,繼而有助于將蘇格拉底辨識出來。
實際上,盡管范恩明確將本質概念視為形而上學概念,但在構造其三組反例時,他本人卻時常訴諸認識論的概念來理解本質概念。比如,在蘇格拉底與{蘇格拉底}的例子中,他說“從來無人主張,為了理解一個人的本性,我們必須知道他屬于哪個集合”。①Fine,K.,1994,“EssenceandModality”,in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8.的確,為了理解蘇格拉底的本性是什么,我們不必知道他屬于哪個集合,通常我們只需要知道蘇格拉底具有〈人〉、〈理性〉、〈出生來源〉等屬性就夠了。以我們的術語來說,識別性本質——而不是同一性本質——對于理解蘇格拉底的本性才有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蘇格拉底的本性是什么并不取決于他屬于哪個集合。在形而上學而言,蘇格拉底屬于{蘇格拉底}這一點對于蘇格拉底的本性本身——而不是對于我們對其本性的理解——而言,至關重要!因為,只有蘇格拉底才屬于{蘇格拉底},如果蘇格拉底不屬于{蘇格拉底},則要么蘇格拉底不等同于其自身,要么{蘇格拉底}不等同于其自身。根據集合的外延性原理,{蘇格拉底}不等同于其自身僅當蘇格拉底不等同于其自身。由此,如果蘇格拉底不屬于{蘇格拉底},則蘇格拉底不等同于其自身。由于自我等同性是包括蘇格拉底在內的任何東西的本性,蘇格拉底屬于{蘇格拉底}這一點對于蘇格拉底的本性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或許,范恩及其同情者仍心存疑慮:很難理解為何蘇格拉底在形而上學上的本質性要訴諸某些不相關的對象。看起來,即使埃菲爾鐵塔不存在,蘇格拉底也不失為蘇格拉底啊!有何理由認定必須通過訴諸埃菲爾鐵塔來給出蘇格拉底的本質呢?甚至,只包含蘇格拉底作為唯一構成物的可能世界也是可想象的!在那種情況下,蘇格拉底的本質問題依然存在,盡管不存在任何其它東西與之相區別。既然本質是使得一個東西成其為自身的東西,那么本質必定內在于對象本身。只要搞清楚蘇格拉底的“內部構成”,就可以搞清楚蘇格拉底的本質。既然埃菲爾鐵塔外在于蘇格拉底,在對蘇格拉底的本質刻畫中引入埃菲爾鐵塔必定是荒謬的。
我們認為,這些疑慮源于我們習慣于在某種形象化的意義上來理解本質,即關于本質的說明就是“深入對象內部的觀察和記錄”。這一形象化的理解忽視了本質屬性的某種外在性特征:既然任何對象的個體本質都將此對象與任何其它對象區分開來,那么通過訴諸外在對象與此對象的聯系和區別,個體本質也將得以呈現。將所有不同于蘇格拉底的對象分別帶入“不同于……”,所得到的這些適用于蘇格拉底的必然屬性的邏輯合取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蘇格拉底的本質。這一情況類似于集合的外延性定義:通過枚舉其元素,我們可以定義集合{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盡管此集合作為一個抽象對象與作為具象對象的那幾位哲學家是“無關的”。雖然集合的內涵性定義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那個集合,但在恰當的限制性條件下,外延性定義與內涵性定義是等價的。同樣,盡管關于本質的“內在主義”說明更加簡明,且更有助于推進我們關于對象的認知把握,但相應的“外在主義”說明在實質上是等價的。
在蘇格拉底的例子中,這一等價性的源頭可以濃縮為:任何對象都是自我等同的。恰好是由于蘇格拉底具有自我等同性,因而它具有屬性〈不同于埃菲爾鐵塔〉。這里并不意味著如果埃菲爾鐵塔不存在,就無法給出蘇格拉底的本質。因為〈不同于埃菲爾鐵塔〉僅僅是〈不同于……〉的實例,而后者才是蘇格拉底的本質屬性的充分表達。當埃菲爾鐵塔不存在時,缺失的僅僅是這一本質屬性的一個實例,而不是那個屬性本身。因此,引入〈不同于埃菲爾鐵塔〉來界定蘇格拉底的本質不僅具有某種相關性,而且也不會導致把蘇格拉底的本質依附于埃菲爾鐵塔這一偶然存在物。總之,范恩的三組反例源于某些本質屬性歸屬在直觀上具有的某種“無關性”,而這種無關性又源于“識別性本質”的認識論要求。但在形而上學上,那些看似無關的性質其實具有相關性,它們是“同一性本質”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接下來,讓我們通過某種技術化的手段來更詳細地闡明這種形而上學相關性的基礎。
三、作為對象反身性屬性的本質屬性
自弗雷格以來,語言表達式在形而上學、認識論和語義學上的相關性被逐步揭示出來。弗雷格之謎揭示了共指稱表達式替換可以導致信息內容上的差異。其次,卡爾納普的“內涵-外延”方法揭示了共指稱表達式替換可以導致內涵或意義的差異。而蒯因關于量化納入的論述展示了共指稱表達式可以導致模態性差異。之后,卡普蘭關于“符征”與“內容”的區分和克里普克用于挑戰描述主義的三大論證表明,語言表達式在模態性、先驗性、分析性上具有某種系統相關性。這種相關性正在當代流行的種種二維語義學中以不同的模式加以刻畫和捕捉。
特別的,以先驗性為例,包含索引詞的語句與包含描述語的語句往往具有不同的認識論地位。“我在這里”或許不是一個很典型的先驗真理,但“此時此地正在說出此話的人正在此時此地正在說出此話的人此時所處的位置”卻毫無疑問是先驗真理。后一語句對“我”和“這里”的呈現使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wayofspecification),這一替換更加明確地展示了“我在這里”所具有的某種非經驗性——大概沒有人是基于經驗知識才得以斷定“我在這里”的。索引詞的這一特性被萊辛巴赫稱為“殊形反身性”(tokenreflexivity)。正是由于對“我”和“這里”的表述是通過訴諸那兩個殊形表達式本身而實現的,其非經驗性(和分析性)才能以直觀呈現。
現在,讓我們把這一觀察加以推廣:屬性與對象間的相關性的展示或許也部分受制于對象或屬性的表述方式。在形如“X是Y”的語句中,Y的某些表述方式或許并不適合于展示X與Y之間的相關性,恰如“我在這里”并不適合于展示那個真理的先驗性。如果能夠通過某種恰當的技術手段來改寫“X”或“Y”,或許二者間的相關性便可得以呈現。先以“蘇格拉底是A和B的孩子”為例來說明這一點。如果某人對A或B一無所知,那么他便無法得知蘇格拉底和〈A和B的孩子〉的相關性。如果把“A和B的孩子”替換為“蘇格拉底的父母的孩子”,則“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的父母的孩子”明確展現了對象和屬性之間的相關性。此例中,改寫是通過訴諸對象而實現的——通過訴諸蘇格拉底這一對象本身來呈現〈A和B的孩子〉這一屬性。基于此改寫方式與“殊形反身性”改寫的類似性,我們可以稱之為“對象反身性”(object-reflexive)改寫,從而把以此方式加以改寫和表述的屬性稱之為“對象反身性屬性”。
把這種改寫方式運用于范恩的反例,我們可以嘗試系統地構造關于屬性的對象反身性表述,以此來展示對象反身性屬性與對象的內在相關性。〈{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這一屬性的表述可以替換為“包含蘇格拉底為唯一元素的集合的唯一元素”,后者表達的對象反身性屬性顯然與蘇格拉底這一對象是相關的。從而,“蘇格拉底是包含蘇格拉底為唯一元素的集合的唯一元素”不僅是必然的,而且,鑒于蘇格拉底這一對象同時介入對屬性的界定,此必然真理的對象和屬性呈現出直接相關性。相比較而言,之所以在范恩的原始例子中這種相關性看似缺失,是因為當那一屬性通過“{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加以表述時,似乎介入此屬性定義的是{蘇格拉底}這一集合。尤其是,集合被視為典型的抽象對象,從而那一屬性的界定最終僅僅訴諸某種抽象對象。進而,由于蘇格拉底是具象對象,它與通過抽象對象加以界定的屬性之間必定沒有相關性。
但是,盡管在形而上學上而言,作為抽象對象的{蘇格拉底}是基本對象,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無法以其它的基礎對象加以定義。特別是,盡管{蘇格拉底}是抽象對象,但它并不是一個任意的抽象對象,而是僅僅包含蘇格拉底這一具象對象——而不是包含其它任何對象——為唯一元素的抽象對象。這種非任意性恰好是我們加以捕捉的那種相關性的真正基礎。那么在埃菲爾鐵塔的例子中,是否存在同樣的非任意性呢?
不像{蘇格拉底}的例子,〈不同于埃菲爾鐵塔〉似乎無法直接通過蘇格拉底加以界定。確實,如果竟然可以做到這一點,那么大概任何對象都可以通過任何其它對象加以界定了。為了展示蘇格拉底與〈不同于埃菲爾鐵塔〉間的關聯性,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當把“埃菲爾鐵塔”替換為“蘇格拉底”時,“蘇格拉底不同于埃菲爾鐵塔”由真變假;而將之替換為任何有別于蘇格拉底的對象名稱時,它都為真。
因此,似乎可以認為,“蘇格拉底不同于埃菲爾鐵塔”之為真的根源在于如下一般性真理:“蘇格拉底不同于任何有別于蘇格拉底的東西”。由于埃菲爾鐵塔是“有別于蘇格拉底的東西”這一概念的實例,可以說“蘇格拉底不同于埃菲爾鐵塔”也僅僅是“蘇格拉底不同于任何有別于蘇格拉底的東西”這個一般性真理的實例。從而,〈不同于埃菲爾鐵塔〉也僅僅是〈不同于任何有別于蘇格拉底的東西〉這一屬性的一個實例,而后者恰好是一個對象反身性屬性。因此,對象反身性的改寫方式同樣適用于這一案例:〈不同于任何有別于蘇格拉底的東西〉與蘇格拉底的關聯性是十分明確的,而通過成為此屬性的一個實例,〈不同于埃菲爾鐵塔〉也與蘇格拉底關聯了起來,盡管我們不得不說這一聯系多少顯得有些“間接”。或許,這一間接聯系性也正是直觀上的無關性的根源。
最后,讓我們嘗試將這一改寫技術運用于范恩的第三組反例。“蘇格拉底是如此這般使得2+2=4”所歸屬給蘇格拉底的屬性〈如此這般使得2+2=4〉看起來與蘇格拉底是毫無干系的。因為我們可以將“2+2=4”替換為任意必然真理,從而獲得相應的必然屬性,但蘇格拉底似乎無法與基于任意必然真理的任何屬性都具有關聯性。然而,首先必須注意到的是,“蘇格拉底是如此這般使得2+2=4”甚至并不是一個真語句。通常而言,必然真理被認為在邏輯上等價于某種關于可能世界的全稱量化。在可能世界語義學的當代運用中,有不少人認為在語義學上引入不可能世界(impossibleworlds)的概念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①Berto.F.,2013,“Impossibleworlds”,inStanfordEncyclopediaofPhilosophy.不可能世界的特征性標志是它使得某些必然真理為假。盡管“2+2=4”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為真,但它在那些違反算術基本定律的不可能世界中卻為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引入不可能世界,本質的模態主義解釋仍然成立。因為只要我們把必然真理看作是在所有可能世界為真的真理,而不是在所有世界(可能或不可能)為真的真理,本質屬性仍然可被定義為必然屬性。因此,范恩的第三組反例的完整表述應該是“蘇格拉底是如此這般使得在可能世界中2+2=4”。接下來讓我們說明〈如此這般使得在可能世界中2+2=4〉這一屬性如何與蘇格拉底是相關的。
在關于不可能世界的種種刻畫中,真矛盾(truecontradictions)的存在被認為是不可能世界的典型特征。存在某些蘇格拉底既是哲學家又不是哲學家的不可能世界。具有矛盾屬性的不可能世界對象與不具有矛盾屬性的可能世界對象顯然是不同一的。亦即,不可能世界是違反對象自我等同性原則的世界,而可能世界是遵循對象自我等同性原則的世界。把此刻畫運用于范恩的例子,“蘇格拉底是如此這般使得在可能世界中2+2=4”等價于“蘇格拉底是如此這般使得在遵循對象自我等同性原則的世界中2+2=4”。由于蘇格拉底即是遵循自我等同性的對象之一,范恩的例子進一步等價于“蘇格拉底是如此這般使得在包括蘇格拉底的所有對象都自我等同的世界中2+2=4”。現在,其表達的必然屬性〈如此這般使得在包括蘇格拉底的所有對象都自我等同的世界中2+2=4〉部分地通過蘇格拉底加以定義,從而使得它與蘇格拉底直接關聯起來。
如前兩組案例,這里所呈現出的關聯性多少顯得有些松散,甚至平乏。這毫不奇怪,因為“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的唯一元素”、“蘇格拉底不同于埃菲爾鐵塔”和“蘇格拉底是如此這般使得2+2=4”這三個真理本身就顯得足夠平乏。根據我們關于語義內容的常識看法,一個語句斷定的內容越平乏,那么它所揭示的對象與屬性間的聯系就越少、越空洞。當范恩給出的必然真理其本身就已經足夠平乏時,我們怎能期待相應的關聯性不那么平乏呢?無論如何,不可否認,在形而上學上而言,蘇格拉底的確與那些屬性具有聯系。這僅僅是因為那些屬性是部分地通過蘇格拉底本身而加以界定的。
綜上所述,針對本質的模態主義解釋,范恩的挑戰并不成功。他所提供的幾組典型反例之所以具有直觀合理性,是因為混淆了我們稱之為“同一性本質”和“識別性本質”的兩種本質觀念。認識論相關性往往比形而上學相關性的要求更高,因此某些同一性本質屬性并不是識別性本質屬性。范恩的幾組反例所提供的必然屬性都不是識別性本質屬性,但卻不失為同一性本質屬性。為了明確展示這些本質屬性與對象的相關性,我們引入了“對象反身性”改寫技術。通過將屬性的表述轉化為涉及對象本身的表達方式,我們看到,范恩反例中的必然屬性均與其對象具有某種內在關聯性。這一關聯性的存在從根本上破除了范恩反例中的“無關性”假象,從而成為我們繼續堅持模態主義解釋的決定性理由。
(責任編輯 任 之)
B089
A
1000-7660(2015)03-0070-0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傾向性屬性的反事實條件句表達研究”(13YJC720014)、東華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科學定律的反事實條件句表達”(13D111017)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何朝安,(上海201620)東華大學人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