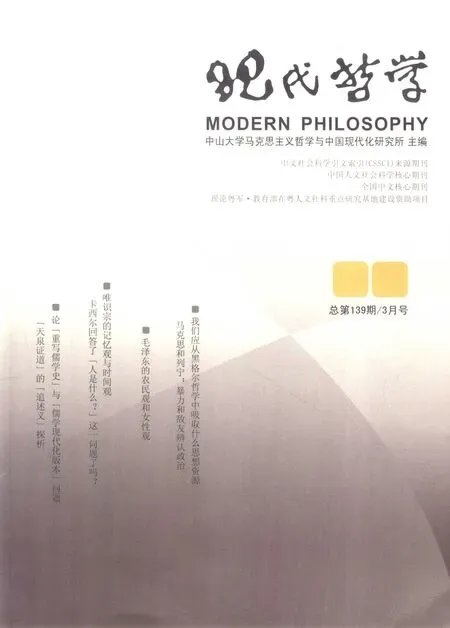論黃道周的宋明理學觀
許 卉
論黃道周的宋明理學觀
許 卉*
針對晚明理學發展的困境和危機,黃道周主張調停朱陸、會通朱王來彌合理學的內部沖突,以期將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整合為統一的思想體系。他認為朱陸兩家學旨本同,咸歸于孔孟之道,尊德性與道問學雖有差異,但應兼重兩者。他提出不同于朱子的圣學傳遞譜系,認為陽明之學也是承續孔孟圣賢學統的嫡親之系。對陽明后學的流弊,黃道周不遺余力地進行批判,主張以周孔《六經》之學救正當時思想界的空疏、蕩越之風,希冀以經典文獻為根本,重建理學的學理根基。
黃道周;朱陸之辯;陽明之學;陽明后學
晚明時期,統治思想界數百年的宋明理學陷入空前危機。朱陸之爭引發的理學內部沖突,并沒有因為宋以后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而消弭;明中期王學的異軍突起,在挑戰程朱學正統地位的同時,更加劇了理學的內部緊張;而王學末流的空疏、蕩越,不僅消解了理學家對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削弱了儒學禮教維衛社會秩序的功能,而且威脅到理學作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在這種局面下,如何化解理學內部的分歧與沖突,挽救已呈頹勢的理學大廈,維護和重建儒學在社會中作為思想和價值權威的神圣地位,成為擺在明末思想家面前的歷史性課題。面對這一歷史課題,與劉宗周齊名的明末大儒黃道周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主張調停朱陸、會通朱王,廓清陽明后學的流弊,回歸《六經》儒學。黃道周對宋明理學的反思,既是對明末理學危機的回應,也是明中期以來理學內部朱王互動的新發展和新動向。
一、調停朱陸,整合理學內部分歧
就黃道周的學路淵源來看,門人洪思稱“黃子善朱子”(《黃漳浦集》卷21《王文成公集序》)。他七歲就懂得《綱目》精神,懂得“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黃漳浦集》卷首《漳浦黃先生年譜》)。黃道周一生對朱熹都很尊崇,對北宋五子、王陽明等人都有過指摘,唯獨對朱熹沒有過明確批評,且對朱子之學多加贊揚,認為其學醇厚無弊。《大滌書院三記》載:“兩日諸友先后間至,剖析鵝鹿疑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泛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抵牾。然而元晦醇邃矣,由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由仆之言,靜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由元晦之言,拾級循墻,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崖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黃漳浦集》卷24)他高度贊揚朱熹,稱“元晦醇邃”,稱其學問百世無弊,但這并不代表黃道周“確守朱熹之道脈而獨溯宗傳”(《黃漳浦集》卷首《道光五年禮部奏表》)。在當時王學籠罩思想界的氛圍下,黃道周尊崇朱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思王學與復歸程朱理學的意蘊。但黃道周并非拋棄王學而復歸程朱理學,他對理學的態度不是完全地推崇接納,如洪思所稱“黃子之學,大則周、孔,小則伊、孟,不盡崇考亭”(《王文成公集序》)。黃道周的基本立場是力求客觀全面地看待朱陸兩家之學的長短,是其所長,非其所短,兼而采之。
首先,在朱陸之辯的起因上,黃道周持有客觀態度。《朱陸刊疑》稱:“伊兩家辯論不自鵝湖而始,卻是陸子美開端明刺濂溪不是,晦翁尊崇濂溪,見子美詆濂溪無極太極為老氏之學,遂生異同。其后,子壽、子靜原本伯兄,與晦翁格物致知之說爭流分源,學者從之,遂分徑路。其實陸氏淵源本自不錯,子靜識見太朗,氣岸未融,每于廣坐中說晦翁,又是一意見,又是一議論,又是一定本。晦翁亦消受不過,所以前面與子美爭論無極,止說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足矣!此極和平中間又露出淺狹邪诐字面,三陸亦如何消受?”(《黃漳浦集》卷30)黃道周認為朱陸之辯起于無極太極之辯。由于朱熹尊崇周敦頤,見陸氏兄弟攻擊周敦頤的學說,與之辯駁,維護周子學說,兩家觀點、立場不同,所以產生了分歧。此后,朱陸又在為學之方上意見相異,即“道問學”與“尊德性”的不同取向。黃道周肯定雙方的辯論是學術上的交流探討,但不贊同兩家互相指責、不能求同存異的態度。在無極太極之爭上,黃道周實際偏向陸氏。他稱:“無極之話更不消說。以老子明目冠于《系辭》之上,尚是小處,即使后人不辯,亦是理路難行。”(同上)
其次,他對朱陸之學進行評價時持有客觀態度,既看到兩家之學的優勝之處,亦指出兩者的不足之處。對于朱子之學,雖認為其百世無弊,但指出“元晦之領此邦,亦五百年矣,未有踵元晦而起者,考其所由,以傳注之說不足以服才士之心”(《黃漳浦集》卷22《尊經閣序》)。對于陸學,黃道周雖有指摘,但仍對其有贊言。他認為陸氏兄弟之學本于孟子,其淵源于孔孟,自是承接圣學一路,“可惜當時晦翁強護濂溪一面,使子靜知愛知敬之說不甚昌明耳”(《黃漳浦集》卷30《子靜直指》)。他稱贊陸學:“子靜說圣賢淵源止在愛敬二字,體貼分明,用之不盡,知之為致知,格之為格物,此處豈有病痛?”(同上)“陸象山論學以孩提愛敬可廢《六經》,雖有激揚已進之論,其大指不失于立身、終始明堂亨帝之說。”(《黃漳浦集》卷21《〈孝記〉序》)
黃道周將兩家之學與孔子圣學相比較:“陸氏專主德性,不入宮墻,只是貧儒,自寶其身。朱氏兼道問學,若見孔子宮墻,猶是當階辦事。”(《榕壇問業》卷4)他認為在孔子圣學面前,兩家之學仍須完善,同時批評了兩家之學帶來的弊病,“諸儒所說尊德性者,皆看性,不看德;諸儒所說道問學者,皆看學,不看問字也”(《黃漳浦集》卷30《子靜直指》)。雖兩家之學有弊病,但皆不遠圣學,“如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瑕舋,亦皆不遠于圣門之學”(《黃漳浦集》卷30《朱陸刊疑》)。
在對朱陸之學各自評論的基礎上,黃道周認為:就朱陸兩家學問而言,其學旨本同,咸歸于孔孟之道,不應起爭執;就為學之方而言,尊、道的不同取向確有差異,但方法論上的差異是正常的,不應各執一隅,而應兼重兩者。他稱:“論學問則學問同歸,論功夫則漸頓殊候。形色之與天性,文章之與性道,總是一物,但下手駐足,確有兩候,朱、陸兩公不合自為異同耳。”(《黃漳浦集》卷30《格物證》)“末宋朱陸分馳,鵝湖門人強半逃空,考亭門人依然傳注,然亦是傳習差池,非云朱藍異質也。”(《黃漳浦集》卷30《書示同學二十一則》)黃道周認為宋末以后陸學向“空”走去,朱子之學以傳注為主,兩家之學在傳習承續上雖出現不同,但兩種學說本身無優劣之別。
由于兩家差異不是根本性的不同,而是方法上的選擇不同,因此為學之方的差異不能成為區分兩家之學的根本尺度,且方法上的綜合和兼重必然有益于兩家之學。黃道周稱:“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瑕亹,亦皆不遠于圣門之學。化子靜以救晦翁,用晦翁以濟子靜,使子靜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滯于沈潛,雖思孟復生,何間之有?”門人朱士美見此論而問:“此莫近于調停否?”黃道周回答:“天下事惟邪正兩家調停不得,既是一家,何必苦自同異?”(《黃漳浦集》卷30《朱陸刊疑》)
黃道周肯定尊、道功夫,認為尊、道雖為兩種功夫,其實合一,只是在常人眼中不同。“自夫子看來,何所不合?自我輩看來,自然有德性、問學、尊道之殊。”(《榕壇問業》卷14)他強調尊、道功夫的重要性:“如無尊、道功夫,任他常無、常約、常虛不墮釋老窖中,只是空山樸自,何時得到君子位上?”(同上)若忽視尊、道功夫,則會有佛老之學的流弊。“釋老只是不學,無尊道功夫,便使后來譸張為幻。如當時肯學踐跡入室,豈能貽害至于今日?”(同上)
黃道周雖主張兩種方法兼重,但其思想中有受王學影響的一面。關于尊之和道之的先后,他將尊之的功夫放在第一位上,堅持德性在先、問學在后:“德性者,問學之所由道也。尊經以道文史,尊德性以道問學,猶尊任督以道營衛,尊山川以導畝澮,尊斗樞以導星月也。”(《黃漳浦集》卷22《尊經閣序》)這種德性第一的觀點亦體現在先驗價值和經驗知識并存的情況下,更強調先驗價值的第一性:“學者須先認至善,認得至善,自然知止。”(《榕壇問業》卷16)德性第一的觀點也表現在黃道周認為踐履必須是德性明確之下的躬行,學人須先“識仁”,只有先立乎其大,才能于顛簸流沛之中而不會有所偏離,且不改追求。他稱:“如識仁者,中間豈有欲惡取舍?豈有富貴貧賤?豈有終食造次顛沛?”(《榕壇問業》卷7)黃道周雖認為應該“尊德性而后道問學”,但他不同于陸氏之專主德性,而是強調在順序上有先后、在程度上無輕重,認為“尊是至善寶座,道是格致威儀”(《榕壇問業》卷4),并提并重。
簡言之,在朱陸異同上,黃道周主張同為根本、異為枝葉,主張調停、打破門戶而會通朱陸,同歸圣學之門。同時,這一調停具有明顯的王學特點,主張德性第一,尊、道兼重。
二、道統視野下的王學定位
對于陽明心學,黃道周門人洪思認為:“黃子學善朱子,素不喜文成良知之說者。”(《黃漳浦集》卷21《王文成公集序》)這一看法值得商榷。其實,黃道周對王陽明的人格、思想和事功都持尊崇的態度。《王文成公集序》說:“明興,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絕學、排俗說、平亂賊、驅鳥獸。大者歲月,小者頃刻,筆致手脫,天地廓然,若仁者之無敵。自伊尹以來,乘昌運、奉顯績,未有盛于文成者也。”他認為王陽明提出心學,使得古來學脈不至于斷絕,開辟了一個不同于埋頭科舉考試、專注形而下學問的理路,引導了一個追求形而上的、心靈澄凈的取向。而且,王陽明的文治武功自伊尹以下,千百年沒有人能與他相提并論,“孟子云‘若夫成功則天也’,如文成者才可說得參贊”(同上)。
對于陽明之學的來源,黃道周認為:第一,陽明心學源于圣學經典,是王陽明對《大學》《中庸》做了一番重新詮釋而確立的,是源于孔門圣學的儒家思想。他稱:“漢初儒者把《大學》《中庸》置禮書中,是圣門奧義。今人抽出以為心學,如一方磚磨作圓錢,又于矩中再變回去,是樂律中黃鐘子聲五變之后,再起清音也。”(《榕壇問業》卷3)第二,陽明之學來源于踐履。《書王文成公碑后》寫道:“諸生因問:‘文成良知之說著于海內,如何說所以得此未之或知?’某云:‘文成自家說從踐履來,世儒都說從妙悟來,所以差了。’唐生問:‘如何是踐履來?’某云:‘伊歷過許多湯火,豈世儒口耳所就?’”(《黃漳浦集》卷23)可見,黃道周認為陽明之學來自于踐履而非妙悟,直指陽明后學輕工夫的流弊。
對于陽明之學的地位,黃道周借助道統來定位。他認為王陽明是延續圣賢之學的嫡親之系:“孟軻崎嶇戰國之間,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于伊尹……孟軻而后可二千年,有陸文安。文安原本孟子,別白義利,震悚一時。其立教以易簡覺悟為主,亦有耕莘遺意……文成當宋人之后,辭章訓詁,汨沒人心,雖賢者猶安于帖括,故明陸氏之學,易簡覺悟,以使人知所返本。”(《黃漳浦集》卷21《王文成公集序》)不同于朱熹的道統譜系,黃道周提出了新的圣學傳遞之脈,認為孟子之學接承周孔,孟子之后,陸九淵以孟子的思想為基礎,注重發明本心,之后是王陽明明陸氏之學,主張致良知。可見,黃道周對陽明之學在傳承圣學方面的肯定。同時,他贊陽明之學“易簡覺悟,以使人知所返本”乃肯綮之語。
黃道周亦贊揚了陽明之學的功績:“吾漳自紫陽蒞治以來,垂五百年,人為詩書,家成鄒魯,然已久浸淫佛老之徑。平和①《王文成公碑》稱:“我太祖定天下既百五十年,吾漳郡邑始有定制,而平和一縣為文成建置之始。”(《黃漳浦集》卷25)獨以偏處敦樸,無诐邪相靡,其士夫篤于經論,尊師取友,坊肆貿書,不過舉業傳注而已,是豈《庚桑》所謂‘建德之國’,抑若昌黎所云‘民醇易于道古者乎’?”(《黃漳浦集》卷25《王文成公碑》)他以漳州地區為例,稱其地受朱子之學的覆被,人人習詩書、遵從禮儀,但依舊受到佛老的浸淫,使得圣賢之學不盛;而平和縣作為王陽明建置之始,受到陽明之學的影響,風氣敦厚樸實,沒有诐邪之說蠱惑人心,士人專注于經論,尊師重道,舉業傳注不離圣學。他不僅肯定陽明之學的功績,而且對其學持有殷殷之望,認為陽明之學能夠清正源、辟佛老,是承遞朱子之學的圣賢之學,可以說是朱子之學的脈流。他稱:“人學與治亦何常?各致所應致,治所應治者,皆治矣。即使山川効靈,以其雄駿苞郁者,暢其清淑,令譽髦來彥泝文成之業,以上正鵝湖,下鉏鹿苑,使天下之小慧聞說者,無以自托,是則文成之發軔,藉為收實也。于紫陽祖禰,又何間焉?”(同上)可見,黃道周對陽明之學并沒有采取激烈批評的態度,認為陽明之學亦是圣賢之學,是朱子之學的延續和救正,他甚至稱“陽明全是濂溪學問,做出子靜事功”(《黃漳浦集》卷30《子靜直指》),將陽明之學和理學開山之人周敦頤、心學創始之人陸九淵的學思等同。這種看法很有創見,因為他看到陽明學其實是從朱子學的語境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是宋代理學發展的內在分化和嬗變,是在理學中孕育產生并吸取了陸學的精髓而構建起來的,是朱陸之學的兼綜和會。這也是黃道周將陽明學和朱子學交融互匯的一個思想前提。
綜上可見,黃道周并非如洪思所稱“素不喜良知之學”,而是對王陽明多有推崇和贊揚,并無激烈的批評。實際上,黃道周“不喜”的是陽明后學中王畿、李贄、羅汝芳等人的學說。
三、批判陽明后學與回歸《六經》儒學
陽明后學在晚明思想界和社會上影響甚巨,其對儒家修養功夫的輕忽、對傳統禮教的蔑視,背離了理學精神,對社會道德秩序也造成了很大的沖擊。這引起了黃道周等學者的憂慮,并對王學末流進行了尖銳的批判。《王文成公碑》稱:“今其學被于天下,高者嗣鵝湖,卑者溷鹿苑,天下爭辨又四五十年,要于文成原本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黃漳浦集》卷25)他認為陽明后學已經超出了陽明心學的范圍,偏離了陽明之學的根本,不僅背離了陽明之學的意旨,而且其在當時社會上造成了消極影響。黃道周稱:
今之君子,為利以考文,為文以飾行。茍取習俗,以誣圣賢,以愚黔首,以誑天子。其稍有意義者,選妙征雋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曉,則里巷之所周譬,揆于古今治忽善敗,則蒙然末視。見之而喜,去之不思,自是而學問之道可廢也。夫茍有令捐圣賢,塞道德,則止猶是制也,而顯棄其教,以仁義為迂衺,高堅為僻昧,則閭巷白望者皆可皐比自命,粉靘而耀先王之業。即使天子一旦顧盼,詢治忽之故、善敗之紀,亦將囁咿舉所熟習,丘蓋聊且以對,則是圣賢所教人仁義文行,為權利貿市者逋藪也。且無論圣賢旒冕在上,但使其妻子董之,見是良人者,脫冠帶,弛灶下。其情態言說,具僮姁之所料得,而出巍冠,坐高堂,衡量天下,無敢難者;退而私怪,此其方法豈可使兒孫復習之乎?(《黃漳浦集》卷21《冰天小草自序》)
黃道周批評王學后學的流弊,如重利、不尊圣賢、虛玄、蕩越、不學、無經世致用之功等,認為它們造成了對傳統禮教和道德的沖擊和破壞,對于圣學的傳承極為不利。
具體來說,黃道周對陽明后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龍溪之學和泰州之學。他指出:“王汝中、李宏甫之言始復重于天下。歸王之言幻,歸李之言蕩,于是勃溪溲溺、不則不潔之言皆形于文章,而文人才士始不復能束修以自師于天下……然知為王汝中、李宏甫則亂天下無疑矣。”(《黃漳浦集》卷23《謝光彝制義序》)黃道周認為王畿之言以“幻”為主,其談玄說悟,流于空寂,無別于佛老之說;李贄之言則“蕩”,其說任由人的自然情欲流瀉而不加約束。王、李兩人倡言非圣無法之說,不以圣賢之說為尊,使士人思想混亂、沒有取舍標準。鑒于此,黃道周對王畿、李贄持全然的批判態度:“天下人各有心眼,那個不知龍溪、溫陵說吃不得?”(《榕壇問業》卷1)他對于泰州學派的羅汝芳、周汝登的態度則緩和一些,稱“如羅近溪、周海門近來諸公,引人入悟,初亦不離仁義禮樂,只要自家卓爾高堅,雖造屢空,不墜空界”(同上),肯定他們仍立足于仁義禮樂,沒有完全脫離孔孟之學的根莖。
此外,黃道周對于陽明后學不重修持和功夫的取向進行了重點批判。他認為,要體認本體,絕不能脫離功夫,即使是圣人也需要工夫。他稱:“圣人言誠,要與天地合德;言明,要與日月合明。此理實是探討不得。周公于此仰思,顏回于此竭才,難道仲尼撒手拾得?圣人于此,都有一番嘔心黜體工夫,難為大家誦說耳。做圣賢人,不吃便飯。”(《黃漳浦集》卷首)黃道周批評當時學人不重修持,稱:“圣賢相引,只是無盡工夫,大禹不自滿假,求仁無怨,欲仁不貪,如就克伐怨欲上消磨光凈,去仁何遠?……參看今人都說不行四者,還有四者根在。又說在外面打迭,不在里面磨礱,難道四者根株尚在外面乎?”(《榕壇問業》卷2)他批評陽明后學放棄工夫、尊崇自然的主張,稱:“如良知不由致知,此良究竟何至?……其言自然者,不過不學不慮一段而已,亦是不學不慮而良,不是不學不慮才訓作良也。”(《榕壇問業》卷5)黃道周認為,良知由致知而來,如果放棄致良知的功夫,良知便無由而至。他指出,不學不慮是良的性質,但不學不慮不等同于良,泰州學派以“不學不慮”來認取良知是對良知的錯誤理解。
黃道周在對王學末流進行批判的同時亦尋求補救之方,并將目光落到《六經》,以期用經典文獻的權威性來改變當時輕視知識、高蹈凌虛的風氣,使得道德和真理的依據回歸到古代經典。他極為重視古代經典,認為古代經典文獻是道的載體:“虞夏以前,宗黃而祖天,故二典之言皆準于天,準天而《易》《禮》《樂》之道出焉。虞夏以后,宗夏而祖人,故誥誓之言皆準于人,準人而《詩》《春秋》之道出焉。故《易》《禮》《樂》《詩》《春秋》者,此百世而不復改也。《易》立于上,《禮》《樂》行于中,《詩》《春秋》者經緯而出之。”(《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論》,《黃漳浦集》卷14)《六經》體現了天道根本,亦是圣人之學。《經綸天地之謂才論》云:“周公知五百而后必有起于吾土、光大吾緒者,故于《易》《詩》《書》《禮》《樂》《春秋》之道,皆不深竟其說,至仲尼而后暢之……故仲尼之學存于禮樂,其識在于《易》,其生平所參贊、手口拮據盡在于《詩》《書》《春秋》。《易》《禮》《樂》《書》《詩》《春秋》者,圣人之所為學也。”(《黃漳浦集》卷12)黃道周重視《六經》的態度亦體現在他對經典知識的高度推崇上,認為“凡學問自羲、文、周、孔而外,皆無復意味……須知羲、文、周、孔止是為造物掌記,至其自家位置,直與造物一般”(《黃漳浦集》卷30《書示同學二十一則》)。《六經》作為知識和思想的根本依據具有絕對性,因此黃道周認為在讀書上要以經書為先。他以孔子為例,稱:“仲尼之所操者,經也。經起而后緯生,緯生而后文作;經正而后權立,權立而后義起。故德性者,問學之所由道也。尊經以道文史,尊德性以道問學,猶尊任督以道營衛,尊山川以導畝澮,尊斗樞以導星月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黃漳浦集》卷22《尊經閣序》)
黃道周對儒家古代經典的強調不僅體現了其希望改變當時學風和糾正社會風氣的意圖,亦有其重建儒學的努力。在晚明階段,無論是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還是高揚自由和心靈自覺的陽明后學都無法承擔起整頓當時思想界秩序、傳承圣學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黃道周主張回歸經典文本,稱“吾將救之于《六經》”(《黃漳浦集》卷21《冰天小草自序》),借助經典文獻在儒家譜系中的特殊地位和權威性,來限制王學思想體系中心體對道德規范的瓦解,控制其發展為情識而肆的傾向,并達到整理知識與思想的秩序、重建思想的權威的目的。
概括而言,黃道周對宋明理學的反思具有鮮明的客觀性、綜合性特征。他在尊崇朱子學的同時,對陸氏心學多有肯定,極力調停、彌合朱陸異同;對陽明之學,黃道周更是從儒家道統譜系的高度給予肯定,認為陽明之學亦是承遞朱子之學的圣賢之學,是朱子之學的流脈。顯然,黃道周想通過調停朱陸、會通朱王來彌合理學的內部沖突,將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思想體系。對陽明后學的流弊,黃道周不遺余力地進行批判,主張以周孔《六經》之學救正當時思想界的空疏、蕩越之風,希冀以經典文獻為根本重建理學的學理根基。黃道周的以回歸經典文本來重建儒學思想權威的路數,對明末清初經學復歸運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責任編輯 楊海文)
B248.99
A
1000-7660(2015)03-0113-05
許 卉,陜西戶縣人,哲學博士,(石家莊050051)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