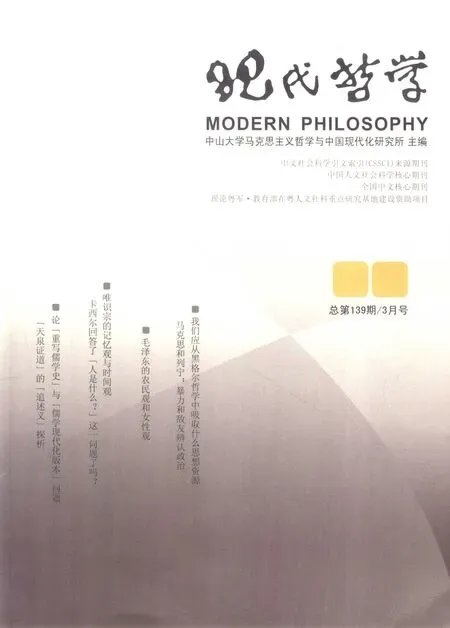比較哲學視野下的孟子人性論研究——以安樂哲的孟學思想發展為主線
李文娟
西方學術界活躍著這樣一批哲學家:他們有著長期的跨文化交流經驗,癡迷于中國哲學研究,為中國哲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漢學家”。基于對學術的嚴謹態度,恰當地說,我們應該稱之為“比較哲學家”。相對于“漢學家”而言,“比較哲學家”的優勢在于有著專業的哲學訓練和學術背景,可以對中國哲學經典與詞匯進行相對客觀的翻譯、梳理、轉化和提升,從而增強了中國哲學的理論高度和哲學地位。在中國古代哲學領域,孟學研究成為比較哲學家們近年來研究的焦點,他們對孟子人性論進行了長期而熱烈的討論,并著書立說,積累了一批優秀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安樂哲 (Roger T.Ames)的觀點,他高度的學術創見是對唐君毅、葛瑞漢 (A.C.Graham)等前輩理論學說的進一步詮釋,也是孟學研究的一個創新和突破。安樂哲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但是其以文化發展觀來理解孟子之“性”的哲學論斷也引來多方分歧與爭議。本文試圖以安樂哲的孟學思想發展為主線,梳理近年來比較哲學界關于孟子人性論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礎上做出進一步的思考。
一
通過考察相關資料,我們會發現,有的學者把安樂哲1991年發表的《孟子的人性概念:它意味著人的本性嗎?》一文看作是對其老師葛瑞漢教授的觀點提出的質疑①楊澤波:《性的困惑:以西方哲學研究儒學所遇困難的一個例證——〈孟子心性之學〉讀后》,氏著:《孟子性善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79頁。。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葛瑞漢在1967年發表的《孟子人性理論的背景》文章中傾向于把孟子所言的“性”翻譯為“nature”(本性)②[英]葛瑞漢:《孟子人性理論的背景》,《孟子心性之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2頁。。但是,被大家忽視的是1989年葛瑞漢出版了他的平生總結性著作《論道者》,對自己的早期觀點做出了修正。他指出:“在我的早期著作中,通常把告子的‘生之謂性’譯作‘It is inborn that is meant by nature’。的確,晚于孟子一個世紀的荀子正是用與生俱來定義‘性’……孟子并不是給這個詞賦予他所喜歡的意思,而是按當時流行的意義精確地使用它,這不太切近于‘nature’。當然,這不是說必須放棄‘nature’去尋找更準確的英文對應詞。英語中并沒有準確的對應詞;如果說我們已經翻譯了許多重要的中國術語而無爭議的話,那只是因為在現有的書籍限度內這種區別沒有暴露出來。”①[英]葛瑞漢:《論道者》,張海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46頁。從這里可以看出,把孟子之“性”譯為“nature”并非切合葛瑞漢的本意。同時,安樂哲也并未表達出針對葛瑞漢的意思,他開篇即說:“‘性’,通常被譯為‘nature’,盡管它是傳統儒家思想中人們研究最多的哲學概念之一,但我并不認為它是被理解的最透徹的。這里所要論證和解釋的是,在我看來,目前我們對‘性’的理解存在著根本的不足,特別是當它指人 (human being)的時候。”②[美]安樂哲:《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家與道家》,彭國翔編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1頁。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得出更加客觀的評價:與其說是安樂哲對葛瑞漢的觀點提出質疑,不如說他是對傳統觀點做出的挑戰。
事實上,在安樂哲關于孟子人性論這一問題的思想發展中,尤其對“人性”及其內涵的理解上,有兩個人的觀點對其影響最大,即唐君毅與葛瑞漢。
唐君毅關于孟子人性論的洞見,集中于新亞研究所1968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一書。事實上,1946年他在《文化先鋒》雜志發表的論文《孟子性善論新釋》③唐君毅:《孟子性善論新釋》,《文化先鋒》1946年第4期。,已經可以看出他的學術立場。“依吾人之意,以觀中國先哲之人性論之原始,其基本觀點,首非將人或人性,視為一所對之客觀事物,來論述其普遍性、特殊性,或可能性等,而主要是就人之面對天地萬物,并面對其內部所體驗之人生理想,而反省此人性之何所是,以及天地萬物之性之何所是。”④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第3頁。可見,唐君毅淡化了傳統人性概念中的生存色彩,而強調人在實現人生理想過程中的內在體驗性。他進一步指出:“凡吾人視事物為所對,而論其種類性,皆指一定之性……然吾人若由人之面對天地萬物與其所體驗之內在理想,而自反省其性之何所是時,是否可言人有定性,則大成問題。因人之所面對天地萬物與理想,皆為變化無方者。則人之能向往理想,能面對天地萬物之性,亦至少有一義之變化無方。中國思想之論人性,幾于大體上共許之一義,即為直就此人性之能變化無方處,而指為人之特性之所在,此即為人之靈性,而異于萬物之性之為一定而不靈者。”⑤同上,第4頁。在此,唐君毅認為人性具有的變化性和不確定性,并指出其源自于人的靈性。從唐君毅的其他論述來看,他多次強調心性有一個自我發展的過程,也會因外力的影響而產生變化,而非與生俱來的被給定的固有的狀態。這一觀點對傳統的詮釋構成了挑戰。安樂哲評價說,唐君毅識別出人性最顯著的特征,作為創造性變化的不確定的可能性是準確的;他把在古代中國哲學家中有關“性”的意義之討論從現代心理科學中區分出來,正是這種存在主義方案,才基本區分了古代中國儒家“性”的概念的特征⑥[美]安樂哲:《孟子的人性概念:它意味著人的本性嗎?》,《孟子心性之學》,第100頁。。
葛瑞漢的相關論述延續用一種發展的眼光去看待“人性”。通過對中國傳統的“性”概念的考察,葛瑞漢的第一直覺是:“性”的能動力量沒有受到充分的注意。他進一步說明:“性”由“生”而來,構成“生”的純化,它包含著出生、成長、最終消亡這一生命存在的完整過程。作為對早期著作的一個修正,他提出:許多諸如“性”這樣的早期中文概念,在最近的英文中找不出與之相對應的詞匯,因為原來中文中更加動態的含義經常會被丟失。葛瑞漢論證說:“那些討論‘性’的早期中國思想家似乎很少想回到其本源的事物的固定屬性……特別是孟子,似乎從來沒有回顧過出生,而總是前瞻一個連續成長的成熟。”⑦A.C.Graham,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Albany,New York:SUNY Press,1990,p.8.對葛瑞漢來說,在孟子用來刻畫“性”這個概念的隱喻中,“性”的動態力量是顯而易見的。他認為,孟子用發展的概念理解“性”,這說明它需要養育而避免干擾,正如牛山之木的譬喻,包括生長的樹木和動物、正在成熟的稻谷以及流動著的水⑧Ibid.,p.43.。在進一步把“性”的動態含義擴展到人時,葛瑞漢將早期將“性”理解為“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東西”的觀念,修改為涵蓋人的存在的整個生涯。正因為如此,安樂哲深受啟發,并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詮釋: “如此一來,在人的語脈中,‘性’就指成人的整個過程。嚴格地講,一個人并不是一種靜態的存在,而首先是一個做人和成人的動態過程。只有在派生和回顧的意義上,人才是一種已經完成的東西。”①[美]安樂哲:《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家與道家》,彭國翔編譯,第289頁。
二
受唐君毅、葛瑞漢等前輩的啟發,安樂哲更傾向于用一種動態的、獨特的、創造性的特點來定義孟子之“性”。安樂哲坦言,對概念內容的再定義是哲學的本分,之所以選擇唐君毅和葛瑞漢這兩位學者的文本進行分析,原因在于,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有將“性”理解為一種成就 (achievement)的預示,這有利于進一步詮釋的展開。他指出,學者們都傾向于把“性”和“心”合起來說,而沒有注意到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忽略了“性”所表達的變化、成長、升華的意義。他以“牛山之木”(《孟子·告子上》)的例子來佐證這個觀點。孟子觀其牛山,“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孟子·告子上》),意欲說明的是,此山之“性”是超出其基本狀況之外的“文化”和“特性”。對于此山來說,那些覆蓋其上的樹木是自然的,并非本質的天賦,而是在其歷史過程中發生的一種美化。那些樹木是山的經過培養的美。在用“性”指稱山林而非山本身時,對于我們認為是山的相對非本質方面的東西,孟子卻給予了優先性,這并不令人感到驚奇。對孟子來說,“性”就是指示那些超出基本狀況以外的東西②同上,第284頁。。在此基礎上,安樂哲嘗試用 “nature”以外的 “character”、“personality”、“constitution”等更為接近的單詞來說明它,可是他謹慎地認為這樣在分析中可能會引發更多的問題,最后他還是決定使用“xing”這一拼音來表示“性”③同上,第291頁。。
在萬物有生論的預設下,安樂哲認為“性”源自于“生” (出生/生命/生長)。理由是,在古典時期中國人的世界里,任何東西都被認為是“活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意識的”。在古文獻中有大量將“性”運用到非生命事物的例子,僅僅《淮南子》中, “性”就被用于水、金、綢以及所有五種元素 (金木水火土)中。這些事物的“性”保持相對的不變性,然而,作為萬物之靈的人受到極多的培養和磨練,情況當另作別論。用唐君毅的話來說:“人性在中國人思想中的討論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這就是焦點集中于變化的無限性,在無限的變化中形成了獨特的人性,而這種人的精神之性區別于其他事物固定的和缺乏精神的性。”④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第6頁。在西方傳統的宇宙演化論中,“性”作為一種天賦的存在。安樂哲認為在古代中國缺乏宇宙演化論,與西方的“性”不能相提并論;從而推論,中國哲學中的“性”不是所有人從出生就內涵著一種超絕的和單義的法則,它是一種在人出生后加以發展的內在組織系統,也就意味著“性”是一種動態過程,包含了最初的傾向、成長和最終消亡。
依照安樂哲的看法,盡管“性”源自于“生”,但它并非是先天賦予的,而是通過最初的“端”培養起來的。就孟子來說,人生在世是作為一種自發的產生和不斷變化的各種關系的基體,通過各種關系終其一生,一個人的“性”才被確定。在人生之初,有一種微弱的“端”將人與社會、自然環境聯系在一起,它將人帶入這個世界之中。這種“端”是一個人的最初界定,為這個人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但是它比身體的特性要微弱和短暫得多,如果不細心呵護就會很容易消失。在安樂哲的定義中,“端”是指孟子所提到的四端。這四“端”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在確定一個人最初的傾向時,它將一個人編織到了一個特定的脈絡當中。這種最初的關系性在四種范疇中得到概念化的把握,即人際的紐帶(仁)、尊重社會的紐帶 (禮)、意義和價值彰顯的紐帶 (義)和理智的紐帶 (智),這些最初的關系為一個人提供了發展的方向和“性”的表達。在根本意義上,“性”不僅僅意味著“善自身”,而且意味著關系意義上的善,正如“善于”發展自己的家庭和社群關系。終其一生,這些關系都在隨著善的變化程度而得到深化、滋養和擴展。“善”是一個事物在其歷史中界定其特性的條件的最優化。
在此基礎上,安樂哲認為,“性”是一種有賴于特定條件的文化產物,與一個人的“修養”密切相關。要說明的是,“性”僅僅在最低限度上涉及到動物性的滿足(“命”)和“心”的最初發端。人所達到而動物不能的是“性”,人與動物共有的是“命”。對孟子來說, “性”指那些將人與動物區別開來的獨有的特性。如果不經過修養,人與禽獸的不同也就剩下了很微弱的“幾希”(《孟子·離婁下》)。“性”最重要的是修養和成長的結果,它在社會化和教化的過程中獲得協調。作為一種修養的結果,“性”總是善的 (某種獲得的東西),但是人的基本條件(“命”)卻不必然如此。因此,安樂哲斷言,“性”與文化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就像“禮”作為一種文化,“性”可以通過它得到發展。但是,安樂哲也對由他而推出來的孟子的理論表示擔憂,孟子區分“命”、“性”以及將“性”理解為一種成就概念,其歷史性的后果之一就是文化精英主義,這種文化精英主義形成了古代儒學的特征之一。不管怎樣,他認為對孟子來說,不曾發展的人 (缺乏教養的人)還不是“人”。“性”是參與文化社會并做出貢獻的成員的標志。沒有文化修養,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人,因為像動物那樣行為的“人”,確確實實就是禽獸。反之,身體的感受一旦修養成為“品味”,也就延伸到了“性”的觀念范圍。總而言之,在安樂哲看來,“人性”是一種高貴的事物,不通過后天的文化修養是無法得來的。
從本文前兩個部分可以看出,唐君毅、葛瑞漢、安樂哲三人都支持“人性”具有發展性、能動性等特征,可謂一脈相承。不過,安樂哲與兩位前輩學者的思想雖有一致之處,但其對“性”的先天屬性的理解卻不屬于同一個層面。不知是何原因讓安樂哲產生了錯覺,傾向于認為中國哲學中不存在宇宙起源論特征,從而推論其缺乏某種核心的起源 (arche)觀念來解釋人性的創造過程。基于此,他斷言:“在孟子那里,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不是某種不可侵犯的自然賦予,而是一種暫時和始終特殊的文化修養。”①[美]安樂哲:《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家與道家》,彭國翔編譯,第288頁。在這里,安樂哲似乎拋開了“性”的先天性,更多地就經驗方面來談論,致其失去“人之為人”的既定方向,不可避免地會使“性”置于漫無目的的經驗論中。
三
安樂哲對于孟子人性論的觀點無疑是孟學研究的一個創新和突破,正因為如此,這引起了二十年前西方哲學界的一場爭論。劉述先、信廣來、江文思、華靄仁、M.斯卡帕里、M.E.劉易斯等人都撰文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這場爭論中,最具有針對性和代表性的是華靄仁的觀點。她的質疑在于:孟子之“性”的概念究竟是生物學意義的還是文化學意義的?如果是生物學意義的,則它一定是普遍的,是一個固有的形態;反之,如果是文化學意義的,則它一定是有其特殊性,是一個能動的過程,因此也就不能將其與西方哲學的“human nature”劃等號。華靄仁主張前一種看法②[美]華藹仁:《孟子的人性論》、《在〈孟子〉中人的本性與生物學的本性》,《孟子心性之學》,第140—144、227—229頁。,安樂哲則贊成后一種意見。在對孟子人性論的分析中,華藹仁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即按照孟子的觀點,是否存在著一種共同的人性或一種普遍的人的本性。另外,她所擔憂的是,如果按照安樂哲的分析,即“人的相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明顯地取得的文化上的成就”③[美]安樂哲:《孟子的人性概念:它意味著人的本性嗎?》,《孟子心性之學》,第110頁。,這勢必會導致過于強調差異的文化上的相對主義。所以,華藹仁選擇堅持人的本性的普遍性立場,甚至認為孟子的人性論超越于“人的本性”之本質,建立在一種更寬廣的歷史和文化限度之上,支持人的本質具有普遍人文主義的合法性。
劉述先認為華藹仁的辯正是必要的,他也敏銳地覺察到這里面存在的問題。他指出,安樂哲為了避免西方傳統本質主義干擾,從而采用杜威的實用主義來解釋孟子,這同樣會造成“兩元對立”的局面。安樂哲的初衷是,杜威強調自然環境與文化環境對于個體成長的重要性,而這一思想剛好可以運用到詮釋孟子之性上來,將孟子之性置于文化環境的背景之下,這樣就可以破除將其僅僅理解為上天賜予、與生俱有的狹隘的觀念①劉述先:《孟子心性論的再反思》,《孟子心性之學》,第178—184頁。。劉述先認為孟子強調的是人禽之別,而杜威強調人的生物的根源,二者是存在一定差別的。在他看來,杜威講的向善,只是人面對環境必須做出的適應,其中缺乏一個超越的層面;孟子不但肯定人有內在的資源,而且相信天的真實性,只是通過心性在天人之間建立了一道橋梁而已。他的觀點是,人雖然在成就上存在殊異,但是在稟賦上是共同的,眾人與圣人的稟賦無別,這正是孟子堅持性善論的根本意旨所在。
與此同時,李明輝對安樂哲詮釋孟子思想的方法論提出異議。此前,他了解安樂哲詮釋中國文化的基本立場,即安樂哲反對用西方概念詮釋中國思想。一方面,他承認安樂哲的方法論有其積極的意義,因為它提醒我們在詮釋中國古代思想時,應注意其有異于西方思想的獨特性以及詮釋學的基本問題。但另一方面,他認為安樂哲的看法似乎有矯枉過正之嫌。因為根據當代詮釋學的觀點,為某一文本尋找完全“客觀”的詮釋是無意義之事,可以說,不同的文化系統或概念系統之間無法完全轉譯。但吊詭的是,詮釋之必要性正是建立在這種不可轉譯性之上。所有的詮釋都是一種轉譯,完全的轉譯固然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仍必須轉譯。一切詮釋工作都是建立在這種“不可能轉譯”與“必須轉譯”的辯證關系上。與華靄仁持同樣觀點,李明輝也認為安樂哲的看法過于強調中國文化 (當然包括孟子思想)的獨特性,而忽略了其普遍性,這使他陷入文化相對主義之中②李明輝:《孟子思想的哲學探討》,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年,第6—7頁。。
在當今學界,圍繞安樂哲提出的具有創造性的孟子人性論的哲學洞見,展開了長期的討論,至今仍不時有新的論點出現,其中楊澤波、方朝輝兩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楊澤波對安樂哲的觀點基本上持肯定態度。一方面,他認為安樂哲注意到了《孟子》中“心”與“性”兩個概念的區別,這就為性的發展做好了鋪墊。他指出:“性植根于心中,作為心的一種功能,表現為一種必然的決定性傾向,因此,性是需要加以修養和改進的。”③楊澤波:《性的困惑:以西方哲學研究儒學所遇困難的一個例證——〈孟子心性之學〉讀后》,前揭書,第285頁。另一方面,他認為安樂哲所提出的文化學意義上的性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理由是,安樂哲看到了性所具有的相對性,這可以使我們得到啟發。“如果孟子之性確實與人們的文化背景相關,那么具體考察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充分尊重他們的文化特點,反對一種統一的文化模式,進而對現在某些國家借助武力強行推廣自己的文化這一做法進行反思,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④同上,第286頁。方朝輝對安樂哲的觀點也做出了進一步分析。他認為,安樂哲所提出的“‘性’代表一種過程,不是一個固定的、死的本質”這一觀點,對于反駁過去的本質論確有幫助。但是,他還認為從發展的角度理解“性”,就會忽略孟子之“性”所代表的成長法則其實也是天生的、并不是后發的這一最重要事實。基于此,他進而指出,安樂哲的說法忽視了性的先驗特征,恐怕會與孟子本義背道而馳。他的觀點是,孟子所說的發展過程,決不是自然而然的發展 (與自然事物不同),而是人為刻意努力的結果,是修身、盡其心的產物。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全部發展,都還是成全其原有的“性”,即只不過是其潛能的展現而已,其終極目標也只是為了成全其自身,并不是創造出什么全新的東西來⑤方朝暉:《本質論與發展觀的誤區:性善論新解》,《國學學刊》2014年第3期。。
四
就學術方面而言,西方哲學家們數十年來試著用實用主義、新實在論、馬克思主義、康德、海德格爾等各種西方學說來解讀孟子,對于我們理解孟子人性論開辟了新的思路,豐富了孟學研究的理論成果。然而,卻很難跳出原有的理論體系回到孟子自身來解讀孟子思想,所以,很多學者提倡應該回歸到儒學自己的傳統上來。就近期作品看,梁濤教授的《孟子“道性善”的內在理路及其思想意義》①梁 濤:《新編中國思想史二十二講》,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33—163頁。一文是“以孟釋孟”的代表性嘗試。其一,他認為對于“性”的理解,應當分清孟子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孟子對“性”的理解與前人有所不同,他擺脫了經驗、實然的觀點,不再順自然生活種種機能來識取人性。雖然耳目口鼻之欲望是事實上的“性”,但在孟子的價值判斷中這只是“命”;而仁義禮智之心是事實上的“命”,在孟子的價值判斷中它卻是人的“真性”所在。“真性”是求自于內,可以為人所掌控的,在此基礎上,人才能充分擴充、實現善性。其二,他還指出,孟子的“性命之分”來自郭店竹簡的天人之分,是對其的進一步發展。仁義禮智體現了人的意志自由,不受外在條件的限制,所以應看作是“性”;感官欲望、求名求利,能否實現不是由我控制、掌握,所以只能看作是“命”。孟子通過這種“性命之分”,也就是內在自由與外在限定的區分,說明人當以仁義禮智也就是善性為性,而不應當以感官欲望為性。基于此,他強調,應該分清“孟子道性善”與“人性是善的”兩者的區別。孟子“道性善”應該理解為:人皆有善性;人應當以此善性為性;人的價值、意義即在于其充分擴充、實現自己的性。
就文化方面而言,安樂哲看到了孟子人性論最重要的一面,那就是人性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具有無限的創造力,通過不斷的文化修養,不僅能使自身的善性才能得到深化、滋養和擴展,還能善于處理好人與社會、自然環境的各種關系,這一切的最終目的在于追求更高層次的人性。也就是說,孟子性善論的真實意圖不在于對各種概念的理論分析,而在于實現它的文化價值。安樂哲一向注重哲學中的文化性,這也許跟他的好友兼學術伙伴郝大維的影響有關。南樂山回憶:“郝大維將文化哲學視為所有哲學的首要類比點。對他來說,各種其他形式的哲學意義和一般結論也將從文化哲學的視角獲得理解。”②[美]南樂山:《文化哲學家郝大維》,《先賢的民主:杜威、孔子與中國民主之希望》,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6頁。安樂哲也坦言: “我從郝大維那里學習了很多。他很年輕就去世了,當時六十幾歲。我學習了那么多,他對我的改變那么大,他去世后,我寫的書感覺應該把他的名字寫上去。事實上, ‘我’就是我跟他。”③源于筆者對安樂哲的采訪,2014年7月15日。
其實,回到孟子,我們可以發現他在邏輯推論上存在諸多不嚴密之處。阿瑟·韋利 (Arthur Waley)宣稱: “作為一個爭論者,他 (孟子)是無價值的,關于仁與義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整個討論是一堆毫不相干的類推,其中之多數完全等同于習慣上去反駁他們傾向于去證明的東西。”④Athur Waley,Three Ways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1939,p.193.楊澤波也有同樣看法:“孟子在論性的過程中,從表面上看,的確是在說人的善性是上天賦予的,是生而具有的,但如果對相關論述加以深入考察,則不難看出,這里面疑點很多……孟子相關的論述并沒有太強的說服力,不足以達到預期的目的。”⑤楊澤波:《性的困惑:以西方哲學研究儒學所遇困難的一個例證——〈孟子心性之學〉讀后》,前揭書,第286頁。盡管如此,現在很少有學者流于把孟子的理性簡單視為類比推理,這說明我們對中國哲學的關注重點不在于此。作為一種邏輯學,它的確顯得不嚴密;但作為一種哲學,甚至一種文化來看,從它背后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偉大的孟子。孟子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對社會蘊含著深切的現實人文關懷,這也許就是我們研究孟子性善論的最大意義所在。對此,二程弟子楊時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養性,收其放心。”⑥[宋]朱熹:《孟子集注·孟子序說》,《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99頁。孟子性善論具有特殊的社會教化功能,雖然它不同于宗教般的超理性的信仰,但其作為個人內心信仰的方面往往掩映在社會功能之中。也許正如安樂哲所理解的那樣,孟子之“性”具有創造性。那么,作為一種心性哲學,我們何不借助它來督導人心向善,進而去創造一個更加完善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