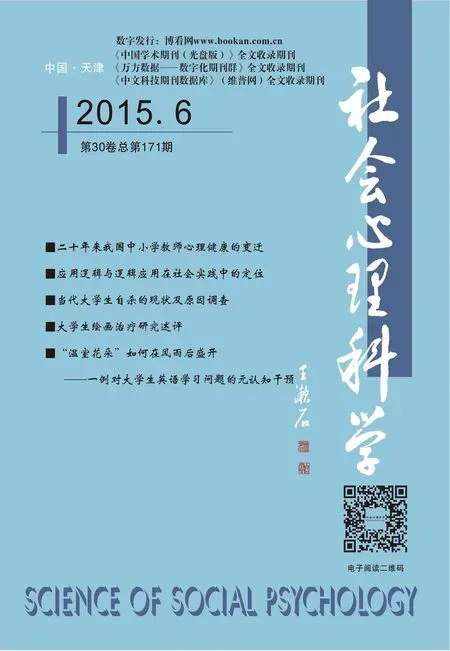基于樣例學習研究的幾點展望
杜雪嬌
(遼寧師范大學心理學院 大連 116029)
1.樣例與樣例學習
樣例(work-example)往往以一步步的形式呈現解題步驟,為學習者提供一種規范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即我們通常所說的例子或范例[1]。它通常包括一個待解決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所有步驟及最終結果。樣例學習(worked-example learning)是讓學生觀察和思考樣例,并掌握樣例中包含的規則,或從中習得新規則(新概念或新知識)的過程。狹義的樣例學習主要集中在結構良好問題領域,如數學問題、物理問題等,這類問題包涵已知的初始條件和明確的目標狀態。而廣義上的樣例學習泛指人類一種重要而基本的學習方式,社會學習中的榜樣學習,學科學習中的例題,教育領域中的教學觀摩學習等都屬于樣例學習。而樣例效應(the worked example effect)是指對于新手來說,與傳統的問題解決方式相比,樣例學習的效果更好且效率更高,即學習者投入較少的時間和心理努力就能獲得較好的學習效果。樣例為初學者提供了已知條件和目標狀態,并給出了從已知條件到目標狀態的解題步驟,因此樣例學習可以阻止學生采用諸如手段—目的分析、嘗試—錯誤這樣一般的問題解決策略和諸如復制—修改這樣的表面策略,這些策略增加了無效的認知負荷,影響學習效果[2]。同時,學習者可以把他們的認知資源投入到觀察和思考樣例中的解題步驟上去,對習得的新規則(新概念或新知識)進行編碼、組織,進而整合到長時記憶中,故而學習效果較好。
2.樣例學習的研究
樣例學習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先秦孔子《論語·述而》中就有“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的論述,這其中就包涵樣例學習的思想。樣例學習的研究起源于20 世紀初對問題解決技能的研究,研究者發現,新手和專家在問題解決技能上存在差異。而產生這一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專家擁有相關領域的知識結構,即圖示,而新手尚沒有習得這一圖示。習得圖示最有效的途徑即為樣例學習。于是,研究者在樣例學習效果和樣例設計方式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已有研究證明,樣例學習是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重要方式。有效的樣例設計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進而改善其學習效果,所以有必要基于已有研究,總結其尚不完善的地方,為未來研究提供參考,進而指導學習與教學,提高實際教學效果。
3.樣例學習研究的展望
3.1 擴展對新樣例類型的研究
近年來,樣例學習所應用的領域不斷擴大,由一般的物理、數學等結構良好領域問題逐漸擴展到了寫作、策略學習、技能訓練等結構不良領域問題。隨著應用范圍的擴大,一些新的樣例類型不斷涌現,樣例類型的劃分維度也越來越多,由原來比較單一的劃分維度逐漸發展為多種樣例劃分維度,相繼出現了動態樣例與靜態樣例的劃分、單內容樣例、雙內容樣例以及多內容樣例的劃分等。然而,相較于傳統的單內容樣例和靜態樣例,尚缺乏針對動態樣例,雙內容樣例等新樣例類型的相關研究。
3.1.1 動態樣例的研究
動態樣例是以動畫或視頻的形式呈現的樣例。一般認為由于動態樣例能夠直觀的表達物體的運動過程,能夠幫助學習者構建“外部動畫”,而不需要學習者在自己的大腦中構建動態的“心理動畫”[3],故而,可以有效地防止認知負荷過高,在樣例學習中效果較好。但動態樣例具有瞬時性特征,信息呈現之后會立即消失,學習者在加工新信息時,需把新信息和之前的信息整合起來理解材料,加重了工作記憶的負擔,反而會影響學習效果。已有的大量研究對動態樣例和靜態樣例的學習效果進行了比較。這些研究中大都采用操作技能為學習材料,那么動態樣例是否同樣有利于傳統的數學、化學等結構良好領域問題的學習呢?它是否顯著優于傳統的靜態樣例呢?動態樣例的呈現速度、數量、類型等因素是否會影響樣例學習的效果呢?針對這些問題,研究者需要進一步對動態樣例展開專門的研究。
3.1.2 雙內容樣例的研究
策略學習、技能訓練等復雜領域的樣例學習往往是雙內容,甚至是多內容樣例的學習。以往的單內容樣例只包含一方面的內容,即所學的概念、原理和規則等,這被稱為學習域的知識,而雙內容樣例包含學習域和示例域兩方面的內容[4]。這里的示例域是指樣例中所涉及的具體內容。那么,在雙內容樣例的學習中,是分別學習示例域和學習域知識的學習效果好呢,還是把兩者整合到一起同時學習效果好呢?對于這一問題,Clarke 以電子數據表軟件(spreadsheet)輔助線性函數知識的學習為材料,進行了實驗[5]。研究結果顯示,對于不太了解電子數據表知識(示例域)的被試來說,分別學習好于同時學習;對于較多掌握電子數據表知識的學生來說,同時學習好于分別學習。對于已掌握電子數據表知識的學生來說,由于已有相關圖示,同時學習也不會造成認知超負荷,且同時學習有利于整合兩種知識,分別學習反而會造成信息的冗余和認知資源的浪費,故同時學習效果好。但對于不太了解電子數據表知識的學生來說,同時會造成認知超負荷,故分別學習效果較好。那么對電子數據表知識(示例域知識)掌握到什么程度時,學習域與示例域同時學習的綜合學習效果更好呢?雙內容樣例的學習順序對學習效果的影響,除了取決于學習者的知識水平外,是否還取決于樣例中學習域與示例域之間的關系呢?單內容樣例中的設計原則是否同樣適用于雙內容樣例呢?雙內容樣例學習時的認知加工過程是什么?學習結果又該如何評估呢?總之,在雙內容樣例的研究領域,尚存在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3.2 增加樣例學習效果的測量指標
目前,樣例學習的研究大都采用遠遷移和近遷移測驗成績作為其學習效果的測量指標。遠、近遷移測驗成績體現了學習者理解和掌握該樣例的程度,是對學習效果最直接、最有效的測量。同時,可以在測驗成績指標的基礎上,增加其他測量指標,補充測驗成績指標,從多個角度評估和解釋樣例學習效果,并且可以進一步解釋樣例設計起作用的機制。比如,可以測量樣例學習過程中的認知負荷水平指標和眼活動、腦成像等生理指標。
3.2.1 樣例學習的認知負荷測量
根據認知負荷理論,如果學習某個樣例所占用的認知資源超過了學習者認知資源的總量,就會出現認知超負荷,影響學習效果。Paas 等人根據影響作用及因素的不同將認知負荷分為三類:外在認知負荷,內在認知負荷和相關認知負荷。在樣例設計中,應降低樣例學習的外在認知負荷,優化和提高其內在認知負荷和相關認知負荷,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因此,針對某種樣例設計方法,實現認知負荷的分別測量就顯得尤為重要。
研究者已開發出了一些認知負荷的測量方法。其中,由Paas 于1993年編制了認知負荷自評量表,在研究中得到了廣泛地應用。隨后,Leppink和Paas 等人(2014)在該認知負荷量表的基礎上開發出來認知負荷分別測量的量表,并通過實驗證實了該量表能有效區分出內在、外在和相關認知負荷且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6]。故設想在今后研究中可以借助這些量表對學習者的內在認知負荷、外在認知負荷和相關認知負荷進行分別測量,結合學生的測驗成績,解釋樣例設計方法起作用的原因,補充單一的測驗成績指標,優化樣例設計方法,進而達到指導樣例設計的目的。
3.2.2 樣例學習的生理指標測量
隨著眼動、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術的涌現,研究者逐漸開始對樣例學習中眼活動指標和腦成像指標等生理指標進行測量。張華(2013)的研究中,分別以樣例學習時的注視點持續時間、注視點數量、訪問時間和訪問次數4 個眼動指標和近遷移、遠遷移測驗成績為因變量,考察了初三學生學習不同相似程度的物體受力分析正誤樣例的學習效果[7]。綜合考慮眼動指標和測驗成績發現,學習高相似組樣例的被試的注視點持續時間較短、注視點數量較少,且能較好的掌握物體受力分析規則。Lee,等人對數學問題樣例學習的研究中,綜合測驗成績指標和由功能性側共振成像(fMRI)測得的腦成像指標,考察了有、無解釋指導和不同樣例類型(強調問題結構樣例和強調解題程序樣例)的學習效果[8]。結果發現,有、無解釋指導不影響遷移測驗成績,且在腦成像數據上也無顯著差異;樣例類型影響學習者的測驗成績,問題結構樣例好于解題程序樣例,腦成像數據也表明,學習問題結構樣例的被試更多的激活了大腦的前額葉皮質和角回區域,并結合這些腦成像數據分析了樣例設計的腦機制。由此可見,對樣例學習過程或測驗過程中的眼活動指標和腦成像指標等生理指標進行測量可以補充單一的測驗成績指標,揭示樣例學習過程中的認知活動機制。因此,對樣例學習中生理指標進行測量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
3.3 探索基于計算機的樣例學習的方式
在以往研究中,樣例題大都通過學習冊或卡片的形式在紙上呈現,這種方式符合學生學校學習中閱讀紙質教材的習慣,不會增加學習者的外在認知負荷。但某些樣例設計方法卻難以通過紙筆的形式實現,隨著計算機、網絡等技術的發展,研究者開始借助計算機程序等技術設計和呈現樣例。Salden 等人在對漸減樣例的研究中,借助由Anderson 等人開發的cognitive tutor 教學軟件,設計樣例[9]。學習者通過該軟件學習樣例,可以在學習過程中動態評估學習者對樣例中每一步驟的掌握情況,即如果學習者對某一步進行了正確的自我解釋,下一個樣例中該步驟將會被省略,以問題的形式呈現;如果學習者不能對這一步進行正確的自我解釋,在下一個樣例中這一步將再次呈現。從而實現了根據學習者的掌握情況,動態漸減樣例的步驟,最后使學生能獨立的解決問題。此外,Moreno 等人通過利用Dreamweaver 編制的計算機程序,實現了樣例學習過程中,對學生學習效果的及時反饋[10]。基于計算機學習環境的樣例設計不僅可以根據學生的掌握情況提供個性化樣例,對學生的學習效果進行及時的評估和反饋,實現交互式的樣例學習,還可以提供動態樣例和操作性樣例。由此可見,如何利用計算機等技術提高樣例學習的有效性,也將成為研究的重要領域。
[1]張奇,林洪新.四則混合運算規則的樣例學習[J].心理學報,2007,37(6):84-790.
[2]張華,曲可佳,張奇.含有新算符的代數運算規則學習的有效樣例設計[J].心理學報,2013,45(10):1104-1110.
[3]Hegarty,M.,Krize,S.,& Cate,C.The rolesof mental animations and external animations in understanding mechanical systems[J].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2003,21(4):325-360.
[4]曲可佳,張奇.雙內容樣例的研究及重要啟示[J].心理科學,2014,37(2):373-376.
[5]Clarke,T.,Ayres,P.,& Sweller,J.The impact of sequencing and prior knowledge on learning mathematicsthrough spreadsheet applications[J].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5,53:15-24.
[6]Leppink,J.,Paas,F.,Tamara,V.G.,Cees,P.M.,Vleuten,V.D.,Jeroen,J.G.&.Merri?nboer,V.,Effects of pairs of problems and examples on task performance and different types of cognitive load[J].Learning and Instruction,2014,30:32-42.
[7]張華.中學生物體受力分析正誤樣例組合學習及促進方法的研究[D].大連:遼寧師范大學,2013.
[8]Lee,S.H.,Fincham,J.M.,Betts,S.,&.Anderson,J.R.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instructional guidance in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J].Trends in Neuroscience and Education,2014,3:50-62.
[9]Salden,R.J.C.M.,Aleven,V.,Schwonke,R.,& Renkl,A.The expertise reversal Effect and worked examplesin tutored problem solving[J].Instructional science,2010,38(3):289-307.
[10]Moreno,R.,Reisslein,M.,& Ozogul,G,.Optimizing Worked-Example Instruction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The role of fading and feedback during problem solving practice[J].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2009,98:8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