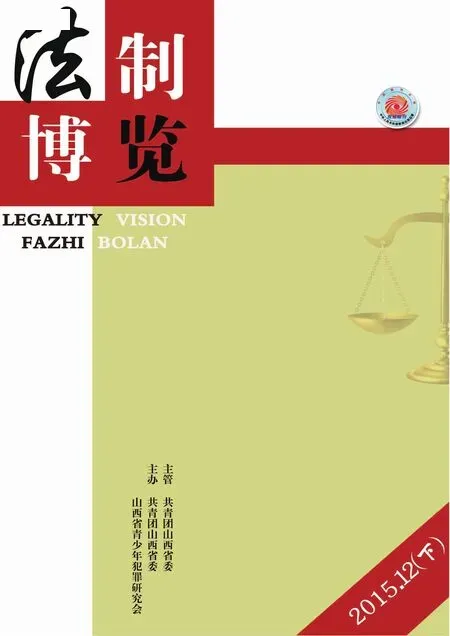淺論非婚同居關系解除時的財產分割問題
王夢婷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201620
一、非婚同居概念之界定
理解概念是認清事物本身的前提。非婚同居顧名思義,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單身男性與女性以不違反一夫一妻制和其他強制性法律規范的前提下,未經結婚登記手續而自愿地長時間持續穩定地共同生活,在感情、經濟、日常生活和性行為等方面形成較為緊密、互相依賴的生活共同體的事實狀態。”其構成要件應為:
(一)同居主體應該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非婚同居因其固有的“長時間、持續穩定”的特點,同居雙方勢必會在此過程中形成較多的權利義務關系,如對自我財產權益的處理和分配問題等。同居主體只有在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情況下的條件下,才可對此承擔起法律責任。
(二)同居雙方無現存的婚姻障礙。即為異性同居且雙方達到法定的結婚年齡,不屬于我國禁止結婚的情形。
(三)非婚同居雙方必須完全出于自愿,即雙方意思表示一致。也就是說,非婚同居雙方是完全出于自愿而建立長時間的同居關系,而非出于婚姻領域經常存在的非自愿因素(如:脅迫、買賣等)。
(四)非婚同居的事實行為必須是長時間且具有穩定性的。只有這樣才能和”一夜情”等行為區別開來,暫時的同居,或者僅僅是互為性伴侶并不是非婚同居關系。
我國部分學者認為非婚同居關系需要雙方無結婚之意愿。但筆者認為:建立非婚同居關系的雙方當事人是否有結婚之意愿這點并不重要。其可能是希望將非婚同居關系作為其婚姻關系的”試金石”,如試婚同居。亦可能雙方自始至終并無締結婚姻關系的主觀意念,但這些最終都不會影響到非婚同居關系事實上的成立和存在。
二、非婚同居的法律效力問題
我國非婚同居關系的法律效力問題應按照時間邏輯梳理,據此可分為兩大方面。
(一)對于那些早于1994年2月1日的未婚男女,雙方自愿以對外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且雙方均符合婚姻實質性要件的,盡管其未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婚姻登記,但仍然可以認定其效力和法定婚姻相同,為事實婚姻,受到與法律婚姻同樣的保護。
(二)在1994年2月1日后,雙方可通過補辦婚姻登記,將同居關系轉變為合法的婚姻關系,婚姻關系的效力從雙方完全符合婚姻法所規定的結婚實質性要件時算起。但未婚男女雙方即使自愿以對外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且雙方均符合婚姻實質性要件的,只要未按法定程序辦理結婚登記,認定為同居關系,不承認雙方的婚姻關系,且同居關系不受法律保護。
2004年4月1日起施行的《婚姻法解釋(二)》第1條規定:”當事人起訴請求解除同居關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只受理同居關系中涉及”因同居期間財產分割或者子女撫養糾紛”的案件,這也表明了2004年最高法的立法態度。即不鼓勵、不禁止、也不干涉非婚同居關系,只有在非婚同居關系觸及到民事案件領域內,即出現財產糾紛和子女撫養糾紛等問題時,法院才參與、干涉。此時對于非婚同居關系的效力可分為兩方面來進行探究:
1.內部效力
法律不承認非婚同居雙方當事人的合法婚姻關系,故雙方不具有合法夫妻的身份。非婚同居關系的建立完全通過雙方當事人的合意一致,即完全自愿,解除時除非涉及財產糾紛與子女撫養問題外,法院將不會干涉與參與,即雙方關系的解除無需經過任何其他機構的同意和承認。
非婚同居關系解除時,財產分割通常按照有約定的從約定,沒有約定的因其未達到合法婚姻的關系,故按一般共同來處分,具體分割財產時,會適當地照顧弱勢群體如婦女、老人、兒童的合法權益。盡管法律對非婚同居財產處置有法律規制,但其具有不明確性,且針對性與可操作性不強,能夠實際解決問題的情況有限,僅僅依靠這些簡單散落的法律條文來對其財產糾紛問題加以規制和處分,是十分不公且不理性的處置方式,無法全面切實地維護我國的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
2.外部效力
非婚同居雙方當事人所生育的子女,通常被稱為“非婚生子女”。《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不直接撫養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應當負擔子女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直至子女能獨立生活為止。即盡管其父母并非合法婚姻關系,但并不會影響到子女在法律中享受到的權利和保護地位。
三、非婚同居關系在解除時的不同處置方式
非婚同居關系的解除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因同居關系雙方自愿協商一致或其中一方要求而人為解除同居關系的,二是因一方死亡而自然解除同居關系的。
(一)一般人為解除非婚同居關系的情況下,當同居關系解除時,同居當事人對于同居期間財產分割有約定且約定有效的,按照約定處理,無約定并未達成協議的,可通過訴訟途徑解決。
對于共同財產的處理標準,通常在實務中會遵循平均分割原則,但其仍有弊端,因其無法考慮到每個非婚同居關系所存在的特殊性,如:一方是否在非婚同居關系解除時保有重大過錯、是否有一方在非婚同居關系存續時家事勞動部分承擔較多、非婚同居關系存續期間是否有一方患有重大疾病而另一方負擔較多撫養義務等。故筆者認為,在堅持遵循平均分割原則的基礎上,應該綜合、全面考慮同居雙方之間的具體實際情況,保證雙方之間的相對公平。
(二)非婚同居關系的自然解除是指一方在同居期間死亡導致非婚同居的共同生活狀態被迫終止。此時,不會產生財產分割的情況,矛盾點在于遺產繼承。
一般來說,在非婚同居關系中,雙方當事人之間由于沒有合法的身份關系而會導致傳統意義上的《婚姻法》和《繼承法》的條文無法適用。但這是否意味著非婚同居雙方當事人無法通過任何方式分得對方的遺產了呢?并不是這樣的。法律為非婚同居當事人提供了兩條救濟途徑。
1.非婚同居關系中死亡的一方生前可通過訂立合法且有效的遺囑,指定非婚同居的另一方作為“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獲得遺產,則另一方即可據此獲得遺產。
2.若非婚同居關系中死亡的一方生前受另一方撫養較多,則另一方可通過《繼承法》第14條:“繼承人以外的對被繼承人扶養較多的人,可以分給他們適當的遺產。”
兩者相比,第一二條救濟途徑在遺產分得的數額上有較大差別。在實務中,第一條救濟途徑可依據死亡一方的遺囑內容分得確定的財產(如遺囑中死亡一方表示“將自己所有的遺產全部贈給非婚同居關系中的另一方當事人,則另一方當事人可獲得其全部遺產)。但第二條救濟方式中,盡管另一方當事人在法庭中一出自己對死亡一方撫養較多以此爭取遺產份額,但法院通常只會給予其適當、部分的遺產數額。
目前,我國對于非婚同居雙方的繼承問題在立法方面仍然較為模糊和滯后,長此以往難以維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筆者經過仔細思考后認為,可以嘗試以下三種情況使得同居雙方有條件的取得繼承權:
3.非婚同居6年以上并且有共同子女的,難免會有不正思想的人視圖利用子女來取得他人繼承權,規定較長的時間限額也可以保證非婚同居概念中的“持續性”。
4.根據死亡一方生前的合法有效的遺囑。
4.非婚同居時間長達6年以上,雖未共同生育子女,但對死亡一方扶養照顧較多或對死亡一方的家庭成員撫養、貢獻較多的,根據實際撫養、照顧情況,分得適當繼承權。
此外,立法中還應明文規定:非婚同居一方當事人死亡時,另一方有析產請求權和對同居期間對方部分財產如房屋、私家車及雙方非婚同居關系存續時所使用的生活用品的優先購買權和優先承租權。
四、我國非婚同居財產關系的法律規制設想
盡管非婚同居現象作為公眾道德方面的自我選擇和自由,在當今社會呈現出普遍、日益增長的趨勢,但我們也不可聽之任之、任由其自由、肆意發展,無視其存在,對于非婚同居關系所引起的各種財產、子女撫養、人身關系等法律矛盾,國家與社會公眾都應該公正理智地對待,將其與合法婚姻關系區分開來,避免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和趨同。故筆者建議,我國立法者可以考慮在以下幾個方面對非婚同居關系有所規制:
(一)確立非婚同居雙方當事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著重體現在債務承擔方面,保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
在非婚同居關系存續期間,因雙方的共同生活而產生的共同債務,非婚同居雙方應負連帶責任,而因個人原因而產生的個人債務應由其個人承擔。在非婚同居持續的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必要生活支出,如:衣食住行的消費、生活日用品的購置和開銷、社會保險的費用和之處、醫療費用等,屬于因雙方的共同生活而產生的共同債務。此項關系和制度的確立可以更好的保護第三方的合法權益,維護我國的社會相對公平。
(二)確立非婚同居雙方之間經濟幫助義務,在特定條件下可以請求對方給予一定的經濟幫助
非婚同居關系雖然不是我國所鼓勵的家庭生活形態,法律對其保護程度不宜提高到與合法婚姻相同的高度,但亦無法無視它的存在,否則將顯失公平。筆者認為,應在非婚同居雙方之間確立經濟幫助義務,即在特定條件下可以請求對方給予自己一定的經濟與物質上的幫助。如:非婚同居關系解除時,一方確有生活困難的情況下,可請求有能力支付這筆費用的另一方給予適當的經濟幫助,而具體數額應根據具體情況與不同因素決定,支付的方式可以定期支付約定的金額,或者雙方通過簽署協議達成合意。此外,還應參照我國《婚姻法》的立法理念,適當照顧、保障婦女、老人、孩童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三)在現行《婚姻法》中增加對于非婚同居關系解除時財產處分的明確、具體條文內容,作為對于合法婚姻的一項有力補充,推動我國法律進程的完善
非婚同居關系作為一項人身關系,其涉及到財產分割和子女撫養糾紛的屬于民事關系,法院應予以受理,且法律應予以規制。而在《婚姻法》中增加相關條文和款項,可以更好地補充、完善我國婚姻法發展進程,從而維護我國社會的安定和諧。
我國關于非婚同居相關的法律制度構建具有迫切性,現如今非婚同居現象逐步增多,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和缺失以及現有法律的滯后性和局限性,致使非婚同居雙方當事人的權益和權利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保護與救濟。因此,筆者認為,對于非婚同居身份關系緊迫且完善的法律規制和立法是實現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緊迫要求。
[1]尚晨光.婚姻法司法解釋(二)法理與適用[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
[2]陳玉玲.非婚同居關系的法律研究[J].福建論壇,2006(12).
[3]韓德剛.非婚同居當事人財產關系淺論[J].法制與社會,2008(2).
[4]李鳳章.非婚同居中女性合法權益的保護[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