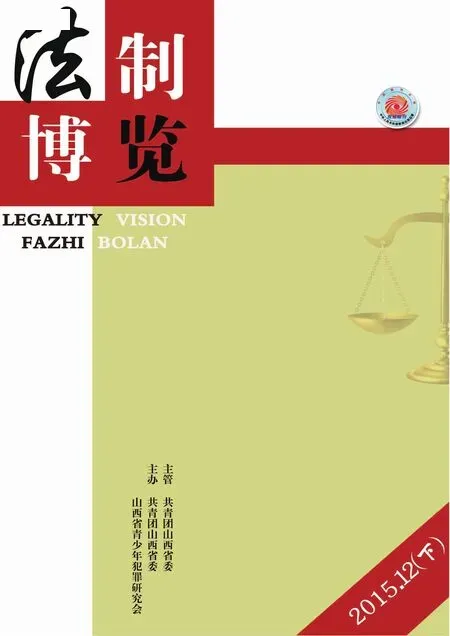論正義與效率的自由融合
申凱笛
江西財經大學,江西 南昌 330013
論正義與效率的自由融合
申凱笛
江西財經大學,江西南昌330013

摘要:正義與效率的關系及如何處理一直是備受關注的問題,文章從探討正義與效率在法律制度中的無形融合,延伸到二者在社會效益實現中的自由結合,最后從社會長期發展中研究二者的辯證關系,論證正義與效率的融合是社會發展自由選擇的結果,而不需要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強把效率套在正義之中,尊重社會發展的自由選擇,以二者最佳的融合來建設和諧社會。
關鍵詞:正義;效率;自由融合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5)36-0106-03
作者簡介:申凱笛(1995-)女,漢族,山西人,江西財經大學,研究方向:法學。

一、正義與效率在法律思維中的融合
正義是法的最高精神和目標,效率本是一個經濟學領域的概念,意指以價值最大化的方式利用資源并獲得滿足。“法學家關注正義,經濟學家看中效率”,這一極具美感的對稱式判斷是相當誤人子弟的。正義與效率是共同融合在法律思維中的,過錯責任原則就是最好的體現。
過錯責任原則,是重要的責任分擔的歸責原則,指如果一個人的行為造成了他人的損害,只有當他具有過錯時才被課定責任,而沒有過錯就沒有責任,但是如何判斷一個人具有過錯呢?過錯表現為故意和過失兩種形式。法律上的過失被界定為“應當預見到但卻沒有預見到或者已經預見到但輕信能夠避免”,然而,這個每個法律人幾乎能夠熟練背誦的條文,卻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操作標準,法官如何斷定一個人是違反了最低的注意義務呢?還是違反了平日處理自己同一事物時的注意義務呢?憑什么說當事人是“疏忽大意”或“過于自信”?由于這條關于過失的定義描述的是人的主觀心理狀態,但一個人的心智是無法判斷,無法觀察的。在這個時候,一切都依靠法官判決案件的真實思維過程,這個思維中,有學者主張通過權衡利弊,以效率為支點處理問題;有學者主張以被大眾共同接受的公平正義觀念作為處理案件的依據。
權衡利弊即為過失的經濟分析方法,也稱為“效率說”。過失的經濟分析“源于美國1947年的一個著名案例:很多駁船用一根泊繩系在幾個凸式的碼頭邊。實際操作駁船的丙公司船員用乙公司的拖船拖甲公司的駁船。由于駁船上沒有人,丙公司的船員在調整駁船時,由于沒有調整好,駁船脫離了泊繩發生了漂移,在大風的作用下,這個漂移的駁船撞上另一條船,連同貨物一起沉入海底。駁船船主甲公司以拖船船主存在過失為由向法院起訴,要求拖船公司以及操作拖船的丙公司對其損失承擔賠償責任。拖船公司認為,駁船的船員盡管不在船上,也有一定過失。美國著名法官漢德在審理此案時,運用經濟分析的方法,提出了著名的判斷過失有無的公式。漢德提出:設損失發生的幾率為P,損失額為L,預防成本為B,當預防成本小于損失全額乘以損失發生幾率時,即B 如果拋開以上的效率分析方法,純粹從公平正義角度出發,法官會如何判決呢?還有什么更公平的方案嗎?這時我們發現,剛才以“過失的經濟分析”方法得出的結果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因為我們在無意識中是按照這樣的思維理念進行價值判斷與評價。比如日常生活中,甲正在開車,接聽了乙打來的電話,于是不幸出了車禍。如果甲將以訴至法院,法院會支持甲的訴訟請求嗎?我們都會毫不猶豫地搖頭,“當然不會”。為什么?普通人可能會說是因為直覺,有法律常識的人可能會提供很專業的解釋:乙的行為與事故后果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沒有過錯,所以不承擔責任。但是,專業解釋中,又是如何判斷是否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呢?這時皮球又被踢回來了。其實,不論是直覺,還是專業判斷,他們背后的思維邏輯是一樣的。在這個案例中,甲完全可以不接電話,可以很容易的避免事故的發生;而乙并不知道甲在開車,讓乙判斷甲什么時刻適合接電話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都會肯定甲對自己的事故負責,而乙不承擔責任,這是最公平正義的。用經濟學家的語言來講,甲避免事故的成本相當低,而乙要在打電話前弄清甲是否在開車,成本相當高。將事故責任強加于能以較低成本避免事故的一方當事人,加強當事人的注意義務,既有利于降低事故的成本,也有助于減少未來事故的發生。也就是說,我們在進行正義與公平的價值評價中,受著“成本最小化原則”即效率指導,在進行公平正義的判斷中,效率已融入其中。 正義感與經濟學邏輯大致是吻合的,正如桑本謙學者所言,如果兩者背道而馳,即一個社會中被大眾接受的正義感正好與利益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相反,那么這個社會很容易成為生態競爭中的失敗者。如前文所提到的過錯責任原則,作為民法的基本精神,按照經濟分析法學派的觀點,過錯責任最能體現效率。經濟分析法學派認為,對于不經濟的損害,應通過對能夠最廉價地避免風險的人課定責任的方式予以制止。在一種損害發生時,以最廉價地避免和預防事故發生的情形大致有三種:一是完全由被告預防;二是由原告和被告共同預防;三是由原告預防。第一種情形和第三種情形為少數情形,而多數情況下是由雙方共同預防成本最低。第一種情形為無過錯責任原則,第二種情況為過錯責任,第三種情形為被告的免責事由。在大多數情況下,當被告在行為時盡到了適當的注意義務時,成本最低,即過錯責任的預防成本最小。可見在法律思維中,正義與效率有者天然的聯系,在需要時人們已在無形中自然地以效率作為衡量正義的標尺。 二、正義與效率在社會效益中的融合 正義與效率不僅共同融合在法律思維中,在社會效益的實現中,正義與效益兩者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社會效益的最大化。法律作為規范的功用在于調整社會關系,是以正義為價值導向的社會關系調整器,達成社會效益最大化的目標。正義與效率在社會效益中的關系可以從兩個方面闡述。 一方面,正義是一個古老的價值命題,而效率則是現代社會賦予法的新使命。長時期以來,人們往往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式,那就是只要一提及正義與效率的關系,就很自然地要分出一個先后、輕重。而二者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效率是正義的基礎,正義是效率的目標。效率有利于社會發展生產力,沒有效率就沒有公平實現的物質條件和源泉。若沒有效率提高和財富的增進,公平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只能是貧窮的公平而難以有什么真正意義的公平。“一個正義的社會,或者一個被認為是正義的社會,其制度框架若不包含對‘效率’的關注,或者用流行的語言來說,若不能有效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它很難被人們認同為正義的社會,因此,效率是正義所內含的價值內容之一,也是法所追求的正義的具體價值名目之一”。[2] 另一方面,在社會法的法律關系中,當事人間的橫向交往產生的是效率價值,而政府的干預行為則是對正義價值的詮釋。[3]社會總體關系的有序性以及宏觀效率都主要地依賴于個人積極性和創造力的發揮,以及人們相互關系的和諧。要達到這種和諧,必須處理好個體與群體的關系。而按照自由放任主義經濟理論的基本理念,只要人民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必然有其最好的結局。并且,在依自己的意志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人們實際上也在不自覺地為社會服務。但是,如果人們對自己利益無限制的追求,必然會引起糾紛和沖突,而這種糾紛和沖突不僅在政治上會引起秩序的混亂,而且經濟成本也十分高,故最好的方式就是制定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則,在承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在避免沖突的限度內,限制個人自由和權利。法律作為規范的功用在于調整社會關系,在保障個體利益的同時維護公共利益,達到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每個個體都會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橫向交往產生的純效率總和再減去對他人造成的損害(負效率)所得的凈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效益。社會效益是效率和正義的結合體,只有效率的提高和公正的維護達到一種均衡的狀態時,才能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優化。 正義與效率作為法的兩種價值,最終意義無非是實現社會效益。效率的提高極大地滿足了人維持生存的能力,然而卻由于對個人價值的極端推崇可能導致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減損;正義恰好使市場固有的缺陷和人的有限理性得以彌補,然而它也存在由于其過分的衡平性所導致的對個人積極性抑制的可能。因此,在效率與正義之間綜合地權衡了的利弊之后,克服單個價值的瑕疵,才能實現1+1>2的綜合效果,共同促進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三、正義與效率在社會發展中的融合 在社會的不斷發展中,正義和效率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交織,效率在飛速提高,正義的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從漫漫歷史長河來看,正義恰恰體現了一種長期的、動態的效率;從長期的、動態的角度看,如果沒有道德和正義作為支撐,真正的效率也不可能實現。 花費10元抓住偷竊1元的小偷,值不值得?臺灣著名經濟學家熊秉元曾在一篇《正義的成本》的文章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認為花10塊錢去抓偷竊1塊錢的小偷不值得。那么按照經濟分析學的觀點,如果花10塊錢去抓偷竊1塊錢的小偷不值得的話,是不是就不用去抓了。從法學的角度,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從純粹靜態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可以簡化為一道數學題,即10塊錢和1塊錢的大小。然而,我們生活的世界并不是靜止不動的,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法律,關注的不僅僅是事后的成本計算,更為重要的是預防違法和犯罪。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向前看,關注這個案例的成本,更要向后看,關注這件事對未來的影響。從動態的視角出發,小偷雖然只偷竊1塊錢,但是,這個小偷存在一定的社會危害性,小偷也許偷了1塊錢后就金盆洗手,也許會得寸進尺再行偷竊。尤其在沒有法律追究的情況下,犯錯的成本會很低,違法行為發生率會顯著提高。所以從動態的角度去考量小偷不確定的社會危害性,這種預防違法和犯罪的考量是無法以1塊錢來計算的。這個案例不是說明正義與效率的分歧,恰恰相反,它體現了正義是一種長期的、動態的效率。從社會發展來看,花10元錢去抓1元錢的小偷,在今后將會節約一大筆資源,不僅包括經濟資源,甚至包括生命價值和精神損害等無法量化的問題,社會效益才會最大程度地得到實現。 關于正義的內涵,羅爾斯和波斯納持有兩種不同觀點:羅爾斯認為正義能夠使社會中的貧困階層的生活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可以得到已構成社會和將構成社會的每個人的同意。這一點波斯納認同,但是,對于羅爾斯所認為的,“只有當沒有任何其他可選擇的分配方式可以使社會中最貧困者的生活得到改善時,那么現存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才是正義的”[4]這一點,波斯納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完全傾向最貧困者的、更為平等的分配會極大打擊工作積極性,效率降低以至于最貧困者所得到的較大份額收入在絕對數上少于他們在較不平等分配情況下所得到的相對小的份額收入。而此時,這樣的正義明細背離了社會發展規律,不僅起不到促進社會效益的實現,反而會造成普遍貧困,阻礙社會發展,這樣的正義,寧愿不要。這兩種觀點,正體現了隨著時代變化,社會效率變化,正義的內涵不同。我國剛剛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為了提高效率,實現抽象的社會正義,實施先富帶后富的政策,個人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發展舞臺,個人利益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視和尊重。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對個人利益追逐的同時也使得貧富不均的社會矛盾愈發突出,社會的不公正已嚴重威脅到社會的基本秩序。而在此時,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在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轉變,我黨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公平正義,堅持共同富裕的政策。因此,法作為反映社會現實的上層建筑,如何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以一種嶄新的價值理念指導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也成為了法所肩負的神圣使命。可見在我國經濟發展初期,正義和效率的關系就如波斯納所言,正義實現的要求與效率對應的標準是一致的。現在群眾消費由追求基本生活資料數量的滿足,發展到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正義和效率的關系更多地體現在羅爾斯的觀點中。 四、結論 在法律價值評價中,效率已在無形之中融入正義,成為人們的法律思維邏輯,使正義的目標變得明確而易于判斷;在社會效益中,正義與效益兩者相輔相成,克服個體價值的瑕疵,實現1+1>2的社會效益;在社會的不斷發展中,正義是一種長期的、動態的效率,在具體不同時期,側重點又有所不同。可見,正義與效率的融合是社會發展自由選擇的結果,兩者有天然的聯系,是無形中的相互滲透。我們應該看到,在經濟分析法學這門新興學科興起之前,正義與效率的這種聯系就已存在。以自然的心態看待這種固有的結合,會更加符合社會的發展。 再者,社會日新月異,錯綜復雜,還存在極大的地域性差別。若一味地運用經濟分析方法,通過研究法律制度作為社會生活組織的工具在資源配置追求效率目標的過程中將會起到怎樣的作用,以此來解釋正義與效率的關系,將會導致體制的僵化。法律的正義不是經濟領域中效益原則亦步亦趨的追隨者。效率在經濟領域中的優先地位并不能成為法律必須以其作為價值分配的基本原則的根據。法律當然不能完全淪為經濟的奴隸,一旦法律完全依附于效率優先的邏輯,那么它的社會價值和功能便會大打折扣。正義不僅僅代表著經濟資源,片面運用經濟分析以效率評價正義,將經濟公式強加在正義中是不妥的。 尊重正義與效益在生活中各個角落的自由融合,尊重社會發展自由選擇的結果,以實現最佳社會效益,更好地建設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王成.侵權損害賠償的經濟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99-104. [2]張恒山.論正義與法律正義[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1). [3]馬德安.試析法的價值爭議問題——正義與效率[J].法制與社會,2011(21). [4][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