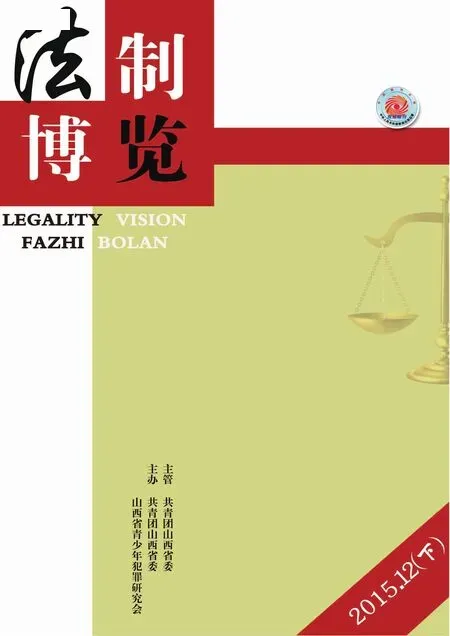論法治社會下弘揚德治的必要性
羅 偉
安徽大學法學院,安徽 合肥230601
在法治環境下對德治進行宣揚并非是無的放矢,德治是對時下社會弊病所進行的診治良方。近幾十年來法治建設可謂是如火如荼,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出臺,法治理念的逐漸普及,司法的日漸獨立,都表明了法治時代的發展與進步。但是,道德水平的滑坡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也不是法治能夠完全解決的。德治既可以因其固有特性對社會治理有所裨益,更因為其作為民族傳統與國情相融而更能被國人接受。
德治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包括道德理念與實施手段兩方面,德最早被認為君主的專屬,道德經中的德經主要就是關于統治天下的圣人之道,從上古時期的人物傳說中我們也能尋找到德的軌跡,舜是我們所標榜的有德君主的典范,其父母不慈,兄弟不肖,舜不僅包容了他們對自己的惡行,更是始終堅持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君主之德也就是君主在治理國家時所采用的原則,這些原則有的也被發展為我們今天所說的道德,例如矜老恤幼。在春秋時期,君主之德演變為君子之德,德既是品行高尚的君子的良好的操守,又是普通百姓的淳樸風氣,論語有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1]道德的高度并非固定,它不僅僅是高尚者的標簽,亦是每一個平民百姓為人處事的潛在準則,這也就為道德的普遍適用提供了可能性;在實施手段上德治以教化為主,以潤物細無聲方式對我們施加影響,“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2]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自然養成道德觀念。因此,德治也就是統治者以道德為根本理念與依據,主要通過教化的手段使百姓從善如流,最終達到人人和諧相處的境界。
德治對法治的借鑒體現兩方面,一方面在于思想理念的補充,一方面在于實施方式的借鑒。禮讓是道德的精華所在,道德更加強調義務,這種義務體現在人與人相處的時候不要過分計較利益得失,“讓則不爭”,法治則有所不同,法治更加強調個人權利而非義務,明確并且注重個人利益的得失,為個人合法利益而斗爭也被認為是法治的應有之義。這兩者看似背道而馳,實則異曲同工。禮讓并非毫無原則的退讓,也并非放棄自己的利益,什么都不爭取,道德在宣揚“禮之用,和為貴”的同時,也提出了“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3]禮讓不是犧牲一方的利益單方面退讓,而是相互之間的行為,在這種互相禮讓的氣氛中,人與人之間的爭端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在涉及到利益沖突的時候,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固然是無可厚非,但是無論處理結果如何,都是對彼此感情的一種傷害,也為之后的爭端埋下了伏筆。
在實施手段上,教化能夠補充法律強制力所不能觸及的領域。法律強制力只涉及行為而不對思想進行規制,教化則通過對思想進行洗禮以約束人們的行為。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4]教化建立在人內心的羞恥感的基礎上,致力于實現人的自我約束,其本質是相信人可以被感化,相信人性善的方面,通過教化使人明辨是非,從而爭端不起,社會和諧;而法治則建立在人性趨利避害的基礎上,國法如爐,觸之者焦,通過禁止的方式使人們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者以德服人,一者以力服人,都蘊含著深厚的人性基礎。從實效性上說,法治的效果可謂是立竿見影,同時也擺脫了對人性善的依賴,更具有普適性,但是在分析人性善惡的基礎上往往發現,社會環境是人性成長方向的重要因素,德治或者法治這兩種不同的治國方略不只是以人性論為來源,更是對人性的引導。“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5]法律文本本身遠遠沒有達到無懈可擊的地步,以法律的漏洞為自己牟利也就成為常態。道德沒有具體的文字,它的作用的發揮并不像法律形于表面,在我們每一個念頭形成的時候,道德就在潛移默化的發揮著作用。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當我們在腦海中排除了不合道德的思想,違法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于無形。“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6]
德治的宣揚帶來了法治公信力的提高。當今時代的法治理念是以西方法治理念為主導的,它與中國本土的傳統有著諸多不兼容之處,同時,中國的法治發展始終還是起步較晚,法治建設進程也略顯倉促,國人的法治觀念尚未完全形成,引進道德觀念有助于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對于法治觀念的形成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對道德而言,將原本屬于法律調整的社會義務納入道德范疇,豐富了道德的內涵,推動了道德的與時俱進,而且,法律在處理道德熱點問題時的傾向性必然帶動了道德觀念的進一步普及。
[1]張晏嬰譯.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07.6.
[2]老子.道德經.
[3]張晏嬰譯.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07.8.
[4]張晏嬰譯.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07:306.
[5]張晏嬰譯.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07.13.
[6]司馬遷.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