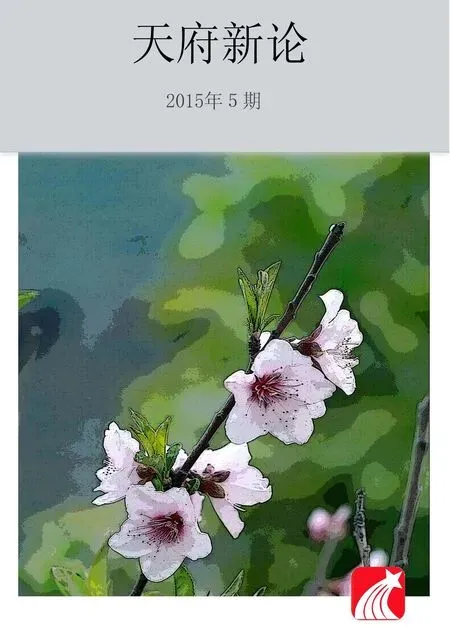嵌入式王權與英國均衡政制
張洪新
一、引 言
英國不存在成文憲法,①當然,在憲法語境下,“成文”這一語詞本身就有模糊性。實際上,無論是成文憲法還是不成文憲法都需要對方的有益補充,參見Ernest A.Yong,“The Constitution Outside the Constitution”,117 Yale Law Journal 408(2007);Jane Pek,“Things Better Left:Unwritten Constitutional Text and the Rule of Law”,83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79(2008).但憲法學者對于英國憲法的“學術典化”卻不曾停止。②對于英國憲法的“學術典化”可以最早追溯到柯克 (盡管只是隱含地),在筆者看來英國憲法“學術典化”的集大成者應該是戴雪,他將英國憲法歸納為議會主權、法治原則以及憲法法律與憲法慣例之間的關系這三項要素,詳細分析參見A.V.Di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6th edition)(London:Macmillan,1902),pp.413-416.實際上,當今圍繞著英國憲法話語的理論爭議,特別是政治憲制主義 (以政治平等和合理分歧為出發點,主張議會至上)和普通法憲制主義 (它堅持法治原則,主張法院至上)之間的分歧,都可以在戴雪的歸納中找到理論支援。對于政治憲制主義的分析,參見Jeremy Waldron,.Law and Disagree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Adam Tomkins,Our Republican Constitution(Oxford:Hart Publishing,2005);Richard Bellamy,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aul Craig,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judicial role:A response,9 International Journal Constitutional Law 112(2011);對于普通法憲制主義的分析,可參見Stuart Lakin,“Debunking the Idea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The Controlling Factors of Legality in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28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709(2008);T.R.S.Allan,“Questions of legality and legitimacy:Form and substance in British constitutionalism”,9 International Journal Constitutional Law 155(2011);對于超越這兩種規范憲制主義的路徑的分析,可參見Jeffrey Goldsworthy,“Homogenizing Constitutions”,23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83(2003);Jo Eric Khushal Murkens,“The Quest for Constitutionalism in UK Public Law Discourse”,29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27(2009);Stephen Gardbaum,Reassessing the new Commonwealth model of constitutionalism,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167(2010).當然,從不同的規范理論出發,不同的學者眼中的英國憲法自然會有一個別樣的形象,由此識別出來的阿克曼意義上的“憲制時刻”也就有所殊異。③在阿克曼看來,美國的憲制敘事是由二元政治所形塑的,包括建國、內戰之后重建時期以及20世紀新政時期三種“憲制時刻”所構成,參見〔美〕布魯斯·阿克曼《我們人民:奠基》,汪慶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1頁。這些不同的乃至沖突的規范理論,就其本身而言,都是融貫的,也為我們觀照英國政制現實提供了某種透鏡。但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相信某種規范理論也就等于是信奉了它的某種前提、概念以及解釋模式,當然也包括它的偏見和先入之見,這就使得有時候某種規范理論所揭示的東西比隱藏的還要多。
因此,從科學方法的角度講,如果我們能夠從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出發,就不應該從某種規范性的理論去發現我們想發現的東西,以至不去看我們不想看的東西。正如迪爾凱姆所說的那樣,“實際上,在任何一項研究中,只有在對事實的解釋達到一定地步時,才可能確定事實有其目的和目的是什么。十分復雜的問題沒有可以立即找到解決辦法的。”〔1〕就理解英國的政制構成而言,筆者認為這里有一個可見而確定的事實,即王權的存在本身,可以為我們拒絕某種規范理論提供理由。
實際上經常的情況是,憲法的性質、議會的行為、黨派的活動以及看不見的輿論的形成,所有這些都是了解起來困難而誤解起來容易的復雜事實。但某個單個意志的行蹤和單個心靈發出的命令,卻是容易理解的東西,任何人都明白這些東西,并記得這些東西。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就在于從作為一種事實的王權出發,追尋其根本,解釋其性質,并探求它在英國政制構成的作用和角色,以看清英國政制的獨特問題以及概觀英國政制構成的整體形態。
二、王權的性質
王權作為英國政制系統的一部分,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政治現實,除了1649年英國人民處死國王查理一世這個特殊事件以外,王權從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艾格博特國王 (Egert)(802-839)一直持續到今天溫莎王朝的伊麗莎白二世女王 (Elizabeth II)(1952-)。在英國整個政制制度史中,從能夠取消王權而沒有取消的意義上來看,①這特別是表現在1215年貴族完全有能力廢除王權或者另立國王甚或以貴族中的某人取而代之的情況下,貴族卻選擇或者說迫使與約翰國王共同簽署通過《大憲章》,在蘇力看來,這一事件不能用貴族的保守或愚忠來解釋,而是他們理性地清楚王權對于英國這個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的重要意義,因為“亂莫大于無天子”,參見蘇力:“何為憲制問題:西方歷史與古代中國”,《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第100頁。王權對于英國政制構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也只有從王權出發,我們才可以理解英國的整個政制構成實踐。“如果從今天反觀英國成為英國的歷史過程,會發現英國憲制的核心問題不是如古希臘那樣以城市共同體為基礎構成一個城邦國家,而是要在英倫三島上,以諸多區域性小型政治經濟社會共同體為基礎,最終組構一個以英王為主權者,政治合法性上不再受控于羅馬教廷的民族國家。英國憲制的其他方面,包括王權與貴族、平民以及再后來與商業階層的先后分權,議會至上以及君主立憲制的確立,包括英國人 (公民)的權利等重要變革都必須以主權為前提。”〔2〕可以說,整個英國政制實踐要么是關于王權的,要么是和王權有關的。英國任何一種政治權力實踐如果不與王權發生聯系,即便這種聯系只是形式上的,則要么這種政治權力不具有政治合法性,要么就不具有政治意義上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解釋王權的性質及其在政制構成中的意義。
(一)作為個人權利的王權
一般而言,所謂王權,指的是國家元首的權力,無論他 (她)碰巧被冠以什么樣的稱號。②對于王權的分析,法國思想家貢斯當 (1767-1830)的最為特別,他以英國立憲君主為模型,將王權界定為一種中立性的權力。不同于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這三類能動的權力,王權調停能動權力之間的糾紛。在貢斯當看來,沒有區分出作為中立性的王權是先前所有憲法的通病。“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是三種各領一方、但必須在整體運作中進行合作的權能。當這些權能的職責被混淆,以致相互交叉、抵觸和妨礙的時候,你就需要一種能夠使它們回到恰當位置上去的權力。這種力量不能寓于三種權能的任何一種之內,不然它會幫助一種權能而破壞其他兩種權能。它必須外在于任一權能,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必須是中立的,以便在真正需要它的時候能夠采取恰當的行動,以便能夠保持或恢復秩序而又不致引起敵意。”參見〔法〕邦雅曼·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閻克文、劉滿貴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在筆者看來,貢斯當對英國立憲君主政制的審視是有失準確的,而且中立性的王權是如何產生的,他也沒有予以論述。這就使得貢斯當對于王權的權力性質理解過于理想化。不過,中立性的王權對于后來司法審查觀念起著重要的啟蒙作用,參見田飛龍:“新君主制與中立性權力:評貢斯當《適用于所有代議制政府的政治原則》中的政體設計”,《天府新論》2014年第1期,第6-11頁。在英國政制體制中,王權的性質首先是一種個人的權利,只不過這個個人是受到英國法律的嚴格限定的,是按照《瑪麗一年法律三》第一章有關王位資格、繼承等相關的法律事先予以確定的。對于王權的分析,布萊克斯通 (1723-1770)就是在《英國法釋義》第一卷“個人的權利”第三章“國王及其資格”中予以展開的。在布萊克斯通看來,有關王位繼承權的憲法概念包括著以下四個方面:(1)在前任王位所有者駕崩或遜位時,王位通常由第一繼承人繼承。王位應該是世襲的,而不是選任的。“為英國法律所認可的世襲權力,其起源應該而且僅應該歸功于我們憲政體制的奠基者。它和猶太王國、希臘和羅馬的國內法沒有關系,也不是以它們為依據的;一個國家的國內法律既不會和其他國家的基本政治體制有何聯系,也不會造成影響。英國君主制的締造者們說不定也會使其成為選任制的君主制,如果他們認為這樣合適的話,但他們有足夠的理性,在締造英國君主制之初更傾向于使之成為通過世襲進行的王位繼承制。”〔3〕(2)就王位繼承的特定方式而言,其與普通法規定的基礎發生轉讓不動產的封建繼承方式大體一致,嚴格遵循男性優先于女性、男性中長子有優先繼承權,代為繼承原則等普通法原則也適用于王位繼承。但也有一些不同,如王位只能由一人繼承。(3)王權世襲的原則并不意味著王位繼承權是絕對不能取消的。毫無疑問,英國的最高立法機構,國王和議會兩院都有權決定破除王位世襲的權利,通過特別限制、預防條款剝奪直接繼承人的繼承權,并將繼承權授予其他任何人。(4)無論王權受到怎樣的限制,即使其有時會被依法轉讓,王權可以世代相傳的本質仍未改變,就加冕者而言,王權仍是世襲的。〔4〕以上四點便構成了英國王權的普遍政制原則,只有按此方式繼承的王權,才構成英國政制體制中的王權。
依據普通法律取得的王權的這種個人權利性質,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英國人的自由和權利觀念不是先天的、自然的。相反,在英國人那里,自由和權利是依據先已存在的法律產生的。正如布萊克斯通所說的那樣,“英國憲法可能是世上唯一一部僅以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為管轄對象并以實現這種自由為終極目標的憲法。這種自由的主要特點,確切地說,應當是一種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做任何事的權利。而只有當各個社會階層、各種社會規則都遵循那些合理的行為準則時,這種權利才能得以實現。”〔5〕換言之,英國人的自由和權利就僅僅是英國人的,既不是古代意義上的自由,也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普世人權。理外英國人的自由觀,對于認清英國的政制構成所要處理的問題,是重要的前提。
首先,英國人的自由和權利和作為個人權利的王權一樣,有著一個共同的來源和基礎,即法律本身。例如,霍布斯就認為,所謂的自由,指的是人們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辦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礙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自由必須是相對于法律、習慣、共同體這些鎖鏈的東西。“如果我們把自由看成是免除法律的自由,那么,人們像現在這樣要求那種自由便也同樣是荒謬的;根據這種自由,所有其他人便都會自己主宰自己的生命了。然而這種事情雖然荒謬,卻是人們所要求的。他們不懂得,法律沒有一個人或一群人掌握武力使之見諸實行,就無力保護他們。因此,臣民的自由只有在主權者未對其行為加以規定的事物中才存在,如買賣或其他契約行為的自由,選擇自己的住所、飲食、生業,以及按自己認為適宜的方式教育子女的自由等等都是。”〔6〕換言之,自由僅僅是個人的,是在法律之下的理性自由。霍布斯進一步認為,“古希臘羅馬人的哲學與歷史書以及從他們那里承襲自己全部政治學說的人的著作和討論中經常推崇的自由,不是個人的自由,而是國家的自由,這種自由與完全沒有國法和國家的時候每一個人所具有的那種自由是相同的,后果也是一樣。因為在無主之民中,那兒永久存在人人相互為戰的戰爭狀態。人們既沒有遺產傳給兒子,也不能希望從父親那兒獲得遺產;對財貨與土地不存在所有權,也沒有安全保障,而是每一個人都有充分和絕對的自由。”〔7〕顯然,在霍布斯看來,英國的革命和處死國王的行為,以及法國反對君主制的騷動,其來源都是一樣,即希臘、羅馬人的自由觀。他認為,正是因為這些虛假的自由觀,才讓現代人養成了反叛國王的習慣。①在英國革命期間,霍布斯是革命的反對者,曾流亡國外。對于新生的英吉利共和國,他肯定不抱好感。他的《利維坦》完成于流亡法國期間,而且可能就是在1649年英國處死國王查理一世之后開始動筆,到1651年左右,當國會軍在克倫威爾率領下,兩度擊敗王黨,國王復辟無望的情況下完成的。在同時期霍布斯流亡之處的法國,也發生了挑戰王權的投石黨運動,法國王權一度遭遇嚴重威脅。這兩大事件無疑深刻影響了《利維坦》的看法。參見晏紹祥:《古典民主與共和傳統 (下卷):現代的闡發》,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頁。
其次,英國人的自由也不是抽象意義上的普世人權。的確,像孟德斯鳩所指出的那樣,英國政體令人矚目的部分就是政治自由。②一般來說,所有國家都有一個相同的目標,那就是保持自己。另外,每一個國家各自還有一個特殊的目標,有的從事戰爭,有的從事征服,然而在孟德斯鳩看來,英國政治體制的直接目標就是政治自由。參見〔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卷),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86頁。維護這種自由的不可侵犯性,就成為英國政治官員的專門職責和正當義務。但英國政體中所說的自由,是那種與秩序緊密相連的自由,這種自由如柏克所指出的那樣,“不僅依秩序和道德的存在而存在,而且隨秩序和道德的消失而消失。自由按其本性只存在于善的和穩定的政府中,一如它存在于政府賴以存在的基礎與根本原則一樣。”〔8〕自由,在英國人那里,就不是對一個人美德的獎賞,也不是一個人的勤奮所得,而是他們的繼承物,是英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抽象地談論普世意義的自由和權利,不僅是無用的,而且是危險的。因為它會教唆民眾輕視他們與政治共同體所達成的有關責任、信任、約定或義務等相關的事情。如果那樣的話,它也會教唆統治者輕視他們與民眾所達成的約定。在這樣的游戲當中,最終的輸家肯定總是民眾。“一個國家的政體一旦依據某種默示的或明示的約定確定下來,那么,任何現存的權力要改變它必然會違反約定,違反各方當事人的意愿。這就是契約的本質。”〔9〕自由和權利是與責任、信任、約定或義務緊密相關的,不論是少數人或是多數人,他們都沒有任意胡為的權利。
總之,王權的這種個人權利性質,并非類似于政府權力的任何一種,因此,關于政治權力性質的一般分析就不能當然適用于王權。但是,同樣按照具有憲法意義的英國法律,一個人一旦按照法律取得了王權,無論獲得王位者是男是女,他 (她)就享有了最高統治權力的一切象征、全部合法性及所有特權。這些權利和特權,顯然不同于普通個人依據法律所取得的種種權利和自由。因此,我們還必須進一步解釋王權對于英國政制構成的獨特意義。
(二)王權的政制構成意義
某種意義上,只要王權是存在的、確定的,我們就可以說英國仍然是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在現代英國,“女王是英國政府的頂端。她是國家認同和國家統一的象征,這種象征在分權 (devolved)的政制體制中尤為重要。”〔10〕因此,英國的政制構成一開始所要處理的問題,就不同于其他國家,特別是不同于通過革命形成的國家。
然而,這并不表示英國憲制問題是易于處理的。實際上,“一旦你從完美的個人自治權當中減去了某些權利,并容許對個人自治權作些人為的、積極的限制,那么,整個政府機構如何建立這樣的問題一下子就成了權衡利弊的問題了。正因為如此,國家建制問題、權力的適當分配問題就成了及其棘手、極其復雜的問題,需要有高超的技巧來處理。它需要對人性、人類需求,以及對社會機制所指向的各種目標達成起著促進作用或阻礙作用的諸多事物,具有深入的了解。國家是要成長的,其失序是要補救的。高談人的抽象的飲食權利或用藥權利,這又有什么用呢?問題的關鍵是獲取、創制它們的方法。”〔11〕英國的政制構成問題,一個重要的方面便是如何在政治權力和個人自由之間劃出一條界線。
首先,作為個人權利的王權對于英國政制的一個重要的意義,便是產生了阿克頓 (1834-1902)所謂的有限政府理念。在阿克頓看來,在英國立憲君主確立以前,曾經存在過民治政府、混合制和聯邦制政府的理念,但是,卻不曾存在過有限政府的理念。換言之,權力范圍受到外部力量限制的國家這種有限政府理念不曾存在過。阿克頓認為,有限政府的理念是哲學已經提出而政治學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雖然那些求助于更高權威的人在政府面前設置了一道形而上的屏障,但是,他們并不懂得如何把它變為真實的屏障。蘇格拉底反對改革后的民主政體的暴政,但是他唯一能夠采用的辦法,不過是為自己的信念而死。斯多噶學派只能建議智者遠離政治,把天道保留在心中。相反,英國立憲的君主政制,不僅頒布法律,而且還創造了實施的力量。“在至高無上的領域保持一個必要空間,將一切政治權威限制在明確的范圍以內,不再是耐心的理論家的抱負,它成為世界上哪怕最強大的機構和最廣泛的組織的永恒責任與義務。這種新的律法、新的精神和新的權威,賦予了自由以新的含義和價值。”〔12〕作為個人權利的君主,通過下面所要分析的某種嵌入式的行動,就可以賦予世俗權力它從未擁有過的神圣,當然也給它加上了它從未承認過的束縛。這既是對專制的否定,也是自由的新紀元的開始。王權及其相關的政治權力由法律所界定和維護,也同時為法律所限制和約束。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作為個人權利的王權,還促生了代議制政府的理念。我們知道,代議制政府在密爾 (1806-1873)那里,不僅是一種政府形式,還意味著一種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在密爾看來,“一切旨在成為好政府的政府,都是由存在于社會各個成員中的一部分好的品質為管理集體事務而組成的。代議制政體就是這樣一種手段,它使社會中現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誠實,以及社會中最有智慧的成員的個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對政府施加影響,并賦予他們以在政府中較之在任何其他組織形式下一般具有的更大的影響。”〔13〕問題在于,為什么是作為個人權利的王權能夠催生出代議制政府呢?理由是這樣的:我們知道,作為個人權利的王權一旦按照法律由某個人確定地獲得,在英國的政制中,所有的權力在象征的意義上就是都屬于國王。①當然,在人民授權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由人民所有。正如本文下面分析所要表明的,英國政制得以成功的關鍵就在于它以嵌入式王權構造了一種均衡政制,從而最終實現了人民的意志。重要的是,在王權已然存在和繼續存在的意義上,關于政治權力所要爭論的就不是權力屬于何人所擁有,而是權力應該如何運作和使用。前者能夠喚起人的欲求,而后者則涉及責任、義務和信任。
實際上,正是權力的運作形式和方式,而不是權力會落入何人之手,將國家攪得不得安寧,而對后者的爭論簡直就是在無政府和暴政之間反復徘徊。“教導人們渴求權力,那大可不必。不過,用道德訓導他們,用法律制度強制他們,使他們無節制的權力濫用和貪婪的權力欲求有所收斂,那倒是十分有好處的。找到實現這兩大目標的最佳方案乃是真正政治家面臨的重要課題,同時也是難題。在考慮授予政治權力時,真正的政治家關注的唯一問題是:如何才能把有益的制約和明智的引導或多或少地落到實處。”〔14〕正如密爾所指出的,代議制正是一種將權力掌握在人民可以接受的人手中的一種重要政府組織手段。同樣,對于代議制的重要性,休謨 (1711-1776)也做出了同樣的論述。在休謨看來,“羅馬共和國的政治體制將整個立法權授予人民,貴族或執政官均無反對之權。這種無限的權力由人民集體享有而不是由一個代表機構享有。其結果是:后來人民由于興旺發達和對外征服,人丁繁衍,擴散到離首都很遠的地方。這樣一來,幾乎一切選舉表決都由城市居民行使,盡管他們是最令人看不起的。他們因而受到每一欺世盜名之徒的哄騙。他們享受普遍配給的谷物,幾乎從每個候選人那里接受特殊賄賂,過著閑散的生活。他們因此日益放縱,而馬梯耳斯廣場成了經常發生騷亂和暴力的場所。后來在這些無賴市民中又引進了武裝奴隸,整個政府因而陷于無政府狀態,而羅馬人當時所能尋求的最大幸福,就是凱撒的專制權力,這就是沒有代議制的民主產生的惡果。”〔15〕代議制不僅在理論上是好的,而且在實踐中也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政制構成。
對于代議制,在現代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說,不去爭論權力屬于何人,或者說哪個人具體地表象了權力自身,而是深究使用權力的方式和程序,并以此形成一種周期性的、持續性的爭辯和較量,是為代議民主的本質。②See C.Lefort,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Polity,1989),p.225.代議制民主,改變了權力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但代議制為政制體制具體設計,同樣也提出了許多難題。對于英國政制構成而言,問題是作為象征性的王權,在政制結構中是如何發揮作用以及充當何種角色,如果它僅僅是象征性的話。③在羅馬王政后期,羅馬平民和貴族就土地和債務之間的糾紛和斗爭異常尖銳,于公元前494年發生了平民第一次撤離運動,即平民利用強敵壓境的機會,攜帶武器,離開羅馬,到阿尼奧河對岸的圣山單獨建立的自己的營地,建立平民政權,以此與羅馬貴族對抗。羅馬派去談判的使節講了如下一個故事,“那個時候人體不像現在那樣協和一致,而是每個部分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語言,各部分發出抱怨,它們以為自己的關心和努力所獲得的一切都是為了伺候胃,而胃安靜地處于身體中央,除了享受為他提供的各種快樂之外,其他什么事情也不干。他們一致商定,從此不再往嘴里送東西,牙齒不再咀嚼接受的東西,當它們這樣憤怒地想用饑餓制服胃的時候,身體各部分自己和整體身體也陷入了極度的消瘦。這時大家才發現,胃也不疏于職守,它不僅受撫養,而且也撫養,把我們賴以生存和強健的東西規劃給身體各部分,食物被消化后形成的血液被均衡地分流在各處血管里。”參見〔古羅馬〕提圖斯·李維:《自建城以來》,〔意〕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王煥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5、87頁。在這個意義上,王權之于英國政制的作用,也可能像胃之于身體的那般重要。這是我們接下來予以回答的問題。為此,我們必須在整個英國政制結構中再次審視王權的政制構成含義。
三、政制結構中的王權
既然王權在性質上講主要是一種個人權利,又既然王權在政制構成中的意義主要是象征性的,那么,這種意義上的王權,能夠在政治權力結構中占據什么角色和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呢?我們知道,由于王權在政制構成中的這種象征作用,在英國所有的政治權力運行都只有與王權建立起某種聯系,才能取得國家層面的意義和重要性。這樣,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王權要想行動 (action),而不是僅僅是個人權利范圍內的行為 (behavior),就必須嵌入到某種政治權力當中。④行為和行動是根本不同的。在阿倫特看來,行為可以是個人的,但行動則必須在關系中,以人的復數性為基本境況。通過言說和行動,人使自己與他人區別開來,而不僅僅顯得與眾不同。去行動,在最一般的意義上,意味著去創新、去開始,去發動某件事,人能開端啟新。參見〔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139頁。因此,問題就是,王權和政治權力之間發生作用和聯系的媒介是什么,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這種媒介的性質。所有人都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這個答案的重要性。
(一)作為承認規則的主權
毫無疑問,王權和政治權力之間發生作用和聯系的媒介就是一般性的規則,即法律,也就是某種特殊意義上的具有憲政含義的法律規則。問題在于,為什么一定要如此,特別是這種一般性的規則是如何確定的。我們知道,王權作為一種權利,從性質上說雖然是個人性的,但王權在作為一種政制構成時,王權的行動僅僅限于與政府權力之間,即便是與個人的行為交往,也必然蘊含著某種政治上的意義和作用。我們很少看見作為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以及國教教會領袖的英國國王 (女王),能夠像普通個人那樣去行為,去展開相應的行動。
重要的在于,主體間性的交往就必然產生某種交往規則的需求。就像休謨所指出的那樣,“人們在路上行走時互讓也不能沒有規則。趕大車、駕馬車以及驅趕驛車都各有其讓路的規則;而這些規則均以相互方便為基礎,當然有時也可能是任意規定的,至少有些變化莫定,就像律師們的許多論斷一樣。”〔16〕因此,決定規則的具體形式和內容的主權掌握在誰手中,就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英國一些被稱為具有政制構成意義的法律,如1628年的《權利請愿書》、1679年的《人身保護法》、1689年的《權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憲政意義,①《權利法案》首先列舉了詹姆士二世破壞憲政的種種行為,提出了限制王權的13條規定。其中關鍵的條款有:第1條,凡未經議會同意,以國王權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實施之僭越權力,為非法權力。第4條,凡未經議會允許,借口國王特權,為國王征稅,或供國王使用而征收金錢,超出議會準許的時間或方式者皆為非法。第6條,除經議會同意外,平時在本王國內招募或維持常備軍,皆屬非法。第9條,議員在議會內有演說自由、辯論或議事之自由,議員不應在議會之外任何法庭或在任何地方受到彈劾或訊問。參見閻照祥:《英國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頁。特別是1701年《王位繼承法》,一方面從制度上讓王權徹底擺脫中世紀以來一直以某種方式凌駕于歐洲各封建君主國之上的羅馬教廷和天主教的力量,根除了斯圖亞特王朝再次復辟的可能。另一方面,制定該法案的行動本身,即議會可以議立新君,是對“君權神授”思想的一次思想沖擊,是“天賦人權”觀念的重大勝利,對此分析參見龔祥瑞:《比較憲法與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頁以下。主要是因為誕生了“國王在議會”這種新的政制構成。②實際上,據史書記載,早在14世紀中葉,英國就已經萌發了“國王在議會”這一習慣法原則,即法律的制定和廢除只能借助于議會成文法,而成文法又只能在“國王在議會”的情況下制定。但這里應當指出,“國王在議會”這時期主要是就憲法意義和國王的實際立法作用而言,卻并非意味著國王可以任意或者隨時參加議會的辯論和立法活動。某國王若要前往議院,也主要是去履行其崇高的、形式主義的職能,即去出席并主持議會開幕和閉幕形式,并在閉幕會議上允準或否決議會呈遞的法案。對此的一個簡要分析,可參見閻照祥:《英國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9頁。主權,即創造政治交往規則的權力,不再僅僅屬于國王,而是屬于議會。但由于國王同時也是在議會中,而不是排除在議會之外,我們也可以說是由國王和議會兩者共同分享了主權。國王在議會,在法律的意義上,便是恢復了政治權力擁有者的主體性。在深層的意義上,則是體現了人類生活交往中互惠這項根本性的原則。主權的意義就在于它是一種哈特所說的承認規則。③承認規則指出某個或某些特征,如果一個規則具有這個或這些特征,人民就會決定性地將這個規則當作該共同體的規則,由社會的壓力予以支持實施。參見 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secon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94.無論承認規則是什么,也盡管有時對于承認規則的具體內容的解釋可能存在合理的分歧,但承認規則本身都必須是存在的。
當然,從承認規則的角度理解主權,這一論斷并不新鮮。實際上,在當代英國關于主權的理論爭論當中,④關于英國議會主權的思想史演變分析,可參見田飛龍:《英國議會主權的思想史演變》,《環球法律評論》2014年第3期。基本上都是把主權理解為承認規則作為出發點。盡管如此,筆者以為,論者對于承認規則仍然是在狹義上理解的,即為了確定法律是什么,這樣,他們就看不到對于主權一個更為寬廣的含義。例如關于議會主權,在英國的憲制話語中,普通法憲制主義的主張者認為,在形式上,以正當形式通過的議會法律是法律的最終權威,法院不能拒絕法律。但在實質上,為了確定法律是什么,特別是在爭議性的案件中,對主權存在著實質性的限制。議會是主權,僅僅是在法規文本的意義上擁有法律權威。議會主權要想獲得實踐上的意義,必須從法治、司法獨立以及包括自由和權利的代議民主等實質性的憲法原則中汲取合法性資源。議會主權,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種普通法學說。⑤See T.R.S.Allan,“Questions of legality and legitimacy:Form and substance in British constitutionalism”,9 International Journal Constitutional Law155,157(2011);see also N.W.Barber,“The afterlif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9 International Journal Constitutional Law 144(2011).相反,政治憲制主義的堅持者認為,即便是在實踐中議會可能受到實質性憲法價值,尤其是人權法案的限制,但最終的法律權威仍然在議會,因為議會對于實質性的憲法價值盡管有義務,但它們仍然有非常大的裁量權,而且議會也可以推翻法院的判決。①See Richard Bellamy,“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86,90 - 93(2011).第三種觀點認為,為了確定法律是什么,議會對于法律的確定仍然是必要的,但作用并不充分。只不過,需要將法院對于實質性價值解釋納入法律界定當中。因此,所謂的主權便存在于法院和議會兩者所共同確立的構成性規則之中。②See Alison L.Young,“Sovereignty:Demise,afterlife,or partial resurrection”,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163,170(2011).
在筆者看來,關于主權的懷疑中所提出的這些問題雖然非常出色,但也同樣危險。盡管有分歧,但它們所探究的是“在法律上誰是承認規則的最終權威”這個問題。如果在這樣的層面上討論問題,就很難做出一個肯定或否定的最終回答。答案會在議會和法院之間來回擺動。不過,如果我們可以選擇不再追問“誰”(who)的問題,而是試圖回答“怎樣”(how)這個問題的話,那么,我們關于承認規則的理解,就不再僅僅是在法律的層面上弄清誰是法律的最終權威,而是將法律的含義拓展到作為一種更為寬廣視野下的一般性交往規則,進而探究這種一般性的交往規則是如何確立和修正的。在此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夠進一步回答主權的自我限制這個經典的問題。③戴雪認為議會主權是最高的,議會不能限制它的繼承者,參見A.V.Di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6th edition)(London:Macmillan,1902),pp.37-52.實際上,這一點已經成為了英國政治憲制主義的共同信念,而政治憲制主義之所以在英國成為主導性的憲法話語,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戴雪的這一著名論斷。如果對議會主權僅僅從法律的角度予以分析,議會當然是不能自我限制的。但是,從一般性交往規則的角度分析,答案就不同了。交往性規則所承諾的是主體間性,而不是某種最高的單一主體。
實際上,當作為主權的議會不能自我限制時,呈現出來的活憲法理念便僅僅是進化論的形式,即“憲法不是存在的一部分,而是不斷生成的過程”。〔17〕但從政治的角度,活憲法的理念可以也應該以政治發展或者政治轉型的方式予以展現。④See e.g.,Bruce Ackerman,“The Living Constitution”,120 Harvard Law Review 1737(2007).因此,對于主權概念的含義,我們必須在法律和政治上做出區分。在法律上,主權雖然是最高的,但它并不是沒有界限的。例如在洛克那里,立法權雖然是一國的最高權力,但,(1)立法權對于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絕對地專斷的;(2)立法或最高機關不能獨攬有權力,以臨時的專斷命令來進行統治,而是必須以頒布過的經常有效的法律,并由有資格的著名法官來執行司法和判斷臣民的權利;(3)最高權力,未經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財產的任何部分;(4)立法機關不能把指定法律的權力轉讓給任何他人。〔18〕主權的界限是由主權本身的法律性質和外在目的所規定的。但是,法律上的界限不能等同于政治上的受限制。主權在法律上如果受到限制,在法律上它就不是最高的,也就不存在主權。但主權可以在政治上受到約束,實際上也必須受到約束,這樣一國的政制構成才能夠發展和轉型,而不僅僅是展現為一種不斷生成的過程,進而抽空了政制實踐的背景性和結構性要素。
在政治上,特別是政制構成的意義上,主權雖然在法律上是最高的,但主權本身卻是受限制的,它所確定下來的具有政制構成意義上的規則和慣例就可以也應該被后續的主權者所修正,當然也能夠修正它之前的主權者所制定的具有政制構成意義的規則和慣例。具有政制構成意義的規則和慣例是在為漫長的歷史實踐所證實的意義上被確立起來的。它們可能要以通過承認規則來加以修正,但這絕非簡單的廢除和修正。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它可能是憲法的崩潰,或者可能是一種確切意義上的革命,而不是對憲法的一種有效修正。像羅爾斯所說的那樣,“一詞修正并非只是一次改變。修正的理念之一,是為了使基本憲法價值適用于不斷變化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或者說,是為了使合并后的憲法對這些價值有一種更廣闊更具包容性的理解。”〔19〕主權自我限制,這種情況并非不可思議。事實是,憲法理念以及原則在許多個世紀里的成功實踐,對我們現在可以視為修正的內容定下了種種限制,無論這一點最初是否屬實。政制實踐不是抽空歷史和背景性的發展,而是深嵌于某種結構和原則敘事之中。對于英國憲法而言,制憲所體現的就不僅是一種政治過程的結束和目的,而毋寧是開啟了一種嶄新的不同的政治類型,特別是當憲法的根本特征與政體之間的聯系處于利害相關時。⑤See Macro Goldon,i“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Constitution-Making”,27 Ratio Juris 387,394(2014).
總之,議會雖然在英國政制構成中是地位最高的,但議會仍然受到自身的限制。在英國的政制實踐當中,為了更有效地行使權力,主權機關必須培養對可靠性的尊重,這就要求主權者依據規則而不是專斷的命令來進行統治。在英國政制體系中,這些規則經常不僅僅包括通常意義上的法律之治,而更多的是一些眾所周知的憲法慣例。這些實踐性、演進性的權威可以視作自我約束原則的表現,是間接增強統治能力的有效技術。通過非正式實踐的運行 (這種實踐確保權力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之下展開運作),并通過政治程序,因為我們可以訴諸公民自由的傳統來確保我們免受法律剛性之苦,主權與自由就可以交織在一起并和諧一致,“議會主權的概念構成了英國憲法性法律的根基與恒久依賴的實踐。”〔20〕
(二)嵌入式王權的兩種含義
王權的具體形式和范圍,由議會所制定的普遍法律所規定,這一點還具有重要的行動意義。由于“國王在議會”,國王雖然可以依據相應的法律規定和憲法慣例進行相應的行為,但是,王權單獨作為一種行動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不存在的。在政治權力的意義上,王權要想行動,就必須在議會中行動。換言之,王權必須嵌入到某種政治權力之中才能進行憲制意義上的行動。因此,行動意義上的王權的性質也就隨著所嵌入的政治權力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權力形態。
國王在議會中,表面上國王所分享的是立法權力,但其首要行動結果卻是造成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之間的必要阻隔,行政權是立法權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這一點對于保持政體各部分間的平衡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如果立法機構與行政機關完全合而為一,立法機關會不斷地侵犯行政機關的權力并逐漸越俎代庖承擔起行政機關的職責,從而很快變得專制。在布萊克斯通看來,“一旦上下兩院將國王排除在外而自行掌握了立法權,他們很快就取得了對行政機關的控制。這兩種權力統一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上下兩院推翻了當時的教會和政府,并實行了與他們自稱希望改善的政府相比更加變本加厲的壓迫。正是為了防止這種侵占行政權的情況發生,國王才必須是議會的一部分。”〔21〕當然,也正是出于同樣的理由,立憲君主予以確立時期的英國憲法所允許國王分享的立法權也僅僅局限于拒絕接受上下兩院的決議,而非參與決議的權力,這已足以滿足行政機關作為立法機關一部分的目的了。因為“國王實際上沒有任何不法行為的能力,而僅僅只有防止不法行為發生的權力。國王不能牽頭對現有的已經確立的法律進行任何修改,但對于上下兩院提議并通過的對法律進行的修改,國王有權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因此,未經行政機關同意,立法機關無法削弱法律賦予行政機關的權力,因為,除非所有的權力機關都同意對其進行修改,否則法律必須維持原狀。而這實際上正是英國政府的組織形式真正精妙之所在,即所有的政府組成部分彼此之間相互制約。”〔22〕因此,當國王一旦決定嵌入在議會中行動,其發揮的作用不是立法性的,而是具有審查意義上的準司法性的權力。
這樣,在英國,立法機關中平民和貴族相互制約,因為雙方均擁有否決對方決議的特權;而平民和貴族又共同受到國王的制約,以防止立法機關侵犯行政機關的權力。行政權力又受到上下兩院的制約,從而被限制在一個適當的范圍內,因為上下兩院享有對國王身邊心懷叵測的顧問而非國王本人的所作所為進行調查、彈劾和處罰的特權。英國立憲的君主政制如此構成的結果便是,各個部分間既可以相互支持又相互規范,“因為從本質上說,上下兩院必然會驅使政府朝兩個分別代表兩種相反的利益的相反的方向發展,這樣一來,它們相互間可以制約其余兩方不至逾越恰當的界限,從而保證政府作為一個整體不會分崩離析,而與此同時,其中各個部分也因國王這種既是立法機關的一部分、又是唯一的行政機關的混合性特征而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這就像三個不同方向的機械力,它們共同推動政府這臺機器朝著與這三個單獨作用時所指的方向都不相同的另一方向前進,但與此同時,這個方向其實又是這三個力同時參與其中,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這個方向所指引的正是社會的自由與幸福的真正軌跡。”〔23〕
總而言之,王權的這種嵌入性對于英國政制構成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于,議會所制定的一般性法律就能夠發揮成文憲法的功能,某些法律可以成為我們所謂的憲法性的法律。在筆者看來,英國之所以不需要成文憲法,很大部分的原因就在于此。在英國,我們可以說一切具有政治性的問題,都可以用普通法律的形式予以解決。正如洛克林所說的,“在某種程度上,建立根本法的框架表達了所有的政治爭議最終可以在法律中發現答案的理念,這種成就也極易導致在法律過程中體現出嚴密的政治特征來。”〔24〕普通法律是英國法院必須予以嚴格適用的,法院不得拒絕適用或者徑直宣告無效,因為這些普通法律的某些規則可能具有憲法上的意義。
另一方面,既然王權只能嵌入到某種政治權力之中才能展開相應的行動,那么,基于本文的目的而言,所需要進一步分析的問題便是,王權應當如何、在什么時候、以何種方式嵌入到政治權力當中,從而維護政制構成中的權力平衡,保護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四、一種真實的制衡結構
英國自“光榮革命”之后,就像其它國家一樣,英國政制也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三權分立,英國的政制結構是混合的,是階級分權以及職能分權的合二為一。①實際上,在英國,早至15世紀混合憲制概念就已經萌芽。約翰·福特斯丘 (1395-1477)在《論英格蘭的法律和政制》中,就把各國政體歸為三種:君主型、政治型和混合型。其中第一種是通過侵奪性手段建立的,第二、三種是由公民建立。英國政體屬第三種,英國人為維護法律,保障國民人身財產安全而設立了王位。參見〔英〕約翰·福特斯丘:《論英格蘭的法律和政制》(劍橋影印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頁以下。對于英國分權理論的演進,詳細的分析可參見〔英〕M·J·C·維爾:《憲政與分權》,蘇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9頁以下。通過王權的嵌入式行動,英國的政制權力結構也形成了某種均衡。正如休謨所指出的那樣,“各類政府,自由的和專制的,看來在現代都發生了大的變化,不論在外交和內政上都變得較前好多了。權勢均衡是政治上的秘訣,只有在現代才充分為人知曉。”②〔英〕休謨:《休謨政治論文選》,張若衡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58頁。休謨認為,政治上的一條普遍真理是一位世襲的君主、沒有奴仆的貴族和由代表們行使選舉權的人民,構成最佳的君主制、最佳的專制和民主,參見〔英〕休謨:《休謨政治論文選》,張若衡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8頁。但英國這種均衡的政制結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理論上的,無論是布萊克斯通還是休謨,都沒有對于英國均衡政制進行實踐上的檢驗,更沒有具體指出英國政制均衡在實踐中是如何發生和運作的。因此,要想真正地確立嵌入式王權在英國政制構成中的真實作用,我們必須分析英國的政制構成實踐,特別是分析隨著1832年將選舉權擴大到中產階級的議會改革之后,英國政黨政治的興起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責任內閣制的最終確立和發展 (這一點標志著延續至今的英國議會制模式的成熟),在王權基本變成“虛君制”的情形下,③所謂的“虛君制”,只是在相比1832年議會改革之前說的。在憲法意義上,國王仍然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國教教會領袖,可以任免首相、大臣、高級法官和海外殖民地總督,有權晉封貴族、任命大主教和主教。關于1832年議會選舉改革的詳細分析,可參見閻照祥:《英國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8-291頁。嵌入式王權在英國政制中是否仍然具有制衡的作用。
復雜地區地震勘探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噪聲問題,對復雜地區的地震勘探而言其噪聲類型繁多,嚴重影響資料品質,因此,如何壓制干擾波是復雜區地震勘探的主要問題之一。山地地震勘探中的干擾大致可分為環境干擾和激發后的半生與次生干擾2大類。因此,要進行波場調整,并針對資料影響較大的干擾設計組合圖形,壓制干擾,提高資料的信噪比。根據干擾波的特征,把沿測線方向最強的一束干擾波作為主測線組合檢波的壓制對象或組合檢波縱向組合基距的考濾對象;把垂直測線方向最強的一束干擾波作為聯絡測線組合檢波的壓制對象或組合檢波橫向組合基距的考濾對象;還可以通過適當的提高地震儀器低截濾波參數或使用高頻檢波器進行壓制。
(一)內閣制中的安全閥和調制器
我們知道,在政體分類上,英國屬于議會制國家。但使英國議會制區別于其它國家的,便是英國1832年議會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責任內閣制。一般認為,英國的責任內閣制具有以下三個特點。〔25〕(1)首相和內閣需從下院多數黨中挑選,并依靠其多數優勢以保證政黨政策和法令的順利實行,首相而不是國王主持內閣工作,政府失去下院信任后必須辭職或重新進行選舉。(2)所有閣員對政府集體負責,并與首相共進退。大部分學者認為,這是英國責任內閣制中最重要的一點,這就使得內閣所有成員維護內閣的“集體形象”,注意保持執行本黨政策的一致性,而首相的失敗意味著整個執政黨的失敗,所有閣員同首相一道辭職。(3)政府在大選失敗后必須立即辭職。議會改革前,內閣的組成和倒臺與議會的召開和解散的時間不一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系統性的全國政黨組織沒有建立起來,這就使得政黨領袖無法得知所有議員特別是新當選的議員的政治態度及黨派歸屬,必須要等新議會召開后,根據分組投票驗明兩黨的議席分配。到了19世紀60年代,全國性政黨組織的建立,使得在投票結束后,議會就可以確定它們各自政黨的席位數,而不必經過分組投票驗證。
對于責任內閣制的確立和發展之于英國政制構成的影響,為同時期的著名憲法學者白芝浩(1826-1877)所敏銳地指出。④在“再版導言”中,白芝浩一開始就指出了描述活生生的英國憲法的困難,即所要描畫的對象一直是變動不居的。因此,白芝浩將英國憲法的論述限定在1865-1866年之間的憲法,并沒有對后來英國政制發展起著同樣重要作用的1867年議會改革法做出評估,在他看來試圖評估其影響還為時過早。參見〔英〕白芝浩:《英國憲法》,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5-6頁。在白芝浩看來,任何一種政制體制都應該包括“尊嚴”(the dignified part)和“效率” (the efficient part)兩個部分。在英國憲法中,尊嚴部分屬于王權和王室,效率部分則屬于議會和內閣。“政制中富于尊嚴的部分給予政府力量——使它獲得動力。政制中富于效率的那部分只是使用了這種力量。政府中體面的部分是必須的,因為其主要力量就建立在這部分的基礎之上。就做某件確定的事情而言,它們不一定比一個更簡單的政體做得更好;但是,它們卻是所有工作賴以完成的必要前提。”〔26〕白芝浩認為,英國政制成功的關鍵就在于內閣。所謂的內閣是一個混合的委員會,它連接的是英國政制體制中立法部分和行政兩個部分,是一種“連字號”。用白芝浩的話說就是,“英國的體制不屬于立法機構對行政機構的吸收,而是兩者的融合。要么內閣立法和行政,否則的話它可以行使解散權。它是一個被創造物,但是它有權毀掉它的創造者。它既是一個由立法機構任命的行政體,又是一個可以消滅立法機構的行政體。它是被造的,但可以破壞;從起源上講它是派生的,但在行動中它卻具有毀滅性。”〔27〕內閣是由立法而生,由行政所撫育和長成,最終又受司法所教育和渲染。內閣可以游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間,擁有三張可以隨時變換的面孔。
總之,在白芝浩那里,英國政制的成功主要是因為英國憲法有特別的規定,這個規定將行政結構的選擇權放在了“人民院”的手里。但是,白芝浩進一步認為,如果不是還存在兩個部件,即白芝浩稱之為憲法的“安全閥”和“調制器”的話,這種成功還不會完全獲取。具體而言,就憲法的安全閥而言,它指的是為消除平民院對于行政政策和決議所造成的阻力,行政首腦所能夠采取的措施,即“行政首腦可以通過選任下院的方式消除下院的阻力;如果他找不到一個多數,他可以制造一個多數。這是一種最真實的安全閥。它使民眾意志——行政機構是這種意識的代表,也是這種意志的被指定者——能夠在憲法的范圍內將憲法的一個分支所不喜歡和抗拒的意愿和觀念付諸實施。它使一種被抑制的權力的危險聚積得到了釋放,而這種聚積是可能使憲法受到沖擊的,就像類似的聚積已經經常沖擊了類似的憲法一樣。”〔28〕
另一方面,白芝浩還認為,立法機構中民眾分支作為一個主權者有三個缺陷,即多變性、黨派性以及自私性。〔29〕為此,必須賦予行政首腦某種類似于單一主權的調制器的東西,即解散本可能成為擁有至上權力的議院的那種權力。在白芝浩看來,英國憲法的調制器產生效果的方式是顯而易見的,調制器的存在就可以使行政首腦對某個平民議院中的某些或者全部議員說:“你們這些議員沒有恪盡你們自己的職守。你們是在以國民為代價滿足議會的多變性,沉溺于派性精神,以及自謀利益。且讓我將你們解散,好讓人民重新選舉代表人民真正利益的平民院。”可見,在白芝浩意義的政制構成中,議會至上意味著平民院至上,而平民院背后真正君主則是行政首腦,后來的內閣“首相”。①1905年12月,經國王愛德華七世批準,行政首腦正式被批準授予“首相”的稱號,在法律上明確了首相與其他閣員的主次關系。而自此之前,歷任“首相”都是以財政大臣、外交大臣或掌璽大臣的名義行使最高行政權的,其地位一向不明確。
進一步分析我們就會發現,白芝浩對于英國政制構成的分析是以政府事務的單一性和統一性為旨歸的。毫無疑問,單一性和統一性在政治活動中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區分和界定它的部分,但政策是統一的和整體性的。人類事務的交叉性要求一種單一的決定力量;用一種分散的力量去雕琢每一個人工的物件,結果只會造成一種駁雜的品成物,如果這種力量存在得足夠持久以便能夠做成任何東西的話。英國憲法的精致之處在于,它達成了這種統一性。”〔30〕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安全閥和調制器是為英國政制的效率所服務的,是內閣在有效政府治理遇到障礙時所擁有的附加砝碼和額外籌資。
(二)作為緩沖器的王權
在白芝浩所的概括中,內閣制已經成為英國政制構成的核心。因此,立法權和行政權的融合確實成為英國憲政成功的秘密。但是,白芝浩所理解的英國政制構成仍然是以有效地政府治理為價值預設和前提,這種政制模式非常適用于緊急情形。用白芝浩的話說就是,“一種已經形成的輿論,一個受尊重、有能力和守紀律的立法機構,一個精選出來的行政機構,一個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拆臺的議會和政府,在重大事情來臨時就顯得特別重要——此時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此外,議會制或內閣制政體在非常危急時刻能夠體現出某種額外和特別的優勢。它具有我們可稱之為適合于處理極端緊急事件的權力儲備。”〔31〕但白芝浩所沒有注意到的是,高效的政府權力運作,仍然可能有侵蝕權力自身的風險,轉化為一種暴政。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內閣制僅僅是聯結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居中機構,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英國政制構成的組成部分,更不意味著政制結構的全部。這臺高速運轉的政府機器,如果沒有某種具有緩沖作用的器件,就會奔著娛樂至死的方向而去。而且,如此理解的英國政制實踐就是一種不斷生成的政治過程,而抽空了實踐中的歷史和背景性因素,英國整個政制的發展和轉型都變得不可理解。如果是這樣的話,政制結構和要素,就僅僅是程度的不同,而沒有實質上的區別。換言之,對于理解英國政制結構,白芝浩意義上的英國政制構成仍然缺少了一環。
那么,這缺少的重要一環是什么呢?如果我們以美國的政制構成為模型,對此的回答顯然是具有司法審查權的最高法院。①美國憲政的典型特征便是阿克曼所謂的二元政治,與一元論者相對的是,阿克曼認為不能僅僅由于司法審查剝奪了國會制定任何它想制定的法規的全面權威,它就可以被推定成是反民主的。與權利本位主義者不同的是,阿克曼也不認為最高法院運用哲學方法闡述對所有時代和所有地點都有效的基本人權這種做法是恰當的。與此相反,最高法院的工作在于維持人民所實現的高級立法方案在日常政治期間免受侵蝕。參見〔美〕布魯斯·阿克曼:《我們人民:奠基》,汪慶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頁。但我們分析的是英國的政制構成,因此,美國意義上的具有司法審查的最高法院就不是一種唯一選擇,仍然存在著其他可能,可以制約立法權力的任意運行從而維護現行憲法秩序,從而達成權力之間的某種制衡。就制約立法權力的任意運行而維護現行憲法秩序而言,如果說這就是司法審查的 (部分)含義,那么,在英國政制構成中,起這種制衡作用的便是議會中的上院,即貴族院。②See Rivka Weil,l“Evolution vs.Revolution Dueling Models of Dualism”,54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29,469-471(2006).實際上,從1832年議會改革法出臺以來,貴族院就已經成為一個修正性和擱置性議院。它可以改變法案,也可以拒絕平民院中尚未完全議定的那些法案,即民眾尚未決定的那些法案。貴族院不再是一個潛在的領導者了,而變成了一個暫時的拒絕者和明顯的改變者。換句話說,貴族院成為了現存政制秩序的保持者和守護者。
當然,公正地說,白芝浩也注意到了貴族院在英國政制系統的重要作用,“所有邪惡利益中最危險的莫過于行使行政權的政府的利益。因為政府是最有權勢的。完全有可能出現這樣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已經出現過,而且將來還會出現,即在下院中擁有強大勢力的內閣可能將一些細小的措施強加給國民們,而這些措施是國民們所不喜歡的;但又由于對其缺乏足夠的了解,因此國民無法予以阻止。因此,如果能夠找到一個修正性團體,政府盡管有勢力,但這種勢力不那么強大,那么,政府的行為就會規矩得多。一個延緩性議院可以阻止輕微的議會專制,盡管它難以防止或組織革命。”〔32〕但是,深究起來,白芝浩對于貴族院的分析,更多的是批評,而不是肯定;更多的是懷疑,而不是一種積極的理解。“貴族院的事情不僅做得不完美,而且經常做得縮手縮腳。貴族院不過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但它卻害怕這個國家。”〔33〕白芝浩并沒有準確地認識到貴族院之于英國政制構成的意義。白芝浩也沒有注意到的是,如果能夠起到緩沖作用的貴族院,總是一味地拒絕和否定,那么,整個英國政制系統會怎么樣。換言之,貴族院雖然能夠起緩沖的作用,但它仍然不是英國政制構成中的緩沖器本身。
在筆者看來,這個能夠作為緩沖器的東西,便是王權。具體而言,便是國王所具有的對于貴族院成員的任命權。盡管新貴成員的冊封,在實踐中仍然很大程度上由內閣制的行政首腦操縱,但國王在憲法上可以拒絕或者做出改變后予以接受。有時候,現象就是本質。國王對于冊封新貴族的威脅就是英國政制實踐這一現象的本質。當然,在實踐中,這種權力并非總是被使用,但其存在本身能同它的能量一樣有用。就像當一個老板得知他的雇工可能舉行罷工時便進行妥協,以期他們可能不舉行罷工一樣,當貴族院得知它有可能在國王的意志下被淹沒或者耗散時,就可能不再是一味地屈服和抵抗,最終不得不做出相應改變。
但是,這里仍然存在著一種風險,王權應該什么時候嵌入到政治權力,如果他仍然希望保持貴族院本身的獨特作用,而不是使其變成一種形式上的機構、一個清閑的養生館的話。如此擔心的結果便是,在英國政制結構中,主權的三個地位同等的構成部分,即君主、平民院以及貴族院,都有停止整個政府機器的權力,它們都指望通過行使該項權力來改善它的地位,并且各自充分行使各自的權力。毫無疑問,如果每個構成部分感到自己受到其他一個或兩個部分的攻擊,當然就會運用其全部權力進行防御。那么,英國政制系統又是怎能防止權力之間的侵奪和相互干擾,并維持政制的平衡的呢?對此,密爾認為,如果我們要知道英國憲制中真正的最高權力究竟屬于哪一部分的話,我們必須依靠不成立的憲法準則,即這個國家的實際的政治道德來判斷。
在密爾看來,“在每一個政體中都有一個最強大的力量,這就是說,假如憲法賴以習慣地進行工作的妥協辦法一旦停止,而出現了力量的考驗時,哪個力量將取得勝利。憲法的準則將得到遵守,并且實際上也起作用,只要它們把憲法上的優勢給予在憲法外具有現實力量優勢的那個力量,這在英國就是民眾的力量。因此,如果英國憲法的法律規定,連同事實上調整著各個政治權威的行為的不成文準則,未給予憲法中民眾的因素以符合于它在國家中的真正力量的、高于各個政府部門的實質上的最高地位,憲法將不具有作為其特點的穩定性;不是法律就是不成文準則,其將很快不得不改變。”〔34〕更確切地說,在英國政制中,真正體現民眾力量的便是新選的平民院。新選的平民院的構成以及相應的決議,反映了英國的確切的政治力量。雖然在實踐中,國王 (女王)對于首相的新貴族冊封提議很少有拒絕,但這也主要是新選的平民院給他 (她)以信心。因此,在英國的政制構成當中,最終的權威在于新選的平民院。每一部憲法中都應該在某個地方設定一種可望也可即的權威。最高權力必須成為一種可即的東西,而英國憲法已經做到了這一點。無論新選的平民院決定的問題涉及行政還是立法,無論是涉及基本政制的重大問題還是涉及日常瑣碎的細小事件,也無論是事關宣戰還是繼續進行戰爭,一屆新議會可以獨斷地并最終地予以解決。
(三)一個例證
為了形象地說明在英國政制發展和政制轉型過程中,英國不同的政制組成因素是如何在一種各得其所的相互關系之中相互作用,從而最終實現人民的意志的,在這部分筆者將以20世紀英國最為重要的1911年議會改革法案是如何通過的,①對于1911年議會改革法制定過程的分析,本文受益于我們歷史學家閻照祥先生所著《英國政治制度史》的敘事,詳細分析可參見閻照祥:《英國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380頁。來展示在英國的政制構成中所存在的真實的制衡結構。②實際上,奠定英國內閣制基礎的1832年將選舉權擴大到中產階級的議會改革法的政制轉型也是以同樣的方式發生的,當時貴族們也并不像維多利亞時代的上院同意當時的下院那樣心甘情愿地贊同平民院的立場,但它最終還是表示了認同。因為國王擁有冊封新貴族的權力,且當時的國王已向當時的內閣許諾進行貴族冊封。貴族院不希望形成這種先例,于是通過了該法案。參見Walter Bagehot,“The History of the Unreformed Parliament and its Lessons”,in his Essays on Parliamentary Reform(London:Kegan Paul,1883),p.107.向前追溯,國王使用冊封新貴族的權力還在英國1711年退出“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一事上予以真實體現。1702年,英國參加有荷蘭、奧地利等國組成的“大同盟”對法國作戰,但土地貴族滿腹牢騷。1710年,安妮女王罷免了不愿停戰的輝格黨大臣,任命托利黨人組閣,以求很快結束戰爭。1711年下院通過停戰法案,但被在上院占據多數的輝格黨貴族所阻撓。為此,女王于當年年底一次將12名托利黨人封為貴族,改變了上院黨派對比,使英國退出戰爭。在英國的政制發展或者政制轉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幅清晰的英國均衡政制圖像,不同的制度性主體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在政制實踐中發揮著各自不同的角色和作用。
我們知道,自1832年議會改革法之后,以黨派競爭為基礎而確立的責任內閣制成為英國政制的核心特征。為了爭取工人階級選民的長期支持,英國自由黨政府1906年開始進行了系統的社會改革,先后實施了《勞資爭議法案》、 《養老金條例》、《國民保險法》、《行業委員會法》等法令,奠立了20世紀英國福利國家的基礎。在改革中,自由黨政府為實施社會福利計劃需要巨額開支,這就要求它不斷調整財政政策和增加預算。
1909年,自由黨的福利政策和軍事改革計劃同時實施,如此下去,不出幾年,政府以往的財政盈余不但會耗費殆盡,而且要承受一筆高達1600萬英鎊的赤字。基于此,新任財政大臣勞合·喬治決心實行更大膽的財政改革。4月29日,他提出一個稱為“人民預算案”的財政計劃。此預算案中,不僅保留累進稅制和對高收入者征收附加稅的做法,還大幅度提高遺產稅,增收土地稅。預算案一出,就受到了英國中產階級以上的強烈譴責。但經過勞合·喬治的努力,財政法案最終在平民院仍以379對149票通過。
1909年秋末,當預算案送到上院時,更引起一場反對風浪。保守黨領袖鮑爾弗及其追隨者痛斥勞合·喬治劫富濟窮,還有人認為這不是一個尋常的財政案,它比普通預算案有更重大的后果,所以,在訴諸選民之前,應該嚴格地不妥協地加以拒絕。最終,上院以350對75票的絕對多數通過了保守黨領袖蘭斯多恩勛爵的動議:在提交全國民眾做出判斷之前,本院沒有理由同意這項法案。當然,貴族院的這種做法同樣立即引起英國社會中下階層的憤怒。平民院和新聞界一致譴責貴族院侵奪了久已確認的由平民院單獨掌管錢袋的權力,是違憲行為。由于此事還與自由黨和保守黨兩黨對立有關,它很快成為1688年以來的最嚴重的憲法爭端。
在這種背景下,當時執政的阿斯奎斯政府(1908-1916)當即接受了挑戰,宣布解散議會。然而在1910年大選后,自由黨的下院多數減少到兩名,只是由于工黨和愛爾蘭自治黨的支持,它才拼湊了大約120名的多數,勉強能夠繼續執政。1910年4月29日,新選平民院對勞合·喬治的預算案略加修改而重新通過。這時,貴族院面對自由黨政府在大選中的勝利,不經分組表決就匆匆通過了。然而,事情并沒有到此結束。自由黨仍然不肯就此罷休。實際上,在阿斯奎斯政府重提財政議案之前,即1910年4月14日,阿斯奎斯就在下院決議宣傳:應該以法律剝奪上院拒絕或修正財政法案的權力;上院對其他法案的權力也應該加以限制,任何法案在下院經過連續3次會期的通過和經國王批準之后,可以不經上院的批準立即成為法律。決議通過之后,阿斯奎斯政府傲然宣稱:如果上院貴族繼續抵制下院的決議,政府將請求國王加封足夠的貴族來改變上院的黨派成分。如果阿斯奎斯政府的提議最終通過,必將根本上改變英國當時已經存在貴族院的權力,從而改變英國的政制構成,將英國政制推向一個新的層面和發展階段上去。
但是,事情并沒有按阿斯奎斯設計好的劇本繼續發展。當時的國王愛德華七世 (1901-1910)并不愿支持政府,他否決了阿斯奎斯加封400名自由黨貴族的建議,只同意兩黨各加封100名新貴。不料1910年5月6日,愛德華七世去世。隨后,喬治五世 (1910-1936)即位,兩院的政治斗爭暫時休止。1910年夏秋兩季,兩黨領袖頻頻會面,以求達成協議,但仍無結果。于是,阿斯奎斯政府重操伎倆,再次解散議會,于12月重新進行大選。自由黨依然依靠工黨和愛爾蘭自治黨的聯合,最終仍獲得多數,重新就貴族院否決權問題提出議案,主張削弱貴族院權力。1911年3月,下院以368票對243票通過二讀。5月又以同樣的票數通過三讀,轉到貴族院。同時,阿斯奎斯宣稱大選之前,他已得到國王恩準,在必要時冊封足夠的自由黨貴族。此時,貴族院保守黨領袖蘭斯多恩建議他的追隨者放棄投票,讓政府議案照原樣通過,但一些死硬人物決心不肯妥協。最后,政府議案以131票對111票通過。新法令于8月18日頒布,英國20世紀一項重要的議會法就這樣正式產生了。①《1911年議會法》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法案規定上下兩院關系,并聲明將來要以代表民主而不是以世襲貴族為基礎所組成的一個第二院來代替現在的貴族院。法令第一條規定:凡下院通過的議案,于閉會一個月前提交上院,而上院于一個月內未加修正和通過者,該法案就可直接呈請國王批準而成為法令。對于其他法案,則規定任何公議案,經過下院連續三次通過,交上院被三次否決后,可直接呈請國王批準而成為法律。同時,議會法的還規定了議員支薪制,即議員每名下院議員每年可從政府領取400磅的薪金,以后隨著國民收入的逐漸提高。議會的任期由七年改為五年。
從1911年英國議會法的通過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在英國政制構成中,或者說在任何一種政制構成中,都應該包括三種要素,即新政制構成的發動者、現存政制秩序的保守者以及新政制構成的確立者。在英國政制中,作為政制發展的發動者是政府首腦,發揮著現存政制秩序的保持者和守護者的是貴族院,還有最重要的一種政制構成的最終確立者,即新選的平民院。在政制實踐中,對于行政首腦所提議的某種新政制構成,經過某種方式重新構成的平民院對此提議所做出的進一步的決定,可以為行政首腦邀請英國國王采取威脅性的手段提供重要的暗示和信息。國王冊封新貴族的威脅就可以迫使現存政制秩序的保守者貴族院,對提議予以全部接受或者對進行修正后予以通過。此種政制實踐,一定意義上便構成了英國式的均衡政制。
五、結 論
在通常理解中,英國作為議會制國家,在傳統的意義上不存在分權,特別是立法、行政以及司法機構之間的權力分立。然而,就分權原則所旨在服務于的價值而言,即防止專制政府的形成、反對立法至上、阻止政府權力的任意運用以及政府行為的運作效率而言,②See Richard Albert,“Presidential values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8 International Journal Constitutional Law 207,211 -215(2010).它們都可以在議會制國家中予以實現。③不僅在英國存在著分權,加拿大、德國、羅馬尼亞、泰國等議會制國家也是如此,實際上議會制和總統制中權力的配置和安排已然存在著相互借鑒和融合的趨勢,更多分析分析可參見Richard Alber,t“The Fusion of Presidentialism and Parliamentarism”,57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31,534-540(2009);Donald S.Lutz,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Desig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18 -123.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議會制國家中也存在著分權。就英國而言,分權并不是在立法、行政以及司法機關之間進行的,而是在國王和議會之間展開的。④在湯姆金斯看來,英國的分權模式主要在國王和議會之間展開,它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議會立法要得到國王的同意,因為這意味著在英國兩個法律上的主權權威達成了一種合意;(2)部長要對議會負責,因為部長代表國王,這樣議會就可以就使國王負有憲法和政治上的責任;(3)在議會有權推翻法院判決的意義上,英國的分權還創造了一個在法院和議會之間有價值的張力,而法院將它們憲法上的權威歸功于國王。參見 Adam Tomkins,Public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44-54.在英國的政治實踐中,貴族院、平民院 (通常有首相的支持)以及人民之間各得其所的相互關系之中,它們共同編制并促進了英國的政制構成的持續發生和不斷發展。
在英國的政制構成當中,王權并不是一種獨立的政治權力,王權要想行動就必須嵌入到議會當中。英國的政制系統,表面上實現的是議會的主權,堅持議會至上。但在政制實踐中,英國政制系統最終所旨在實現的是人民的主權,體現的是人民的利益。如果可以的話,是人民自己,而不是人民的代表,決定了英國的政制實踐的不斷發生、演變及其發展。總之,英國政制實踐就是由貴族院、平民院以及人民這三種要素間的互動所推動的。然而,英國的這種政制構成模式卻隨著2009年10月1日英國最高法院的建立而逐漸變得暗淡起來。傳統貴族院的“司法性”職能,由新成立的最高法院承擔。①2009年英國最高法院是依據《2005年憲制改革法案》第三章而設立的,它的司法權力主要繼承自上議院,這些權力過往一直由12位同時擁有上院議員身份的常任上訴法官擁有。最高法院12席法官席位中,其中10席由原來的上議院常任上訴法官繼續出任,第11席由卷宗主事官 (Master of the Rolls)克拉克勛爵 (Lord Clarke)出任,還有一席至今仍懸缺。其職權是,除蘇格蘭高等法院最終審理的刑事案件外,可以審理來自英格蘭、威爾士及北愛爾蘭三個司法管轄地區的上訴案件。最高法院法官的選任主要通過獨立的司法委員會進行,極力排斥政治因素對于最高法院的影響,參見Stephen Gardbaum,“Reassessing the new Commonwealth model of constitutionalism”,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167,205(2010).圍繞著英國上院的貴族院的爭議性改革,也仍然在進行當中。②See Jeremy Waldron,“Bicamer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31 Current Legal Problems 31(2012).是完全廢除上院,還是將其改革成美國式的參議院,這些政制構成問題必須由英國人民自己來決定。同樣,新成立的最高法院在英國政制系統中的地位和角色,也是英國最高法院本身所正在努力尋找和定位的事情。因此,試圖評估英國的憲制改革的效果目前還為時尚早。正如白芝浩所指出的那樣,“一部新憲法,只要它轄下的公民在舊憲法環境中長大,只要其轄下的政治家受過該舊憲法的訓導,就不會展示其全部效果。只有當它被沒有受到不同經驗訓導的政治家和民眾付諸操作時,它才會受到真正的檢驗。”〔35〕
當然,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就英國之前如何建立起一種均衡的政制模式,從而最終實現人民主權,體現人民自身的意志,卻是我們不得不予以深入思考的東西。實際上,王權在英國政制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形式化和具有象征性。國王在艱難的危機時刻可能是無用的;在事物的一般過程中,他 (她)的作用既不可能也沒必要。不過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發現議會制國家也無需陷入那種宿命的與總統制政府相伴隨的權力分立狀態之中。如果其他條件具備的話,它可以在非皇室型議會制政府形式下確立那種現成的、經過妥善安排的、與屬于英國憲法中權力態勢相同的政制結構。
〔1〕〔法〕E.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M〕.狄玉明譯.商務印書館,1995.44.
〔2〕蘇力.何為憲制問題:西方歷史與古代中國〔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5).
〔3〕〔英〕威廉·布萊克斯通.英國法釋義 (第一卷)〔M〕.游云庭,繆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15.
〔4〕〔英〕威廉·布萊克斯通.英國法釋義 (第一卷)〔M〕.游云庭,繆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16-219.
〔5〕〔英〕威廉·布萊克斯通.英國法釋義 (第一卷)〔M〕.游云庭,繆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
〔6〕〔英〕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165.
〔7〕〔英〕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166-167.
〔8〕〔英〕埃蒙德·柏克.自由與傳統〔M〕.蔣慶等譯.譯林出版社,2012.85.
〔9〕〔英〕埃蒙德·柏克.自由與傳統〔M〕.蔣慶等譯.譯林出版社,2012.68.
〔10〕Rodney Brazier.“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58 Cambridge Law Journal 96,121(1999).
〔11〕〔英〕埃蒙德·柏克.自由與傳統〔M〕.蔣慶等譯.譯林出版社,2012.62
〔12〕〔英〕阿克頓.自由與權力〔M〕.侯健,范亞峰譯.譯林出版社,2011.49.
〔13〕〔英〕J.S.密爾.代議制政府〔M〕.汪瑄譯.商務印書館,1982.24-25.
〔14〕〔英〕埃蒙德·柏克.自由與傳統〔M〕.蔣慶等譯.譯林出版社,2012.69.
〔15〕〔英〕休謨.休謨政治論文選〔M〕.張若衡譯.商務印書館,2010.6-7.
〔16〕〔英〕休謨.休謨政治論文選〔M〕.張若衡譯.商務印書館,2010.198.
〔17〕Martin Loughlin.The Idea of Public Law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13.
〔18〕〔英〕洛克.政府論 (下篇)〔M〕.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84-89.
〔19〕〔美〕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M〕.萬俊人譯.譯林出版社,2011.220.
〔20〕〔英〕馬丁·洛克林.劍與天平〔M〕.高秦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51.
〔21〕〔英〕威廉·布萊克斯通.英國法釋義 (第一卷)〔M〕.游云庭,繆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5.
〔22〕〔英〕威廉·布萊克斯通.英國法釋義 (第一卷)〔M〕.游云庭,繆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5
〔23〕〔英〕威廉·布萊克斯通.英國法釋義 (第一卷)〔M〕.游云庭,繆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6.
〔24〕〔英〕馬丁·洛克林.劍與天平〔M〕.高秦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13.
〔25〕閻照祥.英國政治制度史〔M〕.人民出版社,2012.307-311.
〔26〕〔英〕白芝浩.英國憲法〔M〕.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10.57.
〔27〕〔英〕白芝浩.英國憲法〔M〕.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10.66.
〔28〕〔英〕白芝浩.英國憲法〔M〕.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10.242.
〔29〕〔英〕白芝浩.英國憲法〔M〕.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10.243
〔30〕〔英〕白芝浩.英國憲法〔M〕.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10.242.
〔31〕〔英〕白芝浩.英國憲法〔M〕.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10.76.
〔32〕〔英〕白芝浩.英國憲法〔M〕.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10.144.
〔33〕〔英〕白芝浩.英國憲法〔M〕.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10.155
〔34〕〔英〕J.S.密爾.代議制政府〔M〕.汪瑄譯.商務印書館,1982.66.
〔35〕〔英〕白芝浩.英國憲法〔M〕.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