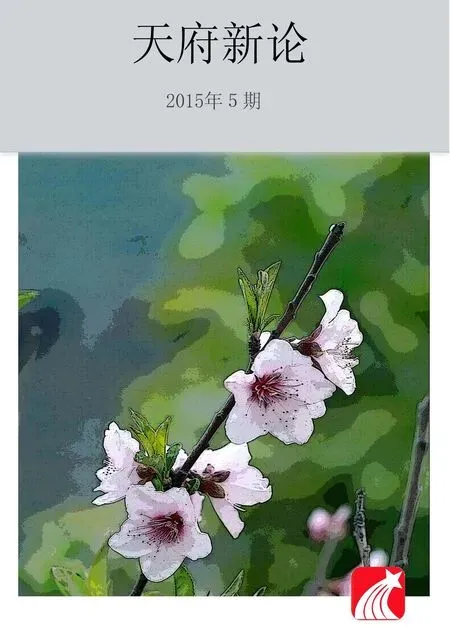基于執法經濟學對收支分離與執法激勵的分析
戴治勇
一、引 言
行政事業單位的服務大都被賦予公益性的標簽,法律的執行則有公共物品的性質。通常的看法是:如果行政事業單位的收費和執法產生的罰沒收入歸他們自己所有,將把他們變成類似于私人的盈利性企業,產生與其職位不相稱的扭曲行為;并且,由于他們被國家授予了競爭性的私人部門所沒有的權力,這將加大行為的扭曲程度。為了有效約束、控制這種扭曲,監察部、財政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和審計署等五部委1999年聯合發布了《行政事業性收費和罰沒收入“收支兩條線”規定工作的意見》。它要求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須存入財政專用預算外帳戶,相關支出由財政利用專項資金劃撥。該規定試圖通過收支兩條線,將行政事業單位、執法部門的收入與支出分離,達到依法行政、公正執法、整頓財政分配秩序,從源頭上治理和杜絕腐敗的目的。許多部門,包括交通部門、法院、檢察院、學校、一些衛生服務機構等,都實行了收支兩條線的預算管理。該項規定實行了十多年,但學術界對它的討論主要限于財政和會計領域,研究如何更有效落實收支兩條線的政策,但有這樣一些問題亟需從理論上澄清:為什么要實行收支兩條線?實行收支兩條線是否能達到預期目的,亂收亂罰是否能因此能從根本上得到遏制?行政事業性收費與罰沒收入應該是兩種不同的預算外收入,實行收支兩條線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嗎?我們是否應該區別對待?收支分離將怎樣改變行政事業性收費和執法部門行為,地方財政又會作何調整?等等。
本文主要討論與罰沒收入相關的執法,兼及行政事業性單位收費。筆者認為,發現并懲罰違法者是要付出努力的,而這種努力不可觀察,需要對其進行監督或激勵,收支兩條線一方面有利于規范執法,強化監督,但另一方面,卻使代理問題凸顯,執法部門有偷懶的道德風險動機,需要相應的激勵制度進行配套。由于最優執法的要求,這里面還有更復雜的成本收益權衡。現有的執法經濟學在公共執法者最大化社會福利的假定下研究最優執法,卻忽視了真實世界的公共執法還可能充斥著執法代理人偷懶、腐敗、“釣魚執法”等等,需要相應的激勵和監督。與此對的是,行政事業性單位收費則不存在這個問題。本文首先引入與最優執法相關的努力投入問題,論證這種努力在公共執法與私人執法情形下有何差別,然后圍繞這一中心問題,討論收支合一與分離情況下公共執法面臨的激勵和監督問題,附帶討論行政事業性單位收費,最后是結語。
二、私人執法與公共執法
違法者違法后將面臨一定的懲罰,我們假定這種懲罰是罰款,而是否被執法部門發現并處罰,是以一定概率發生的,這種概率取決于執法部門為發現并懲罰違法者所付出的努力的大小。如果罰款用f表示,處罰概率用p表示,它是執法部門努力e的增函數,即e增加,p也相應增加,但由于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約束,增加的程度會遞減,那么,違法者面臨的預期懲罰就是兩者的乘積,即p(e)f。潛在的違法者會權衡比較違法收益與預期懲罰,如果違法收益大于預期懲罰,其會選擇違法,反之則守法。Becker認為,相比于其他非經濟性制裁工具而言,罰款的最大優點是它僅僅轉移社會財富,不會引致懲罰成本,而執法部門的努力e卻是要耗費成本的。〔1〕因此,如果適當提高罰款f,相應減少懲罰概率p,同時保持乘積p(e)f不變,那么,違法者面臨的預期懲罰不變,但總的社會成本卻因為p的減少,從而努力的付出e減少而減少了。從此以后,優先使用罰款這種執法工具成為最優執法理論研究的起點。
預期懲罰p(e)f對違法者而言是一種成本,對執法部門而言卻可能是一種收益。既然有利可圖,執法是否可以由私人來進行?Becker和Stigler最早設想,法律如果在一個競爭性的市場中來執行會是什么樣子?〔2〕這種設想初看起來令人驚異,后來的研究很快注意到,無論是在過往歷史還是在當下,其實都有私人執法的影子。弗里德曼考察了古代冰島和數個世紀以來英國刑法的私人執行,〔3〕Landes和Posner則注意到即使是在現代的財產法、合同法、侵權法的執行中,國家的作用也是消極的,私人執行才是積極的動力所在,賞金制度體現了公共執法需要私人執法的幫助,而敲詐則是私人執法的典型。〔4〕Hay和Shleifer發現,當俄羅斯轉型期間國家權力衰落而無力執法時,甚至有私人組織,包括黑社會來執行國家制定的法律!〔5〕國內學者徐昕也討論了當今中國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私人執法。〔6〕
既然法律可以由公共執法部門進行,也可以由私人來執行,那么,什么時候私人執法比公共執法好,什么時候公共執法更優?或者說它們分工的原理是什么?Shavell認為,私人執法的最大優勢來自于私人可能擁有違法者是誰的信息。在有受害者的執法案件中,允許受害人獲得賠償將有助于激勵受害人揭示這個信息 (即在不付出或很少付出努力成本e的情況下就獲得了較高的懲罰概率p)。而當私人不具有這個信息優勢時,公共執法可能就更好。在刑事案件中,受害者或者已經死亡,或者不知道蓄意的加害人是誰,而以特定偵查手段獲取信息要求的投資可能很大,比如指紋識別系統,再加上信息獲取甚至需要強制或暴力的幫助,這些努力投入存在著經濟學上的規模經濟,這時公共執法就更有優勢。〔7〕
私人執法的另一個問題是,當多個私人執法部門競爭性地懲罰同一個違法者以獲取執法收益時,重復的執法投入可能是一種浪費。為什么不可以將這種執法權力授予一個壟斷的私人執法部門,來避免這種狀況呢?Landes和Posner詳細分析比較了競爭性市場上的私人執法、壟斷市場的私人執法和公共執法,他們認為,從社會成本的角度,私人執法非最優的最大問題不在于執法投入的重復浪費,而在于從社會的角度和從私人執法者的角度,懲罰概率與罰款之間的權衡是根本沖突的。〔8〕前面已經證明,從社會的角度,最優的執法要求罰款與懲罰概率是一種反向關系,即提高罰款,降低懲罰概率,在保持預期懲罰不變的情況下卻能節省執法投入帶來的成本。Becker強調,在違法者財富有限的約束下,應該優先將罰款升至最大,即違法者財富的全部,從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懲罰概率引致的執法投入成本。①考慮到監禁有成本,在財富約束下,只有在罰款達到財富上限以后才應該考慮使用監禁。提高監禁,同時降低懲罰概率,保持威懾不變,也能達到節約社會成本的目的。但降低懲罰概率的同時,也降低了先前優先使用的罰款的概率,從而威懾降低,故監禁不會像罰款那樣達到最大。〔9〕但這種罰款與懲罰概率的權衡與私人執法者追求執法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是不一致的,因為罰款越大,執法收益就越大,從而私人就有更大的動機追加執法投入以提升懲罰概率,獲得罰款。無論對競爭性的私人執法者還是對壟斷性的執法者而言,情況都是如此。這意味著在私人執法時,由于私人執法者追求執法利潤最大化,罰款與懲罰概率是一種正向關系。
那么,如果法律由公共執法部門來進行又如何?現有的文獻武斷地假定公共執法者將追求社會福利的最大,認為罰款增加并不會引致努力的增加。經濟學家源于對現實的觀察或猜想,假定公共執法部門并不能將罰款占為己有,執法代理人的收入與罰款可能不相關。但如果罰款不為公共執法部門所有,在沒有激勵、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公共執法部門為什么還要付出努力執行法律?畢竟努力付出的成本是由他自己承擔的。如果公共執法部門有權擁有全部或部分罰款收入,它又可能過度追加努力。結合中國的現實,以下將從收支合一和收支分離兩方面討論公共執法部門的激勵問題。
三、收支合一下的公共執法
收支合一情況下,公共執法部門有權擁有罰款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公共執法部門就演變成了私人執法者,而且是壟斷的私人執法者。這時,我們完全可以一個私有壟斷企業的行為模式來理解公共執法部門的行為。壟斷的執法企業面臨著向下傾斜的違法需求曲線,即預期懲罰越大,違法需求越小,從而有向下傾斜的邊際收益曲線。壟斷者發現,懲罰違法者的努力受到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制約,即有向上傾斜的邊際成本曲線。最大化利潤的壟斷企業將在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等時達到利潤最大,此時罰款收入與執法努力引致的成本之差最大。考慮到壟斷者面臨的違法需求曲線向下傾斜,相比于競爭性企業而言,壟斷者執法的努力投入會相對較小。
作為追求最大化執法利潤的壟斷企業,為了激勵雇員積極發現并懲罰違法者,并防止他與違法者串謀而將罰款收入占為己有,企業會采取相應的激勵、監督機制。比如將雇員收入與其繳獲的罰款收入掛鉤,引入監督者對雇員的努力進行監督,對難以監督的雇員實行效率工資,對腐敗的雇員進行處罰等。現代的公司治理制度在這里都可能得到利用。
進一步,壟斷的公共執法部門追求執法利潤的執法權力若沒有受到有效監督,它甚至有動機去引誘潛在的違法者違法,以收取罰款,或者捏造罪行,敲詐、冤枉無辜者;在可以阻止違法者的情況下坐視違法者違法,以收取更多罰款。還有可能,為了避免因為執法帶來違法需求下降引致罰款收入的減少的情形,執法部門與長期違法運營的違法者達成默契合謀,以犧牲社會福利為代價,收取穩定的罰款或賄賂。因此,這些因為追求盈利帶來的執法部門的瀆職、違法行為還需要其他的執法部門來監督。不過,正如Shleifer和Vishny指出的,執法者與違法者利益沖突的腐敗行為比利益一致的串謀行為更容易被一方舉報,從而更容易被發現,〔10〕因此,主要需要防范的是執法部門為違法者長期提供保護傘,收取保護費的腐敗行為。
如果法律本身效率低下,在執法收入與執法者利益不相關的情況下,執法者很可能自由裁量不執法,當然也可能選擇性地懲罰部分違法者,比如學者曾經討論很多的春節期間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法規執行情況。但是,對于收支合一的壟斷執法者而言,它將有動機執行一切制定的法律,甚至在“違法者”信息匱乏的情況下執行已經失效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法律。①與后文分析的行政事業性單位可能的亂收費對應。
最后,與私人執法者的自負盈虧不同,作為“國有企業”的公共執法部門還可以夸大支出項目,向政府索要補貼。因此,國有企業的一些弊端,如冗員眾多、低效率、缺乏監督等情況都可能出現。
四、收支分離與執法激勵
在討論收支兩條線下的收支分離之前,我們需要先討論收支合一與收支分離之間的中間形態。在中間形態中,執法部門雖然直接收取,但無權擁有罰沒收入,需要將得到的罰沒收入全額上繳,而支出則由財政部門劃撥。而收支兩條線中,違法者的罰沒收入不繳納給執法部門,執法部門只是開具罰單,違法者憑借罰單將罰款直接交給財政部門指定的專用帳戶。為了討論實行收支兩條線的必要性,我們需要研究中間形態與收支兩條線在實踐中的區別及其行為含義。
(一)中間形態
如果違法者的罰沒收入由執法部門收取后轉交給上級財政部門,那么,上級財政部門對于執法情況就所知甚少。它既不知道執法部門付出了多少努力去發現并懲罰違法者,也不清楚實收罰款的多少和構成。這時,上級財政部門如同公司的股東一樣,對企業的收支情況只能被動地由內部人報告,而這種報告常常有虛假的成分在里面。當然,財政部門可以聘用第三方的審計部門對其進行審計,但由于罰款往往是眾多單個的違法者繳納給執法部門,依賴現金交易,而不像企業的帳目是企業之間的帳務往來,這無疑加大了審計監督的難度。所以,這時的收益操縱狀況相比企業而言更加突出。
當執法部門繳納給上級財政部門的罰款小于上級財政部門撥付給執法部門的支出,就意味著財政補貼,那么,預算約束下的財政部門就有激勵審計執法部門執法收入的沖動。但即使審計能夠查知執法部門是否隱瞞罰款收入,由于審計監督成本很高,因而審計并不是一定進行的。這就好像企業的債權人在債權有保障的情況下不會干預企業運營,只有當正常的債務償付出現問題,債權人才會激勵審計、干預企業決策。上級財政部門在這里就好像一個債權人,如果需要財政補貼,或者財政補貼過大,它就有動機進行審計監督。預料到這一點,執法部門將根據違法情況來調整自己的執法投入努力。當審計門檻較低,財政部門試圖分享部分執法收入,歸屬于財政部門的罰款低于一定限值它就會啟動監督,這時,執法部門相當于需要與財政部門對執法利潤進行分成。在不考慮風險的情況下,分成制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弱執法部門的努力。當審計門檻較高,財政部門只是在財政補貼過多的情況下才進行審計,這時執法部門不僅可以獲得執法利潤,甚至還可以獲得一定財政補貼。當審計成本太高,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搞清楚執法部門究竟有多少執法收入時,執法部門的行為就與前面分析的私人的壟斷執法者相同。因此,根據審計成本的高低、財政部門審計監督的難易和積極性,中間形態的公共執法部門兼有私人執法和下面將要討論的收支兩條線下的公共執法的特征。
由于收取的罰款被要求轉交給上級財政部門,審計監督又有一定困難,可以預料的是,在中間形態,腐敗更容易發生。有意思的是,腐敗發生的頻率與審計監督之間可能有一種非單調的關系。沒有審計監督,執法部門可以像私人執法者那樣自由地占有收取的罰款,不存在執法腐敗;審計監督很嚴,執法腐敗很容易被發現并懲罰,執法腐敗也很少。而介于兩者之間的一定頻率的審計監督情形下,卻很可能存在執法腐敗。因此,以審計監督的頻率為橫軸,腐敗發生頻率為縱軸,很可能得到的是一條倒U型的腐敗發生曲線。
(二)收支兩條線
收支兩條線的最大好處就是,財政部門能夠容易地觀察收繳罰款的情況。相比于中間形態,財政部門擁有的關于執法情況的信息更多。但知道罰款的收繳情況,僅只是相當于知道了一個企業的產出;而執法企業的投入情況如何,使用的技術如何,財政部門仍然不知道。收支兩條線實施的目的就是增加上級財政部門的信息,從而有利于監督。但執法部門仍然擁有一定的其他私人信息,會給監督增加難度。這是本節分析的重點。
為了分析的深入,讓我們進一步引入執法者的能力問題。有的執法者善于總結經驗,辦案經驗更豐富,付出同樣努力的情況下發現并懲罰違法者的概率更高。執法者的能力參數我們用θ來表示,那么,現在違法者被罰的概率就是θp(e),預期罰款就是θp(e)f。所以,這時罰款收入既決定于執法者的努力投入多少,還取決于執法者辦案能力的大小。無論是努力的投入還是執法的能力,都只有執法者自己知道,財政部門不知道。這時高能力的執法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私人信息偽裝成低能力的執法者,減少執法努力投入,節約私人成本,這種行為通常被稱為逆向選擇。因此,在這里就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由于執法部門的努力不可觀察引致的道德風險,即執法者可能偷懶,需要激勵或監督的問題;另一個是執法者能力不可觀察引致的逆向選擇問題。而且,由于公共執法部門與上級財政部門重復打交道,這里還會涉及到因動態問題引起的復雜性。
1.道德風險
執法部門收繳的罰款多少既與執法部門付出的努力多少相關,還與一些執法部門無法控制的隨機因素有關,比如違法需求的大小、違法者規避懲罰的努力、受害者或目擊者的舉報意愿等。在收支兩條線的制度安排下,如果財政撥付給執法部門的支出與上繳的罰款不相關,也就是執法部門的收入與產出不相關,那么,在努力不可觀察的情況下,執法部門就沒有動機激勵執法代理人努力執法。當財政部門責問罰款收入為何過低時,執法部門可以用現在公眾更加遵紀守法等理由來搪塞。除非違法情況有大的變動,如違法的泛濫、公眾的質疑,否則,財政部門很難對執法部門的行為績效進行否定。面對這種情況,財政部門有何對策?財政部門可以同時設置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公共執法部門,使它們之間進行執法競爭。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其中一個要訣,就是在不改變產權的前提下,分拆以前的壟斷機構,讓它們相互競爭,比如電信行業、石油行業、航空行業等。這種行業內部的市場競爭會提供一種標尺,揭示隱藏的行動信息。〔11〕但遺憾的是,這在執法領域是不適用的。同一地區設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門征收相同項目的罰款,將導致執法努力的重復投入,而且它激勵執法部門追求罰款最大帶來努力的大幅增加與前文分析的最優執法所要求的罰款和努力投入的反向關系是矛盾的。但如果僅依賴一個壟斷的公共執法部門,又面臨它可能偷懶,造成巨額財政補貼的問題。現實中的解決辦法常常是罰款的全額返還或部分返還。這種罰款的返還制度一直廣受詬病,因為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又把公共執法者變回了追求罰款最大,從而行為扭曲的擁有公共執法權的私人執法者。而且,在罰款返還的誘導下,執法部門將把最優質的執法資源配置到罰款返還最多的違法行為中。比如,經濟類犯罪的違法收入可以部分返還給檢察院,檢察院的檢察資源就更可能向經濟類犯罪傾斜,而忽視其他暴力型犯罪。
與收支合一的私人部門、中間形態不同的是,這里的全額返還或部分返還存在跨時期的承諾問題。即當罰款收入比較高時,財政部門可能違背當初全額返還或以比較高的比例返還的承諾,其理由非常正當——執法部門沒有權利擁有這筆收入。事先預料到這種承諾的不可置信,執法部門就不會投入很高的努力去收取太多的罰款。盡管這種承諾不符合追求動態執法利潤之和最大的目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公共執法部門付出執法努力的激勵效果,但卻是符合最優執法的要求的。所以,不可置信的全額返還和部分返還,相比收支完全不相關的制度有一定的激勵作用,但卻是一種有缺陷的激勵制度,而這種折衷的激勵安排,在執法這個特殊領域卻是很有價值的。它不是最優的,但很可能是次優的。這正是我們在現實中最慣常看到的激勵制度。
前面討論的是財政部門與公共執法部門之間因為道德風險產生的制度含義,接下來我們討論執法部門與其雇員,即具體的執法代理人之間因為道德風險產生的制度含義。罰款的全額返還或部分返還給了執法部門一定的動力,它再以此激勵執法代理人努力執法。執法代理人的努力對執法部門而言也是不可觀察的,為了激勵執法代理人,執法部門可能安排執法代理人的收入與執法代理人收取的罰款掛鉤。但這種掛鉤扭曲了公共執法罰款與努力反比例關系的初衷,為了減少這種努力,可以對執法部門內部采取的激勵執法代理人的制度安排進行一定限制。比如只能實行固定工資制,不允許其收入與征收的罰款有過于緊密的聯系。不過這些限制帶來的后果又可能是執法代理人完全沒有了執法的激勵,這時,也許在固定工資的基礎上向其分派一些固定數額的任務可能是必要的。在現實中,我們經常見到一些執法代理人一定時期有些固定數量的執法任務,比如征收多少罰款,或者處罰多少人次等。這種固定數量的任務有它的好處,它使違法者具有了一定被罰的概率。但由于總的違法需求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那么,要保持一個處罰概率不變,數量就必然需要跟著調整。當違法需求意外減少,或者取證困難帶來執法難度增加,固定的執法數量要求將使執法代理人苦不堪言,這時執法代理人可能會用上各種手段,比如“釣魚執法”,懸賞尋找線索等。而當違法需求意外增加時,固定的執法數量又可能顯得過少,使得被罰概率過低,這又進一步提高了違法的需求量。這里,我們見到了第二個在一定約束條件下有缺陷的激勵制度。
這些有一定限制的激勵措施一方面試圖保持一定的執法力度,另一方面,又試圖不讓執法代理人因為追求罰款最大而過度執法。但擁有執法權的執法代理人如果能將罰款收歸己有,同時又不被發現的話,他仍有很強的執法動機。這在前面討論的中間狀態尤其突出,因為即使是執法部門也無法完全監督罰款過程當中的每一筆交易。在收支兩條線中,執法代理人沒有權力直接收取罰款,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這種狀況。但執法代理人為什么不可以跟違法者進行交易,以少收罰款為條件不開具罰單而直接收取現金?這是一種執法腐敗行為,可以采取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代理人同時執法的辦法,通過增加執法成本來防止違法者與執法代理人之間的串謀,或者使用效率工資。但如果因此增加的執法成本大于了防止串謀的收益,就沒有必要了。更好的辦法是利用現代執法技術,比如交通違法中的電子眼,非人格化的執法防止了違法者與執法代理人之間的串謀。
2.逆向選擇
由于上級財政部門不知道執法者的能力,它僅能憑借繳納上來的罰款推斷其執法能力的大小,并根據收上來的罰款多少進行再分配。可以預料的是,分稅制以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博弈的類似情形在這里出現了。1980年以后,為了刺激地方政府稅收激勵,中央政府實行了以“承包”、“包干”為特征的財政收支安排,并根據各省情況不同采取了多種激勵制度安排,如收入遞增包干、總額分成、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上解額遞增包干、定額上解、定額補助等。〔12〕五花八門的財政包干制度最后的結局是雙方都以財政收入下降為代價,而這期間中國的經濟卻一直是高速增長,原因是它們陷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當中,“如果地方政府不遺余力地加大征稅力度,它們有理由擔憂,中央會在下一輪談判中調高他們的上繳比重。所有地方政府都知道他們與中央達成的分成合同會在幾年之內重新討論,而中央政府則背著‘鞭打快牛’的壞名聲: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省份,基數可能調低,上繳比重可能調高。事先預料到中央的這種事后機會主義,地方政府的響應是自己的機會主義,即在征稅努力程度上留一手”。〔13〕這又是一個承諾問題,是典型的動態逆向選擇中存在的承諾問題。財政部門不清楚執法部門收取罰款的能力大小,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從以前的罰款收繳情況來推測執法部門的能力大小。前一時期較好的罰款收繳情況意味著執法部門的能力較高,反之則較低。政部門從前一時期的罰款情況推知了執法部門的能力大小,然后在下一期對高能力的執法部門要求更高的罰款收繳,對低能力的執法部門要求較低的罰款收繳。執法部門事前預期到這一點,高能力的執法者可以在第一期就減少努力,少收繳罰款,把自己偽裝成低能力的執法部門,由此節省執法努力帶來的私人成本。
財政部門可以試圖做出可置信的承諾,在得知執法部門的能力后不對其要求更高的罰款征收,從而激勵高能力執法者努力執法。其實,截斷財政部門對罰款信息的了解,比如前面討論的中間形態,就是一種可置信承諾,它有利于激勵高能力執法部門努力執法,而收支兩條線使得這種承諾不再可置信。不過如前討論,可置信承諾下的高強度激勵也許并不符合最優執法的要求。放任公共執法部門的逆向選擇,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高能力執法者努力的投入,這種有缺陷的激勵制度與最優執法的要求反而更加一致。
五、可能的制度改進
如前所述,收支兩條線因為方便監督,遏制亂罰款,避免公共執法部門淪為私人執法而產生。但是,收支完全分離導致公共執法部門完全失去執法的動力,因此又有了現實中的罰款分成和罰款任務攤派。比例并不固定,顯得有些任意的罰款分成和罰款任務攤派是一種有缺陷的激勵制度,它遭到了各方的批評和抱怨,卻是當下無奈的選擇。現有制度是否還有改進的空間,本節試圖利用激勵理論進一步展開討論。
罰款的執法激勵面臨著一個兩難問題,一方面需要激勵執法者努力執法,另一方面,又不能使執法者為了追求罰款最大而過度執法。簡單的收支合一將導致過度執法;收支分離卻又導致執法激勵不足。解決上述兩難問題的、可能的更精致的激勵安排如下:執法部門首先擁有一個與收繳罰款無關的固定的運行經費,但為了避免執法者偷懶,這個經費需要略低于執法者的保留工資。其次,與現有不明確的執法分成比例不同,執法者可以獲得事先約定的執法分成,但這個分成比例會隨著罰款追繳數額的增加而減少,罰款超過一定數額,分成比例可降為零。
上述激勵制度試圖考慮和解決的問題如下:完全靠罰款來維持公共執法部門的運轉會回到罰款與努力不得正相關的悖論,一個固定的運行經費保留了公共執法部門的提供公共物品的性質。但同時,為了解決執法者有限制的激勵問題,執法者可以獲得一定的罰款分成,即產出與努力必須掛鉤,但這種關聯 (分成比例)必須隨著罰款 (產出)的增加而減少,這是與現有私人部門的激勵完全不同的地方。在私人部門中,為了追求利潤或產出最大化,分成比例不會隨著產出增加而減少,考慮到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約束,分成比例甚至可能隨著產出增加而增加。
六、行政事業單位收費
行政事業單位收費與前面分析的執法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執法需要付出努力去查獲、懲罰違法者才能收到罰款,但人們卻常常是主動到行政事業單位繳費以獲得相應的服務,比如向法院繳納相應的訴訟費用。而且,前面分析的執法難題是不能過度激勵執法代理人為了罰款多少而努力執法,但又不能讓他們完全喪失了處罰的動機,這種看起來有些矛盾的激勵難題在這里也不存在。因此,行政事業單位收費沒有前面討論的激勵問題,實行收支兩條線就更有利于第三方的監督。
與前面對執法的討論一樣,在收支合一的制度安排下,第三方無法觀察到行政事業性單位的收費情況。這使得原本是以成本補償和非盈利為目的的行政事業性單位有動機為了自己的利益巧立名目亂收費。盡管行政事業單位的收費受到授權的國家機關、司法機關的限制,但由于這種授權使行政事業單位本身也具有了代行國家權力的權威,交費的企業、個人或者根本不知道某些項目的收費是否合法,是否被正式授權,或者即使知道也不愿意為了自己不太多的交費而開罪于收費單位引來更多的麻煩,這增加了監督的困難,使得亂收費愈演愈烈。同時,行政管理性的收費或者具有強制性,或者企業、個人對事業單位的消費具有需求上的剛性,無疑也加劇了收費的亂象。
收支分離使得第三方能夠容易地觀察到具體的收費情況,有利于節約監督的成本。同時,收費的強制性和需求的剛性保證了收入的穩定,避免了在對執法的討論中由于執法者偷懶引致收入小于支出帶來巨額財政補貼的問題。當然,總的收費仍然可能小于支出,行政事業單位過度的冗員就會造成這種情況。與國有企業改制不同,我國行政事業單位的改革一直相對落后,大量冗員極易造成收不抵支。這種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財政部門所不能左右的,但這帶來的財政補貼卻可能是它不愿意承受的。解決的辦法就是對亂收費的一定程度的容忍。因此,單單實行收支兩條線,不是杜絕亂收費的可置信承諾,即使是實行了收支兩條線,亂收費也無法完全杜絕。比如,九年制義務教育實行以后,許多中小學仍然換著花樣和名目實行各種各樣的收費。
對于這種價高質次的服務,經濟學家建議的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引入競爭,比如弗里德曼建議在公立學校中引入教育券,競爭將消除冗員、低效率,減少財政補貼。〔14〕對于有些部門,也許這是更好的解決方式。但對于那些只能實行壟斷的部門,如法院、檢察院,以及帶有強制性的行政管理部門,收支兩條線還是最好的監督方式。
七、結 語
收支兩條線使上級財政部門擁有了更多的信息,從而有利于監督、規范行政事業單位、公共執法部門的行為,減少執法腐敗和亂收費。但是,實行收支兩條線以后,隨之而來的卻是罰款的全額返還或部分返還,以及亂收費仍然局部存在,這使得收支兩條線受到了很多質疑。本文詳細討論了這種情況存在的原因:最優執法要求優先使用罰款,對公共執法實行低激勵,但又不能完全沒有激勵,導致了現實中的有缺陷的激勵制度 (承諾不可置信的罰款全額或部分返還,定額的配給式執法要求,是否根據前期罰款提高第二期罰款收繳總額的承諾不可置信)和收支兩條線這種監督制度并存;行政事業單位改革的滯后與財政的預算約束導致了亂收費可能繼續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主要討論了收支兩條線的“收”這部分,強調了它的信息揭示作用,而對“支”討論很少。由于支出的最佳配置和使用需要利用支出部門的很多私人信息,第三方的過度干預是不適當的。但是,依賴財政支持的部門與依賴自己收入量入為出的私人部門肯定不同,對其需要更多的監督。財務公開常常是最好的監督機制,即使是這樣,對不了解部門真正運作的第三方而言,許多財務公開內容所揭露的信息可能仍然是模糊的,除非有競爭性的可對比參照的部門,而正如我們前面討論的,這種情況往往不存在。這時,對其支出進行一定限制,實行專項資金可能是不得已的解決辦法。受到一定預算約束,公共執法部門、行政事業單位只能進行既有資金的最佳使用配置。比如檢察院優先把預算使用在對社會危害最大、最可能成功破案懲罰罪犯的案件上。當然,這也是一種有缺陷的制度。支出部門常常夸大自己的預算開支,而且為了第二年財政撥款不減少,如果第一年的撥款沒有正常用完,支出部門常常會浪費性地將余額使用殆盡。
〔1〕〔9〕Becker,Gary,Crime and Punishment:An Economic Approach,76,J.Polit.Econ.pp.169 -217,1968.
〔2〕Becker,Gary & George Stigler,Law Enforcement,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ment,3,J.Leg.Stud.pp.1 -18,1974.
〔3〕弗里德曼.經濟學語境下的法律規則〔M〕.楊欣欣譯.法律出版社,2004.
〔4〕Landes,William & Richard Posner,The private enforcement of law,4,J.Leg.Stud.pp.1 -46,1975.
〔5〕Hay,Jonathan R.and Shleifer,Andrei,Private enforcement of public laws:A theory of legal reform.88,Amer.Econ.Rev.pp.270-290,1997.
〔6〕徐昕.法律的私人執行〔J〕.法學研究,2004,(1).
〔7〕〔8〕Shavell,Steven,The Economic Theory of Public Enforcement of Law,38,J.Econ.Lite.pp.45 -76,2000.
〔10〕Shleifer,Andrei and Robert Vishny,Corruption,108,Quart.J.Econ,pp.599 -617,1997.
〔11〕Shleifer,Andrei,A Theory of Yardstick Competition,16,Rand.J.Econ,pp .319 -327,1985.
〔12〕張軍.分權與增長:中國的故事〔J〕.經濟學季刊,2008,(1).
〔13〕王紹光.分權的底線〔M〕.中國計劃出版社,1997.
〔14〕弗里德曼.自由選擇〔M〕.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