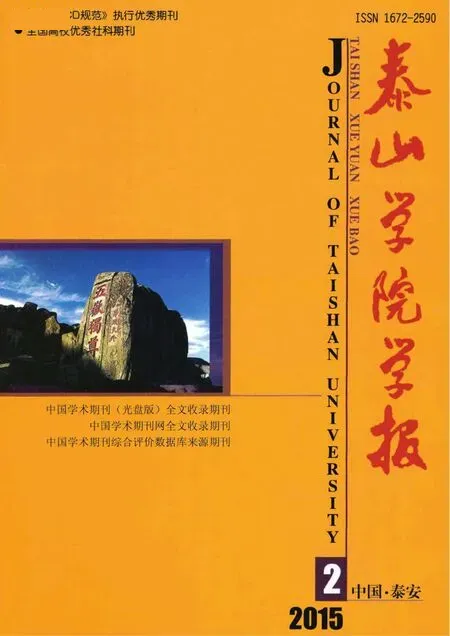實現代際正義與對前人非正義行為的應對立場
張 虎
(中共中央黨校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實現代際正義與對前人非正義行為的應對立場
張 虎
(中共中央黨校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對代際正義的探討不應僅僅局限在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上,還應把前代人與當代人、后代人的代際關系包括進來。后者涉及一些前人的實踐錯誤對現在和未來的不利影響,而處理好前人的這些非正義行為與實現當代人與后代人的代際正義緊密相關。國際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分配是代際正義的重要研究課題,對它的爭論涉及對前人非正義的處理,而目前的處理方式分別訴諸于現狀權利、補償正義和分配正義。
代際正義;前人非正義行為;現狀權利;補償正義;分配正義
隨著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愈演愈烈,人們在繼續重視在場的人與人之間的公平關系之外,也開始關注代與代之間的正義問題,即代際正義(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問題了。同代內正義(intragenerational justice)相比,代際正義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許多理論問題尚未解決。本文即結合國際氣候談判中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分配問題,探討為實現代際正義應如何處理前人的非正義行為留下的發展困境。
一
代際正義,即代與代之間的正義問題,它應該指涉前代、當代與后代三方間的正義關系。但是一提起它,人們首先想到的卻是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利益協調與分配問題,因為前代人已經故去,不會復生,于是對代際關系的探討落到在場的當代人與即將出場的后代人的關系上。根據這種觀點,實現代際正義就是在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實現正義。許多學者持這種觀點,廖小平等人就認為“代際公平在范圍和時域上可以分為‘在場各代之間的公平’和‘在場各代與后代之間的公平’”[1](P25),唯獨沒有言及前代人,有人認為“代際正義就是‘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怎樣公平地分配各種社會和自然資源、享有和傳承人類文明成果’的正義問題”[2](P120),也把前代人忽略了。這種只關注當代人與后代人關系的思路,其實是一種以現在為始點往前看的視角,在與代際正義密切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的最初定義中即有所體現,根據《我們共同的未來》這份報告,可持續發展應“滿足當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3](P10)。有人即指出,“清楚的是,這個重大的論斷從現在出發觀照未來,但是它缺乏對造成當下情形的主體的重視”[4](P274)。“造成當下情形的主體”不僅包括當代人,還包括前代人,某些當代的發展問題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由前人造成的,例如西方工業化以來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造成了氣候變暖這一世界性的難題,需要當代人和后代人共同應對,而忽略掉前人實踐所附帶的這些影響深遠的負效應,只是談論現在和未來的生態保護的責任分配,很容易使問題的討論流于空談。
在處理當下或未來問題時無視之前人們行為的影響,無視這種歷史向度,有時會使一種延續至今的非正義進一步深化。西方有學者區分了兩種處理問題的角度,即“受害者”角度(“victim’s”perspective)和“行兇者”角度(“perpetrator’s”perspective)。受害者角度是“從當下不平等的形成當中理解歷史進程所累積的負擔,并強調在當下和未來的實踐當中積極糾正過去所犯的錯誤”[4]271,而行兇者角度就不是這樣了,它不考慮過去,只關注解決當下問題的最佳手段。舉一個建垃圾處理廠的例子,從行兇者角度來說,工廠建在地價便宜的地方最好,因為這會大大減少成本,而從受害者角度來說就不是這樣。根據受害者角度,我們首先要分析一下以往什么差別化的發展政策導致了土地價格的差異,地價便宜地區的居民相較于別處的人受到了哪種不公正政策的影響以及再在此處興建一座不受歡迎的工廠是否會加重這種不公正等等,綜合考量這些因素,廠址的選擇會更慎重一些。兩相比較,從行兇者角度看問題,即罔顧過去的非正義行為,更容易使之延續并加深。
代際正義作為一種歷時性的正義觀同樣如此,它不僅涉及當代人與后代人的正義關系,還涉及前代人對當代、后代人的正義關系,前者是從現在到未來的向前看的維度,后者是從現在到過去的向后看的維度。實現當代人與后代人的代際正義是我們的目標,而前代人對當代人、后代人的代際關系則已是一種事實,既包括正義關系,也包括非正義關系,代際正義的實現要求我們恰當地處理好這種已然存在的非正義關系,避免使之延續并加深。
以國際談判中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分配為例,消減溫室氣體的排放從而緩解氣候變暖可以保護當代人與后代人的生態環境,從而在二者間實現正義,這為代際正義的向前看的維度所要求。但是排放權的分配又不能不考慮發達國家工業化歷程已經出現的大規模排放行為。總的來說,發達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得到的利益要遠大于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現在和未來的居民,對氣候變暖卻比發達國家的人更為敏感(生活設施落后是原因之一),因此抹掉一些國家過去和現在對全人類欠下的“生態債”(ecological debt),要求所有國家在減排行動中承擔相同的責任,就不能不遭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反對。在氣候談判中也有一種“能力說”,即要求綜合國力更強的國家為應對氣候變暖承擔更多責任,這種觀點看似合理,但道德約束力并不強,丹尼爾·巴特(Daniel Butt)就類比式地反駁說,“如果某人砸碎了我家的一個窗子,我不會問村子里誰最能出得起它的維修費。我會堅持讓那個破壞它的人承擔花費”[5](P759),因此排放權的分配需要嵌入對過去某些群體的實踐錯誤的考量。這也就是《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宣言》中提出“各國負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別的責任”的原因所在,即發達國家的更多責任一方面源于它們的“技術和財力資源”,一方面源于“它們的社會給全球環境帶來的壓力”[6](P5)。
代際正義的向后看的維度要求我們重視并處理前人的非正義行為,在當代西方哲學界,對前人非正義行為的處理卻有截然不同的三種立場,即分別訴諸于現狀權利(status quo rights)、補償正義和分配正義,以下分別簡述之。
二
維護現狀權利的人強調人們的現實處境,重視他們在利益分配的事實上所處的位置,進而否認現狀背后隱含的過去的非正義。與之相伴的一種觀點是溯往原則(grandfathering),即根據歷史上形成的慣例來要求今天的利益分割,以排放權的分配為例,“至少就未來的一定時間而言,溯往原則(要求——本文作者)劃給過去已經有過大量排放的排放者更多的排放權,給排放了很少的排放者更少的權利”[7](P229)。這種觀點在諾奇克的理論當中找到了依據。諾奇克反對模式化的分配正義理論,即反對按照人的能力、貢獻或需要等來分配資源,他甚至認為“分配正義”一詞都不是中性的,“聽到‘分配’這個詞,大部分人想到的是,某種事物或機制使用某種原則或標準來分發一些東西。一旦進入這種分配份額的過程,某些錯誤可能就溜進來了”[8](P179)。他認為這些分配理論假定了人們面前有一些資源等待分配,只關心它們應該怎樣被處理,不關心它們是怎么來的,而人們的一些經過合理途徑獲得的東西是屬于他本人的,是不能隨便被某種分配模式所左右的。因此,諾奇克主張用持有正義代替分配正義,只要持有物的原初獲取是正當的,人們就擁有對持有物使用、支配或轉讓的權利。按照這種觀點,發達國家過去通過工業化已經獲得了排放大量溫室氣體的權利,要求它們減少這種排放量是對他們權利的侵犯,不符合持有正義的要求。但這種說法很難滿足諾奇克的洛克式的對原初獲取的前提規定。一方面,發達國家歷史上占有的排放份額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留下足夠多的排放空間,這從人們為應對氣候變暖所制定的排放限額中就可以看出;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從發達國家的排放行為獲取很多的好處,它們已經并且還會是氣候變暖的最大受害者。
另外一種對現狀權利的辯護路徑訴諸于發達國家居民對其生活水平的正當期望(legitimate expectations),即發達國家居民的正常生活建立在高排放的基礎上,驟然減低排放量會影響他們重要生活計劃的執行。針對這種論調,有學者提出兩點反對:一是發達國家的居民到現在有義務認識到這種高排放的生活方式不可持久;二是排放貿易的引入可以有效地緩沖對居民生活方式的影響。[9](P709)
三
現狀權利的辯護有違人們的道德直覺,很難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對前人非正義行為的處理,人們一般訴諸于補償正義,西方道德和政治哲學界在這方面也是著力最多。但是,這條路徑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人們發現存在一些難以繞過的問題,下面列舉三個有代表性的問題。
首先,前人對其行為影響的無知。代際正義是對正義的一種歷時性的觀照方式,其關注的前人行為的效應一般會經過很長時間才顯現出來,有時前代人也難以預見其行為的負面結果,比如溫室效應。當然,忽略這個事實,可以說“僅僅這個事實,即傷害行為是由我造成的,就使我對補償它的后果負責”[10](P40),但要無知者為其行為負責畢竟缺乏足夠的道德基礎。就認識溫室效應的時間而言,人們有1840、1896、1967、1990和1995幾個備選年份[10](P40),無論確定哪一個,我們都可以要求一些國家為之后的高排放行為做出一定的補償。其次,責任歸屬問題。即使承認前代人應對延續至今的非正義境況負責,但是他們已經作古,要誰來作出補償呢?他們的后人有義務這樣做嗎?最后也是引起人們最為激烈爭論的,非同一性問題(the non-identity problem)。正是由于今天的部分群體因為某些前人的一些行為而受到傷害,我們才可以談論前人的非正義,可是依據非同一性問題,這種傷害并不存在。它最先由德里克·帕菲特提出[11](P356),簡單說來,就是一種深刻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實踐行為(如過去工業化過程中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會影響人們婚姻組合的“機緣”,從而會影響后代的出場,如果沒有這種行為,另一些事件,即不同的婚姻組合方式從而不同的后代就會產生。傷害概念“以可以比較同一主體分別在有某行為和沒有這個行為的情況下所形成的事實狀態和反事實狀態為前提”[10]38,但這里有無這個行為會導致不同后代個體的出生,不存在同一主體境況好壞的對比,因此也就不能說后人被導致他們出生的某種行為傷害了。如果沒有傷害,代際間的補償正義就難以自圓其說。
西方學者提出了許多解決方法回應以上挑戰。阿克塞爾·葛瑟里斯(Axel Gosseries)針對第二個問題提出了一個影響很大的觀點,即用跨代的搭便車(transgenerational free-riding)來使那些因前代的非正義行為而獲益的當代人對因其而受害的當代人做出補償。搭便車行為與寄生蟲行為(parasitism)不同,二者的區別在于“如果行為X的發出者是我,并且隨其產生的傷害被加諸其他人,那么我就是一個寄生蟲……相反,如果X的發出者不是我但仍然對我有益,那么我在沒有分擔由行為的發出者或第三方所承受的代價的意義上就是一個搭便車者”[10](P43)。按這種分類,如果前代因其對他人的傷害行為而獲益,他們就是寄生蟲,如果他們的后人仍能從這種已經結束的傷害行為中獲益,那么這些后人就是搭便車者,要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這種搭便車行為之所以是跨代的,是因為“搭便車群體得到的好處和其他群體遭受的害處是因果相連的,這種關系是由搭便車群體的前人造成的……”[16](P46)。葛瑟里斯的觀點為發達國家所應背負的歷史責任提供了論證,同時我們應注意,發達國家的寄生蟲行為即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有傷害效應的國際行為在今天也比比皆是,當下它們溫室氣體的高排放量就是一例,因此發達國家要承擔雙重的補償責任。
跨代搭便車也就是從前人非正義行為中獲取了不正當的利益。用它提供補償的道德根據有兩點不足:一是如果前人的這類行為沒有給他們的后代帶來好處,那他們的后代應該就可以逃避補償責任了;二是根據非同一性問題,代際關系中不會出現同一主體兩種狀態的對比,獲益的觀點和受害的觀點一樣不能成立,有人就認為,“根據這種論證方式,耗盡資源不會傷害到后人,工業化也沒能提高當代人的生活水平”[12](P757-758)。丹尼爾·巴特因此試圖避開這種利益導向的論證方法,僅僅訴諸于對非正義行為的道德補償責任。他認為除了前人所犯下的非正義之外,還有一種之后未對該行為進行及時矯正的非正義的存在,“前者處于某一特殊時刻,后者則持續進行”[5](P770),前者的責任人是以前的確定主體,后者的責任人則包括之后新出生的個體。巴特借用了經濟學理論中的“重疊世代”(overlapping generations)①來解釋后一種非正義,重疊世代指在存在時間上有一定重合的世代關系,比如父與子、爺與孫等等,巴特認為“當我們考慮群體的歷時性存在時,一種重疊性世代的模型要比接續性世代的模型更現實”[14](P358),正是這種代際間的重疊關系很容易將有過錯的前人的后代卷入這種未及時矯正的非正義中,從而使他們背負一定的補償責任。假設某年甲國拒絕為其國有油輪泄露到乙國水域的大量原油負責,并且甲國政府為民選產生,大部分甲國人可以說都做出了一種非正義行為。一年之后,甲國居民發生了一定變化,即一小部分人去世,一小部分人出生,如果甲國仍拒絕擔責,那么新出生的人也被卷入到非正義之中,不過不是原來拒絕處理泄露原油的非正義,而是未對它進行及時矯正的非正義,即未對這一年乙國的損失進行賠償和道歉。再過一年,甲國仍拒絕賠償,于是又有一些新出生的人被卷入這種非正義中。假設過了50年,當年泄露原油時拒絕擔責的人都去世了,這也只能說原初非正義行為的責任人不在了,而不能說他們的后代就沒有賠償的道德責任了,如果他們仍拒絕賠償,他們仍在做出一種不義舉動。
代際正義在處理前人非正義時所面臨的責任歸屬問題和非同一性問題其實都是基于一種道德個人主義的視角,根據這種視角,一個人與他祖輩的行為無關,沒有理由讓他負責,并且這種原子式的道德主體也難以確定和把握。為規避這些麻煩,西方代際正義問題的有些研究轉而訴諸社群主義,社群主義強調群體的歷史在塑造個人身份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麥金泰爾指出“我生命的歷史總是嵌入那些群體(家庭、鄰里和城市——本文作者)的歷史中,正是從他們的歷史中我才獲得了我的身份,我從出生那一刻起就同那些過去連在了一起,用個人主義的思考方式將我和它們隔斷就相當于解構我現在的關系”[15](P221)。個人與群體緊密相關,而群體身份的同一性非常穩定,不容易隨時間變化而改變,因此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責任不會隨著單個個體的死亡而消失,它會在不同世代的不同個體中延續。另一方面,“……群體擁有內在的價值觀念……群體中心的觀點或可避免非同一性問題。這是因為許多未來群體(例如國家、民族和文化)的存在在不依賴于過去的生態政策這一點上是確鑿無疑的”[16](P63)。
四
有鑒于用補償正義來處理前人非正義所遇到的困難,盧卡斯·H·邁耶和多米尼克·羅澤認為“不依靠關于環境變化危害的補償正義,純粹依靠分配正義就可以為發展中國家現在和未來更高的排放份額作合理論證”[9](P711)。他們認為,分配排放權其實是分配因排放而產生的利益,并且這種分配形式近乎純粹,因為這里的總排放量作為自然容受能力的極限是固定的,不能應用持有正義為高排放國家辯護(前已述及),也不會隨排放分配方案衍生某種負面影響[7](P232-233)。這里排放權分配的關鍵是如何在由于排放獲益較多的國家和較少的國家之中實現一種公平的分配。邁耶和羅澤列舉了三種不同的分配模式,并比較了它們的優劣,這三種模式分別是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足量主義(sufficientarianism)和優先主義(prioritarianism)。
平等主義②的分配模式要求對資源實行平均分配,它重視平等之為平等的內在價值,就排放權的分配來說,使各國人均占有量均等化就是一種符合它要求的分配方案之一。但是在理論上,平等主義卻面對一個著名的難題,即拉平反論(the levelling down objection)。拉平反論指平等主義可以維護一種荒謬的達至平等的方法,德里克·帕菲特打了一個駭人的比方,即為了拉平正常人與盲人視力間的差距,弄瞎前者的眼睛從平等主義的角度來說是一種對原來狀態的改善。拉平反論揭露出平等主義者的邏輯矛盾,他們“認為一種情形是好的,在這種情形下,無人受益,但有人受害”[7](P234)。從這個致命的反論我們可以看出平等主義其實并不關心個人的福利狀況,它“主要關注關系:同各個人相比,每個人的生活是怎樣的”[7](P234),這正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
有別于平等主義,足量主義關注分配對個人的影響。它的理論特點在于設置了一個個人福利狀況的足量水平,滿足低于這個水平的分配主體具有絕對的優先性,而足量水平以上的分配則處于次要地位,具有極小的道德價值。足量主義的缺陷很多,其中用何種原則確定一個足量水平是它難以回答的問題。
優先主義是這樣一種觀點,即“受益人境況越差,分配給他們利益就越重要”[17](P213),換句話說,分配產生的道德價值與分配主體的境況成反比,分配同樣的東西,給福利狀況差的人與給福利狀況好的人相比會產生更大的價值權重。優先主義解釋了我們更同情弱勢群體的道德直覺,同時也規避了平等主義與足量主義的缺陷,因為“平等主義者關注相對性:每個人的狀況同其他人的狀況相比怎樣。而按照優先的觀點,我們關注人們狀況的絕對水平”[17]214,另外它也不需要設置一個足量水平的界限。大致看來,優先主義最終會在分配各方中形成一種平等的局面,但是我們不應忽略它的靈活性,因為它純以分配產生的道德價值為依據,福利狀況較差者的優先性并不是絕對的,“依據它,給境況不利者的利益可以在道德考量上低于給境況有利者充足的更大的利益”[17](P213)。因此,優先主義可以說是一種修正了的功利主義。
邁耶和羅澤用優先主義來解決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分配問題,他們提出三種解決方法來處理發達國家歷史上的高排放。首先,從最近的時間看,現在發達國家的居民已經從其生命歷程中的高排放活動中獲得了較多的利益,這些利益遠大于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居民從其排放活動中獲得的利益,根據優先主義,排放權應更多的照顧后者。其次,現在發達國家的居民不僅在他們自己的時代獲得了排放活動的高回報,他們從出生伊始也接受了前人排放活動更多的有利條件,“這些有利條件由前人工業化歷程留傳下來的好處(例如街道、醫院和學校)構成”[7](P241)。需要注意,這里涉及的是發達國家居民與發展中國家居民當下有利條件的事實對比,因此不會受非同一性問題的干擾。從這種對比中根據優先主義我們可以進一步將排放權的分配向發展中國家傾斜。以上兩種解決方案能夠兼容于道德個人主義的立場,但它們也有缺陷,即局限于當代人的受益狀況,如果采用社群主義的立場,我們可以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排放份額。因為如果把國家看作一個跨代的社群,在分配溫室氣體排放權時,發達國家歷史上所有排放活動產生的利益都應計算在內,它們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利益。根據優先主義的分配原則,給發展中國家分配更多的排放權利會產生更大的價值權重。
處理好前人的非正義行為是實現代際正義的必要條件,以上以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分配為例探討了對前人非正義行為的三種應對立場。很顯然,對現狀權利的辯護很難讓人信服,我們需要認真對待補償正義和分配正義這兩種處理方式。同時應引起注意的是,在代際正義的研究中,前人的非正義行為范圍很廣,除了溫室氣體的排放,歷史上的種族隔離、性別歧視、宗教壓迫等問題也在深深地影響著今天及以后的代際關系,這種影響或者波及全球,或者局限于某一特殊地域,都需要人們積極面對。就中國而言,除了應代表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爭取贏得更多的排放權益之外,也應重視國內以往的實踐歷程所留下的大量發展困境和難題,舉一個突出的例子,現在的區域差距、城鄉差距和行業收入間的差距就與以往的差別化發展政策不無關系,如何破解這些難題,從而實現社會和諧,實現可持續發展,必然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和對待以往走過的發展道路。
[注釋]
①有學者認為,重疊世代概念在代際正義論證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參見Hugh McCormick。
②邁耶和羅澤在這里指目的論的平等主義(teleological egalitarianism or telic egalitarianism),參見德里克·帕菲特作出的區分。
[1]廖小平,成海鷹.論代際公平[J].倫理學研究,2004,(4):25-31.
[2]劉雪彬.正義、文明傳承與后代人:“代際正義的可能與限度”[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7,(6):118-127.
[3]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4]Aaron Golub et al."Sustainabi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Do Past Injustices Matter?"[J].Sustainability Science,2013,8(2):269-277.
[5]Daniel Butt."The Polluter Pays?Backward-Looking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the Environment"[A].Jean-Christophe Merle,Spheres of Global Justice[C].Dordrecht:Springer,2013.757-774.
[6]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宣言[J].世界環境,1992,(4):4-5.
[7]Lukas H.Meyer and Dominic Roser.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Climate Change,The Allocation of Emission Rights[J].Analyse&Kritik,2006,28(2):223-249.
[8]羅伯特·諾奇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9]Lukas H.Meyer and Dominic Roser.Climate Justice:Past Emissions and the Present Allocation of Emission Rights[A].Jean-Christophe Merle,Spheres of Global Justice[C].Dordrecht:Springer,2013.705-712.
[10]Axel Gosseries.Historical Emissions and Free-Riding[J].Ethical Perspectives,2004,11,(1):36-60.
[11]Derek Parfit.Reasons and Perso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12]Simon Caney.Cosmopolitan Justice,Responsibility,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J].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5,18(4):747-775.
[13]Hugh McCormick.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and the Non-reciprocity Problem[J].Political Studies,2009,57(2):451-458.
[14]Daniel Butt.Nations,Overlapping Generations,and Historic Injustice[J].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006,43(4):357-367.
[15]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M].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7.
[16]Edward Page.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Climate Change[J].Political Studies,1999,47(1):53-66.
[17]Derek Parfit.Equality and Priority[J].Ratio,1997,10(3):202-221.
(責任編輯 梅煥鈞)
Realiz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and Ways of Handling Predecessor's Unjust Behaviors
ZHANG Hu
(Graduate School of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100091)
For the arguing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we should not only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people,but also concern about the present and future influence caused by the acts of our predecessors.The latter involves some bad effects inflicted by the failed practice of the past people,the suitable dealing ofwhich having a direct connection with the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future.The allocation of emission rights among all nations in theworl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and the study of which involves the handling of past unjust behaviors.The ways we have now are status quo rights,compensatory justice,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Predecessor's unjust behaviors;Status quo rights;Compensatory justice;Distributive justice
B08
A
1672-2590(2015)02-0058-06
2015-01-02
張 虎(1987-),男,山東平陰人,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