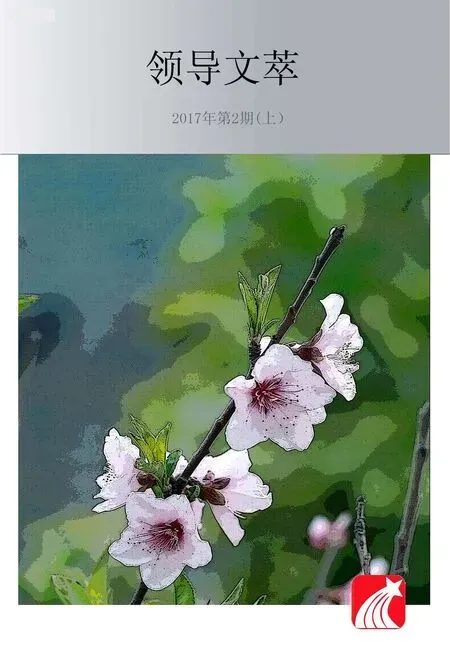張謇:落空的抱負
□黃旻旻
張謇:落空的抱負
□黃旻旻
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張謇動了重新下海經商的念頭,這是1914年,棉紡織業的生意形勢極佳。
進入民國政府之前,他已經是名滿天下“狀元實業家”,他的大生集團設廠棉產區南通,以此為圓心,生意越做越大。這位咸豐二年(1852年)出生江蘇海門的農家孩子對實業救國情有獨鐘。
1896年初,從清流派轉入洋務派的地方大員張之洞奏派蟄居家鄉的狀元張謇在通州設立商務局,并在南通創辦了大生紗廠。從1901年至1907年,圍繞大生紗廠,張謇先后創辦了19家企業,建成了大生資本集團。他努力突破傳統小門小戶的作坊生意,使自己的實業版圖覆蓋了工業、墾牧、交通運輸、金融商貿眾多領域。
張謇做過前清的江蘇兩淮鹽總理,一個與市場、資本家聯系最緊密的政府職位;也曾主持發動了3次國會請愿活動,希望能立憲來實現想法。他考察過“東洋”經濟格局,深受震撼。
1903年,張謇去日本考察,待了2個多月。他看到了對岸國家如何在保留皇室的同時,發展工商業。日本政體從君主制到君主立憲制的穩定過渡使張謇深受鼓舞,他更堅定了自己的設想——實業興國加立憲。回國之后,他把日本的成功模式總結為“圣王之道加機器之學”。
1911年,武昌起義第一槍打響前8天,張謇還在武昌,他受到了湖北巡撫的歡迎。因與湖北官員熟悉,他簽訂由自己壟斷湖北此后棉紗等四項產品銷售的合同。
剛剛簽完合同的張謇正做著“實業夢”,武昌起義叫醒了他。張謇的日記里說,當時他在船上,目睹了暴亂中的大火,他極為“震駭”——剛簽訂大單就碰上戰事,生意怎么辦?
張謇找到了江蘇總督,希望他出兵鎮壓革命。企業家天生討厭一切破壞秩序的暴力行為,實業家十年的心血只需要一把火就可以毀之一旦。這是他今后決定站在哪一隊的評判標準——實業家們需要穩定的時局。這也是1913年二次革命時張謇的態度,他認為革命黨的起事不利于社會穩定和實業發展,他選擇了袁世凱。
辛亥革命勝利后,廣東商人團體曾武裝反抗過革命黨。孫中山一直受到同情革命的商人的資助,但孫主張的政策中卻有節制資本、控制私人資本的內容。孫中山剛回到中國時,臨時政府國庫里只有10元錢,所有的商人都暫時只能是一個錢袋子,持有臨時政府無法兌現的承諾。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任命張謇為實業部長。到任后的第3天,他們見面了。但在當天的日記里,張謇只用了4個字評價孫中山:“不知崖畔”。張謇認為孫中山太幼稚太單純了。張謇想到了袁世凱,早在23歲入官場投奔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時,張謇就和袁世凱認識,他們都是吳的幕僚,一個主撰文,一個主練兵。
盡管張袁之間二十多年不相往來,但張謇不是不知變通的人,現在,張謇覺得自己應該和他談談。
張謇來到河南洹上村,找到被清廷罷黜的袁世凱,他希望為一心干實業的立憲派找一個可靠的靠山,袁世凱雖然遠離政壇,但還掌握著北洋軍權,清政府除了重新起用他并無別的好主意。張謇準備爭取他的支持,再依靠他來達成自己的想法。
他們在洹上村達成了同盟。從袁世凱家出來后,張謇對隨從說:“慰亭畢竟不錯,不枉老夫此行。”密談中,袁世凱許諾張謇:一旦得到重新出山的機會,一定會尊重張謇的意見。
張謇自己在心里做了一個排序:袁世凱、大清而后才是孫中山。革命派沒有治國經驗,很可能把民營資本在折騰中消耗殆盡。1913年,張謇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后開始動手移除阻礙實業發展的絆腳石,肯定私產的地位。他一手操持指定的《公司注冊規則及其施行細則》規定:民有工商企業不經過該管官廳注冊,不準開業。公司一經注冊,就是法人,受到法律保護。
1915年,在袁世凱簽訂了《二十一條》后,張謇決定跟袁做徹底的決裂,他告別了北洋政府,回到經營了十幾年的南通大生集團。趕上北洋政府的政策寬松,加之歐洲內訌,到1918年之間,民營資本迎來了一個黃金時代。這期間,張謇專注于經營自己的試驗田——大生集團和南通城。
早在北去就職前,張謇在南通的經營就已經有聲有色。他在這里施行“地方自治”,使這個江蘇小縣城有著不一樣的光芒。
張謇一直在推銷他的藥方:議會制國家憲政。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乘清朝被八國聯軍戰敗而欲求改革之機,張謇上奏了《變法平議》書。這是張謇的政治宣言書。此前已經在進行地方自治實踐的張謇第一次代表新興的階層,公然呼吁參與政治。他希望為自己正在實踐地方自治的南通尋求一個可靠的保障。
但張謇的“地方自治”只是按照他個人的設想建設南通,他只關注地方的經濟文化建設,不涉及政治的控制。張謇從經濟入手,希望通過興辦實業、教育、慈善,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
在20世紀初的中國,南通像是一座“黃金城”,這個江蘇縣城在張謇的主持下越來越有一個城市該有的樣子。
但好日子沒能撐太久。大生的攤子太大,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本小事大”、“急進務廣”,建大學、修路、造公園、辦水利、興慈善……南通試行的“地方自治”處處依仗張謇口袋里的錢。
張謇何嘗沒有悟明白“在商言商”這個道理。但他仍然把社會扛在身上,拖累大生走向衰落。
“他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終于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于偉大,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胡適說。
張謇本來想在1922年舉辦地方自治第25年報告會上展示自己推行地方自治的功績,但一場暴風雨將他常引為驕傲的水利工程摧毀。這一年張謇70歲,也正是這一年,棉價大漲,紗價下跌。1922年幾乎成了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它的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一去不返。
1925年,大生紗廠因負債不能償還而被債權銀行團接管。張謇“實業救國”的理想早在那時就已經破產。
(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