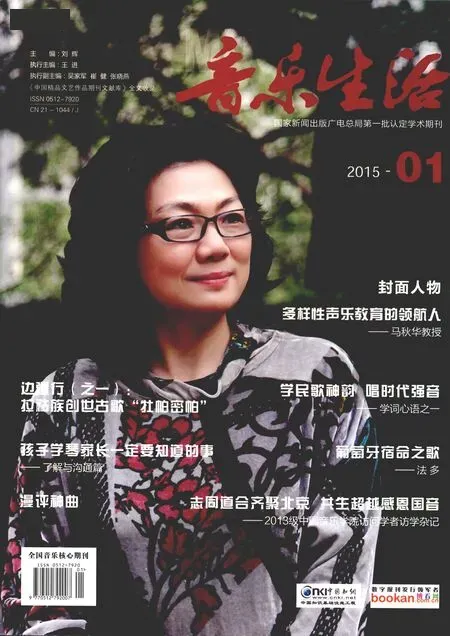肖斯塔科維奇密碼(六)
—— 第六弦樂四重奏 op.101
文/王 晶
肖斯塔科維奇密碼(六)
—— 第六弦樂四重奏 op.101
文/王 晶
一
1953年,斯大林去世。蘇聯的政治以及肖斯塔科維奇的創作都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距離第五弦樂四重奏寫作4年后的1956年,肖斯塔科維奇寫出了他人生中的第六部弦樂四重奏作品 ——《G大調弦樂四重奏o p.101》。從第六弦樂四重奏開始,肖斯塔科維奇進入了一個新的創作時期。斯大林的去世標志著斯大林時代的終結,“解凍”的暗流在蘇聯文化界各個層面悄然涌動。肖斯塔科維奇在此后的一段時間內重新進入交響曲創作領域,連續創作了第十一至第十三交響曲,謳歌著國家光榮的歷史同時也在繼續控訴戰爭的罪惡。而在其四重奏中,自第六弦樂四重奏起,則開始沿著一條隱秘的道路繼續前行。通過一系列四重奏的連綴寫作,隱晦但完整地表達出他對已然結束的一個時代的看法。
1956年的作曲家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過往的歲月讓他通曉了人世間的喜樂與挫折。而在1954至1956年的這幾年間,圍繞作曲家的則是親人離世的傷痛。1954年年底,作曲家的愛妻尼娜(尼娜·瓦西里耶芙娜)因為癌癥去世,留下了作曲家和兩個孩子。尼娜是作曲家的第一任妻子,夫妻感情深厚。1848年的大批判同樣影響了尼娜,為了賺取家用,作為物理學家的尼娜一直在列寧格勒大學的一個實驗室工作,而這個實驗室遠在貧窮的高加索的阿加帕。1954年的年底,患病的尼娜被接到埃里溫接受手術治療,當作曲家得知妻子的病情,只能坐飛機趕去見妻子最后一面,隨后靈柩被空運回莫斯科舉行葬禮。緊接著的1955年,肖斯塔科維奇的母親去世,享年67歲。在短短的一年時間內,作曲家兩次經歷了與親人的生離死別。

此外,在這一時期還有一件事情對作曲家影響巨大。隨著政治氣候的寬松,很多之前作曲家創作而又未能得以上演的作品包括《第一小提琴協奏曲》《猶太民歌詩選》等等都開始獲得演出機會。1955年
的冬天,列寧格勒小歌劇院貼出告示,準備上演之前被批判禁演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20年前,正是這部作品讓年輕的作曲家第一次嘗到被國家集權機器打壓的滋味。這一事實鼓舞了肖斯塔科維奇,他開始努力修改這部作品準備迎接蘇聯文化部的檢查。然而可惜的是,在1956年召開的關于歌劇《麥克白夫人》的審查會上,審查委員會的最終意見是:鑒于歌劇《麥克白夫人》存在著嚴重的藝術思想問題,因此不準上演。這又一次打擊了作曲家。而這部給他帶來不幸的作品真正被蘇聯文化部門承認要等到7年后的1963年。

赫魯曉夫
1956年年初,赫魯曉夫主持的蘇共二十大召開,會上主要批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指出斯大林的錯誤,并開始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蘇聯的各個領域均開始逐漸活化。就在這個“解凍”的年份,帶著對逝去親人的追思、對遭遇不公的憤慨,以及對未來即將到來的那飄渺“自由”的期許,作曲家完成了他的第六弦樂四重奏,開始著力描述關乎自己以及關乎蘇聯的“新”的時代。
二
G大調第六弦樂四重奏(O P.101)在1956年的9月創作完成,10月初首演于列寧格勒的格林卡小音樂廳。第六弦樂四重奏是作曲家弦樂四重奏創作第三分期的第一部作品,縱觀作曲家四重奏體裁的整體創作,這部作品正處于中期,是一部紐帶式的作品。
從音樂結構來看,第六弦樂四重奏與第一弦樂四重奏的地位大致相當,都是嘗試從古典簡潔的形式出發引出新一輪的思考。第六弦樂四重奏是對古典風格的再次回歸,整體結構層面重新回到了四樂章均衡的古典結構形式上,曲中四個樂章之間基本達到平衡,同時音樂語言層面也盡量趨向簡潔,每一樂章中的主題陳述都十分明確。而反觀創作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之前五首四重奏(第二至第六)基本都是基于古典結構簡潔規范進行的繼承與改革。對于這點,阿蘭·喬治也肯定地說道:“所有的這些(作曲家的前期四重奏寫作)都植根于一種幾乎持久不變的對于古典主義形式和結構的忠誠上。”
在第一弦樂四重奏明確基本的寫作步驟后,作曲家就嘗試將交響音樂創作中積累的經驗帶入四重奏寫作。因此,自第二弦樂四重奏起,肖氏四重奏的風格中就明確地凸顯出了交響性的音樂組織邏輯。同時,作曲家著力展示的自我體驗與外部現實的矛盾糾葛也一直貫穿于作品之中,這兩種特質在第五弦樂四重奏中達到頂峰:三樂章的連續演奏,長大的篇幅,極具動感的音響張力牽扯出激烈的戲劇化情感。同時簽名動機的使用使作品的意義指向更為明確。
而至第六弦樂四重奏中,則開始表現出一種回落。不管是整體還是細節層面,都能看出一種復歸,一種對之前具有巨大戲劇性張力音樂語言的復歸。雖然其中仍舊保持了與第五弦樂四重奏細節音調使用上的勾連,然而整體呈現出的均衡的形式感、對語言質樸的追求,均
展示出這部作品的創作風格與之前一系列作品的明顯不同。
三
全曲的四個樂章以“快 —— 慢 —— 慢 —— 快”的速度排列。與其慣常使用的“慢啟動”不同。同時四樂章中最快的是第一樂章,而末樂章則以慢速結束。這種“頭重腳輕”的速度設計與傳統的古典形式并不相符,而在其早先的四重奏創作中,只有第三弦樂四重奏使用了類似的“慢結束”手法。
作品的第一樂章采用了標準的奏鳴曲式結構,在中提琴上持續奏出的同音反復音型之上,呈現以抑抑揚格三音動機引導的主部主題。整個主題建筑在明確的G大調上,清新跳脫,十分明快。同時,在主題中可以看到在第五弦樂四重奏與第十交響曲中被確認使用的簽名動機以一種隱伏式的進行暗藏于主題的陳述之中。分別出現于主題的首尾兩端,同時又在主題樂句重復時出現(見譜例1)這正是作曲家在經歷了第一輪創作嘗試后總結出的獨特的創作手法。
譜例1

這一三音動機不僅僅是第一樂章主部主題的引導動機,同時還是全曲構成的核心動機。整個作品的四個樂章均是在這一三音動機基礎上發展而成。而與這個帶有明確運動方向的動機相對立的,是中提琴聲部持續的同音反復。這一同音反復同樣會作為全曲的一種特殊動機被不斷借用。副部主題將旋律進行態勢由拱形變為環繞式,但仍以三音動機為最基本的構成元素。作品的展開部以兩種主部主題動機進行模進展開。再現較為特色,主部主題再現時配合這個副部的動機要素,形成一種類似綜合再現的狀況。隨后的副部再現則出現調性偏離,并未回歸G大調,而是移動至降G大調再現。正是因為這種再現的不穩定,在副部再現后,主部主題又一次完整再現,并引出尾聲。十分特別的是這一樂章的最后終止以十分閉合的形式在大提琴聲部完成了終止,以降三音的屬九和弦完成像主和弦的解決。(見譜例2)這種終止形式成為這一作品四樂章的又一共通要素。
譜例2


第二樂章采用帶有回旋特征的復三部曲式創作而成,第一部分通過小步舞曲與小夜曲間不同風格的對比構成作品第一段落。降E大調的首段主題中仍舊隱藏了部分簽名動機。第一部分的兩組主題都是由三音動機發展而成,同時對比主題還配合使用了同音反復動機。因此整個第二樂章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做是第一樂章的變化呈現。作品的中段首先以下方三聲部的持續音與第一小提琴的旋律吟唱展開,而后引入中段的對立性主題。作品首段主題再現時,旋律的陳述位置有所變化,樂章最后的結束方式模仿第一樂章,以大提琴聲部的分解和弦導向終止,但不再是屬——主進行,而是導七和弦向主和弦的解決。(見譜例3)
譜例3

第三樂章采用帕薩卡里亞舞曲的形式,以主題和變奏的形式構成。與前兩個樂章的明朗相反,固定低音的曲調相對低沉。井上賴豐在其文中將此段稱為“掩蓋憤怒的悲傷音樂”。全曲包含七段變奏。前三次變奏是沿著中提琴——第二小提琴——第一小提琴的順序,由低向高依此疊加聲部。疊加旋律其核心仍是三音動機。第四次變奏與上方三聲部齊奏出同音反復的音型,以此證明這一樂章與之前樂章間的血緣關系。第五變奏是在此基礎上三音動機與反復動機的結合,第六變奏是最高聲部的獨白。第七變奏又回到第五變奏同音重復的形式。樂章結束依舊采用前兩樂章由大提琴完成終止的方式。(見譜例4)
譜例4

第四樂章以慢板開始,奏鳴曲式形式。樂章開頭以來自第一樂章的三音動機為固定音型引出的類似主題的結構,隨之加以拓展和變化,形成以倒影形式主題動機為引導核心的主部主題。這一主題在形態與氣質上都在努力回歸第一樂章。副部主題以二拍子舞蹈節奏對三音動機進行變形。展開部完全建立在三音動機及其倒影形態的模進發展上。此樂章的再現同樣別具特色,采用倒裝再現的形式,先由副部再現,之后在最低音聲部進行主部主題再現帶出尾聲。最后的結尾仍舊采用大提琴聲部分解和弦式的終止方式,與第一樂章的終止式完全相同。由此形成作品首尾的循環呼應。
四
第六弦樂四重奏毫無疑問是一個嶄新的開始。古典的樂章結構、明晰的旋律走向以及更加簡潔清晰的織體編排都表述出一種向傳統的四重奏寫作“復歸”的態度。在經歷了數次交響化嘗試后,肖斯塔科維奇終于對自己獨特的四重奏寫作風格有了把握。同時,在第六弦樂四重奏中也有一些新鮮的東西正在發酵成形。全曲以一種十分明顯的“凝聚”態勢組合而成。四樂章采用相同的主導動機發展,三音動機和同音反復動機成為全曲最核心且唯一的發展要素。樂章結構層面,除第三樂章變奏結構外,均以一種類似中心對稱式同時兼具回旋要素的結構形式進行布局。在主題材料不斷循環出現的過程中,整個作品的結構也變得十分堅固,首尾呼應。此外,每樂章最后的終止式也在加固這種統一性。而這種統一性一方面來自外部力量的向心力發展,同時也是內在力量自我變化的必然結果。這種內在力量,正是延續自第五弦樂四重奏的D S C H簽名動機。正是這一動機成為全曲中隱藏著的核心要素。
伴隨著簽名動機的復現,肖氏四重奏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自第六至第八,我們會看到一次新的跨越:第六至第八弦樂四重奏的創作完全可以被視為一個整體。作曲家在這一批作品的創作中,著力搭建自己四重奏寫作的核心——一種以簽名動機為象征的“自我意識”。自第一弦樂四重奏至第五弦樂四重奏,足以適應“自我意識”的外部世界已經完成。“自我意識”自第五弦樂重奏出現,并在第六弦樂四重奏中發展,繼而在第七弦樂四重奏中趨向成熟。最終在第八弦樂四重奏中完全成形,并完成對其四重奏世界的控制。然而這一成形的過程同時蘊含危機,“自我意識”的成形更多來自于外部的強行擠壓。因此,第六弦樂四重奏既是成形的起點,同時也是破碎的起點。此時的個體還帶有天真的幻想,而個體的破碎傾向已然隱匿其中。之后的第七弦樂四重奏則出現字面與象征意義的裂縫,自我意識漸趨崩潰。第八弦樂四重奏達到自我崩潰的頂點,簽名動機的頻繁展示正是自我意識的碎裂,而那種碎裂正是“啟示錄”敘述中那種災變式的終結。
(責任編輯 張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