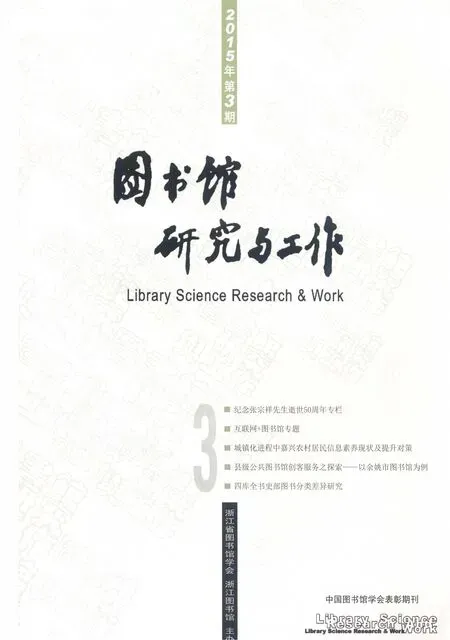外公留下的財富
徐 潔
(浙江圖書館,浙江 杭州 310007)
外公離開我們已經有五十年了。他在世的時侯,我和他只共同生活了三個年頭,而這還是從我出生開始算起的。雖然我的名字是外公給取的,但我的記憶里并沒有外公清晰具體的印象,那時的我實在太小。一些殘存模糊的片段,也可能只是聽家人的描述、我自己的想象。比如我父母老是提到那時的我經常會跌跌撞撞地闖入他的書房,伸手所及之處,總會一片狼藉。那時的家里總是有很多客人,有他的朋友、學生、同事,還有一些曾被他接濟過的、家人也不清楚關系的人。他們有的來談論古籍校勘,有的來討論書法,有的來鑒定字畫和玉器,也有的是來討要墨寶的,真可謂是“三教九流”,絡繹不絕。外公精力旺盛,邊談論,邊抄書,邊抽煙,一樣也不耽誤。那時的家里,滿屋書香……這樣的場景,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清晰,以至于有時錯以為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
外公是在一九六五年罹患肺癌離世的。不久之后文革開始了,我家從寬敞的祖宅遷居進了陋室,記憶里屋子的墻上總掛著這幾樣:一是外公無償捐贈的獎狀。二是“豈能盡如人意 但求無愧我心”的對聯,那是外公寫給外婆的。再是外公書寫的文天祥詩碑文拓片(該碑至今依然在溫州江心嶼,供后人欣賞和憑吊)。睹物思人,這是我們全家對外公的思念。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進入浙江圖書館工作,我與外公的關系開始密切起來了。每每遇到一些老同志,看到我就說,哦,是老館長的外孫女。一句老館長,足以見同事對他的尊重,也讓我體會到,在這個單位工作,我要對得起外公,千萬不能給他抹黑。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對外公生前作為的聞見越來越多,他對我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這些影響,既有外公對事業(yè)的執(zhí)著追求,又有對人生的豁達態(tài)度,更體現了外公一生的價值取向,是外公留給我們后輩的最大財富。
運籌帷幄謀大事。1951年元旦,外公寫下一段話:“人為群眾服務而來,不是為個人權利享受而來。學問、政治須時時去其陳腐,發(fā)起精義,方能有益于世、有益于己。此七十年來處世持躬之旨也。”我想,這就是外公為人處事的基本原則,有了這樣的宗旨,決定了他一生堅守信念,堅持操守,堅定做對浙江文化有益的事。外公一生,做了兩件浙江文化史上的大事。第一件,在1923年擔任浙江省教育廳長一職時,組織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外公對補抄一事,醞釀已久,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工作時,對四庫書就有了全面的了解。雖然是大工程,但外公開始時就能運籌帷幄,在最難的經費籌措上,他事先就明確三點:不是浙江人,哪怕富可敵國,也不去募捐。本省各地區(qū)都有捐助。每500元為一股,不成股的不募。最后,當時的督辦、省長都募了款。這也為文瀾閣《四庫全書》留在浙江埋下了伏筆,當時的政府在抗戰(zhàn)勝利后,欲將書運往南京,因為當初只接受本省籍人士的捐款,文瀾閣本才得以安全運回。第二件,恢復西泠印社。1951年11月,西泠印社將社產和文物,全部移交給了政府,從此完全停止了活動。在毛澤東主席雙百方針的號召下,1956年5月26日,外公在浙江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提交建議,希望恢復西泠印社中的篆刻印泥,兼售書畫和西湖的碑帖等。1957年11月17日,在外公的寓所,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成立籌備委員會,外公擔任主任,陳伯衡、潘天壽為副主任,沙孟海、諸樂三、阮性山、韓登安為委員。籌委會共召開了六次會議,但籌建工作并不順利,到1959年,籌委會名存實亡。期間,先恢復了西泠印社營業(yè)部。外公利用自己的影響,繼續(xù)積極爭取,他認為西泠印社的學術活動,應該繼承下來,浙派發(fā)展勢力較大,不僅是浙江的特產,而且是在東方及世界上獨具的。1963年,西泠印社建社60周年之機,外公當選為復社后第一任社長。擔任社長后,外公第一個建議就是要每月一次社員聚會,討論學術問題。同時,外公自己帶頭,將藏品捐贈給印社,并聯絡許多名家慷慨相助。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陳振濂認為外公是:百年西泠印社存亡繼絕的第一代中興功臣,從而使西泠印社的歷史得以賡續(xù),文脈得以延伸。沒有他,今天早就沒有西泠印社了。
踏踏實實做學問。外公有一句名言:凡人要治學、做事,必當先有傻勁,有傻勁,然后可以不計利害,不顧得失,干出一點事業(yè),成就一點學問。外公學識淵博,著作等身,工書法,善詩文,精醫(yī)藥、戲曲,生前著有《書學源流論》、《論書絕句》、《鐵如意館題畫詩》、《本草簡要方》、《中國戲曲瑣談》等。雖然多才多藝,但他畢生致力于古籍校勘,抄校古籍六千余卷,已出版的有《說郛》、《罪惟錄》、《越絕書》、《洛陽伽藍記》、《國榷》等十余種。
外公一輩子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抄書,他讀的書多,知道書籍對人的影響,因此擔心“人生多歧路,歧路在書中”。外公三十二歲點讀二十四史時,見到劉子庚父親所校的四史,深知讀書應先讎校。三十五歲時,校《資治通鑒》,“見秦使大良造伐魏吳氏注數百字,考定其為必是商鞅后得蜀宋本,方知原有二字,刻本偶脫。乃知胡氏,元人所見,已非善本;而讀書貴精校,又須得善本。自此,乃益用力于讎校及搜抄善本、孤本。是年,抄本已積三四百卷矣。”三十八歲,任京師圖書館主任,“日拂拭灰土中,以求遺逸,檢查舊目,修整殘編,檢校謬誤。……故兩年之間,抄校時間,雖因而減少,所見奇書,實為畢生最富之日。”四十歲,外公欲把抄校古書籍,作為一生的事業(yè)來從事,有自書對聯為證:分明去日如奔馬,收拾余年作蠹魚。八十歲壽辰時,他作詩一首,對自己幾十年的抄校生涯作了總結:四五十年事抄校,每從長夜至天明,忘餐廢飲妻孥笑,耐暑撐寒歲月更。竊寫真同無賴賊,劫余剩書半邊城。天憐手眼今如故,料是償書債未清。
外公刻有兩方印章,“手抄千卷樓”和“著書不如鈔書”,足以表明他對校讎古籍的鐘愛和決心。外公每日可抄書一卷,影抄則三日一卷,如果書主催交急迫,則夜以繼日,可抄二萬四五千字。因為一天能寫小楷一萬五六千字,朋友間戲稱他為“打字機”。如果遇到友人來訪,他能與友人邊談邊抄,從不脫誤。他的抄書方式兼具表演性質,抄書時,就象擺棋譜一樣,從一頁的中心先抄寫幾個字,然后以這幾個字為中心進行布局,能一字不差。有時又能在一頁的四角抄寫幾個字,然后進行布局,一字不漏,可謂出神入化。
開朗寬厚度人生。新中國成立前,外公帶著家人顛沛流離,經歷過戰(zhàn)亂,飽嘗過失業(yè)。一生從事過很多職業(yè),既有解決溫飽所為,更有多種特長的展示,林林總總,外公一直坦然面對,并秉持著“學問要向好的學,生活要向不如的看”的態(tài)度。新中國成立后,外公的生活才漸漸穩(wěn)定下來,雖然年事已高,但一直致力于古籍校讎和圖書館事業(yè),度過了一個幸福的晚年。
外公性格開朗,待人寬厚,做事光明磊落。有幾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文革結束后,我家來了一位客人,自報家門,說是外公曾接濟過他家,現在日子好過起來,特意來看望我媽,并問有啥事可讓他幫忙做。后來,逢星期日,他常來我家?guī)椭鷵Q煤氣,共進午餐后才告辭而去。
我到浙江圖書館工作后,碰到姜東舒先生,他看到我就說:你外公對我很好,在書法和工作上都有幫助和扶持。他還特意去看望我爸媽,表示對外公的敬仰。每次見到他,他總是要我替他問候我爸媽好。我結婚的時候,他送我一幅他的書法作品:最愛孤山雪后來,野梅幾樹水邊栽。著花不過兩三朵,獨向人間冷處開。這是外公的詩作,姜東舒先生告訴我這也是他最喜歡的作品,今天以這種方式傳遞給我,這樣的情誼,讓人難以忘記。
圖書館和昆劇團都屬文化系統,我經常有機會和昆劇團的領導在一起開會。也因為在一起開會的機會增多,大家也漸漸熟悉起來,當他們知道我和外公的關系后,告訴我:你真應該來聽聽昆曲。原來外公很喜歡昆曲,被演員們稱為“張老”。“傳字輩” 在上海剛出道時,外公就去看他們演出,并且常常是拿著曲本去看戲,逐字逐句,細細品味。外公對周傳瑛等幾個年紀小的尤其喜歡,每當手有閑錢時,演出結束后,外公常邀請周傳瑛和其他幾個同科“小囡”一起喝點小酒,講講昆曲戲文,但畢竟曲高和寡,周傳瑛他們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最后,外公點名了五個學生:姚傳薌、張傳芳、劉傳蘅、華傳浩、周傳瑛,在自己家里給他們上國語課,特意挑選《幼學瓊林》作為課本。為此,外公還請了一位廣東人許月旦先生做助教,每天兩個小時的課,在外公家吃中飯,下午不耽誤演出。1954年,為紀念洪升逝世250周年,外公提議周傳瑛排練《長生殿》,并把排練場地放在文瀾閣內,每天去聽演員們坐唱,新排的《長生殿》在杭州市人民游藝場首演,這是新中國戲劇舞臺上第一次演出昆曲版本,非常值得紀念。田漢、洪深等都給予了高度評價。一出戲救活一個劇種的《十五貫》,也是經過外公過目后敲定文本。
今年是外公離世50周年,浙江圖書館為他舉辦了系列的紀念活動,我想,單位為他舉辦活動是表示了一種敬意,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圖書館歷史中的一些人物。作為后人,我在緬懷之余,更要學習外公的優(yōu)良品質,既要做好事,更應該做好人。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外公謝世50年,但他一直并未走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