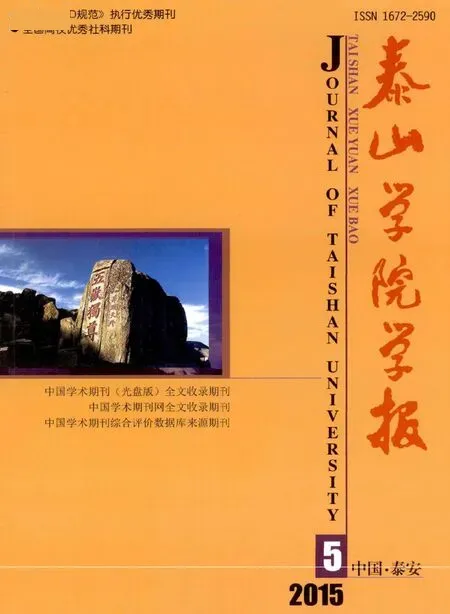自虐的詩意與精神的救贖
——卡夫卡小說《饑餓藝術家》評析
劉 欣
(泰山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山東泰安 271021)
自虐的詩意與精神的救贖
——卡夫卡小說《饑餓藝術家》評析
劉 欣
(泰山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山東泰安 271021)
《饑餓藝術家》是卡夫卡晚年創作的一部重要短篇小說,也是卡夫卡一生文學創作和藝術追求的歸納和總結。它既是卡夫卡自虐式的作家生活的寫照,又是其進行自我精神救贖的一篇象征性寓言。
卡夫卡;《饑餓藝術家》;自虐;救贖
《饑餓藝術家》是卡夫卡晚年創作的一部重要短篇小說,作家以現實主義的藝術表現手法描寫了一個純粹藝術家的生存境遇以及其荒誕的人生悲劇。這篇小說故事完整,卻歧義頗多,具有多重的象征意義,閱讀后產生深深的困惑和無盡的思索,也帶來了理解上的難度。我們知道卡夫卡小說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K,帶有卡夫卡自己的影子,而饑餓藝術家我們不妨看作是卡夫卡的自況,饑餓藝術家的一生也是卡夫卡一生文學創作和藝術追求的歸納和總結。它既是卡夫卡自虐式的作家生活的寫照,又是其進行自我精神救贖的一篇象征性寓言。
一、自虐的詩意
自虐的“虐”,在《說文解字》中,對“虐”字的解釋是“虐,殘也。從虎,爪人,虎足反爪人也”。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虐”意思是“殘暴狠毒”,而“虐待”即“用殘暴狠毒的手段待人”,從字面的意思講,“自虐”就是自己用殘暴狠毒的手段對待自己。這是字典上較權威的含義,也是人們約定俗成的理解。
在心理學上講,是一種自己傷害自己的行為,是一種主客同體的虐待。它屬于自己制造痛苦自己接受的行為,即施虐的主體又是受虐的客體,受虐的客體同樣是施虐的主體。在人類社會中,自殘、自傷以及自殺等現象均屬于自虐行為。這類現象是普遍存在的。自虐按照人們接受的意愿為標準可以劃分出主動型自虐和被動型自虐兩種。主動型自虐是指受虐者心甘情愿地、主動自覺地有意識地進行的自虐行為。事實上,這類自虐者自覺自愿地、有意識地、主動地進行自虐行為在整個自虐行為中占的比例較小,絕大多數的自虐行為都屬于被動型自虐。而卡夫卡的《饑餓藝術家》中藝術家的表演卻是屬于主動型的自虐,這種藝術表演的行為方式是饑餓藝術家自主習得的,而非外人強加的。
卡夫卡,Kafka,希伯來語,意思是“穴鳥”。鳥是渴望飛翔的,穴是鳥棲息的窩。而穴鳥這一名字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的生存困境和人生的悖謬。“卡夫卡的性格是一種極端內斂型的性格,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典型的弱者形象”[1]。在他的短片小說《地洞》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為自己精心營造安全的生存環境——地洞的小動物。這個地洞用力之大耗時之長,建造的非常結實牢固耐用,而這個小動物卻無時不刻地對自己的生存環境顧慮忡忡,驚恐萬狀,“即使從墻上掉下來一粒沙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然而,“那種突如其來的意外遭遇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個地洞的處境恰恰是卡夫卡自己生存處境的象征性寫照。意味著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可能在劫難逃,他的寓意是深刻的。地洞中的這只小動物可以說是卡夫卡的自況。卡夫卡在《致菲莉斯》的信中曾真實描述過自己理想的生存處境:“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帶著紙筆和一盞燈待在寬敞的、閉門杜戶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間里。飯由人送來,放在離我這間最遠的、地窖的第一道門后。穿著睡衣,穿過地窖所有的房間去取飯將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著細嚼慢咽,緊接著馬上又開始寫作。那樣我將寫出什么樣的作品呀!我將會從怎樣的深處把它挖掘出來啊!”[2]卡夫卡對自己的生活幾乎到了非常苛刻的程度,從來不追求物質的享受,只追求形而上的精神生活,在生活上是個極簡主義者,有著較為濃厚的自虐傾向。他完全把自己禁錮在一個密不透風的地窖中,仿佛就像饑餓藝術家把自己裝在鐵籠子一樣,自娛自樂地享受著自己的藝術表演,如癡如醉地沉浸在其中忘卻自我,自虐并快樂著。葉廷芳認為卡夫卡有這種傾向:他贊美磨難,把磨難視為人生的內在積極因素。因此,他愿意接受苦行僧似的自我折磨。
在《饑餓藝術家》中,饑餓藝術家為了達到饑餓藝術的極致,他不顧自己身體的忍受力和承受力,執意要突破饑餓藝術表演的最高期限40天。他嚴格恪守藝術的最高法則,在這40天之內,沒有點滴進食,自覺自愿地忍受各種痛苦和折磨,他既是自虐的主體,又是積極主動地自己對自己進行施虐,既是受虐者又是施虐者,在饑餓表演過程當中,看守人故意制造一些機會,留有一些時間和空間,讓他可以有機會添加一些流食讓他保存體力,以便可以延長他饑餓表演的時間。可他硬是堅持點滴不盡,因為那樣的話就違背自己一直堅守的藝術家的職業操守,是他自己無論怎樣都不會去做的。因為他的藝術的榮譽感禁止他吃東西。饑餓藝術是饑餓表演的最高境界,為了達到藝術的最高境界,他完全可以一直饑餓下去,乃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顧,他是饑餓藝術的殉道者,用自虐的方式為饑餓藝術表演獻身,以此做為求證自身存在價值的方式。正如貝克考特在《文化的精神分析》中指出的那樣:“這些社會中的人們的強迫癥的癖好,來自超我的懲罰性,而超我則隱含于唯一的上帝之中”。[3]饑餓藝術家對饑餓藝術表演的強迫癥的癖好,無異于猶太教徒對上帝耶和華的崇拜和愛戴。
饑餓藝術家為藝術獻身,就像卡夫卡為寫作而獻身一樣,他的創作即是他的生活,寫作成為了卡夫卡的一種生存方式。在生活方式上他別無所求,只要能夠不影響他的寫作,他可以舍棄一切,完全沉浸在孤獨、恐懼、負罪、與世隔絕的生活中,畫出自己“存在地圖”。卡夫卡說:“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朝著寫作的集中,當我的肌體中清楚地顯示出寫作是本質中最有效的方向時,一切都朝他涌去,撇下了獲得性生活、吃、喝、哲學思考,尤其是音樂的快樂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這些方面全都萎縮了。”“外界沒有任何事情能干擾我的寫作。我身上的任何東西都是用于寫作的,絲毫沒有多余的東西,即使就其褒義而言也沒有絲毫多余的東西。”[4]卡夫卡為了寫作拒絕了生活中的一切友情、愛情、婚姻和家庭,曾經三次訂婚又三次退婚,選擇了他自己所懼怕的那份孤獨和恐懼,他把寫作看得高于一切,不允許任何世俗的雜念玷污他的創作,他對寫作的完美追求又近乎絕望。就像饑餓藝術家對饑餓的表演一樣。
他的作品都不是憑作家的技巧“做”出來的文章,而是作家生命的一部分,一如他筆下的那位“饑餓藝術家”,表演的無限性和藝術的完美性是他唯一的追求,至于因此他的生命會消失他是全然不顧的。實際上他是在用生命換取表演(在卡夫卡是寫作)的可能性。[5]這位現代藝術的探險家,仿佛是上天降大任于斯人,為了文學藝術,他把“一切生之歡樂”都搭上了,這是一個藝術殉難者的形象。這需要多么頑強的意志力和毅力,甚至需要把性命都豁出去的犧牲精神。
二、精神的救贖
卡夫卡視寫作為生命,寫作是他內心祈禱的方式,當成“砸碎我們心中冰海的斧子”[6],成了“內心世界向外部世界推進”的手段,他感到只有寫作才“是一種奇妙的解脫和真正的生活”,“是一種巨大的幸福”[7]。卡夫卡生活的時代西方社會動蕩不安,危機四伏,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人們的精神信仰,帶來了嚴重的精神創傷,哲學家尼采口出狂言宣布“上帝死了”,整個西方現代社會陷入了萬物枯死的精神荒原。卡夫卡作為一個特別敏感的作家,他以自己的切膚感受和深刻體驗洞悉了西方社會的這一切。而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人生經歷使他離群索居,走進靈魂的“城堡”,他是個猶太人,不屬于基督教世界,而作為一個猶太人卻又對猶太教義持異議;作為一個說德語的人,他不完全是捷克人,作為一個捷克人,他又是奧匈帝國的臣民;作為一個白領人,他不屬于資產階級,而作為一個資產者的兒子卻又不屬于勞動者;作為一個職員,他認為自己是個作家,可作為一個作家,他既無法完全從事創作也不珍惜自己的作品;他的內心成了一個多元的世界,他無所歸依,是一個生活的局外人和異鄉者,在精神上成了孤獨無依的精神流浪漢和漂泊者。在卡夫卡看來,身外的世界是沒有意義的,是荒誕的,人們甚至不能通過對外在的行動的選擇來確定自身的存在的意義;而對于我們的內心能否支撐起生命意義的沉重,他也是猶豫不決的。“這世界和我的自我在難解難分的搏斗中,看來非撕破我的軀體不可。”[8]由此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處于“搏斗中”的關系,表明了他對通往自身存在之路的一種選擇困境。
在《饑餓藝術家》中,饑餓藝術家一刻不停地與自己的內心在作斗爭。起初饑餓藝術家的表演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理,是很受觀眾歡迎并風靡全城,“全城的人都在為饑餓表演忙忙碌碌,觀眾與日俱增,人們都渴望至少觀看一次饑餓藝術家的表演。”然而幾十年后,情形完全不一樣了,人們對饑餓表演的興趣大為淡薄了,被那些熱鬧上癮的觀眾忘卻了。原來用于饑餓表演的小小鐵籠子居于舞臺的中央位置,小籠子前觀眾圍得水泄不通,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后來被一個大馬戲團招聘了去,安插在場外一個離獸場很近的的交通要道上,籠子周圍是一圈琳瑯滿目的廣告,彩色的美術體大字令人一看便知道那里可以看見什么。人們在看獸畜表演時順便經過,稍停片刻,小小的鐵籠子前,人煙稀少,冷落蕭條。外部的世界經歷了如此大的變化,藝術家經歷了這樣的大起大落、喜悲人生,但藝術家對藝術的追求,執著的信念始終未變,堅守著藝術的純潔和神圣。最后餓到了骨瘦如柴,皮包骨頭,終于倒在了藝術的舞臺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臨死前他說了一句“因為我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這樣的食物,請相信,我不會這樣驚動視聽,并像你和大家一樣,吃得飽飽的。”[9]
饑餓藝術家對藝術的執著追求和信仰可以看做是基督教徒對“上帝”的虔誠和膜拜,通過這種方式以期死后得到精神的拯救。卡夫卡也像饑餓藝術家那樣一直在尋找自己的最佳生存方式而又苦于找不到,他是人類最早感知現代人生存困境的作家。在他的心頭充溢一種對人類生存的危機感,他像饑餓藝術家那樣在用生命做了體味和證實。因此他的內心成了一個“龐大的世界”,借助于文學手段將它宣泄出來,成為他“巨大的幸福”。
饑餓藝術家企圖以一種內在的“不可摧毀的東西”來頂住“上帝”死后的可怖現實。然而,人們不再相信有堅定的信仰。只有他依然執拗地固守著那些信仰,凄然悲慘地死去。正如尼采所說:“上帝只是人的一種猜測,飲了猜測的折磨,誰能不死去?”即使是你的愿望再善良,雄心再堅定,自我克制的精神再偉大,個人是根本不可能阻擋住住歷史時代前進的步伐,改變不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和精神信仰,饑餓藝術家的悲劇在此展現得淋漓盡致。
卡夫卡曾這樣描述他的寫作動機的:“我將不顧一切的寫作,絕對地,它是為自我保護而進行的斗爭。”[10]“如果我不從事寫作,情形會變得更壞,更令人無法忍受。我肯定要以瘋癲終其一生。”[11]“有一種巨大的渴望,想把完全出自我的一切焦慮寫下來,把它寫進紙的深處,正像它出自我的內心深處那樣,或者用這種方式把它寫下來。能把寫下來的東西完全吸收到我的身上去,這并不是藝術方面的渴望。”[12]由此可見,卡夫卡進行藝術創作的深層動機并非出于對純美學意義上的藝術追求,而是通過寫作釋放內心的痛苦,獲得內心的寧靜,為自己尋找到一條精神的救贖之路。
卡夫卡始終在尋找一種精神皈依,他在日記中寫到:“相信存在著一個目標,人們通過經歷各種不幸而朝它前進”,[13]他曾說“人不能活著而沒有一種對他自己內心中不可毀滅的東西懷有恒久的信仰”,“可能表現這種隱秘形式之一是對一位別人不知道的神的信仰”。[14]這體現了卡夫卡精神人格的獨立性和個性。他不愿從眾,更不愿媚俗,他需要的不是人人都信奉的猶太教或者是基督教,而是能真正滿足他精神需要的私人化宗教。作為一個渴望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救贖的生命個體,卡夫卡拒絕接受這種每一個出身猶太家庭的人都擁有的猶太教,他不愿意成為一個大眾化宗教意義上的猶太教徒,而要成為在精神信仰方面保持自己生命個體的精神自由和獨立。
現代哲人尼采說過:只有經歷過地獄般磨難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卡夫卡通過饑餓藝術家對藝術極致的苦苦追尋簡直到了令人靈魂發顫的地步,甚至陷入到對個人的罪惡拷問和心靈懺悔。卡夫卡就是通過描寫人物心理上的自虐性的宣泄和病態的自我折磨,進而在人格分裂的煉獄中對人物的靈魂進行著烤問和批判。卡夫卡用這種殘忍的對自我心靈的透視方法,從對世界的懷疑與神秘的處罰把苦難理想化,并且在宗教的熱忱和原罪意識的懺悔下觸發對人類靈魂的深入剖析,進而達到清洗人的心靈,凈化拯救自己靈魂的終極意義的關懷,即試圖以回歸人性使自己的靈魂獲得精神的救贖。正是在這種深度上卡夫卡的苦難追尋已經上升到對自我追尋的靈魂救贖。
]
[1]吳曉東.從卡夫卡到昆德拉[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2]卡夫卡.致菲利斯[A].論卡夫卡[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3]顧曉鳴.猶太——充滿“悖論”的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4][5][8][9]葉廷芳.卡夫卡全集[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6][德]瓦根巴赫.卡夫卡傳[M].韓瑞祥,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
[7]葉廷芳.西方現代藝術的探險者[J].文藝研究,1982,(6).
[10][12][13][14]卡夫卡.卡夫卡日記[M].閻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11][德]貝勒克.向死而生[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
(責任編輯閔軍)
The Motion of Self-abuse and the Redemption of Spirit——An analysis of Franz Kafka's novel A Hunger Artist
LIU 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Taishan University,Taian,Shandong 271021)
A Hunger Artist is a very important short novelwrote by Franz Kafka in his late life.It is also a summary and conclusion of hiswhole life's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art pursuit.This novel is notonly a picture of Kafka's writing life of self-abuse,but also a symbolic fable of self-redemption of spirit.
Kafka;A Hunger Artist;self-abuse;self-redemption
I3/074
A
1672-2590(2015)05-0059-04
2015-09-02
劉欣(1965-),女,山東文登人,泰山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