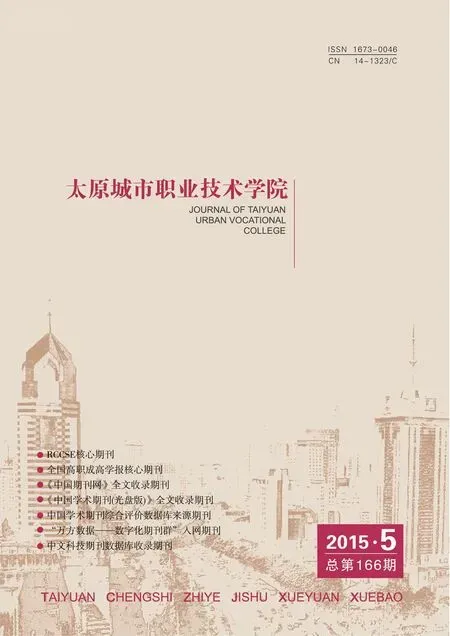論韓寒小說中敘述成長的媒介
房 存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成長”是文學的永恒主題,而成長的命題是復雜的。“80后”的成長環境較前幾代人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們成長在市場經濟發展、文化多元的世紀之交,時代賦予他們的是穩定的生活模式,卻也忽略了青少年的主體需求。在自我與現實的激烈碰撞中,“80后”強烈地追尋“另類自我”,以此來昭示自我的存在,延續著“未完成”的成長。當年的“校園寫手”韓寒進入社會后漸漸褪去了青澀的外衣,在理性自省中實現了創作主題的升華,為“80后”成長書寫增添了諸多不同的內涵與色調。
一、成長的主線——車
在韓寒的成長敘述中,“車”是一種重要的道具,它始終伴隨著主人公的成長,是成長的重要見證。“車”在現代社會代表著速度、激情與個性。“飆車”也成為現代人越來越迷戀的一項運動。在韓寒筆下,“車”是青少年追尋“另類自我”和“高峰體驗”的依附,暴露了他們擺脫不了依賴性和拒絕成長的心理特點。在“失范年代”,青少年情緒動蕩,好奇心強,無所適從,于是他們開始在現實中追尋“另類”。但是他們的自我調節機制和獨立意識不完善,借助著“車”的外界力量武裝自己,成為他們尋求精神滿足的主觀心理原因。
“車”在韓寒的小說中首先是一種“他人認同”,主人公因為“車”而暫時消解了自我迷失時期的空虛,在別人的關注中獲得了價值實現的快感。例如,《像少年啦飛馳》中,“我”和老夏過著無聊的大學生活,我們都迷戀上了車。老夏以交學費為由騙家人寄錢,率先買下了走私的摩托車本田PGM3,開始了他的飆車生涯。他又因偶然的機會進入了一個流氓飆車隊,并且成為隊伍里的老大,獲得了豐厚的收入,成為了學院里的首富,從此女友不斷,成為很多“泡妞無方”的男生膜拜的對象。
若“他人認同”還不足以成為主人公嗜車如命的動力,那么“自我認同”則是其源泉。《像少年啦飛馳》中“我”整日沉浸在對人生思考無果的頹廢中時,只有高速能令“我”清醒,讓“我”感到世界是如此真實和美好。老夏也是如此,他認為成長是越來越懂得壓抑欲望的過程,而飛車是解決方式。《1988》中丁丁哥哥有一輛很酷的單車,這讓孩子們很羨慕,但是他渴望的是一臺摩托車,可以自由地去看世界。有一天他真的帶著“我”去偷了一臺嘉陵摩托,然后載著“我”去兜風過癮,這構成了小鎮的重大案件,使一名叫肖華的年青人含冤坐了十年的監獄。現代人對車速的迷戀,可以借助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緩慢》來解釋。昆德拉對現代人崇拜速度進行了批判。他認為,速度是技術革命獻給人類的迷醉方式,相比跑步者始終待在自己的肉體里,摩托車騎士的身體卻游離于運動之外,這種非物質的純粹感性的高速,使人自流動的時間中抽離,從而自時間中解脫而了無恐懼。可見,“飆車”有兩個存在意義:一是獲得身體上的高峰體驗;二是忘卻自己與時間的變化。近似達到“高峰體驗”的賽車手,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實現感,最大限度地擺脫了阻滯、畏懼、疑慮。而忘卻自己與時間的變化,順應了拒絕成長的心理需求。
然而,現實的常規不允許類似的出格行為,況且自我麻痹式的優越感并不等同于真正意義的強大。車速帶來的快感雖然和高峰體驗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它是一種突發的、剎那間、感性、高潮式的體驗,而不同于馬斯洛最初意義上“一種通過時間、努力、修煉、奉獻達到的一種心靈境界”。心理學家稱“飆車”跟“吸毒”有著相似的心理基礎,都源于一種意識朦朧中的現實和自我解體,真正的動機是逃避現實。所以,主人公們紛紛為“車”付出了代價。《像少年啦飛馳》中,老夏的輝煌期因開車時撞到人被學校開除告終,“我”因處理老夏的車被誣陷也被開除。《1988》中的丁丁哥雖然是鄉親們眼中優秀的大孩子,也沒能逃離命運的魔掌,用生命為自己的選擇埋單。
隨著現代人對速度的渴望,“車”“飆車”這一新意象進入了文學作品,被賦予了深刻的寓意。韓寒在小說中親歷性地刻畫了一群青年對車速的迷戀,滲透出動人的真情。這種刻畫沒有停留在肉體刺激的感性層面,而是理性地交織著成長的殘酷與真實。
二、成長的環境——封閉的城池
“一座城池”是韓寒小說的創作模式,也是主人公掙脫不了的成長環境,這座城池不是傳統成長小說中的宏大歷史背景,而是日常生活秩序,它不斷磨蝕、改寫著囿于其中的人的成長。小說不斷上演著“人生處處是圍城”與“沖出圍城”的故事。
韓寒的小說貫穿著“成長處處是圍城”的被欺騙的無奈。“80后”生活的城池無外乎學校、家庭、社會。《三重門》中,林雨翔千辛萬苦進了市重點,進來才發現沒有想象中美好,千方百計想沖出去,可是家庭施加的壓力使他只能服從,社會也不能接納未成年人,于是他只能是“思想的巨人”,彷徨于無地。同樣,《像少年啦飛馳》中的少年對嚴格的校規恨之入骨,對大學充滿失望,急于解脫,進入社會卻發現進入了更大的“圍城”,有了更多無奈。韓寒在小說中還提到“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發現,原來這個淮海路不是屬于我的而是屬于大家的”。這是現代都市文明中人們常常面臨的尷尬處境,即“在而不屬于”的困厄。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年輕人涌進大城市尋求發展,但又無法被城市文明接納,城市中的人也感到自己生活的家鄉被外鄉人占據,于是都市中普遍彌漫著社會歸屬感喪失的困頓。
但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不會輕易形成“宿命感”,他們飛蛾撲火地挑戰著命運的設定,于是小說中重復著“闖出圍城的沖動與失落”的模式。虛構的城池構成了《光榮日》的背景。《光榮日》中的七位畢業生向往“竹林七賢”的人生,他們憧憬著自由,希望遠離俗世的骯臟糾紛,所以逃離了“城市”這座“城池”“隱居”于鄉下。然而他們卻意外地親手炸了學校附近的大山,意味著連最后一片凈土都消失了,他們最終還是要卷入“城池”中。《一座城池》則是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城池”的意象。從被“學校”拋棄的那刻起,“我”和健叔正式進入了社會這座城池,并被永遠地禁錮。這一主題在結尾處得到升華,工業區的廠房爆炸,人們在大街上哄搶商店,后來就人搶人,身先士卒的男子被扒得只剩下一條紅色內褲,這最后一條內褲被一位時尚女郎當做名牌拿走……這是一座憂傷的城池,城里雖然有著許多有笑臉的人,可作為城外的人卻看著城里人的笑臉想流淚。文章的最后,“我”拉著“永久妹妹”一起朝著城外奔跑,可最后卻還是轉身……說不清原由或許根本就沒有為什么。從進入這座城池開始,“我”就被這城池給圍住,即使沒有半點禁錮。
人是“被拋入”這個必然王國的,“被給予”了特定的“一小片存在”,所有的過程都未得到本人的“同意”與“選擇”。基于此,小說中的青少年的身體和精神不停地飄蕩,卻永遠被限制在固定的空間里,他們試圖建立自己的一套生活秩序,卻不得不被納入成人世界制定的規則。
三、成長的軌跡——流浪
流浪是人類史前的一種深刻的記憶,一種固有的本能,一種培養已久的欲望,一種——借用榮格的一個概念說——“集體無意識”。這種源于本能的“流浪”在現代文明中甚至強化為時代本質的一部分。英國思想家鮑曼認為流動的現代性已經到來,世界與流浪者并駕齊驅,甚至趕超他們,人們不得已不斷前進,每一階段每一驛站都指向成就。流浪作為成長的重要階段和時代本質,在文學作品中自然不乏表現。
以往成長小說中“流浪”的作用是順向的,主人公通過遭遇挫折,身體和思想都發生一定的變化,開始主動向成人靠攏。這種流浪模式是西方成長小說的慣常書寫,中國新時期以來的成長寫作也有借鑒,如曹文軒的兒童成長小說、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等作品。但是,韓寒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在未做好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出發的,此時的青年涉世未深,前方對他們來說是一團迷霧,他們不諳“出走”的意義。正如《一座城池》這樣起于意外的逃命生涯,在這場沒有意義的漂泊中,主人公也在成長,這就是漂泊的意義。在這里,流浪直接導向的不是成長的完結,而是結局的高懸。但是,成長是“波浪式前進”的過程,每次的流浪都為他們長大成人做了準備。
在韓寒的小說中,流浪還可以看做是成長的儀式。莫迪凱·馬克斯認為,“在成長小說中,儀式本身可有可無,但必須有證據顯示這種變化對主人公會產生永久的影響”。據人類學家探究,原始社會就盛行“成人式”,當個人通過各個“人生之節”時,必須接受一連串的神圣儀式的洗禮,或各種嚴酷的“成年禮儀”的考驗,以此使未成年人脫離自然狀態。“成長式”到了文明社會,因其血腥和殘酷被淘汰,但這種“儀式”卻保留在成長傳統中。文學書寫中都會有某種形式標明成長,相比十七年文學中的“入黨”儀式,韓寒小說中的“流浪”是一種“未完成的成長”儀式,預示著成長的可能,卻不是成長過程的完結。《長安亂》中,釋然第三次出走長安便是主動為之,目標是為少林復仇,象征著釋然開始成熟。《1988》中有兩次“我”目標堅定地出發,一次是去接朋友的骨灰,一次是帶著“屬于全世界的孩子”去尋找新生活。
在路上,是一個具有深厚哲學意蘊的成長命題,意味著多種可能性,磨難、希望、離別……主人公身體的流浪激發了精神的流浪。精神的流浪雖是漂泊無依、天馬行空的,但它無疑更接近人隱秘的意識,是成長不可缺少的催化劑。
韓寒以精妙的的藝術表現,借助獨特的意象,將“80后”的精神成長歷程展示得洞徹人心,并且在社會性批判和人生思考的道路上,韓寒已經走得很遠了。至“80后”作家登上文壇,中國的成長小說開始真正關注青少年,表達他們內心的聲音,彌補了當代文學中本階段成長狀態的空白。
[1]韓寒.韓寒五年文集[M].沈陽:萬卷出版社,2008:418.
[2]曹文軒.近二十年來文學中的“流浪情節”[J].文學評論,2002(4).
[3]芮渝萍.美國成長小說研究[M].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