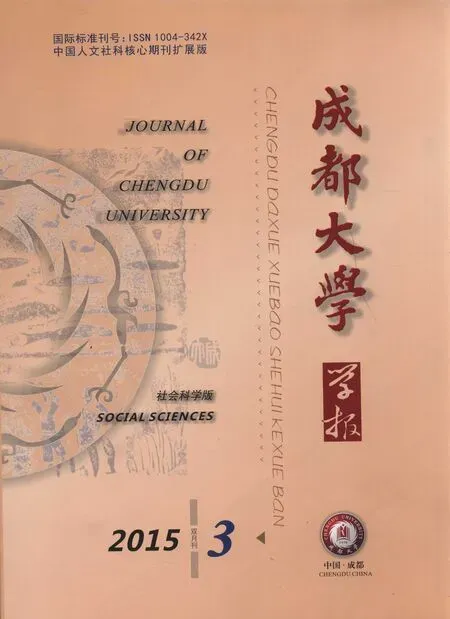川劇老藝術家口述史(四川卷續)之余琛篇*
李軾華 萬 平
(成都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四川成都 610106)
川劇老藝術家口述史(四川卷續)之余琛篇*
李軾華 萬 平
(成都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四川成都 610106)
余琛,川劇藝術家,國家一級導演,具有豐富的編、導、演經驗。在多部戲曲、舞蹈中任導演及舞蹈設計工作,善于將戲曲藝術和舞蹈藝術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同時,作為四川省川劇學校的教師,多年來為川劇藝術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余琛;川劇;藝術人生
余琛,女,1946年出生,國家一級導演,四川省川劇學校(今四川藝術職業學院)教師,中國戲曲學院客座教授。1958年進入四川省川劇學校學戲,1964年畢業留校任教。主工花旦,代表作《拾玉鐲》、《放裴》、《別洞觀景》、《秋江》等。余琛博采眾長,繼承和發展了川劇旦角表演藝術,將戲曲藝術和舞蹈藝術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其學術專著《川劇旦角身韻》是這種藝術風格的完美體現。曾舉辦“余琛川劇旦角表演專場演出”,引起轟動。這臺演出,將川劇旦角身段、動作的舞蹈美表現得淋漓盡致。其參與創作的舞蹈《俏花旦》獲全國舞蹈金獎,在《死水微瀾》、《紅梅記》中的舞蹈設計贏得廣泛好評,還擔任川劇《卓文君》及各種晚會的策劃、導演工作。幾十年來,一直致力于教書育人,為川劇藝術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所教學生中多人獲得戲曲梅花獎。退休后仍堅持排戲、組織晚會、培訓劇院學生,并應其他藝術院團之邀赴各地傳授川劇技藝,將川劇藝術巧妙地融入到其他藝術中,為川劇的傳承振興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采寫時間:2014年5月21日下午
采寫地點:四川藝術職業學院
采寫:李軾華 萬 平
攝錄:劉耀蔚 劉 舒
李軾華(以下簡稱李):余老師,您好,您從事川劇事業已經幾十年了,那么當初您是怎樣和川劇結下了不解之緣的?
余琛(以下簡稱余):我是1958年12歲的時候,就進入川劇學校。當時的家庭經濟狀況不是很好,我媽媽一個人帶兩個娃娃,我是姐姐,當時媽媽工資一個月是29塊5毛錢,要養活兩個娃娃是非常不容易。其實當時我并不知道川劇是什么,當時招生簡章上寫了這個學校讀書不要錢,還要發練功服,吃飯也不要錢,學費也不交,當時我非常心動,我就跟我媽媽說,讓我去讀這個學校。我小學學習成績非常好,親戚朋友都來勸我,為什么讓我去讀這個學校呀,我就跟我媽媽講,我去這個學校讀書不要錢,你把妹妹養好,我一定會有出息的。當時我家里很貧窮,連一床像樣的草席都沒得,墊絮是老師借了一床給我媽媽帶來,坐個車子到學校,翻開一看,草席中間爛了個洞洞,這就是媽媽給我的全部行李。我來了之后在學習當中非常勤奮、非常刻苦,但是當時并不懂川劇是什么。我記得我考試的時候填表,一個是演員,一個是音樂,我說那我就考音樂,因為在小學的時候還唱唱歌啊,還覺得考音樂可能就是唱歌,可能就是表演,后來老師把我眉毛給我一剃,看了說你不要學音樂,你學演員,我說演員要得嘛,那我就學演員嘛。于是我分到了演員專業,就從事了演員事業的學習。我想演員可能就是舞臺上演出,但是我還是不知道這是川劇。后來聽到有些老師在那里唱啊跳的,我覺得咋個有點像唱戲的呀,不過既來之,則安之。但是那個時候小,就想要勤奮地學習,長大賺錢,不要我媽媽去帶賬(注:欠錢),不要我媽媽去吃這樣大的苦。當時沒有更多的想法,沒有什么社會的責任,就想著長大賺錢供媽。
在學校慢慢地認識了川劇,在學的過程中,才知道艱苦,真的是早上五點過就得起床,從早上開始練基本功,上午練基本功,下午練基本功,晚上還要練。1958年、1959年還好,1960年開始飯都吃不飽,我們真的很慘,但是又很慶幸,1960年的時候,因為我們是學專業的藝術學院的學生,我們可以吃34斤糧,如果是普通的居民他們只能吃21斤到22斤,他們真是吃不飽。因為我們是學生,我們要練功,我們就是34斤米,所以那個時候也讓我們度了些難關。再加上后來還有些演出啊,別人就請我們吃一次飯,吃得很飽,或者好的地方,工廠里面還有點回鍋肉,在當時已經是很大的優惠了。但是我進入川劇事業后很奇怪,剛進來的時候不知什么,1959年的時候,回想起來是川劇的鼎盛時期,我剛進校沒有多久,川劇院組織一大批人到東歐十幾個國家去巡回演出,而當時關注我們川劇的是周恩來總理,親自帶劇本,鄧小平、賀龍、張愛萍一大批老革命家非常關注,所以當時并沒有覺得這個川劇哪里不好。而且我進學校開始,現在學校還有照片,戴一個紅領巾,歐陽予倩這些老藝術家到學校來看我們的課,然后看我們孩子。我們戴起紅領巾還去獻花,當時覺得挺好的,所以愛川劇。幾年下來,哪怕它再苦,當自己能夠上角色的時候,能夠演楊八姐,能夠演穆桂英,能夠受到觀眾的歡迎的時候,我覺得搞這個藝術真好。確實我從來沒想過打退堂鼓,我還是那句話,中間肯定有波折,但是我今年68歲了,我終生不悔搞了川劇。當然,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確實就讓我們下去了,只有京劇,川劇就不能,才子佳人全部趕下舞臺,所幸那個時候年齡小,我才20歲,就去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當時就跳個舞,跟歌舞團在一起跳,一起搞活動,經常跟他們在一起,然后樣板戲的演出也參加一些。但是回過來看,這一些和舞蹈演員的接觸,和他們在一起的排練又增長了我另一部分的知識。所以到后來,我自己能給自己搞專場,自己給自己出書,自己當導演,自己當演員,我建立了一條舞蹈和戲曲之間的道路,形成了我自己的風格,也就是我能到全國各地藝術院校、各地院團去進行教學、去進行排練的有利條件,這就是說在藝術這條路上,有一點,是在雄厚的豐富的川劇傳統的基礎上,我奉行這個原則,掌握了豐富的傳統知識,為我們的未來服務,為我們的年輕人服務,為我們以后的觀眾服務,這就是我現在的宗旨,否則就沒有人看了。所以我才去那邊(南充)講了課下來,連續講了3天,很多人都覺得,第一我們不認識川劇,但是這次我們感受到了川劇的魅力,像你這樣講,我們都想來演川劇了。我說川劇確實很好,留下很多寶貴的財富,關鍵是我們怎么去用它、怎么利用它、怎么保護它,是我們需要做的一個事情。我剛從北京回來,在中國戲曲學院上課,去給他們上課、排練、講座,也是講的川劇表演的知識。我的課堂上,越劇、閩劇、豫劇、黃梅戲、各劇種(的學生)都來上課,害得我們的戲曲表演主任貼張表單,不是這堂課的同學們,希望你們安靜,在旁邊只能旁聽,不能下來坐,我在旁邊把水袖穿起,那么上正課的同學我們的地方都沒得走的。而且從正式要求來講,是這堂課的學生才能學,不是這堂課的不能學,后來出了個通知公告以后,他們就乖乖地在旁邊就看課,但是他們要問。其實我很喜歡這種氛圍,中國的戲曲現在能夠這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年輕人這么愛戲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就像我今天在南充,他們市委宣傳部組織了將近五十個人,電視編導、電視節目組、舞蹈編導、戲曲編導,然后就是作家作者,然后還有文化館的館長,還有文化館具體的工作一線的這些工作人員,他們都來了,其實他們是完全不懂川劇的,只有兩個人是川劇團的,經過三天講課下來,就是剛才你們來之前,才拍了照片才回來,他們說這次簡直感覺到了川劇藝術的魅力,川劇藝術它不光是表演好,還有文辭非常優美。川劇最棒的魏明倫老師、徐老師,他們兩個的劇本好棒好棒,走向了國際,馬上《欲海狂潮》要到土耳其(美國)去,以前的《馬克白夫人》到日本、德國、西班牙,還有很多的不停的出國機會都是在宣傳川劇,還有和莎士比亞的戲劇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他們就是在背靠傳統、面向未來,在雄厚的傳統的基礎上,寫下了為年輕人服務、為后來人服務的這種思想性極強、藝術性極強的劇本。所以說現在演出非常好,最近可能曉得,如果是你們稍微關注的話,剛剛徐老師寫的,根據阿來的作品《塵埃落定》寫的川劇,陳巧茹等眾明星演出的反響非常強烈,年輕人喜歡看,老年觀眾也喜歡看。因為它運用了川劇的元素,川劇的這種表現的能力,唱做念打,表演什么都有了。讓觀眾來享受川劇的表演,而它的內容寫的其實是藏族,把藏族的聲腔藝術和我們川劇的聲腔藝術揉和在一起,非常地巧妙,所以年輕人喜歡看,老年人喜歡看,老年人覺得過癮了,年輕人也覺得過癮了,起碼我進入了這種戲曲的狀態。什么叫做戲曲,戲曲以歌舞演故事,它就叫戲曲,而和話劇、舞蹈是三種不一樣的表演形式。話劇是聲臺形表,舞蹈只能舞不能唱,川劇唱、練、打、舞樣樣都有,它是一個非常豐富的藝術門類,所以要求演員也非常地嚴格。戲曲演員也非常地苦,啥子都要練,我只練舞蹈多好,我只練聲樂多好,唱一首歌對不對,它就完了。戲曲又要唱,又要練,又要打。
李:余老師,您剛才說您是1958年進入四川省川劇學院學戲,是哪一年畢業的呀?
余:1958年進入學校后,1964年就畢業了,剛好遇到現代戲和傳統戲的交界,當時我們學校的領導全都拿不準,到底是全部要演現代戲,還是演傳統戲。當時我記得最早提出那個“兩條腿走路”,一個現代戲、一個傳統戲,當時學校領導覺得我是最合適的人選,又可以演現代戲,年輕嘛,18歲,又可以演傳統戲,不管走哪條路我都走得通。于是1964年我和我們學校校長張廷秀,我們8個人留在了學校當老師,但是1965年進行了一次上山下鄉的演出之后,1966年就開始文化大革命。
李:那您后來就一直堅持在舞臺上演出?
余:要演的,因為年輕嘛,因為我們學校經常組織演出,而且到2000年,我們都還在出去演出。
記者:那您演出的代表劇目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
余:《拾玉鐲》、《放裴》啊,《別洞觀景》啊、《秋江》啊,就這些折子戲,學生時演的大戲是《楊八姐》《白蛇傳》。在學校嘛,當時它不是劇團,它的演出,有完成場次的任務,所以在學校的演出當中,可以說幾個角色,像《楊八姐》是男扮女聲,《白蛇傳》演青蛇白蛇,《別洞觀景》花旦,我主要是花旦。這當中是1986年的時候,我曾到中國戲曲學院去進修了兩年,自費進修,1986年去,1988年回來,就一直到現在,2001年退休。
李:那您后來又在做導演工作?
余:對對,這個導演工作實際上是這樣的,我并沒有明確的目標要當個導演,我覺得我不能當導演。但是首先我回過來反思自己,我上課很認真,我就是要把所有川劇表演的所有組合,我自己編,自己給學生排,沒想到這種反復的過程鍛煉了這種導演的能力,這種編導的能力。所以1991年的時候,我自己編了一臺,自編自導自演的川劇旦角表演的、既非完全的程式又非完全的小品,它不是個小品節目,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程式,因為太程式之后就沒有更多的內容,人家就不是很喜歡看。你有一定的程式有一定表演,這個就比較靈活一點。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做了,那么這個晚會做了以后,就引起了我們四川電視臺的重視,幾乎從那年開始,四川電視臺每年春節晚會我都要去弄,那個各種大小型的活動,百花獎頒獎晚會、文華獎頒獎晚會,只要是在四川的戲曲部分我都參與了。所以從1991年到我退休,退休過后的幾年,都還在搞這種活動,編導活動。再加上我們學校后來就經常(組織)出國,出國需要小節目,小節目的內容,這些節目都是我在排,這些就是節目的鍛煉,編導能力也在鍛煉。但是從《死水微瀾》開始,我就開始進入劇目副導演的這種職能,也就是導演總導演的意圖我基本上能夠給它貫穿,所以慢慢開始學會了做導演,也喜歡上了做導演這個工作,我覺得它具有創造性,也很有挑戰性,也非常有意思。
李:那您現在是國家一級導演?
余:對,一級導演。還有中國戲曲學院98年的時候就聘請我為他們的客座教授,我就以這教授的身份去他們學校上課。
李:主要是講授川劇表演的知識?
余:對,一個是講座,一個課堂傳授,一個是排戲,排劇目,排川劇最好的經典劇目。
李:您主要的工作經歷就是一邊當老師一邊進行排戲的工作?
余:還參與很多大型劇目的編導動作,跟導演在一起合作。
李:能不能請說一些您主要導演的劇目啊?或者是您最喜歡的劇目,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可不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
余:《死水微瀾》是徐老師的劇本,當時最早的時候,叫我和徐老師一起做舞蹈設計,在做舞蹈設計的過程當中,我也是看徐培安老師學習怎樣做導演,這個戲得了文華大獎,我設計的舞蹈也得到很多專家的贊揚,雖然它沒有這個獎項,我們這戲獲得文華大獎,各個方面都有,但是獎項當中沒有設立一個舞蹈設計獎,但是我覺得沒有關系,反正我在這里面出了力,得到了大家的贊楊,這是一個。還有就是1991年的時候,曾經和北京的林兆華導演(合作),當時這個戲也是做的副導演的工作,這個我是從最初來講,我是比較喜歡的,后來徐老師排的《紅梅記》,里面所有的舞蹈都是我給他們做的,后來他們到法國演出,都是我做的。去年徐老師的劇《卓文君》,整個我是擔任導演工作,當時這個戲在幾個大學反映是比較好的,這個戲我是擔任導演,該做的工作都是做了的。
李:《卓文君》這部戲啊?
余:對,《卓文君》這部戲就是我的導演,其實我開始沒有那么大的欲望非要去做個導演,沒有這個欲望我要怎么,因為我沒有專門去學,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它自然就形成了這個導演的工作,自然就慢慢形成了。所以徐老師就說我信任你,我相信你,我說沒得問題。所以徐老師手把手和我在一起,然后大家共同在一起搞了《卓文君》。其實最早的時候,剛好打倒“四人幫”的時候我就在(做)導演工作,只是自己沒有意識到。就是我剛才說的,我全部沒想到,我覺得導演好麻煩,而且好深奧哦。沒想到在我實踐當中,慢慢地自然而然融入了導演這個工作,所以現在很喜歡導演,它的創造性,它的挑戰性太強了,而且我自己積累了(經驗)。因為我主要是搞表演,我積累這么多的表演知識,在戲里面是足夠用,而且還可以發揮,舉一反三,這是我最開心的事情。那么經常在電視臺做節目,我覺得有幾個節目做得是比較好的,比較成功的。一個是藍天寫的曲子,以《九九艷陽天》這個歌曲寫成的川劇戲歌,今天上午還放給他們看,這個是很完整的,而且是比較好的,電視臺說的這個節目有聽頭、有看頭、有想頭,就是藝術性非常的強。還有一個我本身是川劇花旦,我和劉莉莉合作搞的這個《俏花旦》獲全國舞蹈的金獎。我和劉莉莉合作,她是歌舞團的,我是戲曲部分的,我們在一起合作過后,中間的大部分動作都是由我提供,提供了之后編成了這個舞蹈,然后全部打響,這是川劇旦角花旦表演的集中體現,而且這個搞了幾稿。我自己本身搞的,1998年獲中國戲劇小梅花獎,一個獨舞,一個小女娃娃,獨舞。然后《小戲迷》,就是演少年鄧小平這個娃娃,他才五歲,我給他排了個節目,叫《小戲迷》,一想到這個川劇變得這么好,我咋個去做,《小戲迷》以致獲中國戲曲小梅花獎,還有個《小小金山寺》,這個娃娃的功太好了,也是參加比賽后,得了個小梅花金獎,三個都是我排的節目,得小梅花金獎。反正這些戲,青年得的獎,都是在今年比賽當中就是演員自己本身得的獎,老師得個指導獎。那個時候不是很重視這個事情,不像現在比較重視老師的編創,比較尊重老師的勞動,以前那個時候真是沒得啥子。所以我自己咋說呢,對獎項我希望得到,獎項沒得到我自己也沒啥子遺憾,這個事情我做了,學生受了益了,我該干的干了,而通過排練我自己積累了,持續到現在。你看我今年68歲,現在我戲約不斷,事情不停地做。而且我這兒六月份,馬上要去湖北排黃梅戲,一個大戲寫畢 ,創作劇目,導演說劇本馬上寄過來。8月1號到溫州甌劇,同樣和導演在一起做《橘子紅了》,這些戲我就覺得非常地好,而且我們有一個強有力的創作班子。所以我覺得平時排練的這些積累對我來說是一個鍛煉,我不停地把這些積累到我身上,然后在排這些大戲的時候,我可以讓他們放光,參加這種排練,參加其他劇種的排練,一個是學習的機會,一個是鍛煉的機會,所以今年就撞上了。我有一個朋友在中央戲劇學院京劇系,他當主任,昨天給我打電話,中央戲劇學院就是演電影這些,中央戲劇學院全部是京劇和戲劇,那個學校就是戲劇,那個學校現在搞了一個京劇表演系,他說我這個地方是一定要請你來上課的。今天在南充講了戲簡直不得了,從來沒聽過這么舒服的這種表演。我說不,是川劇的魅力,我說川劇的劇本怎么樣,它的表演手法怎么樣,為啥子其他劇種沒有,為啥子川劇有,為什么四川人就這么聰明,為什么四川人的智慧就想得出來,這是我要告訴你的。所以大家覺得聽了之后非常好,所以今天說還要請我到這里來,今天在那里照相喲,留念喲,(說)到我們這個地方再來講課這些。我覺得所有這一切并不是我個人怎么樣,第一個我現在愿意做,還有一個就是川劇藝術的魅力就這么強,所以我覺得作為川劇人我很自豪,我走到哪里,人們尊重我,不是尊重我一個人,是我代表了川劇藝術。所以這一天我覺得非常開心,也很愿意做這個事情。別人說你一天精力旺盛,我說不是精力旺盛,我說是迷戀舞臺,藝術一直是我的精神世界,你一想到藝術,就發狂,就什么都忘了。你走的一切都淡淡的,你談起藝術,你就非常激動,你說一句我說一句,哪怕是錯的,但是我想想,為什么他是對的,他是好的。比如說其他劇種我們都談得來,包括畫畫,我演的戲,《別洞觀景》這些,我有個同學專門畫畫的,他就想畫,把它畫出來,心中留下這么個東西,所以我真的覺得搞藝術太好。
李:那余老師,就您的從藝經歷來說,不僅您自己獲得了無數的獎項,而且您自己的學生也獲得了無數的獎項,那能不能談一談您培養學生的情況?
余:行嘛。從招生到學習都是我教的,第一個是鄧婕,她就是電視劇(演)王熙鳳這個,她從招生開始到學校,(我)整整教了她三年,一直到畢業,她能夠拍王熙鳳,就證明她有戲曲表演的這種能力,而且她跟我的關系也非常好,這是一個。然后是田蔓莎,田蔓莎可能就算多一點的,從她到校學習、排練排戲一直到她到上海戲劇學院,到現在當上海戲劇學院戲曲分院的副院長。而且她本身拿了梅花獎,拿了戲曲大獎,拿了榜首,四川十佳演員她拿了兩次,然后上海的白云獎,最可喜的是國際上的獎,她現在走向了國際市場,把中國的戲劇特別是川劇搞了很多的戲宣傳到了國外。然后就是崔光麗,她也得了梅花獎,她從17歲到我們學校,我給她上課,然后也教她,然后排練方方面面。而且這些學生都很自豪,說任何時候我們都是你的學生,我覺得這個滿欣慰的,其他的就不多說了,很多很多。
李:余老師真是桃李滿天下。剛才您談到就是您曾舉辦了川劇旦角表演的專場演出,能不能夠具體地談一談這方面的情況?
余:可以,就是剛才我說,其實我最開始辦這個川劇旦角表演專場,最開始也是沒想到,因為我經常跟舞蹈界的在一起,他們向川劇學習,我就跟他們上課。那年是在成都,首屆四川國際電視節,我們在一起上課,為電視節準備節目,舞蹈界有兩個老前輩,他們也是搞編導的,他說,你咋個不把你那些東西拿來演一下呀?拿來做一下呀?我說也是哈,剛才我說在四川搞舞蹈調研,我說我突然產生了個想法,我說對啊,我就把它集中體現一下,于是我就把我自己所掌握的旦角表演程式分了七種不同的道具,搞了七個節目,比如《折扇》、《水袖》、《蚊帚》、《指法》、《翎子》,然后還有個《長綾》,編了七個小品,然后還有個《打櫻桃》,這個是個表演性很強的節目,就是一個女娃娃到櫻桃園去摘櫻桃,但是她有五覺的訓練,味覺、觸覺、視覺、聽覺,她幾個覺是面部表演,然后看蜜蜂,怎么看蜜蜂,怎么鏟辮子,怎么嘗櫻桃,這是一個表演性極強的戲劇小品。所以當時我就覺得選擇了七個,因為我自己也要演,但是我不能全部演完,我也要給學生排,所以學生演點,我演點,所以說這場晚會叫自編自導自演。這個在排的當中,我都用的本校的學生,實際上現在都是很棒的演員,那么排的這個思路,我排了一臺既非完全程式也非完全小品的晚會,因為小品來不及,每個都要故事情節,每個都要抑揚頓挫,每個都要高潮,一時之間是來不及的,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但是我又不甘心的只有這樣一個程式表演,因為程式表演很枯燥,它就是稍微組合一點它就好看得多,給它一點靈魂,所以我就搞了這么一場既非程式又非完全小品的晚會在我們四川劇團演了后,在舞蹈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而且因為有了這場晚會后,電視臺都找我,因為他們都沒這樣做,而我這樣做了,一直到各種大小晚會,一直到中央電視臺晚會都是我在做,而且高興的是通過這場晚會,評了高級職稱,后來寫了本書《川劇旦角身韻》,這本書寫了評了一級(導演),當然這些都是一步一腳印走的,所以我要感謝川劇。
李:那當時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寫這本書的呢?
余:因為我搞了這么多的東西,還是我的學生田蔓莎,她說老師有這么好的東西,你不把它留下來,那到時候你不動了、動不得了咋辦?我們到現在還可以跟到你學,那以后怎么辦?我說寫書好困難哦,我說我教可以教,隨便教,但是寫書,提筆寫,每個字都要寫得很準確。但是我覺得我確實有這個必要,于是我在家里面關了三個月,自己提起筆來寫。好在它不是很大的理論,我跟人家老講這個事情,我不是先有理論后有實踐,我是先有實踐后有理論,而且實踐當中,我已經教會幾十個院團,已經教了幾十年了,而且在實踐當中證明它是成功了的東西,所以我寫起來信手拈來。我在寫的過程當中,只要我把每個動作術語搞準確,一口氣下來,所以三個月書就出來了,而且寫了過后,自己出了口氣,覺得自己做了件事情,起碼別人拍了些照片,起碼別人看到這個動作是這樣的,實際上就是工具書嘛。工具書我們沒有那么高的水平,工具書上很多專家的評論,比如說文化部的部長給我題了個詞,高占祥題的詞“一代棟梁,滿園桃李花”我裱起的,在屋里貼起,這個對我是個鼓勵。我說部長,你寫的,他說是這么的,他還說小余,你不能只看到川劇,你現在代表的是中國戲曲,你一定要做到中國戲曲這個份上,不要眼睛只看到你的川劇,我說高部長這個提得非常非常好,確實是不光是川劇,川劇有它的共性,有它的特點,有它的特殊性,那么這樣一來,我們互相地交流,互相地溝通,互相繼承,互相傳承,互相支撐,那也是非常好,所以后來就鼓起勇氣把這本書寫了下來。
李:那么您在退休過后,還在從事哪些有關川劇藝術的工作呢?
余:退休以后也就多了,退休后就更自由了,就不用按部就班地上課,今天不用跟這個年級哪個班上課,就不用,我就很自由。比如說單位請我半個月二十天假我就把這個事情做了,這種事恰恰很多,四川(成都市川劇院)這幾年我跟他們排了不少戲,排了不少短小精干的戲,有一個戲是張勇這個作家的,《一觸即發》是她寫的電視劇,而她寫給川劇的是《十二橋》也寫得非常好,她現在很有幾個戲都得了文華獎,戲劇、越劇寫了很多,但是當時她還沒有走上舞臺的時候,是我(鼓勵她),她的第一場戲,我就跟她說,我說張勇你一定要學會寫,我說喜歡幾個戲,你給我寫折子戲,《木蘭歸》、《晴雯撕扇》,這幾個戲你給我寫成折子戲,確實幾下就寫了,但是沒演,沒演怎么辦呀,沒演就需要演員,后來她就進入了成都市川劇院,調入成都市川劇院后,他們這個書記非常好,確實很好的一個領導,非常支持她,就給她搞個《張勇折子戲專場》,幾個戲全部是我的導演,我是第一個把她的戲推上了舞臺,所以她非常感謝我,當時還沒出名的時候,什么人都不知道她,長相很一般,我說她是劇作家,他們說為啥認不到呀,我說因為你不了解,后來我把她的戲,五個折子戲,那么這樣子演完了以后,單位上慢慢曉得她了,幾個戲全部是我導演,把演員全部排練了一番,所以這場晚會我還是比較滿意的。然后一個是排折子戲,一個是排大戲,搞晚會,更多的是到南方,上海越劇院、寧波越劇院、浙江越劇院,給這些劇院的學生培訓和排戲。
李:余老師的講述是充滿了激情,可以看出您對川劇事業的滿腔熱愛之情。那么現在有人說川劇要消亡,那么您對這個問題是怎么看的呀?
余:我是這樣看的,我覺得大環境,川劇的東西本來是很好的,我們本來保存的東西也是很好的,大環境造就了現在的年輕人。一個是藝術門類太多,電視、微信、微博哦,他一天可以坐在那里看很久,而且連續地看,沒有心到劇場聽你三個人幾個人緊到(注:一直)在那里哼腔。再加上我們的劇目,現在一般折子戲的質量沒有以前好。我們這個年輕人學習偷工減料,不勤奮學習達不到以前的標準,他沒有那種在情理劇中展現的跡象,沒有高超的技巧,他吸引不了人,這是一個。再加上人們的懶惰,你想現在的年輕人,他是給你坐起車子走起路到劇場看戲出來,還是在這個電腦上五花八門什么都有,他啥子都能看?所以(現實)對他們誘惑力太強,你要給他講,不光是年輕人,你看今天這些都是很成熟的人,而且都是當領導的,文化管理哦,電視管理,很成熟的人,通過這三天的講課,他說余老師像你這樣講,我們都想學川劇,他才明白。現在的年輕人哪個講呀?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文化大革命我20歲,我接觸了傳統戲,那個時候,20歲以下的,就是十五六歲的娃娃的媽媽們,他們就沒看到過傳統戲,文化大革命只看了現代戲,沒接觸過戲臺的魅力,沒接觸過舞臺的魅力,他們就看的現代戲,八年十個樣板戲,就記得到樣板戲,等他們成熟了,他們長大了,生孩子了,來給娃娃講解的時候,講什么呢?什么都沒有,她沒得辦法給他們講傳統知識,沒得辦法給她講舞臺經驗,說那年我看到個戲真好,她沒得這方面的經驗。我記得我進學校才12歲,我們的宣傳部長李亞群,給我們作報告,說我們學院學旦角的人一定要熟讀《紅樓夢》。那個時候我們就四部名著,我就想我唯一沒看的就是《三國演義》,因為我實在是看到打腦殼,但是水滸、紅樓、西游,我都看,特別是《紅樓夢》,雖然似懂非懂,但是至少了解它的人物,寶黛釵鳳。所以鄧婕為什么演《紅樓夢》,她早就熟讀《紅樓夢》。那么我反過來講,家長們沒有給他們娃娃傳遞傳統戲的知識,他們現在接觸的就是現代,再早點的,霹靂舞現代舞。而且現在電腦上什么都有,微博上什么都有。他拿什么時間去看你的川劇,什么時候去經歷舞臺,有些父母親稍微懂點的還說要學點我們的古典知識,學點我們的民族文化。有些爸爸說不要看,川劇有啥子好看,看都不要看,于是它就形成了斷層。沒有你仔仔細細研究過,沒有看過,沒有理解到過什么是川劇,所以現在學川劇的學生越來越少。再加上經濟的誘惑,比如我把娃娃送去學川劇,但是一了解川劇學校的老師、川劇的演員他們的工資才兩千多,他現在曉得的是五千多六千多,他說我娃娃一輩子這樣子呀?所以他從經濟方面來看,他也覺得學起沒得意思。所以這不光是我們個人的努力,比如我個人的努力,我把我的課教好,我把我的戲排好,我把學生弄好,但是需要黨和國家政府他們來支持,他們來扶持。比如現在越劇、昆曲、京劇,上海的免費,學生免費,除了伙食費還給你發零用錢,家長就想(讓孩子去學)。比如四川省川劇院,免費,不交學費,伙食費包了,畢業過后直接到川劇院,等于說他有工作了,那么你愿不愿意去學呀?家長就想我的娃娃考不起清華北大,當個川劇演員總可以吧,有些就想讓他學川劇,以后長大再跳槽出去做其他的也可以吧,于是就形成了這樣方方面面的思路,所以我今天上午舉例子大家都在笑。而且現在的獨生子女確實不能吃苦,而且個性很強,還說不得,我們那個時候老師一說,我們自己都想肯定自己哪點不對,我下決心今天還不到這個課,明天就要去還了,現在學生不一樣。我前年就遇到,這個學生老是做不到,就是排《金山戰歌》她演女兒,兒子那個甩大錘,女兒這個耍槍花,老學不到,我就很生氣,我說咋個大學畢業了你連這個都做不到,她說你不要我嘛,換人,如果是我,我當時就哭出來了,為啥子把我換掉,她還笑嘻了,然后跟別個說你來你來,我就換了個人,我想(她)肯定外頭去哭去了,結果出去,看到她在那里跳繩,說余老師,下課了呀,你不排了?我說現在的年輕人是這個樣子,你如何去教育她?好像現在除了錢,其他的東西換不轉來了。我說這是一種社會現象,這個社會現象要靠大家共同努力,要靠一些政策保護性的。你看昆曲這么古老的劇種,我看他們發的信息,幾十個學生,中國戲曲學院八個學生,為什么不停地宣傳,不停地給你講,四川宣傳了多少呀?那天萬老師給我說了,說你們成大的來采訪,我說好事情,大學老師,我很喜歡你們來做這件事情,說明你們對戲劇還有興趣,他們才愿意干。從這個事情來講,我覺得是我們的宣傳力度不夠,現在舞蹈很火,為啥子呀,因為他考級,考級過后就加分,加分他讀書就好,那么考級加一分,唱川劇加十分,你看他來不來,必須會川劇唱段,我舉個例子哈,就是政策性的。但是川劇確實需要保護,但是確實到川劇院來的也是因為不交學費,不交伙食費,而且有固定的工作,所以他們來了,他們以后直接分到川劇院。但是和我們當年比起來,幾千個人挑二三十個這樣壯觀的場面確實是沒得了,因為是方方面面對川劇的認識不夠,你的自身,你的目標,再加上現在家長也不想她吃苦,做啥子哦,摔倒了絆倒了,算了算了,隨便找個工作,反正爸爸媽媽養得起。但是我們那會兒不行,我的媽媽這么辛苦,我要讓她過好日子,我就不怕我吃苦,我就一定要去好生學習,我好生學習,我長大掙錢供媽。我媽媽現在已經走了,但是她在世的時候,我反復在向媽媽說的,我做得很好。我媽媽非常滿意,我經常給我媽媽講我怎么教學,怎么成功,怎么出國,我在搞些啥子,她一直跟我同歡同樂,而且她最高興的是我小時發誓,說我長大掙錢供媽。我小的時候腰痛得很,端飯都端不起,不像現在,那個時候死命地,兩個老師給我撇到,骨頭一響,但是還是忍到,但是第二天又去,因為我想我要把它練好。不像現在的娃娃,家長來了說我的娃娃不準撇哈,我的娃娃不準咋子哈,老師就不敢做,所以方方面面造成了現在的娃娃不刻苦,因為她沒有目標,反正她不曉得做什么,她只想反正我考不起清華北大,我在這里把幾年混滿了,就是一個中專生,像現在一個大學好考得很,反正拿個文憑,他們不在乎有沒有真實的本領,這點我是很痛心的,我教了很多大學生,心頭很難過,你像大學生嗎?你夠不夠大學生的資格?但是現在我們國家的學制,學制造就了一批鬼混的人,我在西南大學教過影視專業,一個娃兒上了一節課就再沒有來上課了,期末的時候他來說:“余老師,這個樣子,你給我打個60分就可以了。”我說:“你只上了60分可能嗎?我給你最多打40分,只要你來上課,雖然我筆下生花80分也可以,對你有什么意思?你為什么一學期不上課?”結果那同學給我講:“余老師你太認真了,我的同學百分之五十在那里鬼混。”我說咋個這個樣子呀,那這個大學咋子呀,你們花錢咋子呀?(他回答)耍噻。所以說其實我很痛心,我的心里面很痛,為什么大學這個樣子,我教了幾個大學,我覺得社會現象,社會現象方方面面的誘惑(太多)。當然好的很多,好的也很多,但是這樣的好像有點普遍,也許是兩頭小中間大。但是我還是要堅守,我還是要堅守一輩子,哪怕他完全不懂川劇,我就一點點給你講,我盡我的力量來給你說,起碼這個藝術是好的,這個民族文化的瑰寶是好的,你不理解是你的事情,很多我們也不懂的事情,你能懂多少懂多少,我能講多少講多少,總能說服一些人,你不干這個沒關系,起碼不要罵,你能欣賞那是好事情,你看現在好多文藝作品里面川劇元素多得很,真的是這個樣子。
李:余老師今天跟我們上了很精彩的一課,謝謝余老師接受我們的采訪。
I236.71
A
1004-342(2015)03-102-08
2014-11-16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項目批準號:12YJA760062)階段性成果之一。
李軾華(1970-),女,成都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萬 平(1954-),男,成都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