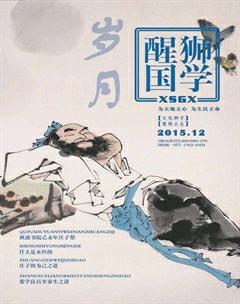拂袖名利場 縱浪大化中
南枝云山
我一直在腦中描畫莊子的形象:先是衣著,須有補丁;穿著芒鞋,須有繩結。是的,他是個標準的窮人。面容身形自然十分清瘦,因其家常便飯即為挨餓。最難的是眼睛,可裝載峰巒大海,亦可聚焦蟪蛄蝸角。那是一雙冷眼,冷對的是世人熱衷執著的種種;他有一副熱腸,熱對的是大化之中一個個大命題。他的眉眼之間總帶著一抹狡黠的笑,遠遠佇立荒天漫草間,看著塵世中人們的種種爭辯。你最好不要走近和他打招呼,因為他很可能一句話不說就背過身去,游向江湖迷蒙處了。
詩性鄉野
莊子終其一生也沒有涉足都市,僅有的做官履歷也止于漆園小吏,后來只好以打草鞋為生。他不是不能做官,而是把鄉野作為堅守的對象。他所棲居的世界是熱鬧的,那里有摶扶搖九萬里的大鵬,也有只在榆樹和草窠間隨便飛飛的蜩與學鳩,有怒氣沖沖擋車的螳螂,有自得其樂的斥鼴,有在河中喝得肚皮溜圓的鼴鼠,有快樂地在淺井中享受生活的青蛙……所以他是不寂寞的。只要在自然之中,他就有講不完的故事、看不完的風景。他一會兒在濮水上泛舟垂釣,一會兒倚在樹下緬懷舊事,一會兒又在土屋前閑坐;今天安坐家中洋洋灑灑地記錄著他的思想,明天跑到樹林里去和那些鳥獸蟲魚交談,后天就又在人們的傳說里飄然悠游去了。他太豐富,太浪漫,太抒情,太不拘一格,或者說,有時他太出格。他使萬物都具備了感動人心的詩性,他使鬼魂、神靈以及種種動物、植物甚至土偶桃梗都主動對我們說話。他在蔑視與摒棄這個世界時,又使這個世界如此的生機勃勃,意趣盎然,充滿詩性光輝!
當其他的那些“子”們四處推銷自己的治國方案之時,他卻把主動“提攜”他的人拒之千里。楚王派人請他輔佐之時,他正在濮水上垂釣,眼神專注地定格在水面之上閑逸的浮子,只幽幽地講了一個故事就委婉地拒絕了。飛黃騰達遠不及弋尾于涂的野田之龜。他故事的主角總是那些不起眼的生靈:夢中翩然飛來的蝴蝶、快活地相忘于江湖的游魚、涸轍之中的鮒魚,只有他最懂它們。惠施說:“子非魚,焉知魚之樂。”而莊子也在迷惑:到底是他變成了它們,還是它們變成了自己。在監河侯委婉地拒絕他借糧的請求之時,他就是那只鮒魚;在夢中迷蒙不清之時,他就是那只蝴蝶;當惠施去世他去祭奠之時,他多希望自己從未認識這位老朋友,多希望原本兩人就是相忘于江湖的兩尾游魚。
挨餓哲學
世人有時覺得他自討苦吃,是的,他雖不如孔孟煊赫與實惠,卻也其樂無窮。這種心境實是人類心靈的花朵,永遠在鄉村野外幽芳獨放,一塵不染,誘引著厭倦城市生活的人們。孔子面對食物尚有所講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莊子卻總在與饑餓抗爭。但比起肌體的饑餓,他更怕的是精神的不自由。《外篇·馬蹄》中談到沒有經過馴化的馬經伯樂“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最終剩下的馬雖能吃飽,卻變得言聽計從,動作整齊劃一。伯樂的訓練讓馬符合人類的要求了,可馬的本性就是為了合乎人的要求嗎?同理,人的本性就是為了迎合社會的某種需要嗎?
我們從混沌中被拋到這個塵世,如顆顆頑石從山上滾落河中,不斷沖刷,變得圓滑。我們把這個過程叫成長,把圓潤的性格叫成熟。很多人苦于此,卻不得已而為之。害怕面對的是生活質量的粗糙,但本性質拙的砍削就不可怕嗎?若說人類能生存發展皆因善假于物,但當為外物所累,以心為形役之時,異化的后果就真的是我們最初的期待嗎?為什么人們總感到不快樂,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缺乏寬闊的心胸與眼界。莊子為我們揭示了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莊子·秋水》)
從天地大道來看,萬物平等,皆為造化之寵兒。從物質層面看,人常會因為物質的貧乏和富有而相互輕賤。從世俗的眼光看,痛苦就更多了,因為在世俗中你無法把握自己,是被社會的標準牽著走。從莊子的立場看,人當以“道”的眼光看世界,把自己放在客觀而又自適的位置,方能培養出積極的生活心態。
《莊子·山木》對莊子的灑脫有過這樣的記載: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逢系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上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挨餓之事根本不能入先生之心,大道不行才是他心恒念之之事,這,才是最高的境界。
冷熱之辯
我們對莊子最熟悉的表情是冷眼,對象往往是權貴或重名利之人。面對天下蒼生,他卻懷著一副滾燙的熱腸。莊子的魅力在于他的激情與超脫,兩者竟能奇跡般熔鑄于一。論超脫,無人能像莊子般冷觀、藐視一切并嗤之以鼻。當是時,他站在世界對面打量著這個龐大豐富的對手,當他終于發現這個世界微不足道如草芥,虛張聲勢如小丑,他轉身就走,深愧來到這里,只有他憔悴的身影仍在人間伶仃而孤傲。
莊子是先秦諸子中唯一不對帝王說話而對我們這些平常人說話的人。當別人都在對著諸侯不厭其煩地說著如何“治人”的時候、莊子轉過身來,懇切而激動地告訴我們如何自救與解脫、如何在一片混亂中保持心靈的安寧與清凈,如何在丑惡世界中保持住內心的自尊自愛,不為時勢左右而無所適從,喪失本性,以及如何在“無逃乎天地之間”的險惡中“游刃有余”地養生,以盡天年。
他繼承了老子“小國寡民”的思想,為我們描繪過他心目中理想社會的圖景:“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此之時,則至治已。”生活豐衣足食、其樂融融,人際關系簡單而質樸,沒有現代的機械化,沒有等級制度,人們靠勤勞的雙手遵循自然之道生活,恬然自適。今天我們進入新的時代,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進程都在迅速進行,人際關系異常復雜,通訊更加快捷,多樣的生存觀、價值觀再次引起人們深思。然而當你停下腳步、反觀初心,你會發現莊先生那抹狡黠的笑就在你的心上滾燙地灼燒著。
編輯/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