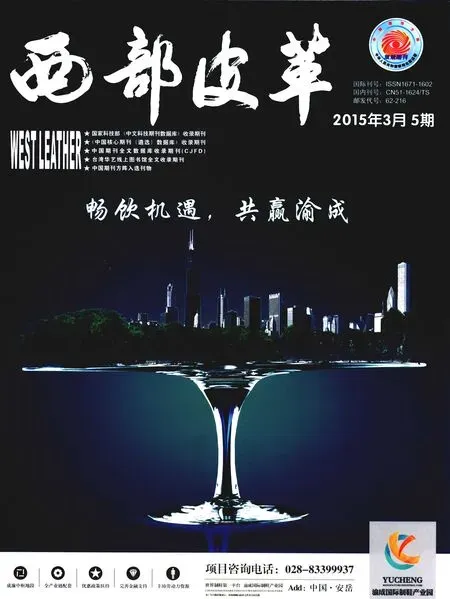古代鞋履改革花如錦(中)
文黑龍江/周祥
古代鞋履改革花如錦(中)
文黑龍江/周祥

【納底鞋納出千層底】
中國古代礦山采掘、選礦、冶煉,有文字記載始于戰國時管仲的《管子·海玉篇》,書中的“官山海”,就是實行鹽鐵官營。由此可知中國早在戰國時期,鐵與鹽已有專業經營管理,鐵制生活工具已很發達。在坊間及閨秀中,早已有鐵針在飛針走線,出現納底鞋已不足為怪。從考古出土文物亦可得到佐證,如廣西出土的兩漢銅質跪像,已見有鞋底“納有線紋”;從山西侯馬出土的周代武士跪像背面,明顯見有鞋底上有整齊的一行行線跡。秦墓出土的兵馬俑中,弓步手所穿方頭口履鞋底,都是統一的納底工藝所成。由此可見,納底布鞋在軍旅群中成為軍鞋,已不是簡單的鞋底制作工藝,而是一種棄舊圖新的制鞋工藝改革,這不啻為一種革命性的嬗變,它標志著納底鞋的結實耐磨耐用,因此由軍旅逐漸普及到民間,并以強大的實用性,廣泛在民間流播久經歷代而不衰。
納底鞋歷經數千年沿革到清代,并由北京內聯升創造出馳名天下的傳統產品“千層底”。清朝咸豐三年(1853)由趙廷以銳意創新的精神,在北京創辦前點后廠的內聯升鞋店,不僅專營朝廷命官的官靴制造,還以小圓口千層底緞子鞋和小圓口千層底禮服呢鞋而聞名遐邇,舊北京曾流傳著“頭戴馬聚源,身穿瑞蚨祥,腳蹬內聯升,腰纏四大恒”的民謠。當時,穿一件綢子長衫,腳上穿一雙內聯升的小圓口千層底緞鞋或小圓口千層底禮服呢鞋,為最時興、最貴雅的上乘人物。內聯升的千層底之所以頗受人們喜歡,因以用料質量好,制作精細而取信于人。有一套嚴格的操作規程,納底講究針眼細,麻繩粗,剎手緊,使層層白布結成整體不走形變樣。這樣的千層布底,
具有冬御寒、夏散熱等優點。辛亥革命前,“千層底”主要用作制靴,辛亥革命后,該店又將“千層底”縫绱尖口、圓口布鞋以及大舌棉鞋等延續至今。
千層底布鞋為中國布鞋最有代表性的鞋種。鞋底用料有兩種,一種講究的是以新布,一種是以舊布三五層打成袼褙,用鞋底樣剪好,用白布包邊,根據厚薄需要,將包好的底片疊好,有專用夾板工具的用夾板夾好;一般民間沒有夾板,而是用漿糊將底片粘好,晾干后就可以納鞋底了,先用錐子錐孔,再用針引麻繩納實,納后鞋底正面針腳為整齊的橫豎成行,背面橫行則為八字形的針腳。千層底正面用料一般均為白布,所以在納鞋底時為了不因手出汗污染,則用厚布或毛巾將鞋底包著一針一針地納。年輕的姑娘媳婦往往三五成群結伴,邊納鞋底邊聊天說笑或唱歌。在徐州地區有首做軍鞋的民歌:“小燈頭,亮又亮,妹在燈下做鞋忙。鋼針尖,線繩長,納了一行又一行。不納龍,不繡鳳,妹盼郎哥立戰功。雙雙軍鞋送前線。俺和郎哥情意濃。”在山西堯都民間曾流傳著一首民歌:“煤油燈,起燈花,新媳婦用針拔了它。燈底下,把鞋納,千針萬線為了他。他在山上搞綠化,連著三月沒回家。山高坡陡不好走,不是尖石是碴碴。倘若鞋爛碰傷腳,叫人心疼說句啥?”(《中國鞋履文化辭典》)在戰爭年代,我軍被服廠生產條件有限,只能滿足“被”與“服”,而大量的軍鞋基本上靠后方廣大婦女手工制作。前首民歌是未婚姑娘為參軍作戰情郎做軍鞋,納鞋幫納鞋底時所寄予的深情愛意;后著民歌則是剛結婚的新媳婦,為上山搞綠化的丈夫做鞋時,抒發心中對丈夫的疼愛關懷。婦女在飛針走線納鞋底中,所蘊含的情深深意濃濃,盡在不言中。
余對千層底布鞋太熟悉了,童年時,親眼所見母親用舊布打袼褙,白天忙家務,常常在晚間夜伴孤燈,千針萬線做一家人所穿的納底鞋,我就是穿著母親做的千層底長大的。走向社會我雖告別了母親所做的納底鞋,而娶妻生子后,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妻仍然繼承祖傳做鞋工藝,為一個個呀呀蹣跚走路的孩子們做納底鞋,直到他們學業有成工作后。在國人眼中四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有誰沒穿過一針一線納出來的千層底布鞋呢?如今,昔時曾浪漫了中華大地的千層底,早已成了明日黃花。毋容諱言,千層底先進的制鞋工藝是從古代制鞋編織工藝演變而來,這種劃時代制鞋工藝的改革,是文明典雅鞋履發展的推動力,將永垂鞋文化史冊而不朽。
【丑陋國粹血淚弓鞋】
南唐后主李煜,雖是一個不通政治、不善治國安邦的皇帝,但卻是一位相貌不凡、多才多藝的風流雅士,不僅詩詞文章出眾,且書法繪畫造詣亦頗深。在面對后周強勁的發展形勢,李煜所主政的南唐上下只是坐等聽從命運安排,已無回天之力挽救敗局。這位才華橫溢風流倜儻的皇帝,雖是一個失敗的君主,但卻是一個成功的詞人,一生中留下了許多不朽的詞作,“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千古傳誦的佳作,就是出自這位可悲的皇帝筆下。不僅如此,李煜還很有艷福,除了花容月貌、氣質高雅的大周小周姐妹,先后為他的嬌妻外,他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妃子,叫窅娘。窅娘雖出身于家境貧寒的采蓮女,但卻輕佻艷麗,能歌善舞,尤善跳金蓮舞。十六
歲時被選入宮中,據說她是一名混血兒,眼睛與中原人不太一樣,雙目深凹,所以李煜賜名“窅娘”。為了欣賞窅娘優美的舞姿取樂,李煜還專為她建了一座六尺高的金蓮舞臺。為了滿足李煜享樂,窅娘跳舞時以帛纏足,使其纖小彎曲如新月,外著素襪,在金制蓮花上翩翩起舞,有凌云之態,飄飄然若仙子凌波,十分動人。李煜看了喜不自禁。窅娘于是常常以白綾纏足,以保舞姿優美,因此很受李煜寵愛。纏足女人之腳因此而得名為“金蓮”。之后,纏足之風流入民間,宮外女子皆效仿起來。從宋開始,名媛閨秀皆以女子纏足為美、為貴、為嬌、為雅,這種陋習漸漸發展到變態的地步。

由于女子纏足腳變形為尖、瘦、小,于是便產生了纏足女子所穿的“弓鞋”。弓鞋其實就是有如春秋時,為被刖刑人定制所穿的“踴”一樣,是一種殘疾人穿的特型之鞋。一些具有變態審美觀的人,窮盡智商贊美變形的小腳與所穿的弓鞋,說纏足形似蓮花、蓮瓣,美其名曰“金蓮”,并愛屋及烏地連所穿的弓鞋也稱之為“金蓮”。所以,古時金蓮泛指女子纏足的小腳或所穿的弓鞋,并以三寸金蓮的小腳與弓鞋為最美,“看腳不看臉”已成為那個時代選妻待聘標準。文人騷客通過詩詞文章更是把三寸金蓮美化到了極致,其泛濫博文屢見不鮮:“凌波步小弓三寸”(徐用理);“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云”(杜牧);“裙邊遮定鴛鴦小,只有金蓮步步香”(李元膺);“翠裙鴛繡金蓮小,紅袖彎銷玉筍長”(王實甫);“捧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底繡羅鞋”(毛熙震);“簾前三寸弓鞋露,知是腰腰小姐來”(朱有敦)。不僅古代文人騷客以贊美歌頌小腳弓鞋為雅,就連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學、曾任上海黃浦浚治局督辦的辜鴻銘,酷愛三寸金蓮幾近成癖,對其妻淑姑那雙小腳愛得近乎癡迷。這個有名的辜瘋子曾對其妻小腳妙論為“小腳女士,神秘美妙,講究的是瘦、小、尖、彎、委、軟、正七字訣。婦人肉香,腳為一也,前代纏足,實非虛致。”又說:“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臭豆腐、臭雞蛋之風味,差可比擬。”據說,他寫文章時,淑姑一定要在身邊,他一手捏筆,一手捏穿繡睡鞋的小腳,鼻子嗅那味,便文思泉涌,下筆有神。他還有詩贊美他老婆那一雙“三寸金蓮”:“春云重裹避金燈,自縛如蠶感不勝。只為瓊鉤郎喜歡,幾番縑約小于菱。”
那一雙雙小腳的女子,哪個不是從五六歲開始纏足,使雙足腳趾變形,皮肉潰爛疼痛難忍,“號天叫地娘不聞,宵宵痛楚五更哭”。那雙雙用血淚繡制精美絢爛錦錦的弓鞋,是一次中國獨有的鞋飾變態改革。經千年近似古代刖刑所著踴,對女子的摧殘早已被時代拋棄。弓鞋,這朵鞋履“改革”的苦菜花,終以丑陋國粹枯朽在鞋文化的史冊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