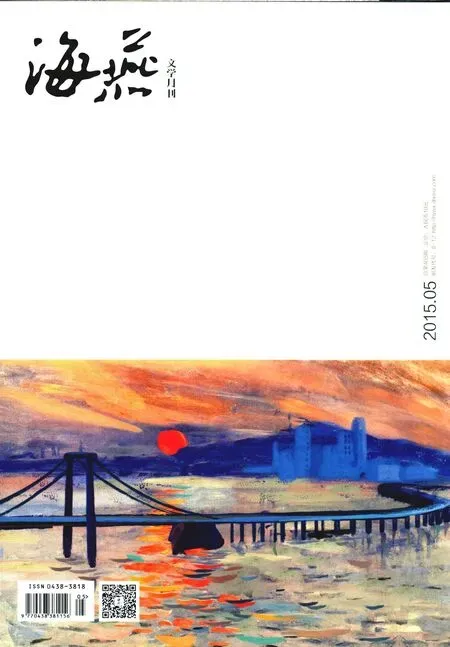潑墨牡丹
□鄭德庫
故事的開始很平常,抑或說是很正常,是絳拉著丹一起去看他。
絳是丹的同學,又同為讀師范時被戲稱為“虹、彤、絳、丹”四點紅中的兩點,進而發展成無話不說的閨密。絳又是他曾經的同事,當年兩人的心里也曾碰撞出火花,但被世俗束著,最終沒有燃燒。而丹和他雖為師院的上下級同學,又曾同在這座城市的教育系統工作,卻不曾謀面,三人說來就是這樣的一個三角。
絳拉著丹去看他,是送書,也為取書。送書是送師院隋先生的遺著,是丹和絳幫著師母編的,代序卻是他的一篇懷念性散文。取書是取他新出的兩本文集,一本散文,一本小說,其中有一篇是寫絳的,丹看過,感覺還不錯。想討兩本看看,所以就跟絳來了。錢鐘書先生的《圍城》中講,借書是戀愛的開始。憑良心,當時的三位可誰也沒想到這一點。
他在一座大廈的十八層辦公。人高高在上,門也難進,保安守著,登記,坐電梯,上去還有電子門。按了好久才進去,他掃了兩人一眼,讓座,目光就基本聚在絳的臉上。“也許在尋找當年的影子和情愫吧。”丹感到自己被冷落,就找茬,“你這樓層真吉利,十八層呀!”
“是十八層,但卻是正海拔。”他的眼皮翻了翻,“也許是鎖住普羅米修斯的巖壁吧!”
丹的心底滾過一陣青春的熱浪:“有點自大了。你為誰盜過火?”
兩人的目光就碰到了一起。
絳見自己搶了鏡頭,就忙給丹廣而告之:“人家畫的牡丹,五千元一幅,每年都能在香港和東南亞賣好幾幅呢!”
“哦”,他抬頭,閉眼,似乎在自言自語,“已綰征西節,新吹幕府笳。如何貪富貴,又畫牡丹花?”
心氣高傲的丹恨不得上前咬他一口。
丹回到自己索居的小家,連外罩也沒脫,就迫不及待地從兜子里掏他的那兩本書。猛然間聯想到影視中男女偷情的場景,一對對猴急猴急的,就莫名地感到自己好笑,兩本書,又不是他,就是他也不值……
想歸想,丹還是很快打開書,翻開扉頁,是他的一幅照片,跟剛才在大廈里見到的形象差不多,老氣橫秋中透出一種傲。丹就生氣,用手指點著照片中他的額頭,心里恨恨的,“你就不能放下你的臭架子啊!”再看,就為他惋惜,“這照片的審美太差,要是我給照嘛!”然而很快,她的思緒就被吸引到書里去了。
草草地把兩本書瀏覽一遍,丹就感到一種難得的親切。書中的那情那景,就像斗室閑聊,星下漫步,一陣陣引起了丹的獨自頷首。丹甚至聯想到自己下鄉的山村、盤桓過的古鎮。那古鎮他也去過,兩人的生命軌跡中就有重合的可能。而在城里,兩人是師院的上下屆同學,雖然一個前腳畢業一個才后腳入學,沒緣沒分,但畢竟是一個流水線上下來的產品,有一種天然的親近。又曾經同在教育口工作,集中批卷,開會,見面的機率更多……漫無邊際地想,就有點想入非非了。
第二遍細讀,丹就開始做卡片,并在書上勾勾畫畫。兩天讀完,一篇書評就成形了。丹回到師院工作后,教的主課就是文學理論,撰寫論文是她的長項,自己用的,替別人寫的,小圈子里很搶手,自己也曾很自豪的。這次拿出點看家本領,殺殺他的傲氣。
丹撥通了他的電話,他一下就聽出是她,讓她心里很熨帖:“喂,我寫了篇書評,評價評價你的蛋,看你這只雞有什么反應。”
“好!”
丹就概略地介紹了書評的內容。
他長長地聽了一陣,還是一個字:“好!”
丹就發火了,還帶著點撒嬌:“人家費這么大的勁,你就迸一個字?”
“好!你把稿發過來。”
丹心里這個氣呀!
丹發完電子郵件,又翻開那書,在照片上他的額頭狠狠地點了好幾下。
三個月后,書評在一家雜志上發表。
他請丹吃飯,捎帶一群雜七雜八的朋友,甚至還有一位專門下掛網的打魚人,出過一本古體詩集的。但沒邀請絳,丹就隱隱地覺得他是注意起自己了。
酒席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風格,酒話也是雅俗兼具,雅的,一下吹上了天;俗的,就讓人臉紅心跳的。他坐在丹的旁邊,又要了兩味女士菜,一盤豬手,一盤拔絲山藥,時不時地給她夾菜,大大咧咧的外表下透出一份關切。
酒席上的話題大多圍繞著文學創作展開。俗話講,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這些人講的也真夠大,仿佛諾貝爾文學獎也沒什么了不起。丹默默聽著,細品,偏激之下,有的似乎也有些道理,讓她這個學院派感到新鮮。談著喝著,話就讓他引到繪畫上,“這一位女士,人家畫的牡丹,在香港和東南亞每幅能賣五千元人民幣呢!”
一桌人就把目光聚焦到丹的臉上。
丹就矜持起來:“以前每年能賣個三幅兩幅的,這幾年世界經濟狀況下滑,不好賣。再說,工筆畫傷眼睛,就改寫意了。”
他就接話打趣:“我聽說,有一位專畫壽桃的畫家,畫兒很搶手。哪知他的畫兒都是沒人時脫了褲子,屁股上涂了油彩,一坐一張,一點兒不傷眼睛。而且這壽桃還是綠色產品,上的是農家肥。”
一陣笑聲過后,有人惋惜,有人感嘆。一位年長些的就順著說:“寫意好,西方油畫靠情緒,東方水墨講空靈,這一點上還是東方畫勝一籌……”

說著說著,幾人的目光就集中到他的臉上,讓他講。大家心里都明白,丹是他帶來的,請客也是借人家的光,這年月,你知兩人是什么關系,也許是情人呢!他也不推辭,一本正經的,還清了清嗓,講:“我看最好是回家多吃,早睡,然后兩個月賣一次血,積德,還給社會作貢獻,收入也比賣畫強,省得讓可恨的老外喝咱中國人的血。”
一番話,惹得酒桌上一片笑聲。
說到底,女人是感性的動物。請客的第二天,丹就開始渴望他的電話。從早到晚,等了一天卻沒等到,等得丹心里五味雜陳,什么滋味都有。先是,她在心里為他開脫,剛見過面就又打電話,說什么呀?反過來又想,他也該打,問問人家的感受呀!也許是他忙,忘了。再想,忙也有功夫打個電話呀?臭男人,就是能裝……
第三天,還是沒有他的電話。
第四天,也沒有。
到了第十天,還是沒有。
在丹的世界里,他就像蒸發了一般。可丹還是等待,并且自己騙自己地為他沒打電話尋找各種理由。漸漸地,等待就成了她寂寞中一種常態,一種活著的方式。這一段的時間對丹來說,是那么漫長,是煎熬,也是醞釀。
三個多月后,他來電話了,一下讓幾近失望的丹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就是一句,“這一段,你哪去了?”
“呵,我還有人關心了。簡直就是老婆詰問丈夫的口氣。”
“你說什么?”丹心里一驚,沒想到開口就讓人窺出了心態,就下意識地反問。
“是老婆詰問丈夫的口氣——”
二人就開始斗嘴,斗來斗去,到底是他做了忍讓,丹占了上風。他就開始說:“前一段市里征文,慶祝正式創辦理工大學。我得了個獎。明天下午兩點在大學禮堂以晚會的形式頒獎,請你去看看。”
“對不起了,明天下午我還有事,去不了。”丹不冷不熱的,其實她是心里有氣,恨他這么長時間不來電話。
“怎么,你不是挺愛八卦的嗎?去了,看看蛋,也看看雞。”說著,電話里就傳來他模仿的“咯答——咯咯答——”叫聲。丹笑了:“真的有事,去不了。”說著就把電話摁了。
哪知第二天,丹改變主意,又想去了。女人的心,連自己都難以把握。她就開始精心地打扮,穿上那套上課時愛穿的類似職業裝的套裝,又用溫熱的濕手巾敷在臉上,以熨平眼角細細的皺紋,再對著鏡子輕輕地描眉。
鏡子里就呈現出一張精致的臉,尖挺的鼻子,小巧的嘴,秋水般清澈的眼睛,白皙的皮膚不知何時泛出了紅暈。丹端詳了一番,嘆了口氣,“鬼迷心竅,都讓他給鬧的。”
好容易挨到差十分兩點,丹才下樓,打車去大學,她要偷偷地看看他的表現。等她進禮堂時,頒獎會已經開始了,市里什么名字的老年合唱團正唱著什么抒情的曲子。這合唱團,藝術水準不低,前一段聽說在維也納金色大廳唱過,后來又聽說是個笑話,拿錢就能進去唱的。想到這,丹就會心的一笑,老師似的坐到排列整齊的大學生們旁邊。再一想,自己本來就是大學的教師嘛,做學生旁邊也算是本色,又笑了。她就覺得今天天氣真好,心情也好。
透過大學生們坐著的縫隙,丹就開始尋找他。得獎的一般都坐在前幾排,她的目光就在那范圍里掃視,果然在第二排的位置看到了他。盯了一會兒,丹就發現今天的他跟平時不一樣,矜持,旁邊的人跟他說著什么,他只是微笑著聽,挺能裝的。
丹就看節目單,才知道他得了一等獎,兩個一等獎中的一個,又是散文體裁中的唯一。“怪不得這么裝呢?”她想。
等一位大學生朗誦他征文的一部分時,丹才被深深感動了。朗誦的大學生聲情并茂,而他的文章寫的就是當年讀師范的事和情,一下就引起丹的共鳴。這一刻,丹才覺得讀懂了他,而且也讀懂了自己。
等他上臺領獎時,丹用手機給照了張相,就一個人提前離開了。站在空曠的廣場上,丹就把照片發了過去。
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回個信息:“唔,你來了?”顯然出他意外。丹就有些竊喜,招手打車走了。“哼,讓你找吧!”
回家后,丹就跟寫意牡丹叫上了勁,不為別的,就沖他得獎的矜持,沖他那天飯桌上賣畫不如賣血的議論,就得用畫堵他的嘴。然而繪畫不是斗氣,得講究藝術規律,更得講究創作心態。丹就這樣帶著女人的小脾氣,賭氣似的,一張又一張地畫。
一張畫完,直起腰端詳,畫面上黑乎乎的一堆,實,缺少了氣韻。
又一張畫完,再端詳,布局有了,卻像骨架似的吊著,又沒了血肉。
再畫,還是不滿意……
丹到底挺不住了,就給他打電話。談畫,談創作上的苦悶。他就笑:“你整天沉浸在豐姿綽約的牡丹里,成了畫中人,品到了創作的真味兒,知足吧。畫的成功與否,那是天意,不能強求。”
丹就繼續述說起自己的人生的坎坷,聲音幽幽的,像受氣的小妹對大哥的述說。
他就把話截住,說:“知道,連你的家庭變故我都知道。”
丹一下敏感起來:“呵,背后調查我,用得著嗎?”
他猛然知道說漏了嘴,就將錯就錯,大咧咧地套近乎:“你要知道,我可是單身。做什么事,總得有風險評估吧!”
丹就在電話里風風雨雨的,喊了好一氣。等平和下來,他才演小品似的:“前些天碰到了你的同事小吳,她是我的同學,順嘴的一說。我氣你呢!”
丹和他的電話就多了起來。丹談繪畫,他談文學,談著談著,繪畫和文學就攪到了一起。時間長了,丹有些明白了,他想讓她再給寫點文學評論,要名呢!可不明說,繞套,想像上回似的巧使用人。丹就裝懵懂,偏偏不提這茬,到底把他的傲勁打下去了。
他開始死皮賴臉地求丹。丹笑了:“再寫一篇,當你的御用寫手,行啊!先付五千元稿費,省得我去賣血。”
“哪天我去你那看看畫,幫你參謀參謀,就算換工了。”
丹就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自豪地說:“咱小窠里還養了兩盆花,一盆名貴的蘭花,一盆碧綠的綠蘿。”
他就逗:“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小時看連環畫時,看到這狐仙洞的對聯。給你貼門上吧。”
“煩人,這比喻特俗。”
“那就叫蜂窠,招蜂引蝶的窠。”
丹就開始等待他這只蜂的到來。
等了很長時間,他也沒到丹的蜂窠,而且連電話也沒有了。丹就把心思用到畫上,等待中竟有了一種充實的感覺。
天氣逐漸轉暖,戶外柵欄邊的麥草都秀出了穗,熏風一吹,點頭招搖著。丹每天都早起,行為藝術似的給自己做好早點,吃完,打扮一番,就下樓,沐浴那朝陽,觀看花草上的露珠,呼吸清新的空氣。漸漸的,她蒼白的臉色紅潤起來。
上樓回到自己的空間,丹就開始畫那寫意牡丹,一張又一張,時間一長,幾百元的宣紙都揮霍了,還沒畫出自己心里的牡丹。其實丹此時的心里沒有牡丹,而是長了草,招招搖搖的草中,會無端地飄出他那張傲氣的臉……丹就感到牙癢癢,想咬人。
突然之間,他就來了,仿佛鬼魅一般飄來,丹就覺得眼前的一切都亦真亦幻了。
“去山里的朋友家,摘了些杏,純綠色的,給你嘗嘗。”
“上我這里,不怕吃了你呀!”丹一邊急急地歸攏雜七雜八的物品,一邊盯著他應酬,不知怎么,連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他就有意回避,開始看畫。丹指點著,解釋著。他卻一言不發,只是默默地看,時而搖頭,時而點頭……丹急了,一下掰過他的肩膀,直視著他:“你說話呀!”
“大象無形,要超脫,褪去形式的殼,去表現牡丹火一樣的生命律動。而你這畫,太沉重了,沒到自由潑灑的境界。”
丹的腦海里的靈感電光石火地一閃,一幅潑墨牡丹就活靈活現了。“怎不早說?”丹邊嗔邊用拳頭捶他,張開的嘴也向他逼來。他躲閃。丹的牙齒就親密接觸了他的肩膀,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哪知這一咬,就一下咬破了兩人的世俗防線。他開始反擊,一張嘴就包含了丹的嘴,又緊緊頂住了丹的鼻孔。丹感到呼吸不暢,繼而是一種缺氧狀態下的亢奮,兩人就瘋狂地扭到一起。
從客廳到臥室,兩人身上的衣物就一件件飄落,仿佛天女散花般……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
風暴過后,兩人像兩條涸澤之魚,大汗淋漓,兀自氣喘。忽然,丹仿佛美女出浴,身披猩紅的睡裙,長長的裙帶拖在地上,人像一團燃燒的火焰,飄到畫案前,那潤飽墨汁的畫筆就開始在宣紙上移動,點,染,勾,皴,時間不長,一幅活潑潑的潑墨牡丹就呈現在兩人的面前。
這幅潑墨牡丹得到美術界權威人士的好評。
一年后,丹和他組成了新家庭。新房里掛著那一幅淋漓的潑墨牡丹圖。
責任編輯 孫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