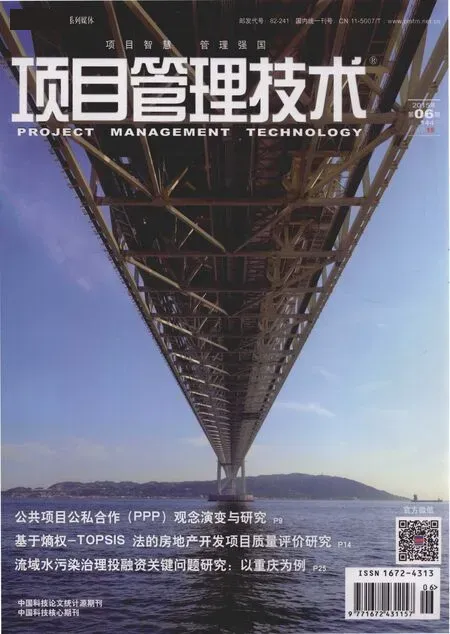流域水污染治理投融資關鍵問題研究:以重慶為例*
覃丹丹 石世英 葉曉甦
(重慶大學建設管理與房地產學院,重慶 400045)
0 引言
現階段,我國水污染事故每年都發生1700起以上,水庫水源地水質有11%不達標,地下水水源地水質約60%不達標,2.8 億居民使用不安全飲用水,嚴重的水污染態勢對水資源、水環境和水安全造成了很大壓力。為此,李克強總理提出了“出重拳強化污染防治”和“向水污染宣戰”,新的治理需求中蘊藏著新機遇與新挑戰。水污染是一種全方位的立體式污染,涵蓋固定排放的點源污染(如工業廢水、生活污水)和分散排放的面源污染(如農藥污染、養殖業污染),需要政府與市場共同努力。單一的治理模式不能適應復雜的流域水環境問題,如英國泰晤士河、法國塞納河和歐洲萊茵河等河流的治理經驗或教訓也體現了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系統性、復雜性、持續性和高投入性[1]。為了突破水污染困境,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很多行動,水環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如水生態文明建設、排污權交易、“碧水行動”等水污染治理專項以及環保部牽頭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2 萬億元投資計劃”。同時,學術界也從水污染治理投融資模式、行政管理和治理結構等方面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實際運用中仍存在諸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明確[2-4]、水污染治理投融資能力不足、效率與效益低[6-7]等。
水環境的公共性決定了水污染治理的公共產品屬性,水污染治理服務的供給集聚了政府、社會和市場要素,有限的政府投資不能滿足整個社會的水污染治理服務需求,而基于市場準入條件和水污染治理公共性,具有水務建設能力和充足資本的私營經濟或社會資本仍被忽略或限制[8-9],這也不符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同時,不同類型的水污染也需要特殊的治理結構厘清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更需要具有針對性的投融資機制解決水污染的治理效率問題。因此,創新水污染治理投融資機制和融資方式,促進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是緩解水資源壓力的基礎。而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投融資、破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及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是當前解決水環境問題的關鍵。
1 研究材料
重慶是我國西部地區重要的金融、交通、資源中心城市,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環境可持續建設,豐富的水資源環境造就了重慶特色的水污染治理模式。為了轉變現行水污染治理方式,重慶政府主導推行環境保護“四清四治”專項行動、碧水行動和完善環保治理體系等,通過對重慶流域水污染治理體制、政策與機制現狀特征分析的剖析,提出制約水污染市場治理融資機制改革因素、水污染治理經濟運行規律和市場投融資規律,探索重慶污水治理投融資政策制約成因,為重慶及其他城市流域水污染治理提供理論參考。
1.1 重慶水污染治理現狀
重慶地處長江上游,地表水資源豐富,河流縱橫,渠系密布。根據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13年重慶市廢水排放總量14.25 億t,比上年增長8.78%,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3.35 億t (96.5%的處理污水直接排入環境,剩余的進入污水處理廠),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10.89 億t (實際處理量為7.61 億t,再利用率為0)。另外,2013 年重慶環境質量年報顯示,重慶市“三江” (長江、嘉陵江和烏江)和74 條次級河流的154 個地面水監測斷面中Ⅰ類、Ⅱ類、Ⅲ類、Ⅳ類、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為0.7%、34.4%、40.9%、14.3%、4.5%和5.2%,其中Ⅰ~Ⅲ類水質的斷面比例為76%,比2012 年下降8.5%。重慶市次級河流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部分監測斷面水質有所改善。
但是,鑒于現行管理體制,治理主體仍為各級政府或其所屬公共部門,流域、區域水污染治理過程中存在條塊分割和分散管理等弊端,污染物的排放未能得到根本遏制,部分流域污染情況依然十分嚴重。2009 年合川區生龍水庫因承包戶大量飼養家畜,導致0.35km2水域面積嚴重污染,水質為劣Ⅴ類,兩年內不能飲用。2010 年重慶市第三屆三次環保會議上提出,包括匯入長江的五布河、御臨河、箭灘河等14 條河流水質長期處于劣Ⅴ類,黑臭問題突出,并有繼續惡化趨勢。2013年5 月永川區紅旗河因商業、娛樂、餐飲等污水直排,加之治理規劃建設、多頭管理、管理經費不足等原因,治理情況不容樂觀。此外,三峽工程建成蓄水后,由于主城區庫區回水末端,水流速度緩慢,自凈能力較差,污水倒入次級河流,導致次級河流水質變差,污染不斷加重。
綜上,重慶次級河流豐富,水系構成復雜,涉及區域多,為重慶工業、農業及人民生活提供了充沛的水資源。但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水資源,在過去大力發展經濟的進程中,忽視了水資源與水環境的保護,導致廢棄物的排放超過了水資源與水環境的承載力。尤其是次級河流及湖泊污染治理存在缺乏資金投入、投融資渠道狹窄、管理功能單一等問題,導致重慶的水污染治理形勢十分嚴峻。
1.2 重慶水污染治理投融資現狀
中央財政撥款、重慶市及各級地方財政撥款、污染企業治污資金是重慶水污染治理資金的主要來源。2007 年至今,國有控股的重慶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重慶市污水治理的主力軍。2011 年重慶市被列入“排污費權”交易試點城市,排污權交易收入上繳財政,在提供水污染治理服務的同時帶動了社會資本的投入。
近年來,重慶市加大水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資力度。2012 年重慶市重點流域水污染治理項目投資計劃為17.027 億元,其中中央預算內投資計劃為11.336 億元。在流域、區域治理方面,2010 年重慶市對主城區14 條次級河流全面實施污染治理,此水環境綜合治理工程將歷時兩年時間、污染治理總投資達32.4 億元,主要由政府財政投入。以2014 年4 月的水質監測數據為例,重慶市61 個城區集中式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標率為95.1%,同比下降3.2%,環比下降3.3%。受四川入境斷面總磷超標影響,下游的江津區鯉魚石、和尚山和南岸區黃桷渡3 個水源地總磷超標。長江重慶段水質監測并非重慶市環保局一家主管,與重慶市環保局按月公布水質數據的做法一樣,長江水資源管理局公布的2014 年1 月、2月和3 月的數據顯示,重慶市飲用水源區達標率更低,分別為55.6%、88.9% 和66.7%。長江水資源管理局評價的飲用水源區共18 個,河長223km,與重慶市環保局選取的地點及數量均不完全相同。長江與嘉陵江不僅是重慶市的主要飲用水源,同時也是接納城市污水、工業廢水的唯一水體,這一基礎性的現狀決定了重慶水源地保護面臨的復雜局面。順長江干流和嘉陵江自上而下,隨處可見兩岸的生活污水及工廠廢水排入江中,與江水混為一體,規模較大的如旅游景點磁器口老街旁的排污水渠,而自來水水廠的14 個取水口則順江排開。重慶水務及重慶水利投資公司每月公布自來水出廠、管網的水質,其出廠水質合格率、管網水質合格率、綜合合格率均長期高于國家規定的95%。
然而,目前重慶市范圍的水廠絕大多數采用常規處理技術,并且不具備先進的專利及非專利技術。雖然加大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工業及家畜飼養業、牧業、養殖業的發展,使原本治理完成的流域再次被污染,目前治理設施老化,運營成本高,治理效率低,但是由于管理體制原因,污染物的排放未得到根本遏制,部分流域污染情況依然十分嚴重。縣區治理的治理機制落后,融資體制缺乏活力,導致次級河流治理資金缺乏,融資容量少、融資模式創新不足等問題出現。
總之,由于原融資平臺利益等原因,對次級流域、區域湖泊投資不足。在地方行政分割體制背景下,多個部門共同享有流域水資源的管理權,職能交叉導致以流域為載體的各個主體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難以實現集體行動,出現了“搭便車”行為。此外,越往流域下游水污染越嚴重,治理成本呈現遞增趨勢。地方行政分割程度越高,流域水污染治理失效可能性越大,治理成本越大。
2 關鍵問題分析
基于對重慶市水污染治理及其投融資現狀分析和實證調研,本文從治理結構、投融資市場、融資主體、融資方式等角度分析重慶市水污染治理投融資機制存在的問題。
2.1 治理結構單一與融資主體創新不足
目前重慶市水污染治理主體是重慶市環保局、重慶市水利局以及重慶市市政管理委員會,同時區縣政府也設置了相應的管理結構,而水污染治理主體是重慶市政府所屬的國有企業(重慶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重慶市水利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其關鍵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政府治理結構屬性是行政管理。政府撥款是水污染治理的主要融資渠道,計劃經濟體制仍在水污染治理項目的投入機制中占主導地位[10],也演化出行政式水污染投融資治理結構。正如黃奇帆市長(2013)提到的,環境容量作為一種資源,需要政府的行政措施,但更需要市場來配置。應從全流域的角度出發,樹立可持續河流治理理念,建立綜合管理新模式[11]。其二,水污染治理融資機制的核心是創新融資主體。水污染治理的經濟性質決定其準公共產品屬性,僅運用“市場的手”或“政府的手”配置資源都存在各自優勢及明顯缺陷,目前的根本問題仍是政府治理結構處于政府融資主體替代市場融資主體。只有“兩只手”共同著力,才能優化融資主體。借鑒美國對Rouge 河流流域治理經驗,主要運用政府聯合企業的融資主體模式和市場參與的運行機制[12],通過優化融資主體實現Rouge 河流流域從融資、建設到治理和經濟發展的全過程管理。為此,創建新型的多主體、多功能的融資治理結構是實現水污染融資機制創新的前提。
2.2 市場融資效能與效率較低
水污染治理與融資機制是經濟發展系統中的兩個環節,要通過市場配置資源促進流域或區域經濟發展。首先,資源配置的關鍵問題是觀念革新。我國執行“誰污染,誰治理”管理原則,觀念上形成了各區域政府博弈、政策博弈、利益博弈,從而影響了市場融資和并造成污染治理“壁壘”[13]。其次,水資源和水污染治理準公共產品的排他性和競爭性。水資源利用的最大問題就是過度開發[14],如2011 年8 月云南鉻污染四省河水流域的重大水污染事件,在1998 年就已開始直排污染物。典型案例證明,傳統治理機制和融資機制都存在著利益博弈至上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按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準則,創新“雙手”配置資源的水污染融資機制,進而提升水污染治理特別是流域水污染的市場治理效能和效率。再次,由于次級河流和湖泊具有地方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重特性,政府必須轉變職能,實施有效的政府治理,例如,重慶市體育局與重慶南岸區進行綜合開發,將“江南體育館”建設與建設新型城市住宅小區結合,通過體育地產開發實現體育事業與城市建設“雙贏”融資模式。
因此,重慶市次級河流水污染治理可以整合建設美麗鄉村、發展旅游、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產品,融合地區資本市場、國內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形成公共產品融資和資本市場融資有機結合的新模式。
2.3 融資方式和融資產品創新性不足
第一,現狀分析表明,傳統的水污染治理項目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投入、銀行貸款和發行債券等方式注入資金,這是美國20 世紀60 年末~70年代初的通行融資方式。此后發展了排污許可證交易[12],從企業控制污染成本角度發揮了市場激勵作用。第二,金融產品是水污染治理的融資載體,水污染治理融資具有地域性、污染流域性、主體多樣性、不確定性等特征,涉及政策、金融、經濟等系統風險,以及污染類型、利益沖突、環境治理技術和社會公共影響等非系統風險。第三,重慶市目前資金容量狹窄、資金效率較低,單一的融資方式加重政府財政負擔。雖然重慶水務集團融資平臺是一種新型融資方式,但市場融資效率有限。增加市場資金容量,可以借鑒我國國家體育場和北京地鐵4 號線的融資、建設及運營過程采用的PPP 項目融資模式,結合“排污權”的產權交易、抵押、質押,股權融資等金融手段,創新水污染治理投融資方式。
2.4 缺乏政策保障
國際實踐經驗表明,實施以政府與市場合作多元化融資治理結構,必須實現法律與政策的配套改革。英國出臺有《公共事業合同法》,澳大利亞出臺有《國家PPP 政策及指引》,南非《公私合作伙伴指南》,我國香港特區政府出臺有《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的指南》等,這些政策明確了政府與市場主體融資的權利和責任。與此同時,為保障融資機制的有效實施,設計有專門的融資機制,從而避免了“能夠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誘惑的情況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15]。因此,探索重慶次級河流或區域水污染治理的PPP 項目融資機制,既需要借鑒國際經驗,同時也需要在重慶市原有《重慶市政府投資項目管理辦法》 (2003年)、《重慶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和規范政府投資項目BT 融資建設管理的通知》 (2007 年)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對政府主體與市場主體合作的伙伴關系、合作法律責任、治理結構框架和融資運行工作機制等進行探尋,從而實施長期、穩定和有序的水污染治理項目融資機制。
因此,構建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適合重慶市水污染治理投融資機制,應該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指針,以全面推進重慶市可持續發展為指導,以排污權融資市場多元化機制為立足點,重視國際融資的金融力量,深化水污染治理融資體制、機制改革,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化水污染治理投融資體制。
3 對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重慶已經進入水污染綜合治理階段,水污染治理投融資從融資手段上,不僅是項目融資,而且是金融創新。從融資模式上來說,既有政府、企業投融資,也需要創新政府與市場合作的投融資,而后者更能提高投融資的綜合效益。因此,本文結合現狀剖析和關鍵問題解釋,嘗試提出重慶市水污染治理投融資治理機制的對策建議。
(1)公私合作是基礎設施或公共服務等準公共產品的有效提供模式,如多元化、競爭有序的PPP、BOT、BT 等項目融資模式,重慶市在公路、橋梁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中已形成融資平臺、政策基礎、工作機制和融資機制,并取得了顯著成果。可借鑒市場化融資方式,探索次級河流或區域湖泊水污染治理融資機制。
(2)重慶水污染治理融資機制創新,在于構建新型的融資治理結構主體。在政府和企業合作的項目融資模式下可采用以下措施:一是以次級河流流域為融資載體,包括對次級河流以及沿邊的自然、生態資源、文化資源、產業資源和城鎮建設實施有效整合,使次級河流污染權及污染治理工程結合,通過流域內政府和市場投資主體的區域合作,實現政府與市場配置資源的合力功效;二是以區域融資為對象,主要包括對湖泊、農業、畜牧業、養殖業等進行污染治理,結合區域內產業集聚要素,可借鑒荷蘭經驗,通過稅收激勵、許可證制度和金融鼓勵等方式設計“綠色基金”;三是涉及次河流流域、湖泊及農業、旅游、生態等產業可組成市級公私合作主體,構建新型的市場化水污染治理機制。
(3)傳統治理機制和融資機制都存在著利益博弈至上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按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準則,創新政府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水污染融資機制,制定水污染治理相關政策或指南,積極引導企業或社會資本進入水務領域,進而提升水污染治理特別是流域水污染的市場治理效能和效率。
4 結語
水污染治理涉及多主體、多領域和多過程,本文從系統觀角度厘清重慶市水污染治理融資特有的地理環境、水污染類型、利益關系和政策模式,這是融資方式創新的前提,也是融資產品設計的基礎。從產權經濟學角度來看,無論是工業型水污染、城鎮生活水污染,還是農村養殖等水污染,其水污染產品的產權關系、產權交易和產權配置都是繞不過去的門坎。因此,明晰政府與市場的產權配置關系是創新水污染投融資機制的重要環節,應將其作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1] 郭煥庭. 國外流域水污染治理經驗及對我們的啟示[J].環境保護,2001 (8):39-40.
[2] 胡學斌,聶健鋒,吳正松,等. 小城鎮污水治理設施管理運營的市場化研究[J],中國給水排水,2013,29 (8):14-17.
[3] 呂福勝,鐘登華. 中國水務行業發展現狀與趨勢[J]. 中國給水排水,2013,29 (10):12-16.
[4] 司漢武,高衛敏,張艷麗. 環境的公共性與水污染責任的承擔[J]. 生態經濟,2009 (3):173-176.
[5] 施祖麟,畢亮亮. 我國跨行政區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機制的研究——以江浙邊界水污染治理為例[J]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7,17 (3):3-9.
[6] 劉娥平. 城市污水處理項目投融資機制研究[J]. 現代管理科學,2008 (1):16-18.
[7] 賈國寧,黃平,張文煒. 重慶水務上市模式分析及其對水業市場化改革的啟示[J] . 中國給水排水,2010,26(8):11-14.
[8] 賈康,孫潔. 城鎮化進程中的投融資與公私合作[J]. 中國金融,2011 (19):14-16.
[9] 方華,馬欣,呂錫武. PFI——我國城市水業發展的融資新模式[J]. 中國給水排水,2004,20 (11):91-93.
[10] 李曉亮,葛察忠. 中國水環境污染治理社會化資金投入現狀、問題與對策[J]. 地方財政研究,2011 (3):18-23.
[11] 付永川,楊海蓉. 對重慶市次級河流水污染綜合整治的思考[J]. 安徽農業科學,2007,35 (18):5535-5536.
[12] 許評. 美國水污染治理融資機制經驗研究[J]. 應用經濟學評論,2010 (1):129-135.
[13] 李勝,陳曉春. 跨行政區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啟示[J]. 湖南大學學報,2010,24 (1):45-49.
[14] 董秋紅,潘偉杰. 論公共問題的政府規制:合法性及其限度[J]. 學習與探索,2008 (5):77-81.
[15]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 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M]. 余遜達,陳旭東,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