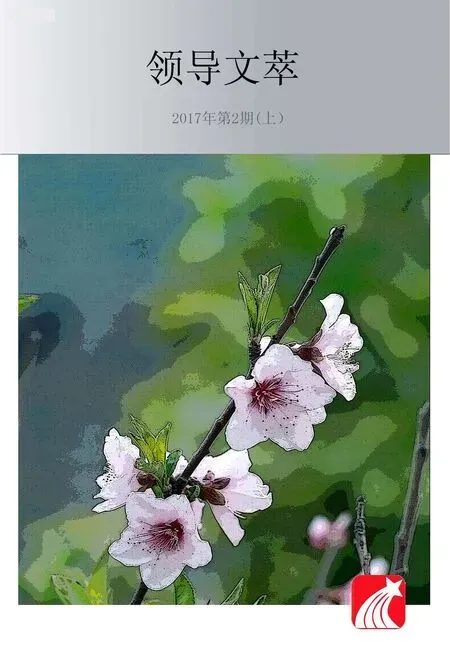學人本色·文化傳燈
——任繼愈先生印象
□左文
學人本色·文化傳燈
——任繼愈先生印象
□左文

2009年1月15日,92歲高齡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等六位先生,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證書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得知這一消息,任老十分高興,并鄭重表示:一定要為弘揚中華文化盡自己最大的力量。孰料,不到半年即當年7月11日,任老竟悄然離世。當天上午,溫家寶總理即委托工作人員向有關負責人,轉達他對任老辭世的深切哀悼,并向任老親屬表示慰問。
與溫總理的“文化交情”
任老與溫總理的交情由來已久,這種交情建立在對中華文化命運的共同關注上。溫總理與任老年齡相差25歲,是名副其實的忘年交。多年來,溫總理對任老始終深懷敬意,任老也將溫總理視為知己,多次贈書、致信,就重點文化工程建設、教育改革等建言獻策,溫總理總是認真閱讀,及時復信。
到了2004年8月,傾注任老大量心血的另一文化工程——《大中華文庫》(第一批圖書24種52冊)出版了。該文庫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系統全面向世界推出的中國古籍整理和翻譯的巨大文化工程,選收歷代以來百余部經典著作,先由古漢語譯成白話文,再由白話文譯成英文。文庫出版后,任老代表文庫工作委員會將書送給溫總理,請他“在百忙之中審閱,并請提出指導性意見,以便于我們今后更好地開展此項工作”。隨即,溫總理回信表示祝賀:“謹對您及從事這項浩繁工程的各出版單位和全體工作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和熱烈的祝賀。這部巨著的出版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有益實踐和具體體現,對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世界文化交流與合作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這部文庫翻譯和出版質量之高,反映了我國的出版水平。”
正是因為有此“交情”,當有關部門于2007年9月17日受溫總理委托,前往看望任老并送上花籃致以親切問候時,任老則覺得“盛情關懷,無以回報”,遂就教育問題向溫總理建言獻策。任老認為,“我國教育面臨危機”,導致他“常為此長夜不眠”。溫總理在復信中表示:“您對我國教育事業十分關心,所提意見中肯,給人以啟示。十七大報告已有教育方面的內容,會后國務院還將就教育問題進行專門討論,當認真吸收您的意見。”
2009年5月中旬,溫總理得知任老生病住院的消息,便委托國務院參事室主任陳進玉同志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先生專程前往北京醫院探望。7月11日,獲悉任老去世后,溫總理心情十分沉重,于當天下午5時左右親自打電話給國務院參事室負責人,并指出,參事室、文史館還有一批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定要把他們照顧好。
一位是矢志不移以振興中華文化為己任的大學者,一位是視文化傳統為國家靈魂的共和國總理,他們就這樣以文化為媒演繹了一段墨香四溢的忘年佳話。
毛主席贊譽后的深層反思
1955年至1962年,任老陸續發表了《漢唐時期佛教哲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等論文,后集為《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出版。這些論文站在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其視野之廣闊,分析之深刻,為開辟宗教學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出色范例,不僅得到了毛澤東主席“鳳毛麟角”的贊譽,也獲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好評,成為中共中央決定設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嚆矢。確實,任老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作為高校教材影響了幾代學人;他埋首傳統文化的古籍整理,主持整理和編纂古代文獻超過10億字;他晚年時仍筆耕不輟,并以每年20萬字的寫作速度在推進……正如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唁電所悼:任先生的開基之功,是不可替代、不可磨滅的。
其實,早在毛主席稱贊任老“鳳毛麟角”前,二人已有交往。1959年10月13日深夜,任老應毛主席之邀走進中南海豐澤園,與之進行徹夜長談。當晚,毛主席對任老用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佛教的方法予以充分肯定,同時談及宗教研究的重要性:“我們不但要研究佛教、道教,福音書(指基督教)也要有人研究。”四年后,毛主席在《關于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中,寫下這樣一段批語:“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在批語中,他還特別強調:“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后來,這一批語被收進《毛澤東文集》。
在政治掛帥的年代里,一個學者能得到最高領袖如此評價,在當時恐怕無有出其右者。如果任老是一個政治投機者,這完全可以成為他博取飛黃騰達的政治資本。而事實上,出自毛主席之手的“鳳毛麟角”四個字,在客觀上也確實成為任老在那個“動亂年代”里得以相對安穩度過的“護身符”,但他并沒有感恩戴德,且一度對此三緘其口。
一般而言,學界公認任老對于中國哲學最大的貢獻是:他提出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三大支柱,它們深刻而廣泛地影響著中國社會各階層。任老力圖把中國佛教思想納入中國哲學發展的主流,并認為道教對中華民族的重要性絕不亞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識中,始終認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從國情出發,而“多民族統一大國”則永遠是中國的國情。當然,任老堅信人類走到某一天,有可能會進入 “大同社會”。
堅守是學人本色的最突出表現
作為一代杰出學人的代表,任老最突出的本色就是“堅守”二字。其一,堅守學術陣地。1934年,任老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西方哲學,一切似乎順理成章,因為他從小就富有哲學思辨,即便是將磚頭翻過來也得問一問上面的螞蟻是否頭暈!唯一讓他感到不安的是,讀哲學很難找到一份合適的職業。也許是對哲學的熱愛沖淡了對安身立命的擔憂,此后他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哲學。
其二,堅守學術立場。學術,乃社會之公器。以學術為生命,需要時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但在任老這里,這份敬畏之心,體現更多的是嚴謹的學術態度和一個學者的獨立精神。馮友蘭先生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哲學史大家,作為馮先生的學生兼侄女婿,任老對其尊重與敬仰自不待言,然一旦涉及學術觀點,任老卻能與馮先生進行面對面的激烈爭論。
其三,堅守學術道德。當前,學術界有一股很不好的風氣,那就是有的導師堂而皇之地在學生研究成果上掛名,且掛第一署名人,這其實是一種變相的學術腐敗。任老則不然,他晚年時不時流露出要撰寫一部屬于自己的《中國哲學史》愿望,但又實在無暇顧及,于是有人提出,能否請任老口述框架、大意,交由學生或助手先開始草稿的寫作。對此建議,任老當即就一口回絕,因為這種做法顯然違背了他 “以己手寫己心,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治學原則。任老常說:“我寫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沒有說別人的話,我反對跟著湊熱鬧。”終其一生,任老主持的古籍整理項目眾多,但從未做過“掛名”主編。這是任老引以為傲的道德堅守,更是后輩學人應該追慕和傳承的大家風范。
“儒者之風道家之骨,從來學人本色;中華大典佛教大藏,畢生文化傳燈。”誠哉斯言!
(摘自《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