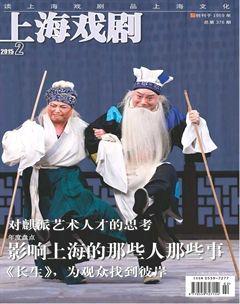但愿那月落重生燈再紅
劉軒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賞心樂事誰家院……”伴隨著裊裊笛聲,2014年12月的第二個周末,北京天橋劇場也透出三春暖意,“大師版”《牡丹亭》在此處熱熱鬧鬧地上演了。這可以說是一場真正沒有“小角色”的演出,不僅劇中男女主角由當今頂尖的昆曲表演泰斗共同演繹。其他配角的扮演者也都是重量級藝術家,如“閨塾”中扮演春香的魏春榮,“離魂”中扮演杜母的王維艱,“道覡”中扮演石道姑的劉異龍,“冥判”中扮演判官的侯少奎等。全劇由十四出經典折子戲串成,分為上下兩本。作為“2014全國昆曲傳承匯報演出”的開端,這也被視為一場頗具“典范”意義的演出,值得評說處甚多。但在我看來,最值得注意的一點仍然是那個看起來老舊的話題:即如何運用“死”的程式表現“活”的人物的問題,也即昆曲界常說的“活”的傳承問題。
昆曲作為我們民族藝術的精華,近代以來幾經沉浮,存續至今,此次參演的大師們多曾受教于“傳字輩”老師,一招一式,本于一脈,而他們經過自己多年的舞臺實踐,從自身理解和條件出發,即使是同一個人物,也往往展現出迥異的風采,例如,這次杜麗娘由沈世華、華文漪、梁谷音、王奉梅、張繼青、張洵澎、楊春霞七位閨門旦藝術家分扮,沈世華纖弱文秀,華文漪華美端麗,梁谷音個性十足,王奉梅端莊雅致,張繼青大氣樸素,張洵澎嬌俏靈動,楊春霞清新內斂,但不論哪一種風格都能在觀眾中獲得擁躉。在不斷強調昆曲正宗的今天,這實在是一個有趣且令人深思的現象。細思想起來,無非就是“合情理”三個字,動靜皆從人物起,歸于情境中。
以王奉梅的“寫真”為例。這是一出比“尋夢”更為難演的“冷戲”,不僅曲詞文雅,唱段繁多,而且由于是表現杜麗娘在屋內作畫的場景,在身段動作和舞臺調度上也不可能像“尋夢”那樣大開大合,王老師在20世紀90年代初左右曾得姚傳薌親授此戲,在恪守昆曲程式規范的同時,她從揣摩人物內心情感邏輯出發,適當地加入了一些富有生活情味和情感邏輯的“小動作”,豐富了舞臺表現手段,既抓住觀眾,又恰切地傳達杜麗娘此時孤凄落寞的心境。例如,表現杜麗娘看到自己不多時“瘦到九分九”的悲哀和吃驚,其他閨門旦演員一般是作照鏡科,繼而作猛然一驚狀,以手捂鏡,低頭做悲嘆介。而王奉梅此處著力突出了“照鏡子”,前后一共照了三次,第一次是春香把鏡子拿起來,離杜麗娘還有一段距離遠觀,王奉梅的杜麗娘在這第一照之后并沒有馬上立起,而是手托腮微微一愣,面部表情是有些迷茫和懷疑,這巧妙地傳達出杜麗娘近日為夢中之情所困,無心理妝已久的背景;第二次是順著第一次的情感邏輯進行,因為第一次遠觀效果令人難以置信,所以要再仔細看看,便招手叫春香把鏡子拿近前來,而此時春香則做不情愿狀,配合漸強的音樂伴奏,整個舞臺節奏開始加強,觀眾的注意力也隨之集中到杜麗娘身上,第二次照是全折的第一次情感小高潮,杜麗娘離開座位沖到臺前仔細照鏡,繼而一驚,順勢往后一退,跌坐在座位上,把鏡子捂在胸前,表達出杜麗娘看到容顏消瘦后的震驚,經過短暫的停頓后,她又慢慢拿起鏡子邊看邊無奈地搖頭,這是第三照。經過這一系列細膩入微的表現,觀眾明明白白地體會到了杜麗娘此時容顏消瘦的狀況和悲戚心情,為下面的描畫真容做了非常充分的情感鋪墊。
另外,雖然《牡丹亭》是傳奇經典之作,但是王奉梅的“寫真”出于舞臺表現和人物刻畫需要,對原作進行了一點小小的改動,即在描容之前,配合【普天樂】的曲牌,增加了一小段“整裝”的表演,在我看來這真是神來之筆:首先,這一段表演使得杜麗娘大家閨秀的身份更加鮮明,與“游園”之理妝形成呼應;其次,【普天樂】四句唱在其他版本的表演中,多為杜麗娘對著觀眾演唱,在這種情況下其中“不因他福分難消,可甚的紅顏易老”兩句中的“他”難免有指代不明之感,而王奉梅在對鏡整裝的同時面對鏡中人唱這兩句曲詞,杜麗娘自傷自憐的情緒就自然而然地感染了全場觀眾,也使得配合這四句唱詞的程式動作有了更為明確的內在情感邏輯。
七旦同臺,纖瘦濃淡各不同,但都從某種角度傳達出了彼時彼刻杜麗娘的閨秀神韻。同樣地,四位巾生表演藝術家岳美緹、石小梅、汪世瑜、蔡正仁在舞臺上或如春風拂面三分暖,或如壁立梅花沁骨寒,或頑皮或寬厚,也都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了嶺南才子柳夢梅的書生心性。
“拾畫叫畫”可謂柳夢梅的本傳,是塑造他“情癡而幻”性格特征的關鍵折子。其中,“拾畫”又被稱為“男版‘游園”,同之前杜麗娘的“游園”相呼應。周傳瑛老前輩曾用“靜、雅、甜”來歸納“拾畫叫畫”中柳夢梅的表演,在我看來,“叫畫”中的柳生或許是甜蜜的,但“拾畫”中似乎“清峻”些更為妥當,它的情感基調應該是籠罩著淡淡的傷感,而不應過分歡快。
石小梅老師的柳夢梅一出場,并沒有像一般出場一樣“亮靴底”,而是以幅度較小的臺步一步一頓地從上場門走到臺口,定睛環視四周,開唱【金瓏璁】——一般演員出場,尤其是獨角戲,為了在一開始就抓住觀眾,都講究亮相,或是身段,或是絕活,或是嗓音,但是在這里,石小梅的頭兩句唱“驚春誰似我,客途中都不問其他”,卻故意放輕了聲音緩緩吟出,結合出場特別的臺步,恰到好處地表現了柳夢梅大病初愈的情境。所謂表演一切從人物出發,不光是善于做加法,也要善于做減法,不符合特定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表演,即使再有亮點,也堅決棄之不用。總體看來,石小梅的“拾畫”表演與尋常演法相比,節奏略慢了一些,身段動作幅度也較小,例如【顏子樂】中“蒼苔滑擦”一句,常見的表現方法是演員雙手拎褶子,原地走兩個趟步,一只腳在原地向前方和側邊做幾下點地,最后做一個滑步。而石小梅老師在表現這一句時放棄了最后的滑步,用左右腳向前方輪番做了三次點地,每次均以腳尖、腳掌和腳跟依次點地三下,最后“擦”字一個小趔趄,向前一小步站穩,一手拎褶子,眼望地面投一只水袖,仿佛在埋怨蒼苔為什么這樣滑,把柳夢梅表現得既謹慎又有孩子氣的天真,令人莞爾。【顏子樂】一曲末尾,柳夢梅看到滿園寒花繞砌、荒草成窠,更添惆悵,石小梅唱此句時在“草”字上用了一個腔,觀眾聽來猶似嘆息一般,同時在身段上,她沒有采用大的調度,只是拎褶子,跑一個小圓場,唱至“窠”站定,放下褶子,卻更加逼真地表現出在茂盛的荒草地中穿行的情景。同為生行表演大師的蔡正仁老師曾說:“我深深體會到,作為一個演員,在臺上動作非常多,這是很容易的;而動作越是少,難度越高。”石小梅的身段表演幅度和動作的復雜程度都不大,但難得都在情境中,如同素描一般,寥寥幾筆,一個蕭索的園林和一個滿懷閑愁的士子便活潑潑立在觀眾眼前了。
作為一場具有“垂范”意義的演出更為可貴的是,除經典的折子之外,一些過場戲也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光彩。“道覡”即是如此。上海昆劇團的文丑表演藝術家劉異龍把這出戲演得精彩火爆,甚至掀起了上本的一個小高潮。他扮演的石道姑一出場,并沒有立刻走到舞臺中央開始插科打諢,而是在九龍口面向半空中有一個停頓,做欣賞科,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當大家正猜不透他葫蘆里賣的什么藥時,只見他伸手一撈,一朵小花出現在指尖,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用俗話說,這一下就把場子炒熱了。這個魔術的運用不僅提升了舞臺表演效果,同時也突出了石道姑這個人物的性格特征:愛美,愛一切美好的事物。有了這一層鋪墊,之后石道姑愿意擔著砍頭之罪幫助柳夢梅開棺并一路庇護二人就更好理解了。
憑心而論,因為年齡和身體的客觀因素,大師們在嗓音、氣息和扮相上與其藝術巔峰時期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演出仍然能使觀眾身臨其境、如癡如醉,尤其是扮演杜麗娘、柳夢梅和春香的幾位藝術家,以年邁之軀出演花季少男少女,卻能給人傳神之感。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們對于扮演對象心理狀態和情感邏輯做了細致深入地體悟,這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了解人物,而是把這種對人物的體驗與自身對生活和生命的體驗結合在一起。正如王奉梅老師講她演戲的體會時所言,一個演員要演好一個角色,必須投入到人物和規定的情境中去,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狀態。這是對固有的程式化動作做生活化的理解和領悟,并且能夠和自己已有的人生經驗、情感經歷融合在一起,把由模仿得來的程式動作變成自己由內心發出的肢體語言——觀眾在觀賞這種表演時,即使是耳熟能詳的老戲碼,同樣能獲得新鮮深刻的感受和觸動。竊以為,所謂“大師”,絕不僅僅在于他們從事藝術時間久,能演的戲多,更在于他們能夠真正從人物和情節需求出發,融程式于人物之中,一點小動作不管是恪守規范還是銳意創新,都能從人物邏輯的角度解釋出道理來——戲之好壞,本沒有絕對的圭臬,但看合理不合理,這也是“典范”的意義之所在。也只有合理地傳達具有普適性的情感,昆曲之燈才能如再世為人的杜麗娘一般,永遠光彩照人。
(作者為上海戲劇學院在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