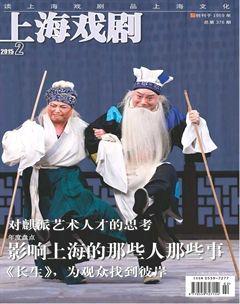眾里尋她千百度
譚蘭燕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藝壇前輩們都認為,這幾句詞描述的意境是初踏藝術舞臺的年輕人所處的第一種境界。
自小便喜歡唱唱跳跳的我,1997年考入湛江市小孔雀粵劇培訓學校,在藝校時,當那些崇拜的藝術偶像出現在自已的身邊,成為自己的老師時,心情是難以想象的。名師們對于我們這些毫無經驗的新人更是傾囊相授,粵劇表演藝術家孔雀屏老師就手把手地對我悉心教導。老師們將粵劇的基本功和各種流派的唱腔、表演,一字一句,一招一式,一笑一顰給我細心分析,并教我如何把技巧融入到表演中去。孔雀屏老師的啟蒙和一步一個臺階的言傳身教,讓我打下堅實的基礎。老師們常說“攀登藝術高峰,從來沒有捷徑”。我也將這些教導當作暮鼓晨鐘常來警醒自已,也逐漸認識到要勤學,苦練,常思,多演。
藝校畢業后,我先是分配到小孔雀粵劇團工作了五年多,2006年5月,調入湛江粵劇團,2012年又被吸收到深圳市粵劇團。在劇團的這些年,我主演了四十多出大戲和折子戲,飾演過各種各樣的舞臺人物,其中有《楊門女將》的柴郡主、《斷橋》的素貞、《紅絲錯》的榴月、《七仙姬》的大仙姬、《張羽煮海》的皇后、《九寶連》的周婉清、《鬼怨》的李慧娘、《周瑜》的小喬、《范蠡獻西施》的西施等。每演一出戲,每扮一個角色,我都要將她揣摩透徹,細膩鮮明地表現出來,這些形象深受行家和觀眾的喜愛和好評,也讓我在舞臺上不斷得到淬煉,逐漸成熟起來。
2006年11月,在“廣東省第五屆粵劇演藝大賽”中,我在粵劇前輩張華老師的細心輔導下,以折子戲《紅梅記》之“鬼怨”參賽。我充分運用自已清越明亮的唱腔,設計了輕盈飄忽的步法,動如脫兔,靜若處子的身段,加長水袖的吞吐揮舞,上下翻飛的動作,把李慧娘的“鬼怨”演繹出來,最終,奪得了銅獎,那時,我還未滿20歲。第二年,我又在曹秀琴老師的指點、教導下,以一曲演唱難度很高的“鬼怨”參加廣東省政協第四屆“四洲杯”粵港粵曲演唱大賽,最終在省、港、澳總決賽中取得了優秀獎。2008年7月18日我在湛江舉行了隆重的拜師儀式,正式拜師上海昆劇藝術家梁谷音為師,同年12月,我把梁谷音老師傳授給我的一折子戲《馬前潑水》帶到了當年的廣東省粵劇演藝大賽,將金獎收入囊中。
現代粵劇《雷雨》從策劃到首演,前后花了近兩年時間,作為中國當代戲劇的經典之作,曹禺先生的《雷雨》是一部家喻戶曉的話劇作品,在舞臺上久演不衰,而且京劇、越劇、評劇、評彈、黃梅戲等劇種也都有改編,唯有粵劇沒有改編過。這次是《雷雨》首次被改編成粵劇,由國家話劇院導演張奇虹、青年編劇鄧艷燕執筆,戲曲導演黃天博指導,朱立熹作曲。
在演員陣容方面,這次創排,深圳粵劇團大膽啟用了年輕演員,我有幸和吳曉毅、吳思明、譚圓圓等80后演員擔綱主演,演繹了一個20世紀凄美的經典故事。
在曹禺先生的劇作《雷雨》中,是以周樸園為中心,展開了一張巨大人物關系網,所有矛盾沖突皆以其為源點,展示了一幕人生大悲劇。而粵劇《雷雨》則繼承了深圳市粵劇團的經典劇目粵劇《風雪夜歸人》的創作風格,根據劇種特點和現代粵劇觀眾的觀賞習慣,淡化了本劇的悲劇色彩,強調作品唯美、人性化的特質。粵劇版《雷雨》最大的特色,就是繁漪占有較大的戲份,通過繁漪跟周家、魯家每個人的關系以及相互的矛盾沖突,串成故事發展的主線。這樣的改編,雖然弱化了戲劇矛盾的尖銳沖突,但體現出了劇本中人性的特點,在呈現上也更具有唯美的觀感。
其實接演這個戲,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挑戰。除了排練場和資料室,我吃飯、睡覺都在琢磨繁漪這個角色,我可憐這個女人,希望能演出她真情的一面。在粵劇版《雷雨》中,繁漪雖然與繼子有著不倫之戀,然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她卻具備超越時代的人性追求、有著其進步的一面。她喜歡看《安娜·卡列尼娜》,認為自己的遭遇跟安娜很相似。她可以說是當時新女性中的代表,探尋著西方的人文精神,敢于追求愛情。當然,戲劇人物的內心需要喜怒哀樂致之情緒,才能讓別人感受到的,這就需要演員用唱腔和形體表演表現出來。粵劇《雷雨》的創作過程,正是強調了演員的內心體驗和唯美的表達,才使得舞臺上的呈現,讓觀眾的審美由“感受”上升到“感動”。
排演《雷雨》的過程,對于我這樣的戲曲演員來說是一種藝術歷練。目前的我,應該說正走入藝術演出的黃金期,也開始了藝術修煉的第二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多年來,在粵劇的繼承傳統,改革創新方面,我也思考了很多,也實踐了很多。“藝術同源”這話一點不假。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華就說過,唱歌猶如書法,輕、重、疾、緩、拖頓、吐、納,技法多樣,有異曲同工之妙,看你如何運用而已,戲曲也是如此。對于表演藝術來說,表面的照搬模仿,是沒有內涵的,沒有充實的感情,是不能打動觀眾的,“離古即邪,趨時便俗,求新忌詭,如鏤金玉”。傳統出根本,脫離了傳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難以生存。過分趨同時勢,容易走入表面熱鬧,實質簡單。創新不能詭異,要合情合理,要步步見功力,招招顯鋒芒,藝術界前輩們的這些富貴經驗和總結,都給我在藝術上的豐富和提高有極大的啟迪和借鑒。
第二境界的前路未見盡頭。“書山有路勤為徑,藝海無涯苦作舟”。我還將會向藝術的第三境界邁進。終有一天,“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那時,機遇呈現,功夫修到,靈犀一點,自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