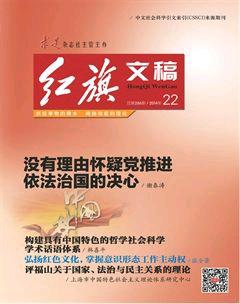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
韓喜平
創造性地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運用中國特色的理論話語系統來表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民族復興的理想圖景,以凝聚民心,共同奮斗,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所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積極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堅持正確的建構方向,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
語言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它不僅僅是對客觀世界的描述和主觀意向的表達,也支配著人們的行為。語言的實踐性源于其中的價值意向和行動指向,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話語更是具有引領文化發展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應當是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內核。不能否認學術話語的歷史傳承,但更不能忽視它的現實的和大眾的根基。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展開與馬克思主義教育宣傳的普及,馬克思主義話語早已為中國大眾所熟知,“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大眾解釋與評價社會歷史的基本概念,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和話語建構的指導思想。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形成與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與實踐更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中國夢”等新概念新話語正在顯示著強大的實踐力量。這些語言是當代中國學術話語的現實基礎。
馬克思主義是實踐性的理論,只有內在于勞動人民的實踐創造,成為現實的思維方式、實踐方式、說話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發揮作用。馬克思主義追求科學力量與道義力量的完美結合,從不把既成的理論當作僵死的教條,而是本著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的原則,探索符合現實需要、解決現實問題的相對的絕對真理。綜觀馬克思主義話語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核心話語的轉換,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實踐的唯物主義”、“剩余價值”、“共產主義”,到列寧的“帝國主義”、“一國勝利”、“無產階級專政”,再到毛澤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工農武裝割據”、“新民主主義”,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等等,不同的核心話語,表達著不同的時代主題和不同的問題領域,從而滿足不同的實踐要求,進而生成不斷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所以,馬克思主義是具體的、不斷創造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本義從來不是用“死人抓住活人”(馬克思語),而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推進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觀和理論觀,就是要創造出符合時代發展需要、符合大眾需要的理論話語體系。
當代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作為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內在環節,應當是用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以概念、邏輯的方式表達當代中國人民自我發展的意愿,按照學理的邏輯來表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內在要求,從而建立起源于現實實踐又高于現實實踐的學術話語體系,為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發揮先導性作用。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的現實話語也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呈現出復雜的結構,公平與效率、自由與平等、經濟與環境、民主與民生、一元與多元等悖論性話語的同在是今天的事實,人們對于作為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有著多元的理解與評判。這使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更為重要與緊迫。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建立與中國特色實踐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理論話語體系,以概念體系的方式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展示當代中國人在社會生活各層次各領域中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理解、對人與人關系的理解、對人自身的理解,從而為調整和控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提供重要的理論參考和依據。
在以實踐性為本質特征的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理論、學術話語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要以大眾話語為基礎。大眾話語直接源于生活,蘊含著大眾經驗和智慧的豐厚積累,理論話語從大眾話語中來,還要回到大眾話語中去。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是用中國的語言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從而建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想圖景,那么,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就是借助大眾自己的語言把他們樸素的生活態度升華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學術語言的大眾化,主要不是指學術語言的普及或通俗性翻譯,而是指學術語言本身就具有大眾化的形式與內容。即是說,學術語言的大眾化,不僅僅在于表現形式的通俗化,更重要的在于政治立場和思想感情的大眾化。這也就要求學術語言的時代性、人民性、通俗性,真正能夠關注大眾需求,回應大眾關切,解答大眾困惑。
當下,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三種話語體系:總攬性指導性的政策話語;深奧晦澀的書齋話語;歧義多元、通俗也容易庸俗的百姓話語。如果在馬克思主義的水平上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話語,那么,就要求整合三種話語體系,講述“中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即政策語言理論化、學術語言生活化、百姓語言規范化,把學術語言塑造為言之有物的實話、言之有據的真話、言之有理的新話,讓人民群眾喜歡聽、聽得懂,記得牢、用得上。
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各種社會思潮相互碰撞,各種話語體系都在爭奪市場。事實上,多年來我們在不斷向世界學習的過程中,在思想理論建構的語言風格上也深深受到其影響。這些影響有積極的、推動發展的,但也有消極的,甚至存在西方敵對勢力打著學術推廣的旗號,不知不覺滲透他們的價值觀。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揭露其中所包含的虛偽的言論和反動的立場,從而澄清問題的實質。用中國理論、中國話語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質疑,化解西方學術界對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誤解或曲解,反擊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思想理論乃至意識形態的挑釁。堅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信念,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話語體系來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捍衛國家意識形態。
二、承繼厚重的中華文化,讓傳統語言煥發活力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學術成長,是對本國本民族文化積淀的理論自覺,也是對傳統文化思想史的延續,更是對傳統語言的傳承。但無論是文化的自覺,還是思想史的延續,都離不開語言和話語的實現方式。語言作為一種表達思想和價值觀念的符號是相對穩定的,具有無法割斷的歷史連續性。古代的思想理論所以能夠傳承下來,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語言的這種連續性。
對于構建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來說,承繼厚重的中華文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傳統語言自身所具有的優勢。傳統文化中語言折射出的深沉學術素養,如法國重農學派有著深受中國傳統農業思想及其話語體系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學術作品大量譯介到中國,這對中國學術成長來說,一方面具有推動意義,但另一方面也有其消極阻礙作用。傳統語言的話語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出現“言必稱西方”的傾向。然而,回顧中國傳統學術語言的特質,不難發現它所具有的優勢。
首先,中國傳統學術語言注重對民族文化精神實質的把握與厘清、對傳統文化理想的發揮,凝聚著古代優秀知識精英對世界、社會和人生的思考,具有明確的價值觀念和深刻的理論內涵。它把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倫理文化統一為一個整體的表達,是中國人現實的思維方式和理想的生活方式。這些思想理論早已經內化為中國人的意識并駐留在中國人心里。對于中國人來說,它不僅僅是遺產,更是在內心深處規定著當代中國人對于幸福生活的基本感受和理解。
其次,知行合一是中國傳統學術語言的基本特質。中國傳統學術語言更多地直接體現為行為方式和行為準則,體現為思想和思維方式,即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人格與學術的統一。這種統一決定了學術語言具有極強的實踐性和普及性,甚至沒有受過專門教育的普通百姓都可以掌握并運用其核心概念。
再次,傳統學術語言具有生動的直觀性。中國古代文化建立在智者的人生感悟基礎之上,無論是《道德經》還是《論語》,其中的諸多觀點都是在對人生的切身感悟的基礎上產生的,這就擺脫了西方學術話語的符號化抽象特征。此外,傳統語言的優勢還表現在語言與生活世界的直接契合。對于當代中國學術發展來說,語言與現實生活世界的契合是直接發生的,正如我們甚至無需對一個概念加以考據,就能夠憑借生活世界的感悟和體驗直接理解這一概念的本質一樣。相反,對于西方語言的使用,就要在嚴格的詞源學考據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
最后,傳統語言超越了西方因為邏輯分析所產生的語言和概念被“肢解”的破碎狀況,是建立在生命觀照之上的有機整體。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語音彰顯了語言的有限性和無限性的張力關系之下的完整意義。所謂“詞不達意”、“言不盡意”等都為語言的無限性留下了生命感悟的空間。
中國幾千年文明的延續發展,有著多種的表面形態和發展階段,但其基底樣式和大眾的文化心理結構則是相對穩定的,并且通過相對穩定的語言結構至今仍然在教化大眾,有意無意地支配著中國大眾的日常生活。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構造,不能忽視對中國傳統學術語言的研究和繼承。現代學術的中國表達具有雙重的可能,從形式上說,人們通過語言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可能是相同的,但表述的方式則是具有民族文化個性和特征的。比如,我們稱為“天道”,西方稱為“邏各斯”;我們稱為“體驗”,西方稱為“直觀”;我們稱為“內省”,西方稱為“反思”,等等。這些概念上的對應關系,雖然不是完全嚴格的,但至少在表達同樣道理的時候,我們可以擁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從內容上說,世界是語言中的世界,思想是語言中的思想,中國語言的邏輯也就是中國人的思想邏輯,只有中國的語言才能真實承載中國大眾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才能真正地決定或影響大眾對于社會生活的一切態度和想法。用中國獨特的語言類型和概念系統來表達中國人的生活和理想,才是中國學術語言形式與內容的真正統一。
三、講述中國自己的故事,轉變西方學術話語體系
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作為中國人獨特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與方法論,作為中國人自我發展追求自己理想生活的理論表達,從形式到內容都應當是具有民族特征的。具有民族性的學術話語,首先應當是對百姓日常話語的尊重,既與日常生活話語中的那些古老且又鮮活的價值內涵相一致,又反映著百姓的現實要求。其次應當以中國人為本,解決中國立場、中國眼界中的問題。再次是總結提升中國經驗,探索中國未來發展的種種可能。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學術話語不是現實或大眾情感的直觀描述,也不是“就事論事”的具體行為設計,它對現實和問題的把握必須站在普遍性和反思性的高度上,它的理論形態必須是概念的體系,它的問題、問題闡釋及研究方式不僅來自于民族的文化與學術傳統,更多地受益于人類思想文化的歷史發展與當代知識的整體狀況。
雖然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創性決定了中國實踐與西方現代理論有著巨大的差別,但西方的現代學術話語又是我們必須借鑒的。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當代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大量傳入國內,國內對于西方的學術也有了相當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這為推進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建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但實際上,西方學術話語在中國有著三種境遇:其一,被當作與現實無關的純粹知識體系來對待。一些學者以一種無立場的態度力圖客觀公正地對其展開研究。這種研究與中國現實無關,最終導致中國問題的學術構造與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分裂;其二,有些人執著于學術研究與意識形態的機械統一,用政治語境限定學術語境,以意識形態為評價西方學術的唯一話語,往往滿足于對其作簡單化庸俗化的批判;其三,被當作普世性的現代“圣經”加以崇拜,被當作中國學術話語的樣品和中國學術發展的理想。不少理論工作者嚴重脫離本土文化傳統、歷史基礎和實踐根基,無論是概念、理論、框架,還是研究方法、研究風格、問題領域、思維模式,都嚴重脫離了中國的現實語境,只會“照著說”。“照著說”的結果就是中國學者本應當具有的歷史感、現實感和實踐感再度流失,進而嚴重破壞了中國學者的創造性和創新性。
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一定的社會條件。在西方是適用的理論,不見得適用于中國。現代西方的學術話語是現代西方人的存在方式,它源于西方民族獨特的精神與文化傳統,圍繞西方社會歷史和現實的問題而建立起來,展示的是由西方的文化路徑所決定的理想前景。歷史和現實都在證明,生搬西方的學術話語,不僅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反而會為中國的發展帶來無窮的困惑與危機。西方學術話語的中國轉換,目前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其一,從歷史演進來看,西方話語體系用于指導和解釋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系列新興民族國家的發展時遭遇了嚴重的困境和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非洲、拉丁美洲、南歐、亞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90年代初以來,蘇聯、東歐等一系列僵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崩潰后的轉型國家,模仿西方國家發展道路,按照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指引,使用西方話語體系,不僅未能實現迅速融入西方國家體系,而且陷入發展困境。歷史實踐反復證明,以西方歐美經驗為主體而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是不顧現實與國情,對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對西方話語體系進行簡單模仿甚至直接移植的做法,不能真正解決各個國家的特殊問題。
其二,在學術層次上回應西方對于當代中國理論與實踐的歪曲和批判。近幾年,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和外向型經濟已經背離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在造成國內兩極分化的同時,也強化了區域間的競爭和壓力,并引起不同國家工人之間的疏離和仇視,因而對于國際工人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實踐是一種消極的力量。美國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把中國的經濟組織形式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美國學者蓋伊·索爾曼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解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澳大利亞學者羅恩·卡利克把“中國模式”描述成這樣一個較為簡捷的公式,即“經濟自由加上政治壓制”。諸如此類的認識都要求我們以中國人的立場和生活體驗為基礎作出理論上的反擊。
其三,西方現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研究目標、研究對象、問題闡釋方式呈現的多樣性特征,形成復雜繁多的成果,極大地開闊了人們的理論視野,值得中國學術界認真對待。例如,中國人可能無法接受現代西方學術中精密細致繁瑣的語言分析方法和理論闡釋方式,但語義的敏感性訓練是需要的;可以不同意西方環境倫理學的一切自然存在都具有內在價值的獨斷,但必須深入研究其所提出的對待環境的“不作惡”、“不干涉”、“忠誠”、“補償正義”等基本原則;可以不同意西方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但卻需要高度關注差異性和特殊性,正視群體內部的矛盾沖突;可以批判實用主義的價值相對論,但必須認真對待其近年來所提出的建立開放的社會科學的構想;等等。在此,轉換西方學術話語的目的在于推動中國學術的自我創造,從而使中國學術具有時代性水準與實踐價值。
其四,當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對于西方現實社會的批判以及人類未來發展的探索,未必具有全部的真理性,但有助于我們看清西方發展中存在的更深層次的問題,看清中國與世界的全面的復雜的關聯,所以值得我們理智地對待。
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的過程必然是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的創新過程。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的原創性和獨特性需要在哲學社會科學的原創性中展現出來。中國學術需要深切地表達中國價值觀念的分量、思維成熟的程度和對人類社會探索實踐的偉大創造,并以此構造自己的根基、靈魂和風格,形成自己的新觀念、新范疇、新表述,從而在自立于世界學術之林的同時,真正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學術話語權,讓世界了解中國理解中國。
(作者: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責任編輯:李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