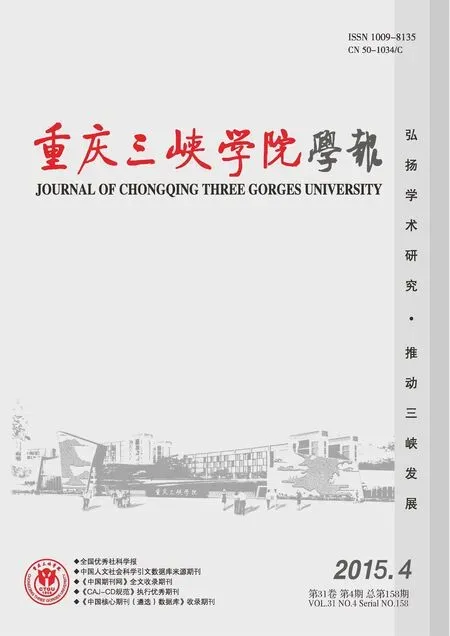淺談“五四”之“反傳統”
陳亞瓊
?
淺談“五四”之“反傳統”
陳亞瓊
(陜西師范大學,陜西西安 710062)
五四文學產生的文學意義,不僅局限在對新文學新思想的倡導,更是打破了古代文學與近現代文學間對話的隔膜,搭建了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間的溝通橋梁,實現了文學自身現代意義的轉型。
五四文學;傳統;反傳統;胡適;周作人
學界有觀點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徹底反對舊文化且與傳統文化一刀兩斷的,即“全面拋棄中國文化傳統”和“全盤西化”。顯然,這一觀點并沒有用辯證的眼光正確看待“五四”之“反傳統”。“五四”之“反傳統”更多的是對傳統的反思,包含了時代所賦予的特殊使命和情感在內。從某種程度而言,正是在對傳統重新認識并加以借鑒改造的基礎上,現代文學的轉型才得以實現。
一、何為“五四”之“反傳統”
如果將傳統文學單純理解為與現代文學相對的文學形態,那么由梁啟超等人所提倡的維新文學,就是文學從傳統向現代進化所必經的初始階段。傳統文學孕育了維新文學,而五四文學作為維新文學的延伸和拓展,以其更為明確的現代性要求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因此,“五四”之“反傳統”,不是,也不可能是徹底地與傳統割裂,更多的是傳統文學不斷發展在某一歷史階段的特定表現。
“傳統”是相對“現代”而言的,五四文學從思想內容到具體形式都顯示出不同于過去的現代性,新文學的建設者們受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性思潮影響,故將人性解放作為第一訴求。五四初期由北大創辦的《新潮》期刊,它的英文刊名是,即“文藝復興”。發表其上的作品,從文學目的、創作原則到具體實踐,都呈現了一種與傳統截然不同的樣態。但由于五四時期特殊的社會背景,人性的解放,又自覺承擔了反帝反封建的社會功能。
二、“五四”如何實現其“反傳統”
五四新文學素以白話文的提倡,以及“人的文學”的發現這兩方面的突出貢獻成功挑戰傳統文學。但筆者并不認為這是五四文學反傳統的最好說明。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強調從“八事”入手,認為“第一,文學向來是向著白話的路子走的,只因為有許多障礙,所以直到現在才步入了正軌,以后即永遠如此。第二,古文是死文字,白話是活的。”[1]胡適所說的第一點是針對于中國文學發展的趨勢而言的。中國傳統文學從詩經、楚辭發展到后來的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各種文體臻于完備。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當時代環境發生改變,會促使在先前頗為興盛的某種文學形態孕育下的新的文學樣式開始嶄露頭角并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新出現的文學形態會被同樣的方式取代,從而推動文學一直向前發展。因此,斷言文學發展的趨勢在于向著白話前進,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而把這種斷言作為發起白話文運動的原因,更是值得商榷的。因為人是無法確定將來社會環境中存在的文學形態具體是怎樣的,最多是依據文學發展規律做出預測。當社會主流需要一定的文學形態時,這種適宜的文學便會應運而生,即便是要克服各種頑固障礙。正是時代的變化使傳統文學選擇白話文作為自己生命力的延續,白話的提倡志在必行。胡適所闡釋的第二點,指出白話相對于古文而言的優勢。白話當然是活的了,畢竟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是不可否認的,但提倡白話文的原因并不在此。周作人曾經對胡適這一觀點進行辯駁,“古文和白話很難分,其死活更難定。而且一句死了的古文,其死只是由于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不能說是由于這個字是古字的緣故,現在很多古句中的字還都時常被我們運用,那么,怎么能算死文字呢?”[2]這同樣說明了提倡白話,不是古文本身出現了問題,根本原因在于時代的需要。
1918年12月《新青年》5卷6號上發表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一文,他明確指出應該提倡新文學,簡言之就是“人的文學”,而反對“非人的文學”。他所強調的“人”,不是世間所謂“天地之性最貴”或“圓顱方趾”的人,而是指從“動物”進化的充滿獸性的人和從動物“進化”的充滿靈性的人這兩方面的結合,即人是“靈肉一致”的。因此,封建綱常和傳統禮教中那些對于人性壓制和扼殺的內容是新文學所反對的,對于個人幸福的追求,對于私欲情欲的正當表達是新文學所提倡的。在之后的《平民文學》中,周作人進一步闡釋了這一主張。可以說,周作人是從思想內容的層面對于胡適從語言形式層面的變革給予支持和補充,從而豐富和完善了新文學理論的建設。但當我們重新審視傳統文學時會發現,早在詩經中就存在著揭露黑暗的作品。比如流傳最廣的農事詩《七月》,全篇詳細記錄了農民一年的農業生產情況和艱辛勞作,無疑是一種有力控訴。除了保存于書面的文字,還有很多口耳相傳的民間傳說,像梁山伯祝英臺雙雙化蝶,孟姜女哭長城等等,雖然他們不被允許在現實中相守到老,但富于神話色彩的結局也正表現了人們的理解與肯定。對于人的解放的要求,一直存在于中國傳統社會中,只不過在“存天理,滅人欲”的封建壓迫下微弱地喘息著。直到周作人將其挖掘出來供人警醒的時候,“人的文學”才第一次以完整清晰的面貌被世人所知。
五四新文學的創建者們在倡導新文學的時候,這種反傳統的態度似乎過于激烈。或許是他們有意而為之,又或許是時代的局限。畢竟,培育五四新文學主要建設者的土壤仍是傳統文學。就以陳獨秀為例,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在對整個封建舊文學宣戰之前,在第一個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之前,他竟然是1896光緒年間的秀才。當中國傳統社會中儒家思想的核心已深入血脈的時候,積極入世、追求仁義禮智信的堅定信念早已轉化成救國救民的真摯愿望。他們“打倒孔家店”的旗號,只是針對當時社會上掀起的尊孔復古的逆流,而不是對于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學的全面否定。很難想象一個沒有傳統文化根基的人如何來承擔建設新文學的重任。換言之,五四新文學反的是傳統文學中那些落后消極的因素,對于那些進步積極的因素還是在有意無意間承襲下來的。
三、如何看待“五四”之“反傳統”
探索新文學發展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掙脫傳統文學束縛的勇氣,需要有在西方文化啟發之下結合現實對傳統文學進行借鑒和改造的魄力,而這一切,新文學的創建者都做到了。盡管他們所提出的主張,在現代人看來并不是無懈可擊,但在當時的年代卻是振奮人心的積極吶喊。其實早在胡適之前,就有裘庭梁和陳榮袞等人提倡白話,當時社會上一直是文白并用的。繼而,胡適提出“八不主義”,后提出了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四條主張”,最后又總結出了建設新文學的唯一宗旨,即“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三大主義”,這和胡適的一系列論斷互為補充,共同推動新文學緊鑼密鼓地進行。這本身就是認識循序漸進、不斷深化的過程,也是新文學在逐漸展開擴大影響的過程,更是為了推行新文學而不斷做出反思改進的過程。
五四新文學雖以新的形態展現在世人面前,但整個運動中存在的缺陷還是必須重視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內容固然是進步的,但新文學所強調的文學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平民文學,沒有真正代表社會底層人民的通俗文學作品的出現,也就是說,五四新文學只是在有一定素養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展開,而沒有和中國最廣大的農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林紓在與新文學辯論的時候,曾攻擊白話文是“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根本登不了文學的大雅之堂。當然新文學創建者利用這一機會,和保守勢力進行了論戰,指出白話不是“鄙俚淺陋”的,是“說的出且聽得懂的話”、是“不加粉飾的話”、是“明白曉暢的話”。但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不論是傳統文學還是新文學,都在潛意識里將真正記錄底層百姓的通俗文學排除在文學范圍之外。從維新文學梁啟超提出“三界革命”起,新文學的創建者們共同致力于開創新的文體格局,把小說推到了備受矚目的地位。但在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影響下出現的黑幕小說、譴責小說等,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并不是很高。直到后來魯迅創作小說,通過對阿Q、孔乙已、祥林嫂等人物性格的展現,對國民性的深刻剖析,才在思想性內容方面達到了最高水平。后來社會各界曾大力支持“國語運動”,白話文學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取得了“國語文學”的尊稱,國語教育變得順利,但教育豈能在一朝一夕間得到明顯效果。因此,在新文學進行得吐火如荼時,主要的受眾依舊是之前那些有一定基礎的小知識分子,而在國語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是活躍不起來的。但值得肯定的是,當國語的推行被重視起來,這本身就是新文學對于傳統文學中文化資源分配不合理的一種補救措施,要讓更多的老百姓也有機會識字讀文。
此外,胡適提出的“整理國故”的主張,應是清楚闡釋五四新文學和傳統文學之間關系的最好說明。“整理國故”的目的在于到“爛紙堆”中打妖捉鬼,把傳統文學中的“國渣”清理出去,將余下的“國粹”繼承下來。“整理國故”并不是一味地對于傳統文學全盤吸收,也不是向傳統文學投降而背棄五四新文學,是以一個成熟文人的身份更為宏觀地把握中國文學的發展概況,以一個年輕學人的身份更為微觀地分析中國文學的具體細節。他還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具體方法,一是“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二是“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三是“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3]從古到今,從中到西,全面細致梳理了新文學興起推進的來龍去脈,為中國文學史的史學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闡述“五四”之“反傳統”這一問題時,最為激進的要數林毓生先生所堅持的五四時期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他尖銳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與“五四文學革命”間歷史發生的相似性,二者都是以徹底摒棄中國傳統主流的思想文化的改革來掀起政治社會革命的。但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共領導人錯誤發動,終極目的在于維護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政權,后被反革命集團利用才發生的,這場災難本是可以避免的。五四文學革命的發生卻是歷史必然,古今中外文化的碰撞與沖突,促使時代在新舊之間做出選擇。文化大革命中的全盤性反傳統帶有極強的功利性,不是文學出了問題,而是要人為地將文學納入為政治發展服務的軌道。而五四文學的反傳統,是建立在傳統舊文學的諸多不合時宜暴露出來,急須倡導新的進步的文學來與時代配合。這種“反”是因為“反思”傳統后,發現有“反”的必要,有“反”的意義,“全盤性”的“反”雖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卻是當時五四文學建設者與傳統割裂去倡導新文學的態度與決心。
五四文學順著時代的潮流,始終在建設與破壞中斗爭,在傳統和現代里糾結,不斷探索建設新文學的正確道路,終在社會各界的努力推動下,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成為富于時代轉型意義的關鍵點。
[1]姜義華.胡適學術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7.
[2]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
[3]胡適.胡適自述[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責任編輯:鄭宗榮)
On the Anti-Traditional Literary Movement in May Fourth Movement
CHEN Yaqio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Movement is not only to advocate new literature and new ideas, but to break the conversational barrier and serve as the bridg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Thus the literature has undergone the modern-sense transformation.
May Fourth Literature; tradition; anti-tradition; Hu Shi; Zhou Zuoren
I206.5
A
1009-8135(2015)04-0053-03
2015-03-15
陳亞瓊(1991-),女,山西大同人,陜西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二十世紀中國重要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