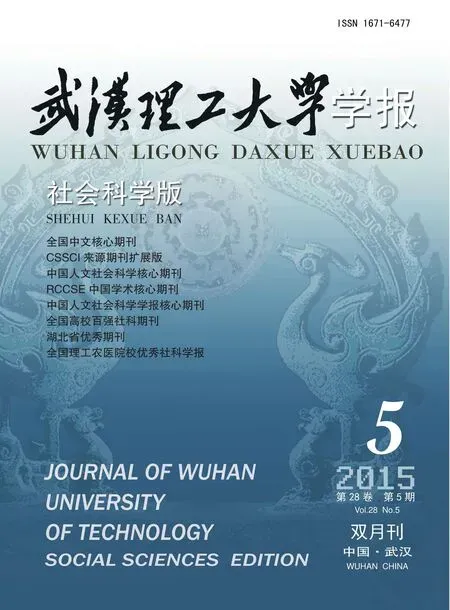董仲舒思想中刑罰與思想教化的關(guān)系
摘要:西漢時(shí)期儒家學(xué)者董仲舒為統(tǒng)治者構(gòu)建了一種理想社會(huì)的發(fā)展模式,即以教化為治國(guó)之本,但在肯定教化的前提下,董仲舒并不否認(rèn)刑罰對(duì)社會(huì)所起的輔助作用。董仲舒通過(guò)天道陰陽(yáng)哲學(xué)論證了刑罰是教化的輔助手段,其存在與作用的發(fā)揮影響到教化效果的實(shí)現(xiàn)。董仲舒在此基礎(chǔ)上通過(guò)將儒家《春秋》思想運(yùn)用于漢代的司法實(shí)踐,通過(guò)“春秋決獄”實(shí)踐著其思想中刑罰與教化關(guān)系的論述,對(duì)后世影響深遠(yuǎn)。
關(guān)鍵詞:董仲舒;刑罰;教化;春秋決獄
中圖分類號(hào):D092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5.018
董仲舒是漢代最重要的儒家學(xué)者,是奠定整個(gè)漢代思想性格的關(guān)鍵人物,其思想見解及政治實(shí)踐對(duì)整個(gè)西漢王朝以及此后的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董仲舒主張以教化治國(guó),但同時(shí)并不否認(rèn)刑罰在教化中的輔助作用,對(duì)于刑罰與教化關(guān)系的論述是其思想中一個(gè)有突出特色的地方。列寧曾說(shuō)過(guò):“所有一切壓迫階級(jí),為了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都需要有兩種社會(huì)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的任務(wù)是鎮(zhèn)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亂。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在保存階級(jí)統(tǒng)治的條件下減少苦難和犧牲的前景(這做起來(lái)特別方便,只要不擔(dān)保這種前景一定能‘實(shí)現(xiàn)’……),從而使他們順從這種統(tǒng)治,使他們放棄革命行動(dòng),打消他們的革命熱情,破壞他們的革命決心。”董仲舒在強(qiáng)調(diào)教化的同時(shí)也需要“劊子手”的輔助,在借鑒法家思想的基礎(chǔ)上通過(guò)刑罰作為輔助手段,意在鉗制人性中的“惡”。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一個(gè)突出特點(diǎn)就是在論述了刑罰與教化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肯定了刑罰作為教化輔助手段而存在的意義,進(jìn)而為西漢政權(quán)的鞏固和穩(wěn)定提出了一套以刑罰輔助教化的思想主張。
一、對(duì)刑罰與教化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教本獄末”
面對(duì)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xùn)以及漢初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董仲舒看重教化在社會(huì)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主張將教化作為治國(guó)的根本之策,但在法家思想的影響下,董仲舒也明白刑罰的存在對(duì)于社會(huì)穩(wěn)定的必要性。運(yùn)用陰陽(yáng)思想,董仲舒將刑罰視作教化的輔助手段從而納入其教化體系之中,通過(guò)必要的刑罰措施來(lái)幫助教化的推廣,形成其思想的獨(dú)特性,此后漢代儒生普遍主張將教化與刑罰看作治國(guó)的兩手策略,認(rèn)為“刑以佐德助治”[2]五刑。事實(shí)上,儒家歷來(lái)在推崇道德教化的同時(shí)本就不排斥刑罰,但“在‘尚德不尚刑’的總體思路上比較輕視法治和刑罰,輕視的程度,也因人因事而異。”在董仲舒看來(lái),“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4]精華這就是說(shuō),教化是政治的根本,刑罰是政治的輔助,這兩件事似乎屬于毫不相干的兩個(gè)領(lǐng)域,但實(shí)際上,它們都是政治的工具,功用是一致的,因此必須互相配合、協(xié)調(diào)一致,君子歷來(lái)是重視教化與刑罰相一致的。如果教化與刑罰不相協(xié)調(diào),那就會(huì)使本應(yīng)受表?yè)P(yáng)的人受懲罰而進(jìn)監(jiān)獄,使本應(yīng)受譴責(zé)的人受獎(jiǎng)賞升大官,造成思想混亂,使民眾無(wú)所適從。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集中論述了刑罰與教化的辯證關(guān)系,他說(shuō):“天道之大者在陰陽(yáng)。陽(yáng)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yáng)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yǎng)長(zhǎng)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yáng)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shí)出佐陽(yáng);陽(yáng)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dú)成歲。終陽(yáng)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dú)任執(zhí)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5]可見,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刑罰與教化的關(guān)系包含以下三個(gè)方面的內(nèi)容。
(一)始終保持教化為主的地位
董仲舒認(rèn)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4]精華教化是政治的根本,刑罰是政治的輔助,教化與刑罰乃是本與末的關(guān)系,切不可廢德教而任刑罰,否則就要重蹈秦亡的覆轍。在長(zhǎng)期有效的教化之后,刑罰自然會(huì)沒有用武之地,“古者修教訓(xùn)之官,務(wù)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5]以德化民,可以使國(guó)家內(nèi)部不設(shè)監(jiān)獄,不僅如此,教化還可以使天下和平,他說(shuō):“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4]郊語(yǔ)
(二)刑罰為教化的輔助措施
教化與刑罰,是“主”與“輔”的關(guān)系,也是“經(jīng)”與“權(quán)”的關(guān)系,反映在教化與刑罰兩者的關(guān)系上,就是以教化為常道,以刑罰為權(quán)變,刑罰只是權(quán)宜之計(jì)而已,不得已而用之,理想的狀態(tài)是“任德而不任刑”。
(三)教化與刑罰殊途同歸
教化與刑罰有諸多的不同,如地位不同、處理不同領(lǐng)域的事情、功用有大小之分,但它們的最終目標(biāo)卻是一致的,即共同致力于王道社會(huì)的實(shí)現(xiàn),但兩者要相協(xié)調(diào),“如果教育宣傳揚(yáng)善去惡,而現(xiàn)實(shí)卻是惡人上了公堂,善人進(jìn)了監(jiān)獄,那就是‘教’與‘獄’不相順。”[6]董仲舒也說(shuō):“聽訟折獄,可無(wú)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眾,與教相妨。”[4]精華)這就是說(shuō),審理獄訟、裁定案件要謹(jǐn)慎,審判對(duì)了,道理就更明朗,教化就更順暢;審判錯(cuò)了,就會(huì)蒙蔽真理,迷惑眾人,妨害教化,教化與刑罰都做好了,就可以更好地實(shí)現(xiàn)王道。
二、對(duì)刑罰與教化關(guān)系的論證:“陽(yáng)德陰刑”
從董仲舒的天道哲學(xué)來(lái)看,自然界有陰陽(yáng)二氣,缺一不可,兩者的運(yùn)行構(gòu)成自然界的生息變化,但陰陽(yáng)二氣有尊卑強(qiáng)弱之分,陽(yáng)氣主尊而陰氣主卑,二者之間適當(dāng)?shù)谋壤偷匚坏牟煌瑯?gòu)成自然界的平衡有序。董仲舒正是在其天道觀的基礎(chǔ)之上談?wù)撔塘P與教化之間主次關(guān)系的,這種比附論證得出“大德小刑”、“德主刑輔”的結(jié)論,這一方面在理論上給予刑罰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刑罰的地位,將其限制在必要的范圍內(nèi),董仲舒在天道哲學(xué)的基礎(chǔ)之上對(duì)教化與刑罰之間的辨證關(guān)系進(jìn)行了具體論證。
(一)董仲舒分析了陰氣和陽(yáng)氣在天道中的不同地位
雖然在天道運(yùn)行中陰陽(yáng)二氣缺一不可,但兩者的地位和價(jià)值并不相同,存在高低優(yōu)劣之分,這種區(qū)分的標(biāo)準(zhǔn)在于兩者的“功”不同。“陽(yáng)始出,物亦始出;陽(yáng)方盛,物亦方盛;陽(yáng)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yáng)而出入,數(shù)隨陽(yáng)而終結(jié)。”[4]陽(yáng)尊陰卑在董仲舒看來(lái),陽(yáng)氣決定著自然界萬(wàn)事萬(wàn)物的“出”和“盛”,陽(yáng)氣的“功”比較大,當(dāng)然陽(yáng)氣不能單獨(dú)主宰自然界,陰氣的存在也是必要的,“萬(wàn)物非天不生,獨(dú)陰不生,獨(dú)陽(yáng)不生,陰陽(yáng)與天地參然后生。”[4]順命“天之道,出陽(yáng)為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4]暖燠常多這都說(shuō)明了陰氣和陽(yáng)氣在自然界中各有其價(jià)值,萬(wàn)物都是在兩者的共同作用下產(chǎn)生和運(yùn)行的。但對(duì)于兩者的地位和價(jià)值,董仲舒認(rèn)為“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4]暖燠常多,也就是說(shuō)陽(yáng)氣占有百份而陰氣只占有一份,兩者在比例上的懸殊差距說(shuō)明了自然界對(duì)陰陽(yáng)二氣的需要不盡相同,也就決定了陰氣和陽(yáng)氣的地位不同,“陰者,陽(yáng)之助也,陽(yáng)者,歲之主也。”[4]天辨在人通過(guò)這種論證,董仲舒認(rèn)為在天道之中陰陽(yáng)二氣的關(guān)系是陽(yáng)主陰輔、陽(yáng)尊陰卑,是故“貴陽(yáng)而賤陰也”[4]天辨在人。
(二)董仲舒將人間的刑罰與教化附會(huì)天道的陰氣與陽(yáng)氣
“天地之常,一陰一陽(yáng),陽(yáng)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4]陰陽(yáng)義陰氣和陽(yáng)氣作為天道的基本元素,其中陽(yáng)氣代表著天的仁德,陰氣則代表著天的刑罰。董仲舒從善惡的角度對(duì)陽(yáng)氣和陰氣的道德屬性作了解釋,他說(shuō)“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yáng),陽(yáng)為德,陰為刑。”[4]陽(yáng)尊陰卑其中陽(yáng)氣占盡了善良美好的屬性,而陰氣充斥著邪惡與陰暗,董仲舒試圖通過(guò)人們趨利避害的自然選擇建立在社會(huì)秩序中崇尚“大德小刑”的心理基礎(chǔ)。“陽(yáng),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yáng)氣暖而陰氣寒,陽(yáng)氣予而陰氣奪,陽(yáng)氣仁而陰氣戾,陽(yáng)氣寬而陰氣急,陽(yáng)氣愛而陰氣惡,陽(yáng)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yáng)常居實(shí)位而行于盛,陰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yuǎn),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jīng)而后權(quán),貴陽(yáng)而賤陰也。”[4]陽(yáng)尊陰卑在這里,董仲舒描繪了陰氣和陽(yáng)氣帶給人們的真切感受:陰氣使人感到暴戾和陰森,陽(yáng)氣則使人感到寬厚和仁愛,由于陰氣代表著刑罰而陽(yáng)氣代表著教化,進(jìn)而通過(guò)這種感受的轉(zhuǎn)移使人們體會(huì)到刑罰和教化帶給社會(huì)的不同效果。
(三)董仲舒通過(guò)比附推導(dǎo)出教化和刑罰在社會(huì)政治領(lǐng)域中的不同地位
由于陽(yáng)氣代表著教化,陰氣代表著刑罰,因此通過(guò)陽(yáng)氣和陰氣在自然界中地位的高下就可以得出教化和刑罰在社會(huì)政治領(lǐng)域中的不同地位。天道的“陽(yáng)主陰輔”以及“任陽(yáng)不任陰”[4]陽(yáng)尊陰卑反映在人事上就是“德主刑輔”以及“好德不好刑”[4]陽(yáng)尊陰卑,人間的君王如果不按此行事,過(guò)于倚重刑罰而非教化,就會(huì)違背天道自然,“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4]陽(yáng)尊陰卑董仲舒又將“德主刑輔”之下教化與刑罰的關(guān)系解釋為“經(jīng)”與“權(quán)”的關(guān)系,“天以陰為權(quán),以陽(yáng)為經(jīng);陽(yáng)出而南,陰出而北,經(jīng)用于盛,權(quán)用于末,以此見天之顯經(jīng)隱權(quán),前德而后刑也。”[4]陽(yáng)尊陰卑也就是說(shuō)天道以陽(yáng)為常經(jīng),以陰為權(quán)變,進(jìn)一步論證了教化是為政的常規(guī)手段而刑罰只是一種非常措施。“天之任陽(yáng)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yáng)出而前,陰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4]天道無(wú)二通過(guò)陰氣和陽(yáng)氣在天道中的地位,董仲舒論證了刑罰和教化在社會(huì)生活中的地位,進(jìn)一步得出“教本獄末”的結(jié)論。如前所述,陰陽(yáng)二氣在量上的比是“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4]暖燠常多,即陽(yáng)占有百份,而陰只占有一份,故“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5]君王如果過(guò)于重視刑罰而不致力于教化就是違背了“教本獄末”這一天意。
總之,董仲舒在教化與刑罰的關(guān)系上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以教化為主,以刑罰為輔,在以教化治理國(guó)家的總體策略下,以必要的刑罰糾正社會(huì)問題,以其威懾和懲治的效果輔助教化的推廣,最終實(shí)踐儒家政治理想。
三、對(duì)刑罰與教化關(guān)系的實(shí)踐:“春秋決獄”
“春秋決獄”是肇始于西漢武帝時(shí)期,經(jīng)董仲舒開始的一種借由儒家經(jīng)籍《春秋》的基本原則作為處理案件依據(jù)的實(shí)際做法,其實(shí)質(zhì)在于以儒家倫理指導(dǎo)司法實(shí)踐。董仲舒本人對(duì)于“春秋訣獄”的基本精神進(jìn)行過(guò)概括,“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4]精華可見,“春秋決獄”的基本精神在于要在案件具體事實(shí)的基礎(chǔ)上重點(diǎn)考慮行為動(dòng)機(jī),即“重志”:對(duì)于動(dòng)機(jī)不良的人,即使其犯罪行為尚未完成或沒有造成社會(huì)危害,也要對(duì)其課以刑罰,對(duì)為首作惡之人要特別加重處罰;而對(duì)于沒有不良動(dòng)機(jī)的人,即使客觀上造成了危害后果,也應(yīng)當(dāng)從輕處理。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認(rèn)為,秦法漢律存在“誅名而不察實(shí),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5]的問題,因而反對(duì)機(jī)械的依照刑律進(jìn)行刑罰。雖然“原心論罪”也容易造成主觀隨意①,但人的善惡乃本于內(nèi)心,從善惡觀念出發(fā)來(lái)進(jìn)行司法審判,對(duì)改革當(dāng)時(shí)嚴(yán)苛的刑罰制度頗有作用。應(yīng)當(dāng)說(shuō)在古代封建社會(huì)的倫理法律體系尚不成熟之時(shí),“春秋訣獄”的出現(xiàn)和運(yùn)用更有助于社會(huì)公平,更為重要的是通過(guò)儒家倫理對(duì)司法活動(dòng)的滲透,真正使刑罰在實(shí)際運(yùn)用中起到了輔助教化推行的作用。
“春秋訣獄”是由董仲舒提倡并得到漢武帝支持而興起的。此后,記載董仲舒曾指導(dǎo)的大量案例匯編而成的《春秋決事比》逐漸成為兩漢時(shí)期司法斷案的重要參考,可惜此書現(xiàn)已失傳,僅有少數(shù)幾個(gè)案例在《太平御覽》等書中記載而得以留存。從現(xiàn)有的幾個(gè)案例來(lái)看,董仲舒是通過(guò)儒家“先圣”之名,在具體案件中借助儒家倫理道德原則去代替當(dāng)時(shí)具體的法律規(guī)定而得出案件結(jié)論,通過(guò)限制嚴(yán)刑峻法確立儒家倫理道德在司法實(shí)踐中的指導(dǎo)地位。董仲舒的“春秋訣獄”其實(shí)就是將《春秋》中“重民、重義、重志”的思想體現(xiàn)在法律方面,也就是教化和刑罰相結(jié)合的體現(xiàn)。《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引《春秋決獄》一個(gè)案例,很好地說(shuō)明了這一點(diǎn):“甲父乙與丙爭(zhēng)言相斗,丙以配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dāng)何論?或曰:毆父也,當(dāng)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毆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jìn)藥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dāng)坐。”[7]刑法部六在這個(gè)案例中,兒子雖出于救父的目的,但由于驚慌失措而誤傷父親,或被按照“毆父”處理,但董仲舒按照《春秋》“原心論罪”的特點(diǎn)認(rèn)為“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由于兒子并無(wú)傷害父親的故意,相反是為了救父親,這與“父為子綱”的倫理要求是符合的,故不應(yīng)判處刑罰。可見,董仲舒反對(duì)機(jī)械照搬刑律,希望通過(guò)倫理道德的溫情化解現(xiàn)實(shí)刑罰的暴戾,這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漢承秦制”的嚴(yán)刑峻法的一種否定,從特定的歷史條件來(lái)看是有其合理性的,對(duì)刑罰的濫用具有限制作用。
在董仲舒看來(lái),作為教化輔助手段的刑罰是否合理將會(huì)對(duì)教化的開展產(chǎn)生直接的影響,刑罰正確合理,就能使教化的原則更加明確,更多的民眾受到教化,使封建倫理教化得到推廣實(shí)行;相反,若刑罰過(guò)于嚴(yán)苛甚至與教化的基本原則相悖,這種道德原則的混亂就會(huì)造成社會(huì)民眾迷惑不解,必然妨礙教化的社會(huì)效果。董仲舒“春秋決獄”的做法直接影響了漢代的治獄,對(duì)漢代較為嚴(yán)格的刑律起到了修正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修正使得儒家經(jīng)義得以深入民心,在一個(gè)個(gè)具體案件的處理中使民眾得到教化,從而使民眾的行為自覺符合社會(huì)規(guī)范。
注釋:
①如馬端臨在《文獻(xiàn)通考·春秋決事比》中評(píng)價(jià)道:“蓋漢人專務(wù)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
[參考文獻(xiàn)]
[1]列寧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48.
[2]班固.白虎通疏證[M].陳立,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
[3]羅國(guó)杰,夏偉東.德治新論[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2:17.
[4]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華書局,2011.
[5]班固.董仲舒?zhèn)鱗M]//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6]周桂鈿.秦漢思想史[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192.
[7]李昉.太平御覽[M].北京:中華書局,1960.
[8]蘇輿.春秋繁露義證[M].北京:中華書局,1992.
(責(zé)任編輯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