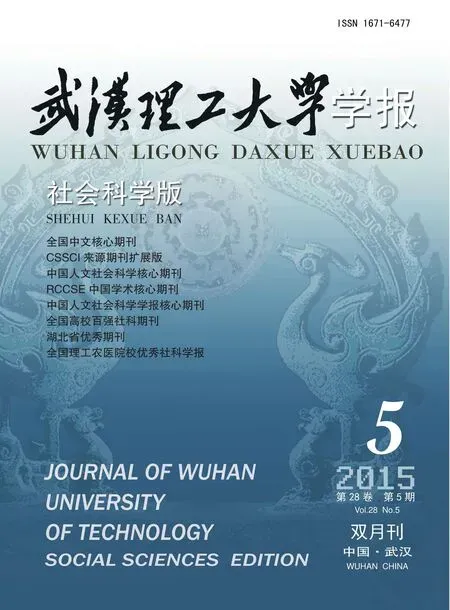問責與履職: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監管行為的實證研究




摘要:學界主流的觀點認為“多頭監管”體制下,問責失效是導致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失敗的主要原因。而在“冗余”的視角下,重復的組織設計卻可以增加組織的穩定性。所以問責與食品安全監管體制下地方政府履職的關系有待進一步理論探討和實證性檢驗。通過梳理有關“多頭管理”體制利弊之爭的研究文獻,并在其基礎上,對問卷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以及最小二乘法(OLS)分析,實證檢驗表明:在現行的“多頭監管”體制下,問責與地方政府履職行為存在著較強的關聯性,從而對傳統的認識予以了有力的反擊。
關鍵詞: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問責;履職程度
中圖分類號:D630.9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5.010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然而從三鹿的“三聚氰胺”毒奶粉,到雙匯的“瘦肉精”,再到農夫山泉的“砒霜門”……食品安全問題由于其“不可接受的損害風險性”[1]不僅直接威脅著億萬人民的生命安全,更對社會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產生潛在的沖擊,成為近年來政府應對的重點公共危機內容之一[2]。
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是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建設的核心。食品安全監管體制,主要是指政府食品安全管理的權力配置模式和機構設置形式[3]。2009年6月1日施行的《食品安全法》規定“國務院設立食品安全委員會綜合協調食品安全相關事宜,衛生、質檢、工商、農業和食品藥品5個部門重新劃分各自的職能范圍。”其中“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承擔食品安全綜合協調職責,國務院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依《食品安全法》和國務院規定的職責,分別對食品生產、食品流通、餐飲服務活動實施監督管理。”[4]可見,在食品監管上,我國采用的是多部門分頭管理的分段監管模式,也有人將其概括為“多頭監管”模式。
在食品安全監管體制中,地方政府作為監督鏈條的最底端,食品安全問題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起著“一票否決”的關鍵性作用,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問責”壓力,而這種壓力恰恰也是食品安全危機下推動地方政府履職的動力所在。然而在當前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多頭監管”的體制下,很多學者認為“多頭監管”的權責不一,直接導致了無法對地方政府問責,從而切斷了“問責”對地方政府“履職程度”的反向激勵作用。權責不一,也就成了“多頭監管”飽受詬病的重要原因。
雖然學界對“多頭監管”幾乎是“一邊倒”的批判聲音,而這其中也不免有不同的論調。劉亞平就從“冗余”的角度提出,“就如同人擁有兩只耳朵、兩只眼睛、兩個腎一樣,這些重復的器官在人體中起著非常重要的補充或者替代的作用,而我國當下對食品安全監管的多部門設計,其實也有著增強監管系統可靠性,提高監管適應性等積極的作用。”[5]同時他還將這種“多頭監管”定義為“互補式監管”,相比較學界所推崇的集中統一的監管模式“壟斷式監管”而言,更適應管制契約不成熟的我國的現狀,同時也可以減少對監管機構的監督成本[6]。
那么面對以上兩種說法,到底哪種說法更加切全實際呢?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對兩種觀點進行相關論證呢?本文將就此問題進行理論梳理與實證檢驗。
二、文獻回顧與假設的提出
(一)文獻回顧
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食品安全“多頭監管”體制下的“問責”是否推動了“地方政府履職”,我們有必要從批判與支持兩個角度分別對對“多頭監管”體制進行文獻回顧。
1.“多頭監管”之弊:問責無法推動地方政府履職。有關對我國食品安全體制的研究,起始于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學者們將多發的食品安全事件歸結為當下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對其進行了多角度的批判,概括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資源浪費。周清杰指出,“‘多頭監管’使得權力過于分散容易導致監管工作各自為政,無法形成合力,不僅增加部門之間的協調成本,降低了監管效率,也是對國家有限公共資源的浪費。”[7]劉亞平也認為這種“分散”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最為人所詬病的地方在于資源的重復和浪費,不能“集中資源辦大事”。
二是效率低下。唐鈞和李丹婷在“三鹿奶粉”事件發生之后概括了我國食品安全的現狀,并認為“多頭監管”第一大弊病為效率低下[3]。譚德凡認為,這種“多頭監管”的模式使食品安全監管領域各部門間無法形成聯動協作機制,影響了食品安全監管的效率[8]。
三是權責不清。陳季修和劉智勇認為,我國食品安全監管行政體制內部的‘多頭監管’直接導致了兩個后果,一是監管過度,二是監管不力。監督過度導致了部門權力和機構的擴張,監督不力則導致了“搭便車”現象。他同時指出,部門之間的爭奪和推諉成為常態,這直接造成監管權力的動蕩更迭頻繁,也構成我國食品安全監管的一大特色[9]。
而朱旭峰將這種對“多頭監管”的批判理論根源歸結于“集體行動的邏輯”。即“公共部門在引入職能競爭者的情況下,其機構效率會下降。進而,公共部門也缺乏動力將自己的職能同別的機構加以區分[10]。
總之“權責不清”成為學者們批判“多頭監管”的最常用的武器,其根本歸結點也就在于,多頭監管切斷了問責與地方政府履職的紐帶,無法推動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危機中積極履職。
2.“多頭監管”之利:冗余的組織設計推動地方政府履職。從“冗余”的視角出發,“多頭監管”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優勢。March 和 Simon創造了“冗余”一詞[11]。冗余最早運用于生物與工程技術領域,后來組織學家將“冗余”運用于組織研究中,Cyert R和 March J將“組織冗余”定義為,組織擁有的資源與實際運行所需資源之差[12]。
國內學者陳龍波,趙永彬和李垣總結了國外研究,概括了“冗余資源”的四個主要作用:第一, 冗余可以作為引導組織成員對超越維持企業生存所需要的資源以外的資源進行投資的手段。第二,冗余可以解決組織內部的沖突。第三,冗余資源可以使組織在動蕩的環境中生存,是組織的一種緩沖器。第四,冗余可以服務于組織的戰略管理目標。其中他們還指出的,冗余對績效的這些有利影響在環境動蕩的時候特別明顯[1314]。
而將“冗余”的觀念引入到行政組織中,我國學者朱旭峰也對“部門冗余理論”進行了簡要總結,他指出“公共服務的壟斷供給會導致公共部門的低效率,而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過程中引入競爭,將促進公共部門效率的提高,并且有利于控制腐敗。同時也可以提高政治委托人對該部門信賴度(reliability)。”[15]
綜上所述,對于“多頭監管”而言,行政組織中重復的機構設置也有其合理性與優勢:一是具有穩定性,尤其是在面對復雜環境與提供繁雜的服務中,多部門的設計可以減少系統可能的風險性;二是具有可調試性,在組織戰略發生變化時可以靈活調整,并且更加適合創新的戰略環境;三是多部門的設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腐敗成本,抑制了腐敗的發生;四是在部門之間形成競爭,不僅可以提高效率,更能提高公眾對部門的信賴度。
總之,冗余的組織設計,最根本的作用在于防止組織失敗,推動組織目標的實現,這種觀點等同于本文所述的履職行為的實現,也就是說“多頭監管”的冗余設計可以推動地方政府的履職行為。
(二)假設的提出
通過以上的文獻整理分析,關于“多頭監管”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會得到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與看法。我們可對此進行簡單的總結,如圖1所示。
通過以上的分析總結,我們不難發現,在有關對“多頭監管”體制的批判之中,大部分學者認為其最大弊端在于“權力分散”導致的“權責不清”,從而會在實際監管中出現“重復管理”與“管理真空”,而顏海娜與聶勇浩更是指出這種權責不清直接“導致了法律上和公眾問責的困難重重”。而“問責”在以食品安全事件為代表的公共危機中“往往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其目的是要以追究責任形式來減少突發事件,減輕政府面臨的危機。”[16]可見“問責”在公共危機中實際上對于推動地方政府履職發揮著重要作用。 因此我們將“問責”作為自變量,將“地方政府履職程度”作為因變量提出:
假設一:“問責”與“地方政府履職”正相關。
同時通過文獻分析,我們找到了以下三個影響政府履職程度的控制變量:
首先,由于食品行業生產經營主體數目龐大且分布極其分散;其次,行業法律不夠健全完善、標準沒有明確統一;第三,地方保護、人情關系網以及權力尋租的存在等原因,食品監管機構的打擊行動屬于高成本類型的監管[17]。因此地方政府財政的緊缺,自然沒有相應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到食品監管中,而地方政府也沒有動力去履行食品監管的責任。食品安全事件當中資源投入程度成為影響地方政府履職的重要因素。
假設二:資源投入程度與地方政府履職程度正相關。
其次,食品安全技術包括食品安全標準、檢測及環保體系以及相關技術器械、技術人員等方面[18]。如果說資源的投入為地方政府應對食品安全危機提供了基本的物質保障,那么成熟的技術也是地方政府順利履職的關鍵所在。只有懂得如何使用先進的技術,才能更好地應對食品安全危機。
假設三:技術的成熟程度與地方政府履職程度正相關。
最后,地方政府在不合理政績觀引導下(如GDP崇拜等)往往將重點放在地方經濟發展上而忽略了對食品安全的監管[19]。由于受地方領導“重經濟而輕危機管理”的思維影響,下級官員們自然會采取“取悅”上級領導的做法,大搞經濟建設,忽視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日常履職。
假設四:地方政府的重視程度與地方政府履職程度正相關。
三、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對象為沿海F省Q市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工作人員。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研究人員利用H大學MPA學生資源對Q市農業、工商、衛生、食品藥品監督管理、質監五個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工作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總共發放問卷150份(每個部門30份),回收問卷119份,問卷回收率為79.33%。其中有效問卷為116份。其中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如表1。
(二)變量操作化
1.因變量“地方政府履職”操作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事件管理的職責主要包括預防準備、監測預警、處置救援和恢復重建。也就是體現在突發事件發生前、發生期間以及發生之后三個階段。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的相關內容,本文將食品安全管理當中地方政府履職操作為 “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努力程度”,“應對食品安全事件準備的努力程度”,“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應急處理努力程度”,“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救援受困群眾努力程度”,“食品安全事件結束后恢復社會秩序的努力程度”,“事件結束后強化危機管理能力努力程度”六個因子。通過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resource”來定義本文的“地方政府履職程度”。
2.自變量及控制變量操作化。謝爾德認為,問責指的是“當 A 有義務告知 B 關于 A(過去或將來)的行動和決定,并為它們辯護,一旦出現不當行為則將遭受懲罰,A 就是對 B 負責的”[20]為保證研究的便捷性,本文將“問責”在問卷中直接體現為“食品安全事件中,被問責的力度”。將“資源的投入程度”定義為“投入足夠的人力物力財力應對食品安全事件”。將“技術的成熟程度”定義為“掌握成熟的技術應對食品安全事件”。將“地方領導的重視程度”定義為“領導對食品安全事件重視且對形勢的判斷總是迅速準確的”。
本研究將因變量、自變量和控制變量都通過詢問問卷對象相關陳述符合自身工作實際的程度的方式,以5級李克特量表進行測量,“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具體問題及變量描述見表2。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食品安全危機中地方政府履職程度檢驗
表2數據顯示,就各個分變量而言,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救援受困群眾努力程度最高,均值達到3.819。說明安全事件爆發后,救援生命是地方政府投入最多的領域。同時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事件管理事前的準備程度(A1與A2的均值分別為3.422和3.500)明顯小于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期間與之后的努力程度。這說明地方政府的危機管理的重心體現在事件爆發期間與之后的處理,對危機事件前期的關注較少。 地方政府履職程度最小值是-2.192183分,最大值1.45398分,兩者相差3.646163分,說明在不同的危機事件階段,政府的履職行為差距較大。同時表2顯示地方政府履職行為的均值為0.2601859,說明在食品安全危機事件中地方政府有較好的履職表現。
(二)地方政府履職行為影響因素的實證檢驗
就自變量與控制變量而言,從表2可見,自變量食品安全事件中地方政府被問責的力度均值達到3.759大于其他三個控制變量均值。同時食品安全事件中資源投入程度(均值為3.741),大于地方政府的重視(均值為3.405)以及技術的成熟程度(均值為3.362)。一定程度上展現了目前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事件當中的行為邏輯,重問責,重投入,但實際上地方政府的主觀重視與技術配備相對不足。
單純的描述統計,雖然可以一定程度反映當前問責力度的重要性,但不足以檢驗“問責與履職程度關系”。本文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方法,采取逐步進入的方式,檢驗前文中自變量、控制變量與食品安全危機中地方政府履職行為之間的關系。得到回歸分析的結果如表3所示。
模型一:主要討論了資源投入變量對地方政府在食品危機事件中的履職行為的影響,模型調整后的R2為0.203,模型解釋了地方政府在食品危機事件中的履職行為的20.3%的變化。其中資源投入程度對模型有顯著影響。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礎上將技術的成熟程度放入模型,調整后的R2上升為0.225,技術的成熟程度對模型有顯著影響。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礎上,把地方領導的重視程度放入,調整后的R2上升為0.312,且系數顯著為正,模型解釋了地方政府在食品危機事件中的履職行為的31.2%的變化。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礎上,把問責引入模型,調整后的R2上升為0.341,問責進一步解釋了地方政府履職程度3.1%的變化,說明以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職程度為因變量時,問責顯著影響地方政府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職程度。
通過實證檢驗表明:“問責”對地方政府履職程度影響顯著,且呈現正相關,從而假設一得以驗證。“資源投入程度”對地方政府履職影響非常顯著,并且呈現正向影響,假設二也得以驗證。“技術成熟程度”對地方政府履職影響不顯著,假設三并未得到驗證。“地方政府的重視程度”對地方政府履職影響非常顯著,并且呈現正相關,假設四得以驗證。
五、結論與討論
面對我國嚴峻的食品安全形式,食品安全的“多頭監管”體制似乎成了 “罪魁禍首”,權責不清,無法問責,切斷了推動地方政府履職的動力紐帶;而從“冗余”的視角反觀這種“多頭監管”體制,穩定性的組織設計卻有助于組織目標的實現。那么在當下的“多頭監管”體制下,“問責”究竟有沒有實質性推動“地方政府履職”行為呢?本文抓住“多頭監管”體制中“問責”這一關鍵評價因素,探究其與“地方政府履職”這一因變量的關系。通過確立“資源投入程度”、“技術成熟程度”以及“地方領導的重視程度”三個控制變量,建立相關回歸分析模型。我們發現,在當下的“多頭監管”體制下,“問責”與“地方政府履職”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從而對“多頭監管”無法問責,無法推動地方政府履職的觀點予以了有力的回應。
那么在當前食品安全監管體制下為何還會屢屢出現官員瀆職以及食品安全事件頻發現象呢?本文的探究側重于橫向的部門權力配置,在食品安全監管中其實還隱含著縱向權力監管的探討。目前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屬于縱向的“過度分權”,如果遵循效率原則的話,食品安全監管無疑應該由中央政府垂直管理[21]。同時,在行政體制之外,仍然存在許多可以動員的監管力量,如行業協會、社會組織、公民個人等,他們作為多元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長期處于被架空與虛置的狀態,將會直接影響體制內部監管的活力與功效[22]。
[參考文獻]
[1]韓忠偉,李玉基.從分段監管轉向行政權衡平監管:我國食品安全監管模式的構建[J].求索,2010(6):155157.
[2]張海波,童星.公共危機治理與問責制[J].政治學研究,2010(2):5055.
[3]唐鈞,李丹婷.我國食品安全管理:特征、根源與政策建議[J].探索,2008(6):7478.
[4]食品安全法[DB/OL].(20090228)[20140409].http://www.gov.cn/flfg/200902/28/content_1246367.htm.
[5]劉亞平.中國食品監管體制:改革與挑戰[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4):2736.
[6]劉亞平.中國式“監管國家”的問題與反思:以食品安全為例[J].政治學研究,2011(2):6979.
[7]周清杰.論我國當前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的制度困局[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2832.
[8]譚德凡.我國食品安全監管模式的反思與重構[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7779.
[9]陳季修,劉智勇.我國食品安全的監管體制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0(8):6163.
[10]朱旭峰.服務型政府與政府機構改革:一個公共物品的集體供給理論[J].中國行政管理,2010(3):113117.
[11]March J G, Simon H A. Organizations[M]. New York: Wiley,1958,22.
[12]Cyert R, March J.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M].New York: PrenticeHall, 1963:12.
[13]陳龍波,趙永彬,李垣.組織冗余研究評述[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7(9):158162.
[14]李苗.知識管理環境下的組織冗余研究評述[J].科學大眾: 科學教育,2015(4):146.
[15]劉俊威.基于信號傳遞博弈模型的我國食品安全問題探析[J].特區經濟,2012(1):303304.
[16]溫志媛,張國強.食品安全問題原因淺析[J].時代金融,2012(26):103105.
[17]聶勇浩,顏海娜.關系合約視角的部門間合作:以食品安全監管為例[J].社會科學,2009(11):1320.
[18]SCHEDLER A. Conceptualizing Accountability[M]//SCHEDLERA,et al(.Eds.)The Self restraining State: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17.
[19]曹正漢,周杰.社會風險與地方分權:中國食品安全監管實行地方分級管理的原因[J].社會學研究,2013(1):182205.
[20]常存平,劉智勇.整合與協同: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改革的方向[J].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12(3):2427.
[21]賴詩攀.權力配置、問責與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監管履職:爭論與檢驗[J].公共行政評論,2014(1):120142.
[22]陳彥麗. 市場失靈、監管懈怠與多元治理:論中國食品安全問題[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5964.
(責任編輯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