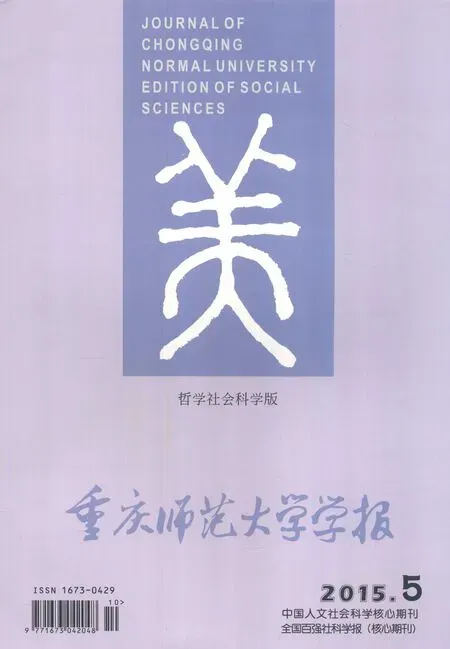宋代對外航海貿易貿易額估算及對經濟的影響
張尚毅
(重慶師范大學黨政辦,重慶400047)
宋代對外航海貿易貿易額估算及對經濟的影響
張尚毅
(重慶師范大學黨政辦,重慶400047)
宋代對外航海貿易發展較快,在其時的東亞乃至更大地區形成了一個國際貿易體系。在此體系中,宋不論是在航海技術還是大宗商品貿易方面都起著主導作用。宋代對外航海貿易可以分為北宋早中期和北宋晚期、南宋時期,不同時期對外航海貿易對經濟的作用不同,占財政的比重也不同,對此進行量化估算更能顯性地說明宋代對外航海貿易對經濟、就業等的拉動作用,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政府重視對外航海貿易原因。
對外航海貿易;進出口額;外貿乘數
中國歷史上對外航海貿易總體上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自漢代在西南沿海進行對外貿易以降,各個時代都有一些變化,但由于時代久遠,對這些貿易中的情況不甚了解,特別是對外貿易量的估算到目前鮮少系統的測算,無法進行量化的分析,這是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的一個被忽略之處。本文擬就宋代對外航海貿易特別是貿易額的大小作出一些估量,以期從定量的角度得到更為顯性的結論。
一、文獻回顧及問題提出
關于宋代對外航海貿易問題,研究得比較多。對于宋代為什么會出現繁榮的對外航海貿易,既有技術方面的探討也有區域經濟發展方面的研究。宋代對外航海貿易得益于科技特別是航海技術的進步,相比較唐及其以前,宋代航海技術比較先進。無論是對航海所需氣象知識的把握、航海所需的地文知識、天文知識的了解,都遠遠超越前代,特別是在指南針的使用、航海操作技術等方面,都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在那個時代基本上處于亞州乃至世界的先進水平,從而既使宋代成為航海船舶主要供應國,也使宋代航海進入了“定量航海”時代。[1][2]那么,為什么宋代航海貿易尤其是南宋時期航海貿易比較發達,其原因雖然有多方面,但是,人口壓力和確保維持政權的費用支出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同時,相對于北宋,其時的土地嚴重不足,進一步加劇了人口的壓力,迫使南宋政府必須開拓新的財源,而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政權的崛起,使宋代為了穩定政權,不得不開拓對外航海貿易,致使宋代對外航海貿易日益發展起來。[3]同時,由于科技的發展,宋代手工業產品的產量能夠滿足對外出口貿易的需要,如瓷器、絲織品的生產等。在糧食生產方面,通過大規模修建水利工程,推進精耕細作,糧食產量和比較價值都有了很大提升,形成了相當的規模,從而能為對外航海貿易提供可資交易的商品。[1][4]
可能更為重要的是,在當時整個國際貿易體系中,宋代由于國土范圍不如漢唐時期那樣廣大,而且在周邊包括航海所達的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實力相當的政權,使對外航海貿易出現了多國貿易體系,這點也如古希臘國際貿易體系的發展那樣,在東亞地區甚至更為廣大的范圍內出現了相對均衡的多國體系及世界貿易,而分立的東亞世界導致對外航海貿易成為宋貿易體系的一部分,同時,由于各國的實力在一個多國貿易體系中相對比較均衡,從而實現了各國之間的貿易正常往來,使宋在當時世界貿易體系中能夠實現交易的正常化。[5][6]這樣,宋代在比較成熟的多國貿易體系中,越來越成為亞州乃至更為廣大地區的貿易中心。這個地位的取得既得益于宋代科技的發展,又得益于宋代經濟中心的南移,不僅在國內形成了不少貿易中心,這些中心相當一部分也成為當時多國貿易體系的中心,從而使宋在實質上成為當時世界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1][6][7][8]而且,借助航海技術的發展,宋已經建立起了多條國際航海路線,這些路線不僅使航海路程變短,也更為快捷,這樣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航海貿易的效率,促進了航海貿易利潤的提升,為航海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充分的條件。[2][8]正是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在宋代進出口貿易額達到千萬貫以上。[9]此外,在宋代還出現了類似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商貿模式,發生了出資者與委托經營的分化,出現了分散航海貿易經營風險的對外貿易運行方式,從而使航海在經濟運行方式上成為可能。[10]
綜合上述論述可以看到,不管是就宋代對外航海技術的研究,還是對宋代航海路線、多國體系等的論述,都沒有或很少提到宋代對外航海的貿易額。有的雖然提出但只是簡單的猜測,而沒有比較確定的數值,而如果沒有相對確定的對外航海貿易進出額的數據,就很難說明宋代對外航海貿易情況以及對整個宋代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一些文獻中在論述對外航海貿易重要性時列舉了一些例證,但是,這些論述也還不足以構建起宋代對外航海貿易的重要作用。如《宋會要輯要·職官四》中列舉宋高宗提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但這個百萬是每一次航海貿易所得,還是一個時期航海貿易所得,抑或是一個財政年度航海貿易所得,卻很少論及。這也說明由于時代久遠,對于確切的數量化研究比較難以開展,但這也正是問題所在,亦是本文所要解決的問題。
二、對外航海貿易的估算方法
宋代航海貿易承唐遺澤,但又有所變革,特別是在推進市場經濟發展方面,更有了新的創新。不僅打破了唐及其以前的市坊制,把市場擴展到整個城市甚至于鄉村地區,而且進一步將市場擴展到整個中亞地區。可以這樣認為,宋代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市場貿易來打造經濟強國。早在宋開國不久,宋太宗“雍熙四年五月,遣內侍八人,資賜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綱資空名詔書三道,于所至處賜之”[11],說明對對外航海貿易的重視程度。這種重視對外航海貿易風氣的發展,使宋人有了更為普遍的利用對外航海貿易獲得收益的愿望。航海貿易對宋代的重要性,一系列文獻都可以佐證。特別是在南宋以后,航海貿易的重要性更為顯現,顧炎武就此提出:“宋室南渡后,經費困乏,一切倚辦于海。”[11]于此可見,宋代航海貿易對當時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南宋初期,由于人口大量向南方聚集,而土地又相對有限,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實現有效統治就成為宋朝政府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論者以為“宋代的人口與土地的關系情況不容樂觀,因此可知,宋代人口壓力由此而生”[12],而且,相關史料也表明,由于金、遼等一些少數民族政權的興起,使宋朝政府不僅于土地變少,而且傳統的北方貿易線路受阻,因而不得不開拓出新的貿易路線,這就是面向東南亞、中東等的對外航海貿易。
對外航海貿易因其豐厚的利潤而極富有吸引力。相關文獻表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海商王元懋一條船就運載了“沉香、珍珠、腦麝價值數十萬”的商品,可見其利潤之豐厚。也正因此,宋代對外航海貿易日益繁榮起來。雖然,當時宋政府對航海貿易實行許可證制度,屢次對違規航海貿易進行禁令,如在元祐五年(1090年)明確規定“即不請公據而擅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登、萊州界者徒二年”(《宋會要輯要·職官四》)。但從總體來說,還是有圖暴利者進行這類貿易的,如宋高宗就與大臣談及:“比累禁私商泛海,聞泉州界尚多有之,宜令沿海守臣常切禁止,毋致生事。”[13]從這段記錄可以看出,在泉州一帶的航海走私貿易已經傳到高宗處,可見海上走私貿易時間之長,否則是不大可能為最高當政者所知。同時,雖然宋朝廷對海上走私貿易處罰較重,但仍然長期存在著走私行為,說明航海貿易利潤豐厚致仍有鋌而走險者,甚至于有當地官員參與其中。
對于這些海上走私貿易無法進行估量,特別是歷經千年更難以測定,因此,我們的重點放在政府認可的航海貿易上。主要的方法是通過政府的收獲進行估量,并且根據各個時期不同的稅率進行測算,這樣可以得出一個相對較為準確的對外貿易數據。那么,宋代在航海貿易中到底可以得到多少收益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數據了,這是因為不管怎樣研究并提出宋代航海貿易對當時政府的重要作用,但如果沒有確定的量化數據,是很難說明問題的,這也是宋代以來無法對其航海貿易進行準確描述及研究的原因。由于相關史料幾乎沒有航海貿易額的準確記載,因此,我們只能通過間接的方法進行估算。由于即使在宋代的各個時期貿易量都是變化的,而相應的稅率狀況也是一個相對變量。可以假設航海對外貿易量為Q,稅率為R,由于當時并不存在累進稅,這樣問題就相對簡單一些,并假設這個稅收額為P,那么,可以得出Q=P/R。當R取不同值時,則可以通過簡單的分類相加的方式進行。因此,解出宋代航海貿易規模問題,必須先知道Q是多少。根據現有文獻,至少可以從各個時期的航海貿易中稅收規模得知,具體可以得到這樣一些數值,“皇祐中,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有五十三萬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萬”[14]140。相關研究認為,兩個時期的市舶收入分別為五十三萬貫和六十三萬貫,同時也說明對外航海貿易具有一定的可持續性。相關記載還有紹興年間,市舶司“抽解與和買計之約得二百萬緡”(《文獻通考·市傘考一》)。這是因為雖然對航海貿易各類收入的名稱叫法多樣,如抽解、博買、禁榷、和買、格納等,但總體上來說都是稅費制度,可以合并為稅收,所以論者以為“抽解是宋代對外國商貨征收的一種進口稅”[15]146。“博買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進口稅”[15]149,“進口貨物的禁榷方式和博買一樣,所以它實際上是特殊的博買,也具有變相進口稅的性質”[15]150。考慮到當時并沒有征收累進稅,只是就貨物的價值相對簡單地按比例征稅,因此,對于這些進口稅可以進行一定的歸并,并且通過對宋代征稅的情況,可以設定形成一定的稅率空間,進而推論出當時的對外航海貿易額。
那么,當時的稅率到底是多少呢,不同的時期有著一定的差距。從現有史料來看,從10%到50%不等,絕大部份正常年份在10%至20%之間。如淳化二年(991年)就有“止齋陳民曰:是時市舶雖置司,而不以為利。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然利殊薄”(《文獻通考·市傘考一》)的記載,這個稅率應該是20%,但從獲利殊薄來看顯然是客商來源過少,而就其根本在于稅收過高。宋仁宗時有記載“凡蕃貨之來,十稅其一”的制度,那么這個稅率應該是10%。而在宋神宗時期則進行了新調整,“抽解之法十五取一”,則稅率為5%。至于南宋初期,由于各方面所需甚多,則又實行了“擇其良者如犀象,十分抽二分”,這部份稅率為20%,但粗細分開,對于粗貨“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正由于此,因而有“舶戶懼買抽解多,所販止是粗色雜貨”[11],由此看來,綜合稅率應該低于10%。之后,如隆興二年(1164年)則又進行了調低稅率的辦法,“十分抽解一分”,這個稅率是10%。當然,也有的時候過于偏高,如在隆興年間曾一度實行“內細色五分抽一分,粗色貨物七分半抽一分”的稅收政策,但其結果是“舶商不來”,這與《宋史·職官志》的指導思想——“提舉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是相違背的。從這些情況來看,對外航海貿易中的進口稅率大體上在5%—10%之間。其間,也有稅率達到20%甚至30%以上者,但由于經濟上無法實現贏利的目標,遭到客商的普遍反對。這種高稅率能夠實施的時間都不長,對正常航海貿易影響不大,因此,可以不將其納入到對整個航海貿易額的估算之中。
那么,博買的情況又是怎樣呢?相關文獻顯示在三成到五成之間,但這里的利潤有多少呢,由于對當時的買賣情況不清,無法計算出政府博買獲利情況,但是卻可以從相關資料進行推算,也就是說政府的征收稅的稅率在能夠實施再生產的合理范圍內,具體來說就是當時客商能夠持續進行航海貿易的需要。基于此,當在隆興二年(1164年),南宋政府改變高比例抽解和博買后,確立了“十分抽解一分,更不博買”,那么,抽解與博買后的綜合稅率應在10%是合理的了。至于禁榷,查閱相關史料,雖然禁榷品種較多,但是真正收益較大者在于乳香,如相關史料還表明,在南宋紹興年間,航海貿易中僅榷香就達上百萬貫,如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行在、建康和鎮江三務場香礬收入達1099108貫,在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中這三個榨貨務的香礬收入達1195854貫。以至于有市舶官可以“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宋史·食貨下》)。至于和買,由于相當一部分屬于強買性質,因此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這也是一般經濟規律所至。所以,從宋代航海貿易的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航海貿易的稅率多數年份可以確定為10%左右,一些相對較短的時期可能出現較高或較低的稅率狀況,不論對于政府來說還是對海商來說都難以形成均衡點,因此,我們基本上可以確定正常情況下宋代航海貿易的稅率為10%。這樣,可以合理地推算出航海貿易進口額的情況,但出口貿易額又有多大呢?由于沒有出口貿易的稅率史料,無法進行這樣的估算,但考慮到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大多是易貨貿易,因此,可以以航海貿易的商品在宋時的價值作為衡量估算出出口貿易額的情況。這里,就不能簡單地假設進出口貿易額相等,這是因為對于不同的時間地點來說,宋代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差距很大,以進出的香料等商品為例,東南亞的原產地與當時的中國差距非常大,相對應的瓷器等商品在中國與外銷地也差距很大,因此,在估算方法上不能簡單進行假設兩者相等,而必須將這些商品放在同一個時間和地點來進行估算,文中將這個估算的地點與時間確定為宋朝。
三、航海貿易進口額的估算
當進口稅率確定以后,就可以推算進口額。那么對外航海貿易進口額有多少呢?根據計算,皇祐中的綜合收入約為53萬貫,其航海貿易額當為530萬貫。至治平中又增10萬的情況下,航海貿易進口額當為630萬貫。紹興年間,在全國各港綜合收益合計達200萬貫的情況下,航海貿易進口額則應為2000萬貫。值得注意的是,漆俠先生在《宋代經濟史》中對市舶收益情況作了論斷,認為“市舶收入約占百分之四五,到南宋中葉6000多萬緡總收入中,約占3%左右”[16]1061。這個觀點與黃純艷大體相當。相關史料表明,北宋初期整個財政收入約1600萬貫,神宗時期(1067—1085年)為6000萬貫,高宗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為6000萬貫,淳熙十四年(1187年)為8000萬貫。對應來看,治平時期與神宗在位的時間相差無幾,紹興年間也就是宋高宗在位的時期。以這些相近年份來看,按照漆俠先生論斷中市舶收入占年財政收入的比例分析來看,那么,紹興年間市舶收入應在180—240萬貫之間,這個估算與相關史料是基本一致的。又治平時期市舶收入《宋史》中有明確記載為53萬貫,治平距離神宗在位時間很近,這個數據應該可用于神宗時期,那么按漆俠先生關于市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計算,當為180—240萬貫,兩者出入很大,這是為什么呢?筆者認為市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在北宋早中期與北宋晚、南宋早中期不同。南宋時期由于人口數量大而土地相對較少,因此,更為重視商業尤其是航海貿易,而漆俠先生的市舶占財政的比例與北宋晚期和南宋時期接近,因此,有必要把北宋與南宋區分開來。按治平(1064—1067年)時期市舶收入為53萬貫,神宗時期財政收入為6000萬貫計算,市舶收入占財政的比例當為0.8%,也就是說對于北宋早中期大體上可以以此進行計算。
那么,對于這種情況又如何解釋呢,主要原因在于當時航海技術的發展。北宋繼唐以后,整體上航海技術不可能在短期內有大的發展,相關文獻表明唐代航海主要用的是蕃船,說明唐代航海技術相對其他東南亞包括中東一些國家來說,還是比較滯后的。那么,到宋代以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還是維持這種情況,一直到北宋晚期以后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了,不僅宋人用自己的船舶,而且相關貿易也大多用了宋代的船舶,正如李約瑟所認為的那樣,“在唐代,中國的乘客大多數乘外國船只;而在南宋和元代,歐洲的旅行者卻喜乘中國帆船”[1]389。這個時期對于航海至關重要的指南針技術也成熟起來,如朱彧1119年在《萍洲可談》中記有“陰晦觀指南針”,這些記載都在北宋晚期。南宋時期,趙汝適《諸蕃志》中也有“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的記載。難怪李約瑟提出“《夢溪筆談》是最先描述羅盤針的著作之一”[1]290,大體上也就是這段時期。而擁有制造先進技術和航海先進技術的北宋晚期和南宋時期,對外航海貿易相對比較發達也就無足奇怪了,這也進一步證明了前面我們所提出應該區分北宋早中期與北宋晚期、南宋時期航海貿易收入所占財政的比例,而在南宋時期當為漆俠先生所言的3%,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出宋代各個時期航海貿易額了。
那么,宋代各個時期的財政收入情況是怎樣的呢?前面,我們已經給出宋三個時期的財政收入。事實上至北宋晚期,每年的財政收入達到6000萬貫,而南宋時期常年超過10000萬貫,最高年份達到12000萬貫。按此計算,在南宋時期,航海貿易收入將達到300—480萬貫,那么,相對應的航海貿易額當在3000—3600萬貫之間,這只是宋晚期后的進口貿易額。之前,按宋初財政收入為1800萬貫的0.8%計算,其進口額為14.4萬貫,這與當時的對外航海貿易總體情況是相當的,也進一步說明有必要將宋代晚期以后與之前進行分期估算。如果引用一些新研究成果,認為有宋一代僅香料的進口所得就達到宋政府財政收入的10%的話,[17]顯然進口額就遠遠高于上述數據,而整個進出口額將會有一個大的提升,那么這是否合理呢。通過前面的分析,利用現有史料所給出的航海貿易的收入,以及相近年份財政收入比較,這種情況應該不會出現,也就是說宋代整個航海貿易收入等于或高于財政收入的10%是有些夸大了。漆俠先生在《宋代經濟史》中對榷香進行了專門論述,得出的收入比例應該比較正確,那么,對于宋代航海貿易進出口額應該在我們所得出的范圍內,或者略高一些是比較合理的。
四、航海貿易出口額的估算
宋代對外航海貿易中出口占據了重要地位,在對外航海貿易中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絲綢、瓷器和漆器,甚至還有書籍。基于此,研究世界貿易史的學者如珍妮阿布—盧格霍德(Janet Abur Lughod)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間的世界體系》一書中就認為,13世紀的歐亞世界包含著一個巨大的貿易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最主要的發動機就是中國,因為中國不僅是香料等的主要消費國,也是陶瓷等大宗熱銷商品的出口者。[6]如果中國在宋代是東亞甚至更為廣大地區經濟貿易體系的發動機,那么,中國的出口額必然不少。而且,從宋代銅錢大量外流甚至到不足以滿足國內流通需要,不得不使用紙幣這種情況來看,宋代確乎在世界貿易中處于十分重要地位。從當時一些與中國往來的國家可以看到,有宋一代來華朝貢的國家有26個,這些朝貢的國家大多與貿易相關,如熙寧十年(1077年)于闐國貢使攜帶的貢品僅乳香就有31000余斤,市價達44000余貫。[24]2688而在元豐三年(1080年)又進奉乳香等達10萬斤,可見朝貢在宋代這個東亞貿易發達的情況下,更大程度上是商業貿易。[18]2897如果把這些國家看作是來中國進行出口貿易的國家,這種情況是可能的,有關史料表明不少國家就是以這種方式與中國進行貿易的。但是,當時中國政府到達的國家則多達45個之多,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宋對外出口的目的地國家相對較多。據《諸蕃志》記載,僅泉州一處港口銷往海外的絲綢就達20多個國家和地區,相比較而言,雖然進口的品種較多,僅以紹興三年(1133年)十二月十七日戶部呈給皇帝關于進口貨物規定的公文中就有商品上百種,但除金銀外大多是一些包括香料在內的土特產,而很少有大宗商品,更少有如瓷器等工業產品,這些情況也說明珍妮阿布—盧格霍德的論述是正確的,在當時的世界貿易中大宗商品出口主要是中國。
當然,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并不僅是瓷器、絲綢等這樣一些大宗商品,還有不少其他商品,據日本學者藤原明衡《新猿樂記》統計,僅日本進口“唐物”就達41種,那么,在這些唐物中肯定也有其他的商品,只是瓷器、絲綢等是大類而已。正如今天在對外貿易中所看到的情況相類似,原材料出口國始終處于相對較弱的地位,而大宗工業產品的出口國大多在對外貿易中處于強勢地位,宋代也不例外。由此可以看到,在宋代航海貿易中雖然大多從進口貿易中獲取稅收以利財政所用,但是,由于出口額度較大,而宋代又大量依靠商稅,這種商稅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域外市場,也就是說宋代通過出口貿易,實則推動了國內手工業的發展,進而促進了財政收入的提升。宋代各個時期商稅所占比例是較高的,龔鼎臣曾說:“士熙道管三司商稅案言:天下諸商稅錢,每歲二千二百萬貫。”王者也有相類似論述,認為“到仁宗慶歷時增加到二千萬貫,成為當時財政僅次于田賦的一項重要收入”[14]140。一些年份商稅占到了整個國家財政收入的30%左右,由此也可見航海進出口貿易對當時國家經濟的作用。但是,宋代出口額到底有多大呢?關于這點我們難以從商稅中簡單地分出出口稅收占比情況,事實上從現有史料來看,包括對此的相關研究材料,都沒有收取出口稅的文獻,因此,無法利用進口相類似方法從稅收推算出航海貿易出口額的大小,而且現有文獻也沒有直接給出出口額大小,只有一些推理性的結論,如《諸蕃志》、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英人巴茲爾·戴維遜《古老非洲的再發現》、《嶺外代答》、《云麓漫鈔》等論著對航海貿易的路線圖、考古發現的估計當時已有中國手工業產品如瓷器甚至銅錢等銷售到東亞、中東乃至遙遠的非洲,但對于出口額到底有多大卻無定論。
由于宋代中國在東亞乃至更大地區的多國貿易體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而中國出口的大宗物質又主要是工業品,可以知道中國的出口必然是一個比較大的額度,但這并不等于說出口額就一定大于進口額,如今天世界貿易一樣,工業相對發達國家不一定就是順差,宋代也不一定就是順差,如果這樣也就不可能輕易得出結論說出口額一定大于進口額。但是,從相關文獻還是可以發現一些端倪。由于當時很大程度上是易貨貿易,那么從易貨貿易的情況也許可以推論出宋代的出口貿易額。相關文獻表明,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商品“每十貫之數可以易蕃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商品之間價格整體估計應該為一比十。從當時長途販運式的對外貿易來看,正常情況一般都是通過來往買賣商品,即在賣出從宋生產的商品后,將帶回相應額度價值的進口貨物,各國商人大都如此。舉例來說,如果商人從中國出口一萬貫的瓷器到東南亞國家,必然會帶回一萬貫的香料等商品到中國,而這個一萬貫的香料到中國后將會實現十倍的價值。按商品在中國的價值為計算點,可以從進口額來推算出出口商品的額度。前面已經估算出的進口商品的額度也是以宋的價值所計算的,按宋代中國出口商品的價值只能達此十分之一來計算,則出口商品的價值應該在300—360萬貫之間,兩者加總起來以宋時中國的價值來計算的進出口額當在3300—3960萬貫之間,這個估計高于黃純艷所估計的2000萬貫,但易貨貿易同一地點價值是相同的。反之,如果按宋朝外的市場價值進行估算,則會降低進口額的價值而增加出口額的價值,但兩者相加也是一致的。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宋代航海進出口貿易中到底是順差還是逆差,論者認為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對外貿易是出超,[19]也就是順差。這種出超很大程度體現出收益,既包括國家稅收方面的收入也包括具體商人的收益。相關文獻表明宋代商人一年期進出口的收益十分可觀,如南宋大將張俊以五十萬為本,“愈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還有“泉州楊客為海賈十余年,至貲二萬萬”。泉州巨商南蕃回回出身的佛蓮,發海舶達八十艘之巨。宋高宗也曾講過,“市舶之利,頗助國用”[13]。可見不管是國家還是商家都獲得了航海貿易之利,這當然是出超的結果。而這個出超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手工業產品與原料價格的差距,這也啟示了一點,就是宋代中國之所能主導東亞乃至更大范圍的進出口貿易,出現出超以資國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技術與經濟的發展,一如約瑟所說,“中國的技術發明在公元后的十三個世紀中,曾不斷地傾注到歐洲,正如后來的技術潮流流向東方一樣”[1]543。也正由于此,自北宋晚期以后,宋代的航海貿易日益興盛起來,進而直接推動宋代經濟的增長。那么,對外航海貿易對出口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對此可以假設外貿乘數為一個固定值,根據前面的計算,對外貿易出口額對宋代經濟可產生出口額倍加的經濟增量,這也是為什么宋代手工業得到發展的重要原因,因為,當時中國的手工業面向一個供不應求的東亞乃至更大的市場,于此,也可見外貿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是比較大的,所以論者以為“宋代的出口貿易不僅是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對解決就業問題亦發揮了積極作用”[19]。對此,斯波義信也明確提出,近海地方“則人口的百分之十至二三十與水運業有關”,“人們為為了擺脫山村特有的落后狀態,積極地投身于交通和商業,成為社會分工之環而謀求自立”。[10]如果再考慮到對外航海貿易商品對經濟的拉動乘數效應,那么,宋代對外航海貿易就不僅在運輸、商業領域提供了就業,而且在手工業的發展方面既創造產值又提供了就業。
[1][美]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
[2]孫光圻.宋代航海技術綜論[J].中國航海1984,(2).
[3]王娟.宋代與南洋地區航海貿易興盛新探[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4).
[4]宋燕鵬.中國前工業化時代的背景[J].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
[5][美]約翰·希克斯.經濟史理論[M].北京:商務出版社,2010.
[6]賈志揚.宋代與東亞多國體系及貿易世界[J].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2).
[7]楊國利.兩宋時期經濟中心南移的思考[J].蘭臺世界.2014,(10).
[8]孫光圻,逄文星.宋代中國與東南亞的航海貿易關系[J].中國與周邊家關系研究.2009,(9).
[9]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10][日]斯波信義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M].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
[11]顧炎武.海外諸蕃人貢互市[A].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20)[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2]歐燕飛.宋代人口壓力及其對策[J].科教導刊.2011,(7).
[13][宋]李心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6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4]王者.中國古代財政史[M].北京:北京財貿學院出版,1981.
[15]王杰.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管理史[M].大連: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4.
[16]漆俠.宋代經濟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7]劉迎勝.絲路文化(海上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1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85)[Z].北京:中華書局,1979.
[19]王偉超.試論宋代經濟三駕馬車[J].開封大學學報,2012,(1).
The Estimation of Foreign Trade Volum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Economy
Zhang Shangyi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the Song Dynasty foreign maritime trade development faster,at that time in East Asia and the greater region formed 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trade,in the system of song whether in marine technology and commodity trade plays a dominant role.Foreign maritime trade in Song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arly mid and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differ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foreign maritime trade on the economic role,accounted for the proportion of finance is different,this quantitative estimates can explicitly illustrate the Song Dynasty foreign maritime trade on economy,the pulling effect of the industry,which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Song government attach importance to foreign maritime trade.
foreign sailing trade;amount of import and export;foreign trade multiplier
K24
A
1673-0429(2015)05-0037-07
[責任編輯:劉力]
2015-07-08
張尚毅(1966—),男,重慶師范大學黨政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