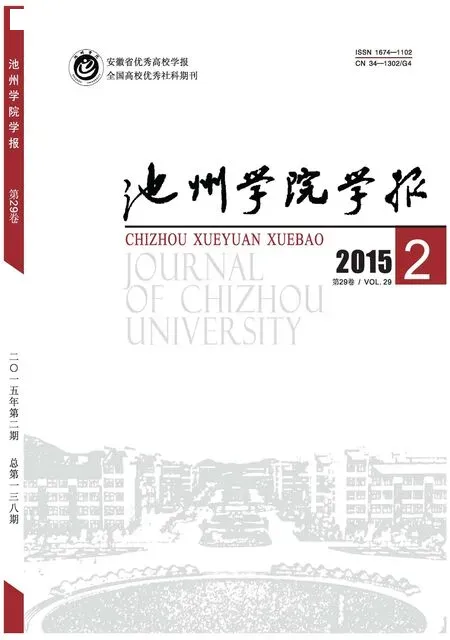方東美論道家之“道”的四維呈現(xiàn)
施保國
(嘉應(yīng)學(xué)院 社會科學(xué)部,廣東 梅州514015)
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是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在這方面,中國現(xiàn)代哲學(xué)家一般有意識地抓住認識過程中的某個環(huán)節(jié),進行系統(tǒng)闡釋,論證自己的哲學(xué)結(jié)論,因此,他們的哲學(xué)具有一定的思辨性和理論性。如梁漱溟將直覺夸大,使之神秘化,以直覺主義為途徑建立生命本體哲學(xué);馮友蘭以知性概念為基本點,拓展論證“理世界”本體的潛存性;熊十力和賀麟以理性為基礎(chǔ),結(jié)合非理性,得出“心與物不可分”[1]30的抽象本體。而宗教家、哲學(xué)家方東美先生多次主張宗教亦哲學(xué),在宗教和哲學(xué)之間走一條融通之路,他以道為超越本體,抓住道的“非理性與理性”相結(jié)合特性,構(gòu)成其機體主義哲學(xué)根本。在此道的精神指引下,道家之“道”的內(nèi)涵表現(xiàn)為道體、道用、道相、道征融為一體。
1 論道體——道的本質(zhì)
道家最初被認為是道德家,自班固《漢書·藝文志》始稱其為道家。道家的共同特征是以道本體為核心的學(xué)說。道本體主要從天地始基、最基本的自然法則和無為而治的人治理念等方面展開論述。先秦以完整的《老子》、《莊子》為典籍的道家同儒家一樣是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影響最大的學(xué)派。盡管在西漢司馬遷編寫《史記》時,它的源流一直模糊,但絲毫不隱飾老莊哲學(xué)的精彩和光輝。從主流上看,道家是中國古代哲學(xué)發(fā)展的重要契機,同儒、墨、法一起構(gòu)成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思想框架的統(tǒng)一體,以自己獨特的本體建構(gòu),推動著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思想文化的發(fā)展。
對于道家的道體而言,方東美認為,一方面,道為無限真實存在之太一或本原,是宇宙的本體,是一種最高范疇的符號,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佛,伊斯蘭教的真主,道教的真人、仙人等,在一切存在之先,也就是說,是一種“有”[2]。而另一方面,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此句揭示了一個超本體論或“無”的問題,指出“無”為優(yōu)先于“有”屬于變易現(xiàn)象界之動態(tài)本體論。就“道體”來說,此“道”具有即“有”即“無”的兩種屬性,既是無限的真實存在實體“有”,又是“難以言說”的本體“無”。方東美概括出,老子至少從六個方面之“有”來把握“無”,也就是以這六個方面說明道體是“有”與“無”的統(tǒng)一體:
第一,道宗——道為萬物之奧、萬物之宗,淵兮不可測,其存在應(yīng)該是在上帝之前。方東美認為,“道宗”來源于“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德經(jīng)》第四章)等表述。老子在春秋時代,經(jīng)歷了殷商之際的西周,當(dāng)時古代神秘的宗教已經(jīng)快死或曰哲學(xué)化時,道家出來拯救,變神秘的宗教為理性的哲學(xué)。老子的“道”等于一個哲學(xué)上的“上帝”,可做宇宙的本體,此本體在宇宙之先,用老子的名詞說即“象帝之先”。方東美表示,此存在甚至在上帝之先,可以這種源頭“宗”之“有”來把握道體不可測之“無”。
第二,道根——道為天地根,其性無窮,其用無盡,視之不見,但萬物都是因之而誕生的。方東美認為,此“道根”的說法源于“谷神不死,是謂玄牡,玄牡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道德經(jīng)》第六章)等表述。這里的道為“天地根”,說明道的無限性,因為天與地都是無窮的,展開來在空間里面代表的是無窮的存在,在時間里面代表無窮的變化,如道有限就不能產(chǎn)生無限的天與地出來。所以,方東美認為,不能以平常的形容去理解、也不能拿自然界的一切屬性去體驗。道為其大不可言喻的一種作用,這樣,才可“生一”、“生二”、“生三”、“生萬物”,因此,以道根之“有”可達到對道體之“無”的理解。
第三,道一——道為元一[3]267,為天地萬物一切存在之所同具。這種思想主要源于“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其致一也”(《道德經(jīng)》第三十九章)等表述。老子視道為“元一”,將之分配給宇宙里一切具體的存在,天、地、神等一切精神體都得到了“元一”,因而得以完善。谷之所以能夠空虛,也是得“元一”;侯王之所以能統(tǒng)治天下,使國家不崩潰,也是分享這種精神;“萬物各自得一以為一”,正是因為分享了宇宙里大道的統(tǒng)一本體。因此,方東美認為,可通過共同“一”之“有”來理解道體之“無”。
第四,道型——道為一切活動之唯一范型或法式。其主要源于“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誠全而歸之”(《道德經(jīng)》第二十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道德經(jīng)》第五章)等表述。老子認為“大道”是一種秘密,微妙之處說不盡。從此方面說此面,從彼方面說彼面,第三方面說第三面,幾乎所有的文字都用來說明這個秘密,也都只能說了一半,故老子用名詞“曲則全”來表示這個情況。只有拐彎抹角的“曲”來表達無盡的道的秘密,拐彎抹角的在那個地方窮盡它的秘密,可知道從一方面說是直的,又是彎的,既是真實的,又是空虛的;所得到的都是一套相互矛盾的說辭,再多的言辭也無法說盡那個大道。方東美以西方意大利畫家郎世寧為例說明,西洋人畫山水、人物所運用的透視法都是單一透視法,難以取得整體的效果。而中國畫,從超越的觀點看,可以大為小以小為大,以凌空、空靈的觀點俯視宇宙的一切,以藝術(shù)家的精神使之和諧統(tǒng)一,實行的是老子的“曲則全”這句話的啟示,達到“全而歸之”,把宇宙萬象分歧的狀態(tài)以哲學(xué)的最高智慧精神統(tǒng)攝起來。此即“道為一切活動之唯一范型或法式”所表達的思想,即道為一個總體,統(tǒng)攝了內(nèi)部一切分析的構(gòu)造,將之化成對稱又和諧的不可分割的一體。因此,方東美認為,可通過分析構(gòu)造之“有”的理解來把握整體范式之“無”。
第五,道無——無象之象是為大象,抱萬物而蓄養(yǎng)之,如慈母之于嬰兒,太和,而無恙。這種概念主要源于“執(zhí)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道德經(jīng)》第三十五章),“為天下谷,常德不離,復(fù)歸于嬰兒”(《道德經(jīng)》第二十八章),“守其母,沒身不殆……無疑身殃”(《道德經(jīng)》第五十二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精之至也……和之至也”(《道德經(jīng)》第五十五章)等表述。“執(zhí)大象天下往”說的是大道在宇宙萬物里面如萬物的母體,宇宙一切現(xiàn)象都落入這個大熔爐里陶融,在此陶融之下,可將實相變成虛相,再“透過一切虛像把握一切真相的統(tǒng)一”[3]272,“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fù)歸于無極”(《道德經(jīng)》第二十八章)。方東美指出,此以大道為天下母體的思想,如柏拉圖在《饗宴篇》里描述的那樣:人們在經(jīng)歷了一切下界、中界、上界、丑陋的世界、相對美麗的世界外,還要繼續(xù)探索現(xiàn)象世界上面的永恒世界里的絕對的真善美的價值,回歸母體。以上界的絕對真善美價值,投向下界,但下界無所容之。在此情形下,柏拉圖再透過幻想——一個拿彩帶的舞者,以委婉曲折的彩帶,化宇宙為一大的圈套,為宇宙的容器即牛頓物理學(xué)所說的“絕對空間”,于是,宇宙的下界為空虛的太空籠罩著,然后創(chuàng)造主將宇宙上界的真善美運輸過來,轉(zhuǎn)移到下界,使空虛無價值變?yōu)橛袃r值的真實。可見,老子所謂的以道為整體的辦法,可實現(xiàn)柏拉圖的“幻想”。所以,可抱萬物之“有”而蓄養(yǎng)大象之“無”。
應(yīng)該說,老子首先提出有無、體用概念是自王弼注老后被突出的。自此有無、體用概念于中國思想界影響深遠。王弼“轂所以能統(tǒng)三十輔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無統(tǒng)眾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道以無形而為,成濟萬物。從事于道者,與道同體,故曰同于道。”(王弼《道德真經(jīng)注》)王弼以為,無形無為是道之體;而成濟萬物是道之用。錢穆認為,《老子》言道,無形無名,唯其無形無名而確有此道,故王弼特為安一體字,此之謂道體,是謂宇宙間確有此道,非可謂確有此無為[4]360。
第六,道極——各復(fù)歸其根,道為萬物之最后歸趨,源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fù),夫物蕓蕓,各復(fù)歸其根。歸根曰靜。是曰復(fù)命,復(fù)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道德經(jīng)》第十六章)等表述。這段話讓我們知道大道的各方面,然后再把大道當(dāng)做最后的歸宿。方東美指出,以西班牙文學(xué)《堂吉訶德》來看,堂吉訶德這位國際人物,全身都是活動的動作,但都是荒唐大觀,只是堂吉訶德本人看不見,自以為超脫解放了卻不知在另一層的荒唐里面討生活。只有大哲學(xué)家、藝術(shù)家會告訴那些經(jīng)歷許多荒唐大觀后的人,停止到“致虛極,守靜篤”,讓各種鬧劇歸到實際的歸宿,從所謂的追求中覺悟開來。如老子說的:“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fù),夫物蕓蕓,各復(fù)歸其根”[3]275,只有找到歸宿時,一切憤怒、紛爭、騷擾,才會變作精神的寧靜。任何堂吉訶德英雄式的創(chuàng)造活動待精力發(fā)揮完之后,無不復(fù)歸于道,即所謂“復(fù)根”,而藉此,人們可安息、含蘊于永恒之法相中,成就不朽的精神。方東美認為,可通過此蕓蕓之“有”體會虛極歸宿之“無”的真諦。
除了以上六個方面從“無”和“有”兩個維度闡釋了老子的道體外,方東美還簡略分析了其“無”、“有”統(tǒng)一之道體概念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一是理性認識對感性認識的提升,對世界本原的認識克服了現(xiàn)象界認識的膚淺與尷尬;二是對宗教的懷疑,在春秋時代,我國上古宗教由產(chǎn)生到高漲到逐漸淡出,人們逐漸覺察出中國古代宗教的欺騙性;三是將道之“無”作為“天地根”、“太一”,以無窮的作用和屬性來把握它,才可以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創(chuàng)生“有”的過程理解清楚。在“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的境界中,萬物都分享大道的統(tǒng)一本體,以大道為萬物的母體,將宇宙萬有的一切實的現(xiàn)象界變?yōu)樘撓螅偻高^虛象把握一切實象,最后以大道為宇宙萬有的歸宿。以老子的道來看宇宙萬有的變化,從本體論方面將宇宙萬有視作慈母的子女,在歸根的最后回歸到大道統(tǒng)一體以享受精神的歸宿。
軍隊的一切工作都應(yīng)以戰(zhàn)斗力為根本標(biāo)準(zhǔn)。軍隊院校文化建設(shè)是軍隊建設(shè)的一項重要工作,堅持戰(zhàn)斗力標(biāo)準(zhǔn),必須注重營造“一切為打仗”的戰(zhàn)斗文化氛圍,并將其作為立校之基常抓不懈。
2 論道用——道的功用
在討論過大道精神的歸宿、本身統(tǒng)一的本體之后,再來討論宇宙發(fā)生論的問題,即所謂道用。道用,指的是道具有無限偉大的作用與功能,道為周傅萬物、遍在一切之功用而取之不竭者。方東美指出,道的顯發(fā)方式有二:一曰“退藏于密,放之則彌合六合。”二曰“反者,道之動”。蓋道一方面收斂之,隱然潛存于“無”之超越界,退藏于本體界“玄之又玄”,不可致詰之玄境,而發(fā)散之,則彌貫天地宇宙萬有。茲所謂有界者,實乃道之顯用而呈現(xiàn)為現(xiàn)象界也,故可自道而觀察得知。故曰:“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5]242-243。
根據(jù)“反者道之動”(《道德經(jīng)》第四十章)的精神,就“無之以為用”來看,要從“有”追溯到根源即“無”,視“無”為大道本體,就產(chǎn)生了第二個運動,即從很高的哲學(xué)智慧的觀點,再一層層下來,追問現(xiàn)實世界形成及宇宙發(fā)生論的問題。自“無”而至“有”,從下回向看,大道表現(xiàn)它的作用,體現(xiàn)為現(xiàn)象界,那么,現(xiàn)象界與本體界關(guān)系如何呢?老子以人類最親切的母與子的關(guān)系來說明。現(xiàn)象是從本體里面流露出來的精神,二者密不可分。在此情形下,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jīng)》第四十二章)。
方東美指出,道家的精神同儒家的精神幾乎是一致的,即從無至有,從有至更大的有,這是“有之以為利”,即老子所說的“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德經(jīng)》第四十二章)。儒家講中和,即將宇宙的奇數(shù)與偶數(shù),宇宙剛強的陽的作用同陰柔的協(xié)和作用,合并起來,成為宇宙的廣大和諧性。創(chuàng)造力的倉庫一旦打開,便向下流注創(chuàng)造的作用,從上往下,從高往低,如機械力、電力、熱力逐漸減少一樣,由高向低,最后為廢棄無用,就要如老子說的“歸根復(fù)命”,在宇宙萬象里找著天地之根和大道的根源。在全有界,即動態(tài)化育歷程中之現(xiàn)象界,其所具之能由于揮發(fā)或浪費而時有用竭之慮,所以,現(xiàn)實世界中人類則舉債告貸,向銀行貸款求濟,同樣,當(dāng)下有界也需求援于“無”之超越界,以取得能源充實,所謂“夫唯道,善貸且成”(《道德經(jīng)》第四十一章)。或者說,道家認為在宇宙向下到窮途末路時,發(fā)現(xiàn)另外一個“宇宙的銀行”,回過頭來向大道稱貸,大道便把貯藏的力量向下貫注,人立刻又振作了,從消極的、頹廢的生命情操,步入積極的“常善救人,使人無棄人;常善救物,使物無棄物”(《道德經(jīng)》第二十七章)[8]279。
所以,此大道流行,有兩個途徑:“順之,則道之本無,始生萬有;逆之,則當(dāng)下萬有,仰資于無,以各盡其用”[3]279。此話說明的是大道向上與向下在本體與現(xiàn)象之間做雙軌運動,如王弼理解的那樣:“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此解釋“反者道之動”為“無之以為用”,又說“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3]279,此說明上回向的作用。方東美指出,“無”、“有”在道用即道的實現(xiàn)過程中是統(tǒng)一的,并不像東晉儒家如裴頠所誤解的那樣,認為道家是“貴無賤有”。莊子在多處明確說老子的精神“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空虛以不毀萬物為實”,道家在“貴無”的同時并不“賤有”,也就是說,此道用是無窮的。
3 論道相——道的意象
從本體和作用兩個方面來看道之性相或道之屬性與含德,即為道相,分為兩類,一為天然性相,一為人為性相。天然的性相,為大道的本性,大道本身所涵養(yǎng)的本性,含一切天德,表現(xiàn)為“無”的方面;“意然屬性”,通過人的主觀理解而賦予它的一種屬性,是大道顯發(fā)出來之后透過人的委婉曲折的了解然后加給它的屬性,表現(xiàn)為“有”的方面。方東美認為,天然之相屬于道體是無待的,只就永恒面而觀之,此本性是真實而無限的,包含以下幾點:
首先,“道無乎不在”。道的天然性相在無界中即用顯體,在有界中,即體顯用,且體不離用,故道體一思。大道是兼綜有無,涵蓋本體與現(xiàn)象界即道體與道用兩個方面,形成統(tǒng)一的整體。道體為超本體論里面所講的“無”,道用就是從本體論里面看出萬有存在。因萬有存在只是本體界向下流注所展開的現(xiàn)象,可能有缺陷和顯示出衰弱的趨勢,故要設(shè)法將之提升到原來所出的根源里面,去補救它的缺陷。大道是兼綜體用而囊括萬有,從中可以看出本體的原來面貌以及作用所顯現(xiàn)出來的現(xiàn)象。
其次,“無為而無不為”。所謂“無不為”,是就“有之以為利”而言,是宇宙萬有在現(xiàn)象界的一切活動[3]282。此“無不為”走到窮途末路的時候,就要返本歸根,就是“無為”所說的“致虛極,守靜篤”,回到寧靜的本源和永恒的境界。二者的結(jié)合便形成現(xiàn)象界“有”的活動與本體界“無”的根源的結(jié)合,所謂“主之以太一”。
再次,“生而不有,為而不侍,長而不宰”,“以無事取天下”、“功成而弗居”[3]282。老子認為,大道把宇宙創(chuàng)造出來后就讓宇宙本身自由自在地去變化、發(fā)展、創(chuàng)造而不做主宰,功成而弗居,宇宙萬有從道體流溢出來之后,完全任由自由發(fā)揮妙用,所以這樣的大道真正代表了高超的自由精神。不似宗教上的創(chuàng)造主,站在超自然界的立場創(chuàng)造自然界后,就以自己的精神主宰和壟斷世界上的一切,使一切生命受到許多限制并失去自發(fā)性。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仍然是一種積極的精神,大道在宇宙里面的精神是“既公且大”,宇宙的現(xiàn)象從它的本體流溢出來后就完全自由發(fā)揮自己的妙用,不加以牽制、束縛和控制,顯示大道的高超本性。
就道的意然屬性來說,不是就大道本身著想,而是就人類外在的觀察去了解大道是什么。而道之人為屬性或“意然屬性”,“即處處以個人主觀之觀點,而妄加臆測,再以笨拙之語言而構(gòu)畫之,表達之者。避開此一切人為之偏計妄測等,道,就其本身而言,乃是‘真而又真之真實’、‘玄而又玄之奧妙’、‘神而又神之神奇’。唯上圣者足以識之”[3]221,指的是以主觀之見對“道”妄加臆測,用本來不能名狀的語言來顯現(xiàn)真相,然而由于不夠細密反而失掉大道的全體真相。在此點上,王弼很了解老子,他說“心必有所分,身必有所受,故善而行者非大善,因而去者非大因也”(《老子微旨例略》)。此段說明對大道的了解,真相與假象應(yīng)該分開來,假象屬于有形世界的一切形形色色,非大道的本源。對一事物的了解,從“真”了解是一回事,從“名”了解卻是另一回事。哲學(xué)家大多是從語言即“名”的角度非實的角度了解的,只能“指虛”不能“指實”,而那“虛”的“名”往往要符合主觀的要求,失去了客觀的真相。王弼說:“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從謂也。名生乎彼,稱出乎我。……名號生乎形狀,稱謂出乎涉求。……故名號則大失其旨,稱謂則未盡其極”[6]5-15。“名之不允當(dāng),稱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稱必有所由;有分則有不兼,有由則有不盡。不兼則大殊其真,不盡則不可以矣”[6]2。所以說,老子說道本身是“真而又真之真實”,唯圣人足以識之。老子認為,一般人只能由人的人為屬性來妄加臆測,像“大,奧,微,獨立,空虛,希聲,無形,無名,無狀,不可測”這些用來“喻”道的名在根本上是不能夠認識道之全體的,甚至?xí)纬烧`解[7]238。通過老子的啟示,我們可以重新掌握大道本身應(yīng)包含的性質(zhì),了解了這種精神之后,才可以顯現(xiàn)出哲學(xué)家的精神人格。
方東美認為,要從意相中識別和發(fā)現(xiàn)天相,即透過“上德不德”來實現(xiàn)“無”對“有”的揚棄。在《道德經(jīng)》第三十八章里,老子把最高的價值叫上德,所謂“上德不德”,后一個“德”指的是相對價值的痼弊。假使以超越的態(tài)度,一直向上追求,到無止境的最高境界時,再回頭來看宇宙的下層世界,使之成為無數(shù)個價值平面。這樣才知道,人類只是在其中的一個價值層面生活。在此一種價值層面覺得很滿意,其實對另外的層面來說并不然。如到博物館看字畫,好似很得意,殊不知天外有天。以文字為例,從甲骨文、金文、鐘鼎文,一直到小篆、秦漢八分隸書,六朝以后的正楷、行書、草書無不達其頂端;以畫為例,漢唐石刻、六朝壁畫、唐宋第一流的大畫家作品,使現(xiàn)在的自矜得意者頓覺無筆無墨。
所以,一定要有解脫的精神,把人間世一切善惡觀念觀察了之后,在層層向上追求美之外的美、善之外的善、真之外的真,然后才“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唯其不德,才是有德。以超脫解放之后的高尚生命理想來衡量,劃分開真的價值與假的價值,分辨價值理想的高低,在相對價值里面找到至善、至美和至高的真理。老子稱這樣的人為圣人,當(dāng)然,此圣人不是獨善其身,而是“圣人之在天下,翕翕焉,為天下渾其心”(《道德經(jīng)》第四十九章)。不像平常儒家說的“放其心而不知求”,道家則以真正的精神、心靈,去追求最高的價值,即通過“無”對“有”的揚棄,去竭力了解宇宙的真相,透過意然之相,提升到超越的價值里面。這樣會達到天然之相,實現(xiàn)“人無棄人,物無棄物”的理想。
4 論道征——道的實踐
“就道征而言,凡此種高明圣德,顯發(fā)之而為天德,原屬道。而圣人者,道之具體而微也,乃道體之當(dāng)下呈現(xiàn),是謂‘道成肉身’”[7]221。道征指的是道之表征。生活在現(xiàn)象世界的尋常人,常冥頑不化,執(zhí)著于虛妄價值,趨于庸俗僵化,直至誤視真善美義,使自己陷入鄙陋、更鄙陋,渺小、更渺小,自私、更自私之中,在開放的世界里把自己收縮起來,變成渺小境地。
而道家所景仰的圣人,可免于尋常人的這種作繭自縛的生活,始終能超脫解放,超升自己平面的生活,把平常人鄙陋的心理、鄙陋的精神都放棄掉,在價值世界上面,能夠接觸、體會、實行更高的價值理想,提高人格。道家所謂的作為理想極致的圣人,憑借高尚精神與對價值追求與向往,超越一切限制與弱點,能夠慷慨無私,淑世救人,從而贏得舉世的尊敬與愛戴。只有這樣,其己身之價值才會更豐富、其己身之存在才愈充實,所謂“既以予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3]221。圣人自己跳出世俗世界偏枯的、狹隘的小生命,然后展開無窮廣大的世界、無窮高尚的領(lǐng)域,把精神向外推廣、向上發(fā)揮,表現(xiàn)出生命精神的大氣魄,才變作圣人。
方東美充分肯定了老子指出的道家精神——圣人精神。在《道德經(jīng)》第八十一章、第四十九章、第二十七章都有對圣人既有理想又有熱情和高尚動機的描寫。以圣人來感染和感召這個世界,使鄙陋者忘掉鄙陋。圣人能遍歷有界萬象,能體會“從事于道者,同于道”之意,而復(fù)歸于樸,尚同自然,“致虛極,守靜篤”(《道德經(jīng)》第十六章)。圣人無事于聚斂,贊譽“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然,為天下渾其心”(《道德經(jīng)》第四十九章)。“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道德經(jīng)》第八十一章)。“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道德經(jīng)》第四十九章)。“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道德經(jīng)》第二十七章)”[3]221。圣人代表道之真正救世精神,是有界一切表相的拯救者。
由于老子的教導(dǎo),使我們認識到,盡性之道在于勤做圣賢功夫——展現(xiàn)犧牲自我精神、百姓為先原則和民主平等及天下為公追求,而孜孜努力、精勤不懈地使之實現(xiàn)乃是人的天職,所以,只有那些具有內(nèi)圣之修養(yǎng)功夫的人才能挺然自立于天壤之間。方東美總結(jié)說,“一言以蔽之:圣人者,代表道之真正救世精神,有界一切之拯救者”[5]246。這樣,就體現(xiàn)了道的表征:高明圣德的當(dāng)下呈現(xiàn)。圣人代表了超脫解放的精神和救人救世的精神,使自然“無”為之道和人“有”為之道融會貫通起來,超越一切相對固有的限制,這是老子指出來的真正的道家精神。
為何老子說自己的話“甚易知”,而世人覺得難解呢?方東美指出,主要在于老子用語的指謂多重、詞意變換所致。應(yīng)該抓住對關(guān)鍵詞“道、常、無、有”等的理解,注意據(jù)上下文辨別其自然義、絕對義、相對義、尋常一般義、滑稽幽默特殊突梯義等,然前人無有今人所用之大體、凸體、小體、撇號等辨別方法。到了三世紀時,王弼學(xué)派在道家眾多詞匯中將“無”、“有”突出出來,提倡“貴無賤有”,引起儒家裴提倡“崇有論”與之對抗,直到十一、二世紀宋人蘇轍、程大昌等解老者,力求貫通有無,才至道儒二家“不相抵牾,通而不隔”[5]246。可見,方東美所理解的老子對有無的本意是“取其均衡”的。
綜合以上,方東美討論道家超越之道本體,從兩方面進行,即以“有”為對象的實有方面,以“無”為對象的超越方面,“無”與“有”并不對立。“無”雖不能名,但通過“悟”的途徑,可“悟”出玄之又玄的道本體。一方面是自有至無,根據(jù)“反者道之動”的原理,將宇宙萬物提升到道之本源、返于大道、歸根復(fù)命,這是“無之以為用”,順之,生萬事萬物之“有”;另一方面,自無至有,自有至大有,這是“有之以為利”,此兩方面代表了“道之雙回向”,此雙回向即“仰”“俯”的立體回向,使天道、人道渾為一體。
應(yīng)該說,老子之道的內(nèi)涵豐富,具有多義性和模糊性。而方東美揭示老子之道,以超越之“無”與實在之“有”兩個維度從道體、道用、道相、道征四個方面探討恒常的道本體,具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性,同時也是較為準(zhǔn)確的。他以道之“雙回向”為方法實現(xiàn)了“無”、“有”二者的融合,將本體與作用、表相、表征的關(guān)系解釋為一個動態(tài)的系統(tǒng)。這種對道的立體的獨特解釋,為解決老子哲學(xué)本體與現(xiàn)象二元溝通的困難提供新的視角。正如有學(xué)者所言:“而他對老子哲學(xué)中本體與現(xiàn)象之間關(guān)系的準(zhǔn)確把握以及對老子哲學(xué)思維方式的深刻揭示,則凸顯了中國哲學(xué)體用一元的獨特思維方式與根本特征”[8]。此外,方東美揭示了圣人形象在老子哲學(xué)中的重要地位。圣人是體道者和行道者、超脫精神和現(xiàn)實品格的合一,圣人具有貫通理想與現(xiàn)實的功能,即出即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yè),將此濟世精神運用于現(xiàn)實中,解決現(xiàn)實問題。應(yīng)該說,方東美的這種研究理路和濟世情懷是當(dāng)今哲學(xué)研究者應(yīng)提倡的。
由上可知,方東美所說的道家之道,深深扎根于現(xiàn)實土壤,與魯迅先生所說的將追求“大地的意義”看做超越之途是一致的。魯迅認為,虛構(gòu)超現(xiàn)實是“不敢正視人生”[9]73,這樣,所謂普遍、圓滿、光明不過是“不敢正視社會現(xiàn)象”,不過是“閉著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9]73-74那么得到何處尋找人生的意義以對付黑暗的人生呢?即執(zhí)著于現(xiàn)在、執(zhí)著于地上,并把追尋“大地的意義”看做超越之途。尼采所謂“超人”,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離開大地而高踩者,而不過是說從上述外在的終極世界中掙脫出來、解放出來,由“鶩外”呼求終極,“轉(zhuǎn)而趣內(nèi)”,忠于自己的意志:“現(xiàn)在,我教你們什么是超人!超人是大地之意義。……兄弟們,我祈禱著:忠實于大地罷,不要信任那些奢談超大地之希望的人!無論有意地或無意地,他們是施毒者。他們是生命之輕蔑者,將死者,他們自己也是中毒者。大地已經(jīng)厭惡他們;讓他們?nèi)チT”[9]74!人如何在沒有“彼岸的天國”和“形而上學(xué)理性世界”之安慰中生活呢?只有忠于“大地的意義”,消解終極,回到大地。這是尼采和魯迅解決危機的思想路徑,也是方東美哲學(xué)的選擇路徑。方東美沒有將道的終極本體作為終極,而僅是新的開始,于是有了道的體用、體相、體徵等方面交相呼應(yīng)的哲學(xué)回應(yīng)。
[1]宋志明.現(xiàn)代新儒家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1.
[2]李安澤.方東美對道家哲學(xué)的現(xiàn)代詮釋[J].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學(xué)報,2008(5):36-40.
[3]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xué)[M].臺北:黎明文化事業(yè)公司,2005.
[4]錢穆.老莊通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360.
[5]方東美.中國哲學(xué)精神及發(fā)展:上冊[M].孫智燊,譯.臺北:黎明文化事業(yè)公司,2005.
[6]王弼.老子微旨例略[M]//道藏.臺北:藝文書局,1956.
[7]宛小平.方東美與中西哲學(xué)[M].合肥:安徽大學(xué)出版社,2008.
[8]金小方,李春娟.言有宗,事有君——方東美論老子哲學(xué)[J].船山學(xué)刊,2006(3):64-66.
[9]王乾坤.魯迅的生命哲學(xué)[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