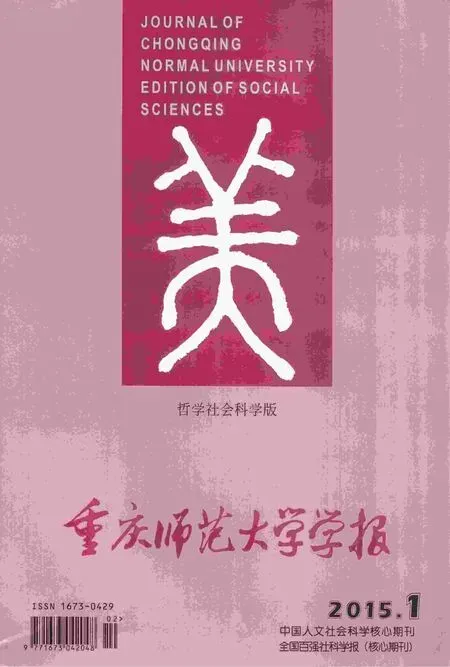解構(gòu)主義誤讀理論的有效性問(wèn)題研究
王 敏
(西安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 中國(guó)語(yǔ)言文學(xué)學(xué)院,陜西 西安 710128)
“誤讀”作為一種閱讀現(xiàn)象,在傳統(tǒng)的文學(xué)觀念中是一種應(yīng)避免的錯(cuò)誤,其反面的正確閱讀即是“正讀”。既有“正/誤”之分,就必然存在一定的閱讀標(biāo)準(zhǔn)。如果以艾布拉姆斯“藝術(shù)批評(píng)的諸坐標(biāo)”為參照系,20世紀(jì)之前的傳統(tǒng)文論主要是以“世界”和“作者”及其之間的關(guān)系為意義來(lái)源。20世紀(jì)形式主義文論以“文本”為研究重心,讀者系統(tǒng)文論則是把“讀者”作為意義研究的中心。在文本意義研究問(wèn)題上,真正實(shí)現(xiàn)顛覆性轉(zhuǎn)變的是解構(gòu)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法國(guó)結(jié)構(gòu)主義理論家羅蘭·巴特也是解構(gòu)主義批評(píng)的奠基者,他提出“作者之死”的觀念,消解作者意圖的權(quán)威,倡導(dǎo)“可寫(xiě)的文本”,這可以看作是“誤讀”思想的萌發(fā)。耶魯學(xué)派的解構(gòu)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家提出“一切閱讀皆誤讀”,一方面否定了傳統(tǒng)“正讀”的存在及其權(quán)威性,另一方面視“誤讀”為一種絕對(duì)的存在,解構(gòu)主義誤讀理論全面展開(kāi)。就耶魯學(xué)派的學(xué)術(shù)歷程來(lái)看,德里達(dá)于1966年在美國(guó)約翰·霍布金斯大學(xué)的著名演講——《人文科學(xué)話語(yǔ)中的結(jié)構(gòu)、符號(hào)與游戲》被譽(yù)為解構(gòu)主義的宣揚(yáng)書(shū),也是耶魯學(xué)派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基本綱領(lǐng),其發(fā)表標(biāo)志著耶魯學(xué)派展開(kāi)文學(xué)解構(gòu)活動(dòng)的起點(diǎn)。在這篇演講中,結(jié)構(gòu)主義的中心全然消解,探討文學(xué)的另一種方法取代結(jié)構(gòu)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這就是“解構(gòu)主義”批評(píng)理論。德里達(dá)從此與美國(guó)思想界、與耶魯學(xué)派其他理論家結(jié)緣。從1966年起,他便定期在美國(guó)幾所大學(xué)任客座教授,與保羅·德·曼、哈羅德·布魯姆、杰弗里·哈特曼、希利斯·米勒一起組成了蜚聲一時(shí)的“耶魯學(xué)派”。耶魯學(xué)派把德里達(dá)哲學(xué)思想運(yùn)用到文學(xué)理論研究和批評(píng)之中,首先由德·曼和米勒分別奠定了其理論基礎(chǔ)和基本方法論,然后發(fā)展成為包括哈特曼和布魯姆在內(nèi)的強(qiáng)大文學(xué)評(píng)論隊(duì)伍。
然而,解構(gòu)主義誤讀理論從誕生之初起,就由于其激進(jìn)的閱讀觀念而不斷受到各方面的質(zhì)疑,以希利斯·米勒為代表的解構(gòu)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家也不斷地與各種反對(duì)的聲音形成爭(zhēng)鋒。這些論爭(zhēng)圍繞著解構(gòu)主義“誤讀”之邊界的問(wèn)題展開(kāi),在討論中把解構(gòu)主義誤讀理論的有效性問(wèn)題推向深入,形成對(duì)這一理論的全方位審視。
一、解構(gòu)主義批評(píng)的語(yǔ)言修辭論與意義觀
解構(gòu)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家認(rèn)為,“誤讀”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種文學(xué)闡釋結(jié)果都是無(wú)限闡釋可能性中的一種,這是因?yàn)槲膶W(xué)文本的閱讀要牽涉到許多因素,正如解構(gòu)主義的闡釋者喬納森·卡勒所總結(jié)的:“給定文本的復(fù)雜性,比喻的可逆轉(zhuǎn)性,語(yǔ)境的延伸性,加上閱讀之勢(shì)在難免的選擇和組織,每一種閱讀都可以說(shuō)是片面的。”[1]181文本內(nèi)部的語(yǔ)言修辭、外部的語(yǔ)境及讀者差異,這些客觀存在的復(fù)雜因素,使得難以形成全面的、絕對(duì)正確的理解,每一種閱讀方式都只能是單方面的、不完滿的,每一時(shí)代的讀者都可以證明前人的閱讀是誤讀,卻又被后來(lái)的闡釋者發(fā)現(xiàn)殘缺不全。因此,概而言之,“在一個(gè)較其倒置更為可信的形式中,理解是誤解的一個(gè)特殊例子,誤解之一特定的離格或確認(rèn)。……在一個(gè)總體化的誤解或誤讀中運(yùn)行的闡釋過(guò)程,既促生了所謂的誤解,也促生了所謂的理解。”[1]157由于消解了“正讀”的權(quán)威地位,“誤讀”不再被視為邊緣化的存在,而一躍成為理解的一種合法形式。
伴隨著對(duì)“誤讀”的重新認(rèn)識(shí),傳統(tǒng)設(shè)定的以獲得“正讀”為目的的各類闡釋標(biāo)準(zhǔn)被取消。首先是對(duì)作者意圖論的消解。羅蘭·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口號(hào),作者原意不再是作品的唯一意義,文學(xué)閱讀和闡釋活動(dòng)成為一種獨(dú)立于原作者的文學(xué)再生產(chǎn)活動(dòng)。其次,文學(xué)意義也不僅僅是文本字面的客觀意義。文學(xué)文本的性質(zhì),正如伊格爾頓所說(shuō):“一個(gè)文本可能會(huì)把它無(wú)力表述為一個(gè)命題的東西,某種與意義與表意的本質(zhì)有關(guān)的東西,‘示’(show)于我們。對(duì)于德里達(dá)來(lái)說(shuō),一切語(yǔ)言都展示著這種超出準(zhǔn)確意義的‘剩余’,一切語(yǔ)言都始終威脅著要跑過(guò)和逃離那個(gè)試圖容限它的意義。”[2]131~132本有所言、有所不言,在言說(shuō)的文字之外,更有許多難以言傳的、不能用命題來(lái)陳述的意蘊(yùn)被文本字面義所掩蓋。因此,文本意義不能通過(guò)字面意義的歸納總結(jié)來(lái)完成,必須通過(guò)反復(fù)的闡釋活動(dòng),挖掘文本內(nèi)部各層面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因素來(lái)揭示更為復(fù)雜的潛藏意義。第三,文學(xué)意義也不是讀者所能完全賦予的,讀者所擁有的視野是有限的,不能闡釋出文本內(nèi)在的所有可能的內(nèi)涵。解構(gòu)批評(píng)家反對(duì)“自信”得到真理的批評(píng)家,任何闡釋都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都具有偶然性,所以都只不過(guò)是極有限的解讀方式,在它之外還有許多種解讀可能性,因而不能簡(jiǎn)單地將某一種結(jié)論作為中心和標(biāo)準(zhǔn)。
解構(gòu)主義批評(píng)家的閱讀實(shí)踐否定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的存在。希利斯·米勒在專著《小說(shuō)與重復(fù)》中指出,艾米麗·勃朗特的小說(shuō)《呼嘯山莊》自從面世以來(lái)受到了各種角度的闡釋,其中米勒較為認(rèn)可其中的十五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xué)視野下的性的戲劇;一個(gè)與門、窗的母題有關(guān)的神秘故事;一個(gè)關(guān)于強(qiáng)烈激情受挫的道德故事;一個(gè)關(guān)于性與死亡關(guān)系的故事;一個(gè)關(guān)于作者對(duì)她死去的姐姐懷有同性戀感情的故事;或者一出風(fēng)暴與寧?kù)o對(duì)立沖突的戲劇……米勒本人則把它看作是一個(gè)關(guān)于作者宗教觀點(diǎn)的戲劇性故事等等。[3]50這些闡釋在批評(píng)方法上有社會(huì)歷史的、精神分析的、原型批評(píng)的……多種方式,它們之間相互矛盾和沖突的地方十分明顯,作者意圖、文本語(yǔ)言、讀者感受等闡釋標(biāo)準(zhǔn)都發(fā)生了作用,但都只是多重闡釋中的一種而不是全部。所有闡釋都只通過(guò)一定方式而強(qiáng)加給文本的一種模式,除此之外還有無(wú)數(shù)模式的存在。由此,米勒總結(jié)道:“最好的閱讀是那些能夠最充分顯示文本的異質(zhì)性的閱讀,這種閱讀是對(duì)由文本決定的、系統(tǒng)相關(guān)卻又邏輯矛盾的意義形式的展現(xiàn)。”[3]51可見(jiàn),在解構(gòu)主義批評(píng)家那里,由于不存在統(tǒng)一性的標(biāo)準(zhǔn),文學(xué)文本也就不存在所謂的“準(zhǔn)確意義”,具有多種潛在的意義生產(chǎn)的可能性,不僅僅是作者意圖指涉的主觀意義、作品“書(shū)頁(yè)文字”的客觀意義,也不只是讀者閱讀賦予的某一種體驗(yàn)意義,而是文本自身因語(yǔ)言修辭而存在的多重意義,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會(huì)生產(chǎn)出不同的意義,只能在誤讀性的接受活動(dòng)中把握它們。
解構(gòu)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家之所以推翻一切闡釋標(biāo)準(zhǔn),是因?yàn)槲膶W(xué)闡釋是在一定語(yǔ)境中發(fā)生的,而語(yǔ)境是不可飽和的,這就決定了意義的不可確定性。語(yǔ)境構(gòu)成了文本闡釋的意義場(chǎng),是制約意義的一個(gè)重要因素。語(yǔ)境對(duì)解構(gòu)主義誤讀理論的影響是雙向的:一方面意義在語(yǔ)境中生成,被語(yǔ)境所限制和規(guī)范,另一方面語(yǔ)境本身是無(wú)限的,因而又賦予意義解讀的無(wú)限可能性。解構(gòu)主義誤讀理論反對(duì)先驗(yàn)化和普遍化的意義闡釋,認(rèn)為文學(xué)解讀是對(duì)某一境遇的反應(yīng),同時(shí)也會(huì)引發(fā)另一不同的反應(yīng),依此類推,不斷延伸下去。這就正如米勒所說(shuō):“標(biāo)準(zhǔn)法語(yǔ)或標(biāo)準(zhǔn)英語(yǔ)中那個(gè)假定的、充分的語(yǔ)境是一種錯(cuò)覺(jué)。”[4]276不存在一個(gè)可靠的語(yǔ)境來(lái)對(duì)文本進(jìn)行孤立、封閉的研究,文本意義總是在開(kāi)放的語(yǔ)境中展開(kāi),在不同的語(yǔ)境中獲得獨(dú)特的風(fēng)格,因而注定無(wú)法一勞永逸地解釋清楚文本的意義。文本在再語(yǔ)境化的過(guò)程中由自身向他者轉(zhuǎn)化,可以脫離原始語(yǔ)境而在其他語(yǔ)境中不斷重復(fù),從而實(shí)現(xiàn)意義的延伸。因此,對(duì)文本最佳的解讀,就是在無(wú)標(biāo)準(zhǔn)的前提下展示出各種可能的意義。這些意義同時(shí)存在于文本之中,但在邏輯上彼此是不協(xié)調(diào)、不統(tǒng)一的。
二、“作者意圖論”之爭(zhēng)
“作者原意”是傳統(tǒng)閱讀理論重要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卻也正是解構(gòu)主義批評(píng)家堅(jiān)決否定、力圖顛覆的標(biāo)準(zhǔn)。在他們看來(lái),閱讀的魅力和價(jià)值不僅不在于遵從作者意圖,恰恰要用創(chuàng)造性的意義形式來(lái)顛覆作者意圖。這正如哈特曼所說(shuō):“認(rèn)真的閱讀不就是一種復(fù)雜的辯護(hù)嗎?這種辯護(hù)反對(duì)一個(gè)騙人的神祗——也就是反對(duì)我們稱之為一部小說(shuō)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奇妙的和有吸引力的實(shí)在的作者——?jiǎng)?chuàng)世者。”[5]61這一點(diǎn)構(gòu)成了解構(gòu)主義誤讀理論與傳統(tǒng)閱讀觀念之間的沖突,使得持傳統(tǒng)觀念的批評(píng)家擔(dān)心由此帶來(lái)文本意義的混亂。美國(guó)學(xué)者赫施便尖銳地指出:“對(duì)作為意義規(guī)定者的原來(lái)作者的消除,就是對(duì)使解釋具有有效性的唯一有說(shuō)服力的規(guī)范性原則的否定。”[6]14赫施是作者權(quán)威的堅(jiān)定擁護(hù)者,在他看來(lái),作者意圖是意義的來(lái)源,也是闡釋活動(dòng)不可逾越的邊界,對(duì)作者意圖的消解會(huì)使得其他任何闡釋失去說(shuō)服力,這意味著闡釋有效性的喪失。
文學(xué)語(yǔ)言不同于普通語(yǔ)言,它具有多義性特征,對(duì)這一點(diǎn)赫施是認(rèn)可的。為了在多重意義中顯現(xiàn)作者意圖的地位,他把意義分為“含義”和“意義”兩種:“一件本文具有著特定的含義,這特定的含義就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號(hào)系統(tǒng)所要表達(dá)的事物中,因此,這含義也就能被符號(hào)所復(fù)現(xiàn);而意義則是指涵義與某個(gè)人、某個(gè)系統(tǒng)、某個(gè)情境或與某個(gè)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間的關(guān)系。……因此,意義總是包含著一種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的一個(gè)固定的、不會(huì)發(fā)生變化的極點(diǎn)就是本文含義。”[6]16-17這里,“含義”是運(yùn)用語(yǔ)言學(xué)方法所得到的意義,具有穩(wěn)定性原則;“意義”則不是固定的,與具體的闡釋語(yǔ)境有關(guān),包含種種變化。由于外在語(yǔ)境的存在,一個(gè)文本可以有多個(gè)并行的闡釋。然而赫施又指出,所有闡釋都不應(yīng)違背作者意圖,否則“意義”一詞就失去了價(jià)值。這也就是說(shuō),“含義”作為一種客觀的、內(nèi)在的意義,它能夠傳達(dá)作者本意,因而是意義闡釋活動(dòng)的基礎(chǔ);“意義”是讀者對(duì)作者本意的領(lǐng)會(huì),是主觀的、外在的意義,必須在作者意圖允許的范圍內(nèi)進(jìn)行。顯然,這種重“含義”而輕“意義”的闡釋思想,是以作者意圖來(lái)限定其他多重闡釋,文學(xué)語(yǔ)言的多義性必須作為對(duì)作者意圖的揣度而存在。因而可以說(shuō),作者創(chuàng)作時(shí)的意圖是文本的唯一意義標(biāo)準(zhǔn)。
赫施用“作者意圖”來(lái)統(tǒng)轄所有語(yǔ)言的意義傳達(dá),認(rèn)為不管是文學(xué)語(yǔ)言還是普通語(yǔ)言,都應(yīng)當(dāng)服從作者的原意,這也就把文學(xué)和其他語(yǔ)言形式混為一談了。巧合的是,赫施和德里達(dá)都有把文學(xué)語(yǔ)言與其他書(shū)寫(xiě)語(yǔ)言一視同仁的傾向,但立足點(diǎn)卻是根本相異的:德里達(dá)把所有書(shū)寫(xiě)都視為如文學(xué)語(yǔ)言般具有修辭性,因而是多義的;赫施卻是把文學(xué)語(yǔ)言視為如普通語(yǔ)言般一定要講究原意和確定性,因而是單義的。兩種迥異的觀念正反映出解構(gòu)主義語(yǔ)言觀和傳統(tǒng)語(yǔ)言觀的根本差異。赫施堅(jiān)持傳統(tǒng)語(yǔ)言觀,把作者原意與文本的“有效性”與“客觀性”聯(lián)系緊密。不可否認(rèn),赫施對(duì)客觀性的重視,對(duì)主觀主義與相對(duì)主義的意義研究有糾偏作用,然而他對(duì)讀者主體的忽視也有偏執(zhí)一端的缺陷,取消了文學(xué)語(yǔ)言的獨(dú)立性和特殊性。因此,僅從作者意圖的標(biāo)準(zhǔn)來(lái)討論這個(gè)有效性與客觀性的問(wèn)題,是失之偏頗的。
美國(guó)文論家艾布拉姆斯也曾撰寫(xiě)了論文《如何以文行事》,不無(wú)譏諷地批評(píng)德里達(dá)、布魯姆以及讀者反映批評(píng)家費(fèi)什:“在我們這個(gè)閱讀時(shí)代里,文學(xué)交際行為中的第一動(dòng)因是作者。對(duì)一個(gè)不再是新手的人而言,看到近來(lái)的書(shū)和文章作者得意地宣稱自己死亡,總讓我覺(jué)得好笑。”[7]251他秉持“作者意圖論”宣告:“不論批評(píng)家針對(duì)彌爾頓而創(chuàng)造的文本是多么有趣,都遠(yuǎn)遠(yuǎn)比不上彌爾頓寫(xiě)給他心目中那些讀者的那個(gè)文本,盡管這些讀者在數(shù)量上并不多。”[7]265關(guān)于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與解構(gòu)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之間的關(guān)系,艾布拉姆斯的理解是建立在一種假設(shè)的基礎(chǔ)上,即把解構(gòu)主義批評(píng)視為全新的闡釋范式,它與傳統(tǒng)理論是根本對(duì)立的關(guān)系,這種對(duì)立把它自身推入顛覆一切的懷疑主義和相對(duì)主義之中,因而失去了批評(píng)的價(jià)值。艾伯拉姆斯打了一個(gè)比方:單義性閱讀是一棵高大的橡樹(shù),它扎根于堅(jiān)實(shí)的泥土里,由于被解構(gòu)批評(píng)這根長(zhǎng)青藤心懷叵測(cè)地包圍纏繞而受到了傷害。然而事實(shí)上,解構(gòu)批評(píng)家存在與傳統(tǒng)相關(guān)的保守傾向。米勒從“deconstruction”(解構(gòu))入手,指出:“任何一種解構(gòu)同時(shí)又是建構(gòu)性的、肯定性的。這個(gè)詞中‘de’和‘con’的并置就說(shuō)明了這一點(diǎn)。”[8]130~131解構(gòu)批評(píng)中同時(shí)包含著否定和肯定、解構(gòu)和建構(gòu)兩個(gè)方面的辯解。誤讀理論反對(duì)傳統(tǒng)批評(píng)對(duì)確定性的追求,這并不意味著誤讀理論完全拋棄了傳統(tǒng)批評(píng),也并不把文本瓦解成支離破碎的片斷,誤讀并不是艾布拉姆斯所說(shuō)的傷害文本的意義,反而以更全面的方式來(lái)建構(gòu)文本意義,以誤讀的方式來(lái)對(duì)既定意義作修正與補(bǔ)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解構(gòu)主義的誤讀理論離不開(kāi)傳統(tǒng)閱讀方式,這并不意味著解構(gòu)批評(píng)是依附于傳統(tǒng)批評(píng)的。艾布拉姆斯把與語(yǔ)法相關(guān)的閱讀稱為“基礎(chǔ)閱讀”(under-reading),認(rèn)為這是意義闡釋的第一層;把針對(duì)語(yǔ)言修辭的閱讀方式稱為“超閱讀”(over-reading),視為闡釋的第二層,并且它是建立在第一層閱讀之上的更深入的闡釋方式。這種分類方式表現(xiàn)出邏輯的力量,修辭語(yǔ)言就是附加于語(yǔ)法功能之上的東西。這也就意味著,立足于語(yǔ)法的閱讀是必需的,而立足于修辭的閱讀則是可有可無(wú)的。米勒反對(duì)這種劃分方式,認(rèn)為解構(gòu)主義誤讀理論不存在這類等級(jí)關(guān)系:“沒(méi)有艾布拉姆斯所假定的那種普通的‘基礎(chǔ)閱讀’的東西……事實(shí)上從一開(kāi)始,超閱讀也就僅有一種形式,即對(duì)語(yǔ)法和轉(zhuǎn)義的共同閱讀。”[8]130~131也就是說(shuō),在對(duì)文學(xué)文本進(jìn)行語(yǔ)法閱讀的同時(shí),就不可避免地進(jìn)行了修辭閱讀,這兩種形式在闡釋過(guò)程中不是相繼而出,而是同時(shí)發(fā)生、并存共生的,當(dāng)一種意義不存在時(shí),另一種也就無(wú)法存在。文本各種闡釋方式之間,不是等級(jí)遞進(jìn)的關(guān)系,不能說(shuō)一種閱讀是另一種閱讀的基礎(chǔ),它們是并列的。文本具有多種復(fù)雜意義,其中的每一種都有另一次閱讀方式的蹤跡,但這蹤跡顯示出的是對(duì)另一種閱讀的消解而不是承繼。誤讀理論不是層層深入,不追求終極意義,而是層層顛覆,體現(xiàn)出文本的非邏輯性,目的在于使文本中各種因素活躍起來(lái)。
三、“文本意圖論”之爭(zhēng)
意大利符號(hào)學(xué)教授昂貝多·艾柯從“文本意圖”的角度對(duì)誤讀理論進(jìn)行了批評(píng)。艾柯并不全然反對(duì)解構(gòu)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關(guān)于文學(xué)多義性的觀念,他接受了文學(xué)可以有許多不同的闡釋這種思想,肯定了讀者在闡釋文學(xué)文本時(sh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早在1962年,他就在被譽(yù)為“意大利新先鋒派”的代表作《開(kāi)放的藝術(shù)品》中提出,任何藝術(shù)作品,即使是已經(jīng)完成、結(jié)構(gòu)上無(wú)懈可擊的作品,依然處于開(kāi)放狀態(tài),具有開(kāi)放式結(jié)構(gòu),提供了無(wú)限多個(gè)闡釋的可能,讀者可以不斷地參與闡釋,發(fā)掘文本新的、甚至作者未曾想到的內(nèi)涵。然而,艾柯小說(shuō)《玫瑰之名》發(fā)表后引起了關(guān)于“玫瑰”的闡釋熱潮,一時(shí)間五花八門、千奇百怪乃至匪夷所思的闡釋一擁而上。面對(duì)這種意料不到的情況,艾柯提出了“過(guò)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的問(wèn)題。他于1990年在劍橋大學(xué)主持了一場(chǎng)名為“詮釋與過(guò)度詮釋”的講座,與理查德·羅蒂、喬納森·卡勒、克里斯蒂娜·布魯克-羅斯三人展開(kāi)辯論,探討有關(guān)意義的本質(zhì)以及詮釋之可能性與有限性的問(wèn)題。艾柯所謂“過(guò)度詮釋”是指過(guò)于主觀、不顧文學(xué)文本內(nèi)在含義的闡釋活動(dòng)。他指出,文學(xué)批評(píng)對(duì)于文學(xué)作品的闡釋不是沒(méi)有邊界,不設(shè)定界限的閱讀只能干擾對(duì)于文本意義的解讀,必須保持嚴(yán)格鑒定的尺度以防止闡釋的失控。艾柯認(rèn)為:“說(shuō)詮釋潛在地是無(wú)限的并不意味著詮釋沒(méi)有一個(gè)客觀的對(duì)象,并不意味著它可以像水流一樣毫無(wú)約束地任意‘蔓延’。說(shuō)一個(gè)文本潛在地沒(méi)有結(jié)尾并不意味著每一詮釋行為都可能得到一個(gè)令人滿意的結(jié)果。”[9]25他明確指出,解構(gòu)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德·曼、米勒的批評(píng)方法賦予了讀者過(guò)多的闡釋自由,由此帶來(lái)“無(wú)限衍義”。艾柯強(qiáng)調(diào)說(shuō),闡釋符號(hào)不能隨心所欲,文本的解釋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和標(biāo)準(zhǔn)。[9]42
為了抵制無(wú)限制的誤讀,艾柯提出“文本意圖”的概念來(lái)作闡釋的標(biāo)準(zhǔn),認(rèn)為讀者闡釋的應(yīng)當(dāng)是文本本身所隱含的意圖。“文本意圖”在文本意義生成的過(gu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不受制于作者意圖,也不會(huì)對(duì)讀者意圖的自由發(fā)揮造成阻礙。它不是一個(gè)先驗(yàn)的存在,而是“讀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推測(cè)出來(lái)的。”[10]68然而這里所說(shuō)的不是一般的讀者,而是具備一定素養(yǎng)的“標(biāo)準(zhǔn)讀者”,即按照文本的要求、以文本應(yīng)該被閱讀的方式去閱讀的讀者。同時(shí),艾柯覺(jué)察到讓“文本意圖”充當(dāng)詮釋的限定仍缺乏足夠的說(shuō)服力,因?yàn)闅v史的發(fā)展會(huì)影響這種操作原則,因此他又引入了“歷史之維”這個(gè)概念,指出文本與特定的社會(huì)文化內(nèi)涵相關(guān)聯(lián),歷史語(yǔ)境的變化會(huì)導(dǎo)致詮釋結(jié)果的不斷追加。雖如此,艾柯又指出:不管在什么歷史語(yǔ)境下,經(jīng)典的詮釋都要考慮文本的意圖,遠(yuǎn)離了“文本意圖”,也就逾越了合法詮釋的邊界。
艾柯一再聲稱:“一定存在著某種對(duì)詮釋進(jìn)行限定的標(biāo)準(zhǔn)”,著力強(qiáng)調(diào)“文本的內(nèi)在連貫性”與“無(wú)法控制的讀者沖動(dòng)”之間的區(qū)別,強(qiáng)調(diào)前者的權(quán)威。[8]130~131然而,艾柯理論有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因?yàn)槿魏卫碚摷叶紱](méi)有資格確定“過(guò)度詮釋”的標(biāo)準(zhǔn),即使是在同一個(gè)時(shí)代也不會(huì)形成所有人都承認(rèn)的標(biāo)準(zhǔn)。就“文本意圖”來(lái)說(shuō),是必須依靠讀者來(lái)發(fā)現(xiàn)的,但同時(shí)它又束縛、限定著讀者的閱讀,“文本”與“讀者”的關(guān)系陷入一種悖論。基于此,喬納森·卡勒批評(píng)道:“艾柯被他對(duì)界限的過(guò)分關(guān)注誤入了歧途。”[11]130他認(rèn)為意義生成過(guò)程中的任意性并不意味著意義是讀者的自由創(chuàng)造,相反,它反映了語(yǔ)言的多義性和模糊性,表明文學(xué)語(yǔ)言的運(yùn)行機(jī)制是復(fù)雜的。并且,甚至可以說(shuō),對(duì)文學(xué)文本內(nèi)在因素及其運(yùn)行機(jī)制的考察即使是“過(guò)度闡釋”,也比只是回答標(biāo)準(zhǔn)讀者所提出的問(wèn)題的方法更好,因?yàn)樗锌赡塬@得新穎的發(fā)現(xiàn)。對(duì)于艾柯提出的“歷史之維”,卡勒也指出:“語(yǔ)境本身是無(wú)限的:永遠(yuǎn)存在著引進(jìn)新的語(yǔ)境的可能性,因此我們惟一不能做的事就是設(shè)立界限。”[11]130語(yǔ)境所蘊(yùn)含的因素是變動(dòng)不居的,不能預(yù)先為它限定邊界,因而對(duì)經(jīng)典作品的詮釋存在著無(wú)限衍義的可能性。可見(jiàn),“文本意圖”說(shuō)的出發(fā)點(diǎn)是無(wú)可厚非的,試圖為共時(shí)的文學(xué)作品閱讀與研究確定一個(gè)意義方向,從而排除那些在共時(shí)狀態(tài)下對(duì)文本不合理的詮釋,但它畢竟不足以囊括文學(xué)闡釋活動(dòng)的多重決定因素,因而是一種難以實(shí)現(xiàn)的烏托邦。
綜上所述,關(guān)于文學(xué)意義闡釋標(biāo)準(zhǔn)問(wèn)題,赫施、艾布拉姆斯及艾柯對(duì)解構(gòu)主義誤讀理論的批判,分別從傳統(tǒng)作者和現(xiàn)代文本兩個(gè)角度展開(kāi),為誤讀理論有效性的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參照。然而,無(wú)論是作者還是文本的意圖,都不是文本意義的唯一決定因素,不能為文學(xué)闡釋提供標(biāo)準(zhǔn)化的意義模式,否則闡釋活動(dòng)又將走回封閉、單一的老路上去。實(shí)際上,由作者、文本、讀者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終產(chǎn)生了意義,這些因素都可以作為意義闡釋的標(biāo)尺,但不應(yīng)將任何一種固定化為永恒的、權(quán)威的標(biāo)準(zhǔn)。這些爭(zhēng)論,體現(xiàn)了解構(gòu)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與傳統(tǒng)闡釋學(xué)、現(xiàn)代文本理論的差異,然而卻很難說(shuō)最終解決了闡釋標(biāo)準(zhǔn)的問(wèn)題,這卻也正說(shuō)明解構(gòu)批評(píng)家主張“一切閱讀皆誤讀”、反對(duì)闡釋標(biāo)準(zhǔn)單一化具有現(xiàn)實(shí)的合理性。
誤讀,反映出人類面對(duì)語(yǔ)言的矛盾處境:一方面,語(yǔ)言是人類存在的家園、交流的媒介,人類必須依靠語(yǔ)言來(lái)相互交流、建立社會(huì)生活;另一方面,語(yǔ)言卻并不可靠,它所呈現(xiàn)的未必就是本原世界,因?yàn)榘凑战鈽?gòu)主義理論的思維原則,“真理”是被懸置的,永遠(yuǎn)不可能存在一個(gè)亙古不變的真理。因此,對(duì)“詩(shī)”的“思”需要無(wú)限進(jìn)行下去,對(duì)已有定論需要進(jìn)行不斷的反省,從而使文學(xué)藝術(shù)更顯生機(jī)與光彩。
[1]喬納森·卡勒.論解構(gòu)[M].陸揚(yáng)譯.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8.
[2]伊格爾頓.二十世紀(jì)西方文學(xué)理論[M].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7.
[3]Miller,J.Hillis.,F(xiàn)iction and repetition:seven English novel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4]米勒.1984[C]//.重申解構(gòu)主義.郭英劍等譯.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8.
[5]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píng)[M].張德興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6]赫施.解釋的有效性[M].王才勇譯.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1991.
[7]艾布拉姆斯.如何以文行事[C]//.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選集.趙毅衡,周勁松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8]米勒.作為寄主的批評(píng)家[C]//.重申解構(gòu)主義.郭英劍等譯.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8.
[9]艾柯.詮釋與歷史[C]//.詮釋與過(guò)度詮釋.王宇根譯.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2005.
[10]艾柯.過(guò)度詮釋文本[C]//.詮釋與過(guò)度詮釋.王宇根譯.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2005.
[11]卡勒.為“過(guò)度詮釋”一辯[C]//.詮釋與過(guò)度詮釋.王宇根譯.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2005.